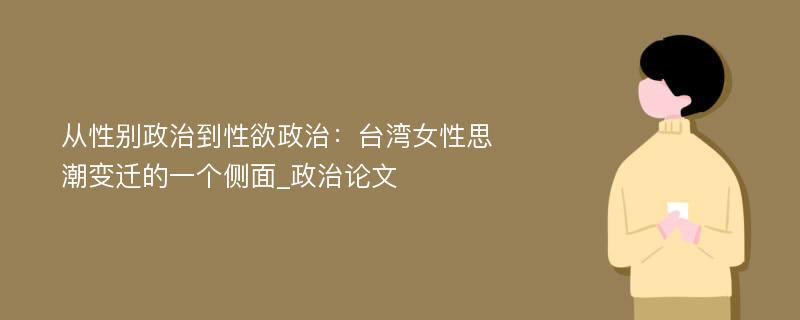
从性别政治到性欲政治——台湾女性思潮变迁的一个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台湾论文,思潮论文,性欲论文,侧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8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9)04-0097-08
一
台湾光复之前,台湾妇女运动与祖国大陆的妇运有着相同且相异的发展轨迹。相同之处是同处五四文化思潮震荡中,由传统而现代;不同的是,台湾又有着日据时代的特殊经验。日据时期,日本当局基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同化的考虑,鼓励台湾妇女废除缠足,认字读书;同时,许多离开台湾外出求学的青年,在新思潮的刺激下,也鼓吹女性解放,把它与台湾的民族解放结合起来。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来台之初,大陆迁台的一些女知识分子曾经一度活跃,并发表过一些女性解放的言论,但很快就在当局的监控中萎缩了。
20世纪70年代本土思潮兴起,在西方文化及商品化的压榨下本土女性的悲惨境遇得到凸显。然而,在大多数言论中,台湾女性的困境还是被归咎于美国大兵、日本奸商和台湾买办,台湾的男性和父权并无过错。
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文化和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在台湾社会长期持续地被内化成为一种社会规范,一种社会教化机制。这些不平等在家庭、教育、媒体和整个社会中存在,女性在两性交往中常常沦为泄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机器;受教育的程度和范围受到限制;在工作的范围和领域以及待遇上与男性也有非常大的差异。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社会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愈加凸显出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台湾“解严”之后,台湾的女性主义运动空前活跃。此前妇女团体主要的功能是维护政权稳定,扶助老幼,救济贫困,以及展开联谊活动;而此时期新成立的妇女新知基金会和晚晴协会等妇女团体,则有突出和明确的女性诉求,它们是女性知识分子发起的自发性的台湾妇女组织,具有广泛的基层参与性,并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团体。
20世纪80年代,台湾妇女运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争取性别政治中的参政权、财产权、教育权和工作权,90年代以后,台湾女性运动由“公领域”转入“私领域”,更多地关注女性身体和性的自主权。前一种诉求称为“性别政治”,而后一种关注与诉求称为“性欲政治”。“性欲政治”包括两个目标,一、拒做客体,也就是拒绝成为男性情欲的受害者;二、营建主体,致力开发女性欲望的主体性,情欲自主。下面我们分别阐释“性别政治”与“性欲政治”的发展和关联。
二
20世纪80年代,台湾女性关注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处境,积极争取法律上的女性权益,以争取消除法律和制度上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和不必要束缚。此时,在社会活动上她们主要关注和努力的方向是,唤醒女性意识和对女权问题的探讨,批判男权文化制度观念对女性情感的压抑,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与扼杀,积极促使体制改革;在文化领域,以文学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女性主义小说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开始繁盛起来,以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丰富的社会内涵,突入社会现实,呈现强烈的叛逆精神,批判男性中心的社会传统和社会秩序。
传统的性别秩序的建构逻辑,是从男性权威权力的角度出发,建构一种不平等的性别秩序。而“社会学和女性主义提出性别社会建构的意义,不只是强调这些差异的社会建构性质,也呈现因差异所造成的权利关系不平等。”① 上世纪70年代初,吕秀莲提出“新女性主义”,主张“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创立“拓荒者出版社”,批判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以演讲、发表文章、座谈会、出版书籍的形式,激发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对女性的关心,在台湾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也使更多人关注男女两性的不平等身份,掀起台湾妇女运动的第一波高潮。吕秀莲在20世纪70年代的言论对学院派女性产生极大影响,尤其是70年代留美的一批台湾女性学者受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这些女学者返台后,更切身体会到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她们都积极倡导女性意识的觉醒。
1982年,李元贞、顾燕翎等人创立了“妇女新知杂志社”。但是,从吕秀莲开始到“妇女新知”的创立时期,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整个社会文化处于单一状态,政府对于群众和集体的行为或社会活动较为敏感,女性运动和女性为争取自身权益的活动受到很大的压制。女性运动和集体活动的范围还较为狭窄,姿态也较为低调而具有政策应对的策略性。“妇女新知”创办人李元贞说:“在当时办活动吸引妇女时,都用很低的姿态,我都不讲女权,也不讲新女性运动。在吕秀莲被抓之后,整个社会就骂新女性杂交,所以我都用(激发)‘妇女的潜能和发展’等议题。”她们探讨各种号性别有关的议题,看女性主义电影,和其他团体联谊,或者是协助其他妇女社会团体的成立,活动规模都比较小。在“戒严”的政治态势下,“妇女新知”成为当时唯一的妇运机构,因此对所有妇女相关的议题可谓是全方位的关注,能够以杂志社的名义举办一些活动,同时从事与女性相关的研究。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无法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而且遭遇了威权社会的强烈指责和反击,参与和回应的女性也很有限,“妇女新知”的主要工作和核心议题是以论述制造和宣言的方式,唤起社会中一般人的性别意识。
而1987年政治上的“解严”,为女性运动和女性建构自我,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在前此有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台湾的女性主义运动空前活跃。此前妇女团体主要的功能是维护政权稳定,扶助老幼,救济贫困,以及展开联谊活动;而“解严”后“妇女新知”杂志社转成“妇女新知”基金会,并催生了台湾妇女救援会(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前身)。此后台湾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女学生自组团体“台大女研社”,台北励馨基金会和女性工会,以及现代妇女基金会、进步妇女联盟等妇女团体也相继成立。此一时期的妇女运动有了突出和明确的性别平等诉求,它们是女性知识分子发起的自发性的台湾妇女组织,具有广泛的基层参与性,并不依附于特定的政治团体。她们积极介入政治改革,不断以互相声援的方式和共同的议题提升可见度,对政党及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并推动法律的修改制定以保障妇女权益,在女性自觉与体制改造的策略下,营造出有利于妇运的政治气候。
“解严”后,台湾妇运团体不断掀起运动高潮,台湾妇女运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积极争取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中的参政权、财产权、教育权和工作权。在工作权方面,积极推动两性平等的工作机会,要求不论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等的差异,凡从事同样工作,都必须给予同样报酬。教育权方面,要求去除学校教育中的性别歧视,因为长期的性别差异造成女性受教育的限制,而女性在家庭、学校、社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又通过教育的不平等加深两性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并且代代相传。这种“‘性别刻板化’将限制个人的成长,也造成了性别歧视,同时影响个人的生活适应。”② 只有从教育上打破刻板的传统性别意识,才能真正树立平等观念。财产权方面,要求保障妇女婚后财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参政权要求妇女保障名额的废除,因为性别关系的界定无论从经济活动或政治参与的表现方式来观察,都在说明某种性别权力的分配差异。而妇女参政议题的凸显,积极介入政治改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在公共领域的体现。1987年8月6日“妇女新知”“反对夫妻合并课税”;1987年8月31日,高市文化中心代表、国父纪念馆代表、主导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请愿成立“男女雇用均等法案小组”;1988年“妇女新知”和妇女救援基金会联合发起救援雏妓华西街千人游行,提倡两性平等教育,并评析中小学教科书的性别刻板印象;1987—1990年,“妇女新知”制定男女平等工作权法草案。相应地,在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通过的国民党政纲中,对于妇女的福利问题就有所改变和关注,贯彻男女平等原则里这样解释:依据“宪法”所定男女平等原则全面检讨修正相关法规,确实保障妇女权益,经由家庭、学校及社会教育,建立两性平等的价值观,匡正社会观念,消除性别偏见,尊重妇女独立人格,促进妇女地位的实质平等。同时还有扩大妇女发展机会、加强妇女福利服务、保护受害妇女、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等条款的修订。
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妇运活动范围基本都在争取公领域内男性政权规范之下的性别平等,并没有挑战更深层的性别机制,甚至有去性化的倾向,并未真正深入女性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处境,对于女性的情欲和私密空间讨论较少,多着眼于抽象的社会公平,或在男性社会的正义原则下寻求支持,将过去一向被视为压抑的女性权益提升为公共政治论述,进而落实为公共政策。女性从突破社会体制的限制和束缚,诉求在法律上的保障,这一改观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从唤醒性别意识到各个妇女团体联合起来请愿再到法律条文的更改,其间经过了一个特殊的政治“解严”。但在文化领域,女性的参与相对自由,无论是创办刊物还是发表论文、文学作品,这些软性的力量总是更能激起女性潜在的意识和对自身处境的关照,唤醒女性意识和社会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在台湾经验中,出身于文学系(院)的女性主义——不论在人、议题、行动和理论上——一直是妇运界的主力(流)”,③ 而“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话语中的渗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性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④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创作的关注点依然是性别政治中女性处境的议题,以文学来反映女性的生存状态,从家庭、婚恋角度剖析社会传统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性别期待的不合理。廖辉英以《油麻菜籽》 (1982)深刻揭示台湾女性的命运、社会地位和婚姻问题;李昂从处女作《花季》(1968)到《有曲线的娃娃》(1970)、《人间世》(1977)等作品,大胆书写女性的情欲和女性的自我意识,以时代的叛逆者的姿态,站在女性立场批判社会对女性情欲的荒谬限制和压抑;《杀夫》(1983)从性角度批判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中,女性所遭受的性禁锢、性无知和性虐待,而最终以“杀夫”来颠覆男性的中心地位;《暗夜》(1985)则直接抨击男权制度下腐朽堕落的金钱交易和性交易;吕秀莲有《新女性主义》和《贞节牌坊》、《这三个女子》等作品,萧飒《小镇医生的爱情》(1984)、袁琼琼的《自己的天空》(1980)、苏伟贞的《红颜已老》(1980)和《世间女子》(1983)、朱秀娟的《女强人》(1984)等小说集中出现,展现女性对自我以及两性关系的思考,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呼应妇女运动。正如梅家玲所言:“小说中性别意识的体现,向来与文学传统、社会现况及政治大环境息息相关;如何以性别研究的视角,去解读小说,想象文学世界,更是多重文化机制交错互动下的政治实践。”⑤
三
20世纪90年代,性别平等的诉求已经撼动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但是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现有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对女性的性与身体的不平等或不必要束缚,却依然存在,而且作为长久以来的社会禁忌,性的相关知识和论述非常稀少,只是作为负面警语的形式流通。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台湾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开放,台湾女权运动再掀高潮,妇女运动组织力量更为壮大,女性所关注的议题也从要求身份重塑的性别政治转换到自我的私人生活领域,性、性欲问题开始成为她们关注的焦点。性研究室、性工作坊在学院或者社会中不断成立,而主持者多是活跃在社会潮流中的激进女权活动家们。女性的性和性爱问题成为一个公共性的私人问题,她们拒绝传统的女性形象,在两性平等基础上为女性重新定位,以大胆前卫的姿态,在对欲望的关注和释放中寻求自我、建构自我。这一时期的文化领域也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中女性的欲望书写也是焦点,通过女性个体的私密事件和情欲问题,关注的却是性/性别/情欲与政治、历史、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性/身体欲望推进到文化建构等层面,文化不是欲望的颠覆者,而是欲望的叙述者。⑥ 这种叙述的主动权是和整个社会相关联的,也是女性在经过了长期的压抑和束缚之后,在集体努力挣扎之后所获得的。
性欲政治强调的是性、情欲和身体等相关议题。按叔本华的理解,性欲是生存意志的核心,是一切欲望的焦点。性欲和其他欲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就动机而言,它最强烈;就表达形式而言,它的力量最勇猛。欲望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性爱欲望是女性欲求经验中最基本最深刻最具悠久现实的一种。艾云指出,“如果说男人是以肉身的残破做了精神的传送地;那么女人,则以丰美充盈的身体,在微醺的醉意和快感中,找到穿越秘密的通穴。”⑦ 女性往往在性的渴求和体验中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身体,并且透彻地认识到自我作为完整的女性而存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女性的“性欲政治”包括两个目标,第一拒做客体,也就是拒绝成为男性情欲的受害者;第二营建主体,致力开发女性欲望的主体性,情欲自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台湾女性以更激进的手段追求体制的改造,以多变化的策略吸引媒体及大众注意,同时也更大胆地探索女人心理、身体、文化的无限可能。1994年5月25日,针对台湾师范大学一女生抗议某教授对她施行强暴事件和台湾中正大学的性骚扰丑闻,台湾众多妇女团体联合举行反性骚扰大游行。在游行中,台湾“中央大学”教授何春蕤教授提出了一句简明有力的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这个口号成为当时的舆论热点,以后更成为台湾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语。这句话将女性主义从经济自主、婚姻自主的层次,推向“身体自主”的层次。而且此次大规模游行,在台湾首次没有借助任何政治或社运团体,纯粹以女性议题为诉求。也是在1994年,当妇运蓄积了足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影响力,将性骚扰、性侵犯等过去被视为个人的、隐私的问题推入公共政治论述,当成社会问题来谋求解决时,其它更为隐晦的议题,如女人的情欲,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女性论述空间,而不再由男性医师或性学专家垄断。⑧
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除了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带动情欲文化松绑之外,围绕着情欲的攻防战主要沿着媒体上的情欲图像开展。⑨ 1995年初,《法国性文学大系》以学者主编法国文学经典之正当形象出版,没有多久便遭查禁,在当时女性情欲解放运动的风潮中还引发了言论检查的争议。1995年5月,台湾大学的学生社团女研社举办“A片影展”,并为此活动发新闻稿。女研社的主办者称,这项活动的目的之一是建立女生情欲对话的空间,另外也具有挑战学校管理部门的意味。因为,校方对学生宿舍的管理有双重标准——对女生对女生宿舍严加看管,对男生宿舍都是放任的(包括允许每天晚上放A片)。针对此举,各式各样劝阻到声嘶力竭的声讨,包括各种污秽的匿名信,往女生宿舍打去的肮脏电话,铺天盖地而来。在公众心目中,对于台湾男性青年,看A片是一种成人礼,而女生应该纯洁无邪,在性方面属于被动的无知的一方,在学校女生宿舍放映A片,当然不见容于社会。宿舍被视为家庭的延伸,是父权制的家长把监控权移交给学校,女生不得放任自流。由于媒体报导所带来的学校压力和舆论压力,女研社最后只得将此活动的名称与定位做了修正,从强调女性情欲对话的“A片影展”,变为具有学术讨论意味的“A片批判大会”。而在A片批判大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张小虹教授等女性学者提出了新主张:“不要贞节牌坊,也不要性解放,而是要身体自主权。”
1996年妇女节前夕,台湾18个妇女团体组成“女人100行动联盟”,召集数百名成员上街游行,并提出一百多项诉求。游行队伍抬着巨型的卫生棉模型,行经“台湾总统府”时抛掷了数百个卫生棉,护卫“总统府”的警察纷纷躲避。戏剧性的场面引来大批媒体的报道。无疑,这样的游行和动作具有关切女性自身的重大意义,台湾首次大选中,四组候选人对妇女议题的冷漠态度,惹出女性的强烈抗议;突破公共空间中对月经的禁忌,展示了对女性身体的关爱。同年的彭婉如事件,亦如一枚炸弹,引起女性的愤慨。事件发生后,台湾妇女团体在短短一天内,迅速动员组成“妇女连线”,召开记者会,同时发起夜间大游行,聚集在台湾“行政院”门前,抗议台湾当局召开的“治安会议”在内容和议程上漠视妇女人身安全。在妇女运动与媒体的压力下,台湾“立法院”迅速通过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规定台湾“内政部”应该设立“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各县市地方政府设立“性侵害防治中心”,中小学每年应该有4小时以上的“性侵害防治教育”。
卡维波早在1994年就断言,一场性革命正在台湾社会发生,它将在数年内改变台湾的性文化,由保守变成性开放。新的求偶文化及两性关系将重组我们的社会,性活动和性商品多样化公开化,性感四溢的身体与逐渐开放的性言论成了广受注目的社会新现象。⑩ 经过1991年“女人影展”、1992年三八节“我爱女人园游会”、1994年4月成立女书店、1995年“大学女生看A片事件”、1997年“台北市废除公娼事件”,女性对自身的关注更为自觉,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个人的存在和情欲成为核心。“身体自主权”、“性自主”、“情欲自主”或“性主体性”这些哲学概念变得特别显而易见,也经常被许多论者所引用,而女性运动所要诉求的“性欲政治”的两个目标,虽然在社会中引起很大争议,但也从更多层面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自己身体和情欲的认知,并且在法律层面上取得一定成果。
20世纪90年代末期,性/别解放运动所形成的影响和效应越来越清楚浮现,两性平等教育在台湾的政策化,各种性/别解放运动都发展出更为具体的组织和人权诉求。(11) 1996年通过“性侵害防治法”,1998年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2001年通过“两性工作平等法”。
在文化领域,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也在何春蕤、李元贞等“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同于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建构,情欲文风膨胀,大量涉足女性情欲的议题,彰显了女性的生命主体和欲望世界。1994年何春蕤的《豪爽女人》,炒热了女人的情欲论述,女人的性事被搬上台面,而她在《女性主义的性解放》中以“性压抑的身体情欲逻辑、贫瘠的情欲文化”为论点,批判女性长期被压抑的身体欲望,鼓舞女性“情欲自主”。(12) 李元贞的三部“私语”——《爱情私语》(1992)、《青涩私语》(1993)、《婚姻私语》(1994),苏伟贞的《沉默之岛》(1994),朱天文的《荒人手记》(1994)对身体欲望的展示与探索更加坦然,邱妙津的《鳄鱼手记》(1994)、《蒙马特遗书》(1999)等,陈雪的《恶女书》(1995)、《梦游1994》(1996)、《恶魔的女儿》(1999),洪凌的《异端吸血鬼系列传》(1995)等都以书写女同性恋的爱欲活动为主。20世纪90年代的酷儿写作,大胆凸显了私密空间的性欲,重新阐释了传统定位的“性别”问题。平路的《行道天涯》、李昂的《自传的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等对女性欲望以及欲望与政治、历史、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便成为此一时期女性书写的普遍状态。王德威在《性,丑闻,与美学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说》一文中,从小说的“性”、“道德”与“政治论述”的主题入手,指出在李昂笔下,性与政治话题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互相指涉的对象。(13) 张小虹的《欲望新地图:性别·同志学》则在理论架构上,以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和同志理论为基础,以性别与性欲取向为切入点,从政治、文化、美学的角度探讨了认同与欲望的问题。(14) 台湾女作家们的欲望书写已经成为思考、阐释、解构台湾社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各个层面议题的符码,在解构男性权威话语的同时,建构起女性自身的话语体系。
四
大体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女性的性别政治,到90年代后女性对个人情欲的关注,以及通过个人情欲诉求政治体制的改变,可以窥测到整个社会思潮20年来的脉动。从性别政治到性欲政治,是台湾女性社会运动诉求的一个大致方向,其间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叠合交织。林芳玫就认为废公娼争议是过去数年中,台湾妇运内部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和性欲政治(sexual politics)两者紧张冲突在蓄积多年后的爆发。(15) 但无论是性别政治还是性欲政治的诉求,其最终目的是要解除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追求女性的自主,追求真正的两性平等。
以社会学的视角看,性别差异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所致。而这些又关涉着整个社会长久的文化体制,以及法律、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种制度建构。因此上世纪90年代之前,女性在公共领域积极争取的性别平等,必然触动社会体制和法律制度层面的改观,社会性别和性别角色的定位发生的变化也必然牵动社会文化和话语的变迁。这种已然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对私人领域的关注以及更为激烈的社会运动做了酝酿和铺垫。女性所关注的议题也从要求身份重塑的性别政治转换到自我的私人生活领域的性欲政治,女性开始对自身身体、欲望重新审视定义、对社会文化另行解释,以在“性”的两性平等和解放上诉求平等和建构自我。因为性是两性关系的连接点,女性所受的压迫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性事而来,透过性事的中介,或者深植于性事之内。女性的性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因此性主动的女人也被迫付出昂贵代价。(16) 表面上看,属于个人的、内省的行为,不致引起政治冲突,也不属运动形态,然而经由集体认同而可能激发的政治需求,以及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却具有重塑女人以及妇运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巨大潜力,也是女性企图从私密空间出发在更广泛领域建构自我的努力。
从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台湾女性关注的性欲政治,是以上文所述的拒做客体和营建主体为核心,从最根本来看是为了取得女性在私人领域的完全自主,但在具体的现实以及操作中却有着很大的争议。西方各个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流派在台湾本土化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性欲/身体的看法自然有所不同。以何春蕤为代表的“激进女性主义”,是否过分突出了女性的性解放/性主动/性多元一直也是争论不休的话题。过于强调身体的欲望,为性而性,抽离社会、情感、精神层面等人性的脉络,否定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豪爽女人的性解放是否有被架空的危险,(17) 同样也引起邱贵芬、朱元鸿、傅大为和郭力昕等文化人的质疑和思考。过激的行为和言论,在没有出现新的道德规范情形下,必然造成一些疑虑和关于情欲泛滥的担忧。
从另一个角度看,“次文化在上升并精致化的过程中,往往骚动着一些让人惊异的创作力和想象空间。”(18) 中华传统文化中虽有“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之说,承认人们对性的基本需求,却对性始终采取忽视的态度和制度性的压抑,(19) 尤其是传统伦理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在这种状况下,长期处于父权文化体制下的女性,所受的是从性别到性欲的束缚。要打破这种长期潜存于人的意识层面的性欲理念,台湾女性主义者和妇女运动采取较为激进的方式,不失为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呼唤得越激烈,自然越能激起大众的反响,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性欲政治为核心的运动也的确取得了很大成果。台湾女性在“性解放”和追求身体欲望的释放过程中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自我,解放了自我。同时,性解放的议题是对传统性观念的有力反拨,弥补了长久以来性问题上的盲点,扩展了台湾社会文化思考的范围,也为中国女性思潮的顺利前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可贵资料。
注释:
① 王振寰编:《台湾社会》,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212页。
② 黄囇莉主编:《跳脱性别框框》,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初版,第37页。
③ 王雅各:《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史》,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9年,第5页。
④ 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⑤ 梅家玲:《性别论述与战后台湾小说发展》,见梅家玲编:《性别论述与台湾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⑥ 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⑦ 艾云:《用身体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⑧ 顾燕翎、梁双莲:《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观察》,见刘毓秀编:《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年》,台北:女性学学会/时报出版社,第93—144页。
⑨ 何春蕤:《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中外文学》,1996年4月,第6—37页。
⑩ 卡维波:《一场性革命正在发生》,何春蕤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元尊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348—367页。(最初发表于1994年救国团主办的“婚姻制度与两性角色探讨会”)
(11) 何春蕤:《台湾性革命、性权、性学的历史互动》,《华人性研究》,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会刊创刊号,2008年1月,第28—34页。
(12) 何春蕤:《女性主义的性解放》,《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元尊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第11—30页。
(13) 王德威:《性,丑闻,与美学政治——李昂的情欲小说》,见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戴贞操带的魔鬼系列》,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9—2页。
(14) 张小虹:《欲望新地图:性别·同志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
(15) 林芳玫:《当代台湾妇运的认同政治:以公娼存废争议为例》,《中外文学》,第27卷第1期,1998年6月,第56—87页。
(16) 盖儿·鲁冰著,张娟芬译:《性的杂想:性欲政治的基进理论》,见顾燕翎、郑至慧主编:《女性主义经典》,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271页。
(17) 参见林芳玫:《美丽“性”世界?》,见何春蕤主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元尊文化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第45页。
(18) 王荣文:《出版缘起》,见何春蕤主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元尊文化有限公司,1997年,第3页。
(19) 顾燕翎:《当代台湾妇运的情欲论述》,见顾燕翎、郑至慧主编:《女性主义经典》,台北: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2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