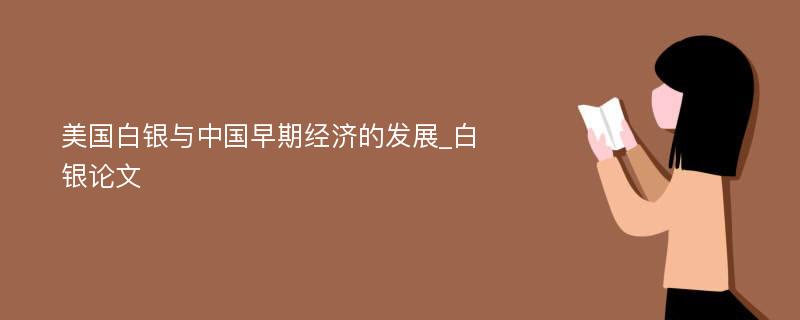
美洲白银与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洲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5)02-0017-09
白银生产是西属美洲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其对美洲本身的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关注比较多的是银矿生产的技术、成本、利润、发展趋势和白银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至于白银生产对美洲当地的影响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则很少受到关注。原因似乎很明显,一是获得白银的矿主们在新大陆的投资机会很少,留在美洲的白银寥寥无几;二是欧洲统治者试图尽可能地控制这些财富,大量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但近年来,白银流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包括理论经济学家和全球史学家的更加广泛的注意,他们明显地改变了研究的方向和辩论的内容,把来自新大陆的白银更多地置于亚洲经济之中,旧的官方统计资料不再被相信,整个美洲的白银流出量被重新修正,其数量远远高于原来的估计,白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被提到新的高度加以评价。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介绍得出一点倾向性的看法。
一、殖民地时期美洲生产了多少白银?
众所周知,哥伦布航行美洲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寻找黄金而不是白银,“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求的第一件东西”。[1](p.450)西班牙美洲的黄金生产在1550年前一二年达到最高水平。根据皮埃尔·肖努的统计,第一个周期运往西班牙的黄金约为25-30吨,1540年前墨西哥生产了20吨,而在这一周期结束前,秘鲁的产量可能与之相仿。[2](p.347)从寻求黄金到白银的转换,是从16世纪40年代以后开始的。秘鲁的著名银矿波托西是从1545年开始开采的,新西班牙的萨卡特卡斯和瓜纳华托则分别在1548年和1558年开始开采,产量在16世纪逐渐增加,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属美洲白银输出总量的65%左右。1581-1600年仅是波多西银矿就每年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墨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墨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美国历史学家彼德·贝克韦尔是研究美洲白银生产的专家,他在《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二卷)写的“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美洲采矿业”一章中,用曲线图勾画出了整个殖民地时期美洲白银生产的长期趋势,认为美洲白银生产在经历了16世纪的繁荣之后,17世纪一度出现萧条,18世纪又再度复兴。他引用于C·H·哈林对1560年前美洲金银产量的估算,即139,720,850比索(注:比索是货币单位,即西班牙银元,约合中国库平七钱二分;1比索等于272马拉维迪或8个雷阿尔,10个雷阿尔为1皮亚斯特。),和阿尔瓦罗·哈拉对1531--1600年美洲白银产量的估算,即79,476百万马拉维迪,[3](pp.142-155)但他自己并没有对整个殖民地时期美洲白银总产量作出一个完整的估算。秘鲁银矿于1680年开始萧条,新西班牙的白银在进入18世纪以后却产量日增,到19世纪初达到顶峰,白银产量已占美洲总产量的67.5%。根据当时西班牙王室的命令,所有产出的白银必须运到造币厂铸造银币。墨西哥经济史学家迭戈·洛佩斯·罗萨多对1536-1821年间新西班牙的铸币生产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的结论是该时期新西班牙铸造了总价值为2151,581,961比索的货币,其中白银是2082,260,657比索;黄金是68,778,411比索,铜是543,893比索。[4](p.27)但这仍不是整个美洲产量的数字,沃德·巴特雷在《1450-1800年世界银块流动》一文中做出了一个总的估算,[5](pp.224-254)认为美洲白银产出在16世纪约为17000吨,17世纪约为42000吨,到18世纪约为74000吨,总计约为13.3万吨。这一数字与我国学者樊亢、宋则行先生曾用过的数字相接近,他们在其主编的《外国经济史》中写到:(西属)美洲年均金银出口额,1500-1545年为300万皮亚斯特,1545-1600年为1100万皮亚斯特,1600-1700为1600万皮亚斯特,1700-1750为2250万皮亚斯特,1750-1803年为3530万皮亚斯特,300年间增长了11倍。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从美洲殖民地榨取了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即10万吨)白银。[6](p.258)这10万吨白银不包括留在美洲本地使用的白银。理查德·加纳(Gar-ner)研究的结果是,从16世纪中期到殖民地时期结束,西属殖民地生产了大约29亿至31亿比索或10万至11万多吨的白银。[7](pp.898-900)如果将黄金(包括巴西出产的黄金)和白银通算的话,他认为,从1492年到1820年的贵金属产量肯定超过了40亿比索,即14万多吨,[8]这是一个估计更高的数字。
二、美洲白银流向何方?
最早关注美洲白银去向的经济学家大概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写到:“自美洲发现以来,一直到现今,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第三,东印度为美洲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这些矿山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从这时起,依赖阿卡普尔科船舶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贸易增加得尤其多。”[9](pp.195-197)但这三地的白银究竟各是多少,斯密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除了美洲本地市场外,其他两地的市场都与中国紧密相连。
首先是通过阿卡普尔科与东方直接贸易流出的白银。
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4月27日,西班牙舰队抵达菲律宾的宿务岛,从而在南洋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1571年时又攻占了马尼拉,三年后开始了在该地的正式殖民统治。贸易史从此开始了西班牙人以菲律宾为基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时期。
关于明代流入中国白银的估计,据英国学者W·S·阿特韦尔研究,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中西贸易增长迅速,仅从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数看,1570-1600年从不到40人增加到15000人。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的通商大部分是非法经营的,很难确切地说出究竟有多少白银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在1602年新西班牙当局给马德里的一个报告中提到,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总计有500万比索,1597年高达1200万比索。1632年(初期的贸易高峰已过)马尼拉的基督教会向西班牙国王菲力普四世通报,每年从阿卡普尔科运来的白银达240万比索。有人对当时马尼拉的商业活动描写到,“中国皇帝能够用从秘鲁运来的银条建一座宫殿,这些白银的运出都没有登记,也未向西班牙国王缴税。”[10]
梁方仲先生是国内较早撰写这方面专题论文的学者,他在1939年写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写到,“自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银及银货,数量究有若干,中国册籍中甚缺乏此项记载。至外国册籍,虽间有一二记载,然亦仅能推知其大约,详数则无从查考。”据他估计,从1573年至1644年的71年间,应有21,300,000比索(约合766.8吨)从马尼拉流入中国,加上葡萄牙人从澳门输入的白银,应为25,500,000比索,如果再加上从日本输入的白银,总数应该在1.4亿比索以上(约合5040吨)。[11](pp.132-179)这一估计相对保守一些。
王裕巽先生通过对国内外史料的分析,认为明代中国从马尼拉贸易中得到的白银为87,750,000两,即11700万比索(约合4212吨)[12]
万明先生认为,据索萨对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运到菲律宾的数额,即在1590-1602年约为2010吨,1603-1636年约2400吨,1637-1644年约210吨,总共达到4620吨。而阿特韦尔则指出,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每年125吨,在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更高达300吨。以此来说,索萨的估计实际上还显得低了。而事实上,索萨的估算还应该上推20年,也就是自1571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的时候开始计算。稍此之前(1563年)波托西等地银矿采用水银分离纯银的方法,开始进入产量激增的时期。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开通后,以平均每年150吨来计算,这20年共运输了3000吨白银。考虑到运至马尼拉的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了中国,因此,综合起来,1570-1644年通过马尼拉一线输入中国的白银约7620吨。[13]这一估计数额是相对较高的。
据格兰(Richard Von Glahn)估计,1550-1650年约有2304吨白银通过菲律宾进入了中国,其中中国船运送了1204吨;葡萄牙船运送了75吨;走私船运送了1030吨。[14](p.140)
再据斯卢伊特尔(sluiter)的研究,1576-1564年西班牙殖民地注册白银为824,100,000比索,向海外出口为680,900,000比索,其中的624,700,000比索(91.7%)运送到了西班牙(和欧洲),56,200,000比索(8.3%,约合2023.2吨)经过阿卡普尔科运到了马尼拉。[15](p.8)
就整个美洲殖民地时期通过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而言,庄国土先生在《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估算》一文中指出,明季(1567-1643)从菲岛输入中国的白银约为7500万比索。而在1700-1840年间从菲岛输入中国的白银为9360万两左右。[16]按每两为1.33比索算,后者为12448.8万比索,与前者相加共为19948.8万比索,可见,从明季到19世纪初自菲岛输入中国的白银应不少于2亿比索。
严中平先生在他的文章引用了普什尔写的《东南亚的华侨》中的数字,即在1565-1820年间,墨西哥向马尼拉输送了4亿比索的白银,其中绝大部分输入了中国。[17]
在沙丁、杨典求诸先生编写的《中国和拉丁美洲简史》中,作者引用了埃梅斯(Eames)推算的数字,“自1571年—1821年间,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共达4亿比索之多,这些白银主要用来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然后运往拉美出售,所以大部分白银流往中国。”但该数字并没有表明究竟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作者继续写到:根据史料记载,中拉早期贸易初期,每年经菲岛输入中国的拉美白银为几十万比索,到16世纪末叶已经超过100万比索,17世纪增加到200多万比索,18世纪则可达300-400万比索,到19世纪则下降到150万比索。在整个中拉早期贸易期间,输入中国的拉美白银总数可达2亿比索。[18](pp.70-71)
全汉升先生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比较有深度,并为许多外国学者所引用。据他研究,从1565-1815年,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1-4艘(通常以两艘为多)的大帆船,来往于阿卡普尔科与马尼拉之间,每年由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之间不等,但以200-300万比索为多。他根据马尼拉检审庭庭长向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提到,“菲律宾群岛被征服(1565年)以来,运到这里的白银已经超过2亿比索”,推定从1565-1765年间,从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共计2亿比索。又据德科明(De Comyn)计算,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比索,其中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流入中国,他认为德科明四分之一的估计显然太低,比较接近事实的可能是二分之一或更多一些。[19](pp.435-446)
从上述学者的估算看,整个殖民地时期通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约为2亿比索,那么按每比索为36克计算,总计约为7200吨。
其次,流往欧洲再转输到中国的白银
输往欧洲的白银通过两条渠道最终又到达了中国。一是西班牙金银船队每年载银从墨西哥和巴拿马地峡到西班牙的商业中心塞维利亚,再非法运到葡萄牙,与从秘鲁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走私到里斯本的白银一起装上大帆船,绕好望角运到果阿,它们在果阿卸掉欧洲货,再补充些通过地中海和中东贸易区渗透到印度的白银,经过马六甲运到澳门。葡萄牙人用白银为日本、印度、中东及西欧市场购买中国货。葡萄牙船此时每年从果阿运到澳门的白银约在6000至30000公斤不等;二是西班牙金银船队运到塞维利亚的一部分白银被转运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然后通过荷、英与中国的贸易而进入了中国。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部分白银运到东南亚以购买胡椒、香料,更重要的是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昂贵物品。尽管这部分白银数量当时比较小,但仍受到早已成为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经济力量强大的中国商人的重视。荷兰和英国人都没有足够的易货商品来换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中国人销售货物只收白银,“他们不喜欢金子,也不喜欢任何其他一种货物”。
万明先生认为,1570-1644年美洲通过欧洲转手运到东方的白银大约有8000吨,除去流入印度和奥斯曼外,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国,估计约有5000吨。[13]
厄尔·汉米尔顿是较早对美洲白银进行专题研究的西方学者中之一,他的著作经常被后来的学者引用,他估计,在1500-1650年这一个半世纪里,从美洲运到欧洲的白银约为1.6万吨。[20](p.42)而根据沃德·巴雷特统计,1493-1600年世界白银产量是2.3万吨,美洲产量就达1.7万吨,占全部世界银产量的74%,美洲白银大约70%输入了欧洲。他还认为,在17世纪所生产的约42000吨美洲白银中有31000吨运抵欧洲,欧洲又将40%约12000吨以上的白银运到亚洲,其中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分别直接运送了4000-5000吨。另外还有6000吨运往波罗的海地区,有5000吨输送到黎凡特地区,这两个地区将其中一部分留在当地,其余部分继续向东输出到亚洲。在18世纪约74000吨的美洲白银中有52000吨运往欧洲。总的估算,在从1545年到1800年美洲出产的13.3万吨白银中,大约75%,即10万吨输出到欧洲,而欧洲输入的白银有32%,即3.2万吨输到了亚洲。[21](pp.202-203)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供了一张1500-1800年期间世界白银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图表。这张图表对美洲白银的去向给出一个清晰的表述,它表明16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1.7万吨白银,欧洲没有向中国输送任何白银,日本向中国输送2000吨白银。到17世纪,有2.7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其中的1.3万吨(约占一半)被运往中国,日本向中国输送了7000吨白银。到了18世纪,美洲向欧洲输送了5.4万吨白银,其中有2.6万吨(仍然是大约一半)转运到中国,日本则没有向中国输送白银。另外,还有美洲白银经马尼拉运往中国的传说,之所以说它是一个传说,是因为弗兰克不能肯定究竟有多少白银运往马尼拉,然后又有多少运往中国。他告诉我们,在1600-1800年期间总数约在3000吨到1万吨上升至2.5万吨。从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得知,在1500-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收到9.8万吨白银,其中3.9万吨运往中国,5.9万吨留在欧洲。中国除从欧洲收到3.9万吨外,还从日本收到9000吨,又从美洲经马尼拉收到3000至2.5万吨,总计5.1万至7.7万吨白银。这个数目和留在欧洲的5.9万吨相差无几。[21](p.209)
再次,留在美洲本地的白银。
根据斯卢伊特尔(sluiter)的研究,在第一个白银生产高峰1576-1645年,秘鲁生产了521,900,000比索白银,其中80%出口,20%留在了当地。同期,墨西哥生产白银302,800,000比索,出口87%,留在当地为13%,就整个西属殖民地看,白银出口占总产量的约82.6%,留在当地约为17.4%。[15](pp.8-11)但是,整个殖民地时期留在美洲的白银有多少呢?弗兰克援引巴雷特的估计,从1545-1800年,在美洲出产的13.3万吨白银中,约3.3万吨留存在了美洲(24.8%),[21](p.203)但这个数字没有排除经太平洋运往亚洲的白银,考虑到这一点,留在美洲的白银应该不会超过总产量的20%。
由于白银贸易涉及面宽广,规模巨大,文献数据零散,何况当时走私严重是世界性问题,更增加了估算的整体难度。所以,实际上很难确切地估算出总额。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作出的估算,证明了占美洲产量近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数量极为庞大。因此,中国被形容为一个白银的“吸泵”和终极“秘窖”。
三、白银流动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推动了白银的世界性流动?大致有三种观点对此作出了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贸易平衡说。这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观点,为传统的教科书所采用,它告诉我们,欧洲对亚洲的一些出口产品,包括香料、瓷器、丝绸、棉布、茶叶等有着强烈的需求,而相比之下,由于亚洲消费者购买欧洲产品的偏好低,所以亚洲对欧洲产品的进口是微不足道的,欧洲于是就通过向亚洲出口作为“平衡项目”的贵金属来弥补它们长期的国际收支赤字。
我国学者严中平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将西班牙殖民地时期中西贸易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无论是西班牙本土还是西属美洲和菲律宾,其生产力水平都拿不出任何商品值得为中国人所欢迎。因此,菲律宾强盗唯一平衡贸易的办法就是向中国输送白银。简单地说,马尼拉对中国和美洲的三角贸易关系,就是以美洲白银交换中国货物的关系,而中国货物中,丝绸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这种贸易被简称为“丝银贸易”。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一文中也写到:“整个复杂的纳贡贸易结构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纳贡贸易区组成了一个统一‘白银’区,即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21](pp.165-166)
第二种观点是套利说。这一观点由来已久,但近年来被弗林和吉拉尔德斯进一步强化。
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注:弗林(Dennis O.Flynn)是美国太平洋大学经济系的教授,早在1986年就发表了题为:“白银的微观经济学和早期现代时期的东西方贸易”的论文,1995年与太平洋大学现代语言和文学系的教授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aldez,拥有语言学和历史学双博士学位)合作发表了“伴随白银繁荣诞生:世界贸易在1571年的兴起”的论文,之后,两人合作发表了一些列关于美洲白银和世界经济体系论著,他们的文章重新强调了新大陆与远东之间的贸易往来,他们比弗兰克更早地注意到了美洲白银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平衡贸易的观点提出疑问[22],认为这种对东西方货币关系的传统的贸易赤字解释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只有白银(而不是抽象的货币)不断地通过欧洲流向了东方,而黄金(一种重要的货币实体)却不断地从中国流向欧洲(以及日本和美洲),还有,大量的铜(另一种货币实体)在后来的17世纪也从日本运往欧洲。印度洋的子安贝壳被运送到了亚洲大陆,以及经过欧洲运到了非洲市场。世界上出产贝壳货币的马尔代夫群岛却进口白银作为它们的本位货币。问题的焦点是,如果像传统所说的欧洲贸易赤字导致欧洲货币流向东方的话,那么各种欧洲货币实体也应该先后被抽取到亚洲,但历史记载却与这种理论相佐。在16世纪至18世纪期间,世界上的4种主要货币实体(白银、黄金、铜、贝壳)从未前后相继地流向任何地方,相反,每种世界货币实体都是独立地流向在特定时期能提供最大预期利润的地区市场。因此,用统一的“货币”标签将各类货币实体都放在一起来分析问题就排除了对这些货币实体生产和分配模式的理解。所以,为了获得关于各类货币实体运动的理论和历史事实的一致性,应该将各类货币实体分开来分析。他们提出了套汇交易理论来取代传统的理论。所谓套汇交易就是在甲地廉价购买一种货币然后到乙地高价出售以获取汇率差价。
早在1609年,一位拥有25年在亚洲经商历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罗·德·芭萨就注意到:“通常1个金比索可以兑换5个或5个半银比索,如果中国白银发生短缺的话,从外地购买白银,价格就上升到1:6或6.5银比索。我所见到的最贵的和在广州城购买的黄金是7个银比索兑换1个金比索,我从没有看见比这个价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个金比索通常值12个银比索,因此,显而易见从中国购买黄金意味着可以产生75%至80%的利润。”[23](p.461)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价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尔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买卖为媒介。”[9](pp.198-199)
据弗林和吉拉尔德斯研究,美洲殖民地时期曾发生过两个套利周期,第一阶段是1540年代至1640年代的波多西周期。由于15世纪中期中国明朝纸币体系的完全崩溃导致了银币的替代和白银税收体系的建立,而当时的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和比伦敦和巴黎大许多倍的城市,其“白银化”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反响。正是中国的需求压力引起了中国的白银价值两倍于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悬殊的差价反过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与银比价是1:6,而欧洲为1:12,波斯为1:10,印度为1:8。到16世纪末,广东的金与银比价为1:5.5或1:7,而西班牙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白银的价格是西班牙的两倍。”同期在日本二者之比为1:10,在莫卧儿的印度为1:9。有不少档案文献表明当时的商人意识到中国的白银价格大大高于世界其他的地方。直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白银价格才最后降低到与其他地方的价格大致均衡的程度。在17世纪的后半期是一个世界白银价格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仍有比较少量的白银继续流入中国,这是鉴于非套利的考虑。
第二阶段是1700-1750年的墨西哥白银周期。18世纪,由于美洲新作物的引进,促使中国的耕种面积扩大了1/2,人口增长了3倍,这时中国经济已经“白银化”,这样的人口爆炸也就意味着中国对白银需求的巨大增加,由此致使中国白银价格比世界其他地方高出50%。在18世纪前半期中国的金银比价保持在1:10-11,而欧洲为1:15。中国高出欧洲50%的利差导致了18世纪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繁荣,世界各地的白银再次争先恐后地大量地输入中国。虽然18世纪的利差明显小于上一个白银周期,但由于输入的数量增大,所以,很难说获利就减少。仅18世纪墨西哥就铸造了10亿多比索的银币,大量白银的进口,最终“到1750年以后,中国的金银比价上升到1:15,而欧洲则下降为1:14.5-14.8。在第一个阶段,全球白银价格趋于均衡的过程用了一个多世纪,而第二阶段的均衡的过程仅花费了50年的时间。[22]
弗林和吉拉尔德斯根据他们的研究,认为在东西方、南北方、欧洲和亚洲之间不存在需要用货币补偿的贸易不平衡,有的仅仅是贸易,货币实体就是用来交换的商品,产生交换的原因与非货币商品是一样的。西班牙等国家白银的低价和中国的白银高价带来了套汇获利的机会,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动力,因此,白银市场的非均衡是早期现代时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原因。[24]
柏林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货币也是与其他商品一样名副其实的商品,正是对货币的需求才使市场上供应商品和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成为可能。因此,这种套利兑换的普遍实践本身已经反映了(或者有助于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21](p.195)
第三种观点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综合。
弗兰克把前述两种观点都吸收到了他《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著作中,用贸易平衡和货币流动来说明他的1400-1800年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理论。他是怎样论证贸易平衡的呢?他告诉我们,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21](p.181)。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
弗兰克同时告诉我们,货币不仅可以用来对贸易赤字进行“结算”,而且是一种能够产生利润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则支配的。“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银价格会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价格会高一些,这就吸引着白银从一地流向另一地”。“任何一种货币都既是价值储存器,又是各种货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媒介。各种面值和纯度的货币都可以相互兑换或套利,也可以换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货币之间的套利兑换性以及它们与商品之间的交换性,使得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场真正地运转起来!”[21](pp.189-190)“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欧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亚洲各国的黄金和白银的兑换差价之间套利,以及在某些贸易往来中、尤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21](p.246)为什么中国需要这么多的货币?他的回答是,无论在微观还是在宏观层次上,货币都润滑着制造业、农业、贸易、国家开支等等的机制,也润滑着制造和操作这种机制的那些人的手。“货币支撑和制造着有效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刺激着供给”。但是,货币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制造出有效需求,只有在已经具备生产能力,因此“有通过投资和提高生产效率来扩张生产能力的可能性”的地方,货币才能制造有效需求。[21](p.196)弗兰克认为中国有这种能力。在弗兰克论述中,没有严格区分“货币”和“白银”的概念,许多情况下二者被替换使用。
四、白银流入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怎样?
戴建兵先生认为,从货币文化的角度看,西属殖民地银元的输入带来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巨大变化,首先是中国传统的以铜钱和纸币相结合的货币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过去,白银虽然很早就成为货币,但其属性多囿于贮藏,流通媒介作用并未取得应有地位,明代中后期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加上政府在税收中征收白银的政策,致使白银在大额交易和政府财政上起着纸币和铜钱无法取代的作用;其次是中国银两的形制由束腰形的银块状变为船形,即俗称的“元宝”。三是引发了中国自铸银元,从清代中叶起,政府和民间就开始了仿铸外国银元。中国的钱币文化便逐渐失去了光彩。[25]
彭信威先生早年也曾论述过:在人类史上主要有两种独立的货币文化,一是希腊体系下的西方货币,以金银为主,没有穿孔,一开始就在币面铸些鸟兽人物草木;二是东方货币,以铜铁为主,有方孔,币面只有文字,没有圆形,甚至若在一种钱币上发现有云朵或飞鸟走马,钱币学家就要疑心它不是正品。由此可知,两种货币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而“外国银元的流入,在中国的货币文化上,引起了一次大革命”。[26](p.539)
国外学者W·S·阿特韦尔着重研究了白银流入对晚明经济的影响。他认为首先是促进了晚明政府银库收入的增加。据1528-1643年明朝太仓银库岁入数额表,在16世纪60年代以前,外国白银对明朝中央政府财政的影响似乎很小或根本没有数字依据。1571年,当银库收入增加很多时,即从75000-86000公斤增加为116250公斤时,进口白银的作用日加明显。此时是明朝驰海禁4年以后,也是马尼拉中西贸易真正开始的同一年。到1577年银库收入为163478公斤,是1560年期间的两倍,直到明亡,政府每年的白银收入从来没有低于100000公斤,这种变化固然与其他原因有关,但与外贸空前发展、白银大量进口显然有直接关系。其次是促进了赋税制度的改革。1581年明朝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法,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取代陈旧而复杂异常的赋税制度。当时中国国内白银产量下降,只有获得大量的经常性的进口白银,才有可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折银纳税。“一条鞭”法最早在直接卷入海上贸易、并有白银进口的福建和浙江试行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再次是促进了晚明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根据“一条鞭”法,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从而使户丁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银两代替实物缴纳赋税,扩大了货币流通,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一条鞭”法的实施和货币法的强化,使诸如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漳州、广州等城市出现了经济上的繁荣,在江浙地区出现了数十个新的乡村市镇,它们大多以丝织业、纺织业和制陶业的专业化生产驰名,在这些手工工场中出现了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简单的雇佣关系。[10]
万明先生从更高的角度强调了白银输入对明代中国的意义,她认为,以白银化为标志,明代中国与两个重要历史转折开端联系在了一起,即一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这种转型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体现了出来,如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转变;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转变;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关系转变;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因此,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证明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性社会转型的性质。二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白银货币化是转型变革中的中国与正在形成中的整体世界相联系的产物,也即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产物。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变化,白银货币化的初步奠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市场经济萌发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扩展,中国由此主动走向了世界。而不是如既往所认识的,是西方东来,中国才被动地与世界衔接起来。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西方创造的,当世界逐渐形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时,明代中国曾积极参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为整体世界的出现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此而言,明代白银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社会转型和整体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它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7]
庄国土先生是从15至19世纪初的整个早期近代时期来分析白银流入中国的作用的,他认为:首先,白银流入使中国能够完成从铜钱到白银再到银元的通货转化,通货的转化对国内商品流通、大规模市场网络的形成意义重大;其次,也是16-19世纪中外贸易发展的动力,银元成为中国通货,造成了中国对银元的大量需求,也使中国商品具有国际性,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促使中外关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英国商人为首的西方商人为了维持利润极大的对华贸易,在白银来源枯竭后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而中国政府禁烟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防止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争夺白银的战争,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16]
弗兰克认为,白银流入刺激了中国生产和人口的增长。“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自16世纪中期起,白银注入中国经济所造成的经济扩张更为壮观。明代经济越来越在银本位的基础上货币化,并且至少到17世纪20年代一直在飞速扩张。只是在17世纪中期,由于气候、人口、经济、政治的综合危机和明、清政权的交替,这种扩张才暂时被打断。但是,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且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又继续扩张。”从1400年到1750年,甚至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比欧洲快得多,原因是它的生产也增长得比较快。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的表现是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丝绸、瓷器、茶叶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还出口黄金和铜钱。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21](pp.159;228;468;224;228;182)
弗林和吉拉尔德斯认为,讨论美洲白银的影响不能仅仅将眼光盯在白银上,应该把视野放宽些,看到与“银丝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美洲农作物的影响。马尼拉大帆船输送到亚洲的商品除了白银之外,还有贸易价值不高但生态意义极大的物品,那就是玉米、红薯、花生、土豆、辣椒等美洲的农作物。它们被引进中国后,引起了中国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使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规模都增长了一倍,与种植水稻和谷子相比,美洲作物需要投入的劳动较少,因此,能腾出更多的劳动力生产丝绸、茶、糖等经济作物,同时,由于人口增加和内部移民,边疆地区的重要性也提高了。可以说,广义的银丝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中国的历史进程。[22][24]
威廉姆·谢尔(shell)认为,白银贸易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美洲与中国的互动影响。他研究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墨西哥经济史,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墨西哥的比索出口就与中国经济处在一种共生共栖的状态中。比索是墨西哥银矿业生产的具有附加价值的产品,“比索贸易”不仅有助于扩大墨西哥的制造业,而且中国出口的生丝支持了墨西哥纺织业的扩大,中国出口的水银刺激了墨西哥银矿业的复兴。在19世纪,矿主们是根据当地经济和中国的白银价格信号生产白银的,中国对墨西哥银元的持续进口使墨西哥的银本位制得以长期实行,1905年墨西哥转向货币的金本位制,使白银生产失去了其在国内和中国的市场,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为1910年墨西哥革命铺平了道路。[28]
当然,学着们也解释了白银流入与明朝灭亡和1800年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关系。
W·S·阿特韦尔认为,明朝政府的灭亡同当时白银进口的锐减有关系。白银的流入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但也鼓励了商业投资和物价飞涨,使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趋于恶化。很多商人和手工业者被螺旋型的通货膨胀引向更加依赖货币经济的扩张,但货币经济发展本身依赖大量白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供应。但从1610年到明朝灭亡的1644年,进口白银大大减少,原因包括:美洲白银产量下降;1630年之前荷兰和英国对中国和西班牙航海的骚扰;1634-1635年西班牙国王的限制贸易政策;1639-1640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的事件;荷兰封锁果阿和马六甲商道;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同时,中国国内明朝政府在1618-1636年为对付农民起义和满族入侵,将税收提高了7倍,投资人宁可将白银窖藏起来等待时机,由此造成流通中的白银大大减少和银贵钱贱,从而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明王朝的灭亡并非仅仅因为这个时期白银进口的锐减,但白银减少必定加重了它的困难,动摇了它的稳定。[10]
弗兰克对1800年后中国衰落原因的分析视野更宽阔一些,他认为欧洲的胜出与亚洲衰落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的结果,应该放在全球经济框架中利用“世界经济—人口—生态范围的经济分析方法”加以研究。在他看来,在1400-1800年世界经济长周期的A阶段,亚洲处在优势地位,这个A阶段是由美洲金银的流入所支持的。但正是这种生产和人口的扩张形成了1800-1970年长周期B阶段的发展阻力和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从而缺乏对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发明的需求和冲动,失去了转化的契机,生产和贸易也随之衰退。相反,欧洲人胜出是由于他们借助美洲白银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并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由于他们的人口—资源比大大低于亚洲,高工资促使人们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发明和利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到1800年,欧洲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陷于普遍衰落之时,欧洲人乘势猛烈入侵,但中国的衰落来得更晚一些,英国人不得不用鸦片迫使中国“开放门户”。“鸦片贸易及其引起的大量白银外流动摇了整个经济体系”。[21](pp.371;397;391;422-423;392-393;368;401)但在整个分析中,弗兰克更强调资本和资本的来源。
结语
从以上对美洲白银研究的观点介绍中,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点结论: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生产了大约10万至13万吨的白银;其中向美洲以外地区输出了大约80%以上,这些白银的近一半流入了中国;白银流入中国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白银作为货币可以平衡贸易,同时,从白银与黄金的世界比价看,白银的价格在中国大大高于欧洲,作为特殊商品的白银可以被从欧洲贱买而到中国贵卖,从中套利;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早期近代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但明朝的灭亡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也同当时中国白银输入的减少甚至外流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美洲的白银生产并非仅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其与中国早期近代的经济发展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上述学者关于美洲白银的研究,尽管争议之处颇多,但至少提醒我们深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世界经济体系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其演变规律何在?二是应该怎样看待早期近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衰落,她在21世纪能否再度复兴?
标签:白银论文; 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论文; 白银投资论文; 英国殖民地论文; 殖民地历史论文; 中国黄金论文; 货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