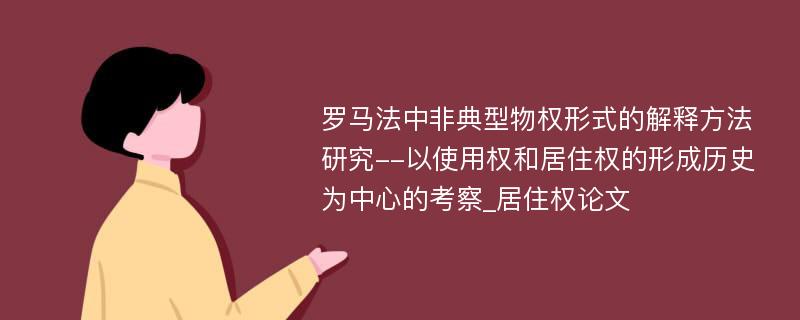
罗马法中非典型物权形态的解释方法研究——以使用权、居住权的形成史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居住权论文,使用权论文,物权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85-07
一、罗马法中使用权与居住权的日常语言表达与效力问题
用益权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前2世纪初之间。随后,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出现了使用权,它与用益权的差别在于权利人没有收取孳息的权利。此外,习俗中还存在着居住权,它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市民法上的权利。在房屋为客体的情况下,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三者的权利内容是非常近似的,都表现为与居住相关的他物权。
在罗马法中,设立物权的一般方式是曼兮帕蓄和拟诉弃权。曼兮帕蓄(mancipatio,也译为要式买卖)是这样一种方式:以不少于五人的成年罗马市民为证人,另有一名司称,买主手持铜牌说出套语,根据奎里蒂法物是他的,然后将铜块交给卖家以获得物权。主要适用于所有权、地役权以及保留用益权的所有权交易。拟诉弃权(ceessio in iure)则是这样进行的:在裁判官或者行省总督面前,物品受让人手持该物说,根据奎里蒂法物是他的,长官询问出让人是否有相反要求,如果后者保持沉默,则受让人获得所有权或者他物权。在这两种方式中,专门的仪式、长官、证人不仅起到公示的作用,而且保证了物权设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但对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而言,遗赠才是它们最主要的设立方式,用益权人、使用权人和居住权人常常同时也是受遗赠人。与拟诉弃权或者曼兮帕蓄方式不同,立遗嘱人不必通过专门的仪式和程序,只要为意思表示即可。对于遗赠而言,法律效力来源于它的套语。没有拟诉弃权中长官或者曼兮帕蓄中的证人的协助,一个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不能清晰地区分用益权、使用权或者居住权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他对于不能直接使用只能享用其孳息的物,比如一片森林,遗赠了使用权;又或者有人在遗嘱中提出了一种当时市民法中不存在的权利形态,像“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或者“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这一类非典型的物权形态,对此如果严格遵守用益权和使用权的逻辑,那么在诉权体系中就会找不到相应的救济方式,结果就是遗嘱目的落空。
为了保证这些非法定物权形态的有效性,法学家不得不重新界定这些权利的范围。重新界定依靠的手段既有扩张解释也有类推适用。随着类似的现象不断增加,这些解释要么改变了物权的形态,使它能包含具有的新的内容;或者由于多种不同解释而使得物权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不得不通过立法来重新塑造。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民法中使用权和居住权最终的法定形态。
二、罗马法学家对使用权的扩张解释
(一)使用权的传统逻辑和法定形态
在用益权产生后的一个世纪,出现了一种与之结构相似但内容更为狭窄的权利,只能满足单纯的个人使用。[1](P431)就其内容而言,一方面权利人只能进行使用没有收益权能;对于物的使用仅仅满足权利人个人的直接的需求,不能用于出租。正如乌尔比安所言,“如果一物的使用权遗留给了某人,他可使用该物,但却不可获取孳息”。(D.7,8,2)。这种权利被称为使用权(usus)。由此可见,从古典法的逻辑上看,使用权与用益权的区分的界限就是使用权人没有孳息获取权能,否则将导致它与用益权的界限混淆。
(二)使用权的非典型形态:孳息收取
虽然两者在逻辑上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但在文本中经常可以看到使用权人的孳息收取权以及法学家对此的争议。
第一,土地的孳息收取。如果一个庄园的使用权被遗赠,内尔瓦认为,权利人享有每日所需的木材、花园、水果、蔬菜、水、草梗和蔓枝,但不能使用小麦和庄稼;另一方面,萨宾、卡修斯、拉贝奥和普罗库鲁斯则认为,包括了农地上的出产物,以满足家庭需求。杰尔苏还认为可以为招待客人和娱乐而使用(D.7,8,12,1)。
第二,房屋的出租,乌尔比安在《萨宾评注》第17卷写道,“她不能转让房屋的使用权于他人”(D.7,8,11);同样在这一卷中,他也写道:“拉贝奥说,本人在一座房子中居住的,亦可接受一个承租人。”(D.7,8,2,1)
第三,动物的孳息,对于羊群,拉贝奥认为只能为了施肥的目的对其加以使用,无论是羊毛、羊羔还是羊奶都不属于使用权人;而乌尔比安则认为可以少量获取羊奶,以满足使用人的需要(D.7,8,12,2)。
文本中的冲突状态,正如彭梵得所描述的:使用权的概念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狭义的解释,坚持使用权的原初含义,排除任何对孳息的收取;另一端是广义的解释,允许使用权人对孳息进行一定量的收取。[2](P114)
导致文本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拜占庭学者对这些文本进行了添加,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片段D.7,8,12,1。
D.7,8,12,1。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对于被遗赠了土地使用权的人,除了居住权外,还可以在其上散步、骑马、驾车以及乘轿。萨宾和卡修斯的理论是,他还享有日常所需的木材、鲜花、果树、蔬菜、花卉以及水源等,但不能从中牟利,只能为个人使用而不得滥用。内尔瓦也是如此认为,他补充道,使用人还可以使用草梗和柴枝,但不包括板材、油、谷物或田里的果实。萨宾、卡修斯、拉贝奥和普罗库鲁斯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还进一步补充说,对该土地上的出产物,使用权人还可因他以及他的家庭的生计需要而加以使用。……尤文图斯甚至认为他可为了招待客人和娱乐而使用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我也同意的看法。因为对于使用权人,为了与其尊严相适应的,应该有一个更大的使用范围。
这个文本谈到了使用权的孳息收取权能。它罗列了古典早期最著名的法学家们的意见,包括萨宾、卡修斯、拉贝奥、普罗库鲁斯、内尔瓦、杰尔苏,全是萨宾派和普罗库鲁斯派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现代法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被全面篡改的文本。里科波诺的理由是,片段中乌尔比安引用各法学家观点的顺序不合理:萨宾和卡西的观点被先后两次援引,内容却不一致。[3](P591ss)他的意见得到了后来潘帕洛尼、彭梵得的支持。[2](P114ss)此外还有格罗索进行的考据,他认为本片段围绕的是“使用”这个概念,而第一句被怀疑为添加的句子中强调的却是“收取”。而且,此句与下一句“尤文图斯甚至认为使用权人可以和其宴请的客人和招待的客人一起使用这些东西”之间也显得不连贯。[1](P449ss)①
因此,可以说这种文本上的冲突,实际上体现的是罗马法两个不同时期法律思想的差异。在古典法中,使用权与用益权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后古典时期,才允许使用权人收取孳息。格罗索认为,罗马人提出使用权概念原本是为了强调有别于收益的单纯使用,并且是与某些物的特性相适应,而在拜占庭学者那里,它却转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数量问题。[4](P432)
(三)古典法中使用权的扩大解释
使用权的孳息收取权能为拜占庭时代的法学家所彰显,但并非从此开始。从古典时代法学家开始,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使用权人的权利在其原初概念基础上的扩张。下文以遗嘱解释为背景说明使用权是如何在解释中被增设了孳息收取权能。
D.7,8,14,1。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遗赠的是用益权(usufructus)或者是孳息收取权(frucutus)是不重要的;因为在孳息收取权(fructus)中也包括了使用权能(usus),但在使用权(usus)中,却没有包含着孳息收取权能(fructus)。
D.7,8,22。彭波尼:《昆图斯·穆丘斯评注》第5卷。神君阿德里亚努斯皇帝认为,一些人被遗赠了森林的使用权(usus),那么采伐孳息的权利(fructus)也应该被遗赠,如果不允许受遗赠人采伐林木并且出售[木料],他就从遗赠中一无所得。
(1)使用权的扩张解释。通过D.7,8,14,1与D.7,8,22这两个文本的对比,可以发现阿德里亚努斯皇帝对于遗嘱中的使用权进行了扩大解释。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如D.7,8,14,1中乌尔比安的文本所描述的,使用权(usus)是没有孳息收取权的。
从D.7,8,22这个文本中可以看到,必须扩张使用权范围的原因在于使用权的客体类型与它的权利性质发生了冲突。从客体类型上看,使用权和用益权是一样的。在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中,按照用益权客体的排序,列举了各种使用权的客体,房屋(D.7,8,2-9)、土地(D.7,8,10.4-D.7.8.12.1)、牲畜(D.7,8,12,2-D.7,8,12,4)、奴隶(D.7,8,12,5-D.7,8,14pr.)。并没有把不能直接利用的孳息物排除在外。如果严格遵循用益权的逻辑,使用权人是不能够收取孳息。那么当遗赠了孳息物的使用权时,就必然产生遗嘱目的落空的问题。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进行使用权的扩大解释的例子还有对金钱设立使用权的情形。
D.7,5,10。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79卷。即使只是对金钱使用权的遗赠也须订立这种要式口约,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使用(usus)这一称呼中也包括收取孳息(fructus)的权能。
(2)解释路径的选择。阿德里亚努斯皇帝的解答中说,给予孳息收取权的目的在于防止遗赠无效。这表明了他关注的重心不是使用权的权限,而是遗赠的目的是否能实现,如果不允许使用权人获取孳息,那么遗赠的目的就会落空。
既然如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阿德里亚努斯皇帝不对遗嘱采取目的解释,认为实际上被遗赠的是森林的用益权而不是使用权,这样就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相反,对使用权进行扩张的解释会导致使用权与用益权之间清晰的逻辑区分被打破。两相比较,后者的解释成本显然更高。D.30,1,4pr这个讨论遗嘱表示错误的文本对此给出了答案。
D.30,1,4pr.。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49卷。如果一个人弄错了庄园的名字,将塞姆布洛尼亚斯努斯(Sempronianus)写成了克尔奈里亚努斯(Cornelianum),那么塞姆布洛尼亚斯努斯是应给付之物。如果一个人希望遗赠一件衣服,但他写成了家具,因他认为在家具的名称中包含衣服在内。彭波尼写道:衣服不是应给付之物,这就如同一个人认为“金子”一词包括镀金或镀铜在内,抑或(这件事是更愚笨的)认为在“衣服”中还包括银子,因为,物的名称是不可变的(immutabilia),而人的名字是可变的(mutabilia)。[5](P559)
这一文本揭示了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目的解释纠正遗嘱表述错误。遗嘱中对于客体的错误表示有两种,第一种是日常名称与物的确定性的认识错误,比如人的名字或者庄园的名字;第二是物品属性与物的命名的认识错误,比如属种关系的混淆,如片段中提到的把“衣服”与“家具”相混淆。虽然两者都存在名称与实质的扭曲问题,但前者是与物的性质无关的名称,后者则是与物的性质直接相关的名称,遗嘱的目的解释能矫正前者而不能改变后者。在彭波尼提到的这个案例中,首先森林作为客体是明确无误的。其次,如果遗赠人误把用益权写成了使用权,那么这种权利名称的错误显然还是属于物的属性的错误,对遗嘱进行目的解释的路径不能改变遗赠目的落空的结果,所以阿德里亚努斯皇帝对使用权进行扩张解释是合理的。
(3)解释的后果。当法律为了遗赠的效力而给予使用权人以孳息收取权能时,使用权和用益权之问的界限就被打破。原本使用权与用益权存在着“质”的差异,权利人只能单纯使用客体;在这样的解释后,使用权与用益权的差异变成“量”的关系,使用权人可以获取孳息,只是数量少于用益权人。
在这种情况下,区分使用权与用益权的标准就体现为“个人需求”。在古典法中,它原本指的是使用权人不能将物出租,仅限于自己使用;但在使用权人获得孳息收取权的情况下,它可以用来确定使用权人的孳息收取范围。使用权人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收取孳息(D.7,8,12,1),这种需求的标准既有主观上的,包括家庭和招待客人的需求,这是根据使用权人的身份和社会尊严所决定的;也有客观数量上的规定,就土地孳息而言,这种个人需求的限制应该是:“最多不超过1年的需求。”(D.7,8,15,1)由此,个人需求标准在使用人的范围、获利的范围上都进行了规定,而用益权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别的限制,所以使用权的扩张没有完全打破它与用益权间的界限。
(四)从扩张解释到使用权法定内容
最初给予使用权以孳息收取权能的目的在于解决遗嘱的效力问题,而后人们普遍承认了使用权人享有孳息收取权,于是使用权的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样的转换过程中,使用权的作用也发生变化,它可以充任不给所有权带来过重负担的“小用益权”的角色。用益权完全掏空了所有权的经济内容,使之沦为一个空虚所有权;而在使用权中,权利人仅仅获取足以满足生活需求的孳息,所有权人仍然可以获取剩余部分的孳息。
从整个物权体系上看,虽然使用权的内容与名称并非完全相符,但是在扩大其权能的同时,增加新的权利选择的时候,没有损害到它与用益权的界限以及整体的法律逻辑,因此可以说对于使用权的扩张解释是成功的。
三、从类推适用到独立的罗马法居住权
(一)遗嘱的解释与居住权产生问题
作为独立物权形态的居住权制度出现得非常晚,直到优士丁尼时期才得以确立。因为“居住权”(habitatio)是一种对他人房屋的权利。在已经存在房屋的用益权或者使用权的情况下,单独的居住权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在古典法时期,要遗赠房屋的使用权能,只有用益权和使用权这两种明确的物权形态可供选择。
此时,居住权虽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用来表达专门针对居住的权利。所以,如果立遗嘱人用一种非法律术语说我把房屋的“居住”遗赠给别人的时候,那么这种遗嘱有效否,应以何种诉权救济之?或者一个缺乏法律常识的人,用一种日常语言与法律语言相混合的表达方式说道,“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或者“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权利的性质?对此,法学家根据各自的立场采用了不同的解释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二)类推适用使用权
D.7,8,10pr.。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居住权(habtatio)被遗赠,那么所产生的权利完全等同于遗赠使用权。帕比尼安在其《问题集》第18卷也对此持赞同态度,从效果上看,遗赠使用权和遗赠居住的权利几乎是同样的。因此获得居住权的人不能赠与这一权利,但可以接纳使用人所接纳的同样的人。居住权不能被继承,但同时既不因不使用,也不因人格减等而消灭。
这个片段以遗嘱中措辞的疑问为开始。因为在遗赠中的“居住权”(habitatio)并不是当时既存的法律术语使用权或者用益权。这时候,它更像一种社会习俗,如何界定这种不明确的物权形态呢?有人提出疑问,是否可以将之等同于既有的使用权呢?这种说法得到了塞维努斯皇帝时期的法学家帕比尼安的认同。通过他的解答,可以看出古典时期的法学家是如何通过类推适用的方法来界定这种介于事实与法律之间的权利。
(1)居住权的内容确定。帕比尼安认为,从效果上看,居住权和使用权几乎是相同的。使用权是指对他人之物进行收益但不能获取孳息的权利。权利人可以让自己、其家庭成员、客人,甚至是家庭之外的人一起居住,但不能将其出租以收取民事孳息。以此类推,这就是居住权的权限范围。
(2)居住权的期限确定。帕比尼安说,这种居住的权利不能被继承。用益权与使用权的期限是权利人的终身,这已经成为此类权利的基本要素。但对于“居住权”的期限,帕比尼安进行了重申。因为与用益权和使用权不同,对于居住权的期限在法学家中一直存在着争议。
D.7,8,10,3。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但一项居住权是一年有效还是终身有效,在先前的法学家中间是有争议的。鲁蒂流斯说,居住权在他活着时都有效。杰尔苏在其《学说汇纂》第18卷中也对此表示了赞同。
文中的鲁蒂流斯(Rutilius)指的是公元1世纪前叶的法学家鲁蒂流斯·鲁弗斯(Rutilius Rufus),他的观点被随后的公元2世纪前期的法学家杰尔苏所接受。由此可见,虽然居住权一直没有成为法定的权利,但法学家对于这种现象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典前期。
(3)居住权的特别内容。虽然可以类推适用使用权,但居住权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内容是使用权所不能替代的。帕比尼安在前引片段的结尾处说道:“居住权既不因不使用,也不因人格减等而消灭。”所谓人格减等,指的是罗马人所具有的三种基本身份:自由人身份、市民身份以及家庭身份部分或者全部丧失。莫德斯丁说,居住权能够在人格减等中得以保留的原因,在于它的性质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法定权利。(D.4,5,10)由此可见,虽然房屋的使用权与居住权都变现为一种物权性的居住权利,但有着不同的基础:使用权人是对于房屋直接的有限利用的权利,而居住权则来源于人类对居住的需求事实。
(三)用益权和使用权视角下的居住权解释冲突
D.7,8,10,2。乌尔比安:《萨宾评注》第17卷。如果一项遗赠是以如下的方式表示:“我遗赠给那人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usus fructus habitandi causa)”,那么,就要考虑他是否仅仅只有一个居住的权利,或者也有用益权。普罗库鲁斯和内拉蒂认为,只有一项居住的权利被遗赠。这是正确的。当然如果被继承人明确表示:“一项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那么无疑就是指使用权了。
I.2,5,5。对享有居住权的人,为了事物的功利,根据马尔切勒的意见发布了朕的决定,朕允许它们不仅自己在[房屋]中过活,而且也可将之租予他人。[6](P208)
如果遗嘱混杂了日常语言与专业术语说要遗赠“以居住为目的用益权”(usus fructus habitandi causa),如何确定这种权利的性质?确实引起法学家的疑惑。用益权人在保障物的状态和经济用途的情况下,他可以如同所有权人一样行使其权利。而“居住”,顾名思义,仅仅是对于房屋的居住权利。那么权利人对于房屋的性质是用益权还是居住权(即使用权)呢?这关系到房屋能否出租的问题。对此,古典法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解释办法,也得到了不同内容的权利。
(1)目的解释加类推适用
对于“以居住为目的用益权”,图拉真到阿德里亚努斯皇帝时期的两位法学家普罗库鲁斯和内拉蒂认为,这只是一个关于居住的权利。因为在遗嘱中写到“以居住为目的”,由此可见遗嘱人所要设立的权利只是一个满足居住需求的权利。在将之确定为一个居住权的情况下,自然要类推适用使用权。对于“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的解释,就更为简单,可以直接把它看做使用权。在这种目的解释加类推适用的路径下,“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就变为了一种不能出租的居住权。所以如果权利人将之出租,是不能提起用益权确认之诉。
(2)文意解释
而安东尼王朝时期的法学家马尔切勒(Ulpius Marcellus)采取了与萨宾和内拉蒂不同的解释径路。他选择的是文义解释,显然,从文本上看,I.2,5,5中所说的居住权指的就是这种“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由于用益权就是一种可以出租使用的权利,所以“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就是可以被出租的。[1](P449)
(四)优士丁尼的统一居住权立法
在居住权还没有被看做一种法定的物权形态时,人们已经在日常的语言中频繁使用,这体现了它的社会需求性。而法学家参照既有的使用权对之进行规范。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它在日常语言中保持着开放状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语词表达自己的居住愿望,比如“以居住为目的的用益权”或者“以居住为目的的使用权”等,对于这些不同的表达又衍生出不同的解释。在没有足以压倒其他解释的权威观点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导致了多种居住权并存的局面。
事实上,在物权的方式之外,对于“居住”的遗赠还能产生出债的居住权形态。
D.33,2,15pr.。马尔切勒:《学说汇纂》第8卷。我的继承人必须让提蒂乌斯在这房子里居住,只要他活着。
这被看成是一项遗赠。
D.39,5,32。谢沃拉:《意见集》第5卷。路丘斯·提蒂乌斯写了这样的信:“你能够免费地利用这样一座房子以及其中所有的房间,我以此信通知你,由于我的同意,你能如此行事。”我的问题是,是否书信人的继承人能够阻止他利用这一房屋呢?答案如此,根据所陈述的事实,书信人的继承人能够改变他的意愿。
与马尔切勒一样,切尔维丢斯·谢沃拉(Cervid ius Scaevola)也是安东尼王朝时期的法学家。在第一个文本中,马尔切勒提到了可以通过遗嘱设立一个终身的居住权。在文中所使用套语“我的继承人必须让……”说明遗赠的类型是容受遗赠。由于它是以容受遗赠的方式产生,所以只具有债的效力。在谢沃拉的文本中看到,如果仅仅是基于债的关系而产生的居住权,继承人可以拒绝提出这种权利。
多种居住权的形态有着不同的性质、效力、权限,这使得统一的立法成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为此,优士丁尼在公元530年做出了一项统一居住权的立法:
C.3,33,13pr.。在过去曾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一个房子的居住权被遗赠,首先(如同与它相似的情形),是否这种居住的权利是属于使用权、用益权或者两者都不是呢,而是一种特别的有着自己特性的权利。是否被遗赠了这种居住权的人能够将之出租,或者宣称对于房屋的所有权,为了平息这样的争议,朕以简洁明了的意见消除了所有的疑虑。
C.3,33,13,1。如果有人遗赠了一种居住的权利,对朕而言,显然更为仁慈的意见是也赋予他可以出租的权利,因为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从中获得补偿,这和他在其中居住有什么区别吗?
C.3,33,13,2。这更为明显,如果他遗留了一个居所的用益权,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否还可以用用益权这个名称?因为朕不想要这种居住权如同用益权一样。
C.3,33,13,3。受遗赠人不能获得居所的所有权,除非有最清晰的证据证明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他,遗嘱人的意愿应该在各个方面都被遵守。
C.3,33,13,4。在所有可以产生居住权的情形中,朕颁布的决定都将被适用。
这些文本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优士丁尼要通过立法结束居住权的混乱状态。在C.3.33.13pr中,优士丁尼提到了制定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在于“平息以往的争议”,由于多种解释导致了权利的不确定状态的困境,必须通过立法予以统一。
第二,居住权具有独立的性质。优士丁尼认为,居住权(proprium)本身就是一种权利形态,由此结束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的居住权属于用益权还是使用权的争议。在C.3,33,13,1中,优士丁尼明确给予了居住权人以出租的权利,这种原因不是来源于对用益权的比照,而是根据一种实用的目的。在C.3,33,13,2中,优士丁尼再次重申在一座房子上设立用益权和居住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在居住权被立法确立后,对于房屋的用益权将属于用益权的范围,不会再发生普罗库鲁斯和内拉蒂的解释冲突。
罗马法学家对非典型物权解释的终点,正是现代物权法定的开始。就使用权而言,现代民法一致选择了使用权扩张解释后的形态。比如《法国民法典》第630条规定:对不动产之孳息有使用权的人,仅得为其本人与家庭请求所需之部分。《意大利民法典》第1021条规定:对物享有使用权的人可以使用该物。如果使用权的标的是可以产生孳息之物,则使用权人可以在自己和家庭需要的限度内享用孳息。应当以权利人的社会地位评估这一需要。《德国民法典》第1090条和第1091条规定:土地可以此种方式设定权利,使因设定权利而受利益的人有权在个别关系中使用该土地或者享有其他可以构成地役权的权限;限制的地役权根据权利人个人的需要加以确定。对于居住权,现代民法接受了优士丁尼法的处理方式,把它规定为一种独立的他物权形式,但在出租问题上,都选择了内拉蒂和普罗库鲁斯的主张,规定了居住权人不能将房屋出租(《法国民法典》第634条[7];《德国民法典》第1029条[8];《意大利民法典》第1024条[9])。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从使用权到居住权的产生,都不是基于充分的逻辑推演,而是法学家为了满足民众现实生活需求,而对既有法律作出的解释。这些传承于罗马的物权类型,带有天然的历史内涵,并非如数学定理一样不证自明。
物权法定在现代民法中是被奉为圭臬的原则,依此要求,物权的内容和类型都不能有新的创设,所以物权类型只能是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甚至范围更为狭小(因为有的国家连基本的类型都不齐备)。在历史分析的视角下,可以发现这些不允许变动的制度只不过是罗马法学家对于日常生活中新现象的把握和分析,我们为什么不担心物权法定原则对现实生活的忽视呢?有什么理由就认为现代民法中的物权形态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又或者我们的生活对于物权的需求,比起罗马法时代没有什么变化吗?
以重视日常语言分析著称的法理学家哈特说过:“任何选择用来传递行为标准的工具——判例或立法,无论他们怎样顺利地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案件,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适用上的问题,将表现出不确定性,它们具有人们称之为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的特征。”[10](P127)法律语词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正常和自然的语言现象,关键是立法者不能觉得自己是神,可以建构出一个详尽无遗的规则,以至于对任何案件都可以预先确定,并且在实际中不会出现法律所没有提供的新选项。从使用权和居住权的发展史中可以看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给出了不止一个的新选项,法学家并没有因为市民法传统的神圣性而拒绝它们,而是考虑到民众需求的特征因素,将之类比既有的权利现象以寻找最优的解释径路。从物权的形成史的分析可以看到,虽然物权法定的原则有利于保持体系的稳定和交易安全,但它不能代替我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更不可能以此为教条无视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
注释:
①对于这个文本的中文评析,可参见曾健龙:《使用权与用益权的界限问题——D.7,8,12,1之文本分析》,载《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