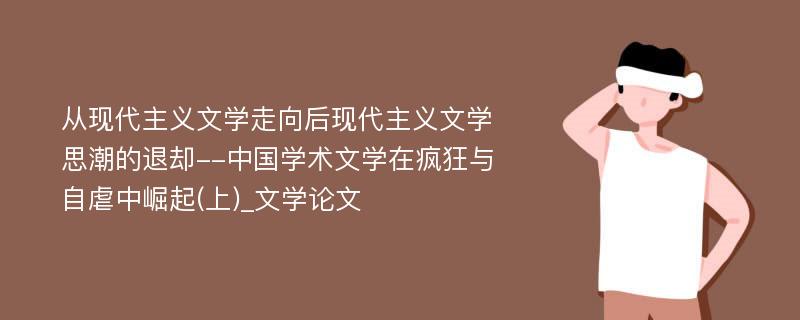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文学论文,学院派论文,疯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暮秋的挽幛悲壮地悬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时空驿站之际,栖息于高校校园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落泪了。他们沉重的告别了成熟于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收揽了拥抱现代主义文学必须以生命代价所付出的非理性精神亢奋和意志张扬,在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中义无反顾地扑向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此,东方大陆学院派文学在这些文学圣徒们的最新赌博下,以其“后现代”(Postmodern)式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话语表述方式, 颠覆和消解着结构这个当下社会“文本”的话语权力。评判一切存在价值的圣权和独占在他们的沉默和无言中被蔑视了。这无疑是一个超越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后的最深沉的反抗。也正是如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空跨度中,学院派文学痛苦地走完了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精神磨难历程,在八、九十年代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学院派文学代表作,正是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展览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痛苦和精神蜕变中所沉沦的人格、灵魂和他们隐匿的内心世界。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给出一个设问,什么是学院派文学?(注:按:这也是当代文学思潮在九十年代的终结期遗留下的历史性设问。对“学院派文学”这个概念的界定及其之所以产生和怎样生存的理论阐释,大陆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还没有过多地涉猎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谢冕曾提出过“学院派批评”的口号。)
学院派文学是在八、九十年代于高校校园文化母体中孤独出的一脉文学思潮,学院派文学的创造主体都是咀嚼过高校校园文化的欣乐和若涩的天之骄子;学院派文学的题材周延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其透视了在校园文化母体中孕育的男女大学生们的文化心理,尽管这种文化心理可能是他们蓄意为情造境所呈奉的虚假文明和真诚丑陋,另一方面其又涉猎了这些受过校园文化洗礼的文学圣徒们用自己的审美价值标准和道德价值标准读解、评判校园文化的题材;学院派文学的主题在这些大学生的激情灼烧和精神窒闷中表现出一种深沉而自虐的无主题变奏,因为,精神的流浪使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他们命中注定要浪迹思想的天涯,他们无法、也不愿寻找精神的终极家园归宿,也正是精神流浪的无所皈依,铸造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思想在无中心散点放射状态中呈现出的未确定性(Unspecialization),无主题就是这些文学圣徒们在学院派文学作品文本中热烈拥抱的主题,正如石磊在《我的大学》一诗中道白:“揣着五颜六色的渴望第一次远游来到这所城市大学/一大堆日子淹没在无主题变奏曲中/听书馆一万个声音重复着世界人生/你一头撞碎了萨特弗洛德们的喋喋不休。”(注:《我的大学》石磊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开放的天空——最新中国校园诗歌选萃》西马、老愚主编,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43页。)
这就是我们给出的关于“学院派文学”这一概念的基本界定。
学院派文学崛起的自觉以八十年代刘索拉描写音乐学院大学生生活的《你别无选择》为历史界标,其起势就以生命的非理性冲动颠覆着痛苦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理性沉思,也更以一种现代主义文学的颠狂势态摇旗呐喊,并且也宣告了八十年代当代文坛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了主潮。从此,学院派文学也开始了它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却的痛苦历程。让我们的思考先驻足于学院派文学的前奏——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从这里启开我们的思路。
毫无疑问,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思潮是从高校校园率先走向社会的。而撕开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帏幕的肇事者也正是那批涉世浅薄且故作城府深沉的男女大学生。他们大都是取胜于激烈的高考竞争,从中学直接跨进高等院校大门的佼佼者:“我们每人都是一座小心翼翼的火山/郁积着无数热情的火焰……长这么大我们学到些什么/考试、考试、考试——然后补考/我们是考大的/并且以后还要考!”(注:《大学生狂想曲》赵月梁著,见于《当代大学生诗选》韦云翔、岑玉珍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他们所拥有的幸运也正在于他们涉世未深的浅薄。他们没有充分地投入过社会,从学校到学校的直线旅程就是他们的人生阅历:因此,他们对历史和社会充满了距离感和陌生感。也正是这种涉世未深的浅薄使他们在精神和思想上,从来就不愿意背负历史和社会的积淀所威压给人们的文化负重感。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是赤身裸体和通体透明的自我。
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丹尔·贝尔(Daniel Bell )曾给出过一种关于现代性身份的定义:“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我在选择和行动的中创造我自己。这种身分变化是我们自身现代性的标记。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认知和身份之源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天启的神谕抑或理性。经验是自我的巨大源泉,并且与各种他者的自我相对抗……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注:Daniel Bell:The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NewYork.P137.)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文化心理就是这样契合于现代性,一切尽如索姆所描叙的那样:“他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人。”(注:《与非门》索姆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所谓“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人”,也就是在人格与思想上没有被界定。索姆在《与非门》中让王征稳坐柏拉图的“理式床”脱俗地高叫:“我就喜欢这个‘可能性’。”(注:《与非门》索姆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这个“可能性”就是现代哲学所倡导的人类生命的“未确定性”。也正是这种生命的“可能性”和“未确定性”诱惑着他们在社会和文化的空缺中自由、彻底地品尝生命,像渴望阅读诗歌一样渴望读尽社会和人生就是他们企盼的期望。
在这个意义上,浅薄恰恰构成了他们走向深沉的绝对可能性。
但是,他们跋涉出高考的泥沼步入高校校园所收揽的第一感觉,就像徐江在《青春》中所言说的那样:“当时大学里流行着这么一句口头禅:‘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154、154、154页。)他们刚刚逃避了高考那种异化人格的束缚, 又坠入另一更高层次的、更文明的束缚人格的学术文化圈。自从孔子退而作“六经”创设学府而授业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学术文化和学术文明的积淀使历代的国家、太学、官学和高等学堂呈现出威严的学术文化压抑感。徐江在《青春》中对九十岁高龄的大学捕捉到的最初印象就是:“从暮色里一望,阴沉庄严的教学楼真有点像一个略嫌严厉的老学者”,(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154、154、154页。 )几幢新楼“那不过是老学者们旧式中山装上的几只新口袋而已。一两幢新楼是改变不了一座学院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内有的气质的。”(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 154、154、154页。)在这里,学术狰狞着一位老者的威严面孔循循教诲着每一位学子,学术文化成为神力无边的法器,谁也逃不出它布下的那种神圣的恐怖和威严的阴影。但是,这些青年学子的年龄指数决定了他们生命的律动跳跃在每一根神经的末稍,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了肉,就有了火”。(注:《幻象四种》楠铁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同上, 第214页。)青春的欲火燃烧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就在于他们还从来没有找到过自我。因此,他们的未确定人格在一切可能性中拒绝来自于学术文化的确定性(Specialization)人格塑造。“寻找自我”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第一要义。也正是如此,橡子带着青春的野性闯入大学后的全方位感受就是“像一头被安置在动物园里的野兽一样,又像被移栽到皇家园林的野生植物,不胜其宠,忧郁、孤寂”。(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2页。)
自我失落了。
既成的文化总是以沉积的道德理性在确定性中成立自己的威严,以使得生命在文化的绝对命令中服从一切,这就是一种文明,而学术使道德性在确定性中沉积的文明更加神圣化了。在这里,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人格的未确定性和文化的确定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学术文化结构的老化,已成为八十年代那些高龄名牌院校的老年文化病。徐江在求知的希望中彻底地失望了:“上课时我发现,与文学者有关的几门课实质上并没有教会我一些什么。文学概念课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古典文学则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154、154、154页。)“写作学教师的欣赏过于古怪, 搞得大家全都昏头昏脑。有一次他竟然把一篇拙劣的抄袭鲁迅风格的散文称为他见过的最好的文章,招来同学们许多不满。”(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154、、154、154页。 )在极度的失望中感慨“听课所得几近于零”是徐江不失高校学子风度的温文尔雅的评价。(注:《青春》徐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55、153、154、154、154页。)野舟在《发光的事物:一个独白》中则把评价推向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诗意性调侃:“第一次坐在我的稚气未消的大学同窗之中,我们接受一个成年人的训诫。我所见的那个成年人有一只肥厚的舌头,它在那扇同样肥厚的唇门里为戒律和美德热烈地蠕动。这是一次有趣的布道:一个笨拙的短衣神甫带着浓重的关东口音面对一群为自己的梦想弄得很矜持的羔羊。我忘不了那枚没有骨骼、跳动在陈辞滥调中的舌头。还有我们这群没有骨骼、驯服的羔羊,宛如一幅匠人的月夜图,阴柔而模糊的一轮半月在茫茫黑夜镶嵌的白云中运行。”(注:《发光的事物:一个独白》野舟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87-188页。)
实际上,徐江和野舟言说了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八十年代人文科学领域的阵地前沿,学术和教学都患有老化症,学术和教学始终处在新陈代谢不通畅的病理状态,而这就是学术功底扎实和深厚的文化象征。但无疑,这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神圣负荷者追求的价值取向。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中曾沉思价值和观念积淀在文化中的代际反差:“确实,这些被文化的负荷者建构起来的理想、准则、信仰和规范常常与表现在实际行为中的价值和观念有惊人的差距。”(注:《文化:历史的投影》菲利普·巴格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也正是这些学术文化负荷者用“知识”为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建造了一个孤独而隔膜的学术世界:“多年的学院生活强加给我许许多多有关写作的繁文缛节,其唯一目的无非是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规约这种从来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自由的个人活动。”(注:《巴特尔絮语》高峰枫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穷的覆盖——影响我们一生的人和事》同上,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版,第105页。)
但是无论如何,好奇和空虚点燃了他们的生活欲望和求知欲望,在青春的野性被学术文化压倒的不可调和中,欲望的无可填补性又使他们必然跌入苦闷的深渊。橡子在《穿越冰山》中以数千字的篇幅描述了他进入大学后的苦闷:“苦闷是心灵的渴望无法满足的折光,是一种消磨灵魂的慢性病,它潜伏在发黑的灌木丛中的某个地方,伺机向生命的阵地进攻。最初的兴奋与骚动过去之后,苦闷像阴雨天一样,没有警示,没有预兆,悄悄向我们笼罩而来”,(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3页。)“苦闷,苦闷是我的遗产……苦闷成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状态。”(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22页。)楠铁在《幻象四种》中描写了自己被苦闷和压抑逼进了教堂:“我去缸瓦寺教堂纯粹是为了感受那里的宗教气氛。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每个周日我都去做礼拜,坐在教堂大厅的最后面一排,获得一种俯视众生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牧师的虚伪。”(注:《幻象四种》楠铁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黄祖民主编,同上,第224页。 )吴伟卿在《孤独谈》中以一种孤独感来沉思孤独:“孤独照原意来说应解释为没有人陪伴自己,梭罗却说:孤独是最好的朋友。看似荒谬,仔细推敲,它真正道出世之常情,理之常然。我们有时看书看得太久晕了头,想得太多昏了头,不免升起一种孤独的感觉……”(注:《孤独谈》吴伟卿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膜拜的年龄——最新中国校园随笔选萃》同上,102页。)但是,这无疑是他们的幸运。 因为正是这种苦闷构成了这些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最佳生存状态”,橡子以一首小诗掬起一种难舍的孤独:“就像你从孤独中逃出/走入一种更深的孤独”,(注:《夏夜二重奏》橡子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致命的独唱》橡子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正是这种“苦闷的最佳生存状态”把他们逐出那个孤独而隔膜的学术世界,跌入了更深的孤独——缪斯空间。无疑,这是一种“诗意性逃避”。这就是西川为什么在《预感》一诗中这样诗意地呤咏苦闷:“你又从思想中引来了黑夜/你又从苦闷中引来了风/你把风引进大门/它敲着明镜:我祖先的明镜”。(注:《预感》西川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超越世纪——当代先锋派诗人四十家》同上, 第184页。)“苦闷是文学的象征”,厨川白村在苦闷的冥想中对“文学是怎样发生”的诗意性描叙在这里产生了同频共振。
从心理学的视角来透视这些文学圣徒们,生存状态的失衡必然导致精神状态的缺损,平衡生存状态失衡和修补精神状态缺损的唯一有效选择只能是“诗意性逃避”。自从人类创造了文化以来,人类生命存在的文人要义就是不断地逃避文化的一生,从“逃避”到“再逃避”,这是人类命中注定在逃避的恶性轮回中不可逃避的劫数。唯有“逃避”不可逃避。然而,在八十年代的学院派文学现象中,“逃避”已经失去了这一话语自身的本然意义。“诗意性逃避”在被引入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生命之后,在这里展现为一种“亢奋”式的生存反抗。在法国哲人布莱斯·帕斯卡乐(Blaise Pascal)那里,“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思想”,(注:《思想录》布莱斯·帕斯卡尔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164页。)而学院派文学圣徒的“诗意性逃避”就是为了俘获思想的自由,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正是在“诗意性逃避”的思想自由中找到了自我存在及其价值。实际上,他们在诗意性逃避中就是为了一往深情地寻找自我存在的“诗人”品格。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沉思中,“诗人”也正是在深切地认识到思想和文化的贫困时,先于他人以诗意的沉思发现且领悟了自我存在及其自我存在的价值。
二
在历史上,文化的反抗者从来不是那些自视清高的文化负荷者,而是这些不曾负荷文化也不甚负荷文化的“浅薄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发烧般的“文化热”把所有自视清高的文化负荷者和不甚负荷文化的“浅薄者”统统卷入了文化的反思中。那是一个倘若你要生存就必须反思文化的年代。实际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这场发烧般的文化反思热中却处于文化的断裂状态。在生存的历程中,他们绝然没有体验过“文化大革命”对人从灵魂到肉体所赋予的“血与火”的洗礼,因此,他们也绝然没有像卢新华、张抗抗、遇罗锦、张承志、郑义、北岛等那一代“老三届下放知青”对“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体验,“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传说在他们童年梦中的一场“现代神话”。在他们稚气的心灵上没有烙烫着以葬送一代人的青春和命运所烙刻下的伤痕。历史在精神上从不同情受难者的灵魂,往往那些被苦难的岁月折磨过的生命怎地也无法忘却对若涩的追忆,在学院派文学圣徒的视界中“回忆是衰老的象征”;(注:《纯洁》冰马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62页。)但历史就是这样把卢新华、张抗抗、遇罗锦、张承志、郑义、北岛等无情地推向对已逝去之痛苦的无限回忆之中,这也正是那一代人所拥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在理性的沉思中,这种痛苦的回忆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蹒跚地走完了三个文学驿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终于带着浓重的文化怀旧意识把八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推到了辉煌的极至。
的确,在理论意义上,任何辉煌的极至都意味着走向死亡的终结。在这个理论层面上,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极至也宣告了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1985年,在北京大学“三角地一带出现了几个卖诗的人,嚷嚷着要‘打倒北岛’,号称他们的诗歌是无理论”什么的。(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1页。)严格地讲,北岛不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朦胧诗是新时期东方大陆现代派诗歌的滥觞,但他在创作和理论上没有走向现代派思潮的理论自觉。(注:按:朦胧诗派也有着自己的理论宣言,但徐敬亚、孟浪所言:“朦胧诗至今未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自我主张,这是欠缺的历史。我们自‘三个崛起’中抽摘几段文字、权代其释。”(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敬亚、孟浪、曹长春、吕贵品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再按:“三个崛起”是指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80年5月)、 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81年4月)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83年1月)。)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张扬“打倒北岛”,表现了他们拒斥一切权威的偏激,他们就是要使诗坛陨落霸主的太阳:“诗坛无主,诗歌统一的太阳已经破碎。我们拒绝以任何方式引导别人,同时我们更拒绝被别人引导,我们一度的沉默和容忍只是为了更大的崛起。”(注:《感悟诗派宣言及诗论》马朝阳、蓝轲执笔,见于《校园文化丛书系列之二·走出荒原》马朝阳选编,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1988年印刷(内部交流),第207页。)以北岛为首的朦胧派诗人曾经也是非常偏激的,他们张扬要以自己的朦胧派诗把崇尚现实主义的中国第一号当代大诗人艾青送火葬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见出在八十年代,文学思潮及流派之间的冲突也是非常复杂的。终于,现实主义文学在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张扬的非理性生命冲动中失却了轰动效应。就是这样,一个以理性支撑现实主义文学的时代被另一个以非理性支撑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驱逐到了文化的边缘。
学院派文学的崛起在审美的非理性精神亢奋和意志张扬中带着崛起的理论自觉。学院派文学圣徒的幸运就在于他们涉世未深的浅薄使他们的创作没有烂在生活淤积的泥沼里,像那些在生活淤积的泥沼里泡透、泡烂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寻根作家,一辈子没有理论的自觉而永远被折磨自己的生活写自己;写完生活后,“人到了一定年纪,诗写到一定程度,生命激情和语言激动均被锤炼得一穷二白。”(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27页。)这是橡子在《穿越冰山》中的表达。学院派文学的创作在理论上有着自己的宣言,这些宣言的深层独白就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遁入缪斯空间张扬非理性生命冲动的反抗,学院派文学的理论宣言散见于学院派文学的各种流派之中。严格地讲,学院派文学作为一脉现代派文学思潮其内部又呈现为审美风格不同的诸种流派。让我们来检视一个学院派诗歌。在徐敬亚选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其仅集入的学院派诗歌流派及其理论宣言就有多种。非非主义诗派宣称:“我们要将语言推入非确定化……我们的批评崇尚对这个世界的自由出入。”(注:《非非主义宣言》周伦佑、蓝马克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徐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海上诗群宣称:“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诗歌生命反抗着另一类‘生命’或死物。(我们)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为了真诚……我们可以不择手段。”(注:《海上诗群·艺术自释》孟浪、刘漫流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第70-71页。)莽汉主义诗派宣称:“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注:《莽汉主义·艺术自释》李亚伟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第95页。)星期五诗群宣称:“我们把星期五这个大家都清闲的日子命名于诗群。我们没有自称什么流派,近乎是为了能更自然地窥视出诗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那部分。”(注:《星期五诗群·艺术自释》吕德安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第118页。 按:星期五诗群在《艺术自释》中声称自己没有流派,从星期五诗群的宣言和创作态度来看,他们声称没有流派其实就是一种流派。)极端主义诗派宣称:“(诗)崇尚借代!崇尚极端!反对模式!文明对于它来说不过是一件破衣服……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回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诗歌就是极端。”(注:《极端主义·艺术自释》余刚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 153页。)撒娇派诗人们宣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写诗就是因为好受和不好受……只是因为撒娇诗会上撒了太多的娇,我们才被人称作为撒娇诗人。”(注:《撒娇派·艺术自释》京不特执笔,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175页。 )大学生诗派宣称:“大学生诗派本身仅仅作为一股势力的代号被提出。它具有不确定意义。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它所有的挽救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注:《大学生诗派·艺术自释》尚仲敏执笔, 见于《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上,185页。)
这就是学院派文学特有的“诗加哲学式的反抗”。
结集出版的《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总序》宣称:“诗的本质特征,亦即海德格尔所说的诗的‘神’性,……先锋诗人的诗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也许非得有一次的地壳运动,他们才有可能重见天日。”(注:《最后的金黄色(总序)》黄祖民撰,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阴影里的倾诉》海童著,同上,第1页。 )从理论上透视学院派文学,支撑学院派文学创作理论的阿基米德点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严格地讲,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是栖息于东方大陆高校校园的西方现代派哲学和后现代派哲学的实践者。他们为什么带着炎黄先祖注入娘胎的血腥气呱呱坠地于华夏大陆本人,却如此钟情地一头扑进西方哲学的怀抱?这是一个值得历史为此沉思的文化命题。
涉世未深的浅薄使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代际文化的断裂中所铸造的未确定性人格从来就没有文化负重感,社会的陌生感和历史的距离感又使本土文化传统对他们的人格心理侵蚀不奏效;因此,在人格的深层文化心理上,他们拒绝承受着沉重的文化负重感去沉思民族文化的命运,这种未确定性人格的开放文化心理使他们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文哲学成为可能。十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浩瀚的东方现代宗教偶像塑造运动,它以“一言为天下法”的现代宗教圣语曾剥夺和毁灭了一个民族的思考,从而在民族的灵魂振荡中形成了文化真空。正如当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伯恩斯坦所描述的:“那些不能上大学的人所体验的被遗弃的感觉……1968年下乡的红卫兵普遍感到幻灭,觉得自己被出卖、被利用。”(注:《上山下乡》托马斯·伯恩斯坦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第340页。)“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性终结反而使一个民族在习惯和适应于崇圣性思维中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那批被生活的苦涩泡透、泡烂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因此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而惶惑着,当他们用回忆向旧的国度讨回曾咀嚼过的苦难,用理性去沉思民族的命运时,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却逃避到西方哲学的智慧摇篮中,去捕捉西方智者哲人的思想闪光。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西方智者哲人的思想总是在东方大陆封建黑暗结束的黎明时刻作为一脉曙光,启蒙着这个古老的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西方思想巨匠辞世后的思想余辉曾完成了对这个古老民族的第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启蒙。“文化大革命”终结后的文化真空和思想真空也必然导致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侵入封闭的现代东方大陆从而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和思想的启蒙;这也是世界东西方文化和思想对抗格局解构之际的历史必然趋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也预言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趋势。因此,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带着青春的野性贪婪地拥抱着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克尔凯戈尔、萨特、海德格尔、帕斯卡尔、弗洛伊德、马斯洛、拉康、杰姆逊、德里达、哈贝马斯、利奥塔等这些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哲学家。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地让这些“浅薄者”在逃避学术文化的苦闷中,不自量力地承受起一位救世主的神圣使命,而每一位使命的承受者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只要信步走进学院派作品的文本空间,可以随意睹视到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西方哲学名著成为学派文学圣徒们拥揽的内容,并诗意地闪光在作品文本的字里行间。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根本问题从来就是哲学的问题,正是这些学院派文学圣派们让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诗意地走进自己的文学空间,从而也证明了学院派文学在创作理论上的自觉。所以,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绝对不是依赖于生活的垂怜,让逝去的生活在一种追忆的痛苦中写自己的被动书写者。
标签:文学论文; 学院派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逃避心理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青春论文; 阳光地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