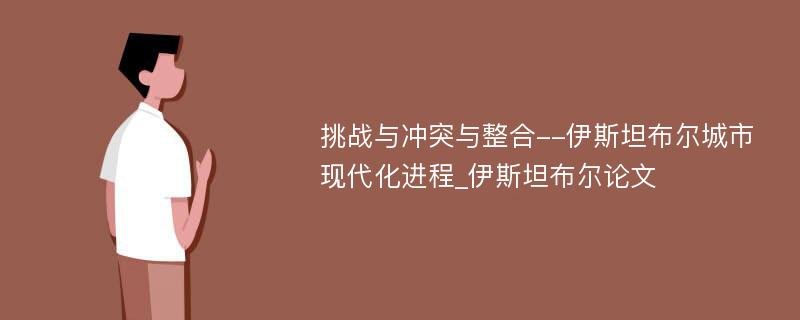
挑战与应战冲突与融合——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坦布尔论文,历程论文,冲突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载体,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开始从传统城市向现代化城市转化。从世界范围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城市现代化起步与资本主义兴起紧密相连,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自然延伸的结果。而土耳其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所以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是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以及伴随而至的西方城市文明撞击之下开始的,这种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缺乏现代化产业基础的“外发型”城市现代化进程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第一,西方现代文明楔入启动和催化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进程,推动城市经济结构转轨,导致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演变。“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② 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下,西方列强打开了奥斯曼帝国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攫取了种种特权,而且使其资本势力步步渗入到帝国传统社会,在将帝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过程中,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先得欧洲现代文明的洗礼。
首先,伊斯坦布尔商业贸易方向和贸易内涵发生变化。西方国家贸易首先冲击伊斯坦布尔。在19世纪上半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贸易方向急剧转变,此前几百年间帝国贸易方向是向东——印度、远东和非洲。在1850年左右奥斯曼贸易转向“工业中心”欧洲。实际上早在18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感到欧洲商业影响,但由于帝国内部商业流通仍占重要地位,所以受到欧洲人正在建立的世界市场影响有限。但是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欧洲商业影响加深。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等地区纺织品出口下降,它们直接被出口原材料所取代,如棉花、亚麻和羊毛等。同时从欧洲进口的羊毛制品、纸、玻璃、五金和其他制造品急剧上升③。外国工业制品涌入,导致当地人生活品改变,使成千上万伊斯坦布尔织布者和其他手工业者失业。
其次,西方现代文明带来了全新经济意识和管理体制,伊斯坦布尔出现新兴商业行业,商业贸易本身发生了质变。1453年苏丹马赫默德二世占领君士坦丁堡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城市成为帝国经济中心。特别是马赫默德二世建立卡帕·卡斯巴扎后,帝国各地的产品汇聚于此。根据1476年的统计,卡帕·卡斯巴扎有各类的商店、仓库、工作间、商队旅馆等3000多个,有许多咖啡屋、茶馆等,共雇佣2万多人④。此后经济进一步发展,17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大约有20个不同的厨师行会,有11个渔夫行会,64种不同的乐器制造行会⑤。17世纪伊斯坦布尔共有735个行会⑥。如此多的行会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经济之繁荣。
伊斯坦布尔的经济虽然繁荣,但其经济模式仍然属于前工业社会,主要经济行业是传统商业和手工业。所有城市人口按照他们手工业和商业类别组成行会,每种职业集中在同一地段,同类的商品集中在同一街道,行会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内部成员的生产和劳动,解决内部的纠纷,规定产品的价格和劳动报酬等等。随着帝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些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现代企业经营手段、会计核算、雇佣制度等等纷纷引进,使城市商业逐渐地实现了从封建自然经济企业向现代资本主义商业企业的转化。1860年,奥斯曼帝国行会被官方取缔。伊斯坦布尔主要计划者强调“市场引导发展”,大公司在土耳其主要工业城市特别是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大不里士等城市的发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⑤。这些新兴的商业行业一开始就具有现代化的性质,把伊斯坦布尔纳入现代商业网络之中。
再次,现代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现代工业、城市市政建设等新兴经济部门出现,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心地位提升。19世纪20年代伊斯坦布尔现代海运出现,1836年跨海大桥建立,1869年电车线路开通,1872年从加拉塔到皮瑞的地铁建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交通系统基本形成。1874年开通了伊斯坦布尔和索菲(Sofia)之间第一条铁路,1888年伊斯坦布尔到维也纳铁路竣工等。这些公路、铁路的修建,电车的引进,增加了伊斯坦布尔作为全国商业中心的意义。特别是1888年,“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之间的铁路竣工,可被看作为是外国思想和企业对城市的征服。(这使)君士坦丁堡成为西方世界的附属物。新观念、新模式现在占统治地位,欧洲企业几乎控制了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与欧洲心脏直接联系便利了交往,同时也强化了已经开始的西化”⑧。同时,新交通工具对这些城市景象有明显现代化影响,在城市主要中心和街道交汇处为旅客和公司雇员建立新式住房成为城市一个新要素,如皮瑞城市大楼等等。现代交通发展加剧了这些城市对欧洲国家的依附,欧洲资本以改善交通和城市设施之方式将城市大部分汽、水、电、贸易和财政控制在手中。与交通运输业相比,通讯业发展更为明显,19世纪末,已经有了一个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布满整个帝国的广大电报通讯网⑨。
随着现代交通运输业、通讯业的发展,城市传统货币连同形式和载体发生变化。1840年,在奥斯曼成立了欧洲式银行——奥斯曼帝国银行,并开始发行纸币,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私人商业银行——奥斯曼民族信用银行。这样到19世纪下半期,国家的初步金融体系建立。外国银行相继设置,并逐渐控制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和金融。这些银行与传统的金融机构相比,更能动员闲置资金、集中信贷、经济结算、调节货币流通,具有钱庄所没有的现代金融功能。银行开出的支票、汇票、信用卡以及各种商业的票据,都可以替代货币的流通,从而对城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现代民族工业在城市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⑩。奥斯曼帝国根据欧洲国家经验将工业化视为国家振兴的主要途径。19世纪40年代早期,国家在伊斯坦布尔的西海岸,狄奥多西城外建立了一些制造业,该区变成了工业圈。在泽廷勃瑞(Zeytinburne)建立一家铸造厂,制造铁管、钢轨、犁、大炮、刀、剑等金属制品。在巴克瑞科(Bak Irkoy)区,建立汽船厂,纺织厂、铸造厂和蒸汽机车间。19世纪70年代后,外国人和少数民族社团(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纷纷投资办厂,食品加工、造纸、木材、制陶等企业在伊斯坦布尔得到发展。1908年革命后,工业得到政府更多鼓励,如进口机器免除关税。1913年《奖励工业法》和1915年的修正案的施行,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发展,1913年对6个主要工业据点的调查显示,共有269个工业企业(开工的242个),拥有工人6000人,在这些企业中15%的资本属于土耳其人,20%的属于亚美尼亚人,5%是犹太人,10%是外国人(11)。在1913年对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部分统计显示,在工厂的工人有17,000名使用电力(12)。根据1915年调查,土耳其总共只有282个企业,主要是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这些企业中的工人总数约为17,000人,这些企业中的75%集中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13)。现代工业在城市兴起,不仅改变着伊斯坦布尔生产方式,而且为城市成为国家现代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
“从工业化开始,服务业的发展紧紧跟随工业化的发展,有时甚至超越工业化的发展”(14),“几乎在任何地方,每当工业化开始加快步伐,就感到住房短缺”(15),这种现象在伊斯坦布尔表现更加明显。工业的发展对建筑业的急切呼唤使这一产业迅猛发展。伊斯坦布尔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大规模建筑活动,从外国引进一种新的住房——排房(Rowhouse)以服务于小商人、手工业者、工人和低收入的官僚。随着这些新兴产业部门发展,伊斯坦布尔人口大幅增长,1800年人口为40万,1860年为50万,1924年达到110万(16),在1840—1900年间,大约有10万外国人到达伊斯坦布尔,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商贸条约而受益的西方投资者和贸易商(17)。
总之,上述这些新经济部门不仅深刻地冲击着伊斯坦布尔传统城市经济结构及与之相呼应行会等经济制度,促使它们迅速解体,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它城市和广大农村,并由此推动着整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
第二,现代观念的传入改变着伊斯坦布尔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外力楔入,欧学之风吹拂了帝国的思想文化界,冲击着奥斯曼帝国多年的伊斯兰教文化积淀。一方面,一些外国的文化机构、教会、学者等致力于向帝国传播西方价值观和各种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并引进、介绍和研究西学。1727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第一所土耳其文印刷所,1831年7月,创办了第一个土耳其语言的报纸《大事概览》,19世纪60年代初,独立经营的报业出现并迅速发展,《协商报》、《君士坦丁堡杂志》、《自由报》等纷纷出现。1827年,建立医学院,1831—1834年,建立帝国音乐学院和军事科学院,1858年,建立第一所女子中学,1869年,建立女子职业学校。特别是1859年成立的作为文官训练中心的米尔基耶(mülkiye)学院,1861年有学生33人,1885年增加到395人,这个作为土耳其新成立的现代高等教育单位中的第一所纯文科学校,甚至在米哈德朝代后期的压力下,也始终保持为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中心,同时也是培养新思潮的一座温床(18)。1855年,电报技术传到伊斯坦布尔等。西方的法典、管理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引进,一方面使乌莱玛和传统的知识阶层过时,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社会改变而建立的新工作部门中找到工作,军队和官僚体系的现代化为某些集团开放了新的机会(19)。
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具有现代特征的各种新思潮,如民族主义思潮、科技救国思潮、现代法制思潮、革命思潮等在伊斯坦布尔兴起,新的社会观念逐渐形成,如开放观念、竞争观念、改革观念、效益观念等各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观念越来越多地被伊斯坦布尔人所接受,并改变了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开明官吏和军官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发展现代化成为这些人追求之目标。这样,现代化取向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发展城市现代化之内在驱动力。虽然这种转变主要发生在城市部分人之中,但其程度之剧烈、影响之深远,堪称思想革命。
首先是世界观的转变。长期以来伊斯兰教一向把基督教看成是未臻成熟的宗教,耶稣基督只是一位略有所悟的早期先知;世界的真谛是由穆罕默德所揭示的,伊斯兰文化因此高于基督教文化。奥斯曼帝国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奥斯曼官方编年史中,国家与伊斯兰精神完全等同:帝国的领土就是“伊斯兰的领土”,帝国的君王是“伊斯兰的巴低沙(国王)”,帝国的军队就是“伊斯兰的士兵”,帝国的宗教领袖就是“伊斯兰的谢伊赫(教长)”(20)。这样帝国的统治者将新思想拒之门外,“它不仅没有任何发明,甚至对别人的发明也无动于衷。当欧洲的科学技术正以破竹之势向前发展的时候,奥斯曼人却满足于自己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停留在中古时代他们祖先们的水平。甚至他们的武装部队也只是慢条斯理地、缺乏效率地跟在他们欧洲敌人的先进技术的屁股后面跑”(21)。但一系列战争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定,使奥斯曼在世界上地位一落千丈。在此状况下,许多仁人志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文明作出了积极回应与思考,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重要社会思潮,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科技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他们对发展现代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相信通过自由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能打断王朝专制主义、宗教教条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锁链。他们认为帝国要成为一个现代的、有力的和发展的国家,就需要激进的社会改革,需要按照西方工业化的模式重建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道路。正如1908年七月革命的英雄尼亚齐所说:“一种如醉如痴的爱国主义,使我的心——一颗赤子之心准备奔向革命。”(22)
其次,个人主义发展。个人主义伴随着西方国家的侵入而至。“欧洲人的想法,随着欧洲的武器和技术以及带进这些武器与技术的人们而传入,于是遂对旧秩序造成不小的冲击。”(23) 正如美国著名的文明史学家威尔·杜兰所说:“在工业社会里,工业革命助长了个人主义,无论男女、成人、儿童都要离开家庭,靠个人的能力去闯世界,他们获得的报酬也都是个别的。个人主义又使父权逐步丧失旧日的权威;个人主义也带来了妇女的解放”,“总之旧的农业社会道德开始崩溃”(24)。在奥斯曼,经济的个人主义是从19世纪引进货币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结果。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使许多的农民脱离了土地,结果为寻找工作而大量移民到城市,而这些到城市的人,他们把它以前的社会团体连根拔起,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在其中他们以前的习惯、社会准则和信仰仅仅部分地得到认可。这种由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方言、不同的历史的个人和家庭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动荡、易变的环境。在其中旧的组织或毁灭或被新的取代。城市改变进程伴随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个人主义的出现(25)。移民在城市特别伊斯坦布尔,每天所追逐的经济活动显示了趋向个人主义而不是背离个人主义的趋势。个人主义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冲破传统文化对人民思想的禁锢,有利于城市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第三,现代市政建立,西方城市建筑风格涌现,改变了伊斯坦布尔城市面貌,促进城市建设向现代化发展。
首先,现代市政初现。在奥斯曼帝国负责城市管理和司法的是至高无上的哈里发或苏丹的代表,他们拥有除了参加宗教法庭审判外的不受限制的责任和特权。在其之下存在着一整套严格的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省督、法官、市场监督员和公共道德监督员、社团谢赫和少数民族社团谢赫、行会谢赫等。不存在市政制度(26)。
随着殖民主义入侵,欧洲市政制度也开始逐步地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城市中。1720年,法国人大卫(在皈依伊斯兰后改名为哲切克),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个消防队。这是此后19世纪和20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城市服务改革中的第一桩(27)。在《坦齐马特宪章》颁布后,奥斯曼首都成为欧式市政设置实验场所和19世纪西式规划运用场所。根据欧洲模式形成的法典被通过,司法管理权从卡迪中转移到新的欧式部中。1854年在城市外国人居住区建立起第一个市政自治机关,设有正规警察和消防队——这些部门以前由土耳其警卫军掌握(28)。新政府有一个选举的委员会,分享一定职能和权力,任命市长。1855年5月政府组建了城市秩序委员会,委员会认为,所有主要国家首都城市的建设是完美的,而伊斯坦布尔城市急需装饰、规划、扩路、改进街灯和引进新建筑方式。城市委员会12名成员,由政府从伊斯坦布尔不同的种族、阶级和行会中挑选,并得到帝国的统治者任命。1865年成立道路改进委员会(简称I·T·K)以处理建筑法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青年土耳其政府在首都建立了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市政组织,执行更广泛的城市建筑项目。在其过程中,改革了警察、消防队、公共交通设施和公用事业。“青年土耳其人在给土耳其提供宪制政府上失败了,然而他们给了伊斯坦布尔排水系统。”(29) 在青年土耳其统治期间,西式的市政概念成为城市机构的一部分,从这一时期到共和国时代。虽然其影响是局部的和分散的,但是1838—1908年改革功绩不可磨灭,它对伊斯坦布尔城市机构和未来发展趋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0)。1913年建立了由选举成员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为创造西式城市管理开辟了一条路。但是这些改变并没有导致任何重要权力下放到城市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新市政的设置是政府努力改进地方服务,特别是伊斯坦布尔现代区的服务必然手段。它们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完全依赖中央政府。同样选举的地方委员会既没有政治独立也没有财政独立,它们是中央政府代表。尽管如此,这些机构与伊斯坦布尔城市传统封建管理体制相比,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市政管理上具有先进性,不仅刷新了城市行政制度的内容,为城市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大大促进了城市发展,而且为此后市政体制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改变了城市布局。传统的伊斯坦布尔城市空间组织与伊斯兰教要求一致,“信仰的首要地位明显地表现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31)。马赫默德二世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改圣索菲亚大教堂为圣索菲亚大清真寺,不久又建立著名法迪赫(Fatih)大清真寺和卡帕·卡斯巴扎,城市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同时根据伊斯兰教的法律,私人的财产权高于公共财产权,在不妨碍其他人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侵犯公共财产的方式确保私人财产。这导致城市大量死胡同的出现和街道的狭窄弯曲。
伴随着西方文明楔入,伊斯坦布尔的市容开始发生转变。1836年穆斯特法·瑞斯特帕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城市的最初规划。他认为街道网的规划应该追求数学和几何学的规则,用笔直、宽阔的干、要道取代已有的曲径。1839年政府聘请德国专家哈玛斯·冯·莫提克(Helmuth Von Moltke)改进伊斯坦布尔的街道网。莫提克首先起草了城市规划,并用砖瓦结构取代木头建筑,这样石砖建筑成为美化帝国首都的象征(32)。
莫提克规划的主要贡献是在首都历史上首次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其主要目的是建立连接城市中心——行政区和商业区到老拜占庭大门的宽阔街道,以便为伊斯坦布尔提供一个通畅的交通网。莫提克规划修建5条主要干道:即:从巴布·胡玛蕴(Bab- 1 Humayu)到阿科萨瑞街道;从阿科萨瑞到图比卡颇(Topkap1)街道,从拜占庭广场到法迪赫区的街道;从沿马尔马拉海岸到卡德加(Kadirga)与耶迪库勒(Yedikule)的街道;从埃米努努(Eminonu)到阿尤布的街道。道路的宽窄依其所处的位置而订,路边植树,完全消除死胡同,在清真寺或其他纪念性的建筑前面建立大众广场。
莫提克规划拉开了伊斯坦布尔街道改造的序幕。大维齐任命的7人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建议,该建议把城市划分为14个区并选皮瑞(Pera)、加拉塔和图费恩(Tophne)组成第六区,做为城市改革实验区。然后把从第六区实验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其他13个区。第六区被选为示范区,是“因为第六区已经存在许多有价值的房地产和许多欧式建筑,这些房屋的主人绝大多数到过其他国家首都,理解其价值,所以改革将首先在第六区开始”(33)。第六区有钱人是市容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如皮瑞的主要大街安装街灯,清扫街道等。
1868年伊斯坦布尔市长瑟佛·艾芬迪(Server Efendi)制订了城市总体规划(A General Plan),即:把改革扩大到整个城市;对伊斯坦布尔历史遗产进行保护;修建从道玛巴哈斯清真寺到塔巴斯(Tabatas)沿海岸线公路(1856年7月,苏丹移到道玛巴哈斯,使该条街道的规划成为迫切的事);对金角湾北部进行改造,拓宽从图费恩到奥地利大使馆的街道。根据瑟佛·艾芬的总体规划,首先首都被划分为14个区,其管理控制在市政府之下,然而把改革扩展到整个城市是不容易的。实际上,除了加拉塔之外,仅有两个区被建立,一个王子岛区,另一个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岸的塔瑞巴(Taraby)区,然而这两个区也为第六区的延伸,因为它们是城市里的欧洲人常去之地。其次,拆除圣索菲亚清真寺和苏里曼一世清真寺周围的木头房屋,对迪范幼鲁斯(Divanyoluis)地区进行拓宽。伴随着迪范幼鲁斯拓展工作的完成,一些不规则街区被取消。规划后的迪范幼鲁斯由宽直的载车大道和人行道组成,这使瑟佛·易芬德高兴地惊呼“就像在欧洲的城市”。再次,在金角湾两边建立了通衢大道,清理了纪念物周围的建筑,建立巨大的广场。最后,道路改进委员会积极帮助居民用砖重建他们的住房和商店,并建立砖和水泥工厂,向重建住房的人提供廉价材料。
1877年政府模仿巴黎把城市划分为20个区,一年后减少为10个。1888年,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在首都建立钟塔,其中一座钟塔作为“公民艺术”建立在图费恩广场,它是西化和进步的象征,表示时间与宗教的分离。1878—1908年,城市进一步发展,拥有了自来水公司和伊斯坦布尔煤气局。
通过这些努力,伊斯坦布尔部分的迷宫似街区得到整齐的规划,但是涉及的范围并不大,整齐化仅限于局部地区,尽管19世纪欧式建筑出现在伊斯坦布尔半岛不同部分,但并不能影响全部居民的生活模式。在伊斯坦布尔半岛,生活模式仍保持原样。
城市现代化最明显之地,则在金角湾以北地区,这里不仅成为城市中最欧化地区,而且在城市中地位大大提高。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首都的主要建筑清真寺、巴扎和宫殿多集中在伊斯坦布尔这边。到19世纪末这种状况改变,金角湾的北边布满了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风格上与伊斯坦布尔相抗衡的建筑。
皮瑞位于加拉塔城墙内北部山上,该区欧化开始于1838年。其主要居民为欧洲人,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皮瑞出现了许多欧式的旅馆,1865年帝国授权给奥斯曼帝国旅馆公司代表詹姆士·米瑟瑞(James Missirie),要他建立和经营欧式旅馆以便为外国旅游者和居民提供方便住所。但旅馆只能建立在皮瑞、布幼科德里(Buyukdere)、幼斯库达(Uskudar)和王子岛。19世纪中期,皮瑞的人口密度达到饱和,于是帝国在1848年命令在潘噶特(Pangaltl)建立一个272,800平方米的居民区,在居民区修建10条主要大街,这样安装有自来水和排水系统的新街道模式在城市出现。到1864年石头建筑取代所有木头住房,并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拥有与欧洲城市一样的整齐外观。1876年希腊商人建立了皮瑞城市大楼,它是一个甚至巴黎本身也为之骄傲的不朽之作。人们能自豪地说皮瑞因它生色,她不仅是业主的骄傲,也使整个城市自豪,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建筑新时代的开始(34)。格德·瑞街区的建立使皮瑞进一步西化,“明亮和令人愉快的,它是欧洲殖民的‘西部的终点(West End)’,街区的生活是舒适的和优雅的,路的两边布满了英国和法国的旅店、精致的咖啡屋和灯光闪闪的商店、戏剧院、外国的领事馆、俱乐部和不同国家的大使馆”(35)。随着这些建筑而来的是西方生活方式,格德·瑞商业贸易繁荣,百货商店、仓库储满了欧洲各地生产的奢侈品,这些商品不仅被外国居民所消耗,而且帝国的上层阶级包括宫廷本身也对之有极大的热情。
随着19世纪40年代人口的增长和皮瑞欧化,城墙成为皮瑞与加拉塔之间的严重障碍。1863年帝国命令拆除城墙,“随着城墙的推倒,加拉塔将得到一个‘现代面貌(Physionomie Moderne)’”(36)。同时,居民点扩展到加拉塔背后的陡坡上,并在高原上形成了佩腊居民区,后来加拉塔和佩腊一起成为今天的贝约卢区。在原城墙线上建立了新公路。同年2月,穆罕默德大街附近的建筑被推倒,该街从加拉塔“最脏的地方”变成“最美丽的地方之一”。1868年第六区管理局为自己建立总部“第六区大厦”,其本身是当时巴黎模式的反映。这样,加拉塔成为城市最现代化地区——办公大楼、银行、剧院、旅店、百货大楼和高层的建筑大量出现在该区。这些建筑与奥斯曼的圆顶和尖塔纪念物形成鲜明的对比。
虽然加拉塔与皮瑞的发展更多呈现出殖民地色彩,但是它们毕竟为城市增添了若干新的因素,与传统城市相比,其起进步与发展是十分明显的。总之,在西方文明作用下,伊斯坦布尔成为帝国最先走向现代化的城市。它们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国际上许多研究城市机构的统计资料证明,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是以大规模发展为特征的——50万人以上的城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至5万人的城市效益高出40%以上)(37),使现代工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部门急剧增长,使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人口增加。大量移民的到来,给城市带来丰富而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行各业发展所需要的不同层次的人才,造就了伊斯坦布尔人衰我兴的发展契机。
二
西方文明的传播虽然对伊斯坦布尔向现代化迈进起到了启动和催化作用,但是由于这种传播是伴随着血与火强行而至的,是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单向度的冲击。对伊斯坦布尔而言,对西方文明它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这样西方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
第一,改变了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性质,使其成为殖民地的象征。
首先,从城市布局上看,形成城市二元结构——即传统的伊斯坦布尔和现代的加拉塔。从行政隶属关系上看,外国人在这些城市享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司法权、开发权、征税权等等。大多数穆斯林感到与欧洲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相比,得到的很少。“除了殖民者,谁因此得利……我在各地发现部分的迹象:一些中间人——犹太人、叙利亚——黎巴嫩人、科普特人和一些利用进口贸易的穆斯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帕夏;获得机械化和建立资本主义庄园的地主”,“商业、金融和法律给帝国的异族人口一个根据自己才能重新分配的机会,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是不平等的;基督教徒是优越的,他们得到土耳其的金钱和土地,并在法院证明他们有权这样做。外国的垄断获利是最多的,在其后的是土著的基督教徒,但是并不是奥斯曼人。”(38)
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改革使加拉塔作为一个国际商业的中心繁荣,得到更多的现代化外表,奥斯曼首都的两重性形成——传统的伊斯坦布尔和现代的加拉塔。1879年的资料显示,“在伊斯坦布尔和加拉塔、皮瑞之间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建筑和秩序上。在伊斯坦布尔,石砖建筑仅仅有300幢,且大多结构简单,而在加拉塔、皮瑞则有几千幢,绝大部分是价值高的和有装饰的。许多被认为是文明象征的东西出现在皮瑞,但在伊斯坦布尔没有。在文明的时代,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仍是黑的,而加拉塔和皮瑞有汽灯”。“皮瑞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第一流的东西,商业大王、各种代表团的官员、外国海军军官、大使馆装备的马车,土耳其的男人在理发店的窗口羡慕地观看理发,妇女则惊奇地徘徊在女帽商的陈列柜前。”(39) 在伊斯坦布尔半岛,生活方式仍是旧有的模式。而加拉塔现在的居民则完全模仿欧洲生活模式。
其次,阻碍了土耳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城市现代化受阻。由于列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等手段把伊斯坦布尔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边缘与依附地位,所以当伊斯坦布尔的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之后,除了面对国内传统势力的压制外,还要遭遇外国资本这个劲敌,不仅享受不到低税率等优惠条件,反而承担各种负担,其结果使民族企业生产成本高,产品销路不畅,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从而使土耳其本身的现代工商业发展十分艰难。1838年条约是……对奥斯曼工业不利的……现在比利时的商人在土耳其付5%的商品税……而土耳其商人的出口税或从土耳其一个省运输到另一个省要付12%的税(40)。在这样的情况下,薄弱的土耳其工业,显然是不可能同不受任何限制而大量输入的外国工业品竞争(41)。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交通网的发展,特别是铁路的发展有利于欧洲商品渗透到帝国各个角落,进一步威胁到地方制造业。1881年《穆哈列姆法令》使帝国收入的一切重要来源都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同时外国人几乎都不把资本投入到帝国加工制造业中,因为他们并不关心在帝国是否建立起工业企业。结果伊斯坦布尔现代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1863年关于伊斯坦布尔的报告指出:“严格地说仅有一个工厂超越手工业阶段:即面粉工厂,有6台蒸汽机”。1868年政府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此前30—40年间,伊斯坦布尔的织布机从2750台下降为25台,锦缎机从350台下降为4台;丝绸机从60台下降为8台。”(42) 不仅如此,仅有的工业完全依赖欧洲技术和专家,正如比利时的工人所说:“你不能称它为土耳其布——它仅仅是通过欧洲的机械,欧洲以外的原料和欧洲熟练工人在土耳其生产的布。”(43) 民族资本主义是城市向现代化迈进的主要推动力,它的发展状态直接影响着市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加重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空间的不合理分布。
随着以进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新城市中心出现,改变了伊斯坦布尔以清真寺和巴扎为中心的城市格局。随着加拉塔与皮瑞的西化,许多人开始跨过金角湾去新区,这些北移之人多为西化的上层穆斯林,当奥斯曼帝国宫廷在1856年从图比卡颇迁到道玛巴哈斯然后再到伊迪兹,进一步靠近博斯普鲁斯,上层穆斯林及其居住区自然围绕新宫廷而发展起来。
上层家庭大批迁移导致传统区居民的几乎全部为无产阶级,城市传统的中心变成大批贫穷农村移民的接收地,绝大部分的农村移民在此寻找他们在城市中的第一个住房(44)。当城市中心向新区转移的时候,旧中心开始边缘化,其经济、社会组织也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现代管理功能和经济活动的外围。巴扎的地位大大下降,大批的零售商从传统的巴扎迁出到新公路的周围,那里有工厂、政府大楼、学校等。穿越城市老区部分的公路不仅破坏了老区的建筑,而且也破坏了该区社会的内聚力。在巴扎过去的严格职业区分现已大为松弛,尤其是在这些经过西化的城市,新的商业区出现在新大街的两旁,特别是在城市中心。城市中心转移的另一个后果是清真寺失去了其重要性。中心与边缘两重性空间分化出现后,以下的因素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建筑材料价格的攀升,建筑工业的不断发展,移民中熟练与非熟练工人之间鸿沟的加大,银行与金融组织扶持中高等收入的集团。此后空间分化与社会分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
城市现代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伴随着现代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生活习俗多层次、多侧面、立体交叉的一种发展。它既是工业化的结果,又是工业化的延伸。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城市现代化过程却展现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点。
首先,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进程打上了殖民地性质的烙印。跨入现代化后,伊斯坦布尔的经济命脉始终操纵在外国殖民者手中,其经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表现在经营倾向上,外资投资的半数以上用于商业掠夺性事业,即进出口和与其相关的运输、银行等事业,工矿企业的投资却很少。表现在城市建设方面,加强了城市建设的不合理性。在19世纪,与欧洲联系加强增加了伊斯坦布尔对巨大内陆地区经济控制。外国资本通过伊斯坦布尔流入帝国其他地方。欧洲商人和他们代理人大量集中在忙碌都市。到19世纪末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世界贸易商、政客、拥有特权的猎取者和外国公司管理人员活动中心。伊斯坦布尔成为欧洲前哨,在这里帝国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控制奥斯曼帝国的经济(45)。到一战前夕,伊斯坦布尔是农村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孤岛,是正在走向衰落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进度也受到外资制约,这些投资迅速转化为垄断伊斯坦布尔经济力量,并以此控制帝国经济命脉。
其次,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过程是非自然的发展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现代化往往是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的发展顺序,而伊斯坦布尔所经历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和经验不是前者的继续,而是违反西方模式,被视为由于局部或不完整地向城市现代化过渡而出现的一种畸形发展。它的城市现代化是以商贸为主,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在城市经济结构上造成了商强工弱的局面,在其顺序上是先城市化后工业化。
帝国主义在商业掠夺和开办大批现代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伊斯坦布尔把奥斯曼广大城镇与乡村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不仅造成了国家乡村自然经济解体,而且造成了乡村对帝国主义经济的依赖性。从自然经济瓦解中游离出来大量人口,虽然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城市巨额资金被掠至国外和民族资本弱小等先天不足,使其容纳不了大量的农村移民,因而大部分移民缺乏转化成商品化劳动力可能,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失业消费大军,造成了伊斯坦布尔城市人口过剩的畸形结构。
再次,市民心理态势呈现二重性特点。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同步进行,城市居民心态与现代化过程也基本相宜。而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则是被动的、突进的,是在其国民缺乏现代化意识的背景下开始的,因而国民心态失调特别严重。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心理与现代意识,传统道德与商品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的交织中,无论是伊斯坦布尔官僚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对西方文明都经历了由拒绝到接受的过程。如1876年,从加拉塔到皮瑞地下缆索铁道的建设曾遭到反对,被轻蔑地称为“耗子洞”(46),所有这些可视为拒绝的表现。而随后大批奥斯曼的官僚、贵族、富商等建立西式别墅,创办新式学校、医院,着西装、看歌剧、说英语等则为接受的表征。英国大使斯塔福·坎尼(Stratford Canning)对皮瑞着装变化评价道:现在刚回来之人注意到这种最显著变化,几年时间,已经看不见头巾……每种被雇佣的人都带着红帽,穿长套裤,黑长筒靴和钉有简单纽扣的红色或蓝色大氅。没有金线刺绣、没有珠宝、没有皮制的长外衣。以上这些过程,可视为西方物质文明渗入伊斯坦布尔市民生活的一个小小缩影。这实际上反映了市民文化心理状态的现代化过程。
最后,伊斯坦布尔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外发性特点。由于伊斯坦布尔现代化过程具有外发性特点,因而这一历史进程本身就充满着特殊的双重交叉之态势。表现为一方面西方文明启动并促进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现代化,另一方面逐渐觉醒的奥斯曼先进人士也在寻找一条本民族现代化之路。同时由于这些大城市现代化进程与农村是脱节的,因而它们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反映奥斯曼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它既不能把奥斯曼农业从封建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奥斯曼跨入工业国的行列,也不可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西方的城市竞争。
由于自身无力冲破封建社会的枷锁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伊斯坦布尔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文明的撞击下开始的,这种外发性的现代化历程不仅使城市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首先,国家独立是城市现代化的前提。奥斯曼帝国虽然早在17世纪末或更早的时候接触到西方文明,开始了从军事、技术等方面学习西方的尝试,并在国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并没有使帝国免遭殖民者的奴役。随着国家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伊斯坦布尔虽出现了现代企业,现代化的城市设施,但是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工业化基地。它仅仅是殖民者原料掠夺和商品输出的中转站。“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在政治方面,殖民地的大城市根本没有竞争力”(47)。
其次,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城市化是人类的共同规律,“人类既没有力量阻挡它向前发展,也没有能力人为地使它超越必经的各个阶段,谁要违背历史这一历史趋势,就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48)。城市现代化曾给伊斯坦布尔经济带来了活力,带来了信息、人才、劳动力、资金,增强了它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现代化使该城市成为国内外企业、商品、人才竞争的舞台,而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从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一种刺激和发酵的效应,能够孕育培养出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由于城市现代化是在没有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现的,所以也给城市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和耻辱。
再次,城市现代化要走自己的道路。对城市进行现代化的扩建也是城市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伊斯坦布尔由于在改建的过程中盲目地模仿欧洲都市,结果出现了一个城市新旧两个世界的二元结构,为城市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综上所述,伊斯坦布尔在外力楔入作用下,踏上了城市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不仅城市管理体制、城市市容、内部格局发生了剧变,而且城市人口空前增长,经济功能加强,城市在国内外的地位上升。但是也应该看到,城市的现代化是伴随着殖民国家侵略开始的,所以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它们与资本主义宗主国联系要多于与本国内地联系,不仅不能把农业从封建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其发展也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现代化水平;不仅展现出与资本主义城市现代化不同的特征,而且也不能成为与西方城市相匹配的竞争对手。
注释:
① 本文为笔者主持的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07BSS010)阶段性成果之一。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③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纽约1982年版,第150—151页。
④ 约翰·弗雷利:《帝国城市伊斯坦布尔》(Johe Freely,Istanbul the Imperial City),伦敦1996年版,第185页、356页。
⑤ 加布略·巴尔:《中东的农民与市民》(Gabriel Baer,Fellan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伦敦1988年版,第152页。
⑥ 约翰·弗雷利:《帝国城市伊斯坦布尔》,第230页。
⑦ 迈克尔·丹尼尔逊·鲁森·凯斯:《快速城市化政策》(Michael N.Danielson Rusen Keles,The Polities of Rapid Urbanization),纽约1986年版,第15页。
⑧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Zeynep Celik,the Remaking of Istanbul,Portrait of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华盛顿1986年版,第102页。
⑨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7—198页。
⑩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57页。
(11) 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8页。
(12)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55—156页。
(13) 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史》,第130页。
(14) 卡治·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6页。
(15) 卡治·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121页。
(16)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01页。
(17)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38页。
(18)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191页。
(18)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0页。
(20)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1页。
(21)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8—39页。
(22)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07页。
(23) 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书之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第408页。
(24) 许启贤主编:《世界文明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25) 玛达尼颇·阿里:《德黑兰:一个首都的发展》,第91页。
(26) 参见车效梅:《中东中世纪伊斯兰城市行政体系》,《学海》2006年第2期。
(27) 伯纳德·路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53页。
(28) 约翰·弗雷利:《帝国城市伊斯坦布尔》,第267—268页。
(29)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32页。
(30)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47—48页。
(31) 斯蒂法诺·比安卡:《阿拉伯世界的城市构造:过去与现在》,(Stefano Bianca,Urban Form,in the Arab World:Past and Present),纽约2000年版,第25—26页。
(32)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50页。
(33)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45页。
(34)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136页。
(35)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133页。
(36)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70页。
(37) 张鸿雁:《论中国21世纪初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优先战略选择》,《南京社会科》2000年第10期。
(38)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2页。
(38)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158页。
(40)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33页。
(41) 安·菲·米列尔:《土耳其现代简史》,第19页。
(42) 查尔斯·伊萨维:《北非与中东经济史》,第151—152页。
(43) 雷奈普·塞里克:《伊斯坦布尔的重造——19世纪奥斯曼城市的素描》,第35页。
(44) 布拉克、劳力斯:《变化的中东城市》(G.H.Blake and R.I.Lawless,The Changing Middle Eastern City),哈米斯1980年版,第181页。
(45) 迈克尔·丹尼尔逊·鲁森·凯斯:《快速城市化政策》,第55页。
(46) 约翰·弗雷利:《帝国城市伊斯坦布尔》,第286页。
(47) 安德鲁·韦伯斯:《发展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48) 林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