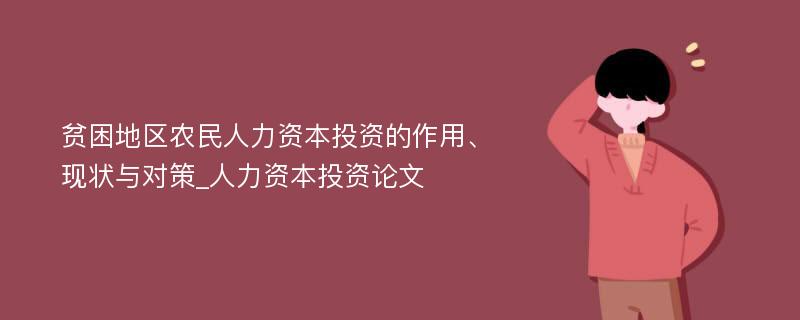
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作用、现状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农户论文,对策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农业领域还是非农领域,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户收入都具有显著影响。在农业领域,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有利于增进农民自身的技能而且可以改善农民对投入品的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1,2]。而据Vijverberg[3]的研究,当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时,无论他是处在自我雇佣状态还是处在出卖劳动挣取工资的状态,教育投资的回报都非常显著。学者们对中国农户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Dennis Tao Yang与Mark Yuying An[4]通过对中国农户的实证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结论,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有利于改善农户要素配置效率的观点。李伟[5]利用中国23个贫困县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教育和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的研究结论是:农户的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对贫困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可见,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改善农户(包括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状况,学术界对这种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农户收入来自多种要素贡献,在广大贫困地区,同其他要素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贫困地区投资极端欠缺的情况之下,到底应该以一种怎样的优先序来合理安排农产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但是迄今为止,从笔者所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笔者选题的初衷正在于此。
笔者以地处湖南西部的1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实证研究对象。所指的湖南西部是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和怀化市三个市(州),该地区总共24个县(市)中有国家级贫困县10个,省级贫困县8个,其中大部分地处武陵山区,少数民族聚集,是全国著名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贫困研究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传统的生产函数通常只考虑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数量对收入的影响,所以函数式一般被简单地写成Y=f(K,L)的形式。由于分析的对象是农户,而农户所拥有的耕地资源状况对收入产生着重要影响,在贫困地区尤为如此。所以,应该把反映农户耕地资源状况的变量(F)引入其中。同时,还在函数式中加入人力资本投资变量(H)用以考察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户收入的作用。因此,进入到模型分析中的生产函数被写成Y=f(F,K,L,H)的形式。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两个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α+β[,1]F+β[,2]K+β[,3]L+β[,4]H+ε(1)
Y=α′+β[,1]′F+β[,2]′K+β[,3]′L+β[,4]′M+β[,5]′T+β[,6]E+ε′(2)
其中:Y为农户收入变量,用农户人均纯收入表示;F为耕地资源变量,用农户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表示;K为资本变量,用农户人均拥有的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表示;L为劳动力数量变量,用农户整半劳动力数表示;H为人力资本投资变量,代表农户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H=Σ(M+T+E);M为农户人均医疗保健支出;T为农户人均交通通讯支出;E为农户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ε和ε′分别为模型(1)、(2)的残差项。其他未提及的为待估计参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精确地计量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是困难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十分宽泛,广义地理解,凡是有利于个人能力提高的任何投资都可以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二是即便将视野局限于狭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即只考虑家庭在正规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以及迁移方面的投资,也会由于资料获取的困难而无法对之进行完整、精确的计量。因此,以住户调查资料中的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的合计数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粗略的估算。
设计模型(1)的用意在于比较人力资本投资与非人力资本投入要素对农户收入的相对重要程度。模型(2)是模型(1)的扩展式,实际上是将变量H进一步分解为M、T和E三个独立变量,以期达到比较三种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之目的。
(二)样本与数据
笔者将实证研究的区域锁定在地处湖南西部的10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别是:湘西自治州的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张家界市的桑植县;怀化市的沅陵县和通道县。使用数据来源于湖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贫困监测住户资料(2003)。这10个县共计950个样本农户的构成为:普通农户859户,个体工商户26户,乡村干部户50户,种养业大户15户。在样本农户中,家庭常住人口中有汉族人口的家庭占22.2%,全为少数民族人口的家庭占77.8%。
(三)模型的分析结果
运用SPSS10.0版软件对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的作用
模型1
模型2
解释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标准化回归系数
常数项668.619**(9.780) 666.032**(9.950)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 3477.371**(8.714)0.246
3572.638**(9.184)
0.253
人均拥有固定资产/元
0.256**(7.420)0.209
.194**(5.604)
0.159
家庭劳动力人数/人 24.240(1.399)0.039
17.199(1.016)
0.028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元
.523**(5.715)
0.157
人均交通通讯支出/元 2.339**(10.369)
0.295
人均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元
.668**(7.509)
0.206
人均人力资本投资/元
.772**(12.788)0.361
调整的R[2] 0.2610.298
F值
84.644** 68.215**
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值;**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统计检验。
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对于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每增加1元可以使人均纯收入增加0.772元。在四个解释变量中,人力资本投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最大(0.361),这表明同其他三个要素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作用更大。可见,对贫困地区农户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理应居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模型(2)的估计结果清晰地显示,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都有利于农户人均收入的增加。但在三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中,交通通讯支出的效果更加明显,支出每增加1元可以使人均纯收入增加2.339元。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的作用居于第二位,这方面的支出每增加1元可以使人均纯收入增加0.668元。相对而言,医疗保健支出的作用最小,这方面的支出每增加1元只能使人均纯收入增加0.523元。
三、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
(一)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及其比较
表2数据显示,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极端低下,人均年支出仅为251.84元,只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20.71%。与之对应的是,在人均消费性支出中,人均食品支出比例高达59.54%。说明这里农户的绝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解决温饱问题,因而用于个人发展的人力资本支出就显得十分不足了。总体而言,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支出水平要远低于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也比城镇家庭要低得多。大致规律是,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则人力资本支出也越多,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也越高。湖南城乡家庭的人力资本支出水平及其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与全国水平大体相当。从表2可以看出,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从全国看,城镇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支出为1958.4元,是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的7.8倍;尽管全国农户的人均人力资本支出水平也不高,只有442.78元,但是也相当于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的1.8倍,绝对数要高出190.9元。
表2 不同类型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比较 元/年
全国 湖南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
城镇家庭 农户 城镇家庭 农户
人均收入
770324766959
2398 1318
人均消费性支出6029.881834.31
5575 2068.74 1215.99
2271.84 848.35 1985.881086.11724.1
(37.67%) (46.24%) (35.62%) (52.5%)
(59.54%)
其中:人均食品支出1958.4 442.78 1823.28 469.98
251.84
(32.47%) (24.13%) (32.7%) (22.71%) (20.71%)
①括号中数据表示该项支出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例;②关于人均收入数据的说明:城镇家庭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户采用人均纯收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和湖南省贫困监测住户资料(2003)整理得到。
(二)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及其比较
表3数据显示,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结构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在总量为251.84元的人力资本投资中,有144.19元用于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所占比例高达57.25%,在所有类型的家庭中为最高;而用于交通通讯的支出只有48.41元,仅占19.22%,在所有类型的家庭中为最低;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为59.24元,所占比例为23.52%,与全国农户的平均水平十分接近。总体而言,人力资本支出结构的城乡差异并没有象它们的投资水平那样显著,除了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以外,大致都遵从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居第一位,交通通讯支出居第二位,医疗保健支出居第三位的规律。但是也可以看出,不管是全国还是湖南,农户的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都要高于城镇家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保险服务而农民没有。农户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比例则明显低于城镇家庭,在湖南西部贫困地区这种结构差异表现十分突出,这里的农户交通通讯支出所占比例仅为19.22%,比全国城镇家庭低出近13个百分点,比全国农户的平均水平也要低10个百分点。
表3 不同类型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元/年
人均人力资本支出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文化教育娱乐服务
全国城镇家庭
1958.4430.08 21.96%
626.0431.97%902.2846.07%
农户 442.78103.94 23.47%
128.5329.03%210.3147.50%
湖南城镇家庭 1823.28343.68 18.85%
596.0432.69%883.5648.46%
农户 469.98102.81 21.88%
118.5725.23%248.6 52.90%
湖南西部贫困县农户 251.84 59.24 23.52%48.4119.22%144.1957.25%
以百分比表示的数据为该项支出占人力资本支出的比例。数据来源:同上表。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户收入产生着显著影响。在耕地、生产性固定资本、劳动力数量以及人力资本投资这四种农户最主要的投入要素中,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居于首位。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同城镇家庭相比还是同其它地区的农户相比,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都存在明显差距。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异常缺乏,农民收入与人力资本投资陷入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当前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关键是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尽快制定有利于快速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发展战略。
在三种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当中,交通通讯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大。如果按照理性人假设来推断,这部分支出应该在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中占据较大的份额。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贫困地区农户的交通通讯支出所占比例要远低于文化教育支出以及医疗保健支出所占的比例。横向比较的结果也显示,无论是同城镇家庭相比还是同其他地区的农户相比,贫困地区农户的交通通讯支出所占比例明显偏低。可见,对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结构进行调整也势在必行。在短期内无力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现实条件下,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同样也有助于农民增收进而达到摆脱贫困的目的。
(二)对策建议
(1)建立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零付费制”。“零付费制”的含义不同于现在的“义务教育制”。虽然“义务教育制”最根本的特征是强制性、免费性和平等性[6],但是免费并不等于“零付费”。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但是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向学生收取书杂费。所以现行的“义务教育制”是一种学生仍然要交书杂费的教育制度,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付费教育制”。从笔者到湖南西部贫困县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村小学、初中生大致每个学期都要缴纳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费用。学生的教育支出成为贫困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对农户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着强烈的“挤出效应”。笔者所提出的“零付费制”是指农村中、小学生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除了要负担自己的衣食住行费用以外无须其它任何费用支付的教育制度。通过建立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零付费制”,一方面可以达到从总体上提升贫困地区农村人口素质的目标,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户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人力资本投资领域,从而引导农户不断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2)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交通费“半价制”。既然在三种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当中交通通讯支出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作用最大,那么就有理由把农户如何才能扩大这方面的支出作为重大研究课题而予以特别关注。在我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共同特点就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特点决定了贫困地区农民的迁移行为有着高昂的成本。这种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费用,即交通费。近年来由于票价一涨再涨,加之路途遥远,使得农民外出的直接费用成倍增长,贫困农民虽然对外部的世界心存向往,但终因收入有限而无力成行。二是间接费用,主要指农民外出的机会成本。由于贫困地区农户多以农业经营为主,且绝大部分都从事小规模的家庭畜牧业,所以外出时间过长会直接影响到家庭经营收入。由于贫困地区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比如山高路远、汽车班次很少等,使得农民即便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县城都要花上2~3天的时间,更别说到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了。所以,贫困地区农民外出的机会成本也很高。高昂的成本制约着贫困地区农民的外出行为,抹杀了农民走出大山的动机,这种状况在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的体现就是交通通讯支出的极端低下。那么怎样才能切实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改进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上的这种不合理性呢?笔者以为,除了政府要一如既往地加强乡村公路建设,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激发贫困地区农民增加交通支出的热情,而推行农村贫困人口交通费“半价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对特殊群体实行交通费“半价制”在我国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所以,农村贫困人口交通费“半价制”在现实中应该具备可操作性。当然,具体实施起来也可能遇到一些障碍,比如农村贫困人口的身份鉴别、农村个体客运的抵制行为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