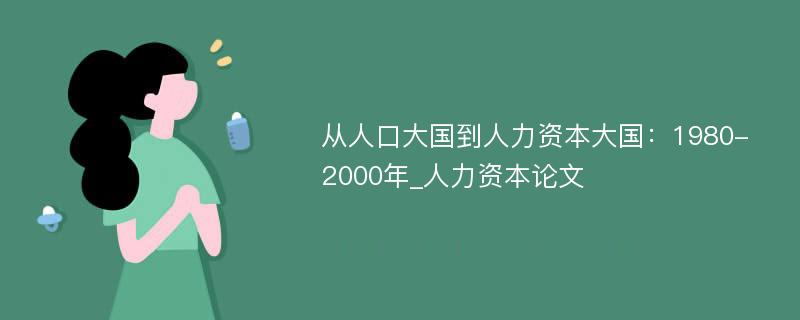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来源(World Bank,1997)。过去20年(1980~2000年)里,中国不仅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5.4倍,而且总人力资本存量(指15~64岁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数乘积)翻了一番,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也由17.5%提高到25%,在八类国家战略资源中最具竞争优势资源。中国总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受惠于“计划生育红利”和“教育投资红利,”其中15~64岁人口增长因素为42%,平均受教育年数增长因素为54%;在各类受教育水平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6.5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1985年增长了1.8倍(见表1)。中国已经从世界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这是中国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最具优势和最重要的战略资产(胡鞍钢、门洪华,2002)。
表1 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增长指数 万人
1982年 1990年2000年 增长指数 年增长率
(1982=100) (%)
文盲人口 2317718178849236.6 -5.4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 359864253245247
125.7 1.3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 180942664043093
238.3 4.9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 6709 9147 14068
209.7 4.2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610 1601 4563748.011.8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73191074818631
254.6 5.3
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 781.7(1985) 1080.9 2165.1
277.0(1985=100) 7.0
注:计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2)》,第34页、第168页。
一、人力资本的定义与计算
人力资本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的,并经贝克尔(Becheru Gary,1964)等人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80年代卢卡斯(Lucus,1988)和罗默(Romer,1990)将人力资源的理论引入新增长理论之中,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源一样是生产的要素,由于知识产品和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对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投入可以持续提高一国的长期增长率。
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World Bank,2000a)提出了新的发展分析框架,将影响增长和福利的要素分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三类,其中物质资本是通过增长影响福利,而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增长影响福利,其自身就是福利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就等于增加人民的福利。
人力资本是指人身上所具有的教育、文化及其健康的投资,既包括私人投资或家庭投资,也包括国家投资或社会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对教育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学校培训和再培训、学习项目、成人教育),使人们获得教育的机会和能力被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决定性作用。此外教育还有“溢出效应”,例如,教育对知识及其在全社会扩散的贡献(A.P.瑟尔沃,2001)。
早期的研究是以测量不同国家组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Psacharopoulos and Ariagada,1986;Lau et al.,1991;Nehru et al.,1995;Kyriakou,1992),试图利用入学率估计平均受教育年限;Barro和Lee(1993、1996、2000)估计了1960~2000年间跨国平均五年的入学率分布,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用来构建和计算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他们的计算包括142个国家,其中109个国家有1960~2000年间每五年的数据。采用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是目前国际上衡量人力资本比较好的指标,能够用于国际比较,但其缺陷是无法反映各国教育质量。Mulligan和Xavier-Sala-I-Martin(1995)计算了1940年以来美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一组各州人力资本指数,发现过去60年美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了1倍。
国内外学者就中国人力资本计算做了有益的探讨(安格斯·麦迪森,1997、1999)。按初等教育为1,中等教育为1.4,高等教育为2的方法,估算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70年,1978年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这相当于1913年德国和英国的教育水平,低于1950年日本的教育水平。我们曾在研究中国及各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来源时(王绍光、胡鞍钢,2000),利用全国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估算全国及各地区1982和1995年的人力资本存量,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978~1995年全国GDP增长来源中,人力资本增长率为2.12%,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5.4%(注:根据麦迪森(Maddison,1970)的研究,22个发展中国家1950~1965年人力资本平均增长率为1.94%,对经济增长率(5.55%)的贡献率为35%。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率高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而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低于这些国家,这是由于中国其他要素增长率及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比较高的缘故。);各地区人力资本增长率在1.4%~3.4%之间,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为4.0~8.3%。刘宗超和吕永龙(1999)也计算了1964、1982和1990年全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沈利生、朱运法(1999)采用投入法对全国人力资本进行了计算,李忠民(1999)采用产出法研究了人力资本。李春波(2001)采用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实际受教育年限两种方法,计算了1949~2000年全国人力资本和1964~1995年各地区的人力资本,同时计算了各类人力资本的地区差异;利用增长账户分析方法,按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了1979~1998年各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将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14~0.2个百分点。蔡昉等(2002)从内生增长理论探讨了具有外部的人力资本禀赋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他们发现在中国各地区之间,越是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在随后的增长中越是倾向于有较高的速度。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的总人力资本及其增长情况。这里我们用人均人力资本与可利用的劳动人口的乘积来表示总人力资本,用人口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受教育年数愈多,劳动力工作技能就愈熟练,劳动生产率就愈容易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本更易于吸收和使用从发达国家引进和扩散的新技术(Barro and Lee,2000)。用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与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或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的乘积来表示。构成一国总人力资本存量用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6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12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9年+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6年;总人力资本=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需要说明的是,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包括了65岁及以上者,这部分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因此,本文的计算偏于保守估计。
笔者根据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人口受教育年数,来分析人力资本增长情况;为了便于国际比较,笔者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和美国哈佛大学Barro和Lee的全球教育数据库。
二、中国用了20年总人力资本增长翻一番
改革以来,中国总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快速增长。如果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并作相应的国际比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文盲人口减少了2/3,其中总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1982年全国文盲人口为23177万人,到2000年降至8490万人,减少了63.4%,平均每年减少5.4%(见表1)。2000年文盲人口比例为6.7%,与1982年相比累计下降16.1个百分点(见表2)。即使考虑到官方统计数字的水分因素,中国成人文盲率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最低的,既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文盲率的平均水平,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
第二,2000年小学人口比1982年增长了25.7%,平均每年增长1.3%,占总人口比例变化不大,仍占15岁以上人口的1/3强;初中人口增长了138%,平均每年增长4.9%,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上升幅度最大,提高了17个百分点(见表2)。
第三,高中人口增长了110%,平均每年增长4.2%,占15岁以上人口比例提高了4.5个百分点,达到11.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相当于1982年的7.2倍,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增长了3个百分点,为3.6%;两者合计为18631万人,占15岁以上人口的14.7%,而大学人口的比例相当于1960年世界平均水平(3.3%)和198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1%),低于南亚国家(3.7%),高于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2.2%),是世界上大学人口比例相当低下的国家之一(见表4)。
表2 1982~2000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文化程度构成与平均受教育年数 %
1982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82~2000年
变化量
贡献年数
文盲人口22.8 15.9 12.0 6.7-16.1
-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35.4 37.2 38.4 35.7 0.30.018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17.8 23.3 27.3 34.017.01.53
高中文化程度人口 6.6 8.0 8.3 11.14.5 0.540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0.6 1.4 2.0
3.63.0 0.480
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4.615.51 6.08 7.11
2.5 2.5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6页。
表3 1960~2000年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国际比较
%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变化量
世界(109个国家) 36.431.429.5
26.426.124.2-12.2
发展中国家(73个) 64.156.149.7
41.738.334.4-29.7
发达国家(23个)
6.1 5.1 4.84.5 3.8 3.7 -2.4
转型国家(13个)
4.5 3.1 2.81.7 2.1 2.2 -2.3
东亚/太平洋(10个)52.5
35.422.6
26.422.519.8-32.7
中国
22.8
15.912.0 6.7-16.1
南亚(7个) 74.3
69.366.9
55.251.2 45.2
-29.1
中东/北非(11个) 81.0
69.855.5
42.836.0 32.0
-49.0
撒哈拉非洲(22个) 68.9
63.856.8
45.944.5 42.8
-26.1
拉丁美洲(23个)37.9
31.223.8
17.215.8 14.6
-23.3
资料来源:Robert J.Barro and Jang-Wha Lee,2000;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6页。
第四,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明显提高。我们估计,195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年,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2.22年,1982年为4.61年,2000年提高到7.11年(见表2),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66年)和东亚太平洋地区(6.71年),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13年),但仍低于发达国家(9.76年)和经济转型国家(9.68年)。20年前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文化程度还低于世界109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东亚太平洋地区水平(见表5)。如果仅计算中国城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在9~10年之间,即使是城镇下岗工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也在9.8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国的原因,外资企业能够在中国城市找到文化素质较高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国比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这表明过去20年,不仅中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而且他们的人力资本也明显提高;反过来也有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营养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和精神文明程度。
第五,中国各类人才大幅度增长但占全国总人口或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还比较低。其中,大专以上人口增长了6.5倍,2000年达到4563万人(见表1);到2000年底,全国已授予600万人学士学位、54万多人硕士学位、6.5万多人博士学位(李岚清,2002),分别相当于全国总人口比重的千分之五、万分之四和十万分之五;专业技术人员(指国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比1985年增长了1.8倍,2000年达到216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0%(见表1),远高于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2%)和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2.5%)。根据国家人事部提供的最新数据,到2000年底,全国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达到63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0%),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8.9%)。其中,党政干部585.7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780.1万人,专业技术人员4100万人,其他人员894.2万人。根据“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到2005年,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专业技术职称的各类人员将达到835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3%左右;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400万人(《人民日报》,2002)。
表4 1960~2000年15岁以上人口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国际比较 %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世界(109个国家)
3.3 5.0 7.5 10.311.3
12.6
发展中国家(73个) 0.8 1.7 3.1 4.6 5.76.5
发达国家(23个)6.7 9.915.8 22.424.8
28.1
转型国家(13个)3.8 6.3 7.7 11.211.4
13.9
东亚/太平洋(10个)1.6 2.7 5.0 7.4 10.0
11.7
中国-- 0.6 1.4 2.03.6
南亚(7个)0.4 1.2 2.1 2.9 3.33.7
中东/北非(11个) 0.9 1.7 3.6 5.6 7.28.8
撒哈拉非洲(22个) 0.2 0.8 0.6 1.3 2.12.2
拉丁美洲(23个)
1.8 2.5 5.2 8.2 9.5
10.9
资料来源:Robert J.Barro and Jang-Wha Lee,2000;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6页。
表5 1960~2000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国际比较
年
1960年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增长指数
世界(109个国家) 4.64
5.16
5.92
6.43
6.44
6.661.44
发展中国家(73个) 2.05
2.67
3.57
4.42
4.79
5.132.34
发达国家(23个)
7.06
7.56
8.86
9.19
9.52
9.761.38
转型国家(13个)
7.42
8.47
8.90
9.97
9.45
9.681.30
东亚/太平洋(10个)2.83 3.80
5.10
5.84
6.35
6.712.37
中国- - 4.76
5.85
6.11
6.351.33
中国*
- - 4.61** 5.51
6.08
7.111.54
南亚(7个)1.51
2.05
2.97
3.85
4.16
4.573.03
中东/北非(11个) 1.23
2.07
3.29
4.38
4.98
5.444.42
撒哈拉非洲(22个) 1.74
2.07
2.39
3.14
3.39
3.522.02
拉丁美洲(23个)
3.30
3.82
4.43
5.32
5.74
6.061.84
注:增长指数是以1960年为基年;中国增长指数是以1980年为基年。
*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6页;**为1982年数据。
资料来源:Robert J.Barro and Jang-Wha Lee,2000。
中国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规模,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人口大国,具有总量大的特点,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迅速建立公平公正竞争的、可自由流动的、统一的人才市场,才能将这些极其丰富的人才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但是,不同高等教育学历人口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占总人口或总就业人数比重还十分低下,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明显不足,仍需要大力培养人才,积极吸引人才,充分利用人才。
第六,中国总人力资本存量20年翻了一番,实现了教育跨越式发展。总人力资本存量由1982年的28.82亿人年提高到2000年63.14亿人年,提高了1.19倍,平均年增长率为4.45%。中国总人力资本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印度增长率(4.69%),明显高于全世界的年平均增长率(2.58%),大大高于日本(1.06%)、美国(0.99%)、俄罗斯(0.82%)。中国总人力资本存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0年的24.0%。这相当于印度的1.95倍,美国的2.79倍,俄罗斯的5.91倍,日本的7.34倍(见表7)。200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45844万人,劳动年龄人口3.2亿人,平均受教育年数约为10年,总人力资本为32亿人年,约占全国总数的50.7%,也不同程度大于上述国家。这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也是总人力资本增长最快的国家,美国需要花60年时间长增长了1倍,而中国只花了20年时间。
中国人力资本形成的长期记录给国际著名经济史学者留下深刻印象(安格斯·麦迪森,1997、1999)。1820~1992年日本和美国人均人口资本增加了10倍,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34%和1.36%,而中国1952~1995年人均人力资本增加了5.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39%,明显高于日本和美国的人力资本增长率。这反映了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追赶效应,而且在教育方面也具有追赶效应。实际上这两种追赶效应具有互补性。正如麦迪森(1999)所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生产潜力的开发,健康状况的改进又进一步促进潜力的发挥。
三、促进中国人力资本增长的因素
过去2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之所以翻了一番,从直接原因看,受惠于计划生育政策和发展教育投资的两大“红利”。
首先,中国15~64岁人口大幅度增长,比1982年增长了42%,平均年增长率为1.97%;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82年的61.5%提高到2000年70.15%。这是中国政府从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促进人口转变的结果,即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与1982年相比,0~14岁人口比例由33.6%下降为2000年的22.89%。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政策作用,按照1982年少儿人口的比例计算,到2000年中国就会多出1.36亿少儿人口,这相当于现有的中小学校在校生数的2/3,在总教育经费不变的情况下,等于减少每个少儿人口的平均教育投资。换言之,少儿人口比重下降,也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
其次,中国人口各类教育水平不同程度的提高,反映在人均人力资本提高了54%,平均年增长率为1.54%(见表6),增长幅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4%)及发达国家(38%)和转型国家(30%)(见表7)。在1982~2000年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提高的2.50年中,小学教育几乎无贡献,初中教育增长的贡献最大,为61.2%,高中教育增长的贡献为21.6%,高等教育增长的贡献为15.4%。
从构成人力资本增长的基础看,一是经济增长(注:安格斯·麦迪森(1997)在总结了1820年以来各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过程的经验之后认为,各国教育发展取决于多种原因,如文化、娱乐和经济的原因,但经济的作用是主要的。)。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居世界前列,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本增长。我们发现,中国GDP与各类人力资本指标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注:国际经验表明,各国在人力资本形成和增长实绩方面显示了很强的相关性(A.P.瑟尔沃,2001:61)。),以GDP增长指数作为因变量的人力资本函数方程具有较高的相关系数,方程t检验值十分显著(见表8)。按各类教育增长弹性系数看,1978~1998年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0.187个百分点,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0.203百分点,总人力资本存量增长0.327个百分点。我们还发现,程度越高的教育的增长弹性越高。例如,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初等人力资本存量增长0.281个百分点;中等人力资本存量增长0.472个百分点;高等人力资本存量增长0.652个百分点。这表明当中国基本实现人口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对中等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二是物质资本投入与增长。人力资本增长与物质资本增长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作用的,不是相互分离而是相互促进的。这是因为物质资本的增长需要产生更高的人力资本需求,同时也为人力资本增长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样,人力资本增长通常伴随物质资本增长,也会提高物质资本投入的回报率和其他效益。我们根据1978~1998年全国资本存量、人力资本与GDP计算了三者之间的协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它们具有极高的相关性(见表9)。由于从1980年起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时期,高资本投入(如较高的国内投资率)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增长、物质资本投入增长,以及人力资本形成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互补作用。
表6 1982~200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增长
平均增长率
增长指数
1982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1982=1)
15~16岁人口(万人) 62 517 76 260 81393
887981.971.420
占总人口比例(%)
61.566.767.270.15 - -
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4.615.516.087.11 2.441.54
总人力资本(亿人年) 28.82
42.02
49.49
63.14 4.45
2.191
注: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6页的数据计算。
表7 1975~1999年五大国总人力资本及占世界比重
1975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9年
15~64岁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
中国 22.2 22.6 23.3 23.6 23.2 22.4
印度 14.9 15.2 15.4 15.7 15.9 16.2
日本 3.27 3.03 2.83 2.67 2.48 2.30
俄罗斯3.93 3.65 3.35 3.09 2.81 2.69
美国 5.99 5.80 5.44 5.10 4.88 4.76
五国合计 50.3 50.3 50.3 50.1 49.2 48.4
平均受教育年数(年)
中国 4.38 4.61 4.94 5.51 6.08 7.11
印度 2.70 3.27 3.64 4.10 4.52 5.06
日本 7.78 8.51 8.74 8.96 9.23 9.47
俄罗斯
9.27 9.23 9.77 10.5 9.77 10.0
美国 9.69 11.9 11.6 11.7 11.9 12.11
世界 5.54 5.92 6.17 6.43 6.44 6.66
总人力资本(10亿人年)
中国 2.25 2.70 3.35 4.17 4.95 6.00
印度 0.9341.29 1.62 2.06 2.52 3.08
日本 0.59 0.67 0.72 0.77 0.804 0.819
俄罗斯
0.8440.8740.9511.04 0.964 1.02
美国 1.35 1.79 1.83 1.92 2.04 2.16
世界 12.8 15.4 17.9 20.7 22.6 25.0
占世界比重(%)
中国 17.5 17.6 18.7 20.2 21.9 24.0
印度 7.27 8.40 9.06 9.98 11.1 12.3
日本 4.60 4.36 4.01 3.73 3.55 3.27
俄罗斯
6.57 5.69 5.30 5.05 4.26 4.06
美国 10.5 11.6 10.2 9.30 9.01 8.60
五国合计 46.5 47.7 47.2 48.2 49.8 52.2
注:根据Barro and Lee,2000;World Bank,2001计算。
表8 中国GDP增长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教育增长弹性系数)
Ln edu1 Ln edu2 Ln human Ln human1 Ln human2 Ln human3
1952~1998年
Ln(GDP) 0.456
0.6910.632
1.028
0.662
(17.906)(20.085) (18.236)
(22.428)
(28.731)
R[2]0.8770.900
1952~1978年
Ln(GDP) 0.7321.8921.0541.467 0.717
(12.343)(14.347) (13.935)
(15.090)
(7.875)
R[2] 0.8590.892
0.8660.901 0.713
1978~1998年
Ln(GDP)0.1870.2030.3270.2810.472 0.652
(23.376) (19.205) (32.451) (30.143) (31.188)(67.785)
R[2] 0.966 0.9510.9820.9800.981 0.996
注:括号内为t检验值。edu1为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edu2为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human为总人力资本存量;human1为初等人力资本存量;human2为中等人力资本存量;human3为高等人力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年数、人力资本存量引自胡鞍钢、李春波,2001。
表9 GDP、资本存量和总人力资本的协相关系数矩阵
GDP 资本存量
总人力资本
GDP 1.000
0.9980.991
资本存量 - 1.0000.988
人力资本 -- 1.000
注:样本期为1978~1998年。GDP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0)》,第53页。资本存量数据引自邹至庄:《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载于李善同主编:《快速增长没有终结——国内外专家看中国经济增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总人力资本存量引自胡鞍钢、李春波,2001。
四、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政策含义
总人力资本增长对提高中国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1998年,由于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对综合国力提高方面总人力资本约占1/5 (21.0%),居经济资源(指按PPP计算的GDP)、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和净FDl)之后排第三位(胡鞍钢、门洪华,2002)。
未来20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就是全面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这也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由于总人力资本构成是指15~64岁人口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因此,未来提高中国总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是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5~64岁人口将呈低速增长,占总人口比重变化不大。过去20年由于提高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同,各类教育文化人口的贡献率不同(见表2)。从今后来看,主要是不断提高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贡献率,这就要求在进一步提高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速发展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本科、专科教育,使未来时期新生的教育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程度至少在9年以上,相当多数人口在12年以上,相当部分人口在15年以上,随着较低文化程度人口不断退出劳动年龄,可以使占70%左右总人口的15~64岁人口平均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如果再考虑到15~64岁人口在完成各类正规教育后,有条件、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各类非正规教育,各种培训等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实际平均受文化教育年限和质量还会更高,从而极大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城市化进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注:教育发展和交通运输设施发展,这本身就成为人口流动过程的强有力的推进因素,它们会扩大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数量(A.P.瑟尔沃,2001:60)。)。这表明中国有可能造就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胡鞍钢,2002)。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制定好以下长期性政策。
第一,打破长期以来非义务教育阶段国有单位的行政垄断(供给管制、价格管制)积极促进竞争机制,激励家庭、受教育者、企业、各类社会组织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私人与社会的教育培训投资来源与比例。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用世界上比例极低的公共教育支出,承办世界人口规模最大、门类齐全的教育,除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外,对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不必“包打天下”、“包治天下”,需要引进新思路、采取新机制,大幅度提高私人与社会投资比例。
目前,中国城市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已经成为重要的私人消费领域。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性支出比1996年提高了1倍,教育消费支出增长弹性高达1.55,即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人均教育消费支出提高1.55个百分点。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性支出比重由1996年的5.2%上升为2001年的8.1%(国家统计局,2002)。这表明城市居民具有相当大的教育消费需求潜力及其相当高的增长率,并成为未来时期居民消费持续不衰的新热点。这反映了教育消费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在日益灵活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也是居民家庭、个人未来获取较高私人回报率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只要打破非教育义务阶段的各类垄断格局,鼓励各类教育机构竞争,就会吸引大量私人投资和社会投资。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几年高等院校大规模扩招就是顺应了这一消费需求发展趋势,使消费需求者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只要是有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有消费需求意愿就有可能购买和实现这一需求,大幅度降低了消费的“门槛”,也使各类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了发展的空间。
第二,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前提下,调整投入结构,提高教育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国家需进一步减少对高等教育占总经费补贴比例和调整补贴结构,补贴对象应区别对待,对那些具有竞争性、私人收益率高的方面少补贴,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对那些具有非竞争性、社会收益高、外部性强的方面予以补贴。
对国家和私人收益率高的专业(MBA、外语类、临床医学,以及计算机、自动化、土木建筑等工程类专业)主要由私人付费购买教育服务,放松对这些专业教育的价格管制,允许鼓励各类学校在这些专业方面开展公开竞争,刺激和扩大供给,也会抑制这些专业的学费上涨过快,同时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其教育质量公开评价,并向社会及时提供各类信息,使消费者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信息。而对那些外部性较强(社会效率较高而私人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专业(基础理论学科、部分人文学和社会学科、师范教育等),则需要对此进行补贴。
国家应对高等学校的基础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因特网、基本教学辅助设施)予以投资补贴,允许民办高等学校申请与竞争这些政府补贴;同时也应鼓励各类学校将这些设施向社会开放,以扩大其规模效益和提高使用效率,并采取低费和付费制,以补偿基本的运行成本。国家应对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予以必要的财政援助,减少对东部发达地区补贴的比例,应该实行以地方投资为主,鼓励这些学校为地方发展服务。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的相对均衡配置,鼓励与支持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合作、各类资源共享,以提高他们在不同专业教师、培养人才、科研合作等方面的互补性。
第三,加快建立各类人才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提高各类人力资本的生产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要素,因此,改革的最终的直接目的是要解放人、发展人的能力,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也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胡鞍钢,1995)。现行的户藉制度,传统的就业制度,僵化的隔绝的城乡与地区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是束缚十几亿中国人民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制性障碍。首先,需要打破城乡格局,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允许并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劳动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部门转移。其次,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机制,建立单位与人才和劳动力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采用更为灵活的合约制、合同制,改革目前人事档案制度,建立集其社会身份、安全、人事、个人税收和纳税等信息的新型档案制度。再次,进一步鼓励人才和劳动力国际间交流、流动,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人力资源,例如,高薪聘任制、绿卡制等,吸引和采取灵活性政策,聘用海外高级人才。
总之,中国人民是勤劳、优秀的人民,一旦创造了公开竞争、公正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专业人才市场,形成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制度环境,那么在改革中被释放的生产力——十几亿人民将继续创造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