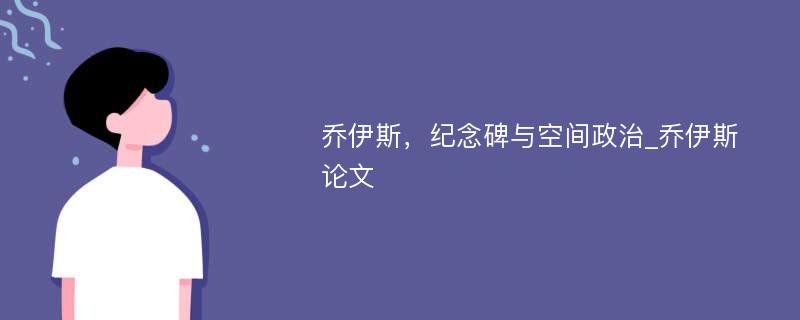
乔伊斯、纪念碑与空间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念碑论文,政治论文,乔伊斯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修订:2015-10-23;本刊修订:2016-01-08 中图分类号:I56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6)02-0140-06 “纪念碑”(monument)一词的拉丁字根是monumentum,意为提醒、告诫。奥地利艺术史学家阿洛伊斯·里格尔(Alois Riegl)区分了纪念碑的两种类型,即“意图性纪念碑”和“非意图性纪念碑”。前者在建立之初即具有明确的纪念意图和纪念价值,后者的历史价值则伴随着时间的累积,其意义来自后人的阐释(Gubser 2005:463)。这种分类既扩大了“纪念碑”的外延,又暗示着其意义的不稳定性和建构性。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能指,纪念碑并没有确定的所指,总是含有多重意义,且意义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是临时性的,处于持续的替代变换之中(Lefebvre 1991:222)。因此,纪念碑这一重要的城市意象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运作的腹地和不同意识形态博弈的场所。本文选取纪念碑意象来探讨乔伊斯作品中的空间政治,并挖掘其中所表现的城市空间的多重矛盾性:一方面,由官方机构主导的建筑景观是殖民统治的外在表征;另一方面,城市又是一个主观自由空间,充斥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反抗着单一权力的垄断性霸权。 1.纪念碑与空间政治 自20世纪空间转向以来,空间便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空洞的背景和既定的存在,而是被纳入广泛的社会化进程中,成为权力错综交汇的异质性场所。对于空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其中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研究影响很大。列斐伏尔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历史建构,“(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Lefebvre 1991:26)。因此,空间不再是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意义上的僵化术语,而被赋予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属性。列斐伏尔曾明确指出:“空间并非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客体,相反,它总是政治的、策略性的。”(Lefebvre 2009:170)以此为基础,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位一体的空间辩证法,三者分别对应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空间实践是指特定社会空间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发生的方式,这种具体化的空间被描述为感知的空间,它直接可感,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准确测量与描绘;空间表征是概念化的认知空间,是科学家、城市规划者等社会精英阶层按一定的原则就城市的规划设计与建筑所构想的空间,是由控制性、条理性的言语符号系统构建的统治性空间,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再现:表征空间是“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是以日常实践为主的历验性空间,它既是被动体验的屈从的空间,又是想象寻求改变和占有的空间,蕴含着有悖于统治秩序的反抗力量,具有无限可能。(Lefebvre 1991:38-39)。 在列斐伏尔看来,社会空间是一个由众多网络组成的巨大结构,而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正是网络的连接点。纪念碑作为空间被生产出来,其目的就是被阅读。它具有内在的可读性,但这种可读性造成的是一种错视画的艺术效果,因此更富欺骗性、虚假性和想象性(Lefebvre 1991:143)。纪念碑作为典型的“菲勒斯”(phallus)意象,就其性质来说,可以是政治的、军事的乃至法西斯主义的,但它将权力意志巧妙地隐匿于符号和表象之下。表面看来,纪念碑传达的是浅显易懂的信息,表现的是集体意志和集体思想,但实际上其显性文本之下潜藏着隐性文本。列斐伏尔指出,统治阶级将压制因素移花接木,使之披上歌功颂德的外衣,意在敦促人们达成共识。因此,纪念碑往往体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集体记忆潜移默化的塑造和控制。同时,纪念碑以空间凝滞时间,形成与时间无关的假象,它将暴力和死亡等消极印记抹除,代之以一种沉静的力量和笃定的姿态。但在纪念碑不朽与永恒的表象下隐匿着的是权力意志,是掌控的欲望,因为只有权力意志能够——或者确切地说,自信能够——超越死亡。纪念碑否定了死亡空间,将其转化为作为身体延伸物的生存空间,而这一转化与(政治)权力、知识等因素息息相关(Lefebvre 1991:221-222)。 之所以选择纪念碑作为城市意象的代表,是因为纪念碑是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典型形式,同时都柏林又是一座纪念碑城市。据统计,截至1922年,都柏林的各式纪念碑至少有34座(Whelan 2002:513)。在乔伊斯作品中,死者、往昔与历史并未真正逝去,它们的幽灵依然徘徊在爱尔兰上空,成为斯蒂芬·代达勒斯(Stephen Dedalus)所谓的必须逃离的“罗网”(Joyce 1992:191)。 2.纳尔逊纪念塔与帝国意识形态 19世纪中期以前,都柏林的纪念碑大多是为纪念与帝国相关的人物而建立的,且通常占据城市重要位置并伴有隆重揭幕仪式,而爱尔兰人的形象则被排除在城市景观之外:“都柏林和爱尔兰爱国主义的联系仅限于断头台和绞刑架。那里的确矗立着雕像和圆柱,但并不是为了纪念这片土地的儿孙。被顶礼膜拜的是外国的君主和英雄……爱尔兰人注定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象征着其臣服地位的纪念碑。”(Whelan 2002:512)因此,纪念碑成为父权力量的空间化象征,作为空间表征,它体现的是殖民帝国的政治逻辑和秩序准则。 在都柏林众多纪念碑中,乔伊斯着墨最多的是纳尔逊纪念塔,该塔是1808-1809年间为纪念英国著名海军统帅纳尔逊而兴建的。纪念塔位于萨克威尔街中部,高达134英尺,从内部攀爬而上可以鸟瞰全城,是当时都柏林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它也是都柏林电车系统的枢纽,《尤利西斯》“埃俄罗斯”一章的第一小节“在海勃尼亚都市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HIBERNIAN METROPOLIS)便描绘了电车在纳尔逊纪念塔前减速、改道的繁忙景象。“海勃尼亚”是对爱尔兰的诗意称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占据“海勃尼亚都市中心”的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形象。纳尔逊纪念塔建造于1800年《联合法案》通过后不久,它不仅象征着爱尔兰在政治上的附属地位,也体现了帝国历史观和官方话语的主导作用。事实上,“海勃尼亚都市中心”并非爱尔兰真正的中心,爱尔兰的行政中心并不在其领土范围之内,而是远在英国伦敦。另外,METROPOLIS一词也颇具反讽意味,虽然都柏林建都数千年,但并未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它只是一个“戴着首都面具”(Joyce 1993:30)的殖民空间。从文本结构来看,“埃俄罗斯”以“纳尔逊纪念塔”为始终,形成封闭的隐喻性空间,既表征了都柏林窒息瘫痪的状态,又象征着殖民权力对城市的监视和压抑,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尔逊纪念塔发挥着福柯所谓的全景敞视式监狱的作用。列斐伏尔认为,垂直和高度是潜在暴力的空间化表达(Lefebvre 1991:98)。纳尔逊纪念塔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具象表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面上因电流短路而停止运行的8条线路的电车——在殖民者目光的注视下,在殖民权力无所不在的渗透中,都柏林陷入了凝滞和瘫痪。 然而,纪念碑不单是权力合法化的空间表征,它也可以成为挑战权威的表征空间。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城市视为语言系统,认为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穿行、居住的行为使城市话语化。城市具有意指功能,这种意指功能与城市的实用价值之间存在矛盾关系。理性化过程意在将个体纳入统一的城市系统,从而使能指(景观)与所指(空间被赋予的功能)的关系稳定化,但因为城市居民对城市的反应和印象各不相同,这一理性化过程常常遭受挫折,导致所指含混不清,能指始终处于滑动状态(Barthes 1994:193-200)。虽然街道景观被意图改造为与历史无关的共时性空间,但个体可以通过身体对空间的感知,以隐秘的方式与秩序暴力进行对抗,使自身对空间的主观性重构超越空间的功能性意义。由此,城市成为差异集聚之处、主体性交汇之所,既是浸润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空间表征,也是动态的历验的表征空间。 纳尔逊纪念塔意在强化爱尔兰对不列颠帝国的从属关系,宣示对帝国事业的团结和忠诚,但自建立伊始就成为民族主义者批评攻击的对象。1922年之后,将纳尔逊纪念塔移除的呼声愈发高涨,最终纪念塔在1966年纪念1916年复活节起义50周年之际被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炸毁。实际上,纳尔逊纪念塔虽然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但也日益“成为广受欢迎的会面地和观景点、电车系统的终点站和市中心的象征”,其政治意蕴逐渐消融于日常生活的世俗性之中(Sakr 2012:45)。乔伊斯在作品中将这两方面并置起来,以“反纪念碑性”①的话语解构了纪念碑的权威性和神圣性。 纳尔逊纪念塔在《尤利西斯》中首先出现于“阴间”一章。在参加狄格南的葬礼前往墓地途中,布卢姆等人正在谈论有关茹本·J父子的趣事,此时马车正好经过萨克威尔街: 帕尔先生忍不住扑哧一声,马车里荡漾着轻轻的笑声。 纳尔逊纪念塔。 ——李子一便士八个!一便士八个! ——我们还是让人看着严肃一些的好,马丁·坎宁汉说。(U 85)② 此处“纳尔逊纪念塔”单独成行,十分醒目,这恰好对应了作为物质实体的纳尔逊纪念塔在都柏林城市景观中的重要地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所隐含的政治意蕴和官方话语也被消解了,它在空间上的显著性只缩减为文本中的一个词语、一个短句。主导叙述的是普通市民漫不经心的私人对话,其中不乏趣闻逸事、插科打诨,纪念碑的神圣性湮没于世俗生活的喧哗嬉笑之中。在马车这个狭小封闭的空间里同样存在着微妙的权力角逐。帕尔先生供职于都柏林堡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总署,这是一个负责压制爱尔兰政治异见者的殖民统治机构。都柏林堡这一纪念碑式建筑是不列颠帝国的象征,因此帕尔先生的笑声代表着权力(帕尔先生的姓Power恰有“权力”之意)的笑声和帝国的在场。马丁·坎宁汉也是都柏林堡的职员,他的适时提醒可以看作官方权力为维护纪念塔的威严而发出的训令,代表着保守和权威的力量。但闲谈与笑声无疑是这一微型权力关系中异质的声音,流言蜚语取代了充斥着意识形态因素的官方话语,象征性地打破了纪念性空间不可侵犯的表象,动摇了殖民权力的独断性和统治秩序的稳固性。 对纳尔逊纪念塔最具冲击力的解构来自斯蒂芬,他故意曲解了纪念碑的公共象征意义而赋予其鲜明的个人印记。在“埃俄罗斯”中,斯蒂芬杜撰了一个都柏林版本的“登比斯迦山望巴勒斯坦”的寓言故事,故事以两个老妪登纳尔逊纪念塔观光为主线,既挑战了殖民主义的权威,又颠覆了民族主义的乌托邦幻想。首先,老妪对纪念塔的历史和它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知之甚少,缺乏尊重。对于她们来说,登塔观光不过是同买肉冻和李子一样的消费行为。纪念塔被卷入世俗经济关系之中,成为可供买卖的商品。登上塔顶之后,她们感到头晕,害怕塔会倒掉,这实则隐喻了不列颠帝国可能面临的分崩离析的状态。老妪漠然惶恐的态度消解了纪念塔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否定了其官方政治用途,甚至将它转变为专供娱乐嬉戏的个人空间,由此解构了官方空间/非官方空间的二元对立。另外,在这则故事中,纳尔逊被斯蒂芬等人嘲讽为“独把儿奸夫”(U 131)。纳尔逊曾在海战中失去一臂,他与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夫人的关系是当时颇为轰动的桃色新闻。“独把儿奸夫”这一戏谑聚焦于纳尔逊个人生活不光彩的一面而非他的历史功绩,突出了其身体和道德的双重缺陷,将这位帝国英雄拉下神坛,解构了官方话语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3.纪念碑与民族主义政治 斯蒂芬寓言的另一颠覆对象是民族主义政治的宏大叙事。根据《圣经·申命记》记载,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后,遵循上帝的意旨,在去世前登上摩押平原的比斯迦山俯瞰迦南全境,那是上帝许诺给其子孙的国土。这个故事常被爱尔兰人用作民族未来乌托邦愿景的原型象征。由于爱尔兰人和犹太人的历史存在诸多相似之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犹太人怀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感,他们也在等待着民族英雄“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奴役的枷锁,走向自治和独立。然而,在斯蒂芬版本的“登比斯迦山望巴勒斯坦”中,主角并不是摩西式的民族领袖,而是代表着典型爱尔兰形象的贫穷老妪。登塔前她们惴惴不安,不住地为自己打气:“let there be life”(要有活路,U 128),这是对《创世记》中let there be light的戏仿,两个老妪被戏剧性地赋予爱尔兰救世主的形象。但等到她们战战兢兢地爬上纳尔逊纪念塔这座爱尔兰的“比斯迦山”后,看到的却只是“可爱的脏兮兮的都柏林”(U 129),满目贫困萧索之景。她们能做的只是坐下来吃李子,边吃边向下吐核。她们担心随时会坍塌的纳尔逊纪念塔并没有倒掉,不列颠帝国仍以其压制性在场占据着城市中心。“埃俄罗斯”极有可能是乔伊斯对1916年武装暴动的暗讽。在民族主义党领导人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等人的努力下,爱尔兰通过议会民主政治初步赢得了在联合王国之内的自治权,并由1914年第三部地方自治法案加以保障。复活节起义后,英国将爱尔兰置于严厉的军事管制之下,随之而来的是严酷的镇压和处决,爱尔兰的政治氛围急剧恶化。乔伊斯以摩西的故事来隐喻自治进程的受挫。③在《圣经》中,摩西在摩押地离世,终生未能踏入神许的国土,因此他在比斯迦山上遥望的只是无法实现的愿景。爱尔兰争取自治的漫长历程恰恰对应着犹太人向着应许之地的长途跋涉,但在乔伊斯完成“埃俄罗斯”这一章的1918年,自治事业依旧挫折重重,希望渺茫。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越来越多爱尔兰文化、政治领域杰出人物的纪念碑开始矗立在都柏林市中心周围,而新建的代表帝国殖民权力的纪念碑则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Whelan 2002:512)。例如,在“阴间”一章,马车行至萨克威尔街,依次经过了菲利普·克兰普顿爵士喷泉雕像纪念碑、奥布莱恩雕像、法雷尔雕像、奥康内尔铜像、格雷雕像、纳尔逊纪念塔、马修神父雕像、帕内尔纪念碑基石,其中大部分纪念碑是为缅怀爱尔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而建立的。这是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尝试性挑战,标志着19世纪后半叶爱尔兰权力政治的微妙变化。但遗憾的是,爱尔兰人的缅怀在某种程度上只流于形式。 帕内尔纪念碑的基石早在1899年就已安置妥当,但其间历经波折,直到1911年纪念碑才竖立起来。在1907年的里雅斯特演讲中,乔伊斯便以讽刺的口吻影射了帕内尔纪念碑缺失这一现象: 在那些思想有逻辑性、严肃认真的国度,人们习惯于以体面的方式来完成纪念碑的建造,习惯于请雕刻家、城市官员、演讲者和一大群人来参加揭碑仪式。但在爱尔兰这个上帝注定要使其成为严肃世界永恒笑柄的国家,即使纪念碑是为最受欢迎的人(其性格也是非常顺从民意的)而竖立的,也基本上只是一块基石而已。(Joyce 1959:176)④ 同样出现缺失的还有帕内尔的坟墓。葬礼结束后,众人决定顺路去看看“首领”,在帕内尔墓前帕尔先生说道:“有人说他根本不在这个墓里”(U 101)。帕内尔的弟弟与帕内尔形容相似,走路像个梦游者,仿佛帕内尔的幽灵,“那张总在眼前晃的脸”(U 146)时时提醒着都柏林人那位爱尔兰无冕之王曾经的存在。帕内尔是都柏林一个缺席的在场:“城市里充斥着提示着自身缺席的纪念碑、可能不是坟墓的坟墓以及活生生的亡魂,所有这一切都在纪念(尽管有违纪念之名)一位爱尔兰国会领导人力图造就社会共同体的未竟之功。”(Duffy 2000:50) 在经过帕内尔纪念碑基石时,布卢姆想到:“衰竭。心脏。”(U 85)布卢姆由葬礼死者狄格南的死因联想到民族领袖帕内尔的死因。帕内尔死于因急性肺炎引发的心力衰竭,但这句话更深层的含义是帕内尔死于心碎。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打击,“侵扰他心灵的抑郁也许是他所怀有的深刻信念:在他需要的时候,曾经和他一起为事业奋斗的亲信会背叛他”(CW228)。因为与奥谢夫人的私情,帕内尔被罢免、被抛弃,天主教人士更是普遍谴责帕内尔道德败坏。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丹特竭力为天主教辩护,把帕内尔斥为“国家叛徒”“奸夫”(Joyce 1992:27)。这不由让人联想到斯蒂芬给纳尔逊起的绰号“独把儿奸夫”,虽然同样身陷桃色新闻,但公众对待两人的态度截然相反:纳尔逊被纪念、被膜拜,帕内尔被背叛、被抛弃。在报道纳尔逊纪念塔基石的落成仪式时,《自由人杂志》不仅盛赞纳尔逊是“真正的英雄”,还将他树立为爱尔兰青年人效仿的榜样(Jones 2011:71)。但当帕内尔的私情被公之于众时,他的政治生涯也随之结束。帕内尔的声名迅速从民族领袖沦为“国家叛徒”,他没有得到宽容,甚至“在他向国人做出的最后绝望的请求里,他恳求他们别把他当作肉包子扔给在他们周围嗥叫的英国狼”,但结果是“他们没有把他扔给英国狼,他们自己把他撕咬了个粉碎”(CW 228)。就在民族自治的目标快要实现之际,爱尔兰人却因为根深蒂固的天主教道德的钳制亲手断送了即将到来的希望。在《帕内尔的幽灵》(The Shade of Parnell)一文中,乔伊斯写道:“他像另一个摩西,带领一个命途多舛不定的民族从羞耻之屋走到了希望之乡的边缘。”(CW 225)然而遗憾的是,帕内尔并没有看到自己亲手缔造的自治事业成功的那一天,他同摩西一样,“在尚未到达天主许诺的国土之前就去世了”(U 127)。从这个意义上说,“登比斯迦山望巴勒斯坦”的寓言可以看成乔伊斯对帕内尔的追怀和致敬;同时他也以此对民族主义给予了深刻反思,他看到了以丹特等人为代表的狭隘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陈腐、盲从、极端、暴力的危险倾向,这样的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与帝国沙文主义并无二致(申富英2011:102)。 综上所述,一方面,纪念碑是意识形态的承载物,具有深刻的政治象征意蕴;另一方面,它又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交锋的场所,是个人话语和官方话语交汇的空间,既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塑造,又被不断地颠覆解构,展现出个体复杂的心理图景。在都柏林这样一个张力空间里,各种政治力量盘结交错,从纪念碑这一简单的城市意象中便可一窥端倪。空间暴力是权力得以实现的方式之一,而空间使用者对空间表征的再阐释则反过来颠覆了权力的合法性,使之成为富于反抗潜能的表征空间。乔伊斯通过反纪念碑性话语的运用解构了殖民霸权和官方空间的严肃性和正统性,同时也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民族,揭露了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实现了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深刻反思。 ①詹姆斯·扬(James Young)用“反纪念碑”(counter-monument)一词来描述某些纪念碑自我消泯的特性。“反纪念碑”取消了传统纪念碑的一些基本属性并将意义阐释的权力留给观看者,其目的不是抚慰而是激怒,不是固化而是改变,不是压制而是交流,不是背负历史的负担而是力求将负担抛诸身后。(Young 1992:277) ②文中对《尤利西斯》的引用均出自参考文献[11],以U加页码形式标注,译文则参考了参考文献[1]。 ③在斯蒂芬讲述寓言之前,众人在谈话中提到了“梵蒂冈的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U124)。事实上,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并不在梵蒂冈,而是在温科利的圣彼得教堂。在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意大利军队开进罗马城,迫使教皇退居梵蒂冈宫,梵蒂冈成为城中之城。其时,都柏林作为“首都”的尴尬地位多少与梵蒂冈有些相似。巧合的是,都柏林法院的门廊里也有一座摩西石像。小说中这处明显的“误置”进一步强调了爱尔兰的殖民地地位。(Gifford & Seidman 1988:146) ④以下对该书的引用以CW加页码形式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