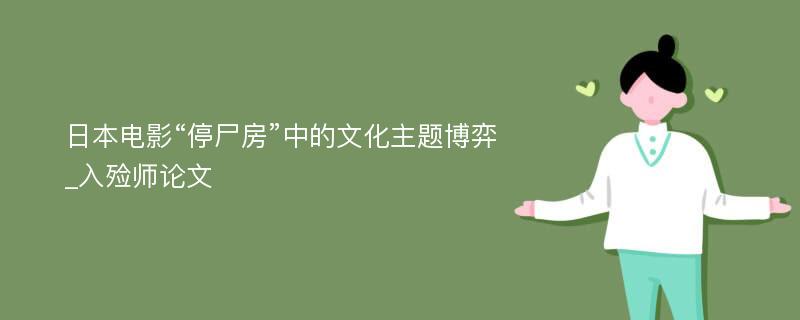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文化论文,主体论文,日本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9)06-0031-09
2009年日本电影《入殓师》在美国获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使我想起了一系列亚洲在欧美获奖的影片,这些影片在国际获奖的同时,往往也会在国内引起争论,认为该影片所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意识倾向于西方,与国内的格格不入。如日本的黑泽明、中国的张艺谋、韩国的金基德等等,他们的作品在西方屡屡获奖,但是在国内却褒贬不一,争论不断。在我看来,电影本不是一种必然反映现实社会文化的艺术形式(尽管某些影片和流派表现出了与社会现实的对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故事中出现的社会形态一般来说都是艺术性的,是影片创作者人为(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设置的,将其对应于现实并没有充分理由。因此,有意义的讨论并不在影片与现实的关系,而在于影片表现出了什么样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倾向,是什么样的动机和文化背景造成了这些与现实脱节或背离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的文化批评一般来说便是对诸如此类问题表示的关注。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日本电影《入殓师》,这部影片不但在西方的电影节上获奖,在日本国内也获得了大奖,成为了2008年度和2009年度日本国内最上座的影片之一,这是否说明这部影片在文化倾向上比较纯粹,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是一个例外?在我看来不是,这部电影充分表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主体的博弈和冲撞。下面我分三个部分讨论不同文化主体在影片中的呈现。
“个人主义”与“集体化”
影片《入殓师》讲述了乐队大提琴手小林大悟(不到40岁)突遭乐队解散的变故,因为经济上的拮据,他和妻子美香离开大城市(东京),回到了母亲死后遗留给他的乡镇(山形)房屋中居住。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份入殓师(执行一种为尸体更衣、美容,然后置于棺椁的仪式)的工作,尽管收入不错,但是却遭到了妻子美香和邻居朋友的反对,以致闹到妻子离家出走的境地。小林在自己的工作中理解了这份工作对于那些还活着的家属们的意义,坚持了下来,终于得到了朋友和妻子的理解,同时自己的境界也得到了升华,原谅了在他6岁时因为情人而离家出走的父亲,为死去的父亲隆重入殓,承担起了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
尽管影片中入殓的场面美丽而动人,表现了独特的日本文化,但我所关心的并不在此,而是在小林这个人物。在我看来,小林这个人物与其说像是一个一般的日本人,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西部牛仔,尽管这个牛仔并没有好马快枪(并非出色的大提琴手),但他也是只身前往西部的荒蛮之地(从城市来到山区),并在那里发现了金矿(了解了入殓师职业能够使人尊严并美丽地离开人世),纵然无人相信他的发现(朋友劝他换工作,妻子离去),他还是矢志不移,最后终于战胜敌人并赢得美人归(化仇恨为亲情,将父亲入殓,与妻子重归于好)。以这样一个西部的故事来阐释《入殓师》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想说明小林这个人物的骨子里有着一种西方人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精神,而不是传统日本社会所固有的“家”的集体精神。
日本传统社会中有关“家”的概念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家”有所不同,鸟越皓之分析日本“家”的概念时指出了三个重要的特征:
(1)“家”是一个经济的实体。
(2)“家”代表所有家庭成员祭祀先祖。
(3)“家”重视血统的世代传承。[1]12-1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家”概念有些类似于我们的“家族”概念,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家”作为经济实体不但把有血缘关系的族人(同姓)聚集在一起,同时也把没有血缘关系的雇工纳入到“家”的范畴之中,在过去的日本社会,雇工与主人的关系一般都是“养子”的关系,养子甚至可以使用主人的姓氏,死后葬在主人的墓地,他们彼此之间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企业中的家族形态(雇员与雇主彼此承担类似于父子的权利与义务),便是日本传统“家”文化的一种延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传统主义价值体系随着战败而崩溃,不仅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文化领域都不再有任何直接阻碍西方价值传播的力量。于是出现了不亚于明治前期‘欧化热’的‘美国化热潮’”。[2]166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又是一个类似于明治维新的“全盘西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奄奄一息的日本传统的“家”和“村落”制度似乎是彻底破产了。但是,富永健一在他论述日本社会变迁的书中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家在战后改革中失去了法律上的依据,家庭制度崩溃,即铃木荣太郎所说的家庭的‘精神’崩溃。但是正如本书反复强调的那样,直到现在,日本的家庭与西方发达社会相比,直系家庭所占比率仍旧很高。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家作为制度继续存在,但说明作为日常社会关系的类型,家庭共同社会与村落共同社会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非制度性的、习惯性的命脉。”[2]190也就是说,“家”尽管作为一种制度的传统形式不复存在,但是并没有被消灭干净,而是以传统习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以“讲”、“组”或类似的非体制性的其他团体形式出现的。
如果说“家”是一种纵向的社会组织机构,个人在“家”的系统中能够得到依靠,那么在“家”的土地经营型经济走向衰落后,在1940年代,在体制性的“村”的机构之下,横向的社会组织机构,所谓“同族”、“讲组”的形式出现了,个人又被纳入到诸如此类的组织之中。“讲组”在20世纪的50至60年代曾遍布日本的乡村,同时也渗透到了城市,并以某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① 这样一种遍布日本的社团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日本人对于传统“家”文化的精神需求。正如土居健郎所言:“只有亲子这种血缘关系无法断离,永远不会变成‘他人’。日本人把这种亲子关系视为人际关系中最崇高的理想模式,社会上所有人际关系都以此为衡量标准。……其他人际关系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向外延伸,逐渐疏远的,这种现象恰恰与依赖心理的原则一致。亲子之间的互相依赖是理所当然的,而其他关系则需要以亲子关系为参照值。”[3]22,23在日本的人际关系中,个人对于“家”的依赖是有历史传统的,在“家”中的个人是以家族的成员,而不是以“个人”面对社会的,因此亲人之间的互相依赖、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互相依赖成为了最为普遍的社会存在方式,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人的不同:“日本传统上一贯是义理重于人情、集体重于个人。……西方人是要比日本人更自觉地意识到自我,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思想里有一个使个人超越集团的要素。”[3]100,104吉野耕作在研究日本民族主义的时候也说:“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得以成立,个人所属的身边集团的作用是重要的。不光是民族主义,在把整个社会卷入的意识形态运动·体制的形成方面,个人所属的身边集团的作用也是重要的。”[4]我国的访日学者田晓虹也看到了这一点,她在谈到日本的大学生时说:“当一个青年人正式加盟某个公司‘集团’,他必定成为以拼搏、效忠、服从、与他人保持一致为底色,以从业集团划一角色为特征的标准化产品。”[5]土居健郎在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时说:“日本人喜欢团体活动,不擅于独自行动,因为独来独往很容易被误解为叛离集团的行为,所以他们不愿搞个人行动。”[3]35可见集体化是日本人行为的一个基本参照。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入殓师》中的小林尽管是一个日本人,但他却没有一般日本人所积极参与的集体活动圈子(他的妻子也没有),放弃从小学习的音乐,离开城市回到乡间的人生重大决定,几乎是他独立作出的。在他失业之后,一天与妻子放生了一条本打算用来做晚餐的章鱼,看着水中游走的章鱼,小林似乎突然想到了“放归自然便能生存”的道理,于是说出了回乡的想法,当时在他身边支持他的只有妻子美香。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小林,完全没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在他工作的乐队之中,他似乎也是独往独来,以致对于乐队将要解散这样的大事毫无准备,如果他在乐队中或者生活中有一群朋友,也就是一般日本人除了家庭之外所归属的“团体”或者“圈子”,也不至于被乐队的解散搞得完全束手无策。影片中小林唯一可以称为“圈子”的伙伴是他小时候的同学山下,但是这个山下并不能对小林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他的影响甚至还不如在温泉浴室中出现的一个陌生老头,这个老头对于鲑鱼洄游是“回故乡”的解释还让小林有所触动。不过,当小林在山下母亲开设的温泉澡堂洗澡时,不经意碰到了正在与母亲争执的山下,山下对小林说:“不好意思,现在正在争吵,下次再慢慢聊吧。”然后做了一个喝酒的动作,暗示日后找机会一起喝酒,小林一边道别,一边也回敬了同样的动作,这算是影片对小林生活圈子唯一的一次“图解”,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小林与山下一起喝酒,影片中甚至连一次这样的暗示都没有。因此在我看来,小林这个人物如果不是影片创作者臆造的“日本人”,至少也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与一般日本人格格不入、有着诸多异样之处的孤独者,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到小林与他的同龄人(除了妻子)或者同事、朋友之类的人物交往,没有看到他对某一团体活动的参与或与之发生关系,他似乎是生活在真空的日本社会之中。而对于个性化较强的西方人来说,这样的表现远称不上怪癖,在他们的文化中,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完全属于正常的范畴,而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则多少有些另类。
也许有人会提出目前存在于日本的“御宅”一族,这些人似乎也是与社会隔绝,足不出户,整日在家与媒体为伍。不过这些人与小林这样类型的人物不同,“御宅族”尽管不依赖社会团体,但是却依赖媒体和家庭,甚至有人认为“御宅族”与“恋母情结”有关,是日本妇女在家承担了教育子女的责任,从而与儿子保持了过度密切的关系而造成的。[6]“御宅族”不是没有可依赖的对象,而是依赖的对象不同于一般传统的社会团体。另外,“御宅”一族往往是在生活没有问题的时候“御宅”,有了问题他们还是会走出家门与人交际的,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个人主义”关系不大。
“罪文化”与“耻文化”
小林这个人物具有西方文化主体倾向的判断除了来自对小林社会活动圈子的考察,同样也来自小林这个人物在日本社会中的羞耻感。按照作田启一的理论,在日本社会中,当集团不是足够强大的时候,集团成员对其的心理依赖也不是完全的,而是一种“半所属”,“集团成员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同时被内部和外部的视线所监视。当一个人在集团内部建立个人的人际关系时,他会因意识到来自外部的视线而羞愧。……另一方面,当集团成员同外部社会依据多少有些抽象的原理建立关系时,他会因意识到集团内部的视线而羞愧”。[7]293日本人的羞耻感便是在社会和集团这两个不同所属视线的注视下产生的。对于个人来说,羞耻感的产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双重标准下无所适从,当其将自己归属于团体时,能够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社会意识形态的背弃;当其将自己归属于家庭社会时,又能够感觉到自己对团体意识形态的背弃。这是日本社会的特殊之处。本尼迪克特很早便在《菊与刀》中区分了西方人的“罪感文化”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她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行。”[8]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小林这个人物的羞耻感从何而来。在影片中,当小林找到了入殓师的工作时,他确实感到了羞耻,因为他意识到了家庭社会对这一工作的不认同,但是当他看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时,他便不再为他人的意见所动,即便是妻子的苦苦哀求和出走也不能使他动摇,这便是他的内心的认定,而不是依靠外部社会的压力。在内心和外部的矛盾压力中,小林往往依靠内心的力量取胜。因此,我们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先是日本人小林,这个日本人因为必须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指责而羞愧万分;然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西方人小林,这个小林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充满了热爱之情,即便是朋友在大街上教训他要他换工作,妻子因为嫌他的工作“脏”而离家出走,他也能够做到不为所动,可见他对自己的追求有着深刻的内心认同,否则他将不能抵抗强大的外部压力。
影片中,小林的妻子美香在离开时留下了一句话:“辞职后来接我。”因此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悬念:小林会不会因为妻子的反对而辞职?接着我们看到小林去公司找到了社长,社长正在吃东西,并邀小林一块入座。社长告诉小林,他的妻子在9年前去世,是他亲手将妻子入殓后安葬。然后他将话题转到了吃的东西上,他正在烤着吃的是河豚鱼的鱼白,他分了一半给小林,这大概是一种难得的美味,但是吃这样的美味没有一定的勇气是不能如愿以偿的,因为众所周知,河豚是一种剧毒的鱼类。社长的哲学是:“生物是吃着其他生物而生存下去的,……要吃的话,最好是选好吃的。”这也可以理解为:如果工作是为了生存的话,就应该挑一个压力不大收入不少的,比如小林正打算放弃的入殓师这样的工作,社长显然是从人生哲理认知的角度在开导小林。小林也因此而顿悟,他没有提出辞呈,而是和社长一起大嚼烤鱼白,按照社长所说的努力去“忘记烦恼”。然后,影片又以一系列小林为客户举行入殓仪式的组合并列镜头,表现了小林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客户对其工作的认可,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易装癖男孩死亡的入殓仪式,男孩的父亲对入殓师表示:自己过去一直与孩子吵架,不能接受他女妆的现实,但是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他也是自己孩子。述说之间声泪俱下泣不成声。这段情节被放在小林妻子出走之后,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意味,这里的潜台词是:无论多么出格,多么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事情,只要是自然的,总有它存在的价值。显而易见,小林是从观念上、从意识上被校正,是从“罪”的角度,也就是从正确与否的判断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在压力之下去妥协,从“耻”的角度,也就是从丢脸与否的考虑去弥合冲突。影片这样的安排符合了西方人的思维和习惯,但并不是日本社会解决问题的一般途径。
对于东西方在“罪文化”和“耻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不同原因,日本学者也有所讨论,他们认为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家庭结构和儿童教育方法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同文化的产生。“西欧的资产阶级家庭正是通过将孩子和外面的社会隔离,培养了近代的自我。但日本近代社会中的近代自我,不是在家庭中,而是在对家庭的反抗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日本的家庭不是密室。就像日本的房屋不能有效防止外界的风的侵入或温度的影响一样,社会的舆论或权力的支配会自由地进入‘家’中。”[7]291因此,可以推论日本孩子的自我意识相对西方的孩子来说要软弱,因为他们从小便没有一个可以建立自我的“私”的场所。正村俊之说:“在日本社会,由家所代表的场设定了允许内部和外部相互渗透的含糊的界限。在欧美,私的领域和公的领域是明确地分化了的,相反在日本,公的领域一直逼近到了个人的精神领域的大门口。”[9]除了这样解释,还有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当代日本的儿童从小接受的便是西方式的教育,但是他们在踏上社会之后还要经历另外一次“教育”,这次教育使他们彻底丧失了自我,“会社(企业——译者)对新来的社员都要进行名为‘社员教育’的道德教育。强制新社员接受成人社会的种种规定和限制,这些规矩给他们展示了另外一个与学校教授的真与善的伦理观念完全相反的世界”。[10]不论哪种解释,都说明了日本人的羞耻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小林大悟,却具有异乎寻常坚强的自我意识,他能够抵御对一般日本人来说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压力。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其称作西方人小林,——至少也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小林。
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
尽管我们在小林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印记,但传统日本文化的印记在影片中也同样强大,甚至是一股更为强大的潜流,它悄悄地为人物的发展提供动力,而观众却不曾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表面上看,影片故事的主线尽管是一个(西方式)人物拼搏励志的过程,但其背后却有着一个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宏大叙事。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日本学者在论述“家”文化时把亲子关系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电影《入殓师》正是把这样一种关系作为了影片情感设置的核心与矛盾冲突的高潮。
首先,我们来看“父亲”的缺失和存在。影片中交代小林从6岁开始父亲便不在身边,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但我们在影片的阅读中却看见这位缺失父亲的时时浮现,出现频率之高,远远超过那位未曾犯下任何过失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片中母亲的出现甚至是为了父亲而设置的。比如小林的妻子在看到家里保存的许多唱片时说:母亲一定是爱着父亲的,否则她不会保留这些唱片。另外,这些唱片也暗示了小林的父亲是音乐爱好者,而对母亲的爱好影片却未置一词,这样观众便会联想小林从小学习大提琴是受到了父亲的鼓励和影响,用小林的话来说:“是我爸硬逼着我去学的。”另外,小林从琴盒中拿出了父亲送他的石头,尽管抱怨说:父亲说好了每年都送,结果只有这一块。但是给观众的感觉,这样的话语与其说是埋怨,还不如说是思念。影片对于家庭中音乐爱好的暗示确实非常重要,以至每当小林演奏大提琴的时候,观众都会感觉父亲站在他的身后,这一点甚至被用主观化的摄影机运动(元叙事呈现)加以特别强调和提点。②
其次是父亲的缺点与伟业。影片中小林恨他的父亲,是因为父亲与情人私奔,置妻儿于不顾。这个父亲是个符号化的父亲,并未在影片中真正出现过。在影片的故事中,入殓社社长这一角色承担了生活中父亲的职责,他不但使小林摆脱了经济上的窘迫,而且在哲学上、美学上给予小林的人生观以指导,他使小林懂得了人的尊严和美即便是在生命逝去之时也是永存的;他教导小林:生活的残酷便在于一个生物的生总是以他者的死为条件的,因此需要坦然面对。一个父亲的伟业不仅是在自己的事业中受人尊敬,而且更要能够在父子关系的延续中传承,这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为了使这点更为明确,影片特别安排了社长这个人物的命运与小林父亲的相似:社长的现任妻子(或者女友)在看到社长这个男人之后,毅然抛弃了自己年仅6岁的孩子跟着社长走了。因此在小林犹豫着是否要去认已经死去的父亲时,她以言传身教告诉小林,自己当年离开孩子只是因为一念之差,想在将来也有一个美丽的入殓仪式。因此,罪过并不是不可原谅,罪过也并不都是由于邪恶的念头而产生。如果说这是一种罪过,那么社长便是接纳这一罪过的元凶。影片中的小林有一句台词:“抛弃孩子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吗?你们这样也太不负责任了!”显然,小林已经将自己的父亲与社长和他的妻子联系了起来,他们作为一个共同的“父辈”呈现在小林面前。在影片中,尽管只有小林与社长妻子的对话,但社长心神不宁的中近景镜头不时被作为“插入”镜头出现在正在激烈争辩的画外音中,这使得他也成为了正在被讨论的有关“父亲”话题的参与者,只不过由于他也是犯有过错的“父亲”,因此在振振有词的小林面前被剥夺了话语权。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父辈”,其功与过两相比较,“伟业”显然还是占据了上风。两代人之间看似不可平覆的代沟,终于在孰重孰轻的功过平衡中有了一个结论,小林尽管还是有些愤愤不平,但终于接受了“父辈”的规劝,踏上了他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
这个“有缺点的父亲”的形象非常有趣,几乎不能从现实生活中得到阐释,但是只要这个形象能够被人构想出来,必定是有着一个原型。原型或许是深藏于潜意识而无从稽考,因此我们有了一个“猜想”:向来奉行家长制传统的日本,在战败之后已经无法否认日本天皇这位家长中的“家长”将人民拖入战争的错误。二战失败之后,日本天皇向人民坦言自己是人不是神,在日本民间引起巨大震动,犯有战争错误的天皇有可能成为人们潜意识中走入歧途的“父亲”,成为日本现代“家”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潜在的情结。
最后是新老父亲的延续和传承。当小林去认他三十多年未见已经死去的父亲时,他也已经是一个“父亲”,他自信自己不会再是他父亲那样的父亲,因此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至少在观众看来如此)。但是当他看到父亲的遗物只有一个小纸箱子的时候,不禁感慨:“这就是人生吗……”我们如果能够充分理解这一感慨的背后,就会知道小林在东京失业时之所以能够在母亲遗留的房屋中居住,这里面也有父亲的恩泽和庇护,因为在小林父亲被情人抛弃后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回到属于他的房屋中的,但是他宁可流浪也没有这样做,如果心中没有对于小林母子的眷顾,他的选择也许会是别样的。意识到这一点的小林,“居高临下”的心理被一扫而空,对这位陌生父亲的认同之感定会油然而生,因为在日本的亲子关系中,父亲的庇护和儿子的奉献应该是对等的,正如鸟越皓之所言:“‘父辈—子辈关系’在功能上的特征是庇护与侍奉。也就是说,一方面,居于社会不安定地位的人向居于社会上层拥有实力的人(称为父辈)要求庇护。另一方面,作为父辈,则根据需要要求子辈为其提供侍奉。”[1]136。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此时小林的感受应该是“亏欠”,尽管父亲不在,但是小林的家庭仍然间接地受到了父亲的庇护,而作为子辈自己,非但没有尽到任何侍奉的义务,反而充满了怨恨。两代人之间对于权利和义务行为的反差过于巨大,一个是风餐露宿但毫无怨言,一个是生活安定仍心有不甘,这足以对小林的心理造成强烈冲击。于是,影片中接下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小林赶走了两个粗手笨脚的当地殡仪馆人员,亲自为父亲举行了入殓仪式,在仪式过程中小林发现父亲临终之时将自己6岁时送给他的小石头紧紧握在手中,小林的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们在影片中唯一一次看到小林哭泣,他说他记起了父亲的容颜,影片中出现了闪回的画面,这无疑是一个象征,30年的分离并不意味着30年情感的空白,父子之情凝聚在这颗小小的石头之中,30年时空的空白在瞬间被充填满溢。尽管这个符号化的父亲在影片中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实体来表现,但是在影片的结尾却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父亲。是否能够成为“父亲”,不在过错父亲对儿子的认同,而在儿子对过错父亲的原谅。那颗象征亲子血缘关系传承的小石头不仅被放在了小林与他的父亲之间,同时也被放在了小林与他的孩子之间。小林把石头递给了妻子,美香将石头放在了自己隆起的腹部,那里是小林尚未出生的孩子,摄影机从小林捧着妻子双手的中景画面慢慢推向了两人微笑相视的特写,影片至此结束。
我们看到,小林在最后的入殓仪式中也完成了他自己从儿子到父亲的过渡。为了“家”的延续,作为家长需要宽容,需要大度,当小林具有了这样的心态和素质,他便会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摄影机镜头在父亲、儿子和腹中之子之间的游移,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代际的交接和传承。当然,这也是影片结束后留给观众细细品味的“绕梁余音”。
《入殓师》的结尾展示了一个曾经背叛家庭的父亲最后被重新认同回归家庭的宏大叙事。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背叛”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儿子的背叛,而是父亲的背叛,亲子关系的重建也不是为了权力的争夺或再分配,而是为了充满温情的“家”的传承。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这部影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重建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关“家”的神话。
《入殓师》这部影片看上去写实,但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日本传统文化中关于“家”的传统与西方文化中个人奋斗的精神交织映衬,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博弈。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西方文化中的个人奋斗占据了影片的大部分篇幅,但是有关“家”和“父亲”的主题却从故事的每一个缝隙中渗透出来:当小林在大都市奋斗失败,是“家”让他有了安身之所;当小林在犹豫是选择入殓师的职业还是向庸俗社会观念妥协之际,是一位循循善诱的“父亲”(社长)告诉了他人生的意义;当小林面对重大伦理抉择的时候,又是前辈们给了他支持,使他能够以开阔的胸怀坦然面对。影片的最终不是告诉我们小林所取得的成就有多么显赫,而是彰显了小林的内心有多么高尚,这就是日本传统的“家”的文化,它以一个温情脉脉的家庭传承表现了传统伦理之美以及传统伦理之可贵。
收稿日期:2009-09-06
注释:
① 参见《日本:两次跨世纪的变革》一书中的说法:“时至今日,日本社会也是处处体现出集团主义的社会结构。工厂或企业是比较稳定的群体,在企业之上也有各种类似的团体,从街头巷尾的小零售商的团体到全国性的大银行或钢铁公司的协会,像金字塔一样自上而下地组成广泛的全国性组织。企业、学校、机关内部也常常形成许多小团体,班组和科室既是工作团体也是重要的社交小团体。在社会上,到处都有地区性的妇女协会,每个城市社区都设有居民组织——町内会。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个人寻求加入某一团体的重要阶梯。”见张健、王金林主编:《日本:两次跨世界的变革》,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84页。
② 此观点来自笔者学生课程作业:蔡博的《视听语言研究课程作业:〈入殓师〉分析》2009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