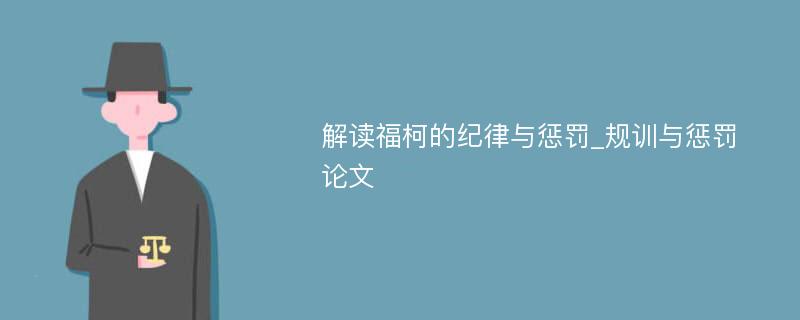
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后现代主义的诸子百家中,福柯对于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的分析无疑是独树一 帜的。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启蒙运动的合法性及其与理性、进步和解放的意义勾连,指出 ,所谓现代性实际上不外是一种新的控制和统治形式,而理性的主体和客观的知识等等 都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权力控制的结果。福柯这种将现代社会中 的宏大叙事置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中去研究其被构成的过程、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的路径 ,就是一种为人所熟悉的谱系学方法。1975年问世的《规训与惩罚》,正是标志着福柯 的研究进路从知识考古学转向谱系学的重要作品,这导致对于这部作品的解读具有极大 理论意蕴和阐释空间。按照福柯自己的看法,《规训与惩罚》旨在从谱系学的立场论述 现代灵魂与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由此证成惩罚权力在现行科学—法律综 合体中是如何获得自身的基础、证明与规则的。[1](P24)因此,《规训与惩罚》很大程 度上是一部关于刑事机构与话语机制的研究作品,是一部关于刑罚的制度变迁、话语变 迁及其权力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作品。最终的趣旨乃是在于证成:灵魂进入刑事司法舞 台以及“知识”进入法律实践,乃是权力干预肉体的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
一、肉刑的隐匿与规训的兴起
正如许多读者已经知道的,《规训与惩罚》是以一部血腥的惨不忍睹的酷刑场景揭开 序幕的。福柯不厌其烦甚至有些津津乐道地描述了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公开受刑的场面 。他详尽描述了刑具如何在肉体上体现权力的具体细节,“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 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 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尸,最后焚尸扬灰”。[1](P3)在细致描述刺客达 米安被公开处决的过程之后,福柯又不动声色地向读者们展示了18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巴 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规章,这份规章非常细致精确地规定了少年犯们在每一个具体的 时间点应当从事的义务的时间表(起床、劳动、进餐、学习、工作、祷告等等),这份时 间表精确到分钟,少年犯们在监管所中的每一天就象一个精心设计、毫无瑕疵的惩罚流 水线,在这个流水线中再也看不到血腥、刑具和热闹的观众。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 ,这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比公开处决更为人道的刑罚观,体现了刑罚的进步 ,是一种“人性的胜利”。福柯认为,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逐渐消失,惩罚不再是一种 公开的表演,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已经逐渐完成,这种转变具有许多历史与社会原因 如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的兴起,但更为重要的是,公开惩罚在展示专制权力的强大和神 圣之余,也具有自我悖逆的解构后果,因为在许多公开刑罚的观众眼中,这种惩罚本身 就是一种罪恶的方式,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犯罪本身,刽子手象罪犯,法官象 谋杀犯,这导致公开处决的角色在最后一刻进行了调换,使受刑的罪犯反倒可能成为怜 悯和赞美的对象。因此,公开处决在展示权力之余有着削弱权力之虞。
酷刑的隐匿实际上与一套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知识转变是分不开的。在中世纪和旧制度 时期,犯罪意味着一种对于君主绝对权力和尊严的侵犯与挑战,刑罚因而主要体现一种 对于君主权力的恢复和重申,对于罪犯而言它是一种报复,对于观众而言它是一种重申 。因此,刑罚具有的多重指涉和意蕴。首先公开刑罚的表演体现了一种审判程序和执行 程序的综合,在酷刑的执行过程中通过罪犯的忏悔向观众展示审判过程,使犯罪的真相 得以揭示。酷刑将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严重程度、犯罪的 特点以及受害者的地位联系起来,通过鞭笞的次数,打烙印的部位,在火刑柱上的时间 等等区别对待,使肉体酷刑成为一个审判的场所,一个惩罚的场所,一种专制权力的凯 旋仪式,一个展示真相的仪式。在18世纪,公开酷刑使真相与惩罚的仪式同步进行,被 拷打的肉体既是施加惩罚的对象,又是强行获取事实真相的地方,这种有节制的拷打使 惩罚与调查同步进行,“公开刑罚的过程既使证据得到确认,又使判决得以通过”[1]( P17),犯罪者在痛苦的号叫过程中任务就是公开承认罪行并忏悔,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 者,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司法的正义。福柯曾深刻指出,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就 已将忏悔确定为我们赖以产生真理和真相的主要仪式。[2]公开刑罚的目的在于产生公 开的忏悔。可以说从司法拷问到执行,肉体一再产生或复制犯罪的真相,更确切地说, 它是整个仪式和审问中的一个因素:供认罪行,承认被告的确犯有这种罪行,显示被告 是用自己的人身来承担这种罪行,支撑惩罚的运作并用最醒目的方式展示惩罚的效果。 “肉体受到多次折磨,从而成为一个承担着行为现实和调查结果、诉讼文件和罪犯陈述 、犯罪与惩罚的综合体”。[1](P51)因此,公开处决在酷刑的展示中具有一种鲜明的司 法政治功能,它通过在罪犯肉体上公开展示精心计算的刑罚,以君权最壮观时的情景来 重建或者恢复一时受到冒犯的君权,并以儆效尤。这是一种刑罚上的恐怖政策,使所有 的人意识到君主权力的无限存在。“它(肉体酷刑)的全部机制都蕴藏在刑罚制度的政治 功能中”。[1](P54)
对于公开酷刑和处决的存在,既有一种司法政治的内部结构的作用,也可能和一种与 内部结构无关的东西相联系。福柯引用鲁舍和基西海默的观点指出,作为一种对于肉体 的漠视的酷刑与处决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后果。在这种生产制度中,劳动力乃至肉体没有 在工业经济中所赋予的那种效用与商业价值。简而言之,就是劳动力还没有进入商业。 另外,对于肉体的轻视也与当时社会对于死亡的普遍态度有关。在当时的历史境域中, 疾病猖獗,瘟疫横行,死亡司空见惯,对于死亡的容忍也逐渐成为一种心理习惯。[1]( P59)因此,对于死亡的漠视导致观众对于实施死亡产生一种心安理得的心理。福柯认为 ,对于刑罚的公开展示在当时也往往被认为是人民的一项权利。在恐怖的刑罚场合,观 众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们需要了解刑罚的过程,防止刑罚中的黑箱。对于刑罚, “民众也有参与权”。[1](P64)但是,观众的参与可能导致危险。因为参观意味着参与 ,意味着评价,它是一种审判参与的抽象形式。因此,一旦观众对于处决产生不公正的 感觉时,他们可能会怀疑惩罚,企图阻止惩罚的发生,甚至怀疑审判和审判者的合法性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着确定的死亡,罪犯可能不会产生预期的忏悔,相反他们可能诅 咒法官,诅咒牧师和上帝,诅咒法律和君主。显而易见,一旦发生这种状况,公开处决 的功能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从恢复、重建和展示君主权力转向了嘲弄和颠覆,从而在 围观者中鼓励了一种对于权威和法律的冒犯和蔑视。这无疑颠覆了公开惩罚的所有积极 的政治功能。因此,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策略,公开酷刑也就必然转向了另一种比较隐 蔽的方式。这个过程表现为审判与惩罚逐渐分离。执行惩罚变成了一个充满羞辱的不光 彩的行动逐渐在公众的视线中隐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了审判。执行惩罚成为了一个独 立的部门,肉体逐渐脱离了惩罚的重心,惩罚的对象被灵魂所代替。对于灵魂的规训也 因此得以展开。
二、规训机制、手段及其知识型
一旦审判成为了焦点,司法也就成为各种权力参与的场域,各种知识和真理也就参与 到审判过程中来。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并非审判的唯一主角,整个刑事诉讼的审判与执 行充斥着一系列的辅助权威,他们围绕着审判衍生了大量的小型法律体系和变相的法官 。按照福柯的理解,这些权威包括精神病和心理分析专家,执行判决的官员,教育工作 者,监狱服务人员。所有的这些人都分享着合法惩罚的权力。[1](P22)由于司法决策权 威的大量衍生,决定权开始扩展到了判决以外的领域。可以说,围绕着辨认和改造罪犯 ,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权力网络,各种知识权力的参与,标志着审判日益民主化,从而使 刑事司法通过非常司法体系的嵌入而获得了合法性,并使一整套的知识、技术和话语逐 渐形成与参与到惩罚实践之中。从知识的形成机制背后发现权力机制,这就是福柯在《 规训与惩罚》中贯彻的谱系学的方法。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机制, 是通过规训的一种权力表达,规训塑造了个体,是权力的特殊手段。个体既是权力行使 的对象,又是权力行使的工具。各种知识参与合作的刑事司法过程目的在于规范化,消 除一切不规范的社会和心理因素,通过对于身体和精神的规训,塑造出温驯和有用的主 体。各种参与规训的学科由于也参与了共同的政治目的而具有了社会规范的功能,这些 学科的研究相应地强化了规训手段,最终强化了社会控制。
按照福柯的观点,规训代替酷刑是古典时期转向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过程 不是启蒙思想家们宣扬的人性的张扬,而是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一种新的控制和塑 造人的权力机制的产生。其实质是“从控制到控制”[3]在这种表面是人道的转向中, 福柯看到:一个使身体受制于思想控制的更为有效的而不是更为公正的惩罚机制,它深 入到社会身体的深处,体现了社会契约论、实用主义和表象符号学三种理性主义思想。 [4]福柯认为,公开酷刑转向规训体现的是一种知识/权力的形成,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实 施惩罚的一种知识建构,是一种新的知识型的产生。福柯非常精辟地阐述了知识与权力 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应当完全抛弃那种传统的想象,即认为只有在权力关系暂不发生 作用的地方知识才能够存在,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知识的条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 ,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 能产生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一种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P29)规训 就是这种知识/权力实施的一种基本策略。这种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惩罚的效率和 扩充其网络来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并相应地建构一种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结构与新制 度,从而导致监狱制度的诞生。
福柯指出,规训产生的前提渊源于古典时代人体是权力的对象与目标被逐渐认识,在 “人是机器”的知识论证下,肉体成为可以被权力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的对象。规 训的过程就是对于肉体进行外部控制与训练,其中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通过对 人体的不间断的监控,通过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编码并以纪律的形式来 实施的。纪律的存在使权力无微不至,形成一张网络。最终造就或者生产了个人。如果 我们细致观察福柯转引的“巴黎少年犯监管所”规章就可以对此产生直观的认识。
福柯专门论述了规训的手段。他指出,规训权力的成功应当归因于三种简单的手段: 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首先,层级监视很大程度上是对规训的物理结构和组 织结构的双重要求,它可以表现为在规训场所的设计上,也可以表现为监视组织的设计 上。层级监视不仅在规训者与规训对象之间建立监视关系,而且在监视者内部建立监视 关系,使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监视,使规训过程没有任何晦暗不明之处。自上而下,层层 把关,形成网络;规范化裁决乃是规训系统中的小型的处罚机制,它意味着规训享有某 种司法特权,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1](P201)这 种规范化的裁决经常体现为纪律及其执行,是一种正式惩罚的法律制度不染指的领域, 往往在法律不那么关心的细节上体现着规训。规范化裁决在许多规训机构的内部规则中 实施,我们经常看到的小学生的行为规则即是。规范化裁决的标准是那些已经精心确立 的各种内部要求,这些要求精密联系,环环相扣,服务于规训目的;凡达不到要求的必 须受到惩罚。福柯认为,惩罚在规训中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为它不仅仅采用普通的 司法模式(如罚款、鞭笞、禁闭),而是更偏爱操练惩罚,这种惩罚就像小学生经常遭遇 的那样:一个字不规范,老师命令我们抄写一百遍。因此,“惩罚就是操练”[1](P203 ),它是对纪律的加倍重申,从而进一步强化纪律。另外,在纪律中奖励和惩罚构成了 一个二元的规训体制,通过奖与罚的界分,规训机构可以排列出一个什么是好与坏的行 为列表,借以对规训对象进行更好的指导和监督。但是,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都必须 按等级分配[1](P205)。最后一种规训手段是检查。检查是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 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也是权力行使的一种技术,检查不是把权力的符号强 加给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对象。福柯认为,在检查这种支配空 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整理与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1](P211)考试、阅兵可以 说都是检查的不同形式。
由此可见,规训权力行使的三种手段是三种配套的技术,它们相互契合将身体置于一 种可控制和分析的结构中,并围绕着身体朝着某个特定目标建立起知识和制度。在规训 的结构中,权力的实施不再是“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方式”, 而是弥散的、细致的、微观的、无微不至的。这是一种知识型的变化,也是一种权力机 制和权力策略的变化。在这里,权力已经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法律权力,而是一种微观的 权力,微观权力往往就是规训的常规形式。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正是企图展示这种 规训权力的政治作用。在一次讲座中,他曾指出,“我们应当关注权力的极端状况,权 力的最终归属,权力的微细管道,也就是说权力的区域和局部的形式和机构。事实上, 我们最应当关心权力在什么地方超越了对它进行组织和限制的权力规则,把自己扩展到 这些规则之外,把自己付诸制度,具体化为技术,用工具甚至暴力的手段来装备自己。 ”“我们应该在权力实施的极端情况下把握它,在那里,权力总是呈现不太合法的特性 ”。[5]可见,规训作为一种微观的权力行使,往往是在规避合法性地隐蔽行使着,由 于它必须借助于对身体的一种外部控制和训练,所以往往涉嫌对权利构成了一种隐蔽的 侵害,而这种侵害往往容易在公众视线中被忽视。因此,公开的惩罚转化成规训,实际 上是权力的行使策略从公开转为隐蔽、从宏观转向微观的一种形式,最终表现为新的知 识型的产生。而监狱的诞生就是这种知识型的集中和极端的产物。
三、监狱的诞生和主体的命运
监狱的诞生是一种典型的规训作用形式。福柯曾对此精辟指出,从公开处决到监狱刑 罚的转变,是从一种惩罚艺术向另一种毫不逊色的精巧的惩罚艺术的转变,这是一种技 术的变化。[1](P291)福柯认为,监狱作为一种规训形式其实在刑法体系系统地使用它 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深刻指出,“当整个社会处在制定各种程序—分配人员,固定他 们的空间位置,对他们进行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 肉体,把他们的连续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彻底可见的状态,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观 察和记录机器,建立一套关于他们的知识并不断积累和集中这种知识时,监狱已经在法 律机构之外形成了。如果一种机构试图通过施加于人们肉体的精确压力来使他们变得驯 顺和有用,那么这种机构的一般形式就体现了监狱制度。”[1](P259)因此,监狱的诞 生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显然仅仅是稍微有些强化性地模仿了社会中已有的各种机制。 如兵营、医院和疯人院。但是,监狱不完全类似于社会其他的规训结构,它是一种更为 彻底而严厉的规训机构:首先,与学校、工厂和军队不同,监狱必须对受规训者的所有 方面全面负责,包括身体训练、劳动能力、日常行为、道德态度、精神状况;其次,监 狱是一种封闭的规训,没有受到外界干扰,没有任何内部的断裂,直至目标实现。因此 ,监狱是一种不停顿的规训;最后,监狱的规训对于罪犯实施的是一种几乎绝对的权力 ,它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在其他规训机制中的各种做法,更为彻底和有效地实现规训的目 标。[1](P264)可以认为,监狱的诞生是知识/权力最为成熟、最为典型的体现,是规训 权力的集大成。
值得指出的是,监狱作为各种常规规训的强化,对于罪犯的监视与检查必然如同其他 规训机构一样,形成知识和制度,将罪犯纳入到一种客观的机制中,通过持续而全面的 监督,将罪犯改造成人。但是,由于规训的一种重要手段是规范化裁决,它需要监狱如 同其他规训机构一样制定细致、全面而有效的纪律。权力正是通过纪律作用于身体,它 是权力行使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因此,纪律作为一种微观的规训权力与法律是否冲 突成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换句话说,规训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是否与权利理论 相冲突。对此,福柯指出,纪律不过是一种子法,它把法律所规定的一般形式扩展到个 人生活的无限细小的层面。因此,纪律几乎是在另一种范围内构成了同类的法律,使之 更精细也更宽容。但是,纪律更应当视为一种反法律(counter-law),作为司法体系的 法律往往在一般层面上确定实施权力的对象,而纪律却按照一种尺度,围绕着一种规范 对对象进行区分、归类和作出决定,进行检查和监督。因此,“纪律的存在使法律暂时 搁置,但是决不是全面的搁置,也不是废除法律。纪律虽然可能是有规律的和制度化的 ,但就纪律的机制而言,它是一种‘反法律’”[1](P150)。纪律的存在使法治社会中 法律的不入之地运转着一种宏大而又细密的机制。这些机制既然可能在更为微观的层面 体现与实施权力,同时也可能超出了法律的界限,成为一种反法律运作,侵犯了法律权 力所要保护或者追求的价值,构成了一种非法的惩罚。纪律的这种反法律性在作为规训 的强化实施的监狱之中发生的可能性最大,频率也最高。而在社会中的纪律则可能对正 式制度构成冲击、颠覆、挑战、规避并导致变迁。
以纪律为特征的规训社会的形成,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符合特定的政治—经济 发展进程。福柯认为,纪律是确保对复杂群体治理的技巧,以最小的代价、最经济的形 式来行使权力,使权力分散化、外在化、相对无形化并使其引起的阻力尽可能减少,进 而使权力效应达到最大强度,既无失误又无间断。规训使权力经济地增长和扩张,一旦 其与特定的机构结合,则可以增强机构内一切因素的驯顺性和实用性。[1](P244)规训 的最大特征就是,用一种隐蔽地、把对象客观化的权力,取代那些表现在权力行使者的 显赫之中的权力,并形成一套关于这些个人的知识体系。“各种纪律是这样一些细小技 术发明的组合,这些技术能够通过减少权力的不灵便之处增加人群的有用规模”。[1]( P247)显然,规训使权力具有了实施轨道,强化了权力的力量和密度,在权力的不入之 地衍生了作为技术的权力,使权力变得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和弥散性。一旦围绕着普 通的权力建立了规训,就意味着建立了权力的微观基础,使权力的行使日常化和可监控 。随着监狱的诞生,规训开始围绕法律在监狱中针对罪犯展开,构成有效而细微的知识 与制度,具有了独立的力量。这导致监狱作为一种规训,既实施和强化了法律权力又可 能颠覆法律权力。这是阅读《规训与惩罚》应当致力关注的话题。
福柯曾经在不同的作品中指出,规训的任务是制造新人,是按照权力的要求制造温顺 的主体。而在社会中,规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导致了规训社会的产生。在规训社会 中,各种规训可能成为一个配合的机制,有效而精确地制造符合需要的主体。主体因此 成为了规训的产物。这种观点反映了福柯对于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主体假定的颠覆。在 主体性这个问题上,福柯继承了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的主张,认为作为主体的自我 ,尤其是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乃是权力借以使个人将社会控制予以内化的策略以及 这种内化的后果。这种观点显然与现代性哲学假定的统一主体和永恒人性相冲突。福柯 鲜明指出,“我们必须摒弃构成性主体,并废除主体本身,也就是说,要通过分析来说 明主体在历史框架中的构成过程”[6]福柯认为,在规训社会中,主体是规训的产物, 是知识/权力的产物。规训形成秩序,并通过各种控制技术来维持秩序,如空间分割、 时间管制、禁闭、监视以及检查。通过一系列技术与话语的设置,规训致力于主体的生 产。这种权力产物的主体显然失去了启蒙运动的神圣地位,变成了一个受到操纵的工具 。监狱的诞生就是规训的一种极致。它是规训进入司法并变得极为有力而有效的标志。 监狱在使审判和惩罚分离的同时,隐匿了惩罚的压迫形式,使其变成一种在技术上可以 监控的教育、治疗和矫正行为。如果说专制时代的惩罚是进行肉体消灭的话,那么以规 训为特征的现代惩罚机制则是一种制造新人的生产性活动。
对于这种以监狱为典型的规训结构的广泛权力,福柯表示了应有的担心,他在《规训 与惩罚》中指出,如果说围绕着监狱有一个全局性的政治问题,那么,“目前的问题是 ,这些从事规范化的机制及其通过新纪律的扩增所具有的广泛权力被过分使用了”。[1 ](P352)“监狱是执行法律、教育人尊重法律的机构,但是它的全部运作都具有滥用权 力的形式”。[1](P300)福柯的担心渊源于对现代性后果的忧虑,渊源于现代性对人性 的规训而导致人的客体化的趋向。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规训社会产生的历史背 景及其运作机制的揭示与剖析,使人不禁对规训社会与法西斯集中营产生关联性想象, 从而喟然猛醒。在《规训与惩罚》的末尾,福柯有意识地重申了规训社会的任务及其实 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 人性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多种‘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 身就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话语的对象。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 来的战斗厮杀声。”[1](P354)福柯认为,人性中这种足以令人警醒的厮杀场景,应当 成为一种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历史背景。无疑这反映了福柯对主体命运的深深忧虑,而这 种忧虑之中也渗透了极大的无奈。但毋庸置疑的是,福柯的论断使关于主体解放的哲学 思考和如何建设自由的法律制度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这是福柯给我们开辟的最大的 知识领域。
收稿日期:2004-0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