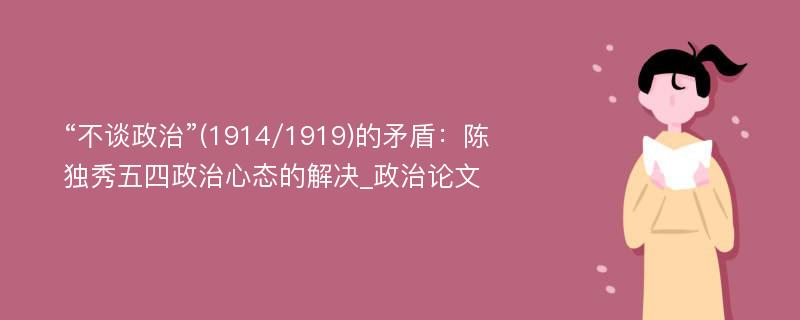
“不谈政治”的悖说(1914-1919):对陈独秀“五四”政治心态的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不谈论文,陈独秀论文,心态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主要是为解决“五四”时期陈独秀介入“政治”与否而为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位一直充满政治热情的人物由“行”而“知”的转变众说不一,而且有着不同程度的偏颇。但归根结底还都是流于对陈独秀不以“批评时政”为旨的声言之理解,从而得出了不涉政治的皮相之论。比如有的学者就曾这样轻率地将政治和文化作了水与火的处理:“他(指陈独秀)在文化战线上是勇敢的斗士,到了政治战线上便成了软弱的懦夫;空说些政治原则时,好象还激昂,涉及现实政治时,便失去了勇气。”①更有甚者,这种现象竟成了“思想上的两重性”——“革命性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②如果说这些说法不免有“历史”的痕迹,不必苛求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顺从海外来风将《新青年》说成因惧怕袁世凯反动势力而不涉时政就不可回避了③。当另一位美国学者把“一直到1919年,陈独秀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循政治上不参与的原则”④作为证据填补空白时,我们尤感如是。笔者以为,在“不谈政治”与“谈政治”之间存在着历史的表象与历史的真实相左的悖论。若是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形成对话,我们就很难理解陈独秀政治心态的真实内蕴,也就无法对这一历史悖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本文在对“谈”与“不谈”作一扫描后,继之将“谈”的内容作实性分析,同时也对其角色转换的动因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
关于不涉政治与“谈政治”,本来就是一个悖论。值得说明的是,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并非一个心理或说思想变化过程,而只是潜意识的显现、外化。换言之,“不谈政治”是意识中显露的层次,“谈政治”是意识中潜隐的层次。下面本文就从“五四”实际出发考察一下陈独秀心理流程的来龙去脉。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即申明曰:“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⑤1917年7月陈再次声明:“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⑥这些都是学界同仁得出陈不愿与政治为伍的主要事实根据。勿庸讳言,从文字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真实。然而时隔一年陈独秀的“食言”却又不能不令人“瞠目”:“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说什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⑦1918年7月陈独秀的这段表白其实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输”的表现。毕竟,压抑在心里最底层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不甘寂寞,以至于陈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为自己开脱:“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但我们要认真了解政治底价值是什么,决不是争取权利的勾当可以冒牌的。”⑧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无论“政治底价值是什么”,但就先前与同仁的契定而言,也堪称是对诺言的“食言”了。将不愿谈政治的责任推给同仁,一样使陈独秀尴尬,这从他最亲近的朋友胡适的回忆中可窥见一斑:“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但是不容易做得到,因为我们虽抱定不谈政治的主张,政治却逼得我们不得不去谈它。”⑨
从胡适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确是他与陈独秀等同仁的默契。而且两人对后来的角色转换的心理动因却异口同声。诚然,如其所言,作为“政治人”,只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中,他就不可能逃避政治。就此而言,他们的有违初衷,实在有些“逼上梁山”的味道。关键还在于,在“逼上梁山”的背后有着更为值得论析的内在真实。我们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渐进流变过程中不难由“微言”见“大义”。
《新青年》杂志同仁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一开始就将“政治”与文化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切割后的文化与政治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更何况这种切割只是一种表式上的偶然,而非质意的必然呢?必须看到,无论是谈与不谈,也无论是陈还是胡,其溢于言表之辞中每每都出现“辅导青年修养”与“政治因素”的对立问题。从这种“言必称”的对立并论中隐约可见其不可思议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愈是当事者强调两者的对立,愈令人感到两者外疏内亲。其实笔者对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暖昧并不是乱出狂言,从胡适所说的从思想文化这些“非政治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这一悖论中我们不正可以求证到一些蛛丝马迹吗?这样的例子很明显地表现在陈独秀的言辞中。众所周知,《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那段声明已够明晰的,无非是以辅导青年修养为天职,不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然而时值1917年7月那篇《答顾克刚》中对“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的发挥就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当胡适将“教育思想文化”列“为政治的因子”与“政治”相对时,当陈独秀把“青年修养”与“政治”作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处理后,我们同样感到这种简单的划定背后潜隐着即将来临的困窘。
果不其然,就在答顾克刚的公开信中作了明确声言之后不到一年,陈独秀便有了有违初衷的逆转:“一方面固然不以绝口不谈政治为然,一方面也不愿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钱当作政治的先生们谈政治。”⑩针对外界批评和形势所逼,陈独秀本来想为自己开脱,但他并未因此找到一个轻松的“台阶”,连他本人后来也不能不对自己难以自圆其说的立论感到苍白:“以上的说话,虽然可表明我对于政治底态度,但是过于简单,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11)因此,他不得不在1920年9月专此撰写《谈政治》一文为其陡转辩护。
二、“谈政治”的方位与内涵
令人费解的关键在于,在种种声明背后,陈独秀一直是一位关心和追求政治理想的学者。这也是有人将其说成是学者加战士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满意陈独秀的“此一时”与“彼一时”。笔者同意他本人所承认的“没有说出充分的理由”之自谦,同时需要他个人出面对此作出解释。
我希望读者同意本文即将论证的一个观点:陈独秀从思想文化入手解决问题,不是逃避政治,更非惧言,而是立于更高层次,站在新的角度,从更为切近现实的着眼点去关心政治。他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之演说中这样谈到:“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我们不是不要宪法,是要在这会上造成自然需要新宪法底实质,凭空讨论形式的条文,是一件无益的事。”(12)这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正是本文“大胆假想”的立论基础。为了便于理解“此一时彼一时”的原委,我们不妨从批评与回应的双向矢动中找证据。
就在陈独秀“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声言发表后,很快就有了社会上不同意见者的批评。汪叔潜在前,顾克刚在后,两位读者分别于1916年9月和1917年7月向陈发难。对此,陈只得仓促应战:“《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腐败无耻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13)在与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的讨论中,亦有这样的论述:“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14)这里的回应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辅导教育青年并非与政治无关,它是求未得之进步政治的一个出发点;二是谈政治不一定非要有语言涉及政治术语和具体事件才算此范畴。可见,陈独秀在未公然申明谈政治之前已胸有成竹。这也反映出陈不但一直未脱离政治领域,而且个人所理解的“政治”在此有了全新的意义。
那么,何如其然呢?他曾将谈政治的人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更进一步”的“大政”。陈在将自己要谈的政治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作了区分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自命道:“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遍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心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5)他之所以作此表白,实与外界压力有关:“外边对于本志的批评,有许多人说《新青年》不讨论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对于这个批评也不能十分满足。”(16)正是从其辩护色彩浓厚的口吻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更进一步”的政治,“国命存亡之大政”,还是“新的政治”,抑或“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归结到“政治底价值”一点上来,都不越走文化启蒙主义之路。
针对国民“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下的状况,陈抱定“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17)由此开出了疗救国疾的处方:“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数,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8)所谓“社会国家基础”,即是胡适所说的“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大政”方针。就此而论,陈独秀从思想文化入手,立足于“政治思想学说”,同样是对“全力解决政治问题”的努力。如果说这种立于“政治思想学说”的努力尚属政治文化层面的运作,那么必须指出的是,“五四”文化启蒙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并没有停滞在先前知识者的政治改革之思想水准,而是将政治文化启蒙与其它文化因素的变革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19)并驾齐驱,这不能不说不但不是畏言政治,而是立于更高的层次关心政治。
三、角色转换的动因
本文认为,陈独秀的由“行”而“知”的转变充其量是一种不带任何质变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是与其前期活动一脉相承的。问题在于,新文化运动既非一场单纯的文化革命潮流,亦非以文化与政治简单相加所能概括的社会思潮。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分别归属于启蒙与救亡范畴,便二者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非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有陈独秀思想上存在着“两重性”的认识。其实,陈独秀的角色转换有其真实的内在背景。
承上可知,在“政治”问题上,陈独秀由“行”而“知”只是完成了从“政治家”到“政论家”的角色变化。应该看到,这种“换角”自身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不经过一番深沉痛苦的思考不能道此言:“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20)深知国家发展在教育与实业,而现实却需反其道而行之,这正是痛苦而又切实的救亡之举。
近代中国的现实是:“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请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21)此等现实,也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老革命党人在身体力行的感悟中发誓要刷新“过去之长物”,(22)抛弃“党派运动”,从事“国民运动”。陈认识到,囿于“范围过狭”的政党政治革命,民主共和终将“不保”。“政党政治”毕竟与“专制的个人政治”情同手足。因此他笃信启蒙的不可或缺作用。陈认为,“其民适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23)鉴于国内现状,中国启蒙的任务分为两步:第一是使国民有一个“政治的觉悟”,第二是实现“伦理的觉悟”,而且这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而其中第一步又分为三步走:首先是对国家责任感的认同;其次是对专制与民主政治良莠的通达;最后是“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的能动性发挥。不难发现,“政治的觉悟”与政治文化水平相对应,实现这第一步的觉悟就必须以政治文化之思想修养启迪民智,促其速醒!用陈独秀的话表述即是:“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24)基于这种认识,真正的民主共和就必须打破这一格局:“例如今日之中国政象如斯,吾人有何方法从事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乎?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所讪笑者。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25)
“政治家”的卓见不仅表现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启蒙。如上所述,关键还在于“五四”文化的价值取向已将伦理觉悟与政治觉悟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对此,我们可以从先驱者由立人而立国的思维逻辑中窥见一斑。勿庸讳言的事实是,既然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26),那么我们就容易理解和认同这么一个理论述说:“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27)可见,陈独秀“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28)正是对前期言行的彻底检讨,而其检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彻底觉悟”的基础上求得进步光明的政治国体。从“文化运动”,到“国民运动”,再到“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这就是文化先驱的追求。他说:“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的问题”。(29)与此同时,人人参预的“国民政治”乃为真正的民主共和,所以又必须在心理与观念变革中扎营垒,打硬仗:“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革,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30)从陈独秀的心态来看,他决心花大力气、用长时间去解决近代思想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共和,此皆吾民之师矣。”(31)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思想为武器,借鉴法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从而使陈独秀的文化选择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审视文化冲突的基本线索不难发现,陈独秀的这一文化价值取向顺应了历史的要求。追溯中国近代思想上的启蒙历程不难发现,先代知识者业已觉察到心理思维层面翻新的必要性。如严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智”,梁启超的“新民说”均属“立人”思想的发端。然而无论是受益于进化学说,还是恍悟于日本明治时期脱亚入欧改造国民性潮流,这种个性解放的思潮始终为直接力行的救亡呼声所压倒。于是在启蒙与救亡的课题下形成了不协调的变奏曲。连梁启超这位深明大义的思想巨擘也不能“服从”了这一选择:“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32)此后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未能解决好这一矛盾:“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33)由于时代的局限,提高国民素质的“立人”课题始终未能提到重要日程。这种追求“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表现在,即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34)历史进展到“五四”,不能不说埋下了时代的里程碑。
要而言之,从“文化运动”(思想启蒙),中经“国民运物”(运作方式),直至“国民政治”(理想目标),三者之间构成了联环式的因果逻辑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条件,后者则成为前者的目的和归宿。来自现实感的文化选择之逻辑构成自成一体,这正是陈独秀由“行”到“知”,由“知”而“行”之悖论的来龙去脉。
余论
综上,我们得出了这样几点结论:陈独秀不谈政治是虚,谈政治为实,他所谈的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立足于更高层次去关心中华民族走向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从“政治家”的直接行动到“政论家”的间接投入,其角色转换是中西文化冲撞下对现实体认的结果。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好象给陈独秀开了一个玩笑。我们看到,自1920年始,陈认识到了唤醒国民觉悟的虚妄,深感面对如此庞大之系统工程的无力,转而又对自己设计的由个人改造积累进而获得整个社会改造方案进行了否定。这种内心失落的痛苦与矛盾突出表现在《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本来,五四启蒙的宗旨就是借助新文化运动达到改造社会、国富民强的“救亡”目的,陈独秀本人就曾把文化运动称之为“人的运动”,但在这里陈又故伎重演,再次将文化与政治革命截然分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35)对照陈“谈政治”的原委,真有自我嘲讽的意味。难道这种自我不一的变幻不正是陈所嘲弄的那种最不幸的“一班有速成癖的人们”吗?两相类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36)岂又不是自我的写照?
曾经在幽幽显显中的反复反映了陈独秀的政治心态的何等复杂!诚然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陈的“转换”与变化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岁月中仓促应急的表现。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令其只能在理论的可塑性上寻找栖身之地。如果说前“分”是一种理论零乱的潜在,那么后“离”不能不说是有意识的人为悲剧。该借鉴的“师资”不能得以履行,该走的路不能走下去,而且是“ 梦醒了以后”有路可走而不去走。对“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启蒙耐不住寂寞,结果只能是饮恨千古。
注释:
①②⑨《陈独秀评论选编》,上篇分别见孙思白和彭明先生两文,下篇第289页,见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一文。河南人民1982年第1版。
③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1988年版。
④[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43页。
⑤⑥⑦⑧⑩(11)(12)(13)(14)(15)(16)(17)(18)(19)(28)(21)(22)(23)(24)(25)(26)(27)(28)(29)(30)(31)(35)(36)《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篇见第82、225、268、82-83、127、148、172、127、103、109、269、144、99页。中篇参见《谈政治》及《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文。
(32)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
(3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34)《马恩全集》一卷第4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