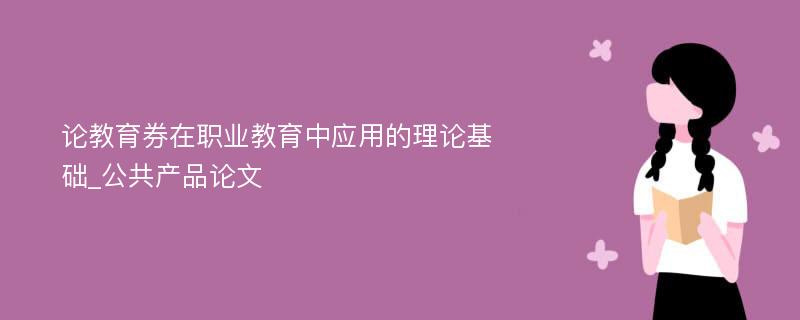
论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理论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08)09-0126-03
一、职业教育应该被教育券排除在外吗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但正式提出教育券理论并使得这一理论为世人所知晓和接受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理论。1980年在著作《自由选择》中,弗里德曼又进一步阐述并完善了这一理论。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提出,政府应该承担教育的职责,但政府的官僚主义和集权政治造成了教育的低效,解决的办法是采用政府直接管理的方式,运用教育券赋予学生和家长充分的择校权利、调动学校的竞争积极性,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解决政府对教育垄断的弊端[1]126。弗里德曼在提出教育券理论时,将职业教育排除在教育券的适用范围之外。其理由主要是,邻近效应的功能决定了政府应该投资义务教育,另外,高等教育培养领导阶级和社会精英,国家也应该支持高等教育,而职业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个人,所以应该由个人支付教育的费用。在这里,弗里德曼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不在教育券的适用范围之内。笔者认为,实际上弗里德曼误解了职业教育的性质,进而错误地将政府从职业教育投入的主体地位上排除出去。近年来,教育券的实践也突破了这一限制,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一些地方之所以引进教育券正是为了解决职业教育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但是如何从理论上论证教育券在职业教育中适用问题却没有最终得以解决,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二、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是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的前提理论基础
弗里德曼将职业教育排除在教育券的适用范围之外的立论基础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受益者是受教育者本人,这就首先牵涉到关于职业教育的性质定位问题。在经济学上按一定的标准可以将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统称产品)分为三类,即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2]24~28。如果将职业教育定位为公共产品,其费用应该由政府承担;如果将职业教育定位为私人产品,费用应该由受益者本人承担;如果将职业教育定位为准公共产品,费用应该由受益者本人和政府联合承担。具体到教育券能否在职业教育中适用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将职业教育定位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这样教育券才能在职业教育中适用;如果职业教育为纯粹的私人产品,则教育券就不能在职业教育中适用。
王善迈教授认为,私人物品(亦称产品)和劳务是指这些物品和劳务的利益只为购买它的消费者个人单独享有,而不产生外在的利益;公共物品和劳务是指这些物品和劳务的利益为社会共同享有,而不能为任何一个人单独享有[3]27。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nl.A.Samnelson)指出,纯粹公共物品是这样的物品,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4]58~59。从上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区别主要在于三点。其一是效用是否具有排他性,公共产品是向整个社会提供的,没有排他性,私人产品则相反;其二是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一个人或一个单位消费时,实际上就排除了他人或其他单位的消费,公共产品则不然;其三是费用由谁负担,私人产品由享有该产品的个人或单位依据市场价格来承担,公共产品的费用则由政府来承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它兼有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一方面,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将不付费者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具有外在利益,可以为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不能把一些人排除出去。由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主要由政府提供。同时又由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私人性,所以享有者应支付一定的费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给职业教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一方面职业教育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在既定教育规模下,职业教育消费的边际成本为正,不可能使所有希望接受职业教育者都如愿;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不仅仅使受教育者受益,还能产生巨大的外部效益,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等等。因此,职业教育既不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它兼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性质,属于准公共产品。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要求受教育者和政府共同分担教育成本,教育券无疑可以成为政府分担职业教育成本的一种形式。所以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
三、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主导作用是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的核心理论基础
教育券是一种公共教育费用的支付形式,是指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凭证的形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学生或家长可用来支付所选学校的学费和相关教育费用。学校收到这一凭证后可以从政府那里兑换与券值等额的教育经费[5]17~19。从教育券的运行过程来看,其实质就是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投资由原来的直接拨款给学校,转化为通过教育券的形式对学校的间接投入。如果政府需要在职业教育投入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则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反之,如果政府不需要对职业教育进行任何投资,则教育券就不可能在职业教育中适用。所以,要想论证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就必须明确政府在职业教育中所处的地位和应该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正是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主导作用构成了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的核心理论基础。政府应该在职业教育投入中发挥主导的作用,其依据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不可否认职业教育具有很大的内部效应,受教育者可以从职业教育中获得一定收益。但是也不能否认职业教育同时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个人接受职业教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对社会文明的进步甚至对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上看,国家始终是职业教育的最大买主,也是最终受益者,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正是职业教育的外部效应决定了政府应该在职业教育投入中负主要责任。
2.保障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职业教育纯粹依靠市场来提供,那么将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与状况受到个人家庭收入水平的制约。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子女很可能因家庭收入较少而得不到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已成为决定一个人未来收入水平高低,乃至成为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关键性因素,一个人若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则意味着他可能继续贫困下去,或者说,不均等的职业教育机会将会使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局面继续下去。那么这种状况,对那些家庭收入低,但本身又很有才华的子女来讲,是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也就是作为社会代表的政府有义务改变这种不平等,保障每一个符合条件的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对职业教育进行投资,从而降低职业院校的收费水平,以便减少因家庭收入低对个人接受职业教育的制约和限制。
3.政府集中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主导地位,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而是指财政收入的集中性。它归政府所有和支配,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分配。相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收入虽然在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份额,但这部分收入属于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它是分散的,每个企业和个人所能支配的仅仅是归他们所有的部分。这就决定了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量来看,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另外由于个人和企业对职业教育投资作为一种“自发”的投资,很容易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或影响,使本应由个人和企业提供的投资可能因此出现一定的供给不足或短缺,从而影响到整个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这时也需要发挥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无论从负担能力来看还是从保证职业教育顺利发展来看,都需要政府积极投资职业教育事业。
四、教育券理论自身的发展是教育券对职业教育适用的关键理论基础
随着教育实践需要的变化,教育券理论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弗里德曼教育券理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美国公办教育质量差、效率低的现实,着眼于在教育中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于是弗里德曼主张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与此相适应,教育券发放的完全平等,反对运用教育券对现存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进行调节,所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又被称为自由市场竞争模式的教育券理论。自由市场竞争的教育券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但是不能解决教育发展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由于教育券的券值有限,穷人的孩子虽然拿到了教育券,仍就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只能选择收费较低的学校就读。
这种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教育券理论在提出之后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认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研究者将教育券用于改进社会公平的目的,他们设想出一种带有更多社会调节作用的教育券。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多佛·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他把教育券看作为贫困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应根据家长的收入水平来提供教育券[6]63~69。197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约翰·库恩(John Coons)和斯蒂芬·苏各曼(Stephen Sugarman)完善了詹克斯的教育券理论,提出解决教育不平等的有效方法,就是给贫困生发放教育券[7]20。由于这些教育券理论着眼于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而非市场效率,所以被称为社会政策调节模式的教育券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的冯晓霞教授用“排富性”教育券模式和“无排富性”教育券模式[8]26~310,来分别指称社会政策调节模式的教育券和自由市场竞争模式的教育券。如果说“无排富性”教育券模式主要关注的是提高公立学校的办学效率问题,则“排富性”教育券模式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公平问题。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价值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讲,人们往往将公平等同于正义,认为实现了公平也就实现了正义。从教育券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现代教育券更多的是侧重教育公平,并且日益成为政府调节教育的一项重要的手段。教育券理论的发展和关注重心的转移,为教育券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适用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像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一样,实现教育公平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要求。通过发放“排富性”教育券,可以保障贫困家庭子女在接受职业教育方面有均等的机会。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要求政府应成为职业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主体,为教育券在职业教育中适用提供了前提理论基础;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为教育券在职业教育中适用提供了核心理论基础;教育券理论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关注重心的改变,为教育券在职业教育中适用提供了关键理论基础。总之,无论是从职业教育的性质、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教育券理论自身的发展,都证明教育券可以而且应当在职业教育中得以适用。
收稿日期:2008-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