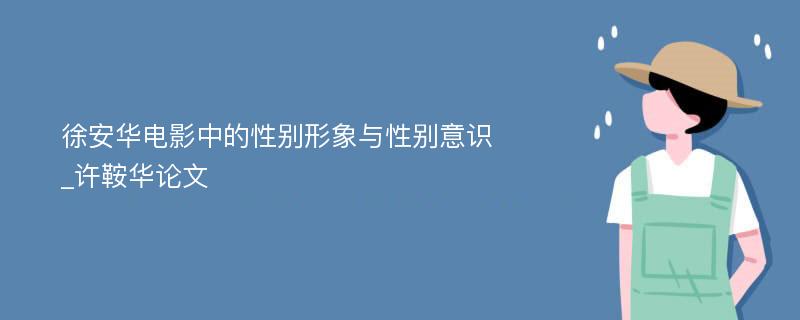
论许鞍华电影中的两性形象及其性别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性论文,性别论文,意识论文,形象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4-146-06
一、一个悬了十多年的问题
许鞍华曾经是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中唯一的女将。她执导的电影先后三次荣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她本人则两次赢得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奖。2003年,许鞍华还应邀担任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她被誉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女导演之一。毫无疑问,她是港台女导演群体中成就最卓著、国际影响最大的一位。但早在1997年,香港影评家石琪在评论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许鞍华执导的《半生缘》时写道:“想不到女人原著、女人导演的此片,简直有点‘反女人’。”[1](P80) 换言之,十多年前,许鞍华的电影就已经背负了反女人的嫌疑了。
2007年,风云再起,许鞍华执导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再一次被质疑为具有反女人的倾向。北京电影学院杨慧副教授认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勾勒了一幅人生失败的女性群像图:从不断遭遇人生尴尬、最终从热情自主走向颓唐依附的姨妈,到人鲜衣丽、号称热情欢快却骤然魂随宠猫逝去的水太太;从另类不可一世、却只有半张面目的少女飞飞,到舍命为女儿却沦为阶下囚的贫女金永花;从得意洋洋却疯癫痴傻的老外婆,到刁悍张扬却心高命薄的少妇刘大凡,以及那蓬头垢面、愚蠢得可怜的洗鱼妇,这是一群在容貌/身体、婚姻/家庭、精神/物质、职业/地位等各方面都命运多舛、最终未逃过苟且结局的女人们。由于她们基本涵盖了女性的各个年龄段及其相应的人生角色……因此,影片的中心意图显然是从一定侧面描写当代(我国相当一部分)女性的精神面貌和人生处境,并且影片似乎是在断言:女性的人生奋斗只能落得荒唐无奈之果。”“由于影片在结局中实际强化了一种来自姨妈自身的忍辱负重、认命无奈的情绪,所以,又似乎是以姨妈的现身说法宣示:一个女人,她的自主追求终归是竹篮打水,她无法拗过命运的安排,最好是安分守己地不要追求、挣扎。”文章问道:“究竟影片是在同情女性被压抑的处境,还是在默认社会束缚她们的现实,抑或意在继续潜移默化女性的传统宿命观?”[2](P19-20)
我并不完全认同杨慧副教授的观点,但我以为,她至少是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许鞍华在青年时代曾获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远赴伦敦电影学校,系统地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属于文化程度很高的知识女性。那么,许鞍华是怎样理解并在其电影中表现女性的不幸和苦难的?她真的以为女性的人生奋斗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女性应放弃一切的人生理想和自主追求,而接受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加诸她们身上的种种不合理的压抑和束缚吗?本文就从这些问题切入,来探讨许鞍华电影中两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性别意识的表达。
二、许鞍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早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前,许鞍华的电影就已经塑造了一系列不幸的女性形象。在《胡越的故事》(1981)中,越南华裔少女沈青打算偷渡去美国,却被卖到了菲律宾的妓院。胡越(周润发饰)想方设法“英雄救美”,但结果,沈青却被飞刀击中颈部而香销玉殒。在《投奔怒海》(1982)中,阮琴娘是一位14岁的花季少女,生活在越南社会的底层。她在被枪决的人的尸体上寻找值钱的物品,来获得一点经济收入。后迫于生计,她去卖淫,被摄影记者芥川先生劝止。琴娘的弟弟被地雷炸死了。琴娘的母亲是私娼,得知儿子惨死的噩耗后,她精神失常,自杀身亡。《投奔怒海》中还塑造了一位女子,她是一家黑餐馆的老板,曾先后做过日本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的情妇,如今则为越南的新贵干部服务。这是一个完全认命的女人[1](P44)。显然,这个女人与琴娘母女都是不幸的女性。
《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是许鞍华早期电影的代表作。《极道追踪》(1991)则是她中期的一部电影。这三部电影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片中的女性大多数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而她们都没有主动地进行反抗(琴娘母亲的自杀充其量只是一种很消极的反抗)。拯救她们的,都是男性(胡越、芥川先生等)。或者说,领导并支持她们反抗的,都是男性。其次,《胡越的故事》的女主角被卖到妓院;《投奔怒海》中的琴娘一度打算去卖淫,琴娘的母亲是私娼,那家黑餐馆的女老板是交际花;而在《极道追踪》里,女主角孟铁兰在日本一度沦为陪酒女郎,小张的女友潘大好则沦为三级片的女演员。简言之,这三部电影中的大多数女性都险些要从事或已经从事色情行业,充当男人的性玩偶/性奴隶。
在这三部电影中,许鞍华虽然对女性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悯,然而另一方面,她在电影中所传达的,首先是传统男权社会对两性关系的狭隘而刻板的认识,即男性是启蒙者、领导者和拯救者,女性则是被启蒙者、被领导者和被拯救者。其次,这三部影片把大多数女性角色的职业设置为与色情服务有关,这固然可以被读解为对丑恶社会现实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却也具有了迎合某些男性观众的窥淫癖之嫌疑。实际上,《胡越的故事》中就有唐人街的钟老板(男性)玩弄沈青身体的段落,《极道追踪》也以一些篇幅详细表现了夜总会里的女演员在男性观众/消费者面前展露自己的身体、进行色情表演的过程。
我们可以为许鞍华辩解说:执导《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时,她还只是一位新人,所以不得不屈服于电影公司的老板,不得不迎合市场的需要;而《极道追踪》本身就是一部商业片,自然得遵循商业片的游戏规则。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十分清楚,在传统的男权叙事里,女性角色的价值主要在于甚至仅仅在于她们的身体/美色是满足男性性欲的对象;而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电影里,女性角色的价值主要在于甚至仅仅在于她们性感的身体是供男性观众进行色情窥视的客体和视觉消费的商品。许鞍华在这三部电影中对大多数女性的职业身份的设置,暂且不论其主观动机究竟如何,仅就客观效果而言,是体现了与传统的、男权至上的性别文化策略的高度一致。也就是说,虽然身为一位女导演,许鞍华在这三部电影中所表达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与一般的男性电影人几乎并无二致。
2006年初,香港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栏目曾经专门对许鞍华做过一次访谈。在节目中,女主持人许戈辉问:“假设有来生的话,您愿意做什么职业?”许鞍华答:“我希望我的来生呢,要不就是一个警察,要不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对于许戈辉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有来生的话,愿意做男人还是愿意做女人?”许鞍华的答案仍是:“如果是男人,就当警察;如果是女的,就要漂亮。”[3] 如果做女人,就要做一个漂亮的女人。这表明,在许鞍华看来,社会目前是而且未来将依然是男权社会,女性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她的外貌,而不是她的学识和才能等;对于这样的社会(男权社会)现状,许鞍华的抉择并不是反抗和颠覆,而是(无可奈何地)顺从和接受。
《客途秋恨》(1990)中女主角晓恩被设计为曾留学英国,晓恩的母亲被设定为一位日本籍女子。这些都与许鞍华本人的情况完全一致。所以有评论把该片称为许鞍华的“半自传体”电影[4](P91)。然而,该片“取了女性题材的外观,但主旨并没有落在女性问题某个单一层面之上,它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5](P91),以及游子对祖国及其文化的复杂的心理认同过程。这些,显然是具有普泛意义的主题。而由于许鞍华在该片中关注的是这些具有普泛意义的主题,所以,女性立场、女性意识和女权意识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的表达。
《女人,四十》(1994)是迄今为止许鞍华最优秀、最重要的女性电影。《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表现了乱世之中年轻女子的不幸遭遇;《女人,四十》则反映了和平环境之下中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艰辛。电影进行到2分28秒处,有这样一个镜头:丈夫和儿子穿着休闲的衣服,悠闲地躺靠在沙发上,双腿翘在茶几上,而一旁的阿娥脖子上搭着毛巾,腰上系着围裙。在这个镜头里,男性在家庭中的轻松、悠闲与女性在家庭中的忙碌、操劳,形成了直观而鲜明的对比。不久,婆婆突然去世,公公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于是,照顾公公的重担就几乎全部落在阿娥的身上。此外,阿娥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对阿娥也很依赖;阿娥的儿子也经常要向母亲请教恋爱等方面的问题。然而,阿娥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她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她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业务熟练,深得老板的信任和依赖。
在《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和《极道追踪》里,男性往往充当着领导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女性则基本上是被领导者和被拯救者①。但在《女人,四十》里,阿娥成为实际上的领导者、拯救者、施助者,而男性则恰恰相反。并且,男性与女性之间也具有平等合作和互助的关系②。因此,《女人,四十》标志着许鞍华对两性关系表现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女人,四十》还塑造了一位老年女性霞姨的形象。霞姨患了胃癌。在医院里,她对老公说:“我求佛祖下辈子不要分配我做你的老婆,而是让你做我的老婆。”这句台词不仅道出了为人妻子的辛苦,而且表达了对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的不满。霞姨的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阿娥的明天。霞姨的这句话也道出了阿娥的心声。许鞍华对阿娥、霞姨等女性人物表达了由衷的理解、同情和赞美。从这个意义上讲,《女人,四十》是许鞍华电影中女性立场、女性意识和女权意识表露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影片。这样的性别立场和性别意识在她此后的电影中究竟是得到了坚持和深化,还是发生了游移呢?本文将在后面再进行具体的论析。
《半生缘》(1997)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改编的。石琪先生评论说:在该片里,“女人不断与女人作对,越亲密(的女人反而)越可怕。亲姐陷害亲妹,母亲(和)祖母也不帮女主角谋求幸福,男家母亲又擅自烧掉(女主角寄来的)求救之信。可以说,打击女主角最重要的不是命运与环境,而是其他女人一个一个使她陷于悲剧。想不到女人原著、女人导演的此片,简直有点‘反女人’”。[1](P80) 我认为,石先生根据这些情节设置而说《半生缘》有点反女人,或许有失偏颇,因为就许鞍华而言,电影这些情节都是小说原作所设置的。《半生缘》删掉了小说原作的结局,大大降低了小说原作反女人的倾向。被姐夫强奸以后,女主角曼桢怀孕了。于是,她被幽禁了10个月,直到因为难产而被送往医院,她才伺机逃出魔窟。后来,姐姐病死了,姐夫也破产了。女主角出于母爱,跑去照顾正在患病的小儿子。电影的情节演绎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但小说原作的结局是:在照料小儿子的过程中,女主角与姐夫又相见了;后来,女主角居然嫁给了她深恶痛绝的姐夫,但姐夫却继续在外面花心,女主角苦苦忍受了好多年,最终才下定决心,与姐夫离婚。许鞍华之所以删掉小说原作的这些情节,是因为女主角自愿嫁给一个强奸犯,这样的情节设计实在是有违常理;如果按照张爱玲小说的这种结局拍出来,将大大损害女主角作为女性的人格尊严[1](P82)。在《十八春》和《色·戒》等小说中,张爱玲倾向于将中国女性塑造成受虐狂。在这一点上,许鞍华显然并不认同张爱玲。
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许鞍华是先通过宽宽的视角来看姨妈的。宽宽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生活在东北。那是我国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的地区。长期在男权文化中耳濡目染,宽宽对姨妈(一位女性)很可能带有鄙视乃至敌视的成分。此外还有代沟的因素。所以,宽宽视角中的姨妈有可能被丑化甚至妖魔化。许鞍华虽然先以宽宽的视角来表现姨妈的形象,但这未必表明她就认同宽宽对姨妈形象的丑化或妖魔化。实际上,当影片进行到27分半钟的时候,宽宽就已告别姨妈、离开上海了。一直到影片进行到1小时34分钟的时候,姨妈抵达东北鞍山,才与宽宽重逢。也就是说,自第27分半钟至1小时33分钟,在长达65分半钟的这段时间里,影片并没有采用宽宽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宽宽的视角进行叙事的那27分半钟内,关于姨妈的信息几乎全是负面的。
情节1:姨妈家里明明有冰箱,但她不用,而是把需要冷藏的物品放在附近小卖部的冰箱里。该情节凸显了姨妈的吝啬。
情节2:夏天热,宽宽要求姨妈开空调,但姨妈一口拒绝了。没有空调,宽宽热得睡不着觉,而姨妈的卧室里却开着空调,她老人家睡得香喷喷的。然而早餐的时候,她居然装出一副睡眠不足的模样,对宽宽诉苦道:“昨天晚上姨妈都没睡好,失眠了。”该情节凸显了姨妈的吝啬、自私和虚伪。
情节3:姨妈见一位老板娘在路边宰杀一条鱼,把鱼鳞扔在路面上。姨妈请老板娘将鱼鳞捡起来,老板娘却置若罔闻。于是,姨妈请来了城管人员,好好地给老板娘上了一课。表面上看,姨妈是在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但姨妈是在她的一份家教工作几分钟之前刚刚被辞掉之后做这件好人好事的。所以,姨妈的动机就非常可疑了,很有借维护环境之名来发泄自己不爽情绪的嫌疑。
情节4:姨妈去向“匪徒”交赎金,虽然有几位警察贴身监护着,姨妈却仍然害怕得要命,吓得全身哆嗦。该情节凸显了姨妈的胆小怕事。
情节5:在与水太太等人的交往中,姨妈表现出说话尖酸刻薄、嫉妒心强等缺点。
在以非宽宽的视角进行叙事的那65分半钟里,关于姨妈的信息就变为以正面信息为主了。打工女子金永花被黑心老板拖欠工资,而金永花的女儿重病住院,急需用钱。姨妈与金永花素不相识,却向金永花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段情节表明,姨妈是善良而乐于助人的。当发现金永花通过碰瓷来讹诈别人钱财时,姨妈立刻辞退了金永花的保姆工作。这显示出姨妈是非分明。至于投资墓地被骗,在该事件中,姨妈显然是一个受害人。许鞍华此时在片中对姨妈表达了充分的同情。
有研究者指出,影片名为《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而“姨妈”这个称呼是宽宽使用的,所以影片应该始终采用或主要采用宽宽的视角。但实际情况是,影片的视角非常不统一[6](P69)。这个说法有道理。不过我以为,倘若撇开这个问题暂且不谈,而将片中视角的转换读解为许鞍华是在以较为客观的全知视角(摄影机视角)来纠正宽宽的主观视角,继而对被宽宽丑化或妖魔化的姨妈形象进行一番拨乱反正;或者读解为许鞍华在以另一种主观视角(即一位女导演的视角)与宽宽的视角进行对比,进而表现不同视角之下同一个人物形象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似乎也未尝不可。而且,如果这样来读解该片,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从更加多维的角度来梳理电影文本所提供的关于姨妈这一形象的众多信息符码,而且可以比较不同视角(宽宽的视角,摄影机的中性视角或许鞍华的女性视角)下姨妈形象的差异,及其折射出的不同的性别立场所导致的对于信息素材的大相径庭的筛选、改装和变形。
对姨妈这个人物,许鞍华说:“不能一刀切地说她的人生是悲哀的,或者说是很好笑的。”[6](P71) 我认为,许鞍华对姨妈这个人物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同情和悲悯,也有讽刺和批评。姨妈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她年轻的时候,正是我国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时期。姨妈当年为了在政治上争取进步,嫁给了一位工人,但发现自己与丈夫之间难以建立起真正的爱情。“文革”结束后,也是为了争取上进,姨妈不愿意继续呆在落后的小城市里度过后半生,她回到了大都市上海。在上海,为了紧跟时代的潮流,她积极投资墓地什么的,但结果反而把自己弄得更狼狈。于是只好再回到鞍山去。当然,姨妈之所以回鞍山,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自己当年离开鞍山,毕竟对不起女儿和丈夫,现在想回去弥补一下,为自己以前的行为赎罪。总之,姨妈的不幸也是她那一代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不幸的缩影。对此,许鞍华是充满同情和悲悯之心的。但姨妈的不幸又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和历史;她自己身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加剧了她的不幸。对于姨妈的缺点,许鞍华给予了善意的讽刺和批评,目的应该是提醒女性观众反省自身的不足之处,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女导演往往喜欢表现女性的不幸,而有些女导演会把女性不幸的原因完全推给社会(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或完全归咎于男性(男性对女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这样做或许比较简单、省事,但实际上,女性不幸的原因通常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历史的和男性的原因,也有女性自身的原因。《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的每一位女性都经历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幸。但影片的中心意图并不是为了断言:女性的人生奋斗只能落得荒唐而无奈的结果;女性最好是安分守己地不要追求和挣扎。我认为,在客观效果上,该片可以启迪女性观众:女性摆脱不幸、追求幸福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而是漫长和艰难的;女性必须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能面对来自社会、来自男性的各种压力和挑战,并克服女性自身的缺陷,从而真正踏上幸福之路。
许鞍华在谈及故事片《玉观音》(2003)时曾说:“不希望用(女主角)安心的悲惨命运来感动观众,而要让观众看到她那种承担命运的勇气和力量,那才是最动人的。”[7] 这或许也可以表明,至少在主观上,许鞍华并不认为女人“最好是安分守己地不要追求、挣扎”,并不认为女性应该放弃人生的理想和自主的追求而去接受种种不合理的压抑和束缚;相反,她赞美的是女性“承担命运的勇气和力量”。
三、许鞍华电影中的男性形象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不谈,那就是:许鞍华在电影中是如何书写男性形象的?在《胡越的故事》中,男主角胡越牺牲自己的幸福去帮助女主角沈青;但唐人街的钟老板(男性)则玩弄沈青的身体,欺辱沈青。在《千言万语》中,已婚的宽哥与女主角凤娣发生了婚外恋,并导致凤娣怀孕。但影片并没有谴责宽哥。况且,另一位男性阿东一直喜欢并关心凤娣。阿东不抽烟,但他知道凤娣是抽烟的,所以他身上经常为凤娣准备着一盒香烟。简言之,虽然给凤娣带来痛苦和伤害的是一位男性(宽哥),但另一位男性(阿东)给予了凤娣温暖和关爱。在《男人四十》中,陈文靖在读高三时,曾爱上了自己的一个老师(盛老师),一位有妇之夫,并怀上了他的孩子。在这不幸事件里,盛老师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影片也没有对他表示谴责。况且,陈文靖怀孕之后,林耀国细心地照料她,让她生下孩子,并与她结婚,做起了孩子的父亲。也就是说,虽然是一位男性(盛老师)导致了一位少女的不幸,但另一位男性(林耀国)救助了这位少女,帮她度过了难关。在《玉观音》里,贩毒分子毛杰和他的哥哥对女主角安心及其家人造成了伤害,但安心的丈夫、警察队长老潘和杨瑞这三位男性却爱护和帮助着安心。这四部影片呈现出一个大同小异的模式:伤害女性的男性←女性→帮助女性的男性。在这样的模式下,许鞍华对男性既不是单纯的批评和鞭挞,也不是纯粹的赞美和歌颂,而是辩证的、一分为二的。
许鞍华的其他影片没有采用上述模式,但在男性形象的塑造上仍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立场。在《女人,四十》中,阿娥的丈夫虽偶尔流露出大男子主义倾向,(他曾经对阿娥半是质问、半是抱怨道:“在这个家里,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谁是一家之主?”)但在总体上,他与妻子是一种平等、互敬、互爱和互助的良性关系。
在《半生缘》里,在强奸了曼桢以后,姐夫对曼桢的姐姐说:“都是因为你。本来二妹对我的印象挺不错。这一次,我在她的心目中……”这段台词有两层意思:1、姐夫把责任推到姐姐身上;2、姐夫对强奸曼桢的行为感到后悔和愧疚。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说原作并没有写姐夫在强奸曼桢后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后悔或愧疚(哪怕是在内心里)。因此,许鞍华在电影中给姐夫增加的这段台词,其产生的客观效果很可能是:为姐夫(一位男性)开脱责任,降低观众对姐夫的厌恶。
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老潘是唯一戏份较多的成年男性角色。他到底是与那家公司串通一气欺骗了姨妈,还是与姨妈一样也是该骗局的受害人呢?如果他是骗子,那么在骗局被揭穿以后,他为什么不赶快远走高飞,反而不辞辛苦地守护在姨妈的床边、整整一夜都耐心地陪伴着伤心欲绝的姨妈呢?我认为,老潘的形象设定,既是一种叙事策略,也是一种市场策略。说是叙事策略,是因为它给观众留下了自行思考和独立判断的空间。说是市场策略,是因为它避免了将姨妈的不幸归咎于男性的欺骗,从而规避了得罪男性观众的风险。
四、结语
许鞍华早期的《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等片主要表现社会动乱给女性带来的种种不幸,中期的《女人,四十》等电影重点揭示现存的家庭结构、两性角色分工和社会分工模式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压力,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则不仅探讨了导致女性不幸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且从女性自身去探寻造成其生活不幸的原因。许鞍华更多地是从探讨人性的角度来展开其对两性形象的塑造。她不仅赞美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真、善、美的品格和行为,也讴歌男性的真、善、美的品格和行为;不仅展示女性身上的假、恶、丑,也展示男性身上的假、恶、丑。而她判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准绳,往往是人道主义,而非女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大多数女导演(尤其是当代欧美女导演)相比,许鞍华大多数电影的性别立场比较温和,性别意识较为含蓄。
许鞍华之所以运用较为温和的性别立场,并且淡化其影片中的性别意识,商业层面的考量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按照我国内地电影的标准,许鞍华的许多影片可以划归文艺片的范畴,但在香港电影投资方的企划中,这些影片还是要力争主流市场的。这样,就既要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并抒发女性观众的心声,也不能过分得罪男性观众。实际上,在香港,只以女性作为目标观众的影片,或只以男性作为目标观众的影片,在数量上都极为有限。因此,纯粹女性立场的香港电影是很少的。绝大多数香港电影都是兼顾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许鞍华的电影也不例外。在对于女性人生处境及两性关系的揭示上,许鞍华电影之所以表现出某些局限性,是香港电影的市场环境所导致的。
许鞍华在其电影中表现女性身上所存在着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位“反女人”的女导演。实际上,她同样也揭露了男性身上的各种缺点。人类的发展史应该是人类不断自我完善的历史。用电影胶片来显影人类尚存的缺陷和人性的瑕疵,在主观动机上,或者在客观效果上,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8](P82) 倘若认为女导演就应该一味地偏袒女性、讳言女性的缺点,那就未免有一点狭隘了。况且,那样将无益于女性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收稿日期:2008-08-30
注释:
① 《胡越的故事》有一点例外。片中的女二号李立君与男主角胡越是多年的笔友,李立君无私地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帮助胡越。所以,李立君是一位施助者。
② 这一点,在阿娥与丈夫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丈夫在家庭生活中虽然对阿娥很依赖,但这对夫妻总体上是一种互敬、互爱和互助的关系。
标签:许鞍华论文; 胡越的故事论文; 半生缘论文;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论文; 极道追踪论文; 投奔怒海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