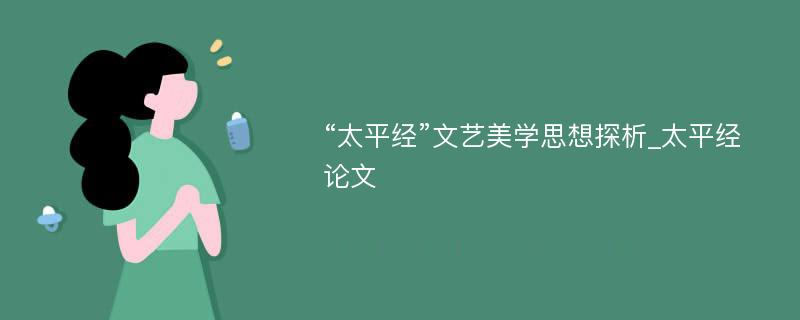
《太平经》文艺美学思想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论文,美学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艺术之美,从本质上来说当然是属于人为美。奇怪的是,崇尚“自然”、“无为”的道教,从《太平经》以来一直用文艺弘扬“至道”精神、宣传教理教义,且在道经中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强调文艺美的必要和重要,常常将儒家传统的“文—道”观点、“文—德”观点,吸收改造为道教的宗教文艺美学观点,将文艺美作为体道之途、弘教之器、化人之大音。这是否与它的“自然”“无为”的理想相冲突呢?它又是怎样把重“道”与重“文”统一起来的呢?应该说,这方面正是一般美学史的阙如或相当薄弱部分,从这里深入开掘一下,也许我们会发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种表现。
一、“出真文”:对真善美的呼唤
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理解,《太平经》所说的“文”,是包括“文艺”形态和自然形态美的。因此,它主张的“出真文”,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欲得天道大兴法者,取诀于拘校众文与凡人诀辞也。欲得良药者,取诀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欲得疾太平者,取诀于悉出真文而绝去邪伪文也。欲乐思人不复杀伤女者,取诀于各居其处,随力衣食,勿使还愁苦父母而反逆也。欲除疾病而大开道者,取诀于丹书吞字,欲知集行书诀也。如其文,而重丁宁,善约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独人心,一旦转而都正也,以为天信。”(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七庚部,影印《正统道藏》本,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出真文”是与太平道的“天道大兴法”、“得良药”、“太平”世界、“乐思人而不复杀伤女者”、“除疾病而大开道”、“消百害独人心”等等重大的宗教理想和具体的救人度世的种种计划相关联的大问题,也是作为达到“太平”世界的前提条件提出。这不可谓不重要了。
什么是“真文”呢?《太平经·核文寿长诀》说:“文书亿卷,中有能增长寿、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文书满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治者,真文也,其余非也。”(注:《太平经》,卷九十八,4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个体讲, “真文”能“增寿”、“益命”、“安身”,是一种有助于、有利于修道的文本;从其内容看,“真文”是“得天心”的,且有“平理治”作用,有助于理顺政治、社会关系。“真文”所运载的“真”理,也就是《太平经》教理之核心的至美的“至道”,其作用和效果是十分巨大、周全的。如在《去邪文飞明古诀第六十七》中,以“上皇神人”答“六端真人纯”问的形式说,如果要“求真”,“欲使天地平安,阴阳不乱,常顺行,灾害不得妄生,王者但日游冶,为大乐之经”等等,诀窍何在呢?神人说,你应该致力于“进至道而退去邪文”,使“帝王能力用吾书,灾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乐,皆欲为道德之士;后生遂象先世,老稚相随而起,尽更知求真文校事”,“如是天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欢乐,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佑之,但有日吉,无有一凶事也”。(注:《太平经》,卷五十,230~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求真”,也就是“求真文校事”,即用“神人”所说的“吾书”来教化天下、指导王者政治,所以要推崇“至道”,远斥“邪文”。说穿了,“真文”就是体现和宣扬“至道”的“神”造经书,包含的是能使天下“太平”、“欢乐”,“各得其所”的至理明言。
《太平经钞》也有对“真文”之“真”的解说。它模拟“神人”语气说,“吾之为文也,乃与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方同理同好同恶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按用之,无一误也;万万岁不可去,但有日彰明,无有冥冥时;但有日理,无有乱时;但有日善,无有恶时也。故号天之洞极正道。乃与天地心相抱,故得其上诀者可老寿,得中诀者为国辅,得下诀者可常自安”,这就是“正言正文正辞,乃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家国宝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万物所受命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里,“真”即“至道”,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本质和总体规律。而至道是至美的,这个“真”,就是一种有别于世俗涵义的宗教“伟大”、“崇高”之美。《太平经》的确也是这么说的:(真文)“书凡事之至意,【故】天地阴阳之文,略可见矣。其头足皆具,上系下连,物类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善者集成一说,是以圣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调定阴阳,而安王者;使天下【太】平,群神遍悦喜。故取众贤荣贯中而制以为常法,万世不可易也。”(注:《太平经》,卷五十《去浮华诀》第七十二,2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笔者作了必要的文字校订。)这也是说“真文”是体现“道”之本质美的一种“形式”。古汉语“真”、“正”相通,“真文”也就是“正文”。所以,其《校文邪正法》就说,(正文)“真得天心,得阴阳分理,帝王众臣共知其真,是乃后下于民间,令天下俱得诵读正文。如此【则】天气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气来矣,颂声作矣,万物长安矣,百姓无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游矣,阴阳悦矣,邪气藏矣,盗贼断绝矣,中国盛兴矣,称上三皇矣,夷狄却矣,万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称万岁矣。”(注:《太平经》,卷五十一《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就将这部道经关于“真文”至高至大之美的观点,通过它的周详而巨大的作用展现出来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太平经》已经将“真文”美学观点阐释得多么清楚透彻,而只是说,它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道教经典之一。因而,它在道教美学思想上的开创性,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代表意义,是应该得到重视的,也是值得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
“出真文”的哲学渊源或美学渊源,很容易在《庄子》中发现。这说明道教(包括早期的太平道)在美学思想上与道家的“血缘”关系。《庄子》中有一段话,简直就是对道教“真文”观点的理论铺垫,它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札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注:《庄子·渔父》,《道教三经合璧》,315~51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庄子的“贵真”,与老子的“信言”(即《道德经》第八十一章所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第六十二章所说的“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又是一脉相承的。老、庄讲的内在之“真”、“信”,到了道教美学思想里,就成为对“道”的“精诚”之心的高扬,对修道人排斥物欲、甚至排斥物质之美的鼓励。
二、“弃除邪文巧伪”:对假恶丑的批判
与“出真文”相应,道教艺术美学还提出反“邪文”、反“伪文”、反“巧伪文”的主张。《太平经》几乎每一涉及文风、文品之处,都要旗帜鲜明地大反“邪伪文”。除前文所引外,激烈的还有“吾书本道德之根,弃除邪文巧伪之法”,“按行真道,共却邪伪”等说法。(注:《太平经》,卷九十七《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39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太平经》认为,不反“邪文”,就无法排斥奸灾、奸伪、邪恶东西对人心的侵蚀。它以主、客作比,论证“邪文”、“邪言”与“奸伪”(即假恶丑)的关系说:“邪文邪言,乃奸灾之主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遂【逐】邪奸恶之吏也。以文正言,以吏正奸伪,无主人则无止宿之所矣。夫邪言为奸主人,比若盗贼有舍止之所也。主人已死亡,盗贼无缘复得来止息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太平经》将“邪文邪言”作为假恶丑的外在“形式”,认为只要将其“弃除”,假恶丑的“内容”就没有存身之地,也就无法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反对“邪文邪言”,目的在于反对它所运载的假恶丑。
《太平经》基于古已有之的“天人感应”的宗教理论,不但反对道经之外的“邪文巧伪”,而且反对道经之内具有“邪文乱道”内容的东西。它说:“夫邪文乱道经书,道经乱,则天文地理乱矣。天文地理乱,则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风雨四时五行,战斗无常。岁为其凶,帝王为愁苦,县官理乱,民愁苦饥寒。此为邪文所病矣。夫邪文邪言误辞以理国也,日日得乱,于是臣为枉法而妄为,民为之困穷,共吁天地之理乱,天官大怒,哭泣呼冤不绝矣。夫邪言邪文误辞以理家也,则父子夫妇乱,更相憎恶,而常斗辩不绝,遂为凶家矣。”(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六己部,67~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照《太平经》的说法,“邪文”要是进入道教经书,将会引起道教思想的混乱,还会进而造成“天文地理”的混乱,天灾人祸将由此产生,社会将会动乱,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将深受其害。要是遵照这种“邪言邪文误辞”办事,治国国乱,治家家乱,以至于不可收拾。这也是从“文”之“用”的角度论证“邪文”的非正统性。它进一步讨论,“浮华伪文”一旦以宗教形式出现,将会对政治、社会、伦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将造成许多恶果。它说:“非真要德,……下愚之师,【以之】教化小人也,忽事不以要秘真德敕教之,反以浮华伪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贤得邪伪巧文习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贤得习伪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其谨其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无义理,欺其父母,巧其邻里,或成盗贼不可止,贤不肖吏民共为奸伪,俱不能相禁绝。睹邪不正,乃上乱天文,下乱地理,贼五行所成,逆四时所养,共欺其上,国家昏乱,其为害甚甚,不可胜记。”(注:《太平经》,卷九十七《妒道不传处士助化诀》,3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而且,对于个人来说, 注意防止和克服“邪伪文”的坏影响,是修道人在“道德”方面达到善、美,进而多“正气”、“多寿”的必须。它说:“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注:《太平经》,卷四十七《上善臣子弟子为君父师得仙方诀》第六十三,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总之,“伪文”之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文风范畴,而成了是否得真道以治天下、天下是否太平的政治、社会的问题了。“伪文”所运载的,必然是“伪道”,而《太平经》所指“伪道”,实际上是远远超过宗教思想(包括其美学思想)斗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
《太平经》反对“邪文”,还注意了解其根本和来历。所以,《太平经》还探讨了“伪文”的根源问题:“今念从古到今,文书悉已备具矣,俱愁其集居而不纯,集厕相乱,故使贤明共疑迷惑,不知从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从其忤是也。使与天道指意微言大相远,皆为邪言邪文。书此邪,致不能正阴阳,灾气比连起,内咎在此也。”(注:《太平经》,第五十一卷《校文邪正法》,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这是说,“道”教之外来“邪言邪文”,虽出于“文书”,但其结果和效用是灾难性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危险和威胁来自于内部,即打着“道”教旗号的“浮文外学”。本来,“真道”之教已有成法,照办就行了。但掌握这一“真道”法又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稍不留心,就会学“道”不成,转入“浮华”“外学”去了。它模拟“神人”的口吻说:“吾之道法,乃出以规阳,入以规阴;出以规行,入以规神;出以规众书,入以规众图;出以消灾,入以正身;出以规朝廷之学,其内以规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学者各以其才能,反失其常法,外学遂入浮华,不能自禁;内学不应正路,反入大邪。诸学者乃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学,才大过者,多入浮华,令道大邪,而无正文,反名真道,更以相欺殆也;内学才太过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今古文众多,不可胜限,凡学得其真事,勿违其本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五戊部,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从读书学习角度说,这实际上是要求读书要有所选择,要有意识地排斥那些包含假恶丑内容的东西。
《太平经》还从“文”(形式)与“意”(内容)的关系上,要求不能只重“章句”,而应求得真道之“要意”。它说:“夫学之大害,合于外章句者,日浮浅而致文而妄语也;入内文合于图谶者,实不能深得其结要意,反误言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五戊部,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拨开其宗教的说教的外衣,这话可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文”(广义即文艺作品),应该以内容的上达为要的美学观点。真“文”,应该为传播真“道法”而作,而不只要求写得漂亮,否则就可能成为只有“浮华”“章句”的“浮浅”之文,甚至可能脱离传道的写作目的,变成“大邪”的“妄语”!这说明,《太平经》重视“文”的内容甚于其形式,重视文艺的教育作用更甚于其美感作用。它说:“学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众贤说以安之者,是也;守众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为神者,是也;神无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书相驱使之术耳。”(注:《太平经》,卷七十《学者得失诀》,《道藏》第24册,460页,上海书店。)强调得“天道意”的追求,否定只讲“章句”的做法,在那个时代是有积极意义的,也与同时代的“魏晋文风”合拍。以此观之,《太平经》批判的“浮文”,不但是空洞的,更是假恶丑的。它反复告诫说:“今愚人日学游浮文,更迭为忤,以相高上,不深知其为大害,以为小事也。安知内独为阴阳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注:《太平经》,第五十一卷《校文邪正法》,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浮文”之害,提到了是否以“真道”治世的高度,可见这部早期道经对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重视和认识的深刻程度。这也使我们联想起现、当代中国文艺美学中,曾经出现过的将文艺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直接挂钩的做法,原来是有其历史文化的思想渊源的!
《太平经》这种“除邪文”观点,对后世道教文艺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影响很大,如在后世与佛教的多次辩论和“斗争”,道教其实就依托了“除邪文”思想的批判锋芒和绝决态度。这是后话。
三、“乐盛刑绝”:文艺美学价值观
《太平经》文艺美学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对文艺美的社会教化作用的认识和强调。这是道教文艺美学的强烈“时代意识”的自然流露。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在萌芽初期,就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意识。太平道、五斗米道不约而同地将民间宗教组织政治化、甚至军事化,决不是偶然的。从外部看,当时动乱的社会需要一种能够凝聚民众的组织、即使是宗教组织;从内部看,太平道、五斗米道是应运而生的,其宗教思想中必然包含社会运动思想因素,必然反映民众以“宗教”形式干预社会、参与政治的需求。这种内在需求,反映在道教的文艺思想中,就必然将古代的“诗言志”的传统思想扩展一步,转变成以文艺(主要指道教之“文艺”)来团结民众、教育训练信徒、推广教义的理论工具。《太平经》说:“太平气至,人民但日相向而游,具乐器以为常,因以相和相化。上有益国家,使天气调和,天下被其德教而无咎。和与不和,以为效乎?得天地意者,天地为和。人法之其悦喜;得天地人和悦,万物无疾病,君臣为之常喜。是正太平气至,具乐之悦喜也。”(注:《太平经·太平经钞》,卷七庚部《虚无自然图道必成诫》,《道藏》第24册,358页,上海书店。 )以《太平经》本身的宗教逻辑来讲,这样看重和推崇文艺的“德教”作用,是自然而然的,并无故意的夸张其辞。《太平经》还分上、中、下三个层次来阐释文艺的作用,认为发挥文艺的最高级的作用,可使人得到守道诀窍而“度世”成仙;发挥文艺中级的作用,可使人得到太平美好的生活;即使仅仅发挥文艺最低级的作用,也可使人得到审美的快乐。对于社会人群来说,文艺的作用虽然有高下之分,但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积极的,统治者可通过文艺活动沟通、打动“神灵”;中等人群,可通过文艺使身中的“精”(精神)感到愉快;下层群众,也可通过文艺欣赏去愉悦自我。因而,要是全社会的人都得到文艺的熏陶,那就天下太平了,天上的上帝和地上的帝王会轻松得无事可干了。它说:“故举乐,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太】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乐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乐神灵也;中得其意者,可以乐精;下得其意者,可以乐身。俱得其意,上帝【帝】王可游而无事。”(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为什么以“乐”(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美,会有如此周详而巨大的作用呢?《太平经》按照自己的宗教哲学和美学价值观做出解释说:“乐起而刑断绝,精神相厌也。……乐者,太阳之精也;刑者,太阴之精也。阳盛则阴服,阴盛则阳服。故乐盛则刑绝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从这样的艺术美学价值论出发,《太平经》就必然会以“乐”(文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作用来区分艺术之高下:“上士治乐,以作无为以度世;中士治乐,乃以和乐俗人以调治;下士治乐,裁(才)以乐人以召食。”而修道人“治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天下回到“道”的规范和“道—美”的形态。所以它又说:“乐,则五方道德悉出;怒,则五方恶悉出也。乐,则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则天地恶悉出也。故天地乐者,善应出也;天地不乐者,恶应出也。故五方乐而和者,五方善应出也;故五方不乐而怒者,五方恶应出也。是非小事也”!这部道经还详细分析说:“乐小具小得其意者,以乐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乐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乐天地。得乐人法者,人为其悦喜;得乐治法者,治为其平安;得乐天地法者,天地为其和。天地和,则凡物为之无病,群神为之常喜,无有怒时也,是正太平气至,具乐之悦喜”。因此它认为,道教艺术美之作用的极致和理想是“太平气至,人民但当日相向而游,具乐器以为常,因以和调相化,上有益国家,使天气和调,常喜国家寿,天下亦被其德教而无咎。”(注:《太平经》,卷一一三《乐怒吉凶诀》,507~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乐”治天下,以“乐”安国家,音乐的艺术作用和价值,已经被宗教和准宗教的美学思想,加工成了远远超出其实际能量的“超级”意识形态。
由于重视文艺的社会价值,《太平经》进而提出“使用”文艺也必须慎重、得当。它说:“将太平者,得具作乐。乐者乃顺乐王气,平气至也。先以道之凶年者,不得作乐,不得无故兴乐。囚废之气,与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无故作乐也。故王相之气,德所居也;囚废之气,刑所居也。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乐;无德之君,不得作乐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4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就叫道教“德—乐”对应观,也就是“政治—艺术”批评方法的宗教形态。在太平道看来,艺术与“天时”也有感应,它说“乐”要与“天气”相匹配才能和谐,要“皆顺其气,如其数。独六月者,以夏至之日,并动宫音,尽五月、六月者,纯宫音也。又乐者,乃举声歌舞。夫王气者宜动摇,动摇见乐相奉顺见奉助也。……故天之所向者兴之,天之所背者废之。是为知时之气,吉凶安危可知矣。”(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哲学思想上说, 这自然是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观点的翻版。不过,也要看到它对音乐理论本身的价值,因为它同时也强调说,“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可见,仅仅从“政治—宗教”或“天人感应”的观点去分析,还是远远不够的,它的确还包含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美学的内容。比如,《太平经》讲音乐艺术要符合“天”之“三气”中的“乐气”与“和气”:“天有三气,上气称乐,中气称和,下气称刑。故乐属于阳,刑属于阴,和属于中央。故东南阳乐好生,西北阴怒好杀,和气随而往来,一藏一见,主避害也。故乐但当以乐吉事、乐生事,不可以乐凶事、乐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注:《太平经》,卷一一六《某诀》,《道藏》第24册,583页,上海书店。)这“乐”, 不仅是“乐气”(属东南之阳气),而且是可以操作的、演奏的欢快音乐,是可以用来表达快乐情绪、烘托吉祥喜庆气氛的艺术形式。从它对音乐(欢快音乐)的美感愉悦作用的理解来看,其观点基本上还是正确的。只是它将音乐同“天”和“三气”生硬地加以比附,自然会把它对音乐的正确理解,本末倒置地放置在它的宗教思想基础上去。当然,如果从《太平经》是强调音乐的社会价值方面去理解,那么它实际上是在呼吁正确发挥音乐(特别是道教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或美育作用。
总之,仅从以上三个与文艺思想内容有关的方面,就可看出《太平经》在道教史上和中国美学思想史上有特殊地位。它是展示中国的“人为宗教”之美学思想最早、最集中、最丰富的文本,也是当时最接近民众思想的宗教普及文本。从中国民族的宗教美学思想发展源流说,它的价值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