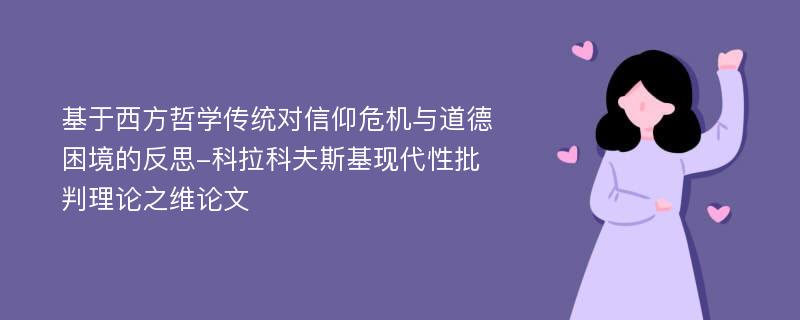
基于西方哲学传统对信仰危机与道德困境的反思
——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批判理论之维
李晓敏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 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所面临的道德困境一直是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批判理论关注的重点。在科拉科夫斯基的理论体系中,传统权威的恢复与道德绝对性的确立是同一过程,为此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尼采,认为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言和取消善恶划分的绝对标准的主张均瓦解了道德的神圣性。同时为了使批驳尼采更富成效,他更是借助于理性主义者康德的先验道德和“抽象的人”的学说。需要指出的是,科拉科夫斯基的以信仰的权威来重建道德绝对性的理论构想并非主观臆断,一方面,这一理论是以传统基督教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力为大前提的,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基督教文化一直担当着传统道德捍卫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科拉科夫斯基以道德为关节点在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建立联系,进而将宗教批判引入现代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做法本身,也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新视角。当然其以信仰的恢复来挽救道德的倾颓进而解决现代性难题的理论构想最终必然无法实现,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道德由特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绝对的普遍意义的道德在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社会并不存在。
关键词: 科拉科夫斯基;基督教;道德;现代性
20世纪以来,各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应运而生,在这之中,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科拉科夫斯基的思想就极富创建性。科拉科夫斯基指出,理性主义的滥觞加剧了信仰的衰败,最终导致了当今以道德危机为突出表征的西方文化的整体危机。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提出,只有信仰的恢复才能挽救道德的倾颓,进而实现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集体脱困。因此,尽管科拉科夫斯基在自己的理论中,一再倡导向传统的基督教复归,但我们却不能就此将其视为一个复古主义者或宗教主义者,原因有二:其一,科拉科夫斯基思想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指向都是困扰西方文化的现实问题。其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科拉科夫斯基并非基督教的信徒或捍卫者,他对基督教本身亦持理性主义的批判态度。其仅是试图通过信仰权威的确立来重建现代道德的绝对性,守护西方人的精神家园。也正因如此科拉科夫斯基才反对尼采将基督教文化彻底摧毁的做法,甚至为此而求助于康德的先验道德学说。
一、“上帝已死”与西方传统道德的倾颓
历史地看,即便在理性主义繁盛发展的17世纪,基督教也未丧失对道德领域的控制。毋论一般民众,许多以理性为明灯极具批判精神的哲学大家都坚信,善恶源自并且应当源自上帝的绝对意志。直到尼采的出现,情势和论调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关于所谓的基督教危机》一文中,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尽管尼采明确认识到了基督教是关于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悲悯意识,却由于盲目的自傲——对人类意志力非理性的推崇,憎恶和否认这种意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尼采痛恨基督教,痛恨耶稣,是他对自我创造能力无限可能性的推崇的合乎逻辑的结果”[1]90-91。信仰也正是由于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信念,即关于人类自身完满性的信念——无须上帝的在场和干预,仅凭自身便可趋于至善与完满——的增强而日趋式微。尼采对基督教道德彻底贬抑的立场和做法,无异于在基督教内部和整个西方文化世界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而在这一颠覆性的过程中,以下两个命题显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第一,“上帝已死”的断言。尼采指出,基督教道德的核心主旨就是将上帝的绝对意志和命令看作道德的最终因,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上帝“死亡”,道德也必然由于失去最核心支撑而走向消亡。据此,他充满自信地宣告了自己的发现:“上帝是一种猜想:但谁能饮进这种猜想的全部苦酒而不至于丧命呢?……上帝是一种思想,它使一切直者变曲,使一切站立者倒转。……我们把它叫做恶的和敌视人类的:所有这些有关唯一者、完满者、不动者、满足者和不朽者的学说!”[2]106众所周知,在基督教为西方人营造的信仰体系中,上帝具备全知、全能、全善的位格,也正是由于这种位格,其才有能力充当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和道德准绳达上千年之久,而今尼采竟然宣称上帝是恶的,这也就等于宣告了以信仰为基础的一切绝对性的死亡,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基督教道德的死亡“我的兄弟们呵,用你们的德行的权力,保持对大地的忠诚吧!……不要让你们的德行飞离尘世,……像我一样把迷失了的德行引回大地吧——是的,回到身体和生命:使得它能为大地赋予意义,一种人类的意义!”[2]95显然,尼采对“上帝之死”可能会引发的一系列后果,特别是在道德领域内将造成的颠覆性影响是早有预见的。换言之,尼采对上帝的反动是以对基督教道德的颠覆为切入点来施行的。尼采指出,上帝使人成为一种消极、逃避责任的存在,这是一种最大的不道德,因此人要想真正的生,上帝必须死!只有上帝死了,人才能摆脱基督教伪道德的束缚!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上帝被宣布为可朽的以后,我们又拿什么来支撑道德的大厦呢?尼采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凭借生命意志。世界本就虚无,人生亦是一场悲剧,如果用绝对道德的眼光去度量它,结果只能是灰心失望。相反,如果在自我肯定、自我确证的生命意识的指引下,于变化不居的个体表象背后,寻找生命意志,那么纵然人生是悲剧性的,你也可以战胜它。尼采此处一再强调的生命意志即他后来在理论中极为看重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亦称酒神精神。尼采认为,酒神精神通过高扬本能与强力意志完成对生命的最高肯定。其一方面可以使人摆脱基督教伪道德的控制,另一方面更是制衡以理性为核心的希腊式日神精神的有力砝码。总之在尼采的理论体系中,在关乎人向自身复归,向真正属人的尊严复归和健全的欧洲精神养成的意义上,上帝之死确实是必要的。
对于上述观点,科拉科夫斯基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于他而言,上帝死亡,并非人类自我确证的起点,而是意味着禁忌的消失,堕落的开始。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上帝之死——以理性主义或生命意志的形式被消解,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禁忌的消失。当然,这也是尼采全部理论生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更深入地把握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一论断,我们有必要对禁忌本身进行一次社会学维度的考量。禁忌一词,始见于玻利尼西亚土语tabu,英文为taboo,意为“禁止”或“不被允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禁忌一般体现为世俗和宗教两个层面。其中,宗教禁忌涉及人神关系的定位,关乎人的终极救赎,因此实施起来也就格外严苛,而一旦被触碰,其给人带来的负罪感也是世俗禁忌所无法比拟的。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广泛而特殊的禁忌:在低级宗教中,禁忌每每与社会习俗融合在一起,共同模塑原始民众的生活方式;而在高级宗教中,禁忌则“通过神学教义或教法学演变为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宗教戒律和礼仪,从而有了新的社会意义”[3]72。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某一宗教形式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教理、教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道德的效力——《圣经.旧约》中“摩西十诫”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和规范功能。而且科拉科夫斯基还进一步指出,道德规范只有扎根于宗教禁忌之中才能具有恒久不变的绝对效力,也只有宗教禁忌才能将自身对象化为一种活动原则的同时,也内化为一种心灵的自律性渴求。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论中反复强调并力主重构的也正是这种道德,他称其为神圣道德,具体落实到西方文化和社会,即传统的基督教道德。
合理选择排水管材对于管道的使用寿命、日常维护以及控制工程造价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次施工选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双壁波纹管、排水检查井选用塑料检查井(成品),此类管道、井体不仅抗压耐冲击、内壁光滑摩阻小,而且重量轻、施工快捷[2]。
如图6,应用层中包含多个功能模块,并且各模块之间相互独立,通过Spring MVC向表示层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口,在接收到表示层请求之后,根据Spring MVC的控制器分发请求,直接调用对应的模块进行其中的业务逻辑处理,同时这一过程有着Spring的管理与Mybatis对象关系映射,从而能够完成接收请求,分发请求,业务处理,访问数据源,模型生成,视图填充以及给予响应的完整过程[9]。
尤为严重的是,尼采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先破后立,紧跟着,又抛出了第二个更为颠覆性的命题:“取消关于善恶的绝对划分。”这一理论建立在对基督教道德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尼采以生命意志为天平对基督教道德的核心主旨进行了重估,结果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尼采批判福音,指出福音经由对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幻世界的宣扬来鼓动人们奉行禁欲主义,这种压抑本能的主张和做法是其所无法忍受的,他将其视作由基督教道德所引发的欧洲官能症之一;尼采贬斥虔敬,并援引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认为虔敬是心灵的一种危险状态,更提出在一切病态的现代主义中,虔敬最为不健康;尼采否定博爱,指出由于等级性优劣的存在,非但人与人之间的爱无法真正实现,人对上帝的爱,亦不过是功利性的索取,至于上帝对人的悲悯,更是爱的面具下掩盖的强烈的控制欲。由此尼采提出,博爱不但过去从未在人类的历史上真正实现,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实现,其提法本身不过是基督教道德伪善性的又一次证明;尼采质疑良心,认为良心乃是一种痼疾。他坚决反对传统基督教道德所极力倡导的通过唤起被惩罚者的良心来维护正义的主张,指出一方面作恶者中绝少有人真心悔改,另一方面这种主张和做法也可能导致人完全被负罪感所控制,在神的面前放弃一切属人的本能、尊严,而这无疑对人的损害更大。
第二,为了捍卫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性,科拉科夫斯基还极力鼓吹康德的“抽象的人”的学说。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康德对人的规定沿袭了17世纪自然法的原则——作为自由的理性存在物,人具有本质上的平等与尊严,因此康德相信,所有标准,只要它们是道德的,就必定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个体。显然,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道德的普遍性绝对性与对人性的抽象考察和定义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与之相对照的是马克思的关于“具体的人”的理论——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和物质生产活动,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0,在此科拉科夫斯基走向了马克思的对立面,认为“具体的人”并不“具体”——本质上他们并非作为纯粹个体而存在,而是隶属于特定民族、特定阶级和社会关系。如果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这一逻辑深入下去,必然会得出只要将人置于某一具体的历史关系和背景中考察就是对人的限制和尊严的冒犯的结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科拉科夫斯基何以将康德的“抽象的人”的思想当作人权原则的基础了。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正是经由对个体的人和普遍人性的强调,康德才得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结论,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有理由宣称无人是他人的私有财产,奴隶制本身是反人类的。而所谓的“具体的人”则是一种否定人类的普遍本性,使其受制于种族、民族、阶级和社会关系等多余的个别性范畴的提法。作为特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是以弱化普遍性的人权为基础的将人客体化的理论,其中包含着使奴隶制变相合法化的危险倾向。然而只要深入到马克思的理论内部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得出相反的结论:“具体的人”的理论是其摆脱人本主义的思考模式,立足于社会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对人本质的正确揭示,这种揭示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得以实现的理论先导。当然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科拉科夫斯基虽然鼓吹康德的“抽象的人”的理论,但在一些原则问题的看法上,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科拉科夫斯基虽然同意康德及其后继者的关于文化意义上人的规定不能建立在经验性说明的基础上,而只能是一个道德伦理范畴的思想,却坚决反对将这一规定的有效性诉诸实践理性的绝对原则,而非宗教传统的做法。而这无疑也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论断:科拉科夫斯基对康德的认同是建立在后者的理论与基督教道德不矛盾或有相容的可能性的前提下的。
综合所述,与其他代谢性疾病相比,糖尿病患者的握力有所下降,除性别、年龄外,糖尿病患者的握力可能与其病程长短、并发症、相关代谢性疾病、机体蛋白质储备情况有关。血糖水平及胰岛素抵抗情况也与糖尿病患者的握力呈负相关关系。临床上也可以考虑将握力水平也作为一种快速评估和监测糖尿病患者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以便尽早开展有效的营养干预并及时调整方案,为病情控制或延缓起到一定作用。
从上述禁忌的观点出发,基督教道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以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的畏惧心理——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一切道德义务均源自上帝的意志,人对上帝的服从与道德的履行是一回事,而对神圣道德的任何最微小的背离行为哪怕仅是观念动机层面的,都会遭致来自神的最严厉的打击和报复。但另一方面,只要真心忏悔,由于神圣悲悯,即使是罪人也还是有被救赎的可能的。在尼采的理论体系中,上帝的上述奖惩均被斥为“虚伪”与“伪善”。然而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威严与仁慈这两种品格在上帝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这与其对于原罪、人的自由意志乃至人性的理解是相一致的,即出于爱与悲悯,上帝不会彻底抛弃人类,但罪人也必须受到与其恶行相匹配的惩罚。据此,科拉科夫斯基指出,与具体的宗教道德诫命这种有形的束缚相比,上帝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威慑。而今尼采竟然宣称上帝死了,这也就等于从根本上消解了道德的神圣性,瓦解了西方传统伦理道德的根基。而此种做法无疑会使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都坠入一种无意义的真空状态。
二、先验道德与道德绝对性的重构
事实上,科拉科夫斯基对康德的解决方案并不完全赞同——虽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理论为信仰预留了地盘,于《实践理性批判》中又肯定了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朽,但从根本上说,康德的上帝与笛卡尔的上帝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即均以维护理论自身的圆满性为目标,区别仅在于前者是为了树立道德的权威,而后者则是为了在认识领域内实现思存关系的统一。由此可见,科拉科夫斯基真正注重或维护的乃是问题本身,即关于善恶绝对区别之存在的意义的肯定。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如果取消关于善恶的绝对的、先验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的划分,文化就不会存在,而一旦将这种划分诉诸经验性的层面,文化就会走向虚无。按照他的分析,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康德才会对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而滥觞的实证主义持批判的立场;同时康德也必然认识到,真正有价值的,关涉人类命运的一定是关于善恶的绝对划分、道德的绝对性与普遍性是否存在等问题,而绝非某些抽象的道德符号。一如我们所知,科拉科夫斯基对康德的解读是恰当的——康德进一步为人规定了必须遵守的三条先验的绝对的道德命令,即一、“你应当这样地行动,使你的行为的准则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5]73二、“你的行动,要把你本己(Person)中的人,和其他本己中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手段。”[5]81三、“每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理念。”[5]83-84有人曾据此批评康德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竟然指望人们从纯粹的道德动机出发去行动。但按照科拉科夫斯基的分析,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康德从未寄希望于绝对道德律令能够得到彻底贯彻。在他看来人的自由意志本身就包含着作恶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在经验领域内恶是无法被取消的,只有在上帝那里,以灵魂不朽为前提,至善在实践上才具备可行性。至于所谓的盲目的乐观主义的诟病则更适用于理性主义至上者——由于对理性的过度信赖,他们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幻觉,即人类可以借助理性,经由政治组织的完善和宗教形式的取消来达到社会和文化上的绝对和谐状态,道德和谐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维。然而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这不过是理性主义为我们开的又一张空头支票——绝对的和谐只存在于天国之中,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和对基督教道德的严格恪守是接近它的唯一途径。理性的自傲,不但无助于这种和谐的建立,反而会打破经验领域内现有的平衡,数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在信仰和道德领域所起的消极作用就是证明。
第一,道德的先验性、绝对性、普遍性。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康德关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思想本身就非人类学而是超越性的。关于理论理性,康德看重认识的先天经验范畴,提出这种先天的范畴与形式对一切具备健全理性的人类都有效;关于实践理性,他强调纵使是抽象的道德也具有绝对标准的效力,适用于一切具备自由意志的人,“这也就意味着人不是一个被生成或本性被设定的客体,而且人之为人是一个道德而非动物学概念”[1]45;关于这一点伦理社会主义者也持同样的看法。总之根据康德的理论,人与其他生命物种的根本区别并非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而在于其能够借助先天综合判断参与到理性的必然性领域,能够经由对绝对命令的执行参与到非经验的道德领域。康德对人的如此界定显然触及一直为尼采所诟病的道德的绝对性和先验性问题,即人们必须无条件遵从的道德原则不能由人所从事的活动中推导出来,或者说“是”与“应是”的鸿沟是天然且无法跨越的。康德的上述主张在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议,经验论者就曾指责他抹杀了目的、责任领域内的客观性。然而据科拉科夫斯基分析,这完全是对康德的曲解 :虽然康德提出价值和道德原则并非关于经验性活动的总结,但他并未据此就将二者置于非普遍性的个体主观领域而不顾;相反,其对先验范畴、先天综合判断的一再强调,最终都是为了说明存在于纯粹理性领域内的道德原则的先验性和普遍性。康德真正关注的,或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人们的活动原则无法成为善恶划分的绝对标准,道德义务也不能从中推导而出,那么绝对的,独立于简单经验之外的这种标准和原则在实践理性领域又是如何被揭示的呢?
必须指出的是,尼采全力批判和否定的道德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正是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论中所极力维护的,甚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种绝对性与普遍性对西方文化及人类自身的价值与意义,科拉科夫斯基在明知康德哲学的道德观是立足于理性而非启示神学的前提下,还是援引了其思想中能为自己所用的观点来对尼采进行还击。在《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一书中,科拉科夫斯基明确指出,当康德主义与历史主义发生冲突时,自己是其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同情者——当然,这并非说康德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无关紧要,仅是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康德的道德理论对于我们发现、克服和解决时代的难题更具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内部张力进行批判性分析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关节点。科拉科夫斯基认为,除了理性之外,康德的道德哲学还在弘扬另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使康德在历史激变面前能够保持冷静审慎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也正是这种精神在维系西方文化的命脉——在此科拉科夫斯基将其言简意赅地归结为“关于道德绝对性与普遍性的信念”。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康德道德哲学的突出贡献就在于重构了道德不受制于任何经验性条件的最高权威和最大范围内的普遍性,换言之,尼采理论体系中被取消了的关于善恶的绝对划分,在康德这里又重新确立起来。至于这种普遍性、绝对性的恢复是借理性还是上帝之名施行,则不是科拉科夫斯基关注的焦点,毕竟在他全盘的理论设计中,康德的道德哲学只是向传统复归的一个桥梁,基督教道德才是其最终的目的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拉科夫斯基在理论中具体分析了以下两个命题:
事实上,自上帝已死的论断发表以后,尼采就不得不面对科拉科夫斯基所说的,关于善恶划分的绝对标准的丧失的难题。当然,按照尼采的理论,这并非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是他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之一——他力主取消关于善恶的绝对划分,并认为这种划分是出自神的对人的本能的一种压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区别善恶的绝对标准根本就不存在。在尼采的理论建构中,不但善恶的绝对界限被取消,就连最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也不存在,“对一个人是正当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不可能完全是正当的,为一切人所要求的一种道德恰恰损害了更高等的人,简言之,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因此,在道德和道德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4]146。
经由上述两个命题,尼采实现了对基督教道德的重估与根本性颠覆,并得出了“在基督教道德谱系中,一切价值原则都颠倒了”的论断。尼采提出,长期以来基督教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毫无意义与价值的压抑本能和生命意志的奴隶道德,这种奴隶道德是对人蓬勃生命力与高贵尊严的彻底否定,它只能造就懦弱、驯顺的懦夫——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完全处于幻影性的上帝的掌控中。如果任由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整个西方文化必定会走向虚无。作为药方,尼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超人道德,主张用出自人本身的道德来代替毫无价值的基督教道德。尼采在理论中对超人道德做了一系列详尽而多维的规定,但归根结底这种道德的实质乃是一种强者道德——强者的意志本身成了善恶的依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非道德,而尼采本人对这一点也从不讳言。
主动脉返流症状发生率为31.11%,肺动脉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55.56%,三尖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66.67%,二尖瓣返流症状发生率为38.89%。见表。
三、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科拉科夫斯基道德理论批判
作为一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青年马克思的理论无疑是科拉科夫斯基思想最深刻的理论来源。然而在道德问题上,其却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经由对理性主义的批判,科拉科夫斯基将矛头直指青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马克思。按照他的分析,黑格尔的“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本就充满矛盾,而青年黑格尔派则在误读黑格尔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错误——黑格尔本人从未许诺历史地确立起来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应用于未来。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则突破了这一界限——他们于历史进程中寻求可能胜利一方的蛛丝马迹,并积极投身其中。为此科拉科夫斯基称他们为“伪黑格尔主义者”,并且批判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等于宣告,任何行为无论是以纳粹还是斯大林集权主义的形式施行的,只要它能促进某种趋势的成功,就是道德的正义的。如此一来善恶的绝对对立,道德的先验性、神圣性、普遍性也就为历史决定论的大潮所淹没了。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科拉科夫斯基之所以对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持如此偏颇的态度,一方面与其向传统基督教道德复归的立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的生存境遇有密切联系。“二战”以后,科拉科夫斯基不满自己的祖国波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受控于苏联的局面,再加之当时苏联的最高统治者斯大林又总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自居,这些客观上都有碍于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他的道德观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事实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是立足于辩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是根植于内心的一种无法辨识的先验范畴,而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内在于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所谓的绝对的普遍意义的道德并不存在,至少在充斥着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不存在。而人只有自觉地投入到以变革现有社会秩序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内建立起超越阶级的、绝对的和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而这一过程本身一方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一方面又以伦理道德目标为指向。纵观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根本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来分析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但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始终是其理论的焦点和最终指向,这一点明显体现于关于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的理论中——与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相伴随的是人自身的发展,即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全面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而个人的全面发展显然包括道德层面的完善。因此,纵然我们十分理解科拉科夫斯基力图挽救西方文化与传统道德的迫切心情,却必须指出,其立足于宗教,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为历史机会主义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
综上所述,科拉科夫斯基经由对尼采与康德的道德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在基督教信仰的式微与西方的道德困境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理论关联,其后更是以此为基础逻辑地将宗教批判引入到现代性和文化批判当中,而这一做法本身无疑开创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新视角。当然对其思想价值予以客观的承认,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赞同其脱离具体的历史实践和社会关系来考察道德本身及其对文化和人自身的意义的做法,“如果责任之行使只是由外在力量推动的,那么这种责任还构不成自觉的责任。”[7]4更为关键的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道德所起的作用及起作用的方式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所推崇遵从的道德原则,本质上都是这一社会阶段特殊利益的反映,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8]167。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功能上,道德都不具备所谓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只有从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践活动出发,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道德;只有依靠主体自身的努力,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道德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也只有在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中,属人的道德才会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Leszek Kolakowski.Modernity on Endless Trial[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
[2]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尼采.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M].程志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5]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建青.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历史伦理化的尝试[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19,(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作者简介: 李晓敏(1982— ),女,黑龙江巴彦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当代意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 中央编译局项目目“科拉科夫斯基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SQWT07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科拉科夫斯基的文化危机理论研究” (项目编号:16ZXC01 )和黑龙江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项目编号:UNPYSCT-2016025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B5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 2019) 04-0026-06
收稿日期: 2019-05-25
DOI: 10.19563/ j.cnki.sdzs.2019.04.004
[责任编辑:赵 强]
标签:科拉科夫斯基论文; 基督教论文; 道德论文; 现代性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