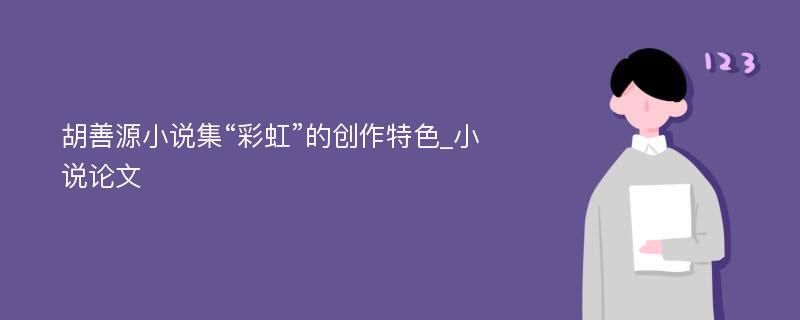
胡山源小说集《虹》的创作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集论文,特色论文,胡山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文艺观念的不断演进,对现代文学作出新的评价、判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在当时熠熠闪光而在后人的品评、选择中因种种原因划归另册的作家重露头角,得到世人的注意。研究者的责任则在拂去历史的积尘,探索阴影下曾经鲜活的灵魂,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胡山源这位当年“弥洒社”的创始人,几十年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一千万字的作品,其思想、艺术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文试图从胡山源的短篇小说集《虹》,探讨一下其创作的特色。
《虹》出版于1931年,是胡山源青年时代一部分作品的结集。据作者称,《虹》的寓意一为其长子“高虹”,一为表示作者希望自己的苦难生活象虹那样雨过天晴,从此走上安定而光明的道路。《虹》收小说11篇,其中《五里湖之雨》、《几个忘不了的面孔》和《表话》按现代观点来看应属散文。五·四时期文学革命颠覆了传统的文艺观念,小说从“琐小”之言一跃而成文坛之主。小说理论的重新构建是在与西方小说理论的交汇中发展起来的,初期阶段免不了在概念上、分类上有不完备之处,小说、散文的划分不甚明晰,三篇散文姑且不论,让我们把视线转向集子中的8篇小说。
一
与同时代其它作家,如老舍、巴金广阔、宽泛的选材视域相比,《虹》中诸作的视域是相对集中的。作家把视线投到他亲身经历过的、最熟悉的、曾经真切地激起他情感波澜的校园。《黄大利》《卢光斗》两篇作品描写了两位脱离实际、缺乏实际生活能力、各有弱点的知识分子。其余六篇,则剪取校园内外的生活场景、片段,主要以青年学生为主人公,表现他们的生活、情感。相对而言,此六篇作品也更能代表作家的艺术个性。
生活本身具有它的多层次性、立体性,校园生活也蕴含着它多面性的生活内容。一个小小的校园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它以相对封闭的完整的特性隔离开与社会的超近型融合,而其略显单纯的人物与单调的生活表层下则蕴藏着社会、时代、政治、道德、文化的潜流暗动。作家对生活的不同的切入点往往能体现不同的审美个性。冰心的校园小说《斯人独憔悴》、《去国》截取的是社会上新旧两方思想斗争在校园内的投影,从青年学生的命运透露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注。新时期刘心武的《伤痕》也以青年学生思想的被扭曲,暴露政治文化对人的异化。胡山源切入校园生活的突破点在于青年学生的情感交往上。作品真切的记录了青年人情感交往的情绪、心理反应。尤为重要的是,胡山源笔下的这种情爱交往又非肯定性的情绪体验,情爱给予人的振奋、欣喜、甜蜜等诸种积极性体验都是昙花一现,真正留下的是永久的伤痕与疮疤。这种以青年学生情感世界的伤痕体验所传达出的生命体验值得玩味。
《珂莲》是有代表性的一篇。女主人公珂莲对同窗女友品芝怀有好感,平日里对她殷殷相待。品芝一面享受珂莲对她的呵护照看,一面又态度冷淡,终于离她而去,且和她人背后恣意讥笑,令珂莲伤心欲绝。珂莲和品芝的交往是青春期女性在性爱之前的预备性演练。从心理角度看,同性恋作为异性爱的替代品,临时性地对青春期的寂寞起着某种安慰作用。它以友情为外衣,但给心灵世界带来的震动的程度恐怕不亚于异性恋。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微妙现象,勾画出女性之间这种情感交往带来的伤痕体验。另一篇《秋雨》中环蛾与秀波的关系也如出一辙。伤痕主题模式的变体还有《手套》、《董妈的伤心》。无论身为男性的敏成,还是身为仆妇的董妈,他们所遭遇的无非是造化的捉弄,敏成(《手套》的主人公)暗恋同学孙学贤,又羞于表达。同学克德托他AI写作两篇文章,以文章赢得孙的芳心。敏成得知真相后大为痛苦,又无可奈何,唯有藏身被中呼喊:“上帝,救救你的孩子。”董妈在学校作佣人,把学生赵锦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般爱护。不想赵对董妈的关心根本不以为然。尽管董妈与青年学生的内心世界不能等同,但她情感世界的伤痕性体验却是一致的。
从主人公的伤痕性体验中,作家进而又体察到人生凄凉的一幕。人生愿望的失落,人生价值的不被重视,美好情感的被漠视与被践踏。内心世界美好而又富有情感的人小物,因种种条件的限制,或容貌的平常,或地位的低微,或个性的怯懦等等,不能获得所爱或与所爱不能有平等的情感呼应。他们对所爱抱有满腔的热爱,有着真挚的心肠,却又无端地受到轻视、冷漠、嘲弄。无论他们个性的特点如何不同,共同的命运却是陷入了情感的困境。
作家看到生活里种种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分歧和人性中不和谐之处。外表美丽而内心冷漠的品芝,家境富裕而心地卑下的克德,人性中美的软弱与丑的强大的对立给予作者以强烈刺激。追究困境的根源,有些可以说是性格悲剧。敏成的失意大部分归因于他的懦弱。有情而不敢示爱,反被心地卑鄙的克德利用。挫折之后又缺乏抗争的勇气与智慧,对伤害他的人没能积累相当的愤怒,只会向虚无的上帝哭述他的烦恼。另外一类可以称为“命运悲剧”或“时代悲剧”。愿望的必然性与他们所处时代的滞后所带来的矛盾冲突。《虹》的时空环境并不明确。校园是人物活动唯一清晰的载体。从男女分校的性质及人物普遍具有的性格来看,胡山源笔下的校园当不是处于文化的中心,能站在前沿接受新式文明的洗礼,而是处于后方。前沿的风稍稍拂动了这些年轻人的心房,激起些微的涟漪,这些敏感可塑性极强的年轻人很容易接受了与己切身相关的平等独立意识。并把这种崭新的意识贯彻于他们情爱的自由追逐中。尽管这种意识是朦胧的,他们的情爱行为是含蓄的,或是秘密的,但对他们自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第一次出自本身的愿望,确立了一个目标。他们羞怯地敞开心扉,怀着隐秘的喜悦与忧愁,开始他们人生的第一次寻求。希望与他人建立温柔的关系。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能给他们单调的学生生活增添些许魅力。胡山源给这些憧憬中的年轻人以迎头的冷水,他们的真情换来累累的伤痕。他们的挫败在于他们新思想的幼芽无法获得适宜的土壤。《虹》中的校园周围的大环境还远未给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相反,由于处在非前沿的地段,新思想的微澜不足以抵抗固有的文化沿袭。封闭保守的观念还禁锢着多数人的思想。品芝鄙夷珂莲的内在心态曾经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伊哪一样配和我们往来”。赵锦章对董妈的亲情般的关怀不以为意,隐约也有董妈低微的仆妇身份起作用。传统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于人心深处,制约着人们的交友标准与行为样式。即使在这些受损害人物的身上,也能看出传统心理的积淀。《手套》中克德的胜利未始没有敏成因家贫而生的自卑在作崇。个体之间是无法对等的,美好的个体愿望在与强大的现存观念的撞击中显出它的软弱无力来。新式人物的伤痕体验有它的时代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笔触还涉及到人类普遍的困境:失落的不可避免性。无论个体的主观愿望多么强烈,如何为愿望的实现倾尽全力,最终的结局依然是失落。《秋雨》中秀波对环蛾的厌弃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她既没有新的女友,也非嫌弃环峨,更不是环蛾有负于她。总之一句话:“我总不明白,我为甚么不肯亲近伊了,真是无可奈何。”环蛾在骤然的打击面前张皇失措,她面对着一座迷宫,一个不解的谜。她不知道自己身犯何错,忽然间就遭到抛弃。人在莫名其妙中被送上了屈辱、悲哀的境地。作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变故的前提,前提并不重要,可怕的是你必然会遭到挫折。挫折是不避免的,又是无可挽回的。他的主人公经历一场凄风苦雨的感情挫折,暂时又未找到排解痛苦的良方,因而哭泣、悲哀成为《虹》中常见的情绪符号。命运的莫测,人的不由自主,胡山源的生命体验逼近现代意识,《虹》的意蕴大大超过作品表层所给予的启示。
人生的困境,奋争的无力是“五·四”时期大的人文环境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五·四”唤醒了个人的尊严、价值,前所未有地张扬个体生存、生活的权利,也前所未有地感到自身在社会、集体、他人挤压下的损伤、变异。胡山源的伤痕体验显然包容着作家个体的伤痕经历。少年时代家境的贫困,读书的机会屡屡被不公正的势力剥夺;成人后屡屡失业,爱情也遭磨难,26岁时其爱妻便不幸去世。这一切变故不能不在作者的心灵深处烙上永恒的创伤,不能不使作家带着悲哀的心情看待他面对的世界。诚然,作家的不幸不是纯粹属于他个人的,他的悲剧命运又是属于时代的、社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这种伤痕体验实际上也就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虽然作家主观上没有对此类不幸与悲剧作出积极的解释,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达到对人生、对社会本质的深刻把握。胡山源校园题材作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
一个作品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作家以文字为单元,构建中心理想的艺术世界。作家的审美个性决定了其艺术世界的基调、色彩、氛围。对胡山源来说,他在《虹》中构造了一个单纯、柔美、富有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
在《虹》中,进入艺术画面的人物并不多。胡山源习惯于把笔墨放在他认为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其它人物,则明显减弱其在文本中的地位、分量。《珂莲》中以珂莲为主,尽管她与品芝的关系变化构成情节的主线。品芝是性格冲突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琴键。但胡山源始终跟随珂莲的脚步,以她的行为、内心活动构成全篇的主要部分。作家的意图并不在于重铸生活的全部。他删除与作品内蕴关系不大的人物,往往只用二、三个人构成艺术画面的全部,显得画面干净、简洁、单纯。
胡山源笔下不仅人物少,人物的性格也大都呈现单纯的特色。《虹》讲究画面的整体感、和谐感。人物在画面中没有格外的凸出感。按照一般的小说理论,人物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任务之一就是塑造典型的、富有立体感的人物。然而文艺理论对艺术实践的指导并不能偏狭地理解为对文学样式的唯一规范。归根到底,艺术是个性的创造,要求作家以适合自身艺术才能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艺术把握。《虹》中人物没有达到所谓的典型化和立体化效果。作家追踪的并非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而是性格的显示过程,人物性格的基调从一开始就被基本定型。《虹》中人物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他们多情、善良,而又软弱。他们没有复杂深层的心理活动,也没有刚强果敢与外界抗争的强者气质。胡山源截取的是他们一段情感挫折历程。一个人心理的成长正是根源于一次次的人生经历。对《虹》中的青年人来说,情感的挫折正是他们今后性格分化的契机。但作家并没有把视线延伸至人物今后发展的某种可能性上,而在挫败来临之际嘎然而止,以哭泣的暂时性心理反应结束人物可能有的性格发展,呈现出单纯却不单调的艺术轨迹。
与人物性格的单纯相映照,《虹》中作品情节显示出完整性的单向性。故事通常设置为一条情节发展线。胡山源不讲究扑朔迷离、悬念陡生、暗悬伏机的戏剧性情节,材料往往取自日常生活。情节结构遵循日常生活的逻辑,流畅自如、水到渠成。作家在平凡的生活中提炼有意味的情节,这种情节的魅力不在于其紧张性、丰富性、曲折性,而在于洋溢于其间的真实的生活气息。《珂莲》是选择的几个场面。变故之前珂莲对品芝的情感依赖通过一系列的细节行为加以体现,对品芝的悉心照顾与变故之时的震惊、失落形成强烈反差。作者的缺损性人生告白在极简单的情节内得以展现。在叙述角度上以传统的第三人称叙述为主,采用单向性顺序叙述,没有突兀的断裂、插入和重新组织造成的迷离暧昧感,总体上干净利落、枝蔓不生,具有单纯、洁净的审美特点。
《虹》的语言特色也不容忽视。小说的语言不只是一种再现小说世界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存在。胡山源的语言典雅、优美,充满书卷气息。作家幼年时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他喜欢古诗词,也擅长写作古诗词。深厚的国学基础与文学修养潜移默化的流贯于他的作品创作中,文字清新自然,音色柔美,颜色清淡,像江南的山水一样淡妆素抹。
作家还注重小说的情感效应,力图使境与情合,达到心物合一,意境飘逸的境界。压题小说《虹》中青年学生醉红堕入爱河,因思念恋人而作一首诗反复咏叹对恋人的思念与期待,这首情深谊绵的诗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气氛。人物、情节、叙述、语言等要素的结合,形成了《虹》轻淡、柔美的审美特点。
三
一种创作特色的形成,与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审美追求是分不开的。
校园中伤痕性情感体验的描写胡山源并不是第一人。早在20年代初,女作家庐隐就曾发出对抗社会的悲怆之音,写到了校园内年轻人的苦闷问题。同样面对青春的伤痕,庐隐作品中青年的苦闷有时代的阴影,更有个体争取自由与社会正面交锋带来的挫折与伤感。对人生的失意,庐隐有明确的认识,并归因于社会的黑暗。传统文化观念的保守和社会发展的滞后,其作品满怀对强权专制社会的痛恨,呐喊出一代女性个性解放的抗争之声。庐隐身处京都,处于政治文化斗争的交界点,新思潮深入灵魂,又兼个性倔强,虽经历坎坷,屡遭不幸却挫败愈多、愤懑愈深,其作品充满肃杀之音。胡山源却不同。面对人生困境,作家无意去探求现象背后社会、政治的原因,亦无意以政治、道德来解释人生命运的一波一折。在作者看来,人生的失意是无法避免的。《秋雨》中借环蛾之口说出了对世界的看法:“人情的冷暖正如一年有四季的天气。”命运的变幻是必然的,困境的无可摆脱也是必然的。作家不探求悲剧命运的根源,让所有的人陷入困境,确认了人生命运的不自主性。比起那种天真地以为改换一种制度,换一种生活方式就可以解决人所有问题的浪漫性的作品,胡山源的艺术天地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人生的真实。
作家的好友丁淼回忆胡山源时,以“淡泊明志的胡山源”为题,说他“向来不问政,不问党,与人无争,与人无求,真真实实,安安乐乐。”作家在回忆录中也称自己“决不怨天尤人,自叹生不逢时”,“我活到今天,已深知世界本来如此,以往及将来也无不如此。”尽管这是作家暮年时的感叹,但也约略说明了他安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一个作家的人生观不能不渗透到他的作品中去。胡山源对世界采取了低调姿势,他承认社会的不完美乃至它的凶恶残忍,他以惊人的调和能力化解了疑问与愤怒,艺术地接受了缺憾的人生。《虹》中醉落在美漪那里失落的情怀于美棠那得到了补偿,正透露出作家自我平衡的能力。正因为有这种旷达的认识,人生的失意才没有向极端处发展,悲哀没有演变成悲观颓废的哀叹。与庐隐放纵于悲哀之中任己浮沉的风格迥异,胡山源真切深刻的伤痕体验艺术的化为轻淡、柔美的艺术世界,由浓而淡,没有大喜大悲的爱之切、痛之深,显示出雍容娴雅的特色。
《虹》的轻淡、柔美既是作家艺术个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作家自觉艺术追求的结果。胡山源创办弥洒社时发表了自己的文艺主张“无目的,无艺术观”,“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他注重文艺本身的特征,强调作品的真情实感,在《弥洒宣言》里作家以诗的形式宣告了自己的艺术追求:
于是Musai们来了,
飘着流云飞露的轻裙,
系着明星亮月的宝带;
执着和鸾鸣凤的乐器;
翩跹回翔的舞着,
宛转抑扬的唱着。
舞要“翩跹”,唱要“宛转”,说明“弥洒社”文艺倾向上的一些唯美主义倾向,力图以审美性创造滤去现实苦难浓重的阴影,建立纯粹的艺术世界。
胡山源重情感效应的艺术观从《虹》中也略见一斑。只发表“顺着灵感写出来的作品”,非深刻、真切的体验不足以成文,他以自己的文艺观念对生活加以检索,凡合乎艺术规律,能产生美文效果的方可纳入作家的素材之中。胡山源大学时代参加过学潮,并被开除回原籍。中青年时代足迹愈广,历任编辑、大学教师等,社会接触面不谓不广,但许多创作材料却如轻风过耳,转眼无踪,唯独校园生活中的人和事屡屡成为他作品中的形象素材。并且,在作品中创造出一个个清新如画、充满诗意的纯然与文网密织、腥风血雨的现实生活环境截然两个天地的艺术世界。这其间,作家的文艺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弥洒社”的艺术观的评判历来多歧义,“弥洒社”被归于另册与这种“艺术至上”的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以为,以作家的文艺观来片面判断其作品的价值是不科学的,或者至少是不全面的。作家有各自具体的情况。胡山源所宣扬的“无目的、无艺术观”并不是说作家完全否认了艺术的社会功能。胡山源曾解释当年的主张,说“任何文章当然要‘露出目的’的,没有目的的文章是没有的。不过,‘目的’,只能指写成文章后而言。若先有目的,然后找寻材料,写成文章,只有某种论文为然。”他明确表明:“我们并没有打出‘为文学的文学’或‘艺术至上’的旗号。”“我们的用意:弥洒社的作品,应该在内容方面,是无所不包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而惟一的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必须是足以感人的,真正的文艺作品。”“无目的”论主张文艺独立性,恰当地揭示了文艺的特性,它反对把文艺作为政治、道德的附庸,在当时是值得提倡的,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启示意义。
从胡山源的创作实践上看,他的艺术主张并没有使作家背向社会,闭门造车,陷入构造虚幻世界的艺术绝境。鲁迅先生曾评说“弥洒社”说:“一切作品诚然大抵致力于优美,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五十年后,胡山源在《弥洒社的经过》一文中说:“所感觉的范围相当狭窄这话很对,我完全接受,因为我们的生活,只在这‘狭窄’的‘范围’内,我们的写作,自然就跳不出这个范围了。但我们以为‘一滴水可以看太阳’,狭窄的范围,未尝不可反映全世界”。胡山源内容的“狭窄”,与他的经历有关,亦与他的写作意图,创作主旨相关,意欲以“一滴水”反映整个太阳之大、之宏。题材的大小并不必然与作品的价值成等比。文艺作品关注者乃为人,人的生活、人的命运。一个大的、政治性命题或许其中蕴含的人的生存信号却寥寥无几,一个小的材料又因作者生命体验的真挚而达到对人本质的了解,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并不乏此类范例。一切文艺作品,其价值并非能简单地以其政治历史含量的多寡为唯一评判标准,艺术的政治、道德教化作用也不能涵盖其社会教益的全部功能。鲁迅当年对“弥洒社”的评价未始没有其强烈的时代意义,又难免失之于“苛”。“五·四”文学革命提供了文艺创作自由宽松的空间。一大批艺术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得以发出异彩。历史为胡山源的出现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民族解放的严酷任务又使作家的文艺探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艰难、不合时宜的选择。胡山源的创作和他几十年的被冷落让我们看到“五·四”人文精神的一段辉煌和暗淡。对胡山源的再认识提供我们对现代历史的一次更为深长的思考,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
标签:小说论文; 胡山源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艺论文; 秋雨论文; 手套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