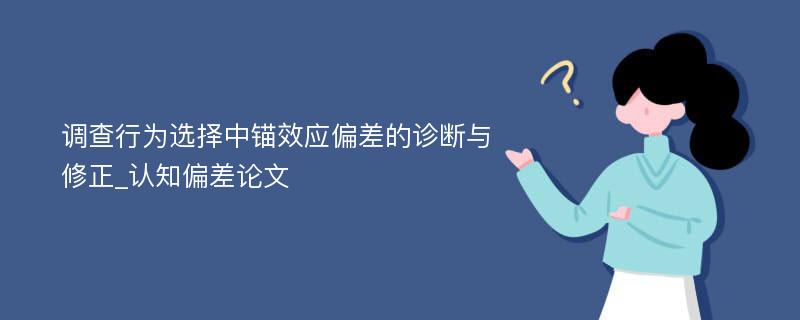
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诊断与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偏差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140(2014)05-0034-13 锚定效应偏差既是个案侦查参与者思考、判断专业问题最常见的认知现象,也是其最不容易自觉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该类偏差既可成为其他认知偏差的“支持基”和“孵化器”,与其他认知偏差交互作用影响侦查行为,亦可单独对侦查活动产生较大的干扰。刑事错案特别是典型的刑事错案几乎都根源于此。然而,长期以来,不仅我国侦查学界对于该问题未进行全面、深入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侦查实务部门同样未对这类偏差开展整合式应用研究。为了解决这个基本的、重要的且几近研究空白情境的侦查理论和应用问题,本文从侦查行为科学视角和跨学科论域讨论了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基本属性、主要来源、典型样态及其修正策略。 一、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属性分析 (一)认知“锚”是一种典型的侦查认知现象 “锚”是指侦查人员针对不确定性个案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时,依据预期性信息作出的实证前侦查预断,是侦查人员特别是有经验的和“科班出身”的侦查人员开展侦查活动时的一种常见的认知现象。 根据侦查认知锚的来源,可以将其分为内在锚和外部锚两种。内在锚,是侦查人员认知待证犯罪事实时所依据的参照标准,主要包括侦查人员自身的类案侦查经验(直接经验或实务经验),偏好的预期性信息和由此形成的实证前侦查预断等。外部锚,是侦查人员认知待证犯罪事实时所依据的参照标准,主要包括其自我直接经验以外的类案侦查经验,外部指定的信息和由此形成的实证前侦查预断(包括间接经验、书本知识和外来指令)等等。 一般情形下,侦查认知内在锚和外部锚对侦查人员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力。有研究表明:内在锚往往会受侦查人员实施侦查行为的动机和可获得预警的影响,而外部锚则一般不受此类因素影响[1];在个案侦查实践中,相对于外部锚而言,内在锚导致的侦查锚定效应往往可能更为显著和持久。 (二)侦查锚定效应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普遍存在 侦查锚定效应,或可称之为侦查认知定势①偏好,是指侦查人员在不确定性侦查情境中对犯罪行为要素及其整体状况或“行为模型”进行信息挖掘及处理时,基于已有的侦查认知锚进行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的偏好。 当侦查人员面对不确定性侦查情境时,通常会借助自以为有把握减少不确定因素的“思维捷径”即侦查认知定势缩短或简化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过程或任务。在此种情形下,由于侦查人员更偏好和专注于利用这样的认知定势理解和处理不确定性侦查问题,往往会受到该定势所具有的先验的信息选择倾向或实证前侦查预断的引导,使其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指向、集中于侦查认知锚,并因此而抑制离散信息特别是较远偏离此“锚”的其他信息或可能性,导致相应的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其普遍性不仅有很多成功的实验研究结果证明,更有大量的侦查实案特别是刑事错案证明。 不仅如此,侦查所处其中的整个刑事执法共同体都普遍存在着锚定效应。有研究表明,最终的法庭判决常常受到辩护律师第一次提案的影响[2],侦查、起诉亦不例外。由于人们习惯于把思考定位于最初获得的信息或者实证前预断,就像船被下锚了一样[3],所以,如果办案人员不注意克服这种思维定势的负效应,就可能使办案活动受其内在锚的影响。 分析所有的刑事错案,不难发现它们具有的最基本的共性因素就是办案人员办理个案过程中均发生了显著的锚定效应偏差及其累积性迁移效应: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起诉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审判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侦查、起诉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 (三)侦查锚定效应具有类向量属性 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通常都是受侦查人员参与侦查之基本需要或者主要目标驱动而不是由案件某个具体事实的刺激驱动的。由此所决定,侦查人员对个案犯罪事实的认知机制既不完全符合“S-R”模型,也有异于“S-O-R”模型,而应当是“S-O’-O(-A)-R”。即是说,侦查人员在启动个案犯罪行为认知之前,往往会在其需要或目标导向下形成一定的预期,并以此预期作为待证个案事实(S)认知的参照系(O’),即在锚定效应影响下进行犯罪行为侦查认知(O);如果侦查人员觉察到认知锚可能会导致偏差时,便可能对由此引发的认知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A);然后作出自己的侦查预断(R)。由此而论,侦查锚定效应是一种典型的类向量性认知现象[4],其效用在所有的侦查中均具有双重性:积极的正向效应和消极的负向效应。 一方面,侦查锚定效应可能表现为消极的负向效应。大多数侦查人员做出侦查行为选择时首先会根据给定的信息或者已有的经验找到一个参考点即“锚”,然后将所面临待证个案实际问题的具体情形与这个“锚”进行比较并对新的信息进行“合锚”认知而得到答案(推论)[5]。而且,即使这样的认知本身可能存在着错觉、偏见或其他非理性的因素,它们也可能因为锚定效应而不易被侦查人员察觉,从而顺利融入其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之中,对其侦查决策和执行产生消极影响。锚定效应与人的认知与行为选择间的这种常伴常随的关系状态使得许多研究者对锚定效应本身及其与人的认知及行为选择间关系性质与特征,以及影响人的认知及行为选择的机制、方式和结果等问题特别是认知定势负效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尽管侦查认知偏好也是侦查人员认知及行为选择中的普遍现象,且其负效应通常是刑事错案的最深刻原因之一,但侦查学界和实务界的专家们却很少关注并对侦查锚定负效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已有成果多是所谓侦查基本规律的正面讨论,且其最终成果通常集中体现为教科书描述的类案侦查之“金科玉律”,却罕见关于侦查锚定负效应的描述——当个案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与其所属类案之规律不相吻合的情形下,侦查认知定势的负效应的典型样态往往表现为:因侦查人员忽视自己的认知定势所具有的负向功能,或者偏好于选择性对待个案信息的行为惯性而增加个案侦查的不确定性因素,强化无效侦查认知及行为,导致相应的侦查决策及执行偏差。 另一方面,侦查锚定效应可能表现为积极的正向效应[6]。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利用自己或他人办理相似案件所形成的类案侦查经验正确决策,提高个案侦查效率,但其所需的基本的支持条件有:一是侦查人员能够相对完整地掌握个案信息;二是能通过证否方式充分考虑其他因素;三是个案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与其所属类案之规律具有较高吻合度;四是侦查人员掌握并能够正确运用法定侦查原则。只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侦查锚定效应才能在提高侦查的确定性和效率、降低侦查成本、减少侦查人员尝试错误行动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侦查锚定效应具有不可避免性 国外科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证实锚定效应是人类认知的一种普遍的、顽强的、难以消除的判断偏差。杰米奥·布鲁纳和利奥·波斯特曼于1949年进行的实验是关于选择性知觉的最早和最著名的实验之一。笔者采用同类实验方法检验了锚定值域差异及对象差异对于人们选择性认知的影响,特别是对经过大学的系统化专业教育的学生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的影响,②通过实验结果的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锚定效应是人们的认知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尽管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不同,但人们的认知存在锚定效应却是一致的。我们所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所想看到的、习惯看到的,或是大脑中已生成的东西,并可能因此而忽视异常的个案特殊情境。尽管受到提醒,我们仍然会倾向于注意那些与“认知锚”相近或相似的信息或景象[7]。 其二,锚定效应一旦形成,就会很容易转化为人们认知及行为选择策略的“定势”,改变它虽然并非不能,但却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人们在这种认知情境中,更容易选择维持自己最初的认知及行为选择风格,即按照一个相对固定的认知定势惯性地走下去——这个“锚”不仅影响其此时此刻的选择,也会影响其后续的选择,从而导致锚定效应偏差,影响最终的决策及执行结果。 其三,认知者所拥有知识的专门化程度越高、越单一,锚定效应的效用越显著,它所导致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越大;其知识的跨专业、可迁移程度越高,越具有复合性,其认知锚修正的可能性越大,锚定效应所导致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越小。Wilson等人于1996年通过实验发现基本锚定效应只发生在低知识个体的认知之中。个体有关锚定信息的相关知识越丰富,越不容易受到锚定值的影响,从而越不易产生锚定效应。其他研究者基于传统锚定范式条件所做的实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此种现象符合选择通达模型原理:个体的相关知识越多,建立的与锚一致的心理模型就越少,所产生的锚定效应就越弱;反之,个体的知识越少,建立的相应模型就越多,锚定效应也就越强。 其四,刑事诉讼各环节的运行无一例外地存在着锚定效应。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往往会受其已有的知识(通常体现为教科书所传递的所谓类案侦查规律)、经验(集中体现为侦查人员自身或有影响的同行成功的侦查实践经验积累和模仿)、价值观念(包括法律价值选择、职业角色价值偏好和个人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通常表现为侦查人员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定势)影响,对个案相关信息中的某个(些)信息的发现、描述、应用表现出更显著的偏好,并倾向于依据这样的信息作出实证前预断,导致其对待证犯罪事实的认知明显亲和于认知锚。另外,亦有研究证明在法律专业领域的问题判断中,无论是专家(法官)还是非专家(非法律专业的大学生),都会受到认知锚的影响而产生锚定效应偏差[2,8]。 其五,尽管侦查锚定效应不可避免,但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方法,却能够明显减少侦查锚定负效应。 二、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主要来源 (一)不确定性侦查情境中先验概率③计算或满意决策选择偏好的影响 人的认知特质和水平影响人的决策,而人的认知又受人的性格、知识、文化背景、所处情境、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侦查人员的专业行为与传统侦查学的假定有很大不同:侦查人员认知个案犯罪事实的过程中,时常会面临不确定性情境,加上侦查时间压力,很难进行传统侦查学特别是侦查学教科书所假定的完全专业化理性认知,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衡量个案犯罪事实生成过程及结果的各种可能性及其发生的准确概率。因此,大多数侦查人员面临不确定性侦查情境时,常常会采用某种可以使之形成经验性预见或有助于自己作出实证前侦查预断的方式认知犯罪事实,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具有较高经验概率、令自己和所属侦查群体能够接受的满意决策。其适用情境主要有: 一是在个案犯罪行为比较典型,案情比较简单、具有较大确定性,并且侦查人员能够根据相对充分、确凿的证据确切判断待证犯罪事实的情境中,他们往往更习惯或偏好于直接从专业学习获得的某种规律性知识或者自己的经验仓库中提取相关信息,对个案犯罪行为直接作出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在此种情形下,如果犯罪行为客观上具有较高确定性,侦查人员的这种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将因正向锚定效应而获得事半功倍的侦查效用;若个案犯罪行为呈现给侦查人员的只是作案者制造的假象,则侦查人员的这种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好将因负向锚定效应而造成事倍功半或侦查僵局或失败的侦查效用。 二是当个案犯罪行为虽不具有侦查人员可以把握的确定性,但其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却显示了比较突出的该案所属之类案的基本特征时,尽管侦查人员不能确认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形或准确判断犯罪事实与类案标识性特征事实间相似之确定性程度,他们仍会习惯于从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中挖掘、提取与类案标识性特征事实相似的信息,并以这些信息作为自己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的依据或参照系。在此种情形下,如果个案犯罪事实与其所属类案之标识性特征事实间的相似为真相似,则它与正向锚定效应成正比,与负向锚定效应成反比;若个案犯罪事实与其所属类案之标识性特征事实间的相似为伪相似,则它与正向锚定效应成反比,与负向锚定效应成正比。 三是当侦查人员既不知道确切的个案犯罪行为过程,也不能简单地运用类案标识性特征事实进行判断时,他们往往不得不依据自认为相对可靠的已有知识或经验进行更为复杂的侦查认知,对犯罪行为过程及其结果构建一种具有显著偏好的对比性认知模型或关于犯罪事实的实证前侦查预断,并以此作为解读犯罪行为事实模型的参照系。在此种情形下,侦查人员为了解决待证犯罪事实之认知模型与事实模型间比较、判断的侦查问题,他们往往会致力于验证待证犯罪事实模型具有符合自己所构建之认知模型的可能性:他们首先会假设待证犯罪事实模型与自己构建的认知模型基本相符,即对于自己的实证前侦查预断进行证实性的假设验证,假设自己所参照的锚——认知模型可能就是待证犯罪事实模型,从而使其知识、经验及信息仓库中与该认知模型相一致的知识、经验和信息被提取和应用的概率得以增加。随后,在验证实证前侦查预断的过程中,由于侦查人员习惯于优先依赖这些更容易获得的知识、经验和信息,其验证过程及结果通常体现为侦查人员努力通过信息筛选和偏好性应用确认自己的实证前侦查预断,从而完成对“认知模型”与待证犯罪事实模型相符的检验,并因此而产生侦查锚定效应[9]。但需要关注的是,如果侦查人员发现了自己所构建的认知模型与待证犯罪事实模型间不相符合,或者后续的可确认信息与先前所依据的“通达性信息”即用以构建及强化认知模型的信息相冲突,并在验证自己的实证前侦查预断时不再依赖或应用这些信息,锚定效应则可能不会发生[10]或使之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二)个案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锚定效应非充分调整习惯的影响 与上述研究结论不同,一些研究者通过新的实验发现并描述了有别于“选择通达机制”的“不充分调整启发机制”[11-12],并与选择性通达模型理论并存为两个最基本的锚定效应发生机制理论。根据该理论,当侦查初始阶段不具备充分信息、侦查人员难以对个案犯罪行为事实模型基本构架形成知觉性概念时,侦查人员为了正常推进侦查活动,往往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信息仓库先行建立一个初始的犯罪行为认知模型,并因此而产生内在认知锚。在此种情形下,由于可确认的犯罪事实模型信息特别是全息性信息或类案标识性特征信息稀缺的制约,侦查人员往往不能具备将其构建的犯罪行为认知模型与待证犯罪事实模型进行比较、判断的必备条件,由选择通达机制引发侦查锚定效应的可能性也会因此而降低。 此处作出如此描述并非意味着此种情境不会产生侦查锚定效应,而是要说明此种情境中的侦查锚定效应往往不会因为“选择通达机制”产生,而是通过侦查人员普遍存在的侦查锚定效应偏差非完全调整的习惯做法或者“不充分调整启发机制”形成。实际上,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对自己所觉察的负向锚定效应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十分常见,问题是既然侦查人员会有意识地根据后续信息对先前设立的侦查认知锚进行相应的修正,为什么还会存在侦查锚定负效应?其关键在于这种修正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侦查人员对其内在锚的“不充分调整”。基于这一解释,锚定效应对于侦查活动的影响程度及结果是受侦查锚定效应偏差调整程度及实效制约的。 一方面,当侦查人员觉察到自己针对待证个案犯罪事实设立的侦查内在锚不正确或具有某种明显的负向效应时,往往会对该认知锚及其负向效应进行相应的调整或修正,以进行正确的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另一方面,处于此情境中的侦查人员对于自己所设立的侦查内在锚的自我调整或修正通常又是不充分的或者很难实现充分调整或修正的目标,并因此而导致锚定效应的产生。其调整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调整资源稀缺与认知懒惰惯性的共同作用。侦查人员欲将自己的认知锚及其负向效应调整到完全适配于犯罪事实模型的程度,不仅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而且需要付出许多认知努力,甚至承担一定的责任压力。若这种调整是根本性、全局性的调整,则主、客观方面的要求或许会更高。由此所决定,侦查人员往往更偏好于以已设立之“锚”为调整的依据,并努力围绕着该认知锚进行并不充分的上下调整或有限调整。二是调整区间有限与可接受性标准的共同作用。当侦查人员面对不确定性个案侦查情境时,对于预设之认知锚的调整通常会先赋予一个可调区间④或可行区间⑤,并以实证前侦查预断为基准,尽可能地进行充分性的调整,同时检验调整过程及结果是否可接受。当侦查人员觉察自己所做调整可能突破可调区间或者已经进入预设的可行区间,且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或让侦查人员自己和所属侦查群体感到“满意”,调整便会停止,从而形成调整不足,导致锚定效应的产生。三是单一机制与复合机制的共同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单一认知效应与多种认知效应共同作用导致锚定效应的产生及强化,如证实效应偏差、时间压力效应偏差等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偏差与锚定效应偏差共同作用于侦查人员所形成的复合性影响。其二,“选择通达机制”与“不充分调整启发机制”共同作用导致锚定效应的产生及强化。其三,内在锚与外部锚共同作用导致锚定效应的产生及强化,关于此,有研究者用“双加工理论”进行了描述。实践中,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个案的犯罪行为都有其独特且比较复杂的具体情节,加上侦查所具有的法律及社会功能要求以及侦查行为的群体化、系统化特性的影响,侦查人员对个案犯罪行为的认知过程通常不存在单一的内在锚和外部锚影响,而当内在锚和外部锚共同影响个案侦查认知时,就可能发生“选择通达机制”和“不充分调整启发机制”的整合加工[13]:当外部锚信息与内在锚信息一致时,更容易通过选择通达机制形成侦查锚定效应;当外部锚信息与内在锚信息不一致时,更容易通过不充分调整机制形成侦查锚定效应[14]。 三、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基本样态 (一)先入为主偏差 先入为主,是指人们面对不确定问题情境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做出能够帮助自己脱离困境的实证前预断,并在后续的认知过程中倾向于寻找或选择那些支持和证实该预断的信息的认知偏好。 这种认知偏好普遍存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刑事执法阶段。弗兰克曾对此作了精确的描述:一般情形下,执法者的判断过程很少由前提开始,而是从形成一个模糊的结论开始,然后试图找到证明此结论的前提。实际上,个案刑事程序中各个环节的执法主体都可能对相关犯罪事实形成自己的第一印象,而且,他们通常会按照该“第一印象”预设待证犯罪事实的认知框架,并依赖自己的认知定势,选择与实证前侦查、公诉、审判预断相匹配的思路分析、理解、把握、应用待证犯罪事实之信息。这种“第一印象情结”呈现给我们的典型样态就是先入为主。关于此,法律共同体已有认识:美国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认为最基本的社会利益之一就是法律统一且无偏私,法院的司法活动没有偏见、偏好以及专断和间歇不定[15]。美国学者Levental提出的正当程序标准也明确指向审判者需要克服先入为主偏见[16]。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先入为主、倾向认可有罪的承认和根据不确定的材料认定事实等预断行为和心态[17]。反观可知,刑事执法共同体普遍存在的锚定效应均可能以执法者先入为主的认知及行为选择偏见形式呈现并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和科学性,作为该共同体成员且通常以先入为主之“始做俑者”角色⑥出现并发挥作用的侦查人员更不例外。 从侦查科学理性角度看,严格遵循逻辑、科学、法律规则进行严谨的、无懈可击的推理是所有侦查人员都必须运用的最基本的犯罪事实认知方式,而且,在这样的认知原则下,不同的侦查人员对同一个案件或者对具备相同或相近要素的不同案件应当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同样的推理过程并得出相同的推论。然而,在理论上,这样的理性判断和原则有悖于共性与个性间关系原理;在实践上,它与出自大多数侦查人员的个案侦查经验相抵触。事实上,不同的侦查人员面临相同或相似案件时,他们对待证犯罪事实的认知及其对具体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的推理却可能不尽相同甚或大相径庭。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侦查人员对于任何一个案件之犯罪行为的推理过程实际上都是他们的知识结构、认知定势、人格特质、需求目标以及个案侦查任务、推理条件、侦查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侦查人员事实上很少按照所谓学者所生产的闭门造车式侦查学理论特别是传统的侦查逻辑教科书所描述的推理模式进行侦查推理活动,其推理路径的选择通常会依赖自己的认知定势和源自侦查实践并真正对个案侦查具有实际指导价值的应用性规律⑦进行,而先入为主作为其主要角色往往在该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且不能为其他因素所取代的作用。 从侦查技术应用角度看,科学技术检验的唯一任务就是为再现犯罪行为过程及结果提供可靠、可信、可获得普遍接受的事实支持,而作为科学技术检验完备形态的科学证据也因此而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科学证据在构建犯罪行为证据链及论证链方面的这种功能定位往往会促使侦查人员对技术检验活动进行积极的“干预”——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努力把自己所作的实证前侦查预断传递给技术检验人员,以期将自己通过先入为主形成的犯罪事实认知结果转化为他们所雇用的技术人员或其本部门内设之检测机构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检验之外部锚。事实上,如果侦查人员事先交代了自己所作的实证前侦查预断,那么,此类所谓的专家通常会“先入为主”,以此外部锚为依据进行非中立、不纯洁的“技术检验”,并向侦查人员提供他们所期望的与其实证前侦查预断相一致的鉴定意见。 (二)选择性注意偏差 选择性注意,是指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从案件所有的信息源中优先选择特定的信息进行加工,同时忽略或者无视其他信息的认知过程。 布鲁纳和波斯特曼认为,人们的知觉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建立在过去和情境基础上的预期所决定的[18]。当人们对某一特定情况有了足够的经验时,他们就会习惯于看到那些他们预期看到的东西。这类锚定效应偏差的基本样态通常表现为侦查人员构建犯罪事实认知模型并将之与犯罪事实模型进行比较时的选择性注意偏差——“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19]。其基本原因是侦查人员对犯罪行为的实证前预断不仅界定而且限制着他们的认知,而且,即使这种认知可能存在着歪曲或者忽略的情形,侦查人员依然会倾向于看到那些符合自己预先假设的事物或者偏好于挖掘、处理与之一致的信息。这种认知偏好导致侦查人员几乎不可能避免选择性注意偏差。 任何一起个案所发散的信息的本身并不具备实质的法律意义,只有通过执法者遵循法律程序挖掘这些信息、依照法定规则构建证据链和论证链,并运用法律标准对之进行价值描述后才能赋予它相应的法律意义,而且,这些案件信息和建立其上的证据链及论证链只有经过执法者的专业编码才能进入法律预设之框架,并为执法体系所理解和接受,将之作为法律推理的依据和刑事裁判的基础。由此所决定,作为犯罪事实的最初的证据链和论证链构建者,侦查人员对犯罪事实的心理指向和信息注意偏好必然会对后续的执法环节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决定着侦查人员选择性注意最初态度的核心要素便是其内心早已具备的价值观念,⑧它可以从内部强有力地引导侦查人员对自己期望注意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取舍,而且,侦查人员对与其实证前预断相一致的信息注意得越多,越容易将之纳入犯罪行为之因果归因,所发生的选择性注意负向效应也会越大[20]。 (三)权威遵从偏差 此处所说的权威遵从,是指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遵从行政领导、所属群体以及技术专家所作的“权威性”实证前预断构建犯罪事实认知模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者无视其可辩性、可逆性和可否性,将犯罪事实模型与其认知模型进行“套模”式比较的认知过程。 其一是行政权威遵从。侦查领域之权威遵从的最典型样态体现于侦查机关内部的上下级关系之中,而且,这种关系能够非常典型地描述LMX理论⑨:一个组织的LMX质量越高,下属表现出的指向组织和人际的反生产行为CWB越少[21-24]。国内有人运用该理论对中国行政文化圈中的上下级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层级关系、职务隶属关系和伦常关系的混合体[25];也有人将之描述为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性的上下级关系。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动机性行政权威遵从偏差,通常表现为侦查人员对不确定性侦查情境不自信、习惯于将行政权威的决定奉为不可罔顾的行政指令、行政权威自我中心或过度自信相整合所导致的行政权威遵从偏差。二是非动机性行政权威遵从偏差,通常表现为当侦查人员面对不确定性侦查情境时,需要行政权威对不确定情境因素作出初始的特异化处理,⑩继而将该初始、“特异”的实证前预断作为贯穿个案侦查始终的依据所导致的行政权威遵从偏差。 其二是群体权威遵从。由于刑事执法具有典型的群体性、系统性、阶段性特点,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安排,该体系所承担的个案办理职责必须由相对独立的不同群体分段实施。而参与其中的各个群体为了保障其群体职责目标的实现和群体专业活动的一致性,往往会显性或隐性地适用一套本群体的角色行为准则或者习惯性规则,即该群体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思想评价和行为准则,用以调节本群体成员的互动过程,并因此而导生受模仿、暗示、遵从等心理支配形成的群体意见一致和维持这种一致的异议对抗机制,形成群体权威遵从偏差。刑事执法实践表明,这种群体认同和群体偏见间的密切的共存关系及其导致的群体权威遵从偏差不仅可能发生在分属不同阶段的执法群体之间,也可能来源于同一个执法机构不同部门群体之间或者同一个执法部门的不同专案的群体之间。 其三是专家权威遵从偏差。格雷戈里·诺思克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的研究显示,在现实生活情境中,专家并不能避免锚定效应。尽管一些研究者采用不同的范式就预警对锚定效应的影响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预警对锚定效应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这样的预警来自专家意见时,更容易出现权威遵从偏差。专家通常被描述为具备外行人不能直接获得的专门技能和专业知识,能够解决一般人所不能解决的专门性问题之专业能力的人。由他们提供的科学证据若能够被恰当利用,往往可以成为确认案件事实、定罪量刑的最好证据,正因为此,刑事执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各式各样的专家鉴定意见。然而,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不争事实是,一方面,没有科学背景的人很难准确地理解一些科学技术测试(例如刑事执法特别依赖的DNA测试等)是如何进行的,更不用说评价这些科学技术知识在个案办理中是否得到了正确的运用,这就使法庭科学作为第三方树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不会去对它进行科学和技术上的深究细查,而更习惯于将之作为不会错误代表或偏袒任何一方的专业知识[26]。另一方面,刑事执法实践中的“专家之战”几乎是司空见惯的。这种现象既可能产生于专家的科学技术服务通常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价值选择的某种影响,(11)也可能更经常地来源于科学理论、技术方法和调查结果的动态变化,而且,随着刑事执法领域的科学与技术质素组分比例的提升,这种现象将会有增无减。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理由达成一个共识:刑事执法者既要充分利用专家意见,又应谨慎对待之。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重新审视赋予专家意见特殊地位的基础性假定——某种技能或知识领域的专家对该领域证据材料或知识具有非专家所不拥有的特殊的认知途径,并由此而从逻辑上把诉诸专家意见等同于诉诸权威论证来处理。事实上,科学实验研究和刑事执法实践都表明,专家意见也可能是一种误导形式,故若未对其论证的细节全面适用科学的、逻辑的、法律的标准进行质问,均不应赋予它太高的证明力[27]。 四、侦查行为选择锚定效应偏差的修正 (一)合理设计刑事预断排除规则进行制度性修正 刑事预断排除规则,通常是指审判阶段之法官预断排除规则,(12)即法官只能依据在庭审过程中经过控辩双方间相互质证与辩论所确认的证据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做出公正的判决,而排除其他任何可能导致法官先入为主的偏见和预断信息的诉讼程序总和[28]。也有学者更具体地将之界定为防止法官在审前或审中就案件事实产生某种偏见,形成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预断心理的各种诉讼程序总和。 此处所讨论的刑事预断排除规则是一个更宽适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审判阶段之法官预断排除,而且,还必须将法官预断排除建立在侦查和起诉“预断”(锚定效应)排除的基础之上,既以侦查、起诉锚定效应可容错度的限定来保证法官锚定效应偏差的最小化,又以法官审判锚定效应的最小化督导、审查、评断、制约侦查、起诉锚定效应,将之控制在可接受、可容忍的限度之内。提出此宽适概念的依据是我国刑事共同体现行的制度安排和运行实况的改革需求和刑事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规律。 从侦查、起诉、审判证据结点视角分析,设计刑事预断排除规则时,需要关注三个基本问题: 一是任何个案的起诉、审判都不应也不可能离开侦查阶段所获证据和侦查人员构建的证据链、论证链及其以此为基础构建的犯罪行为认知模型。实际上,法官进行审判、作出判决的基础是侦查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再由检察机关提交法院的承载着个案犯罪行为证据链、论证链和侦查、起诉认知模型的案卷材料。由此所决定,我们在分析刑事执法锚定效应偏差问题时,必须弄清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即个案办理过程中关于“主要证据”取舍范围的“划定”权往往集中在检察院的手上,检察机关为了确保起诉犯罪的准确率和成功率,往往只向法院移送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它们通常都会成为法官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所必须考虑和加以审查的关键证据。因此,需要通过构建、推行法官预断排除机制,将侦查、起诉锚定负效应对法官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促使侦查及起诉人员真正认识到产生于该机制的法官裁决是自己必须接受的个案结局,而且学会并自觉地尊重这些裁决,确保自己工作的高质量和高效度[29]。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共同体及其运行实践中,通过确立侦查锚定效应可容错度标准减少检察人员起诉锚定效应偏差,通过确立起诉锚定效应可容错度标准减少审判锚定效应偏差,通过确立精细的法官审判锚定效应偏差问责标准以减少侦查及起诉锚定效应偏差是设计及运行刑事预断排除规则的关键。 二是起诉人员对于侦查结果的审查和以此为基础作出起诉决定应当具有一定的“超然性”,(13)既不能将侦查部门建构的证据链和论证链视作“零”,一切都从头开始,也不能通过各种形式直接移用侦查人员构建的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而应当坚持采用逻辑、科学、法律的标准对侦查部门构建的证据链和论证链进行独立的全面审查,在形成证据确信、内心确信基础上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三是依循我国主流的诉讼阶段理论和现行制度安排,侦查、起诉、审判被视为前后相继但彼此独立的诉讼阶段,由于侦查阶段与检察起诉之后的审判阶段被相对隔离,在刑事执法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种常见现象:侦查与审判间这种形式上的隔离不仅遮蔽了侦查活动对审判活动的实质影响和重大作用,也掩盖了法官过分依赖和直接移用侦查结果的审判现实。因此,需要通过构建、推行法官预断排除机制,确保审判独立而不直接依附于侦查人员构建并通过起诉人员强化和传递的证据链及论证链,使法庭的裁判结论独立来自于法庭审判过程,而不是自然地、直接地生成于侦查——起诉结论。这既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侦审关系的关键环节。 (二)立足锚定效应形成机制进行对应性修正 Alexander A.Petrov和John R.Anderson通过实验发现了锚定效应的形成机制,并将之描述为下列模型: Ⅰ.基本模式:刺激强度→内部增量→锚定值→校正量→应答 Ⅱ.变式1:刺激强度→内部增量→锚定值(校正量)→应答 Ⅲ.变式2:刺激强度→内部增量(→锚定值)→校正量→应答 一般而言,侦查要素参与个案侦查的实际过程通常有五个共同的重要环节:其一,侦查人员接受个案侦查任务后,通过涉嫌犯罪现场勘查或其他信息通道对侦查情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显态信息汇集;其二,侦查人员在挖掘、利用相关数据或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侦查认知定势形成实证前侦查预断、设定犯罪信息选择性注意方向,并依循这种偏好采集、处理某些特殊的个案信息;其三,侦查人员通过信息的选择性采集、处理和初始的侦查预断的证实性检验,构建确信度更高的实证前侦查预断,形成初步的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其四,采用一定的外部策略弥补自己认知及行为选择的某些局限,同时又通过与个案侦查情境相关因素特别是一些新信息的共同作用推进可接受的侦查活动;其五,获得可认同、可接受、令人满意的侦查结果。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个案侦查演进模式说明,利用上述模型分析侦查锚定效应的形成机制,控制侦查锚定效应以提高其正向效度或降低其负向效度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和适用。 通过上述模型分析不难看出,立足侦查锚定效应形成机制进行对应性修正的核心问题是侦查人员内在锚效应的修正,其关键技术集中于“刺激强度”结构设计、“锚定值”形成引导和“校正量”合理赋值等方面。 一是通过运用强势的外部预警方式,有效干预侦查人员初始的“不确定性侦查情境”分析,引导或限制侦查人员之“锚前估计”——侦查人员对不确定之个案犯罪行为的认知合模于其内在锚之前的侦查预期——生成过程,以防止其依据这种先入为主的“锚前估计”在后续的侦查认知过程中给予个案信息以“选择性注意”,以证实其内在锚偏好的侦查认知及行为,导致“内部增量”发生方向性偏差。由此而论,个案侦查管理者一开始就采取一个“极端”且与侦查人员内在锚相反的立场或许会获得更好的干预效果。(14) 二是通过运用强势的外部预警方式,有效干预侦查人员锚定信息结构,最大限度地平衡办案人员内在锚信息与通过外部预警方式传递的外部锚信息对侦查人员认知及行为选择的影响力,赋予两类信息以合理的效度权重,(15)以保障侦查人员构建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的过程中,既能够强化其理性侦查的信念,加快其认知及行为选择的灵敏度和确信度,又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其由于内在锚信息与外部锚信息影响力或权重的不均衡所导致的过分自信或自信不足,避免侦查决策的失误。需要强调的是,采用这种方法限制侦查锚定负效应的前提是所引入的外部锚信息应当对侦查人员的认知所依赖的内在锚信息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足以使之理性地与外部锚信息结成同构关系。(16) 三是与前两类干预不同,对于侦查人员已经形成的实证前侦查预断进行修正的难度要大得多,通过运用强势的外部预警方式对之进行校正的技术也更为复杂。其一,从证否的视角通过七个步骤审视侦查人员的实证前侦查预断:了解哪些信息可能与待证个案犯罪行为相关→挖掘和收集各种确信的、可能的犯罪信息→对收集的所有信息进行经验的、逻辑的、科学的分类和解释→在专业分类标准指导下评估所有信息对于个案犯罪情境的符合概率→采用逻辑的、科学的策略对所有的评估信息进行证据意义的整合→根据证据关联意义上的整合结果与个案犯罪情境间的匹配状况判断两者及其基本要素事实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法律标准指导下评估可确信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判断这些相关关系仅只是一般关联,还是因果关联。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的每一步皆不可偏废或省略,因为任何一个侦查人员包括侦查经验非常丰富的侦查人员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以上七个环节的认知中可能出现的锚定效应偏差。其二,针对侦查人员的实证前侦查预断确定一个反方向的相等的锚定值,或者通过外部强力输入多个具有显著差异的锚定值,以帮助侦查人员避免因对自己所建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的偏好而进一步固化其锚定负效应,并导致附随的证实偏差。(17) (三)引进批判性思维工具进行方法性修正 在个案侦查实践中,不论是新手还是具有丰富知识的专家,都可能受到锚的影响而发生锚定效应,特别是在复杂的、严重的、影响大的个案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通常都会受到来自行政领导、侦查群体和技术专家等方面的外部锚影响。这类外部锚一方面可能促进个案侦查合理、有效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侦查人员的个案认知形成外部锚定负效应。可用于修正这种锚定负效应的批判性思维工具或许有很多,此处讨论三个相互关联且具有一定递进关系的方法: 其一,整合多种“外部锚”来源,联用复合式外部锚定效应避免或修正外部锚定负效应。许多成功的个案侦查实例都显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性经验,修正或避免锚定负效应最重要的思维方法是对个案犯罪行为进行多角度的独立思考,而对于外部锚定效应的修正,更有效的则是集思广益,寻求不同的意见、方法,以开拓个案侦查人员和侦查管理者的认知及行为选择空间,打破可能来自行政领导、同质化群体和专业权威认知框架的束缚。运用这类思维激荡方法需要关注四个技巧:一是邀请具有独立性、不同知识结构且非“唯命是从”的参与者。二是真正为这些参与者提供不受限制、不定调子的自由表达情境。三是所有的参与者真正具备进行个案分析、提出差异化待选决策方案所需要的跨专业知识及其整合应用能力。四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独立自主地发表有独到见识的分析意见或待选方案,形成复合式外部锚定效应联用格局。 其二,在复合式外部锚定效应联用情境中,运用反向思维或异化锚定效应(18)避免或修正外部锚定负效应。在个案侦查中,由于侦查人员对来自行政领导、同质化群体和专业权威认知框架的外部锚很容易形成同化的锚定效应,因此,个案侦查的组织者应当有计划地引导、鼓励、支持侦查决策的所有参与者对于外部锚采取批判性的“反向思维”策略,帮助其清楚地意识到外部锚提供的侦查预断与个案犯罪事实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或差异,从外部锚提供的侦查预断相反的方向认知和选择,通过相互间形成的异化的锚定效应减弱、矫正外部锚定负效应。一般而言,如果真正运用了批判性思维工具,个案侦查人员通常都能得到多个待选侦查方案。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从这些待选方案中选定执行方案。 其三,通过对异化的锚定效应产生的若干个待选方案的理性比选和个案侦查基本要素的科学平衡避免或修正外部锚定负效应。尽管不同的人对于决策方案的好坏优劣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并可能因此而得出不同的评判答案,但通过理性的比较,侦查人员总能够得到一个可认同、可接受且能够令人满意的侦查执行方案。此处,提出“一必须、四不能、二确定”的关键指标作为侦查人员比选不同待选方案的最基本的标准:“一必须”,就是必须运用经验的、逻辑的、科学(技术)的和法律的标准,找出待证个案犯罪行为发生、发展的脉络,并以此脉络和可信、可靠的证据为依据选择侦查执行方案。换言之,符合个案犯罪行为发生、发展脉络且具有可信、可靠证据支持和可获得侦查资源支持的待选方案,就是可认同、可接受且能够令人满意的侦查执行方案。“四不能”,就是不能采用降低刑事诉讼证据标准、损害执法公正的做法以迎合某种政治设计,例如严打中出现的由于政治指标异化为执法指标导致的侦查外部锚定负效应;不能采用降低刑事诉讼证据标准、损害执法公正的做法以迎合某种社会口味,例如引起社会舆论炒作的个案侦查中出现的由于社会指标异化为执法指标导致的侦查外部锚定负效应;不能采用降低刑事诉讼证据标准、损害执法公正的做法以迎合特定个体的不当需求,例如面对精于、敢于无端闹事的当事人或具有某种特权的人的不当需要(诸如薄谷开来杀人案等)而将个体特质指标异化为执法指标导致的侦查外部锚定负效应;不能采用降低刑事诉讼证据标准、损害执法公正的做法以迎合行政或群体或专家权威维护的需要,例如薄熙来、王立军当权时期的重庆打黑案中将“权力”指标异化为执法指标导致的侦查外部锚定负效应。换言之,能满足刑事诉讼证据标准和执法公正目标达成需要且具有可获得侦查资源支持的待选方案,就是可认同、可接受且能够令人满意的侦查执行方案。“二确定”,就是围绕“确定相信什么”进行合理而成熟的思考,既充分考虑到侦查学理论所描述的类案侦查规律和行为法则,也合理权衡个案特殊情况及其所有证据,仔细考察这些证据以及支持和反对实证前侦查预断的所有论证,全面地评价所有证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正确推理作出侦查抉择;围绕“确定做什么”对所有证据及其相关性进行批判性评估,并始终立足于案件的实际情况、具体的问题情景,运用批判性思维工具,从这些证据中找到可确认的证据和侦查要素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理、实用的行动策略和路径,形成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行动不确定性并可以切实解决具体行动问题的侦查执行方案。换言之,具有深思熟虑性和合刑事诉讼目的性、意志性以及合个案侦查目的性、侦查主体意志性,且具有可获得侦查资源支持的待选方案,就是可认同、可接受且能够令人满意的侦查执行方案。 (四)借助科学决策辅助工具进行技术性修正 随着计算机技术功能的不断拓展,一些研究者开始借助计算机开发各种决策支持系统,并在帮助决策者更完备地调用各种信息资源和分析工具,科学分析专门领域的决策问题,合理构建模拟决策过程和方案的虚拟环境,利用数据、模型和知识建立模型,采用人机交互方式进行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和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遗憾的是,关于决策偏差的DSS系统的开发成果仍不多见。在该领域,George,Duffy和Ahuja针对锚定调整启发式开发了关于锚定效应的DDS决策支持系统,期望能够帮助人们在作决策时避免锚定效应的产生[30]。也有研究者利用此类决策辅助平台,通过DSS实验发现传统锚定效应对单独的警告有一定抵抗力,但采用让认知者思考锚定值与目标值之间的差异、反思锚定值的不合理性等方法却可以减少传统锚定效应的强度。 同时,侦查决策辅助系统的开发也顺势而动,并已研发出几类典型的刑事侦查决策系统:一是传统刑事侦查专家系统[31],其决策支持功能集中于储存、收集专家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做出应答等方面。例如针对持枪抢劫嫌疑犯特征分析而开发的AREST[32]专家系统;为满足调查、处理非法入侵案件,收集、记录案件资料以及提供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类似案件等有用信息而开发的Investigate B & E[33]专家系统等。二是在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领域开发了COPLINK(19)系列工具和RECAP(20)地方性犯罪分析程序等。三是为满足侦查活动综合需要而开发的犯罪侦查CBR(基于事理推理)系统,它利用预先定义的信息集进行犯罪类型分类、可并案侦查之盗窃案件检索[34]、电子商务异常交易[35]和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危险发现等决策分析。四是英国爱丁堡约瑟夫·贝尔刑事统计和法律推理中心的科学家近年来设计的侦探软件,它擅长于全面考虑所有的证据,推测不同情形的可能性,帮助调查一些不甚明朗的线索和解决比较复杂案件的侦查问题[36]。 但总体而论,现有的刑事侦查决策系统多为自行开发,而且适用类案比较单一,开放性、通用性尚有较大改进空间,不同系统之间尚需建立起关联性[37]。这就需要在未来的DSS系统研发中加入足够的批判性认知因素:Fischhoff(1982)为此提出了减少判断偏差的四个主要步骤:警告,描述,反馈和训练[38]。据此,未来可以从警告发生锚定偏差的可能性,描述出偏差的方向,提供相应的判断反馈、利用反馈以及使用一切可以改善决策、减少锚定效应偏差的方法进行拓展项目的训练等四个方面去开发有助于避免或减少锚定效应偏差的DSS系统,帮助侦查人员减少侦查锚定效应偏差,提高侦查水平和质量。 ①是指侦查人员对不确定性个案犯罪行为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时,受其已有的侦查经验和相关知识的影响所形成的心理准备、预期偏好或认知倾向。 ②该项实验由王均平指导的翟远烨硕士研究生法科学实验项目小组实施: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32名2010级侦查学专业本科生为被试,有效结果32人,其中有5人辨认出道具牌,占15.6%;以45名2010级治安学专业本科生为被试,有效结果45人,其中12人辨认出道具牌,占26.7%;以68名2010级法学硕士生为被试,有效结果68人,其中有7人辨认出道具牌,占10.3%。 ③是指侦查人员根据自己和他人以往的侦查经验或历史资料(包括侦查实案、教科书和研究成果等)分析得到的待证个案犯罪事实之发生概率。其中利用历史资料分析得到的先验概率,称为客观先验概率;依据侦查人员的主观经验得到的先验概率,称为主观先验概率。 ④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对自己的实证前侦查预断进行后续的适配性调整的“可容忍”范围,但这种调整一般不会超出“性质”的预设边界。 ⑤主要是指侦查人员对自己持有的侦查之锚调整的“可执行”或“可接受”范围。 ⑥一般表现是侦查人员借助侦查之锚构建初始的犯罪行为认知模型框架,作出实证前侦查预断,并将之作为后续侦查活动的“指南”。到了起诉阶段,公诉人员直接将侦查机关移送的犯罪行为证据链及论证链置换为审查起诉的依据和起点,根据它作出审查前公诉预断,并将之作为后续审查起诉活动的“指南”。到了审判阶段,审判人员直接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提出的犯罪行为证据链及论证链置换为审理裁判的依据和起点,根据它作出庭审前预断,并将之作为后续审判活动的“指南”。 ⑦侦查推理不是学者的学理思考或者理论推导,其常态形式并非单一的、标准的、纯粹的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更符合侦查实际的往往是似真推理。 ⑧一个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体现是经过执法者选择性注意挖掘的信息输入其具有一定思维定势干预的大脑信息加工系统之中,并按照执法的要求进行编码、储存、提取、展示、解读和应用。 ⑨领导—成员交换理论(Leader-member exchange,简称LMX理论),阐述下属与其领导者之间在工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参见Graen G B,Uhl-Blen M.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LMX)Theory of Leadership Over 25 Years:Applying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Perspective[J].Leadership Quarterly,1995,6(2):219-247. ⑩包括对侦查环境压力的性质和强度的不明确,对各种不同侦查假设选择的意思及含义的不明确等。解决该问题通常依赖行政权威所作的初始的特异性处理和引导,特别是兼具行政和专业权威者——通常是分管侦查的领导——所作的初始的特异性意见往往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参见[美]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M].方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2. (11)当参与个案证据调查的专家从聘请他们作证的一方那里得到一定的报酬时,便可能使之对“事实”形成包含自己价值判断的评估。 (12)法官预断排除规则来源于日本,强调起诉书仅仅是检察官的一种“主张”,与说服法官确信的案卷材料是两回事。并以此为核心,通过法官回避制度、证据调查方式、案件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来防止法官滋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预断心理,保证法官在初次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时拥有“空灵如白纸”的心境,这些程序的总和在日本被称为“法官预断排除法则”。参见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61. (13)此处所谓“超然性”并非是指审查起诉超然于侦查所追求的揭露、追诉犯罪行为的价值之外,而是指以中立的审视者角色,对侦查部门所呈交的证据、构建的证据链和论证链及其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个案犯罪行为认知模型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逻辑标准、科学标准和法律标准审查,并独立地形成自己的审查结论和起诉决定,而不是直接移用上述侦查结果。 (14)如果由锚启动的信息是易得的,那么锚对决策的影响是相当稳定和持久的。而且,当外部锚信息不足以修正侦查人员内在锚时,它们只能对锚定效应产生微弱的影响而不足以削弱锚定效应。参见Mussweiler,T.Sentencing under uncertainty:Anchoring effects in the court room[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1(31):1535-1551.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司法认知实验研究显示,陪审团向法官陈述证据的顺序(从严重的到轻微的)——这也是现在正在使用的一种标准程序——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判决。参见Greenberg J.,Williams K.D.& O'Brien M.K.Considering the harshest verdict first:Biasing effects on mock juror.verdicts[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86(12):41-50.;[美]斯科特·普劳斯.决策与判断[M].施俊琦,王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129. (15)此处所说的内在锚、外部锚信息的影响力,主要是指相关信息能够引起侦查人员作出偏好性预期反应的力量。而信息的权重则与其内容的性质、效用和可靠性有关。如果侦查人员重信息之影响力而轻其权重就可能导致过度自信;反之,如果侦查人员重信息之权重而轻其影响力就可能导致缺乏自信。在决策领域中,缺乏自信和过度自信都会导致决策失误。参见杨晓华.梦对决策的锚定效应影响研究[D].宁波大学2008级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1(1):10. (16)外部锚来源于个体外部世界,具有不确定性,而诱发自发锚定效应的内在锚则来源于个体自身内部世界,其确定性程度更高,信念程度也更强。而且,由于过度自信偏差的作用,可能使侦查人员更相信内在锚。参见Moore D.A.& Healy P.J.The trouble with overconfidence[J].Psychological Review,2008,115:502-517. (17)证实偏差,是指侦查人员选择支持自己期望的假设、理论、观念或方案而忽视否定例证的普遍倾向。参见[美]D.Alan Bensley.心理学批判性思维[M].李小平,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10.;王均平.侦查认知及行为选择证实偏差的诊断与修正[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1):63-76. (18)异化的锚定效应指的是人们对一种呈现在相反背景下的目标刺激物进行思考之后做出的决策,可用“相反的决策”解释。参见Mussweiler T.& Strack F.Hypothesis-consistent testing and semantic Priming in the anchoring Paradigm:A 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99(35):136-164. (19)COPLINK可以对罪犯线索数据库和报告进行分析,使得侦查人员能够利用有限的信息,找出他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调查线索。参见Chen H.,Schroeder J,Hauck R.V,Ridgeway L.,Atabakhsh H.,Gupta H.,Boarman C.,Rasmussen K.,Clements A.W.COPLINK Connect: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law enforcement.Decision Support System:Special Issue on Digital Government,2002,31(3):271-285.; Hauck R.V.,Atabakhsh H.,Ongvasith R,Gupta H.,Chen H.Using coplink to analyze criminal justice data.IEEE Computer,2002,35(3):30-37. (20)RECAP可用于搜寻有着类似作案手法的案件,以发现有组织的犯罪。参见Brown D.E.The regional crime analysis program(RECAP):A framework for mining data to catch criminals.In Proceedings for the 199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MAN and Cyberntics,1998:2848-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