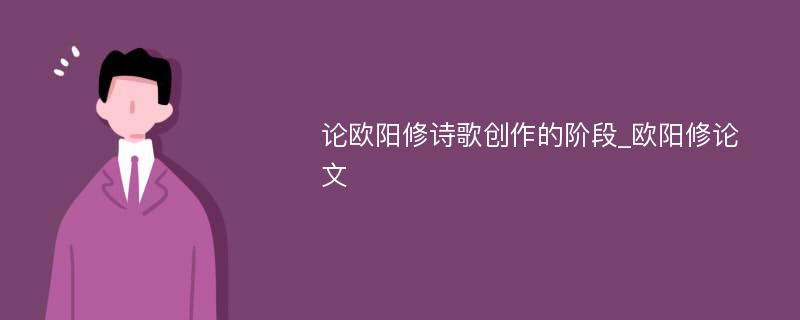
欧阳修诗歌创作阶段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修论文,阶段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在宋诗发展史上起过开创作用,是宋诗中一大家。我们研究欧阳修现存的八百多首诗,如果将他的诗歌创作按阶段论述,或许更能够作出比较清晰的说明,而且也可以从中窥见宋诗发展的轨迹。欧阳修的一生与政治活动不可分离,他的诗歌创作阶段的划分也与其政治活动时期大致相应。欧阳修一生的活动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一、自少年应举至景祐三年(1036)贬官夷陵前,这是翩翩才子时期。二、自景祐三年(1036)至庆历五年(1045)贬官滁州前,这是勇于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期。三、自庆历五年(1045)至至和元年(1054)入朝,这是被贬外任而进取心理与退避心理并存的时期。四、自至和元年(1054)至治平元年(1067)外任前,这是地位显要而未能尽展抱负的时期。五、自治平元年(1067)至熙宁五年(1072)去世,这是从外任到退隐而归心天然的时期。
从注重记叙性出发
欧阳修自天圣元年(1023)十七岁起三次应举,天圣八年(1030)中第,次年春赴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任满,入京任馆阁校勘。洛阳三年,对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创作起着决定方向的作用。当时,西昆派诗人钱惟演为西京留守,身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尹洙、梅尧臣。钱惟演优礼文士,宴饮唱酬,鼓励下属自由创作,不以个人好恶施加影响,营造出非常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欧阳修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仍俯仰留连:“文僖公善待士,未尝责以吏职,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树,奇花怪石,其平台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间,余得日从贤人长者,赋诗饮酒以为乐。”(《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文士间的唱酬,常带有互相激励竞争的性质,引起切磋,促进创新。欧阳修有诗曰:“予生本是少年气,磋磨牙角争雄豪。”(《绿竹堂独饮》)这正道出了以文会友时的竞争心理。
西昆体在宋初诗坛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此时其弊病已日益明显,诗坛已酝酿新的风气,而身在洛阳的梅尧臣、欧阳修适逢其会,探索创新。欧阳修早年诗作在西昆体笼罩之下,其《居士外集》收天圣、明道间未第时及洛阳所作近体诗,风格明显接近西昆体。但是,综观欧阳修洛阳诗作,已大部分属于探索创新的产物。探索源于借鉴,从欧阳修此时诗作中可见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的痕迹,其中尤其重视者为韦应物、韩愈,其主要倾向在注重诗歌的记叙性。
在洛阳,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时说:“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书梅圣俞稿后》)他晚年所作《六一诗话》称韩愈“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从“本人情,状风物”到“叙人情,状物态”,可见他评诗的一贯性,即重视诗歌的记叙作用,并可由此察觉他学韩诗的本意所在。以中国诗史的深厚抒情传统作为对照,这实际已是对此传统的部分疏离,要求诗歌起到散文以记叙方法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扩大诗歌的容量,从广义来说属于“以文为诗”的范畴。对此,不论欧阳修本人是否已有自觉的认识,这是欧阳修他们的探索创新最重要的意义。当然,这时的根本出发点还是走出西昆体。
这一时期的记游写景之作,集中地反映了欧阳修的探索。欧阳修作有《游龙门分题十五首》、《嵩山十二首》,都是短篇五古,读来颇有韦应物清淡之风,又绝大多数是三韵诗,更近韦应物三韵五古之幽远,而叙行程常历历分明,写景物贴切悠然,又具韦诗之记实性。元人刘壎认为欧阳修诗“有甚似韦苏州者”,曾举《游龙门上方》、《伊川独游》等五古为证。(见《隐居通议》卷七)欧阳修的一些五律也有次序分明、写景细致的特点,如《秋郊晓行》、《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从这些记游写景诗里,可以感到对清淡风格的追求,对西昆体艳丽雕琢性的规避。在写景细致的同时,避免重蹈晚唐体之琐碎,这应为欧阳修所虑及,故诗篇整体格局阔大,疏密得宜。在共同探索的初期,年稍长的梅尧臣对欧阳修有较大影响,因此两人的创作有很强的一致性。宋人朱弁说:“圣俞少时,专学韦苏州诗,世人咀嚼不入,唯欧公独爱玩之。”(《风月堂诗话》卷上)考察欧、梅此期诗作,可知此语确为有得之见。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对韩愈的学习模仿。欧阳修由学韩文而及于学韩诗。在记游写景诗中,有几首长篇五古应是学韩以散文结构法作诗的产物,如《代书寄尹十一兄杨十六王三》、《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前一篇的结尾是“因书写行役,聊以为君导”,明确地规定了这首诗的记叙功能。这些诗采用顺叙方法,条理清晰,平稳流畅,显然借鉴了散文的作法,可以看出对“以文为诗”的初步尝试。由于欧阳修这时的散文创作尚未成熟,他在诗中使用的记叙方法也稍嫌平衍,缺少曲折变化。对韩诗心摹手追的作品当数七古《巩县初见黄河》。全诗长达七十句,纯为单行,无一对偶句。清人施补华说:“少陵七古多用对偶,退之七古多用单行。退之笔力雄劲,单行亦不嫌弱。”(《岘佣说诗》)此诗用单行、重气势,正是学韩愈七古。诗可分三个层次,首赋所见,次叙历代治河及水患情况,最后颂扬当代治河的成功,层次分明,无冗长庞杂之弊。诗中多用散文句式,如“巩洛之山夹而峙”、“众臣荐鲧帝曰试”、“制之以力不以德”、“其势不得不然尔”等。诗中取古史传说铺叙,辅以一些奇特的想象,增强了全篇的气势。凡此都能看出学韩的痕迹,但铺张扬厉不及韩,章法嫌平直,笔力也不及韩雄强。
注重诗的记叙性,这在梅尧臣诗中也触处可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事本源于谢绛等人因进香而游嵩山,叹梅尧臣未能同游,谢绛于是备记始末,致书梅尧臣。梅就来书中叙述加以剪裁,构成记事长篇。谢绛读诗后,复书云:“忽得五百言诗,自始及末,诵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见《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在此时洛阳文士中,谢绛实为主盟人物,与欧、梅等人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从他对梅尧臣此诗的称赞来看,注重诗的记叙性,力求穷形尽相,文字雅正,这已是他们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应被看作宋人“以文为诗”的发轫。
理性思考的发展,以古文章法为诗的成熟
景祐三年(1036),主张革新而抨击守旧势力的范仲淹遭贬,欧阳修写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而远贬夷陵县令,外任数年,重返京城复充馆阁校勘,又一度自请出外为滑州通判。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任谏官,积极参与这一政治改革。随着新政的失败,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知滁州。这是他勇于实现政治理想而最富进取性的时期。夷陵之贬在欧阳修的人生道路上具有特殊意义,它使欧阳修的京洛文士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使文学创作随之产生重大变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随园诗话》卷一录庄有恭诗)夷陵之后的发展变化,皆源于夷陵生活的赐予。
自贬夷陵起,欧阳修诗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渗进理性思考,这尤其体现在他对贬谪的看法中。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注重诗歌记叙作用而疏离抒情作用的逻辑进程,最终走向“宋诗主理”,而由于生活的剧变使进程加速。当然,抒情与理性思考之间并不存在彻底对立的关系,说“宋诗主理”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判断宋诗排除抒情,只不过宋诗的抒情也融入了理性。这次打击对于欧阳修来说不免太突然,他不能不对身边所发生的事加以审视辨析,确定自己的态度。贬夷陵途中,他曾作书与尹洙曰:“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与尹师鲁第一书》)以这种态度形诸诗歌,就有了一些心境坦然的诗句,如“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黄溪夜泊》),“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戏答元珍》)。在写给友人的以描写夷陵风俗为主的诗中,他仍坚持记叙性的原则,出以白描手法,很少带感情色彩,从中可以察觉经过理性思考的平静心情。在七律《初至虎牙滩见江山类龙门》中,他将夷陵与洛阳的景物加以对比,冷静得令人吃惊,几乎看不出人生道路上刚刚受到挫折。这些诗是理性思考融入记叙之中。而在《金鸡五言十四韵》中则直接发表议论,无疑是对韩愈“以议论为诗”的仿效。此诗前半以叙述为主,后半自“岂知文章著”以下七韵全为议论,但不够精警,结尾之“用晦有前言,书之可为诫”颇觉烦冗。如何“以议论为诗”,这还有待于欧阳修的进一步实践。
欧阳修继续进行诗歌篇章结构的探索,在借鉴散文作法的道路上前进,于七古尤为显著。七古中,又有学韩愈者与学初唐歌行者的区别。以风格言,则有重气格与重情韵的不同。
《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这首七古是学韩愈之作。方东树评曰:“起段从源头说起,夹叙夹议,学韩而老,但少其兀傲。‘高台’二句逆入。‘舟行’四句学韩之奇。凡此皆从《赤藤杖》来。”(《昭昧詹言》卷十二)此为会心之语。“从源头说起”,指起首历叙古瓦所出之地铜雀台建成前的历史及铜雀台的始末。诗自“高台已倾渐平地,此瓦一坠埋蓬蒿”,始叙古瓦,这是“逆入”。“舟行屡备水神夺,往往冥晦遭风涛,质顽物久有精怪,常恐变化成灵妖”,这四句“学韩之奇”。再看结尾“长歌送我怪且伟,欲报惭愧无琼瑶”二句,也是学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结尾“妍词丽句不可继,见寄聊且慰分司”二句。这首诗讲究章法,远胜于前一时期的《巩县初见黄河》,只是前段叙述稍繁。至于方东树说欧诗不如韩诗兀傲,则因才性不同之故。
《晚泊岳阳》、《三游洞》、《黄牛峡祠》、《千叶红梨花》、《代赠田文初》、《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等一批七言歌行是学初唐歌行之作。这些诗一般四句一换韵,意随韵转,曲折澹荡,清丽空灵,情韵俱佳。方东树评欧阳修七古曰:“欧公情韵幽折,往反咏唱,令人低徊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馀味,但才力稍弱耳。”(《昭昧詹言》卷十二)欧阳修七古并不尽如方氏所言,若用来专指这些歌行则极为恰当。初唐歌行的特点何在呢?胡应麟评曰:“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诗薮》内编卷三)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这些歌行与初唐歌行相近之处甚多,而欧阳修以古文章法入诗,更讲究开合转折,这是不同之处。
在律诗中,欧阳修也借鉴了古文的章法。律诗形式的本身固然已包含了开合承转等因素,但欧阳修仍进一步追求起伏动宕的表现方式。如一向流传人口的七律《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首联构思奇妙,上句突兀而起,下句接得峭折。欧阳修自己对这两句也很得意:“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笔说·峡州诗说》)以下写早春景物、自身境况,转折拓开,而尾联振起全篇,又与首联呼应,形成结构上的回旋往复。
僻居夷陵,为此后诗歌内容的拓展、表现方式的日趋成熟、个人风格的自觉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离开夷陵后,面对卑弱国势、深重时弊,欧阳修诗中的理性思考很自然地扩大到了社会政治范围。在《赠杜默》诗中,他说:“京东聚群盗,河北点新兵。饥荒与愁苦,道路日以盈。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这表现出对诗歌劝戒作用的重视,因此而产生对社会政治作大段议论的倾向。《答朱寀捕蝗诗》针对严重蝗灾,提出改驱民捕蝗扰民为出钱奖励捕蝗,而结尾“因吟君赠文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二句明确表达出作诗的政治目的。《送任处士归太原》对与西夏作战的不利局面感到焦急,呼吁不次用贤。《答杨辟喜雨长句》指陈时弊,强调以农为本,其内容与康定元年(1040)所作政论文《原弊》几乎一一相应(注:《答杨辟喜雨长句》,《居士外集》列于天圣九年至明道二年间,不确,当作于庆历元年后。参见笔者《欧阳修年谱》庆历三年事。),是典型的“以议论为诗”。他反对佛教,作《本论》,于是在《读张李二生文》一诗中有反佛的议论:“千年佛老贼中国,祸福依凭群党恶。拔根掘窟期必尽,有勇无前力何荦。”他认为后儒惑乱《春秋》经,于是在《送黎生下第归蜀》一诗中有对“妄儒”的抨击:“妄儒泥于鲁,甚者云黜周。大旨既已矣,安能讨源流。遂令学者迷,异说相交钩。”宋人以议论为诗,关注社会政治,不自欧阳修始,如苏舜钦在明道元年就有指陈时弊的《感兴三首》,景祐元年有感慨与西夏战事失败的《庆州败》。但议论量大且广泛,成为一种特点,或许应以欧阳修这一时期的创作作为开端。
庆历初,欧阳修文名日盛,其散文进入成熟阶段,而以古文章法为诗的表现方式也已成熟。同样是记叙性的代书诗,《忆山示圣俞》的结构就不同于洛阳时所作之平衍,诗以“吾思夷陵山”陡然而起,接写入山初程所见总貌,“忆尝祗吏役”以下逆折重起,写山中一次游观,接着过渡到三峡奇秀景观,末以京城难得幽赏,道出忆山之起因。全篇布局曲折,颇有深度。如果以题材类似的诗与文作一番比较,或许更能看清他以古文章法为诗的手段,这里试比较文《释秘演诗集序》与诗《哭曼卿》。《释秘演诗集序》从石曼卿引出秘演,说二人皆奇男子,又插写自己与二人游,亲见二人盛衰。以下转说二人之诗,复以曼卿诗引出秘演诗。最后点出曼卿死,秘演将行,“于其将行,为叙其诗,因道其盛时,以悲其衰。”全文从二人盛衰着笔,两番转折。诗《哭曼卿》从石曼卿壮时“天下奇”起,描写其饮酒、作诗之豪,诗成自写,而“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馀”,好题屋壁,“遗踪处处在”,寄寓对曼卿身死的感叹。自“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转写与曼卿二人离合,直至“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叹其溘然长逝。自“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以下,又转到叹其才高不为世用而卒。全诗突出写石曼卿之才,反复叹其死,与《释秘演诗集序》反复“道其盛时,以悲其衰”的写法同一机杼。
在这一时期的末期,欧阳修有几首诗比较集中地论诗。《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分别以气雄豪、清新古硬评苏舜钦、梅尧臣二人之诗,描绘确切,感觉敏锐。而从“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几句诗里,固然能看出好诗无人欣赏的感叹,但似乎也能察觉从诗人自身探讨原因的沉思,即是否有不阿世取容而又易为人知的可能。《读蟠桃诗寄子美》诗中,以孟穷韩富论韩愈、孟郊诗:“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穷者啄其精,富者烂文章。发生一为宫,揪敛一为商。”继而以梅尧臣比孟郊,暗含自己诗风仿效韩愈之意。就欧阳修此时诗作来看,他注意的是韩愈之“浩穰穰”,故而发越铺张,畅所欲言,并不是随韩愈亦步亦趋,所以回避韩愈诗力求奇怪之风。在《绛守居园池》诗中,他不满樊宗师的奇险文风:“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盘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可见他要求语言的平易可解。总之,欧阳修通过对当代诗坛的思考,认识到豪放、奇险、生涩等不同风格所存在的不足,它们对读者可能造成的惊惧感、生疏感等心理距离,感到平易疏畅的必要性,开始了自觉的追求。
理性思考的博大,平易疏畅诗风的确立
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知滁州,历知扬州、颍州、应天府,守母丧居颍州,直到至和元年(1054)入京任职。贬滁州在政治上给予欧阳修以巨大的打击,“盗甥”罪名更是莫名的人格污辱,这都促使他深入思考社会人生。在外十年,是他进取心与退避心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达到成熟阶段。
欧阳修复杂的心理活动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是理性思考常起到平衡作用。《菱溪大石》、《紫石屏歌》都有学韩愈《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奇想的痕迹,然又与韩愈有所不同。朱自清先生评欧阳修此二诗曰:“皆能用所谓持久的想象者。永叔似恐创意太新,足以惊世骇俗,故两诗末幅均以常理自衡其说。”(《宋五家诗钞》)《菱溪大石》叙述中入奇想,却以传说的形式表达,并以“争奇斗异各取胜,遂至荒诞无根原”扫清,将自己置于冷静的评判者的地位。《紫石屏歌》设想月影入石,其后曰:“大哉天地间,万怪难悉谈。嗟予不度量,每事思穷探。”则同样表现出与想象拉开距离而探索事理的理性思考。
欧阳修的理性思考也常表现在对日常生活的歌咏中。如《喜雨》写田家喜雨之情景,以描写为主,开端却是一番议论:“大雨虽滂霈,隔辙分晴阴。小雨散浸淫,为润广且深。浸淫苟不止,利泽何穷已。无言雨大小,小雨农尤喜。”这种对大雨小雨加以区别比较的看法,流露出一片仁爱之心,用之可以推广到社会政治中去。更有《飞盖桥玩月》一诗耐人寻味:
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馀晖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翛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诗人于天水清粹虚静间,见皎皎月色,万物光洁可爱,感觉天地生生不息之大德,于是尘杂尽去,表里澄彻,襟怀坦荡,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情操进入崇高的境界。闲适中静悟有得,含蕴人生哲理,而绝无迂腐气,颇有杜甫《江亭》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那般意趣。诗作敷腴温润,代表了欧阳修诗风的一个方面。
这一时期,欧阳修的诗风得以确立,与他多方面的尝试有关。在他的诗中,有几篇诗题标明效李白体、效孟郊体、效贾岛体、效李贺体,而《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则是效李白又效韩愈之作。其气势飞动,句式参差,是仿效李白,而用险韵则是学韩愈。《六一诗话》称赞韩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之后说:“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韩愈《病中赠张十八》用的是窄韵江韵,《庐山高》也是用江韵,因难见巧,追步韩愈。欧阳修颍州聚星堂诗会所作《雪》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苏轼《聚星堂雪》题下语),是“白战体”的创始代表作品,从中可见变更表现方法的创新意识,在诗艺上的孜孜探求。“禁体物语这种手段,用意在于使咏物诗在表现中遗貌取神,以虚代实;虽多方刻画,而避免涉及物的外形。它只就物体的意态、气象、氛围、环境等方面着意铺叙、烘托,以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从而在他们心目中涌现所咏之物多采多姿的形象。”(注:见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载《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也表明,欧阳修仍然关注诗的记叙功能的丰富,为发展积累经验。
平易疏畅,是欧阳修诗风的基本方面,这在滁州时已得到确立,尤其体现于记游写景诗中。《游琅琊山》、《题滁州醉翁亭》、《幽谷泉》等五古皆明白如话,贯通流畅。七绝由于诗体本身的缘故,就更加自然通达,如《丰乐亭游春三首》其三;“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至于七古,在讲究章法的同时,出之以流畅的语言,如《沧浪亭》开端数句:“子美寄我沧浪吟,邀我共作沧浪篇。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读来一气而下。《啼鸟》由叙述、描写转入议论,不乏情韵,其中描写鸟啼一段尤能见出与前此诗作的不同。与夷陵时七古比较,此时已不似仿初唐歌行之作那般清丽有风藻,流丽已转化为流畅。这标志着欧阳修借鉴前人而不事蹈袭,故能自成面目。
以文为诗的随心所欲,记叙范围扩展的文化内蕴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服母丧期满入朝,不久,留修《唐书》,为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名益高,位益崇,不改刚正敢言之态,但由于主政者因循随时,在政治上未能有大的建树。值得欣慰的是,欧阳修的文坛活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坚决打击文风怪诞的“太学体”,使古文运动获得全面胜利。他的诗歌创作也沿着已开拓的道路发展,在频繁的寄赠唱酬之中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影响诗界。
欧阳修“以文为诗”,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这时通篇议论的诗不多,而似乎注意在诗中关键处突发议论,树立新意,振起全诗。如《再和明妃曲》在叙王昭君远嫁事后,以“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夹叙夹议,继以“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翻出新意,精警透辟。如七律《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中“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二句,备受称赞,清赵翼曰:“此何等议论,乃熔铸于十四字中,自然英光四射。”(《瓯北诗话》卷十一)他以古文章法为诗,更觉纯熟多变,这间接反映在用韵形式上,是转韵七古的数量超过不转韵七古,转韵时不拘于四句一转的常规,句数常多寡不一,盖以转韵之层层变换配合结构之错综变化。他以散文句式入诗,也比以前大量、集中,如《鬼车》、《赠李士宁》等,《赠李士宁》后半尤为淋漓尽致:
与之游者,但爱其人,而莫见其术,安知其心。吾闻有道之士,游心太虚,逍遥出入,常与道俱,故能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尝闻其语,而未见其人也,岂斯人之徒欤?不然,言不纯师,行不纯德,而滑稽玩世,其东方朔之流乎?
这与韩愈比较,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韩愈以散文化的语言风格,追求“非诗之诗”,反对中国诗歌形式中已形成的过分对称、均衡、和谐、圆润,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作出了贡献。但如果稍有过头,就只剩下了“非诗”,韩愈就有不成功的尝试(注:关于韩愈诗散文化的评价,此处取舒芜《〈韩愈诗选〉序》意。序载陈迩冬《韩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欧阳修《送李士宁》诗,也是过分散文化的例子。
欧阳修仍注意对诗歌记叙功能的开掘,这表现在记叙范围的扩展。这时期他以咏物为主的诗增多,所咏对象有些属于新奇而琐细的物品,如《梅圣俞寄银杏》、《初食车螯》、《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尝新茶呈圣俞》、《奉答圣俞达头鱼之作》、《初食鸡头有感》、《双井茶》等诗。这一类诗并不拘泥于刻画形貌,而常常叙述其物来历,“惟当记其始,后世知来由”(《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通过详尽叙述,得出通达的感受。如《初食车螯》先叙五代时九州分隔,南方特产不至,北方食品简陋,“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而“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南方水产连舳盈车而来,于是“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在这客观性的叙述中,可感到对天下统一的内心喜悦。《双井茶》诗描绘双井茶的珍贵,富贵人家的趋时争啜,结以“岂知君子有常德,至宝不随时变易,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尤能体会出以记叙蕴情理的作法。
欧阳修对记叙范围的扩展,更值得注意的是含蕴文化精神的题材。这一时期他观画、听乐、读书、咏纸笔各类诗作比较多,浸染着文人雅致,常表露出一个文坛领袖对文化演进的关注。《盘车图》在描绘画中景象后,又言及梅尧臣题画诗,曰:“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乐能自足乃为富,岂必金玉名高赀。朝看画,暮看诗,杨生得此可不饥。”其中“忘形得意”的审美观,后来有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为同声,而这正符合后世文人画的标准。诗中称赞杨褒忍饥买画,也流露出自己对文化“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执着。顺便要说一下的是,梅尧臣的题画诗名曰《观杨之美盘车图》,诗有其善写情状的一贯特点,但不免就画谈画,缺少欧阳修此诗所表现的阔大眼界,当然这与两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和刘原父澄心纸》有这样的诗句:“百年干戈流战血,一国歌舞今荒台。当时百物尽精好,往往遗弃沦蒿莱。君从何处得此纸,纯坚莹腻卷百枚。官曹职事喜闲暇,台阁唱和相追陪。文章自古世不乏,间出安知无后来。”从中可见对文化遭到毁灭的痛心,对努力发展文化的信心。这类诗中的文化精神其影响之深远不可估价,无疑是此后宋诗发展所继承的无形财富。举例来说,欧阳修《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兴》开端曰:“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坂。”黄庭坚《送王郎》曰:“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云云,宋人已指出二者间句法上的因袭关系(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殊不知以笔墨相赠的类似内容入诗也代表着文人意趣的相承,归根结底反映了宋诗之文化精神的持续演进,而这也正是宋诗的一大特色,所谓“以才学为诗”应当只是其外在表现而已。
归于抒写自然情趣
治平四年(1067)之前,欧阳修已多次上表请外任,此时因“濮议”之争而受诬告,求退之心愈坚,终得出京外任,又连乞致仕,至熙宁四年(1071)如愿退居颍州。一年后即去世。与政治上的退避相关,这一时期的诗作多反映归心天然的追求和情趣。
欧阳修诗作的明显变化是社会政治意识的淡化,这主要表现为不再“以议论为诗”,而从诗的体裁来看也有助于说明其倾向。这一时期有诗八十多首,其中近体诗六十多首,古体诗不足二十首。近体诗占如此大的比例,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的。根据一般看法,自杜甫起,诗人反映国事民生常用容量大、伸缩自如的古体诗,抒发个人情趣常用简短的近体诗。欧阳修此前的诗作亦复如此,而此时大量写近体诗正是用来抒发个人情趣。
欧阳修平易疏畅的诗风,在抒写自然情趣时得到相宜的内容,写来更觉坦易,颇似白居易晚年。赵翼评白居易诗曰;“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瓯北诗话》卷四)若以此语评说欧阳修晚年诗,亦无不可。如《再至汝阴三绝》其一:“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此诗写眼前景,道心中意,两联皆对,却无刻意组织之痕,应是对此际情景的自然摄取,于笔底流出。
分 期考察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出他对记叙作用的一贯关注。由此出发,诗歌便于反映社会人生,容量扩大,易于说理议论。于是,诗与文的表现方法有所接近,主抒情转向主说理,“以文为诗”与“以议论为诗”很自然地成为宋人的艺术手段。欧阳修对宋诗的开创作用正在于此。
标签:欧阳修论文; 梅尧臣论文; 韩愈论文; 以文为诗论文; 宋朝论文; 释秘演诗集序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散文论文; 洛阳论文; 理性思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