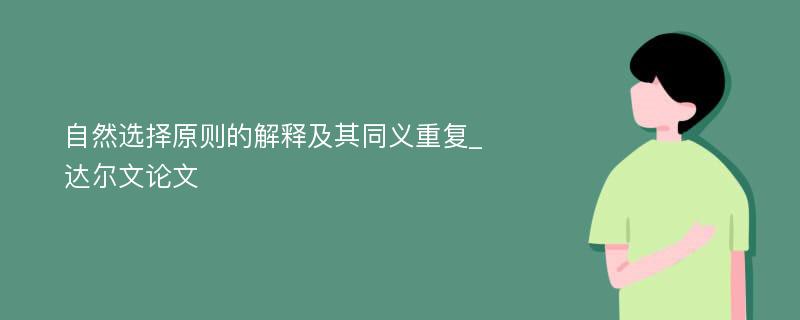
自然选择原理的解释作用及其同义反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选择论文,原理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6—0003—06
一
自达尔文以来,有关进化论的科学地位问题就一直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所争论。这是因为,达尔文给我们留下的理论体系是以自然选择原理为核心的,而自然选择的概念始终没有一个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定义。在1970年代,波普尔指出了自然选择的同义反复性,从而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并非一个合格的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成功的形而上学研究纲领。当对于进化论有了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达尔文主义者提出强烈抗议以后,波普尔着手收回对自然选择理论的意见。他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我一直把这种理论看作是‘近乎同义反复’的理论,……。然而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可检验性和逻辑地位问题,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我很高兴有一个让我认错的机会。”[1] 波普尔还承认,可以反驳自然选择解释的事实是可能存在的,如在缺少选择压力的情况下一个小的群体能够因“遗传漂变”而使得基因库中的基因分布发生改变,生物的许多性状不能够用它们的有用性来解释。
然而,波普尔的认错并没有改变自然选择理论难以检验的事实,有关自然选择的解释作用问题仍然是严重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就难以成为合格的科学理论,从而以往进化生物学的理论化成果受到怀疑;而达尔文以来的成功,特别是进化生物学的新进展,又不能支持对达尔文理论的贬损。因此,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在试图走出这种二难困境,为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地位进行辩护。这种辩护大致有三条进路。
第一条可能的进路是继续波普尔的先前做法,怀疑自然选择理论的科学性质。如果按照正统科学哲学给出的科学标准和目前达尔文主义者对自然选择原理的理解,这种怀疑并不为过。按照这条进路,自然选择学说将被理解成一种方法论原则或者研究纲领,而不是关于差别繁殖原因的真陈述;其作用在于启发发现,而不是解释,从而就不能按照评价经验陈述的标准来理解它,也没有必要顾忌所谓同义反复问题。波普尔的退却已经表明,这个策略难以服众,而且也不能对解决自然选择理论的同义反复问题给出建设性答案。不过,仍然存在一些反对进化学说的主张,而反对进化学说的人往往是要诋毁自然选择原理的。其通常的做法就是把进化学说说成是一种宗教或者形而上学。例如K.Ham说道:“当我们争论进化还是创化时,实际是在谈论不同的信念,也即宗教。这种对立不是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而是宗教与宗教、一种宗教的科学与另一种宗教的科学之间的对立。”[2]
第二条可能的进路是承认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有缺陷,然后根据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等领域的成果改进和完善有关概念的定义,明确自然选择理论的使用范围,从而消除自然选择原则的同义反复性和不可检验性。这条进路大致包括这样几种策略和努力:一是承认自然选择原理的同义反复性,但认为达尔文理论的其他部分是可检验的和有经验内容的;二是企图通过缩小达尔文模型的范围来消除自然选择原则的同义反复性和不可检验性;三是致力于对适应(adaptation)、适合度(fitness)进行重新定义,特别是要给出倾向定义,把“最适者生存”这一命题变成经验命题。
索博尔(E.Sober)主要采取第一种策略。他以这样的命题为例:“性状X比性状Y更适应,当且仅当X具有比Y更高的生存概率和/或更大的繁殖成功的期望”。他说:“进化论包含这种同义反复的事实并不表明整个理论是同义反复的。不要混淆部分与整体。”索博尔指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两个主要命题——所有物种都有共同的由来和自然选择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都是历史性假说,即关于特殊客体的判断,都不是同义反复的。[3]70—71 索博尔为进化论辩护的策略还包括这样的主张:进化论中存在一些数学真命题或概率命题,如哈代—温伯格定律,并非是空洞的,因而也不能被作为纯粹的同义反复。[3]72—73
关于第二种策略,高尔德(S.J.Gould)和列沃汀(R.C.Lewontin)在“圣马可的三角拱腹与潘哥洛斯范式:对适应主义纲领的一个批判”一文中的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说的适应主义纲领(adaptationist programme)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自然选择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它用于支配生物体的设计与建造的,将是可能方案中最佳的。按照这种纲领来研究适应现象,就是去讲述适应的故事。其论证风格是:“当一个适应性论证失败了,就去试另一个”、“如果一个适应性论证失败了,就假定还存在另一个较弱形式的论证”、“强调直接的功利性而排斥结构的其他性质”、把这种论证的失败归因于对生命过程缺乏完善的理解。[4] 这样,就产生了不可检验性问题。达尔文在解释物种变化时,实际上是遵循多元论的策略的,自然选择只是主要的解释,而非唯一的解释。按照这种多元论的思路,高尔德和列沃汀列举了非适应主义纲领的解释策略,如完全不承认适应和选择而只通过遗传漂变解释物种变化、将适应与选择相分离、基于相关性和整体的观念只承认部分性状是选择的结果、在多适应峰的情况下不存在选择的基础、把适应性状解释为结构的附属性状,等等。[4] 通过这样限制自然选择的范围,适应解释就有了可检验性。
第三种策略主要是改进费希尔适合度概念,力图找到适合度的超越繁殖成功的意义。目前,布兰登(R.N.Brandon)、米尔斯和彼蒂(S.K.Mills & J.H.Beatty)等人给出的“适合度的倾向解释(the propensity interpretation of fitness)”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只要对适合度倾向定义的认知意义给出恰当地阐释,也就能消除同义反复和不可检验的困难。布兰登和彼蒂等人倡导的适合度倾向解释,主要有以下内容:①适合度是生物个体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或概率倾向(probabilistic disposition),由生物的生理结构、遗传结构以及环境等物理基础决定,规定着生物实际行为的范围。用布兰登的话说就是“在本体论上,倾向性质必须与其背后的物理基础相一致”。[5]17 ②适合度是数学意义上的期望值,由生物留下子代的各种可能数目的概率权重之和来表示。可以把平均效应与倾向概率相类比,从而可以按平均效应来计算适合度的强度。布兰登说道:“在认识论上,倾向解释允许两种非常不同的估计概率的方法:一是根据被观察到的相对频率,二是借助背后的物理性质。”[5]16 这样,适合度的倾向定义与费希尔的定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用以往的相对频率来说明实际的繁殖成功,需要考察较长的序列,是一种期望;后者则是实际繁殖成功本身。③适合度的倾向解释是个框架定义(schematic definition),它与繁殖成功的因果关系只在具体的场合才有经验意义。按这个说法,适合度概念就不必同时是普遍的和认识上可应用的。布兰登和彼蒂把适合度倾向解释的意义总结为:“按照倾向解释,适合度是一种由期望而非实际的繁殖成功来说明的概率倾向或能力(数学意义上的‘期望值’)。只要实体的倾向性质或能力与实体的实际行为之间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分析关系,适合度的倾向解释就能保证差别适合度为差别繁殖提供真正的解释性说明。”[6]
尽管适合度的倾向解释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自然选择原理对差别繁殖的循环解释问题,但仍然有困难。罗森博格和威廉斯指出:“然而,这里的概率不可能只是理论上未涉及的参考类——即群体中最近n代——的实际相对频率。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如此理解的期望值并不是确定的因果倾向,而只是对可获得资料的统计;第二,如果这种计算结果被看成是某种确定的因果倾向,那它就不可能是适合度,因为仅当足够大群体的相关代中导致进化的力保持不变时,实际繁殖水平和短列相对频率才能成为适合度的可靠指标。”[7] 罗森博格主张,在进化论中,适合度是一个初始概念,不可能有恰当的定义。他说:“如果适合度是一种倾向性质,那它就是一个影响生物繁殖机会的各种‘因果相关特征’的函数。但这些特征在自然选择理论中是完全不被涉及的,只由诸如地质学、气象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进化论以外的理论来提供,适合度就因果地附着于这些特征之上。正因如此,就自然选择理论来说,适合度是初始的,只能由其他理论来定义或刻画。”[8] 罗森博格和威廉斯相信,无论是把适合度定义为概率倾向还是说适合度在自然选择理论内是没有恰当定义的初始术语,都表明自然选择理论并没有因适合度与实际繁殖成功之间的同义反复而被贬损。
第三条可能的进路是重新定义科学的标准形象,进而容忍或者化解自然选择原理的同义反复性和不可检验性。一些生物学家如高治(T.A.Goudge)、迈尔(E.Mayr)等,特别强调进化论代表着一种更为普遍的科学形象,正统的科学标准不能容纳进化论只能说明标准本身有问题,而不能动摇进化论的科学地位。
在这条进路上,一些哲学家的工作迈出了实质的一步。这主要体现为苏佩斯(P.Suppes)、萨普(F.Suppe)和范·弗拉森(B.C.Van Fraassen)等人提出的科学理论语义观被彼蒂(J.Beatty)、汤普森(P.Thompson)和劳爱德(E.Lloyd)等人运用于进化论结构的分析上。
按这种观点,理论是由一组关于理想系统的模型构成的超语言学实体(extralinguistic entity),理论对经验系统的解释是通过判定理想模型与经验系统同形(isomorphism)来进行的,模型的建立就是对理想系统的定义;规律如果存在的话,只是作为模型的定义描述了理想系统的行为而不是经验系统的行为;仅当模型被成功地应用于经验系统时,规律才获得了经验意义。换言之,规律并不是理论的必要成分,即使存在规律,它也不是对经验现象的概括,因而也不能直接用于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预见。劳爱德说:“依据理论的语义观,确证一个理论就等于确证一组模型,更确切地说,就是要确证关于模型的经验判断,也就是陈述一个(或一类)自然系统在某些方面与模型同形。”[9] 对于达尔文进化论来说,自然选择原理可被用于任何存在差别繁殖的生物集合,而基于具体适应性特征的关于差别繁殖的解释则属于自然选择模型族一员的局部模型。当我们作出这类局部解释是自然选择模型的具体化这样的判断时,总是要依据充足的经验证据。这里,并不涉及自然选择模型本身的可检验性问题。
上述这三条进路,最有希望的当数第二条。这是因为:第一条进路事先假定一种固定不变的科学标准以及自然选择理论的不变性,是一种消极的做法,很难与进化生物学理论的研究实践相协调;第三条进路没有区分对自然选择理论的理解现状与该理论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弄清同义反复性、不可检验性究竟是与正统科学标准的要求相悖,还是与进化生物学的基本目标不一致,况且,“它没有交待一个能够统一各种具体模型的普遍模型的结构,即没有说明在其应用范围内应当怎样检验一个普遍模型。”[10] 我说第二条进路有希望,并非是说沿着这条进路已经对于自然选择原理的同义反复性问题有了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情况恰恰相反,仅就上述列出的三种策略来说,都存在严重问题:索博尔的说法只是确定了达尔文理论的其他部分是经验可检验的,还不是正面回答自然选择原理是否同义反复以及怎样消除同义反复的问题;像高尔德等人那样收缩自然选择原理的解释范围,仅仅指出了存在进化的非选择解释,即使情况真的如此,也不能消除同义反复问题;在定义适合度时,如果给出生态学定义,那只能暂时掩盖同义反复问题,而最被看好的倾向定义也面临着意义阐释问题、操作测量问题。尽管如此,这条进路仍然是建设性的,它可以引导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为进化生物学的理论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
上述列举的各种解决方案,都没有清楚地说明适合度的不同定义与不同的解释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没有真正解决自然选择原理的同义反复问题。实际上,同义反复仅存在于这样的情况:适合度是由实际的后代数目来定义的,并被用于解释一类个体(或者基因型)的存在。这种错误的实质在于企图从概率陈述推出存在陈述。
二
杜布赞斯基指出,把自然选择过程描写得过于生动,如说“生存竞争”、“最适者生存”等,是导致达尔文主义被误用的原因。[11] 的确,达尔文把“最适者生存”作为自然选择原理的简略表述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简略表述远没有表达出自然选择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选择原理是一个同义反复的责难大多针对“最适者生存”这个命题。
一个同义反复,本质上是这样一个逻辑论证和因果命题:它有“如果A那么B”的形式,却又通过B来定义A。这与数学上的相等关系并不一样。例如,6=2×3是对一种等量关系的陈述,无所谓同义反复问题。“最适者生存”这个命题暗示了这样的关系:适应是由生存来定义的,生存是由适应来解释的。这里我们还想到了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这个命题包含同义反复的关系:“存在”定义了“合理”,“合理”解释了“存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特点是:把存在本身作为某种性质的定义,再用被存在定义的性质解释存在。可以看到,一个因果关系陈述,如果其中涉及用存在本身定义的性质或者把存在本身作为原因,就有可能包含逻辑上的同义反复。
现在的问题是:自然选择原理是否可被概括为“最适者生存”?或者至少包含“最适者生存”?笔者认为,自然选择原理不能被概括为“最适者生存”,但包括了这个命题。
说自然选择原理不能被概括为“最适者生存”,那是因为自然选择的实质是差别繁殖(差别存活),即,在某种性状上存在差异的不同个体,如果这种性状是影响个体生存和繁殖的,则它们对后代的基因库的贡献不同。显然,自然选择被用于解释群体的现象,而不是某种个体的存活。自然选择机制加上遗传变异和成种作用,被预期有新的物种形成。达尔文本人也是明确这一点的,他那部影响世界的著作就是以“通过自然选择或者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为标题的。达尔文没有把解释的目标指向存在本身,而指向了存在的变化,也即新物种的形成。同时,坚持自然选择原理的生物学家也不企图预见最适者生存,而只是要预见这样的事实:厌氧细菌在缺氧条件下比需氧细菌更能生存,进而在缺氧条件下厌氧细菌繁盛起来。
自然界中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适应者并不生存。鸟类学家发现,有些鸟类在繁殖中遵循“一夫一妻制”。设想A、B两只雄性鸟,A鸟比B鸟更适合于环境(如更容易躲避天敌的捕食、更容易获得事物等),但A的配偶已经死亡,留下的后代少于B的。这样,A所携带的有利基因没有在种群中扩散开来。如果自然选择原理断定适应者一定留下更多的后代,那么我们设想的情况就与自然选择原理不一致。这样看来,自然选择原理就是可错的,并非是一个没有经验内容的同义反复。说自然选择原理包含了“最适者生存”这样的表述,那是因为自然选择作为一种自然过程发生作用的特点在于“筛选”,即,有利者被保留,不利者被筛掉。“最适者生存”显然表达了自然选择过程的这个特点。一个种群中各种基因型频率变化,最终体现为某些类型的个体在群体中的比例增加了,而另外一些类型的个体的比例降低了直至为0。从结果上看,在种群中占优势的类型就是适应的类型。不论我们怎样来理解自然选择原理,“最适者生存”总是其中的重要命题。只要满足下列这几个条件,自然选择的“筛选”作用就会发生:(1)存在一个个体集合;(2)这些个体是繁殖的;(3)存在可遗传的变异;(4)这些可遗传的变异在特定环境中使不同个体留下后代的机会不同。
“最适者生存”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同义反复呢?笔者认为,不一定。这取决于我们怎样定义和使用“适应”这个概念以及怎样估计适合度。当适应被定义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并运用工程分析的方法来估计适合度值时,无论适应被用于解释种群构成的变化,还是解释一类个体(基因型、表现型)的存在,都不会出现循环定义或者解释的同义反复问题。当适应被定义为生存能力或者繁殖能力并用实际的后代数量来估计适合度的值时,用适应解释种群构成的变化并不产生同义反复;而要用适应解释一类个体(基因型、表现型)的存在就要出现同义反复。还必须指出,把适应定义为繁殖能力,进而用适应概念来解释一类个体的存在,这不是生物学家所要做的。
在有些情况下,依据适合度的先验定义就可以检查出选择效应的存在。达尔文曾谈到这样的例子:栖息在卡次启尔山的野狼种群有两个变种:一个变种是长腿体瘦型,奔跑的速度快,主要靠捕食野鹿为生;另一个变种是短腿体胖型,奔跑速度较慢,经常捕食不到野鹿,因而经常攻击羊群并被猎人捕杀。我们可以想象,种群中的敏捷、狡猾、奔跑速度快的个体,一定要比迟钝、愚笨、奔跑速度慢的个体有更多的捕食野鹿的机会,因为野鹿的奔跑速度也是很快的。在野鹿数目有限且只能保障一部分野狼生存的情况下,后者就要被淘汰。这时,我们说长腿体瘦型比短腿体胖型更适应。这种适应,是指生物与环境的一种关系,一些先验的标准规定了什么样的生物——环境关系是适应的。这种先验的标准可以根据某种生态学(或者工程)的分析来确定。在我们的例子中,要根据野鹿和野狼的数量来确定野狼维持生存必须达到的奔跑速度以及奔跑速度与成功捕食野鹿次数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些先验的标准,还能够给出适合度的先验估计。这时,不论用适应(适合度高)来解释长腿体瘦型野狼的存在,还是解释卡次启尔山的野狼种群中两种类型的比例变化,都不是同义反复的。
遗憾的是,这种适合度只有局部定义(local definition),我们无法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先验标准。适合度最好被看成是一种依附性(supervenience),即,适合度不同,其物理基础必定不同;适合度相同,其物理基础未必相同。如果适合度是依附性,那就意味着没有必然的物理陈述能够说明包括选择在内的生物学现象。既然给不出先验标准,就要通过考察选择的结果——实际繁殖率来估计适合度。当我们比较一个工业区内的浅色桦尺蛾和深色桦尺蛾的频率时,会发现深色尺蛾的频率有逐代增加的趋势。假如我们不知道体色的生态学意义,也能够通过深色尺蛾的繁殖成功了解到体色对尺蛾繁殖的影响。留下许多后代的事实意味着深色这种性状在下一代中具有代表性。通过计算两种类型的频率变化,可以得到相对适合度的估计。
这样得到的适合度虽然不对应于一种先验标准,也可以用来准确地衡量选择优势。这是因为,哈代—温伯格定律给了我们一个基准线,使得我们能够比较一个种群中各个等位频率的实际变化。对这条基准线的超越就意味着在世代交替中这种基因型频率的平衡被打破了。导致这种平衡破坏的原因可以是突变(遗传物质改变)、迁移、遗传漂变以及选择的偏好等。假如其他打破平衡的力量被排除,就可以用一种基因型频率的变化来估计这种基因型的相对适合度。由于一种基因型的相对适合度就是基因型的实际繁殖率,所以用基因型的相对适合度解释基因型的实际繁殖率就等于用实际繁殖率解释实际繁殖率,因而是同义反复的。这种适合度的定义方法与估计方法是一致的。与此情况不同,用相对适合度解释一个种群的构成变化,意味着要建立各种基因型的实际繁殖率与种群构成之间函数关系的模型,其中还要估计迁移、漂变等其他可定义参量对种群构成的影响。这时,相对适合度、迁移、漂变等因素与种群构成变化之间就是一种因果关系,没有所谓同义反复问题。这时使用的适合度概念,其定义方法与适合度的估计方法是相分离的。也就是,估计相对适合度的值就是测量实际繁殖率,而相对适合度的本体论意义则是由实际繁殖率所代表的倾向或者能力。
根据哈代—温伯格定律,各种不同类型的比率在后代是不变的。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这样的结论:当种群中的各种基因型频率处在平衡状态(环境不变)时,后代各种基因型的比例与亲代的一致,每一种基因型的繁殖率在世代交替中也是不变的。这样,一种基因型的实际繁殖率才可以被近似地当作这种基因型的属性或倾向。相对适合度作为一个倾向性概念,必定是以往实际繁殖率的统计平均值。统计的样本越多,就越可靠。显然,这种相对适合度不能被用于解释作为统计样本的个体的繁殖率,只能用于解释和预见样本的后代的繁殖率。
怀疑自然选择原理的科学地位,还有另一版本,即认为依据这一原理不能给出可以接受经验检验的预见。这主要是由于不能给出适应概念的工程定义,生物学家的工作就集中于这种作为统计结果的适合度概念上,根据哈代—温伯格定律确定的基准线来估计适合度的值,并据此区分出各种导致群体变化的原因。适合度是统计结果,因而对未来的预见也是一种概率陈述。如果根据以往的统计已经确定A型个体在种群中的相对适合度是10%,那么就可以预期在选择压力不变时,下一代A型个体将占种群的10%。对于后代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它们是A型个体的概率也是10%。这是一个概率陈述,而概率陈述可以推出任何存在陈述。例如,即使在后代种群中发现多于10%的个体,我们也不会怀疑这个陈述,因为这个陈述是对多代的统计结果。这就意味着这种预见不可证伪,也即没有经验内容。按照我在前面的分析,这种情况的产生还是由于把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解释一类个体的存在。实际上,这不是一种合法的应用,因为解释一类个体的存在不是通过自然性选择而进化的理论的任务。
收稿日期:2006—09—12
基金项目: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进化生物学前沿的几个重大哲学问题”(批准号:05BZX030)。
标签:达尔文论文; 基因型论文; 自然选择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进化论论文; 适者生存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