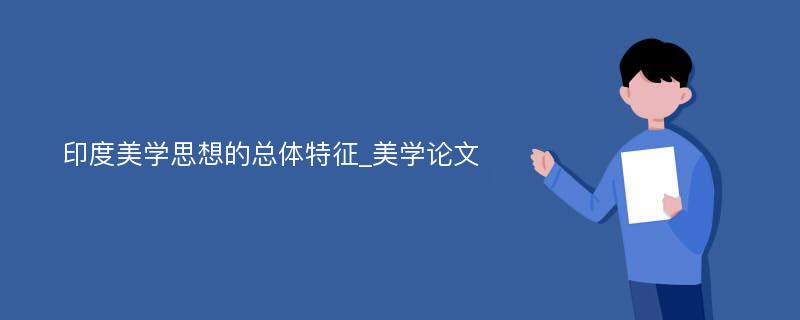
印度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美学论文,总体论文,特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02)01-0004-04
综观印度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它在历史演变和不断深化过程中,有某些较稳定的反复出现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催化和制约作用。这种呈规律性的思想,在其美学思想的不断变化中起着不变的作用,这就显示出印度美学的特征性的东西,这些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印度美学和宗教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印度思想体系中的宗教哲学意识相当发达,拥有若干庞大的不同的宗教思想派别。马克思所说的:“哲学产生于意识的宗教之中”的论断在印度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然而,宗教哲学同美学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却又显得疏远和间接。因为在大量的宗教哲学著作中很少发表明确的对美与艺术的见解。这种状况从最早的《四吠陀》到后来的《奥义书》以及浩若烟海的佛教经典中都可以看到。但是,从印度艺术和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古代印度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或“纯艺术”作品,它们几乎都是在特定的宗教意识支配下对人生和现实生活所作的图解。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的所谓艺术和文学都是这样,很大程度上都是教义的表达。即便是被视为文学作品的两大史诗,根据汤用彤的说法:“溯邃古以来,先有黎俱吠陀之宗教,中有梵书之婆罗门教,后有纪事诗之神教,最后则由此衍为印度教。”[1](P63)它们也是宗教和哲学性很强的著作,是构成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因如此,现代的印度人仍把它们看作是宗教“圣典”和宗教生活中的“百科全书”。这种状况既矛盾,然而又是事实。这说明古代印度宗教哲学家们尚没有阐述审美理论的自觉。但是,在他们对现世生活和彼岸世界所作的大量的描绘中,在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比较中,在他们宗教哲学的观念中,又潜藏着丰富的审美思想,这些思想必然要在宗教哲学的外衣下显露出来。例如,神创的世界的完美,自然界所显示的梵的生命性,生命的动静交替的韵律之美等,都显露出了某些审美思想。在对神像、神庙、神陵的艺术创造中,尽管目的是为了颂神,但在客观上,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艺术宗教》中所说:“神的庙宇和厅堂是拿来供人们享用的,而且在庙宇中,所保存着的宝物,在需要的时候也是属于人的。在艺术装饰中神所享有的光荣就是富于艺术天才和宏伟气概的民族的光荣……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民族便通过他的劳动而与神相结合,不在于空洞的希望和推迟到渺茫的未来的现实性,而在于为神争光和对神献礼的实际考验中直接享受这个民族自己的财产和装饰。”[2](P208)这就是说,宗教艺术在崇拜的外衣下,掩盖的是为人自身的利益和对人自身创造美的能力的一种客观化的确证。可见,宗教观念制约下的审美创造中,蕴藏着丰富的美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美学观念。在某种程序上可以说,古代印度艺术所表现的几乎都是宗教性的观念,或者说印度民族的审美观念都是融化在、被掩盖在宗教的外衣下表现出来的。正因如此,我们在总结奥义书美学思想和佛教美学思想时,才借用黑格尔美的定义说:美是梵性的感性显现或美是佛性的感性显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在论及印度的艺术时说:“舞蹈在印度历史的大多时期,乃是一种形式的宗教崇拜,是一种动作和韵律之美的展示,以荣耀神并且陶冶神的性情;……对于印度人,这些舞蹈不仅是肉体的展示,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宇宙间韵律与过程的模仿。Shiva便是舞蹈之神,而Shiva的舞蹈正象征着世界的律动。”“印度的音乐家如象印度的哲学家,他从有限开始而把‘灵魂放入了无限’,他据着曲题先作一番发挥,直到后来,他藉着一种有催眠性的单调音符,创造了一种音乐性的瑜珈,而忘了意志、个性、物质和时空;灵魂被提高到一种与某种‘深度渗合’的东西达到神秘的境界,那是某种深沉、巨大而安详的存在体,某种原始而周遍流行的真实,微笑地俯视着一切挣扎的意志,一切的变化和死亡。”印度绘画“它所要表现的并非物而是情,而且它所要做到的并非是表现而是暗示;它所依赖的不是色彩而是线条;它所要创造的是审美或宗教的情绪而不是复制真实;它所感兴趣的是人与物的‘灵魂’或‘精神’,而不是物质的形式。”在雕塑创造上,“雕塑者所刻出的不是他的梦想,而是僧侣的规定;并且印度的每一种艺术都是属于宗教的,是神学的使女。”[3](P358)尼赫鲁指出:“印度艺术和宗教哲学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地联系着,所以如果对于支配印度人头脑的各种概念没有一些认识,就不容易彻底理解它。……在印度艺术中总含有一种宗教的冲动,一种看到来世的心思,大概正象那些建筑欧洲大教堂的人所具有的灵感一样。”[4](P262)美国美学家托马期·门罗也指出:“印度美学史是印度哲学与宗教史中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因此常与《吠陀经》和《数论》体系、与湿婆崇拜以及某些种类的瑜珈术相联系。”[5](P22)“印度艺术皆为宗教性的,无论其表面有多么世俗化,其中也存在着神的象征意义。”[5](P60)这些论述是深刻而确切的。我们面对佛像的超尘脱俗的圆融宁静,面对他美妙的三十二像、八十种好的无限完美,面对阿旃陀石窟轻盈飘逸的飞天,面对舞神湿婆汪洋恣肆生气充盈的铜雕,谁能不惊叹宗教的想象与艺术的想象合二为一所达到的绝妙和谐呢?谁又不能深深感受到印度美学精神的独特魅力呢?正因印度美学与宗教哲学的这种亲密关系,才决定了印度美学思想一系列的其他特点。
第二,热爱现实之美,追求超验的精神境界之美。在审美领域中灵与肉的对立被弥合了,灵与肉的价值取得了完美的和谐。
古代印度思想都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领域:现实的物质生活领域和超验的精神生活领域。由《奥义书》所开创的灵肉二元的人生哲学对印度人的人生态度、伦理观念和美学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社会责任和伦理观念要求在人生中的某一段时期必须承担应尽之责,享受现世人生的欲乐和体验人生的悲苦。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人生的欲乐是作为积极内容和肯定面出现的。印度美学家K·C·潘迪指出:印度“传统否定感观快乐与精神满足间的对立”,印度人的心“与现实联系着,经验着精神的满足。”[5](P25)英国艺术史家L·比尼恩说,在印度艺术中“感官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有一种完美的融合”。[6](P31)“人类的情感象征着个人对至高灵魂的寻觅,这在性交绘画与雕塑中得到了表现。印度教通过这种将肉体作爱快感与宗教狂热情绪协调起来并融为一体的方法,极大地避免了曾骚扰希伯来人和基督教徒的良心上千年犯罪感的这种肉体与灵魂间的冲突。比较开明的人即使在肉欲享乐的中途,也能意识到精神的意义;而其他人则是以某种较为肉感的方式去经验后者的。”[5](P29)正因为印度思想把现实人生看作是攀登崇高精神境界的必由阶梯,所以其美学和艺术才充盈着对现实生活之美和自然之美的热烈情绪。所以,在诗歌、戏剧和雕塑绘画中,才能够大胆地率真地表现性爱和情欲,才大量高亢赞美女性富于肉感的人体美,甚至在古典艺术时期,美女这一概念被置换成性满足后的“倦慵的少女”的称名,“‘倦慵的少女’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中连这些‘美女’原有的精灵本性都消失了。”[7](P37)但是,这仅仅是印度思想的真理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印度美学在肯定和享受现实之美时,又充满了对现世之美的超越冲动。《奥义书》要求人们透过现实之美,去领悟梵的真、智、乐的绝对美的本性而不能眷念和停留在物欲的有限之美的樊篱之美中。“在佛教艺术更为成熟的阶段里,这种强烈的感官性并没有被抛弃,而且也不与精神性相对抗,这两者反而是和谐一致的。”[6](P26)但是,佛教则在肯定现实美的态度下,要求信众超尘脱俗,去追求圆融宁静的美妙无比的涅槃境界,即消解了现实之美丑后的静穆的精神境界。
由于这种经验之美和超验之美的和谐统一,因此印度美学才有灵肉双美的特点;美的概念才有两个既对立又统一、既连接又有区别的层面之分;才有精神美之高于物质之美的独特的审美价值观;才有印度艺术独特的美学风格:既充盈着生命之气、强调生命是美的,又显示着空灵超脱的精神之美。只有了解这种美学思想的独特性,才能够深刻认识到印度美学情味理论和韵论的真谛和它们出现的必然性。
第三,美是和谐。
美是和谐并非是印度美学的独特思想。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早就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论证,并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以后的德国古典美学家们,尤其是在康德、歌德及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中,和谐是美的观点都得到认可和清晰的表述,只不过他们以不同的哲学出发点和不同的方式来论证这一命题而已。美是和谐这一命题之所以是印度美学的特征,不在于这一命题的结论本身,而在于其背后潜在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印度各派宗教哲学殊途同归的必然结论,可以看作是全民族审美思想的共识。早在吠陀经典中,就把美区分为现象之美和绝对美,有限之美和无限之美。只有通过前者而把握了后者才是对真理的把握。《奥义书》、《薄伽梵歌》、《摩奴法论》乃至佛教哲学和数论哲学、瑜珈哲学都进一步以清晰的表述深化了这一思想;真理是合和而成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构成事物的真理,任何一种把二元因素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观点都被叫做“双昧”(虚幻的认识)。这种调和二元对立,视合和为真理的观点可以说是印度思想共同的最基本的特征。《奥义书》宣扬的“万物皆梵”,所追求的“梵我如一”;瑜珈哲学要求人的认识超越这种幻象之间的对立而强调联合、和谐;数论哲学强调变异与非变异本质上的统一,即“一切法一”的观点;佛教的“万法归一”的“空论”及涅槃;在以迦梨陀娑等作家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唵’声奥义书》中所宣扬的合和为真理的印度思维模式等,都可以得出和谐是宇宙的终极真理的结论。这一印度思想或思维模式在现代美学家泰戈尔的思想中仍然表现得清晰深刻。可见,美是和谐的命题有着深厚的思想根基,是印度思想总体特征在美学领域中特殊化的显现。
正因为印度美学思想强调和谐是美,才引导出其他一系列独特的美学思想。例如,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方面的审美“同情观”理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善与美的价值论上及美感上的统一,正因为善表现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欢乐,所以美与善相互融化为一体;在灵与肉的美各自具有的合理性及灵肉双美的并重方面;对超越有限的现实之美去追寻无限的超验之美的早美理想追求方面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昧”、“韵论”美学思想方面;在艺术创造的富于生命力的表现和神秘空灵的风格方面等等,没有哪一点不是导源于美是和谐这一命题。就一个民族思想的总体特点同美学观念达到如此亲密的程度而言,美是和谐的命题就显示出了印度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尽管其他民族的美学思想也有相同的命题,但其思维基础同这一命题的关系却有着具体的差异。法国著名的艺术家艾黎·福尔(Elie Faure):“和谐是一种深层规律,源于最初的统一的规律,大于世界中最普遍、最无法抗拒的实相,决定了人类对和谐的向往。……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诸般要素无不竞相参与,以和谐的方式,实现着这个世界的种种功能。……于是艺术家出现了,他捕捉到宇宙的普遍规律,并且还我们一个整的世界。”[8](P13)这说明“和谐”是人类共同感受和发现到的美的规律。应该说,印度民族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很早而且相当深刻的。因为这一规律贯穿在他们全部意识领域中而不仅仅局限在审美活动的范围之内。
第四,印度美学思想同原始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印度的原始宗教和原始世界观中有着浓厚的原始思维成分。这些观念被延续继承了下来,并直接影响到审美方式和美学观念。由于原始思维同审美思维有着血缘关系和方式上的相似性,所以印度的原始思维极大地滋润了审美思维,促进了审美思维的成熟与发展。例如,万物有灵观制约下的灵魂不死、轮回业报和万物“生命一体化”的观念,就决定了审美思维中的“万物同情观”和情昧观念;原始思维对自然生命力、性力的崇拜决定了绘画雕塑形象的重重叠叠的美学风格,对此L·比尼恩指出:印度的浮雕“表现出印度人对于密集拥挤、一团一簇的形式的喜爱这一特点。……印度艺术家不讲究任何形式上对称或是明显的条理,他使之产生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形式上的自然和谐。这使人想起布莱克的感叹之语:‘繁盛即美’。它的美,宛如结满一串串的葡萄的沉甸甸的葡萄藤。你越是对它沉思冥想,你就越是感到它的形态所含有的那种丰富性。”[6](P50)印度绘画理论家阿邦宁德拉纳特·泰戈尔所著的《关于印度艺术解剖学上的几点注意》中也说:“这种对模仿花朵及动物曲线的研究,并使男女的姿式,相辅相依,也象并蒂的花枝一样,给印度美学的典型,注入了新的生命。……这样遂产生一种浑成、柔韧、朴素而且和谐的艺术。”[9](P33)
此外,原始思维中的具体性思维方式就促成了印度民族发达的有象思维和艺术的意象性和情感性;原始思维中的象征性思维一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印度审美思维的想象能力和主观幻想性,艺术中那些超现实的形象和超现实的世界就是这种天马行空幻想的结果,另一方面促成了印度艺术大量采用象征比喻暗喻的表现方式。再如,原始思维的完整性特点决定了印度叙事的环中环结构及绘画雕塑对叙事时空在构图上的独特处理方式,以及诗歌中反复咏唱的形式等等。原始思维对印度美学思想和艺术表现在本人所著的《印度美学史》各章中都有论述,这里就不再赘叙了。
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相互作用、彼此渗透、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合力,制约着印度美学和艺术的独特形态。当然,印度美学的特征可能还不仅于此,而且这些特征也不仅止于印度民族所独有,这一问题还应当进行更深的研究,但就它们同东方其他民族的美学思想相比较而言,上述特征更鲜明突出而已,它们最能体现印度美学的基本性格。如果只能允许用一句最精炼的话来表达印度美学思想的特征的话,这就是印度诗圣泰戈尔所说的:“美是在有限之中达到无限境界的愉悦。”
[收稿时间]2002-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