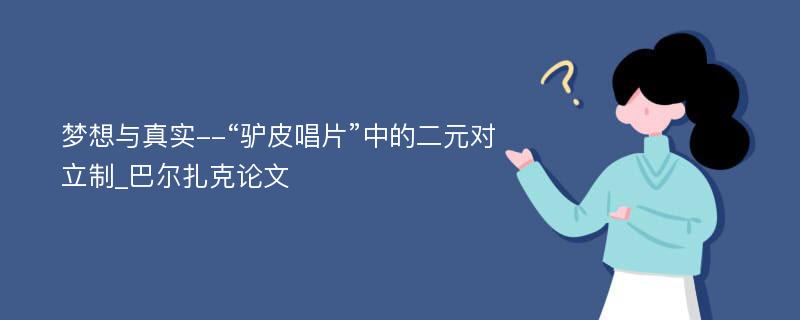
梦与真——《驴皮记》中的二元对立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体系论文,驴皮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之一,他的客观忠实的描写手法、敏锐的观察力、刻画人物个性的技巧以及对当时政治、历史背景的反映和对社会丑恶现实的揭露为人所共知。但是,巴尔扎克浪漫主义幻想性的一面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特别是在我国。除了《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等家喻户晓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外,巴尔扎克还写了许多富有浪漫色彩的志怪小说。
志怪文学是法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19世纪初正是它的黄金时期。许多作家都在这方面进行过尝试,他们的创作动机各有不同,作品所产生的效应也各具特色。有的是因为对超自然现象本身感兴趣;有的是想借助这类作品来逃避他们深恶痛绝的现实,幻想另一个理想的世界;有的是以此抵制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的时代观;有的是为了表现潜意识幻想与超常现象之间的关系;还有的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这类体裁的主要代表有维里耶、莫伯桑、梅里美、戈蒂耶、巴尔扎克等。巴尔扎克曾在十几部短篇小说(如《百岁老人》、《长寿药水》等)和《驴皮记》(1831)、《路易·朗贝尔》(1832)、《塞拉菲达》(1835)三部中篇小说中表现了人对超自然现象的反思。这类作品后来大都被归入《人间喜剧》中的“哲理研究”部分。它们一方面反映了年轻时期的巴尔扎克对权力、财富和成名的梦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神秘主义和超自然世界的兴趣,这种兴趣伴随了他的一生。《驴皮记》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超自然现象相结合的典型作品。本文意在从作品中超自然现象的标志——驴皮这个法宝的表面象征意义出发,揭示出隐藏在它背后的贯穿整个作品的二元对立体系。
一、神秘效应与现实情境
《驴皮记》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个名叫拉菲尔的贵族青年,在遭到失恋和破产的打击之后,接受了一个古玩店老板送给他的法宝——驴皮,谁接受这个法宝就可以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但每实现一个愿望,驴皮就随之缩小,接受者的生命也就随之而缩短,直至和驴皮一起消逝,这便是主人公最终的命运。在这个简单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含义。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小说中超自然现象的神秘效应所依赖的叙述机制是如何建构的。
小说中的超自然现象集中体现在驴皮的魔力上。首先,这个法宝的主人古玩店老板就是一个神奇的人物:他的年龄是102岁, 他的出现充满神秘的色彩。他像幽灵一样出现在小说主人公拉菲尔面前,后者既没有听见他走近,也没有听见他说话和动作。作者写道:“他的出现像是变魔术似的”,他的样子“像从邻近古墓里钻出来”,“那个鬼怪似的人物双眼一动不动,放射出奇特的光芒”。 (注:H.de Balzac,LaPeau de chagrin,Garnier-Flammarion,Paris,1971。见《驴皮记》, 郑永慧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第22页。以下出自此书的引文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他的笑容“使拉菲尔的活跃的想象力立刻认为这个怪人同画家理想中的歌德笔下的魔鬼惊人地相似”(第178页)。其实, 主人公拉菲尔接受法宝,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与魔鬼签约,所不同的是,歌德笔下的魔鬼是神话世界的魔鬼,而巴尔扎克笔下的“魔宝”却出现于活生生的现实世界,这也正是志怪文学的主要特征。
与超自然现象有关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志怪文学,(注:“志怪”一词的法文是“fantastique”,既可以作形容词,也可以作名词。 法语小罗伯尔词典把它解释为一种“被想象所创造,而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它最早来源于拉丁语的形容词“fantasticum ”和希腊语的动词“phantasein”,意思与幻觉和幽灵相关。经过历史的演变,该词成为19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志怪文学的特定修饰语。这个词今天已经转义,常常被用来表达一种惊叹的感情色彩,它的原义人们已经很少想到。)我们可以把表现超常现象的文学体裁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神话类,包括一些童话或者神话类的作品,如《一千零一夜》或《西游记》等。这类作品所涉及的超自然现象毫无神秘性可言,因为在那个神仙无所不能、动物会说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可能的,读者不会感到惊奇,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纯属幻想的世界,它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冲突。第二种是怪异类,在这类作品中,读者不会像在前一类作品中那样只是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因为,这里的超自然现象往往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而且它会使人产生疑问,引起人们的恐惧感。但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起初貌似神秘的东西最终会找到理性的解释。捣鬼作假、误会、梦幻、疯癫、醉酒、毒品都可能是神秘现象的谜底,最终的胜利者是逻辑推理。侦探小说就是这种体裁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种才是我们所说的志怪类,这类文学作品试图展示的奇异现象是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现象,它使读者产生疑问、困扰和犹豫,是非理性向理性的一种挑战。这类作品的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法国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最先在《志怪文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以上的划分模式。 (注:参见T.Todorov,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Ed. du Seuil,Points,1970,第3章。)
综上所述,志怪文学最主要的特点表现在现实与超自然现象的冲突上,也就是说,在这类作品中往往有某个超常的现象或事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而这种现象或事件无法用自然法则来解释,它们往往带有令人担忧、恐惧的色彩,动摇人的理性思维。叙事情境和叙事主体在这里的表现至关重要,因为真实可信的时空环境和叙述主体是志怪效应的保证。《驴皮记》中的超自然现象正是在这样一种真实、可信的叙述背景下出现的。
小说这样开始:“去年十月末,在赌场开馆的时刻,一个青年走进了王宫大厦,毫不犹豫地踏上了36号赌馆的楼梯。”(第1 页)小说结束时的落笔时间是:“巴黎,1830—1831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出故事发生的时间:“去年十月末”指的是1829年或1830年。由此,作者的创作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几乎相吻合。“王宫大厦”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巴黎,同时小说落笔的地点巴黎也与故事发生的地点吻合。这一切都表明了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密切关系,给读者造成一种可信的空间。另外,小说所再现的真实的历史、社会和政治背景,比如七月革命、君主立宪制、卡洛斯派、开明君主等,也加强了作品的可信度。
叙述主体为读者营造的“真实感”和“可信度”对提高文本的可信性也很重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点在志怪文学作品中尤为突出,因为,要让读者去相信一个不可能存在的现象或至少让他对其产生疑惑,叙述者在读者眼里的身分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只有和读者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才有可能影响后者。叙述者和受述者之间的距离越小,他们之间的认同性就越大。志怪文学的目的就是让人在奇异的现象面前不置可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自然是最理想的。
然而,我们看到,《驴皮记》中的叙述者并非第一人称,而是第三人称。但是,这个第三人称在小说中常常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出面亮相。比如小说一开始就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对话性的话语语境:“去年十月末”中的“去年”这个时间定语在语言学中属于表示话语情态的“离合词”(embrayeurs);它的出现表明叙述主体的介入和语言行为的开始,从而产生一种对话情境,使受述者或读者仿佛面对一个讲话者。小说的结尾是叙述者和隐性读者的直接对话,后者很想知道女主人公后来的情况:“后来波利娜怎样了?”而前者总是答非问,一再勾起后者的好奇心。后来当读者又问到另一个女主人公福多拉的情况时,叙述者回答:“昨天她在滑稽剧院,今晚她要去歌剧院……”(第252—253页),“昨天”和“今晚”这两个离合词进一步明确了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情境。此外,叙述者的介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时地使用动词的现在时,插入自己的感慨、评论,向受述者进行一连串的发问,频繁地用第二人称“您”来称呼读者,以衬托出“我”的存在,从而与读者建立起对话关系。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主人公拉菲尔身上看到青年巴尔扎克的影子。像巴尔扎克一样,他也有一个年老的父亲在帝国时期发了财,在王朝复辟时破了产,死时没有给儿子留下任何遗产;他也在中学毕业后开始学习法律,居住在巴黎一间简陋的阁楼中,里面也有架钢琴,生活清贫却追求奢侈;到处躲避债主,为生活所迫而给别人写假回忆录;想象力发达;他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论著《意志论》曾是巴尔扎克在旺多姆中学时的论文题目;他也对法宝和超常现象感兴趣。巴尔扎克在1846年写给汉斯卡夫人的一封信里说,他当时在巴黎的生活就是《驴皮记》里主人公的生活。(注:参见Pierre Citron为La Peau dechagrin
(Garnier-Flammarion,Paris,1971)所作的引论,第42页。)
二、法宝的象征意义与二元对立体系的统一关系
我们可以把法宝即驴皮的表面象征意义概括为:有得必有失,欲望的满足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主人公接受了法宝。过度的野心折磨着他,他认定自己要干大事,经常梦见自己当了将军、皇帝。他父亲也对权力充满幻想,不想让儿子成为律师和公证人,而想让他成为一个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小说中的百岁老者认为,死亡的两个原因是人的意愿和能力,驴皮就是两者的结合,前者“焚烧我们”,后者“摧毁我们”。
驴皮在小说中的双关意义也体现在字面上。“驴皮”(“La peaude chagrin”)既有令人兴奋的一面,同时也是忧愁的来源,两者缺一不可,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文“le chagrin”本身既指驴皮,也有“悲伤”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件与驴皮相关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值得一提,读者常常不会注意到它,那就是“帽子”。首先从形状、大小上看, 驴皮和帽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其次, 法文“帽子”(“lechapeau ”)一词几乎是“驴皮”这一词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颠倒的组合形式。帽子是权力、王冠的象征,是梦的象征,而法文“La peau”在俗语中有生命的意思,那么,象征权力的帽子同时也含有“生命的悲哀”之义。帽子从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当主人公走进赌场时,赌场的看守告诉他把帽子留下。后来,它在不同的场合先后出现过二十多次。它像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贯穿整个作品。主人公拉菲尔有一次在他的帽子被雨淋湿后这样说:“雨水将我的帽子淋得走了样了。以后怎么能接近一个时髦女子,在沙龙里出现呢?……它现在已经损坏、变形、完蛋,成为真正的破布,完全是它的主人十足的象征。”(第108页)
在具有二重性的法宝所表现的象征意义背后存在着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对立组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神秘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的对立
西方19世纪完成了一个大转折,或者说大断裂,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它动摇了社会、宗教的传统价值观,开拓了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领域,它使很多人相信科学就是认识世界的惟一途径。勒南曾声称:“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提供一切有关生命的真理”。(注:E.Renan,L'Avenir de la science,1890,p.91.)但同时,科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却使另外一些人深感不安,他们往往同情日落西山的贵族,怀念过去的辉煌,讽刺、抨击科学对传统精神价值造成的威胁。
巴尔扎克在《驴皮记》中暗暗地讽刺了唯科学论。小说展示给读者的第一个画面——献词——具有象征性的讽刺意义:“献给科学院士萨瓦里先生”。科学院士的名字“萨瓦里”(Savary)绝非偶然的选择,它与“知识”(savoir)和“学者”(savant)两个词有着明显的联系,而这两个词与科学的联系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在这里的讽刺效果跃然纸上。献词的下面是一条蛇形曲线(引自英国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商第传》),它起伏不定的形状象征着命运的曲折多变,正像法宝驴皮的魔力一样神秘莫测。作者献给科学院士的是神秘力量的挑战。小说的主人公拉菲尔就法宝的超常现象走访了四个科学家,他们分别是自然科学家、著名力学教授、出色的力学家和大名鼎鼎的化学家。但无论是力学家制造的压力机还是化学家的化学制剂,都不能使驴皮发生丝毫变化。那位张嘴不离“您一定知道”(第196—198页)的动物学界的大权威,对法宝缩小的原因其实也是一无所知。面对驴皮这一神奇现象,力学教授对其他三位科学家说:“我们千万不能把这件奇遇告诉科学院,我们的同僚会嘲笑我们的。”(第209页)
神奇的驴皮就是在这个不应该存在巫术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得到理性解释的19世纪——和地方——启蒙摇篮之都巴黎、法国怀疑主义大师伏尔泰断气的屋子隔壁——开始展示它不可抗拒的魔力。自称对科学充满信心的拉菲尔起初还在嘲笑相信法宝魔力的人,认为这一切纯属幻想、神话,但事实使他在超自然的力量面前不得不沉默。
科学与神秘主义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射了东西方文化的对立。科学属于西方,神秘主义属于东方。巴尔扎克起初曾打算以驴皮记的题材写一部类似《一千零一夜》的东方童话。小说中的法宝是一块来自东方的皮革,被认为是所罗门之印的标记,刻在驴皮上的字是梵文(实为阿拉伯文),它出自一位东方僧侣之手。拉菲尔起初不相信驴皮的魔力,因为它来自东方,而东方人都讲迷信。
2.个人、天才与社会的对立
叙述者多次流露出主人公拉菲尔在“这个忽视他崇高生命的社会”里怀才不遇、孤立无援之感。“多少困居斗室的天才青年,由于在茫茫人海中缺少一位朋友、一个女人来安慰他们,只好面对着厌倦了金钱和感到无聊的人群慢慢地枯萎,以至死亡”。拉菲尔顾影自怜,认为自己“死了倒值50法郎,活着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提携的天才,没有朋友,贫无立锥之地”。(第8—10页)他渴望同人交往,却形影相吊; 他认为自己应该在社会上闯出一条路,却一事无成;他自信是个天才,却不被人理解。他抱怨平庸之辈经常获得成功,而他这样的天才却到处碰壁。他厌恶社会,厌恶社会的礼节和包装。温泉疗养地的人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他们遵守上流社会的法律,排斥软弱、不幸、无权无势的人。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充满了虚荣和自私。伯爵夫人福多拉就是这个社会的化身,“她就是整个社会”(第253页)。 拉菲尔与社会的对立反映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倒置——物质利益支配着人的精神生活。
3.空间的对立
《驴皮记》向我们展示了两组空间的对立。首先是赌场和古玩店的对立。前者被描写为恶魔之地,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性。“这里有刺激神经的轮盘赌,给人以欣赏血流成河的快乐”(第3页)。自杀之前, 拉菲尔去了古玩店,他去那里是为了给自己的感官一点精神食粮,是去向艺术寻求勇气和安慰。充满艺术品的天地使他进入了梦的世界,摆脱了丑恶的现实。叙述者明确地道出了小说主人公来古玩店的目的:“原来驱使他到这商店来的欲望已得到了满足:他从现实生活中走了出来,登上一个理想世界,到达了令人心醉神迷的魔宫里……”。那里陈列的艺术品再现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的意大利、基督教、文艺复兴、印度等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犹如“一首无尽的诗篇”。 (第14页)
第二组空间对立是主人公拉菲尔居住的圣康坦公寓的小阁楼和福多拉伯爵夫人的公馆。前者周围街景优美,卢梭曾在这里住过。这里的陈设具有一种传统的美。拉菲尔住的阁楼虽然显得有些寒酸,但他在那里度过了十分愉快的三年,“这里的人和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相反,福多拉的家里表面上奢侈豪华,金碧辉煌,鲜花芬芳,到处都是品位极高的陈设、名画、丝绸帷幔、优雅奇特的装饰,然而这里的豪华却是“枯燥乏味的”,它只能唤醒人的卑劣思想。整洁简朴的阁楼与上流社会富丽堂皇却充满卑鄙龌龊的宫廷形成鲜明对比;狂欢酒宴、旅馆里豪华的摆设与里面的人所表现出的丑态也构成一种表里对立:“在这时候环视一下客厅,就等于提前看到了弥尔顿的群魔殿的景象。”(第64页)
这种表里对立还表现在两个舞女阿基莉娜和厄弗拉齐身上。她们在酒宴上出现时穿戴得珠光宝气,她们的美貌灿烂夺目,然而,背后却隐藏着铁石般的心肠。她们俩一个代表没有灵魂的邪恶,另一个代表邪恶的灵魂。
4.善与恶的对立
小说中善与恶的对立主要体现在波利娜和福多拉两个女主人身上。前者穿的虽然是粗布衣裳,但天真、纯洁、优雅、温柔、聪明、迷人。她和母亲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却有着很强的贵族意识,母女俩构成一副美妙的图画。福多拉伯爵夫人有着优雅的微笑、抑扬动听的声音和富有魅力的步伐,“但却缺乏温柔,也没有人情味道”。她对艺术不感兴趣,不喜欢音乐,对于催人泪下的戏剧,她的反应却是“冷酷和欢笑”。金钱对她来说最重要:“有了金子,我们早晚能够创造出为我们舒适所必须的感情”。(第118—124页)
除了上述几组大的对立面之外,我们还发现有的人物本身就是矛盾组合体。如古玩店老板身上既有邪恶魔鬼的一面,又有睿智老者的一面。“从他的脸上看出来洞悉一切神明所具有的清醒的安详,或者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自豪的魄力”,他“以无边的威力粉碎了人类的一切痛苦,但同时也扼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欢乐”。(第22—23页)
小说中还使用了大量的矛盾修饰法,即将两个对立的成分组合在一起。比如,埃米尔认为艺术家不可能在“富有的贫困”和“贫困的富有”之间犹豫;百岁老者说他的好运是贫穷带来的,他的智慧归功于无知(第89、30页);拉菲尔也说人类的堕落来自理智,无知无识倒能净化他们;在拉菲尔眼里,福多拉既是“十足的女性,又完全没有女性的味道”,她是“一个可爱的怪兽”;(第143 页)拉菲尔的生活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向往东方式的悠闲生活与梦想、娱乐、爱情,却不得不埋头工作;他的表情充满了矛盾:一层阴霾覆盖在他青春焕发的容貌上,“光明与黑暗、生和死,在他身上进行着搏斗,因而同时出现了高雅和下流”。(第6页)
《驴皮记》中的二元对立体系构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文本世界。如果说小说中的法宝所表现出的二元象征意义犹如一幅图案中的主线条,那么,在它周围展开的一系列隐藏的对立价值组合就好比图案中与主线条相配的一系列暗线条,它们交相辉映,构成一个统一体。在19世纪初的法国,矛盾异常激烈,在许多作家眼里,当时的社会是非颠倒,他们怀念失去的“乐园”,对现实充满忧郁的情感。忧郁也是自始至终笼罩在《驴皮记》中的感情基调,“忧伤”(“le chagrin”)一词贯穿全篇,连小说的中心法宝——“驴皮”——也含有此义。
从某种程度而言,拉菲尔就是一个怀旧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高傲的贵族青年,他以拉菲尔·德·瓦郎丹侯爵自居,以家族昔日的辉煌为荣,让人们相信他是瓦郎斯皇帝的后裔。他心目中向往的情人是一个富有、高雅、有贵族头衔的女人,他认为一个女人要有公主的举止。拉菲尔的遭遇让我们想起法国19 世纪另一位作家维里耶(Villiers
del'Isle-Adam)的志怪小说《未来的夏娃》中的主人公。 同拉菲尔一样,他也是一个贵族青年,也因为对爱情绝望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所爱的对象和拉菲尔的福多拉一样,外表迷人而心灵丑陋。为了阻止拉菲尔的轻生念头,古玩店老板建议他接受法宝驴皮;而维里耶小说中的科学家爱迪生为了同样的原因建议埃瓦尔德接受一个外表和心灵同样美的机器人。《驴皮记》里的法宝不是尽善尽美的东西,它满足欲望的代价是生命;机器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它毕竟是一台没有血性的机械组合体。但是驴皮和机器人都是梦想的寄托物,是理想主义逃避现实的慰藉品。只是,梦终究要结束,最后等待它的是残酷的现实。
虽然巴尔扎克始终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但他的志怪小说的创作目的并非在于动摇理性思维,而是要传达象征意义和哲理性,这也是《驴皮记》能够在法国志怪文学中占有一席特殊地位的原因。
在巴尔扎克看来,意念、思想是人最大的敌人,它们是烈火;少思少虑是长寿的秘诀。他所说的思想是指邪念、过度的忙碌、痛苦、享乐。《驴皮记》的寓意之一正是“知足者长寿”。文学创作正如享乐一样,是一个可怕的能量消耗过程。巴尔扎克应该很清楚这一点。然而,他还是在长寿和消耗生命的创作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并非不知道自己为实现文学之梦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因而,就巴尔扎克本身的行为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抉择。
标签:巴尔扎克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超自然现象论文; 驴皮记论文; 文学论文; 法国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志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