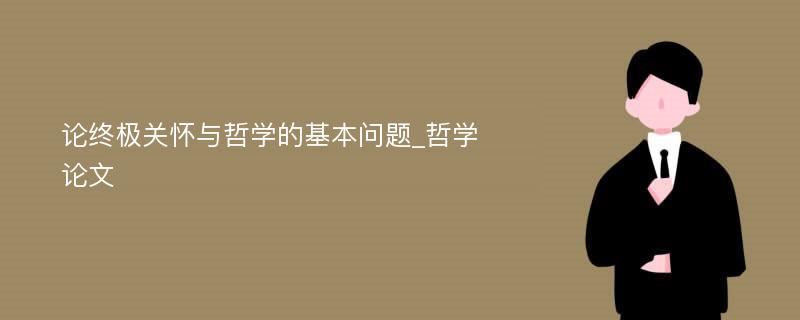
论终极关怀与哲学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类的“终极关怀”的基本问题是由人类共性发展趋势的共同的指向所决定的,这就是求真、崇善、爱美。在回答“何者为真、善、美”的“终极关怀”问题的同时,必然也必须回答“如何达到真、善、美”的问题,而这就是“超越之路”问题。因为要达到真、善、美,必须超越假、丑、恶,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必然关联到“超越之路”的设计。迄今为止,世界上影响深远的各大哲学体系都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可以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而且必须是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和对“超越之路”的设计。通常所谓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只是人类“终极关怀”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其涵盖面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把物质赋予实体的涵义后,就把哲学本体论局限于实体论的范围内,把它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无异于在给哲学研究对象画地为牢,是不利于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哲学研究的深入的。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更不能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思维本身也是一种存在,两者根本构不成一个矛盾统一体。两者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都无法使哲学成为人学,而哲学本来是、也应当必须成为人学的最高理论基础和最高根据。因此,哲学只有在基本问题上来一个根本性的观念更新,使之真正转移到人学的轨道上来,才能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启迪智慧的钥匙和“开物成务”的利器。为此,就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世界范围内和全部哲学史上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类型和模式。
二
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和对“超越之路”的设计,关系到全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以不同的形式涉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对涉及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自我意识进行形而上的反思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就是带有各个民族自身特色的哲学。尽管特色不同,但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必然是关于“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和对“超越之路”的设计,所以哲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由于各个民族生活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不同,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其形式、侧重、具体思想内容和理论结构模式各有特征,对“超越之路”的设计,其途径方法也各有不同。这些归结到一点,即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有所不同。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应当而且必须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正是由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模式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各个民族在思维模式与认识方法、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审美观念与抒情方式等文化传统上的各个方面才显示出自己本民族的特征。
三
哲学作为民族精神支柱,其社会作用平时是隐而不现的。但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作为各种观念、信念的最高理论根据的哲学观必然在最关键的时刻起最关键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这是意识形态中的任何其他因素所不能替代的。低估、轻视、排斥哲学的社会作用不仅是愚昧无知的表现,而且必然陷入最反科学的所谓“哲学”的泥沼之中。而哲学社会作用在历史上往往很少健康发挥,因为哲学和宗教一样,一旦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以后,就可以为实际运行的政治制度的代表者用来为其从政治实用主义目的出发而进行欺骗说教甚至对被统治者横加罪名的依据。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搞“一元化(即唯一模式论)”,抹煞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传统的特点,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助长了把一种哲学体系不适当地推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的错误倾向。历史无数次证明,具有至上权威的哲学一旦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就不可避免的被扭曲变性,背离原来的主旨、要义。
四
从宏观角度分析古今中外哲学史上存在的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不同模式,不难发现东方(以中国哲学为代表)和西方(地中海文明圈)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总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一种模式,而且是以西方哲学(特别是欧洲近代哲学)为根据而做出的概括,并不能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到世界所有哲学体系上,特别不能硬套到中国哲学体系之上。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考察和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从根本上和西方不同,而思维模式上的特征又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由此完全可以断言: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哲学。不加分别的机械套用,是100多年来的“西学东渐”所造成的“中学西范”心理模式在作怪。
五
以“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为哲学基本问题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的特征。这个特征的指向是把回答“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作为“终极关怀”的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问题,而事实上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绝不只是这一个。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中的他人、人与自我内心世界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作穷根究底的形而上的反思的时候,都可以也必然能够形成带有一定特色的“终极关怀”问题,从中也会很自然的引发出一整套的哲学体系来。数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正是用这种本质上是西方模式的理论框架来“削足适履”地硬套中国哲学,从而扭曲和掩盖了中国哲学的真实面貌。因为中国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上所关注的是“现象”(phenomenon)和“关系”(relation),所要回答的“终极关怀”的问题是:“万物之情”、“神明之德”、“大化之道”三种现象之间的关系“何以如此”,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一味地去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世界的本质和本源问题,中国哲学历来认为是存在于“六合之外”,只需承认其“存在”就够了,对问题本身无须探讨,完全可以“存而不论”。中国哲学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天我相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哲学所强调的主体与客体、天与人、空与实、物与我、人与己、灵与肉、此岸与彼岸等等一系列的对立与分割,在中国哲学这里统统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下兴起了哲学基本问题模式转向的热潮,在这一口号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哲学体系,如存在论、现象论、结构论、逻辑式争论、符号论,等等;所有这些哲学体系在学术风格旨趣、终极关怀指向等方面都有一个与18、19世纪哲学完全不同的风貌,即不再去纠缠什么“物自体”,而专注于现象与关系,把哲学从专门关注实体论的本体论的狭小圈子里走向广阔的天地。这个趋向就为其和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在总的趋向上有了从接近到交融贯通在深层理论基础上铺平了道路。因为回到康德去实际上就是否定了从古希腊以来以重实体为趋向的西方哲学传统,这样,很自然地在哲学基本问题模式上向中国哲学接近和靠拢。因此,“回到康德去”是一个正确的口号,因为它为东西哲学的交融会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21世纪已经到来,在新的世纪里,哲学的发展趋向如何?这是哲学界众所关注的问题。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交融贯通的世纪。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哲学基本问题模式独霸的时代必将随着经济多元化而式微。哲学的认识方法,即启迪智慧作用将大大加强,伦理哲学和艺术哲学在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净化人们的灵魂方面将逐步取代传统宗教的功能。全新的汲取东西方哲学精华的更带有全人类普适性的哲学将显露端倪。新哲学是面向全世界、全人类的,其趋向绝不是单纯的“东”或“西”;新哲学也许将真正走出专门学者的书斋和政治家的殿堂,真正成为芸芸众生“爱智”的追求。哲学作为一种专门职业被消灭之日,也就是哲学的光辉普照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