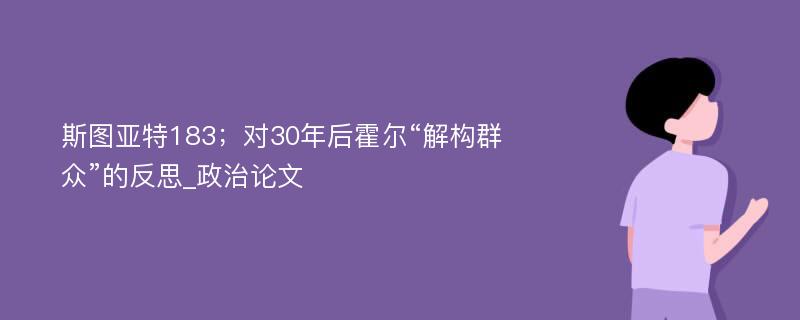
斯图亚特#183;霍尔的“解构大众”30年后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图亚特论文,霍尔论文,大众论文,年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媒介及文化研究者而言,当下日渐复兴的大众政治运动无疑已成为最为复杂难解的社会现象之一。近年来,无论是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中东地区爆发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抑或当前希腊愈演愈烈的反紧缩政策大抗争,这些风起云涌的集体政治运动在变得日益高涨的同时,也令全世界感到震惊。伴随着网络媒介技术及其传播制度的深刻影响,类似运动的参与者们开始学会利用各种网络媒介传播方式,以使政治运动与大众文化水乳交融。然而,大众政治运动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仍然矛盾重重。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最为明显的悖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文化生产仍旧遵循着其固有的结构,而这种文化生产只会延误社会变革并继续维持个体日渐疏离的生存状态。有鉴于此,尽管许多社会斗争惯于将政治与大众文化二者联姻,但是这种联姻却有蜕化为民粹主义运动的风险,而民粹主义不仅阻碍了实现民主主义的各种可能性,而且还固守甚至加剧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褫权(disempowerment)形式。 本文旨在描述、分析并揭示出当代英美语境之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正如爆发激进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正在与日俱增一样,这里所指的复杂性体现为某种特定的社会问题必然会与各种积极干预的社会势力相互交织,而一旦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没有遭受直接镇压,就会使社会异议得以持续升级。本文承袭了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逐步形成的有关媒介和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将“大众”视为集体运动和个人参与的重要活动场域,并且“大众”以一种横断面的方式直接勾勒了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损益(push and pull)关系。在《解构大众笔记》(“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中,霍尔借鉴了葛兰西旨在分析意大利社会问题的“霸权”范畴,并且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社会语境相适宜的重要分析方法(可参见霍尔于1978年主编的《监控危机》一书,该书对此分析方法进行了极佳的阐述)。在《解构大众笔记》中,霍尔留给我们一段有关政治与大众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著名论述:“在研究大众文化方面,我们唯有以此起步:须知大众文化具备双重支点,即其内部必然包含遏制(Containment)与抵抗(Resistance)之双向运动。”① 《解构大众笔记》最早发表于1981年,尽管霍尔以极为谦逊之心将其仅仅题为“笔记”,但是这份笔记自发表以来便不断得到其他作者的选录与引证,可以说它在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尽管学者们对大众文化产品的研究已经明确成为媒介和传播学研究下属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这些分析本身往往暗含着一种对“大众”的静态定义。尽管在媒介对构造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许多研究对与此相关的媒介表征和媒介消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但是几乎都没有切中伯明翰学派定义“大众”的方法传统。事实上,并不能以与媒介有关的场域及文本形式来定义“大众”。在霍尔看来,“大众”必须通过“权力关系”的维度来定义,而这种权力关系则是彼此相连的特定对象、主体性及其制度所共同铸造的产物,而大众文化体系则是集体机构与集体活动的重要行为场域。尽管文化表达、社会形态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难以捉摸,但是霍尔强烈主张,如果非要对“大众”进行定义,必须诉诸对上述三者关系的深层挖掘。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构筑当今大众文化的社会根基已然发生了变化,而对于这种变化的把握是对大众文化进行危机分析的必经环节。有鉴于此,本文并非只是对霍尔及其当代文化研究之诉求的简单重构。正如霍尔及其伯明翰学派的其他同事所进行的研究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特殊语境一样,本文同样必须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新视角来解读当下的社会问题。尽管我们还在使用“大众文化”一词,并且对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较为熟识,但如今距离霍尔发表《解构大众笔记》一文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而霍尔在该文中借以分析社会事件所使用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大众”阐释模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而我们有必要对霍尔的经典方法进行一次反思与扬弃。出于这个原因,本文并未将霍尔的研究方法视为过时的老古董,而是试图论证当代学者重新解读霍尔的大众文化概念的价值所在。 以此观之,我们对待霍尔的作品绝非仅仅是为了论证革命而引经据典,而是转用其中的方法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实际上,霍尔的此种方法也是从马克思和葛兰西那里转化过来的)。该方法关注政治、统治技术和抵抗策略的偶然性。当霍尔通过重读葛兰西的著作来阐释撒切尔时代的英国社会现状时,在他看来,“对于已经凝聚起来的集体政治认同(比如阶级)以及已经成型的政治抗争形式而言,政治并非只是一个对它们进行简单折射的舞台”,而是“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内的权力关系的展现,这种权力关系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来不断生产权力和控制的特殊形式。而这就是政治生产——政治本身也成为一种产品”。②霍尔对作为偶然事件的政治(以及大众)的概念化一以贯之地引领着其对集体政治机构的文化关系所进行的透彻分析。不过,适合“大众”的集体性主体是“人民”(the people),而该术语的典型属性即是它依旧“没有固定的内容”。然而,倘若以今日的眼光来阅读霍尔的话,读者们或许会觉得他显得有些“稀奇古怪”,这里涉及的阶级概念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带有机械论色彩的铁证。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回忆一下霍尔思考“阶级”的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即诸如“大众”、“人民”及“政治”等概念都带有历史偶然性。 因此,就“大众”这个概念而言,不是将其视作历史得以不断延伸的舞台,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构成阶级或集体力量的潜力——这才是政治和文化抗争的本质:让分裂的阶级与分散的人民凝聚成为一股大众民主文化力量的洪流”。进一步而言,这也就是为什么那种以特定舞台或表达形式所进行的大众文化定义无法取代政治的原因;因为,它无论是在概念定义上还是分析方法上都没有切中政治的本质。然而,尽管此二者的关系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但政治几乎无法在没有大众文化参与的情况下发生,因为文化毕竟是大众存在的重要形态,而且它是政治参与者及其政治活动的基本场域和重要内容。而恰恰是因为霍尔强调大众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复杂性、偶然性,甚至是时常出现的矛盾性,因而他对于将大众研究作为目标本身并“不十分在意”。 由于霍尔极力推崇政治的偶然性与情境性,因而他最初所假设的许多范畴更能适用于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分析。尽管许多文化已经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詹金斯称之为“融合文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霍尔的大众概念彻底失效了,当我们利用霍尔的方法来分析当下问题时,甚至会发现它在复杂性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文化和政治中存在着一些具有丰富资源的参与者,他们可能会不惜重金聘请网络公司来进行“声誉管理”,而这与草根政治运动基金在传播集体吁求并争取社会变革时的情况极为类似。然而,大众可能仍然充当着组织、管理和传播集体行动的最为有效的构造工具。 笔者认为,或许我们可以与那种拥有大众参与的新自由主义紧密合作;这种新自由主义具有清晰的经济规划,是一种旨在组织、管理和传播特殊的集体机构和集体行动的社会和政治方案。在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就兴起了这种今天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而当我们重新阅读霍尔当时旨在分析英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大众文化时,我们会发现,尽管《解构大众笔记》一文对此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毕竟此文只是一篇“笔记”),但是霍尔确实尝试去分析并影响当下的这种社会变革。大卫·哈维就曾指出,尽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危机爆发之后,它才被世人正式理解为一套具有社会形态联盟属性的社会理念;而在北美与欧洲地区,这种持续不断的社会危机掺杂着一系列急剧变化的政治联盟和重要事件,从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民主党和新工党、法国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阵线,到反全球化或另类全球化运动、“9·11”事件、茶党、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等。 然而,在当代特定的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假如利用霍尔对于大众的特殊定义来引领对权力关系的批判性文化分析,我们就必须认真看待霍尔对于不同历史分期的权力关系的分析,而这其中无疑涉及文化与传播。任何有说服力的大众文化分析都必须考虑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关系,并且还需要认识到这些政治关系具有地缘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此类学术就只能提供一种对大众文化的漫画式的简单复制,而这种复制只是一种故调重弹(新自由主义是既有的,政治则是随后的点缀)。此类学术时常认为大众文化研究是非政治的,但是又心满意足地认为文化当中的“政治因素”当然也是题中之义。 一旦我们以带有历史偶然性的大众概念来理解集体机构的构成,就很难理解当前那些趋向激进民主变革的运动没有任何传播技术的参与。正如霍尔等人曾经指出的那样,传播技术是一场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行的重要平台。然而,也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传播技术与媒介产业的紧密结合被定义为对构筑团结之潜力的认识与传播革命潜力的工具二者之间的矛盾。今天仍是如此。例如,近来有人主张,作为民主式的民粹政治的新形式,“融合(媒介)文化”以及“生产者—消费者一体化”的乌托邦方式是一种天真的误解,因为它错误地认为“聚合的和竞争的政府网络把目标锁定在特定人口上(进行监控与管制),围绕着政府在技术和合理性方面的不稳定性问题进行统计,并将自由具化为政治民粹主义”③。 近来,詹姆斯·海(James Hay)开始以民主自由及其与媒介技术之关系的名义将新民粹主义理解为“参与”(participation),例如,整合了传统媒体的网络将民粹主义的参与变得可操作化。无论是茶党还是“求真相的快艇老兵”(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④,融合文化有助于我们所谓的民众(demotic)参与——而非民主(democratic)参与——技术的扩散。这些参与形式的规则和逻辑往往并非显而易见,但却包含着而非有助于实现民主形式的组织和行动。当然,要大众(以及人民)支持结束非民主的状态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以美国为例,这要追溯到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转变,这些社会变革与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寡头政治和技术统治紧密相连,共同反映了公共关系、职业记者以及群众心理学的崛起。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曾对有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反思,认为英国民粹主义中针对“普通人”(ordinary people)的“召集”(summoning)和“注册”(enrolment)显然已经被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搞得支离破碎,而此类研究方法无外乎两大类:其一,“关注惩罚性政府和调控性文化”,其二,“关注统治行为的扩散形式和中介形式”。克拉克强调,这些借助政府至上主义(governmentalist)策略来召集“普通人”的社交网站,其共性仅仅在于这些策略的效力基本上都是偶然的。 为了描述当下各种政治民粹主义与社会统治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两大类研究方法潜藏着一种隐性对峙状态,一种是强调大众的符号学或意义方面的重要性,另一种则是以生命政治学的方法来关注人的情感状况。“或许人们会辩称这两种方法都将我们牢牢捆缚住了,并且将我们人类弄得四分五裂——要么视为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要么视为某种聚合物或聚合物的元素,要么视为某种主体性群体(subject-group)或其构成要素,要么视为多样性和杂多存在。而这也是一种在达成共同意义的过程中毫无意义的反意指(asignifying)经历。”⑤正如海的分析所论证的那样,就这场辩论本身的形成而言,政治机构的基础正危机四伏,并且就它们的关系而言,大众分析正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惑。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在政策研究语境下对福柯式治理术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析大众之谜题。在政治与政策的关系方面,斯特恩考察了“在政治改革和解放(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的人本主义哲学与利用权力暗中破坏这种表征政治的反人本主义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⑥毕竟,在缺乏提升自我意识的形式以及缺乏传播技术(除非我们只进行人际传播)的情况下,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上来看,政治走向都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我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域中那些具备颠覆性的制度规则、实践逻辑或竞争逻辑是如何形成历史性联盟的。另外,尽管对当代文化在各个方面所呈现的情感状况的理解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洞见,但是后符号化(postsignifying)与后霸权(posthegemonic)的方法已然将政治学引入社会工程与治理术领域(或者引入对传统政治选举的设置存有争议的潜在的非代表性选区之中,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然而,我们也无需假设对于这些趋势的分析就不能彼此进行相互综合的互补。实际上,人们可以参见默里·福尔曼(Murray Forman)对于头巾文化(Hoodwork)的分析,福尔曼将其视为试图利用嘻哈文化及其意义(通过其粉丝、设计师及媒介物)来治理参与者的复杂斗争领域,而这就有了些许社会斗争的感觉,于是参与者的努力及其活力就不再被这种刻板的模式所俘获。同样,乔·利特勒(Jo Littler)对于当代英国母亲的探讨也为我们揭开了后女性主义的碎片化形式,后女性主义关注母亲的亲身经历,这种经历是与大众保守主义(popular conservatism)交织在一起的,它包含并传递了地方与全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团结一致。 无论人们能否以一种更为葛兰西式的或者更为福柯式的方法(或者以我们在此囿于篇幅限制而无法列举的其他方法)来直面大众和民粹主义⑦,都应该容许以不同的方法来分析大众的全球性抗争。文化传播学者们或许会质疑,究竟这些有关大众的观点是如何解释当代政治机构的,比如朗西埃(J.Ranciere)的“人民”(the people)与寡头政治,或者哈特(M.Hardt)和内格里(T.Negri)的“群众”(multitude)。有鉴于此,我们还是以近期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和政治风潮来尝试回应希腊财政危机大抗争以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学者们或许会思考是否诞生了一种所谓的“全球性大众”(international popular),并且他们正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之下奋力抗争。因此,我们认为霍尔的大众概念对于当下世界局势中的文化研究依然适用,尽管它已经与霍尔原初发展此概念的英国本土语境相去甚远。 *本文原载国际传播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出版的期刊《传播、文化与批判》(Communication,Culture & Critique)2013年第6期。 注释: ①S.Hall,"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In J.Storey,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3rd ed.),Harlow,England:Pearson,2006. ②S.Hall,"Gramsci and us",Marxism Today,June,1987,pp.16-21. ③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海认为霍尔的葛兰西式的大众概念在当前的社会局势下依然适用。海的观点也包含了保罗·威尔诺(Paolo Virno)对诸众概念的论述,即对群众(multitude)、大众(popular)、全体国民(body politic)与人民(people)的区分。 ④2004年美国大选时,政治团体“求真相的快艇老兵”(Swift Boat Veterans for Truth)曾投放大量电视广告,以越战老兵的身份质疑民主党候选人克里越战事迹的真实性,使克里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译者注 ⑤J.Gilbert,"Signifying Nothing:'Culture','Discourse',and the Sociality of Affect",Culture Machine,6,Retrieved from http://www.culturemachine.net/index.php/cm/article/viewArticle/8/7,2004. ⑥J.Sterne,"Cultural Policy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The Communication Review,5,2002,p.61. ⑦囿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深入论述那些在公众、宣传、人民、集体及舆论方面都进行过研究的学术观点,例如,这其中就包括哈贝马斯、塔尔德、布迪厄、德勒兹等人的各种方法,这些学术研究都与霍尔的大众概念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