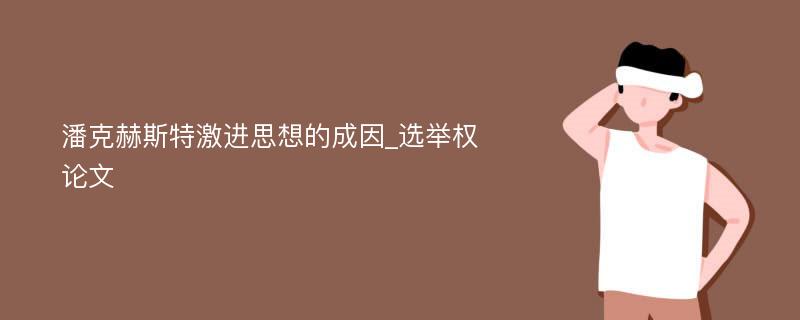
埃米琳#183;潘克赫斯特激进思想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斯论文,成因论文,激进论文,思想论文,埃米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8-0084-06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年)是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直至今天她在欧美大众心目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与其长女在1903年创立了著名的妇女参政组织——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以下简称同盟)。从1905年至1914年,为了扩大妇女参政运动的社会影响,给政府制造压力以获得议会选举权,同盟在埃米琳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进运动。她们从干扰政治家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到砸窗户、纵火、制造爆炸事件等,以及她们的绝食抗议行动,震撼了世人。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追求正义,视妇女选举权为妇女的不可或缺的天然权利,认为它是改变妇女命运的基石;二是强调公正的理念,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三是反抗权威,认为抗议和不服从是迫使政府让步的最有效武器。正是她的激进政治理念,改变了英国传统的妇女参政运动模式,使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本文试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长的背景以及她早年政治经历入手来分析其激进思想的形成,以便更好地理解20世纪初英国激进妇女参政运动的缘起和发展。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年7月14日出生于曼彻斯特的一个充满激进主义的殷实中产阶级家庭。曼彻斯特不仅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路先锋,而且是激进政治改革的中心,具有激进主义传统。这里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前沿阵地和社会暴动频发地区,1819年8月16日曾经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圣彼得卢惨案”。这一事件导致了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和宪章运动。此后,反谷物法联盟总部也设在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在全国不断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和请愿活动,最终导致了谷物法的废除。同时,曼彻斯特作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之一,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矛盾在这里也表现得最为尖锐,工人运动十分发达。曼彻斯特还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重镇。正如埃米琳的女儿西尔维娅在《潘克赫斯特的一生》中所说的,古尔登家族的孩子成长于英国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个“为宪政自由和人的思想和个性自由而战的振奋人心的时代”[1](p9)。反抗权威的传统和氛围,也深深影响了埃米琳的家族。
埃米琳的激进思想还与马恩岛有着密切的联系。马恩岛是位于大不列颠岛与爱尔兰岛之间的一个小岛。埃米琳的母亲索菲·简·克雷恩(Sophia Jane Craine)1833年出生在马恩岛一个敢于挑战权威的古老家族。埃米琳曾声称其激进思想至少应部分归因于马恩岛人的血统。马恩岛的妇女拥有较高的法律和政治地位,比英国妇女拥有更多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1881年马恩岛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她们比英国的同伴整整早了37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妇女以议会选举权的地区。马恩岛妇女成功地参与政治生活的例子,影响着埃米琳的母亲对妇女参政的态度。
埃米琳的父亲罗伯特·古尔登(Robert Goulden)的家族是一个英雄的家族,她的祖父母都积极参加过反谷物法的斗争,特别是亲历了1819年的“圣彼得卢惨案”。埃米琳的父亲热衷于各种公共事务,是曼彻斯特自由党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是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支持者,美国著名的废奴运动领袖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到曼彻斯特访问和作演讲时,他曾经接待了比彻。①埃米琳的母亲婚后在丈夫的影响下,也成为一名政治激进主义者,积极反对奴隶制度,并成为英国早期妇女选举权的倡导者之一。埃米琳回忆小时候母亲在临睡前常常给她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成年后的她一直都无法忘怀小说中美丽的女黑奴伊丽莎(Eliza)为了逃离奴役、寻求自由,打破俄亥俄河坚冰的情形。小说中描绘的奴隶所遭受的不幸,使她意识到追求平等的可贵和抗争的重要性。埃米琳的母亲不断鼓励她不仅要同情弱者,反对非正义,而且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她在个人自传中回忆了幼年时和母亲为废奴事业募集资金的情形:“当我还不到5岁的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奴隶’和‘解放’这两个词的含义。”[2](p1)
在母亲的启蒙下,少女时代的埃米琳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自觉的妇女参政者。埃米琳15岁那年,母亲带她参加了妇女参政协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是埃米琳第一次对妇女参政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她在自传中写道:“我被这些演讲的内容所吸引,甚至为此感动。”[2](p9)埃米琳对母亲充满感恩,认为母亲是真正把她领到妇女参政事业大道上的启蒙者和指引者。[3](p22)
埃米琳少女时代在法国的4年经历对其激进思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2年她被送到法国巴黎接受教育。埃米琳所在的学校是巴黎著名的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具有女性平等受教育的理念。在求学期间,埃米琳结交了她终身的好朋友、法国姑娘纳米尔·罗什福尔(Noemie Rochefort),纳米尔的父亲罗什福尔—吕凯侯爵(Marquis de Rochefort-Lucay)曾经是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纳米尔给埃米琳讲述了其父辈的英雄事迹,给埃米琳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埃米琳在巴黎学习期间,接触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的《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此书对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她认为该书的观点“激励和影响了她的一生”[2](p3)。卡莱尔认为,历史进程是无法预测的、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每个个体在面对未来时有更好的选择机会。他在论及政府时说,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建立在它能够正确地运用权力的基础上,一旦它不能正确地行使这些权力,否定人民的需要,人民就有权推翻政府。反抗政府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光荣的。[4](p123,132)卡莱尔在他的著作中还强调了领导人个人的魅力在实现社会理想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埃米琳在未来的妇女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的激进思想。[5](p13~14)
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埃米琳,就是在这样一种激进主义和改革氛围的环境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这个阶段为她日后的激进思想奠定了基础。
尽管埃米琳的父母要比当时英国中产阶级的父母开明得多,但是他们依然无法完全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观念,在女儿的培养问题上,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甚至保守的观念。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观念冲突:一方面,古尔登家族孕育了埃米琳的自由和正义的理念;另一方面,在教育上,父母又施以传统的规范来约束她。随着埃米琳的逐渐成熟,这种情形必然激起她对维多利亚式中产阶级女性生活的强烈不满。而理查德·潘克赫斯特(RichardPankhurst,1838-1898年)的出现,使她的人生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作为一名激进的律师,理查德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他对社会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疾恶如仇,强烈希望改革现存不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中就包括改变歧视妇女的各种法律规定。理查德是曼彻斯特妇女参政全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他积极参与妇女的参政运动,为妇女争取权利做出了各种努力。1867年,在他的帮助下,曼彻斯特的妇女组织获得了选举的注册登记权。1870年他参加了《妇女解放法案》的起草,提出要消除把性别作为是否授予投票权的资格的做法。他还是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起草者,1882年《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通过正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1888年英国已婚妇女获得地方议会的选举权,也与理查德帮助她们建构法律的框架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理查德是一个彻底的妇女参政者。
埃米琳通过跟随父亲参加理查德的政治集会而有缘结识这位激进的政治家,渐渐地,理查德成为埃米琳心目中的英雄。1879年9月8日,理查德就妇女运动问题致信埃米琳:“正如你所知道的,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行动就是给妇女更高的教育……你必须要关注到这一点。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试图找到一个能使教育成为真正有效的方案。”[6](p21)这封信成为埃米琳和理查德恋爱的开始,以后双方经常就彼此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讨论。从此,埃米琳进入了理查德的激进的世界。
1879年12月18日,埃米琳和理查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富有自由激进思想的理查德没有按照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去要求埃米琳,相反,他鼓励埃米琳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并不希望埃米琳变成家务劳动的机器,而始终认为除了家庭,社会同样需要女性做出努力。[2](p13)正如他婚前的信中所言,“每一项斗争事业都将是我们共同的事业”[6](p21)。埃米琳和理查德的结合,使她青少年以来形成的自由理念得以实现,也对她的未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因为正是和理查德的结合,埃米琳开始正式进入政治生活。
在理查德的鼓励和引导下,埃米琳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关注妇女参政问题。他们的家常常成为激进主义者的聚会场所,许多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在这里发表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们讨论的话题,从妇女权利、废除上议院、激进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到不可知论和新工会主义等,无所不有。来访者中有激进的自由党议员雅各布·布赖特(Jacob Bright),著名的工党领导人、社会主义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安妮·本森特(Annie Besant),社会民主联盟的领导人之一汤姆·迈恩(Tom Mann)。②此外,俄国的政治避难者、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苏格兰工党领导人凯尔·哈迪(Keir Hardie),未来的工党领袖、两度任英国首相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也是这里的常客。美国妇女参政者和废奴主义者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oyd Garrison),埃米琳在法国时期的心中偶像、当时正流亡在英国的巴黎公社女革命家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还有德国的革命者卡尔·威廉·李卜克内西(Karl wliebknecht),都曾经到潘克赫斯特夫妇的家造访。[3](p33)各类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思想主张和学说,使埃米琳大开眼界,也使她对激进的社会民主运动有了充分的感性认识。
埃米琳加入新生的独立工党后经历的事件对她日后“要行动”的激进政治理念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独立工党在成立之初,由于资金的缺乏,根本没有开会的场所,经常只能在户外举行集会,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曼彻斯特的克拉夫(Clough)公园。1896年5月17日,独立工党在此集会演讲,其发言人被警察以扰乱公园秩序罪传唤,由于他们拒交罚金而被捕入狱。此后,埃米琳作为唯一的女性和其他工党成员多次来到此地继续演讲,抗议当局的行为。由于男性演讲者陆续被捕,埃米琳被推到政治斗争的前沿,成为集会的主持发言人,其不俗的表现使这场斗争继续保有活力。面对屡禁不止的集会,地方当局恼羞成怒,通过法律附例,宣布未经公园同意禁止在此集会。8月16日,独立工党成员在克拉夫公园举行了盛大的抗议活动,有2.5万~4万名民众参与集会。这种情形迫使内政大臣拒绝同意地方当局的附例,因为他们担心该事件可能会发展为全国性风潮。独立工党的此次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埃米琳认识到:只有抗议和不服从,才会迫使政府做出让步,而扩大社会影响就是让政府屈服的有力武器。[7](p17)可以说,这场经历强化了埃米琳以激进的方式对待现实社会的政治意识。
埃米琳还协助丈夫进行了三次议会竞选,这些活动的参与对埃米琳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活动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1885年的第二次竞选活动,它对埃米琳激进战斗策略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1885年的大选之年,理查德作为自由党代表参加了竞选。尽管此次选举有自由党的支持,但理查德最终还是输给了保守党的代表。埃米琳把这次失败归咎于爱尔兰自治者的影响。她认为,在选举中,爱尔兰选民在自治党领袖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的引导下拒绝投票给自由党——即使自由党的代表是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而把票投给了保守党。虽然埃米琳的分析未必完全正确,但是理查德的确成了自由党全国政治和爱尔兰自治分子搅乱的牺牲品。19世纪80年代中期,自由党面临诸多的问题:爱尔兰的自治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对抗,土地国有化,教育和地方政府的改革,税收问题以及帝国政策。这些问题日渐成为人们抱怨的焦点,很多地区出现反自由党的选民,即使在自由党势力强大的地区,也出现被保守党势力蚕食的现象。但1885年的大选却出现了微妙的局势:自由党获胜,比保守党多出了86个议席,而帕内尔的爱尔兰自治党在这次选举中恰好得到了86个议席,如果他们站在保守党一边,自由党的多数席位就丧失了。因此,爱尔兰自治党得到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谁赞成他们的主张,他们就可以让谁掌权。首相格拉斯顿清楚地明白这点,他于是决定让爱尔兰自治,认为这是维护帝国统一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自由党掌权的唯一办法。爱尔兰自治党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局势,对于埃米琳的政治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说:“这样一个小党,几乎是没有可能从绝大多数的敌对中赢得自治的,但是帕内尔及时用他所能用的种种方法使政府屈服。这是可资借鉴的政治经验,今后要为我所用。”[2](p18)
潘克赫斯特夫妇共同的政治取向,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伴。他们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并期望能够通过选举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寻找到自身的社会政治价值。
1894-1903年,埃米琳把自己主要的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独立工党的工作中。这个时期是埃米琳独立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也是她政治意识日趋成熟的时期。在这之前,她是以潘克赫斯特夫人的角色协助丈夫参与各类社会政治活动的,而今她的个人政治身份开始显现,并在地方政治中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埃米琳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兴趣与日俱增,特别是与独立工党领袖凯尔·哈迪的友谊,影响了她的价值取向。她被当时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深深吸引,并把它视为“修正每个社会和政治错误的手段”[6](p32)。她决定加入独立工党,寄希望于工党改变贫穷妇女所遭受的不幸,并能够支持女性的议会选举权。因为埃米琳对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反对给妇女选举权心存芥蒂,在她看来,自由党只是一个让妇女为其服务的男人的政党,所以,埃米琳与自由党分道扬镳。这对她而言不仅是一次党派和组织的选择,更是一种政治取向或政治理念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埃米琳独立政治意识的形成。
此时,独立工党领导人鼓励其成员进入地方政治,以便能够进一步帮助穷人,特别是鼓励其成员参加济贫法监护人的选举活动,希望借此改变工厂条件。埃米琳积极响应,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济贫法监护,都有助于当地工人阶级改善生活条件,并且有助于妇女了解议会制度,锻炼政治才干。她曾经这样建议年轻女子:“她们应该先从地方政府做起。地方政府的工作将会使你了解民众最真实的一面以及他们的真实需要。而通过在地方自治机构的工作,将有助于你了解议会制度。”[8](P5)
1894年,埃米琳以独立工党代表身份毫无争议地当选为奥彭肖(Openshaw)的济贫法监护人。当时的中产阶级妇女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并不令人愉快的工作,因为必须经常面对那些处于最困顿的社会群体,“必须到救济院去看望那些医院都不想护理的病人:那些忍受病痛和精神折磨者、流浪者、厚颜无耻者、堕落者、酒鬼、被虐待者”[9](p229)。只有像埃米琳这样具有仁慈、坚韧和非凡勇气品质的女性,才能担当起这样的工作。通过济贫法监护人工作,她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妇女的悲惨境遇。她在担任曼彻斯特独立工党济贫法监护人期间,参观了曼彻斯特地区的很多工厂,亲眼看到女工、童工的悲惨境遇。20年后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这样的场景:“当我第一次进入工厂,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严寒的冬日里,一些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跪在冰冷的地上擦拭长廊,衣着单薄的她们瑟瑟发抖。”[2](p25)不仅如此,那些临近分娩的女工仍然进行着艰苦的劳作,她们当中甚至有的还是未婚的单身母亲。她说:“这些可怜的妇女为了生存,在医院分娩两周之后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为了日后的生计重返工厂,忍受和孩子分离之痛;要么离开工厂,怀抱婴儿流浪街头,无家可归。”[2](p27)担任济贫法监护人,强化了埃米琳的政治意识,使她强烈地意识到,妇女只有获得选举权,才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而只有通过妇女的参政运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她说:“在我成为济贫法监护人之前,我已是一个妇女参政者,但是正是担任济贫法监护人的工作,使我开始意识到,女性拥有选举权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迫切的、不容置疑的需要。正是那些无法得到保护的贫困母亲和婴儿的悲惨境遇,激励我成为战斗的参政者。”[2](p28)
1900年,埃米琳作为独立工党的代表被选为曼彻斯特的教育督导。地方督导职位的设立主要是为了配合1870年《教育法》的贯彻实施。曼彻斯特是第一个成立教育督导委员会的城市,该委员会也是当时英国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督导的设立给妇女参与地方政治提供了新机会,妇女可以通过选举成为教育督导。尽管埃米琳在当时很多致力于妇女教育改革的女性主义者心目中并不是一个教育者,受到了一些轻视,但她毫不介意,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致力于推进工人阶级的教育事业。这份工作强化了她女性主义的观念。她发现,女教师明显处于劣势,不仅工资低于男教师,且在常规的课目外,要额外承担家政课程。为此,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902年《教育法》废除了教育督导制度,代之以新的体制。埃米琳认为,这是对妇女代表的一种侮辱,妇女不再有资格进入地方政府的教育机构。在她看来,导致妇女在地方政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妇女没有选举权。在妇女地方政府协会和全国工作妇女联盟的共同压力下,政府做出了让步,同意地方教育当局允许女性成员参与。1903年4月,在独立工党的力荐下,埃米琳成为曼彻斯特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4年,并被任命为曼彻斯特技术学院的指导。曼彻斯特技术学院是欧洲排名第二的技术学院,每年要花费数千英镑的费用用于男性的技术培训,却不为女性提供任何技术培训。由于男性工会反对给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只有面包和糖果制作技术的培训才允许妇女加入。[3](p34,35)埃米琳认识到,这是男性把女性置于服务的位置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更加坚定了她为改变妇女社会政治地位而斗争的决心。
然而,这一时期埃米琳的家庭出现了变故。1898年7月5日,理查德病逝。丈夫的去世使家庭生活陷入了窘境,为生计所迫,埃米琳辞去了济贫法监护人的工作(该职位不带薪酬)。不久,她承担了一份带薪的工作,负责地方政府中的婚姻、出生和死亡登记注册。这一职位使埃米琳有更多机会了解妇女的生活境遇。她所在的工作区域是工人阶级集居之地,因此在担任注册员期间,她和众多女工有了面对面的接触,所见所闻她们各自的不幸遭遇,促使她决心要让妇女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社会中生活。
这个时期埃米琳通过承担各种社会工作,开始了独立社会政治活动的生涯。其间,她通过从事各类社会公共事务来努力尝试实现她的一些激进思想,在这些社会政治活动中不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独立工党委员会中的工作以及担任济贫法监护人和曼彻斯特教育督导等的经历,培养了她的政治能力和自信心。通过接触大量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她强烈地意识到社会现实的不公正,意识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早期的政治生涯和经历,极大地促成了埃米琳激进的妇女参政思想的形成。她把妇女选举权视为妇女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天然权利,认为这不仅是女性成为公民的通行证,也是一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标志。“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着各种义务,就应该享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和参与法律的制定。”[10]埃米琳认为,选举权的获得对女性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选举权的获得首先是一种象征,“是自由的象征,公民身份的象征”;其次是“获得自我权益的保护”,通过纳入政治体制之内来保障妇女的各种权利;再次,它是一种“武器”,是改变妇女不平等境遇和不合理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7](p31)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埃米琳激进思想形成于英国的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争取民主权利成为社会和思想的主旋律。童年的家庭环境孕育了埃米琳追求平等正义、不畏强暴的激进理念;少女时代在法国求学的生涯,使她深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激励;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的婚姻,则为她投身政治提供了舞台,使其激进思想进一步确立;早期独立的政治生涯,使她进一步意识到妇女参政的紧迫性以及行动抗争的有效性,其激进思想最终形成。当英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宪政努力毫无成效时,埃米琳认为,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于无声处听惊雷!她要通过激进的行动来让英国全社会认识到妇女选举权问题的重要性。她坚信,只有通过战斗,才是走向胜利的最基本途径。正是这位看似美丽娇弱的女性,重新点燃了趋于沉寂的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之火。
注释:
①亨利·沃德·比彻(1813-188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自由派牧师、废奴运动领袖,主张妇女参政,赞成进化论。其姐姐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撰写了著名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②雅各布·布赖特是英国自由党激进的议会成员、女权主义者,曾在议会中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大声疾呼。约翰·伯恩斯是1889年英国码头工人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安妮·本森特曾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在1888年领导火柴厂妇女举行大罢工,反对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低工资,是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汤姆·迈恩是八小时工作制的积极倡导者,也是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为英国重要的工会主义者,1894年成为新的独立工党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