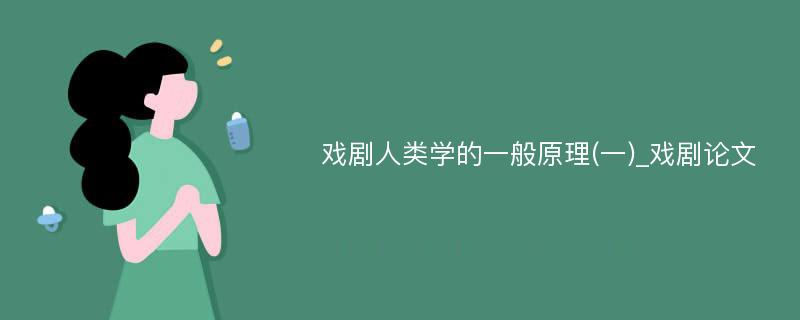
戏剧人类学的常见原理(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戏剧论文,原理论文,常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剧人类学是一种为表演者而进行的关于表演者的研究,属于实用科学。其有用之处表现为:使得创造过程可以为学者所介入,并增加表演者在创造过程中的自由度。
让我们从考虑两种不同的表演者类型开始,根据一般思路,它们被界定为东方戏剧表演者和西方戏剧表演者,这是一种错误的分法。为避免产生与特定的文化和地域之间的错误联想,我们将翻转罗盘,置其于想象层面,称之为南极与北极。
北极表演者显然不那么自由。她或他按照一个充分验明的规则系统来塑造她或他的舞台动作,而这个规则系统用以定义一种风格或一个编排就绪的剧种。这种肢体或声音行动的代码(不管是芭蕾的,还是某种亚洲古典戏剧、或现代舞、歌剧、或哑剧的),定位在自身的独特而又细节化的人为性之中,易于接受演化与革新。
然而最初,每一位选择了此类戏剧的人必须遵循这个规则系统,以自身的非个人化来开始他们的学徒期。他们接受一个由传统建立的舞台角色的样板,而这个样板角色的个人风格化将成为他们艺术成熟的第一丝迹象。
南极表演者并不属于这样以细节化风格代码来界定的表演类型。没有全套现成的特定规则需要他们恭敬以待,表演者必须自己建构支撑的规则。学徒期的开始伴随着每个人个性中内在天赋的发挥。即将上演的文本中包含的暗示、对日常行为的观察、对其他表演者的模仿、对书本和图片的研究,以及导演的指导都将为之所用,作为表演的出发点。南极表演者显然相对自由,但在连贯发展个人舞台技巧的素质时,却遭遇更大的困难。
与最初看来的情况相反的是,拥有更大艺术自由的是北极表演者,而南极表演者因其任意性和缺乏支撑点,轻易地成为囚徒。然而北极表演者的自由完全地停留在他们所属的剧种范围之内,并以一种使他们很难跨越已知领地的特殊化作为代价。
理论上讲,绝对的舞台规则并不存在。他们是常规和一个将成为矛盾的绝对常规。但这只是在理论上正确而已。在实践当中,一个充分验明的规则集合要对表演者真正有用,就必须被当作一个绝对规则的集合来加以接受。为了达成这明确的虚设,与其他风格保持距离是有帮助的。
许多亚洲和欧洲伟大的戏剧大师们(比如德克洛克斯)禁止他们的学生接近其它的表演形式,即便只是作为单纯的观众。关于这一点有无数的事例来说明。他们坚持: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艺术的品质与纯洁性才得以保持;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学生才能够显示他们对所选路径的专注。
这种防御机制的功绩在于避免了从对于规则相对性的意识中派生出来的病理学倾向,即在路径之间动来动去,幻想能由此积累经验并开阔自身技巧的视野。的确每一条路径都各有千秋,但只有当你沿着它走到底时,才会这样。长期的专注是有必要的,它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允许人们去思考任何其他的可能性。路易斯·约福特宣告:“用简单的规则约束自己,永远不要违背。”他意识到,一个表演者最初使用的规则必须被当作她或他最宝贵的财富来加以守护,以免它在一个过于匆忙的合并过程中受到无可救药的污染。
今天,戏剧环境是受限制的,但没有疆界。表演者们经常到自己的文化以外去游历,或接待外面的来客,在陌生情境中对他们的艺术的特定性进行理论化和分解,或观看别的戏剧,长久地迷恋,并想尝试把一些打动和吸引了他们的结果交织进自己的作品;或为这些常常导向误解的结果所鼓舞。这些误解可能是富有价值的,只要想想巴厘对阿尔托,中国对布莱希特、英国戏剧对川上音二郎意味着什么,就行了。但存在于结果背后的知识,赋其以生命的隐藏技巧和艺术视野却依旧被忽略。
对于表面的这种迷恋,在今天由于接触的频繁,冒险把传统的演变置于飞快的加速度之下,可能导致一种搅拌中的混合状态。
人们怎样才能吃掉别人获得的成果,并具备消化它们的时间与化学性质呢?被殖民或被诱奸的文化的对立面并不是一种自我隔绝的文化;而是这样一种文化:它既知道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做饭,也知道怎么吃掉从外面送来的或拿来的东西。
但表演者们已经采用,并继续在采用的原理不仅包括属于每个传统的原理,也包括某些相似的原理。采用这些原理而不引起任何形式的混合是有可能的。
追踪这些常见原理是戏剧人类学的第一任务。德克洛克斯写道:“艺术彼此相似是因为他们的原理,而不是作品。”我们可以这样补充:表演者彼此相似也是因为原理,而不是技巧。
通过研究这些原理,戏剧人类学向表演者们提供了服务。包括拥有整理成规的传统的表演者和为缺乏传统所困的表演者,包括陷入常规退化困境的表演者和受传统腐化所威胁的表演者,也包括北极表演者和南极表演者。
日常和超日常
北极表演者(舞蹈者、德克洛克斯学校的哑剧演员、由一个已精心演绎出自身代码的小团体的传统中塑造出来的演员、以及由严格的传统所塑造的亚洲古典戏剧的演员)具备一种能量的品质,即便当他们在进行的是漠然的技巧展示时,也能激发观众的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表演者并不试图表达什么,但他们仍拥有一个能量核心,一个未经预设,却可以会意并充满暗示的辐射源,俘获了我们的感官。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应该归功于表演者从年复一年的工作与经验中获得的能力,归功于一种技巧素质。但一个技巧是对身体的一种独特运用。身体在日常生活中被运用的方式却与舞台情境中的被运用方式大异其趣。在日常情境中,身体技巧受到文化、社会地位和职业的限制。而在表演中,存在着一种不同的身体技巧。由此,分辨日常和超日常技巧成为可能。
日常技巧越是处于无意识状态,它就越具有功能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走动、坐下、携带物品、亲吻、表示同意或反对时,做着那些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但实际上却是由文化所决定的手势。根据人们走路时是穿鞋子还是光着脚、携带物品时是用脑袋顶还是用手拿、接吻时是吻鼻子还是吻嘴唇,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身体技巧。去发现那控制表演者舞台生命的原理的第一步可能存在于这样的理解中:身体的日常技巧可以被那不遵循身体运用的习惯规定的超日常技巧代替。
日常技巧一般遵循最省劲原则,即以最少的能量消耗获取最大的效果。超日常技巧则相反,建立在能量挥霍的基础上。它们有时甚至象是在暗示一种与日常技巧所遵循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最大的能量投入换取最少效果的原则。
随奥丁剧院在日本时,我对观众在表演结束时用来感谢演员的那个短语感到好奇。这个短语—otsukaresama(你辛苦了)—是日本礼节中许多专用于表演者的短语之一,意思是:“你为我们受累了”。
但单单能量挥霍并不足以解释构成表演者生命特点的力量。
杂技,或其它的表演形式、甚至京剧里绝技展露的某一刻中表现出来的活力与这种生命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杂技演员向我们显示了“另一个身体”,它所使用的技巧与日常技巧如此迥异,以至于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这已经不再是超日常技巧的问题,而是“别的技巧”的问题。如此,当超日常技巧代替日常技巧时,能量扩张并不成其为特点。换句话说,一种辩证的关系不再存在,只有距离关系,或者说,表演艺术家的身体的不可及性。
日常技巧用于交流,艺术技巧用于取悦。另一方面,超日常技巧却导向信息。它们一招一式地把身体置于形式之中,使之具有人为性或艺术性,但却是可信的。把超日常技巧从那些使身体转变为杂技演员或表演艺术家的不可思议的身体的技巧中区分出来的本质差异就在于此。
动作的平衡
对于舞台存在的一个特质的观察引导我们在日常的、艺术的和超日常的技巧之间做出区分。正是后者决定了前表现性,表演者的舞台生命,甚至在这种生命尝试表现之前就赋予其特性。
预先的肯定不易被接受。在表演者的艺术中,或许存在这样一个层面:它使表演者无须再现什么或具有任何意义,也能够“活着”,依旧在场?正因为面对观众这一事实,表演者看来必然要去再现某某事或某某人。而且,有的表演者以他们的舞台在场来再现他们自身的缺席。这也许仅仅象是一场脑力游戏,但却是日本戏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在能剧,狂言和歌舞伎中,我们可以辨别出一个处于通常用于界定表演者的两个可能性(真正身份与虚构身份)之间的中间形象。比如,“胁”(配角),能剧中的次要演员,常常表现他自身的“不存在”,在动作中的缺席。他采用的是一种复杂的超日常技巧,这种技巧不是用来人格化,而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避免人格化的能力上。这种艺术上精心安排的不存在,也出现在主要演员退场时。脱去角色外衣,他并没有还原到日常身份,而是以使其表演获得生命的同样的能量,从观众面前抽身而退。
身穿黑衣,辅助主要演员的“后见”(检场),也被要求“表演缺席”。一个“后见”的在场既不表现,也不再现什么,而是直接汲取来自演员的能量和生命之源。如此直接,以至于行家们称“后见”比演员更难当。
这些极端的例子表明了一个层面的存在。在这个层面上,表演者的能量被纯粹地用于超日常身体技巧,这就是前表现层面。在日本传统戏剧中,这个层面有时是公开显露,有时又隐而不现。但它总是出现在每一位表演者、每一个传统或每一种戏剧中。它是舞台表演的实质。
说到表演者的能量,这是一个会引起上千种误解的名称。能量一词必须被立即赋予操作价值。从词源学上看,它的意思是:“在工作中”。那么,表演者的身体是如何在前表达层面上进行工作的呢?有其它词可以取代能量一词吗?
在把亚洲表演者的原理译成欧洲语言时,人们使用能量、生命、力量和精神等词来取代日语名称“气合”(呼吸),心,余韵,和腰;巴厘语的taksu,virasa,chikara和bayu,以及汉语的“功夫”(kungfu),“渗透”(shun toeng)和梵文的prana,shakti。 不甚准确的翻译中复杂的名称模糊了表演者生命的原则的实际意义。
让我们以退为进:我们的能量一词怎么翻译?
歌舞伎演员泽村宗十郎为我作了翻译:“在暗示一个表演者在工作状态中具不具备合适的能量时,我们说的是他有或是没有‘腰’。”在日语中,“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准确的身体部位,臀部。说你有没有“腰”,意思是你有没有臀部。但对一个表演者来说,没有臀部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以日常身体技巧行走时,臀部会随之而动。而在歌舞伎、能剧和狂言的表演者的超日常技巧中,相反地,臀部必须保持不动。在行走时要限制臀部动作,有必要稍稍弯曲膝盖,脊椎下压,使躯干成为一个独立的动作单元。通过这种方式,分别在身体的上部和下部产生两处不同的张力,支配着一个新的平衡点。这首先是产生表演者舞台生命的一种方式,其次才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格化属性。
事实上,表演者的生命是建立在平衡的替换中。
“摺足”(脚贴地面行走),舔过地面的脚,这是为日本能剧中的走步方式起的名字。表演者从未把脚抬离过地面。他们向前走,或转身时,只抬起脚趾,一只脚滑向前方,前腿微弯,后腿伸直,身体的重量便与自然状态下相反地落到了后腿上。腹部和臀部收缩,骨盆前倾并下压,就好象有一根线在往下拉它的前部,而另一根线在往上拉它的后部一样。脊椎骨挺直,要直得象“吞了一把剑”时一样。肩胛尽可能并拢,使肩下沉,颈部、头部要与躯干成一线。而身体——根据梅耶荷德有机造型术训练中所采用的一个意象——要象那受鱼骨架启发而建构的船只龙骨一样。但和鱼不同的是,它并不灵活可动,而是被一个坚固的支轴所固定。
这精致的张力之网,其脉络细节被隐藏在浓重的妆彩之下,是能剧表演者示意性在场的源泉。他们说:“能剧是一种行走舞蹈。”
歌舞伎也是一种行走舞蹈。在此,表演者遵循两种明确准则:“荒事”和“和事”。在“荒事”中,即豪放风格,采用的是对角线法则。脑袋是锐角对角线的一端,另一端是伸向一边的那只脚。整个身体,由一条腿支撑,保持一种改变了的动态平衡。
“和事”是所谓的婉约或写实风格。表演者采取一种蜿蜒曲折的行动方式,令人想起印度传统舞蹈中的tribhangi。Tribhangi的意思是“三曲”。在印度的奥迪西舞中,表演者的身体必须经由头、肩和臀部弯曲成S状。Tribhangi的弯曲原理在印度传统雕塑中清晰可见,就象在普拉克斯特力斯(praxiteles)之后的希腊塑像中一样。在歌舞伎的“和事”中,表演者以一种单侧的,起伏不定的动作来移动身体,在身体的重量支撑的脚之间产生一种连续的强化失衡作用。
在巴厘戏剧中,表演者以脚底来支持自己,同时尽量抬起脚趾和脚的前部,这样就把与地面的接触减少了几乎一半。为了防止跌倒,他们必须张腿屈膝。
印度的卡塔卡利表演者以脚侧来作为支撑,但结果是相同的:新的支撑点带来了平衡的剧变,导致一个张腿屈膝的动作。
在另一个整理成规的形式古典芭蕾中,基本姿势里存在要迫使表演者采用不稳定的平衡的意图。如果,在一个典型的日子里,进入伯诺威尔于1830年创立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的芭蕾舞学校初级班,我们会听到老师在向七、八岁的小孩们重复:“臀部收紧。想象你的腿被拉链扣到了一起。重心在前,而不是在后脚跟。脚跟微微从地面抬起,不要太高,能够塞进一张纸就行了。不要让观众注意到它们抬起来了。身子不要动,就象腿支撑着一只盒子一样。站直!就象你们饿了,肚子被拉紧一样。躯干要挺直,象我扯着头发把你们拎起来时一样”。正是这种基本姿势中令人筋疲力尽的平衡带来了姿态的轻盈和奇妙。
所有整理成规的表演形式中都包含了这个连贯的原理:是日常的行走技巧、空间活动技巧和保持身体静止技巧的变形。这种超日常技巧建立在平衡替换的技巧之上。目标是一个永不稳定的平衡。拒绝了自然的平衡,表演者以一种“奢侈的”平衡介入空间,这种平衡复杂、看似多余并消耗过多的能量。“一个人可以生就优雅风韵,却无法生就我所指的这种平衡。”
这种奢侈的平衡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形式化、风格化或规范化……,但是人们在使用这些名称时,却没有问过是什么动机导致了人们选择这种有违我们自然存在的方式和日常使用身体的方式的身体姿势呢?
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
平衡——人类保持身体直立并以此姿势在空间活动的能力——是一系列的关系和肌肉张力的结果。当我们加大动作的幅度——步子跨得比平常大,头向前伸或往后仰得比平常远时,我们的平衡便受到了威胁。于是一整套的张力程序被启动以防止我们跌到。现代哑剧的传统是建立在这种失衡的基础上的,作为一种拓展舞台在场的手段,就象现代舞蹈中的失去平衡。
任何看过马塞尔·马尔索表演的人都会停下来考虑一下,那个在马尔索的节目之间的几秒钟里单独出现在舞台上的哑剧演员的奇特命运。他举着一张牌,上面写着下一个节目的名字。
皮埃尔·佛瑞,那个出示马尔索节目名字牌的哑剧演员,描述了他如何在不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的情况下,趁出现在舞台的短暂一瞬来达成最大限度的舞台存在。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台上的几秒钟里,他集中精力去找到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于是他静止的姿式变成一种动态的静止。佛瑞使自己还原到实质,并且发现了平衡转换中的实质。
当我们笔直地站着时,我们从未静止过。即便当我们自认为不动时,细微的动作却正在分置我们的重量。在一系列连续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我们的重量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时而在脚的左侧,时而在右侧。甚至在最为绝对的静止中,这些细微动作仍存在,有时压缩,有时加大。依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年龄、职业,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
有些科学实验室采用测量双脚加于地面的各种类型的压力的方式来对平衡作专门的分析。从这些分析结果图表中,任何人都能看出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要做多少复杂而又费力的动作。有的实验是关于专业表演者的。如果他们被要求想象携物奔跑、行走、跌倒或跳跃时,这种想象本身立刻对他们的平衡产生了修改作用。而这在非表演者那里并没有产生平衡的变动,他们的想象停留在脑力活动范围内,没有带来可见的体力影响。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平衡,关于脑力活动与肌肉紧张之间关系的事实。但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关于表演者的新东西。事实上,说表演者习惯于控制他们的在场,或把脑力想象转换成体力冲动,仅仅意味着,表演者就是表演者。但测量平衡的科学实验室里揭示出来的一系列的细微动作却把我们引上另一条思路:它们是表演者舞台在场的生命之源。
让我们回到能剧上来。作为它的表演特点的精神性会跟随主要演员的流派风格而变化。这些风格差异与构成奢侈平衡的各种不同的程序有关。一个日本戏剧专家写道:
看过一些不同的演员表演之后,我得出的大致印象是:他们的身体微微前倾。但城(音译)说在能剧的Kanza(观世)和Kongo(金刚)流中存在足够的个别差异以至使人们无法总结出一般规律;在Hosho (宝生)流中,演员的身体向后微靠;而Kita(喜多)和Konparu (金春)流十分强调弯曲膝盖,以至于身体象是沉下去了,而不是前倾或后仰。城说作为一般规律,过分的前倾使身体看来不稳,有损演员的舞台在场;过分的后仰则阻碍了能量向前投射。我把这个理解为:每个演员都必须找到关键的倾斜度,使之适合自己的基本姿态。
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站直时,身体的重量等量分散在双脚底部,但能剧中的情况不是如此。北长世,一个喜多流派的能剧演员,在198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暑期学院计划中对他班上的学生解释说重量应该落在脚的拇趾球上。这种描述我也从别的能剧和狂言演员处听到过。野村城却说,当他站着时,重量是在他的脚后跟上……重量在脚部的特定放置可能也是受全身姿势影响的结果。一个能剧演员认为这对自己最有影响。
亚洲传统戏剧和舞蹈中的基本姿势为这种有意识的、有节制的打乱平衡的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例子。芭蕾、德克洛克斯哑剧系统的基本姿势也一样,在此日常平衡技巧被抛弃,而一种拓展身体张力的奢侈平衡被采用。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因为:这种奢侈平衡对观众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也已经以明确的规则为演员整理成规。同样的原理也可以在每一位熟练的表演者身上观察到,不那么明显,但同样是有意为之,即便那些演员出自非规范传统,即便他们属于写实风格。
“你问的是你的舞台走步方式与你在街上的走路方式是否有所不同吗?是的。”以这种方式,托佐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了他关于可塑性的课程,在戏剧演员的走步和舞蹈演员的设计动作之间作出区分。他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夸张两者的危险,以及可塑性的必要条件。这可塑性是“从他们最深的存在之井中冒上来的能量……当它流经你的肌肉系统之网,唤醒你的内在动力中心,就触动你去进行外部活动。”他详细讲述了正确的舞台步,以及它的发展和调整系统。“换句话说,让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学习如何行走,不管是在舞台之上还是之下。”
托佐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做法,解释着各类鞋子的不同穿着效果:中国女人穿的那一种,“紧绷绷的鞋子把脚变得象牛蹄一样;而他那时候的女人的行走方式则成为时尚祭坛和愚蠢的鞋跟的牺牲品。”他说明了腿和脚的构造;脚与地面各种各样的接触方式;当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时动作的步骤;如何升到空中,不是向上,而是沿水平线向前。他分析臀部与骨盆的功能:“它们具有双重功能。首先,象脊椎一样,能减缓走路时侧面的震动和躯干向两边的摆动;其次是在我们每次举步时,把整条腿甩向前”。在这个分析中,他描绘了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场景:一次士兵游行。士兵们在栅栏之后,只能看到他们的胸部、肩膀和头部。“他们看来不象在走,而是在从溜冰场上或一个绝对光滑的平面上滑过。人们感觉到他们的滑动……他们的身体的上半部无可置疑地在栅栏后的水平线上漂流而过”。
梅耶荷德坚持:从一个演员使用脚的方式,以及他们移动时或与地面接触时的推动力,可以识别出他的才能。他为演员勾勒出一个水手在前后颠簸的船只甲板上的生气勃勃、实用但不优美的步态意象。为了他的一个训练,他甚至谈到揭示演员在一个动作的结尾的反应的“两腿的狂喜”。他宣称,通过对有一天他在结冰的街道上滑倒时的反应所作的思考,他已经发现了运动的基本法则。当他往左边倒下去时,头和手臂都不自觉地向右移,成了抗衡重量。
在有机造型术里,梅耶荷德说:为了使维持平衡时的自动反应中所蕴涵的推动力保留下来,每一个动作都必须有意识地重建,不是以静止的方式,而是丢弃以后,在一系列连续的调整中重获。这个原理与多瑞丝·汉佛雷据以建构她的舞蹈方法的跌倒-站起原理相同:一个人从摔跤开始行走;下一个步骤,就是控制下跌的重量。
查尔斯·杜林常常说一个初学者不知道如何在舞台上行走是很典型的事情。他为移动方式的即兴发挥发展出无数的主题和做法,并分析它们对肌肉、姿势、韵律和用眼的影响。
“脚是表现性的中心,并把它们的反应传达至身体的其它部位。”格洛托夫斯基的这个信条对他和他的演员们一起开展的构成训练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训练牵涉到十几个开发新的姿势和推动力的练习与任务。
在奥丁剧团,gangene是移动、行走和停止的方式。 演员们在他们的单独训练中不断地要返回到这上面来,不管他们已经工作了多少年。
“所有的舞蹈技巧,都是基于身体的垂直等分,基于体重的不等分布, 有时在这一半多一些, 有时又在那一半多一些”, SanjuktaPanigrahi说。虽然他描述的只是印度的奥迪西舞, 但指的却是影响表演者生命的一般原理。
就象在显微镜下一样,舞蹈放大了那些使我们站立时保持静止的细微而不断的重量替换,这种替换已经被专管平衡测量的实验室用复杂的图表显示出来。
表演者在通用于所有舞台形式的原理中揭示出来的就是这种平衡之舞。
Fei-cha(飞叉),即飞起来的脚,是京剧中一个基本步的名字。
标签: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