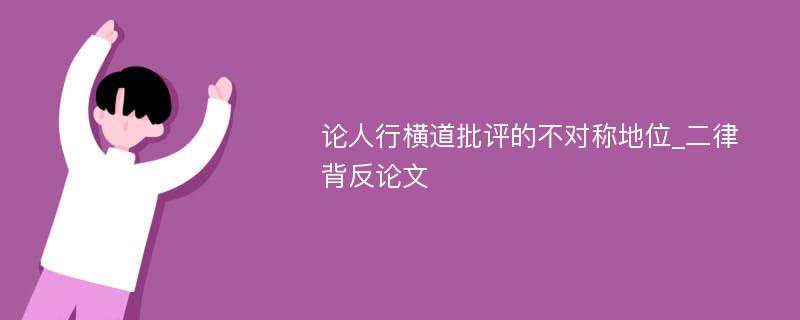
论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的非对称性立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称性论文,行人论文,立场论文,论柄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以下简称柄谷)上世纪80年代便以《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声名卓著,他在其中通过对文学现代性之起源的批判来解剖现代性,揭示出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构架的共生关系。但是他在20世纪初期写作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却被认为是从文学批评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尝试,即“重铸反抗现时代资本帝国的哲学政治学基础”①。齐泽克就认为,“在异端的理论野心和对另类革命传统(此处指无政府主义)的关注方面,《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或许堪与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在巴西出版的政治学三部曲比肩”。但齐泽克也指出,柄谷的思想世界更接近于马克思,“因为他身后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②,实际上主要是康德的传统。本文拟以柄谷的《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为文本依据,首先考察他对康德与马克思之间亲和性的论述,然后基于此立场,考察他为反抗“资本—国家—民族”三位一体的圆环时确立的政治哲学基础。 “自我”与“他者”的非对称性:重评康德的“二律背反” 在主流的哲学史中,一般认为,从笛卡尔经过康德,一直到胡塞尔的现象学,三者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并共享一个基本的问题结构:康德不过是继承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基本精神,有机融汇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实现了主体哲学意义的哥白尼式革命,胡塞尔则是将笛卡尔主义贯彻到底。但是,柄谷认为,康德与笛卡尔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存在着某种另类的“非对称性”。换言之,康德与笛卡尔、胡塞尔并非共享着同一个“问题式”,因此,决不能简单地在笛卡尔主义的延长线上理解他。 具体而言,在柄谷看来,如果说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出现了三个“我”:一个是作为单独的实体存在的笛卡尔本身,这是一个“经验性的自我”,另一个是怀疑这种“经验性自我”的自我,第三个是“超越论的自我”。但是,这三个“自我”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是模糊不清的。而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一种超越论的现象学,自觉地置于笛卡尔主义的延长线上,并通过区分“经验性的自我”、“超越论式的予以还原的自我”以及“在超越论层面上被发现的自我”,将笛卡尔没有详细区分的三个“自我”做了清楚的界定。他说:“如果在经验或别的其他方面自然地专注于这世界的自我可以说是对世界‘感兴趣’的自我,那么,现象学地改变了、继续坚持着的态度就存在于自我的分裂中,正是在自我的分裂中,现象学的自我把自己塑造为处于素朴的自然兴趣者之上的‘不感兴趣的旁观者’。因此,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只有借助一种新的反省才可理解的。新的反省作为一种超验的反省同样要求不感兴趣地旁观那种态度——自我唯一仍然保持兴趣的,是去查看、去妥当地描述他所见到的东西。”③但关于“自我”的区分却给胡塞尔带来了深刻的悖论:“世界是由超越论的自我构成的,而试图怀疑一切的我却属于这个世界。”④换言之,在胡塞尔那里,一方面,人类本身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组成部分的人的主观性,又如何能够构成世界,即“将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意向形成物而构成呢”?⑤ 胡塞尔试图通过主体间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柄谷所言,“这又转化为另一个难关,即通过自我能否构筑起他者的问题”⑥。胡塞尔最终不过将“他我”视为“自我”的“变身”,即通过“自我”与“非自我”的区分来寻找“他者”:“超越论自我在其固有的东西的内部,构成其对自己来说作为他者存在之全体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客观世界的最初阶段,构成具有他我形态的他者。”⑦柄谷认为,胡塞尔所构造的“他者”并非真正的“他者”。如果说胡塞尔从康德那里借用了“超越论”这个词,但是他实际上抛弃了康德,回溯到了笛卡尔那里,“他没有认可康德所发现的感性、悟性、理性或者物自体、现象、理念这样一些结构,对他来说,康德的超越论批判显得很不纯。但是,这正说明了康德的超越论批判中包含了‘他者性’”⑧。而柄谷认为,康德所引入的“他者”,正是以“物自体”或者“感性的受动性”而被言说的“他者性”。 具体来说,在柄谷看来,胡塞尔所揭示的“自我与世界”的悖论不过是康德在“现象”与“物自体”区分之下所揭示的“二律背反”所讲的事情而已。即胡塞尔最后所遇到的这个问题,不过是康德首先就在二元论区分之下必然导出的问题:“康德所遇到的乃是世界之内与构成世界的主体,即胡塞尔碰到的那个悖论。”⑨但康德是透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强烈视差”而直接目击到的。这个“他者”就是康德在“二律背反”之下所逼问出来的“物自体”的存在,“康德通过‘物自体’揭示了我们无法事先获得也无法随意内在化的那个‘他者’的他者性”⑩。而“二律背反”中的“正题”与“反题”之间的“强烈视差”,只有基于“物自体”这个“他者性”才能得到理解。反过来说,也正是基于“物自体”这个“他者”,才可能站在两种立场之间的位置,实现真正的“跨越性批判”:“批判从何而来呢?这正是康德所处的场域,即来自于经验论与理性主义‘之间’。对他来说,经验论与理性主义并非两个不相干的学说。”(11)由此可见,面对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我们不应指望化约一方面而迁就另一方面,甚或通过某种“辩证的综合”,妄图将两者沟通起来。恰恰相反,按照柄谷的看法,我们应该坚持“二律背反”的不可消解,并以此为出发点构想一个基本的批判立场。正如齐泽克所说,“这不是某个与其他立场相抵牾的既定立场,而是立场之间不可消除的鸿沟所在”。因此,“柄谷从康德物自体概念中所读出的,并不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的先验实体,而是只有凭借现实经验不可消解的二律背反特征才能辨认之物”。(12) 柄谷从康德的“二律背反”入手,进一步依据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所区分的“反思性判断力”与“规定性判断力”,提炼了“事前的立场”(Ex ante Facto)与“事后的立场”(Ex Post Facto)的区分:前者是在既成的法则中无法得到整理的例外事物,只能依靠理论的信念,而后者则可以直接运用既成的法则。在柄谷看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乃是视综合判断为已然确立的前提,这是一种事后的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综合判断是容易的。因为综合判断蕴含着飞跃,存在着危险。因此,当康德在综合判断中发现困难,出现各种二律背反的时候,正是他站在“事前”的立场思考的时候。 基于这种区分,当黑格尔以嘲笑的态度抛弃了“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认为这不过是“被认识的东西”与“已经认识的东西”之间的区别而已,甚至宣称“再也没有比物自体更容易被认识的东西”的时候,柄谷认为,这只是“因为他站在‘绝对精神’这一绝对的事后性(终结)来观察罢了。由此,一切生成都作为精神的自我实现而得到了目的论的理解”。(13)按照这种区分,以“分析判断”来证明只能是“综合判断”的事物,便是形而上学即思辨哲学,从这个意义说,“形而上学就是将只能是事后性的东西投射到事前这样一种思考”(14)。 正是从这个意义,柄谷认为,康德所实现的“哥白尼式转向”的意义,并非向主体性哲学的转移或者再推进,而是由此向以“物自体”为中心的思考转移,即已经不再是笛卡尔主义意义上的主体哲学,而是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奠基。如果基于康德与笛卡尔主义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来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话,柄谷认为,笛卡尔所谓的“上帝”便是促使人们怀疑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一个绝对无法内在化的“他者性”。“换言之,在怀疑这一行动中,一开始就隐含着他者的他者性存在。”(15) “商品”与“货币”的非对称性:马克思的“之间”立场 在柄谷看来,对黑格尔主义之“事后性”综合提出异议的思想家,主要是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语境中强调了“综合判断”需要“惊险的跳跃”。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是在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展开对黑格尔“事后立场”的批判,那么,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就不能离开《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柄谷基于“事前”与“事后”的视差关系,以“商品”与“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为线索,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刻的阐发。 在柄谷看来,古典经济学缺乏对“货币”的分析,他们仅从劳动的角度来观察商品的价值,仅将“货币”视为单纯表示商品的内在价值的尺度或者单纯的流通手段;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如贝利却拒绝劳动价值论,将“价值”视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纯粹关系。柄谷将前者比作是哲学上的“理性主义”,而后者相当于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两者的对立类似于康德意义的“二律背反”:“价值”必须由生产过程中产生,但又必须通过流通才能实现。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则体现了马克思与康德之间的亲缘关系。 具体来说,在柄谷看来,马克思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同于斯密:马克思从“事前”的立场认为,商品要成为货币,即从“商品体”跳到“金体”,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16)即“商品”如果卖不出去而无法进入到流通领域,那么便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被废弃掉。因此,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综合统一,这还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斯密从“事后”的观察认为,“商品”中已经存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就是购买力,即“货币”。既然无论什么“商品”无形中都被视为了“货币”,那么,“货币”只是次要的存在,实际上的“货币”只能是对此的表示形式了。用柄谷的话来说:“他们是将货币内在于各种商品之后,便把货币抹消掉了。这与把神内在化于个人之后否定神的存在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是一样的。”(17)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将“货币”视为“商品”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阐明“商品”何以会成为“货币”,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斯密与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18)。正由于古典派的“劳动价值学说”否定了商品交换中“货币”所固有的“位相”,而将此还原为“一般生产”,柄谷认为,“这就开拓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观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位相”(19)。马克思则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差异:“我们要做资产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20)这里的“差异”是明显的:古典经济学的“事后”立场实际上将一切商品视为有交换价值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否定了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实在性,但是马克思的“事前”立场则揭示了从“商品”跳跃到“货币”之间的惊险! 柄谷认为,这种“惊险”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同样也体现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货币所有者掌握主动权,拥有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与任何物品直接交换的“社会抵押权”。但是,只有当作为总体的雇佣劳动者自己买回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之后,资本的剩余价值才得以实现。如果资本最终不能卖掉生产物,剩余价值本身就无法实现。而购买这些生产物的人乃是其他的资本或者在其他资本家手下工作的劳动者。“就是说,资本也必须一度站在‘卖的立场’上,这时他从属于站在‘买的立场’上的雇佣劳动者的意志。”(21)由于“站在货币形态上和站在商品形态上的两者,其关系是不对称的”(22),因此,这种买卖关系显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主人”与“奴隶”辩证法,而是如前所述的“惊险一跳”。这也意味着,为了完成再生产的循环,资本必须经历关键性的“角色倒置”。在齐泽克看来,“这一点对于柄谷至关重要:它提供了今天反抗资本逻辑的必要杠杆”(23)。但古典经济学家却“看不见处于购买立场的资本和只能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因此也不可能发现资本为了自我增殖必须一度站在卖的立场上所引发的‘危机’”(24)。 一般来说,资本回避“卖出”危机的方式就是“信用”。即先在观念上实现卖,采取发行期票,然后结算的方式,没有必要等到G-W-G’这一过程结束再进行投资。正是“信用制度”加速了资本的转动且使得其永无休止地运动。从这个意义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大,也就是“信用”的扩大。但从根本上说,“信用延缓”没有从根本上回避“卖的危机”,即只是将眼下的危机留给将来。于是,“卖的危机”表现为“结算的危机”,“表现为结算时能否用货币来完成这样一种危机”(25)。为了回避这种危机,必须使得决算无限延期,一旦出现了“终结”,“信用”必将崩溃,如果决算的时刻突如其来,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事实上,资本主义既然根本上是一个信用的世界,那就必然会经常伴随着经济危机。正是在卖与买、买与支付的分离中,蕴含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然而,“这同时也是资本(自我增殖)本身的可能性。就是说,剩余价值、信用与经济危机相互之间不可分离”(26)。 从这个意义说,资本的逻辑就是“信用经济”,但“信用并不是单纯的幻想,也非意识形态”(27)。也正是从这个意义说,“现代资本主义”与“宗教”就具有某种同构性与亲缘性:资本所主导的社会,与神和信仰的世界一样,一方面貌似是完全虚妄的,但同时又是现世的宗教,以强大的力量蹂躏着我们。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当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然后通过物的形式,将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的时候,“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28)。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组织世界的能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观念性的力量,它并不是什么经济基础,亦非上层建筑,也不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某种辩证关系,按照柄谷的说法,相对于从“事前”的立场对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这里发生了“视角的转移”,似乎又回到了德国的观念论,即基于“事后的立场”,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引来描述资本占据主导的“虔诚的幻觉”或“精神错乱”的世界。(29) 由上可见,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考察,不是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而是通过危机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通过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来考察。“不是从正常的情况下而是从看似异常的方面来观察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种视角使《资本论》得以成为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性批判,甚至蕴藏着对以往所有哲学史的总体批判。”(30)但是这里的困难在于,在叙述形式上要同时展示“事前”与“事后”两种立场,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因为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本身只能作为“差异”、“之间”存在,而不是实在性的东西:“我们无法先验地谈论这个‘之间’,因为一旦张口述说它便将立即消失掉。”(31)正如我们无法谈论“此时此地”的“单独性”(singularity)一样,“我们感到‘此物’和‘这个我’是特异的,但一说起来,变成了一般概念的限定化了”(32)。如果说黑格尔基于“事后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宣称:“凡是被称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不真实的、无理性的、仅仅是意谓着的东西。”(33)而当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逻辑学来述说“资本的逻辑”时,这个风险尤其大:虽然从“事后的立场”看,“资本”确实是类似于黑格尔的“精神”,但如上所论,黑格尔式的叙述方式可能掩盖了马克思揭示的“事前”与“事后”之间的“视差”。而面对一种强大的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氛围,无论怎么强调这种“视差”都不过分。柄谷就坚定地认为,《资本论》绝不是那种对黑格尔做了唯物论式的颠倒的东西:“把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固有物的马克思,需要一种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视角。”(34)这种视角就是柄谷所谓的“跨越论批判”的立场,其特征就是在“事前”与“事后”的非对称的“视差关系”中确立批判的立场。“马克思是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通过不断地移动与回转来批判各种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但是,这种以外的立场并非什么实体性的存在,他所站立的位置是话语的差异或各种话语‘之间’,这又使任何一种立场都变得无效了。”这里的关键在于:“针对观念论而强调历史的受动性、针对经验论而强调构成现实之概念的自律性力。”从这个意义说:“如果没有这种不断的移动与回转,马克思的思想是不存在的。”(35) “可能的共产主义”:柄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 柄谷在《跨越性批判》中对康德与马克思思想的分别阐释,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亦非简单论证两者在处理“非对称性关系”意义上的亲和关系,而是有着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我所谓的跨越性批判,旨在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之间,即康德式批判和马克思式批判之间往复跨越,也就是透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同时透过马克思来阅读康德。我要做的是重新恢复两位思想家所共有的‘批判’之深远意义。”(36)原来,柄谷是试图在康德伦理学的“自由王国”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建立某种关联:如果说马克思的批判是要弄清楚资本的本能及其限界,进而发现其根底上人类交往行为中不可避免要遇到的困难,“《资本论》没有简单昭示出走出摆脱资本主义的路径,而只是暗示对此进行实践性介入的可能性。”那么,与之相似的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更试图通过毫不犹豫地照射出人类理性的局限,从而暗示了其实践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实践的可能性”的意义上,柄谷才“将康德与马克思结合到一起”(37)。认为康德与马克思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对道德实践之可能性的探寻:正如康德致力于论证“科学的形而上学”一样,马克思也拒绝把“共产主义”视为康德意义上的“建构性理念”,而是视为“范导性理念”,称其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是一个类似于康德“绝对命令”那样的实践性与道德性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并非单纯的经济或者政治性的东西,也并不是单纯的道德性的东西,而是一个“伦理—经济”的运动,如果“模仿康德的说法,即没有经济、政治基础的共产主义乃是空洞的,而没有道德性基础的共产主义则是盲目的”(38)。 但柄谷也清楚地意识到,与康德及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在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已经高度扭结,相互无法分离。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一样,三者咬合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这是一个全新的形式,“一旦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使各国经济受到压迫,就会谋求国家的保护(再分配),而转向对民族文化同一性和地区经济的保护”(39)。正如资本不可能自行消灭一样,国家与民族共同体也是不会轻易消亡的。而“资本—国家—民族”构成一个“圆环”,三位一体,互相强化,根本就无法逐个击破。在柄谷看来,发生在《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后的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颠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也没有构成对民族国家的扬弃,反而被“收编”进这个圆环之中,而列宁以来发生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变形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诉求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立。虽然葛兰西提出了“游击战”与“阵地战”的战略分别对抗市民社会的霸权与政治性的国家,但是法西斯却诉诸民族主义而粉碎了葛兰西式的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柄谷还认为,即使是马克思也并没有提供一种现成的革命“路线图”。他的《资本论》针对的是德国的重商主义国家经济学而试图从原理上探索资本的运动逻辑,因此,他暂时将国家打上了引号,“那是因为国家的介入最终也依然只能遵循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原理”(40)。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所说的,他是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视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即从“事后的立场”来观察的,因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所以,“我绝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因为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41)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是没有“主体”维度出现的。柄谷引用宇野弘藏的话说,“《资本论》里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没有革命的必然性,因为革命属于‘实践性’的问题”(42)。而这个“实践性”不如说应该在康德的意义上来思考,“即对抗资本运动的运动是‘道德性’的。反抗资本运动所带来的榨取、异化、不平等、环境破坏、女性歧视等的运动是‘道德性’的实践”(43)。由此可见,柄谷对康德与马克思之亲和性的考察,也是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事前”与“事后”立场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中展开的,也只有在这种非对称关系中,才有共产主义之可能性问题。 具体地说,柄谷认为,如果资本的自我增殖不管伴随着怎样的危险都不会自动停息,那么,“唯一可以阻止它的就是伦理性的介入”(44)。实际上就是作为行动者的“主体”的介入,那么,在哪里,怎样的介入才是可能的呢?柄谷回到资本运动的公式G-W-G’,发现当资本购买劳动力商品和向劳动者出卖生产物时,存在两个容易遇到的危险契机:一个是买,一个是卖。“不管在哪个方面失败了,资本都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换言之,资本无以成为资本。”(45)柄谷认为,作为“行动主体”的劳动者可以在这里与资本相对抗:前一个是不出卖劳动力,即不出卖资本主义之下的雇佣劳动,后一个是不买资本主义生产物。“两者都将在劳动者得以成为主体的场域中来实现。”(46)而替代这种买与卖的办法,就是生产—消费合作社。“在这种‘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马克思)中,不存在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反过来说,只有通过生产—消费合作社才有可能扬弃劳动力商品。”(47)原来柄谷是试图在商品与货币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中寻求主体介入的契机,进而寻找突破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柄谷认为,如果基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非对称关系,这种替换实际上就是如何解决“既要有货币”同时“又不能有货币”的二律背反的问题:之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货币在商品交换中所处的独特位置,“货币并非单纯表示价值,而是通过货币交换对所有生产物的价值关系进行调整的东西”(48)。如果把货币否定掉,一定会有别的等价形式存在。所以,货币不是一个可以否认之物。之所以不能有货币,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货币被实体化了,成为了货币拜物教即“货币神学”,产生了作为货币自我增殖的资本运动。“或者不如说,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在隐蔽其为资本运动的产物这一点后,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的。”(49)那么,是否可能有一种不转化“资本”的“货币”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共产主义是否可能的回答。柄谷的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之所以可能,原因就在于“《资本论》为此提供了逻辑依据。即,价值形态中的非对称关系(商品与货币)产生出资本,同时这里也存在着使资本停息的‘positional’力矩。而活用这种力矩正是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性批判”(50)。 柄谷引证了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的“地区贸易通商制度”,即一个建立在非市场货币基础上的有限交易体系,作为“一个反作用于资本的经济模式”,来论证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合作社”与“替代货币”的存在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国家也可以作如是观,“我们需要某种中央集权,但不是对一个自在权力实体的崇拜”(51)。正如柄谷对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揭示的、处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非对称关系中所揭示出来的“国家”一样,“国家”与“货币”处于同样的位置。如果一种“替代货币”是可能的,那么一个“替代国家”也是可能的。因此,基于此主体能动性的立场,突破“资本—国家—民族”三位一体的圆环是完全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柄谷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亲身实践,组织起抵抗资本主义的“新合作社联盟运动”(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 从“对称性”到“非对称性”:跨越性批判的实践意义 一般认为,“理论”作为“观看”,是以概念作为“纽结”来重构世界图景的。在这种重构的路径中,世界成了概念中的“世界”,概念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世界本质的反映,于是,世界的变动不居,或者表现为单个概念的内涵演变,或者表现为多个概念之间的转化关系:前者基于认识与对象的“区分”与“对应”关系,通过概念内涵的扩张来把握对象,此时概念的实质便表现为“自然之镜”;而后者表现为许多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如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世界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而世界的发展过程便是“现实的诸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而无论是“概念”与“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规定,还是概念内部的“对立”关系的构造,都可视为源于一个“对称性”关系的前设,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称性、概念之间的对称性等等。这种“对称性”关系在形而上学传统中表现在“矛盾”之对立统一的规定性中,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52)。作为矛盾的“对立”的方面与“统一”的方面本来是不同的两个方面,但是在这种“矛盾”的思维方法看来,两个方面却是高度“对称”的:统一的关系存在于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在它内部就包含着对立关系;对立关系存在于统一关系之中,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统一关系。所以“对立是统一中的对立,统一是对立中的统一”。这就完全将“世界的逻辑”与“逻辑中的世界”、“概念之外的世界”与“关于世界的概念”强行“对称”起来了。在哲学史上,这种“对称性关系”表现在形而上学的多种形态与其基本问题之间的“同构性”中。正如怀特海所说,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而已,他所揭示的乃是后柏拉图哲学与柏拉图理念论之间的“强对称性关系”。从这个意义说,如果将“对称性关系”的确立与强化视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特征,那么,如何真正走出形而上学的对称性结构,则是“后形而上学”阶段一个人见人殊的问题。 一般来说,黑格尔哲学代表形而上学的完成,而在此之后的哲学家走出黑格尔,至少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颠倒形而上学“对称性”结构中的对立两项之上下关系,如以“直觉”挑战“理性”的霸权,以“偶然”颠覆“必然”的逻辑;二是发现与确立相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结构的“外部”,并在“内”“外”之间的关系中重新确立批判的立场。如果说形而上学的内在问题结构乃是根源于那个自我指涉的、具有高度对称承载能力的巨无霸式的“自我”,那么,正如很多学者所揭示的,第一条路径所谓的“颠倒”依然在二元结构中改变对立两项的上下主从关系,貌似工作艰巨,且成绩斐然,但实际上没有真正挑战形而上学中所蕴含的“对称性关系”,因而不仅没有对形而上学的自我指涉体系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有可能被重新纳入到其内在惯性中。因此,只有坚持第二条道路,通过发现与确立外部的“他者”的存在,才可能真正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如何理解这个“外部”进而避免重新将“外部”改造成为“内部”,则构成了问题的难点。从这个意义说,柄谷跨越性批判展现出的深刻洞见,便具有了深远的意义。 如上所论,柄谷以“事前”与“事后”立场的区分,对康德“二律背反”以及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与货币之间“非对称性”关系的阐释,实质上就是要确立一个“外部的他者”,以区分形而上学所消化吸收之后的“内部的他者”,进而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称性关系”转换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实际上,自柏拉图直至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也强调“他者”的存在,并致力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但因为是在同一的理性原则之下的对话,所以最终只能成为将“他者”内在化“自我”的自言自语:“所谓近代哲学中的唯我论正是将他者的他者性抹杀掉,使与他者的对话变成与自己对话这样一种思想模式。”(53)从这个意义说,形而上学的问题结构消解与同化了真正作为“外部”的“他者”,从事的不过是形而上学“内部”的能指游戏。换言之,如果说在“对称性关系”中,貌似对立的“二元”不是被还原为“一元”(或物质,或精神),就是被归结为一元的变形(辩证的综合、否定之否定),那么,在一种“非对称性关系”中,二元之间就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始终存在一个“差额”,立足于这个“差额”,每一个“元”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而不能简单地还原或者化约:它不能在知性统一性之上被概念所反思,也不能在理性统一性之上辩证地把握。毋宁说,这是一个永恒延拓的空间,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柄谷借用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资源,肯定了维特根斯坦从哲学的“外部”而不是哲学的“内部”批判“哲学”的做法:如果从哲学的“外部”看,“自我”与“他者”便不是从共同的游戏规则出发,而是站在不具有共同规则的位置,即在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中,逐渐确立游戏规则的,但是对于这种规则能否最终达成,却没有充分的把握。“这就是我们的悖论:没有什么行为方式能够由一条规则来决定,因为每一种行为方式都可以被搞得符合规则。”(54)柄谷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反复论述的,正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非对称性,或者说是对消解了非对称性的思想的批判”(55)。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这种“非对称性关系”中,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才存在“改变世界”的哲学。 如果基于这种“非对称性关系”重新理解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十一条,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不是强调从“理论”到“实践”或者从“书斋”走向“街头”,而只是立足于与“解释世界”非对称的“改造世界”的立场,对一切“解释世界”的哲学进行再解释,即从哲学的“中心化”“普遍化”与“对称性”关系中解读出其中所掩盖的“差异性”“非对称性”与“异质性”来。因为只有在这种“视差关系”中,才存在着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如果一切被“绝对”或“无对”所统摄,哪里还有现实的可能性?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谈何改变世界的行动? 柄谷对共产主义之可能性的论证,也正在这个“非对称性”空间中展开。正如他经常引证的:“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6)在齐泽克看来,不管柄谷对共产主义之可能性论证在枝节方面多么的不够严谨,但他的著作对有志于突破资本主义“文化”反抗僵局的人是必读的,因为“它重申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性”(57)。 注释: ①②(12)(23)(30)(51)(57)齐泽克:《视差之见》,薛羽译,《新文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8、52、14、15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14)(15)(17)(19)(21)(22)(24)(25)(26)(27)(29)(31)(32)(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49)(50)(56)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51、52、52、52、57、22、57、151、151、54、150、115、170、166、172、185、186、186、102、96、67、118、125、1、2、91、247、234、252、253、259、259、259、260、261、261、265、1页。 (16)(18)(20)(28)(4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98、62、97、10页。 (3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73页。 (52)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2页。 (53)(55)柄谷行人:《作为隐喻的建筑》,应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96、120页。 (5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1页。标签:二律背反论文; 笛卡尔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康德资本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经济学论文; 康德论文; 胡塞尔论文; 他者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