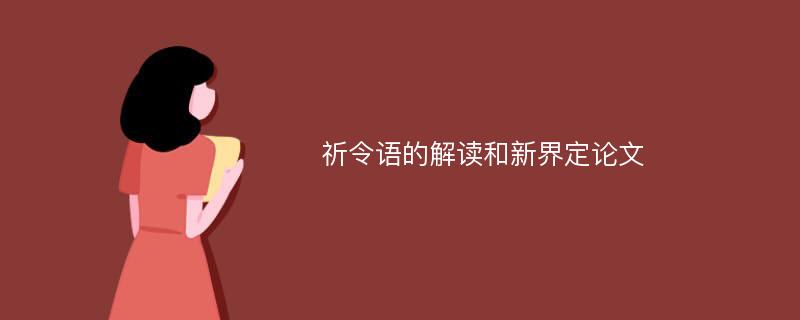
祈令语的解读和新界定
○ 徐飞,范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089)
[摘 要] 祈令语作为儿童语言发展中最早出现的言语行为,借助非言语性的刺激促使说话者产生新的言语和非言语行为,故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祈令语的界定,进行了激烈批判。此后,学界致力于祈令语界定的完善,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界定分别建立在已形成操作(EO)和动机化操作(MO)之上。然而,学界对祈令语仍有较大的误解,鲜有研究深入解读祈令语。更为重要的是,MO基础上的祈令语的界定,仍可进一步完善。鉴于此,通过系统阐述祈令语的界定和分类,在综合相关学者的观点及祈令语泛化中MO和区别性刺激(SDs)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尝试将祈令语重新界定为:祈令语是一种言语操作反应,其形式受制于MO,SDs决定其是否出现,无须直接训练亦可出现新的祈令形式—反应泛化。
[关键词] 祈令语;动机化操作;区别性刺激;祈令语泛化
一、引言
早在1957年,斯金纳(Skinner)在其《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中,将言语行为定义为通过他人的中介而得到强化的行为,并指出该行为主要涉及对操作(operant)这一基本言语行为单位产生影响的刺激和强化物[1]2。斯金纳在将言语视为行为的同时,还建构了描写和分析言语行为的框架,试图找出影响言语行为的各种变量,以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言语行为。然而,言语行为毕竟不是个体内部因素(如遗传、基因)的产物,而是一种操作性行为,因而它还受环境选择的影响。
乔姆斯基(Chomsky)在1959年,撰写《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A Review of B. 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一文对《言语行为》中的许多观点和概念界定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质疑实验室低等动物的行为研究结果是否同样适用于人类的言语行为;第二,质疑言语行为、强化、祈令语(mand)等概念的界定;第三,质疑强化和刺激强化的观点,并提出不依赖环境反馈的先天心理过程[2]。虽然《言语行为》受到了乔姆斯基的激烈批评,但由于祈令语的刺激是非言语性的,是对说话者最有效的言语操作,是儿童语言发展中最先出现的一种言语行为,所以《言语行为》对语言本体的这种研究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斯金纳在1974年详细回应了乔姆斯基对其研究的误解和疑惑,并发出《言语行为》没有被语言学家或心理语言学家们所理解的感叹[3-4]。斯金纳此处所言的不理解主要是指语言学界对《言语行为》中一些言语行为概念的理解上的困难。其中,祈令语也备受误解。事实上,开展祈令语的研究对于祈令语的教学实践和自闭症等儿童行为的调节有着重要的意义[5-6]。所以,即便斯金纳的祈令语在语言学界存在诸多的质疑,但却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种言语行为。在已有的研究中,由于乔姆斯基等人的批判,学界对祈令语存有诸多误解,鲜有研究深入解读祈令语,72%的言语行为分析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祈令库(mand repertoire)的讨论、判断和分析[7-8]。所以,祈令语的界定仍需进一步完善。据此,本文将详细阐述斯金纳对祈令语的定义和分类,并结合乔姆斯基等人的批判和观点,以及在祈令语泛化中MO和SDs之间的关系,尝试对祈令语进行深入解读和重新界定。
二、祈令语的界定和分类
(一)斯金纳的祈令语界定
斯金纳依据听者的反应、区别性刺激(discriminative stimuli,以下简称SDs)、强化及其他言语反应,将言语行为划分为祈令语(mand)、反照(tact)和自我附着(autoclitic)三种类型。并指出祈令语与服务于听话者的其他两种类型的言语操作(verbal operants)的不同之处,在于祈令语是一种为说话者服务的言语行为[1]2。
首先,斯金纳将祈令语视为一种有特征的结果(characteristic consequence)强化,是受短缺、反感性刺激等条件控制的言语操作反应。其次,斯金纳指出祈令语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在于其所反应的形式与先前的刺激没有具体关系,亦即其口头或书面语言是由动机化操作(motivating operation,以下简称MO)而非SDs决定的[1]35。而迈克尔(Michael)的研究则认为祈令语这一概念所涵盖的口头、书面和指示性言语行为(indicative verbal behavior)主要受制于当前发生效力的动机变量。然而,祈令语的控制变量具有多样性,不同的MO可能会共同控制某一行为,某一行为也可能受制于不同的MO,诸如一个人即使饿了很久,但若生病的话,食物作为强化物的价值就会降低。据此,迈克尔于1988年对祈令语的界定进行了改进,承认MO控制具体的反应形式(口头、符号及书面语言等),其界定下文将详述[9]。
(二)祈令语的分类及延伸
斯金纳在以听者为中介行为的基础上,将祈令语分为请求(request)、命令(command)和恳求(prayer or entreaty)三种类型。他认为,“请求”可独立驱动听者来强化说话者;“命令”则是说话者在听者的行为通过减少威胁而得到强化时的一种反应;“恳求”是说话者通过产生某种情绪倾向来促进听者的一种强化。
斯金纳根据听者的行为特点,将祈令语分为“建议(advice)”“警告(warning)”“许可(permission)”“提议(offer)”和“呼喊(call)”五种类别。一般而言,在完成说话者发出的强化时,听者有时会受益,此时说话者并未参与,却仍能实现强化。据此,斯金纳认为,若其中的强化是正面强化,该祈令语就被称为“建议”;若听者执行说话者所指向的具体行为时,能避开反感性刺激,此时的祈令语被称为“警告”;若听者本打算以某种方式行动,却因受到威胁等的限制,而能消除这一威胁的祈令语通常被称作“许可”;若听者的无端强化(gratuitous reinforcement)行为被说话者拓展,该祈令语则被称为“提议”;若说话者能继续发出其他对听者具有强化作用的行为,该祈令语可被称为“呼喊”。
此外,斯金纳还指出,若将听者发出和强化一个反应的刺激条件考虑进来,可观察到祈令语延伸(mand extension),并认为祈令语延伸是任何与强化情境的某些方面相似的、当前情境均可增加反应出现的概率,是一种刺激条件间的泛化(generalization)。据此,斯金纳概括了出现祈令语延伸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同样的反应形式出现于不同的SDs之间;另一种是同样的反应形式出现于不同的MO之间。他认为祈令语延伸还应包括在已有强化的反应形式上偶然获得的新刺激形式,斯金纳称其为迷信祈令语;对于那种从未受到过强化,也无法用偶然强化来解释,倒像是从旧祈令语类推而得到的祈令语,斯金纳称其为神奇祈令语(the magical mand)[1]38-48。
针对乔姆斯基的批判,诸多学者亦提出了异议,例如MacCorquodale认为乔姆斯基的批判完全是对“祈令”的误读。首先,他认为在斯金纳的祈令语定义中,“有特征的结果”指的是具有某种形式的结果,而并非乔姆斯基所认为的程序或者必然出现的结果。其次,他认为,乔姆斯基没有意识到强化不一定能降低内驱力。如“找不到那本书里的参考文献,我就写不完文章,也没法睡觉”“我需要个东西顶住门,不让它关上”“我在书里藏了10美元”。在这三种情况下,“书”作为一个条件强化物,它的效力受控于其他动机性的条件和短缺形式。但是,这种部分相关性不是斯金纳言语系统的一个缺陷。他指出《言语行为》的一个创新点在于其通过他人的强化中介作用来强化听者的非动机(non-motivated)、非祈令(non-mand)。再次,MacCorquodale认为乔姆斯基对“要钱还是要命?”这一祈令语的理解有误。他认为除非说话者有过被杀的经历,否则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但由于乔姆斯基忽略了祈令语中说话者发出祈令不需要对其反应这一特点,才会认为说话者只要曾经缺过钱就可以[14]。我们认为乔姆斯基可能当时有笔误,他想写的或许是:除非听者有过被杀的经历,否则不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那么这里就可以用反感性刺激来解释,即“要命”是一种威胁,听者本能消除这一威胁,就得听从说话者的祈令,把钱交出来,避免丢命。因而此例仍属于祈令语,即使将乔姆斯基的“说话者”理解为“听者”,其辩驳也毫无道理。
教师在创造力教育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应地,创造力教育对教师也提出相当高的要求.要能胜任创造力的引导者和把关人,数学教师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创造力教育观念,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丰富数学创造力教学的实践性知识,切实将创造力培养融入教学中.
酱油是我国传统大宗发酵调味品,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酱油俗称豉油,是以非转基因大豆(粕)、小麦(粉)为原料,通过固态制曲、液态发酵、过 滤、杀菌和调配等工艺酿制而成。酱油的成分比较复杂,除食盐的成分外,还有丰富的氨基酸、寡肽、多肽、糖类、有机酸等呈味成分。小麦酱油是以小麦粉、小麦面筋蛋白为主要原料,通过制曲、液态发酵等工艺得到的液态调味品,如雀巢的美极鲜味汁等。
三、祈令语的不同解读
(一)乔姆斯基的批判
事实上,我们需要客观看待乔姆斯基对祈令语的批判。一方面,乔姆斯基对祈令语的确存在误读。首先,乔姆斯基提到斯金纳在创造了请求、命令等概念之外,还创造了迷信祈令语和神奇祈令语。也就是说,不能仅用短缺或反感性刺激这些控制变因来界定祈令语,还需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界定。其次,对于请求、命令等祈令语的概念,乔姆斯基认为不应按照常规意义来理解,而应将其置于斯金纳独特的系统中来加以考量。在《言语行为》中,由于没有先例供参考,斯金纳才独创了一套术语,目的是想从行为过程的角度对言语行为重新定义和分析[16]。同时,由于斯金纳无法用传统的语法术语来对言语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所以斯金纳的新术语看似与普通英语形式一致,然而其实际上所被赋予的新意义却难以理解。但斯金纳的这些新术语多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其在行为方面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在沿用[17]。从语言学角度而言,由于传统的分类方法不清晰,尤其是在通过语言形式来描述语言的系统中,句子的划分没有考虑到言语行为或说话者的影响,所以斯金纳将祈令语从言语行为中抽离出来加以研究,是有助于简化言语分析的。而且斯金纳的祈令语,是基于行为主义的操作条件进行界定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因果关系来加以分析,而得出斯金纳的祈令语并未涵盖所有影响祈令语变量的结论。
对于这两种祈令语延伸的特点,斯金纳也给出了界定,他指出迷信祈令语是祈令的刺激泛化,是在新的区别性刺激条件下出现的祈令语;神奇祈令语是真实祈令语延伸(the true mand extension),是新的MO呈现时发出的祈令语。米格尔(Miguel)则认为,若这两种祈令语延伸的形式同时出现于非训练的MO和新刺激条件下,那么这两种类型的泛化会一起产生[10]。此外,Rosales 和 Rehfeldt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若对受试进行一个新祈令语的训练,并使之在形式上等同于旧祈令语之后,那么受试可以在同一MO条件下使用新祈令语替代旧祈令语进行祈令[11]。而Barnes-Holmes和Cullinan则将这种替代视为祈令语延伸或反应泛化,并将其所产生的祈令语称为“衍生祈令语(derived mands)”[12]。
(二)学界对乔姆斯基的回应
有针对性的教学语言同样是有效教学语言的直观体现。很多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对于教学语言的选择缺乏针对性,无论什么文体,无论文章要表达怎样的感情色彩,都一成不变,采取相同的教学语言进行讲学。这不仅容易让学生觉得课堂教学枯燥乏味,也无法凸显每篇课文的特色与精华,对于提升课堂教学效率无疑会构成阻碍。因此,教师要深化对教学文本的研究,在透彻分析教学文本的特点上选取更为适宜的课堂教学语言,使课堂教学收获更大。
(三)对祈令语的客观评价
乔姆斯基认为斯金纳关于祈令语的界定中每一个字眼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对祈令语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控制变因识别困难和分类方法无效这两个方面。首先,他指出斯金纳没有提供短缺和反感性刺激相关的条件。如“把书给我”“你让我坐你的车子出去吧”,都让人无法看出它们与何种短缺状态相联系;“要钱还是要命”[1]38的反感性刺激条件不充分,除非说话者之前曾被人杀过。其次,他认为斯金纳关于“请求”“命令”等术语的意义均与传统英语不一致。如英语中“疑问”不能包括“命令”“请求”“祈祷”“劝告”和“警告”。他认为正是由于斯金纳对这些概念的区分标准不合理,才使得听者的行为或倾向不能区分请求、命令、劝告等特征。因此,他认为借助祈令语的定义,无法判定一个反应是否是祈令语,并认为即使听者能够识别,也不能实现全部祈令语的特征性强化[13]。
1950年,Keller 和Schoenfeld率先提出已形成的事件描述能影响行为产生的动机变量。迈克尔在此基础上将EO定义为一个环境事件、一项操作或一种刺激条件,从而临时改变其他事件的强化效果及与结果事件有关的行为发生频率,对个体的行为施加影响[18]。迈克尔从习得的角度把EO分为非条件性已形成操作(unconditioned establishing operations,以下简称UEO)和条件性已形成操作(conditioned establishing operations,以下简称CEO)。前者的发展无须条件或训练,是非习得的,而后者的发展却是习得的,必须借助特定的学习过程,才能获得动机效果。UEO涉及的环境事件或操作能在短时间内改变非条件强化物的强化效果,而CEO则能将短缺、反感性刺激等动机变量进行整合,使其纳入至共同的范畴,促使影响行为动机变量的定义和种类得到清晰的阐释,从而形成一个有机体系。然而,EO这个术语本身也存在问题,其本意指改变一个既定行为后果而得到的强化价值,而这个价值却指向两个方向—升高和降低,但EO的字面意思却只包含“升高”这一方向。因而,迈克尔用MO取代EO来弥补这一缺陷 [9]。
所以,除MO间的泛化外,祈令语只有在听者和环境不同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尽管祈令语的形式受MO的功能控制,但其出现却受制于SDs的各种变量,因而祈令语的泛化(mand generalization)指的是祈令语可以扩展到MO和SDs。换言之,祈令语是否泛化既要看是否有负责其形式的新MO,也要看是否有负责其出现的新SDs,还要在直接训练的情况下看是否会出现新的祈令形式—反应泛化。例如,小孩不会系鞋带,就需要不仅教会他如何向老师求助,还要使他具备在遇到其他困难时(MO泛化),在不同的情境下向其他成人求助(刺激泛化)的能力[10]。
四、祈令语界定的沿革
(一)基于EO的祈令语界定
其次,如果30个月停摆期届满,法院仍未作出有利于仿制药申请人的判决,FDA也会批准仿制药上市。但如果最后法院判决仿制药侵权成立,则仿制药企业在获得FDA批准后生产销售仿制药的行为仍然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甚至承担最高达3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统计发现,在2003-2009年间,共有28例仿制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上市,占同期首次第IV段专利挑战诉讼(238件)的11.7%。⑳ 同注释⑭。
(二)基于MO的祈令语界定
迈克尔采用MO取代EO改进了祈令语的界定,他认为是MO对具体的反应形式(口头、符号、书面等语言)进行控制[9]。而Laraway 等则指出,由于MO既包括可改变作为强化物的某个刺激的价值,也包括改变先前所习得、产生的强化物的行为出现频率。因而他们认为MO是一个比短缺和反感性刺激更宽泛的概念[19]。Sundberg系统阐释了斯金纳的30条关于行为分析中动机作用的观点,也概括了迈克尔及其同事对动机的改进和扩展,并指出使用MO来描述短缺和反感性刺激有众多益处[20]。在综合考虑相关学者关于MO研究的基础上,迈克尔将祈令语重新定义为:祈令语是一种言语操作反应,而且其中的某种反应形式受到与结果相关的MO或EO的功能控制。譬如,一瓶未开启的啤酒瓶会由于短暂性地提高开瓶器而作为(有条件)强化物的价值,未开启的啤酒瓶也可能引发像称呼祈令语(vocal mands)这样的习得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曾经帮助说话者得到开瓶器。但在这种情况下,未开启的啤酒瓶明显不属于短缺或者反感性刺激[10]。
五、祈令语的泛化及新界定
(一)祈令语泛化中MO和SDs的关系
斯金纳在《言语行为》一书中除去提及请求、命令等祈令语之外,还提到过祈令语延伸,即祈令语的刺激泛化(迷信祈令语)、真实祈令语延伸(神奇祈令语)。此外,Barnes-Holmes等还提出了衍生祈令语的概念。而迈克尔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祈令语是唯一受MO功能控制的言语操作。他指出只有出现具有相似价值-替换(value-altering)和行为-替换(behavior-altering)效应的新MO时,先前习得的祈令语才会再次出现,从而实现祈令语的某种程度的泛化。他明确指出祈令语的形式受MO功能控制的条件与其他言语操作类似,亦即只有听者在场或环境的其他方面也获得对祈令语的区别性控制(即多元控制)时,祈令语才最易被强化。而祈令语的区别性变量通常与祈令语的形式(topography)无关,只与其出现有关。因为听者在场增加了说话者进行祈令的可能性,而其所祈令的首先是当前MO的产物。例如,一个具体的动机性变量(如食物短缺)可激活一组同类反应(如意大利面、日本寿司、墨西哥卷饼)。这就是所谓的“发散控制”(divergent control)。而通过增加一个发挥SDs作用的变量(如日式餐馆)来强化某种形式(如日本寿司)并弱化其余形式(如意大利面和墨西哥卷饼),就是“聚合控制”(convergent control)。诸如在菜单上印有日本寿司这一刺激,SDs就能增强MO对反应形式所施加的控制。
在对乔姆斯基的回应中,瑞谢尔(Richelle)指出,由于乔姆斯基混淆了言语的功能性与形式性反应,以及言语事实的心理与语言描写的区别,才对“祈令”概念的分析产生严重的曲解。就“把盐递过来”这个例子而言, 乔姆斯基是将其视为文本反应(textual response)而非祈令语。然而,当说话者在餐桌上使用这句话来给汤加盐时,它就会变成一个祈令语。因此,同样一句话形式相同,但功能会不同。所以,形式和功能描述不是完全对应的,前者阐释后者,却无法替代后者。针对乔姆斯基提出的疑问不包括命令,瑞谢尔亦以“把盐递过来”为例,指出“把盐递过来”是请求而非疑问,而所有的请求并非都可以得到正面回应。事实上,只有命令,即使没人遵从,也还是命令,而疑问是不会变成命令的,所以劝告也不一定都要有人听从;警告虽可能没有意义,但听从警告反而会受反感性刺激,即使不听仍会有积极强化的作用。所以,瑞谢尔认为形式分析是无法界定一句话是否为祈令语、为何种祈令语。瑞谢尔以“把盐递过来”为例,指出判断此句是请求还是疑问,取决于听者的反应是否强化了说话者的言语行为。如果听者完全不加理会,它就并非请求,在说话者的言语库(verbal repertoire)中就成了一个疑问。因此,瑞谢尔认为一句话的功能分析不是通过说话者的意图来体现的,而是与某种强化依存(contingencies of reinforcement)曾经引发的行为有关[15]。针对乔姆斯基声称斯金纳用“X缺Y”来代替“X想得到Y”是没有把行为描写得更客观的论断。王宗炎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分析,认为这种替代至关重要,它能使得Y短缺的时间变得可控,短缺所引发的变化易于观测,而意图却无法来控制[13]。
冷榨和热榨的汉麻籽油在5种不同的储存环境中,温度和光照均影响油脂的颜色、透明度和气味;温度变化越大,光照越强,油脂颜色褪色明显,透明度降低,易产生刺激性气味,稳定性越低。GC-MS方法分析2种不同榨油方式的汉麻籽油脂肪酸成分相同,含量有所差别。油脂在UVC (200 ~ 275 nm)和UVB(270 ~ 320 nm)处有很强的吸收峰,可以较好的吸收紫外线,适合作为防晒霜原料;储存汉麻籽油时,要尽可能避免让油脂与空气接触,应该采用低温避光或者采取真空、惰性气体保存油脂,防止油脂被氧化。
另一方面,乔姆斯基对祈令语这一概念的界定所提出的质疑,也不无道理。乔姆斯基的质疑直指祈令语的动机与短缺、反感性刺激等之间的关系。斯金纳祈令语概念的提出是主张语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找出行为的动机和引发该动机的外在因素。但乔姆斯基认为言语与行为和动机紧密相连,而影响言语行为的依存关系又和行为动机密切相关,所以动机成为言语行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对于言语行为而言,外因产生动机,动机引发行为。外因可分为强化和惩罚两类。斯金纳将短缺、反感性刺激等负面强化物与动机相联系,这一点在祈令语的定义中可见一斑。但仅将动机变量视为短缺、反感性刺激,是不全面的。因而,应该找到比斯金纳祈令语定义中的短缺和反感性刺激更宽泛的概念来涵盖祈令语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已形成操作(establishing operation,以下简称EO)及MO应运而生。
(二)祈令语的新界定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知,建立在MO之上的祈令语泛化,尚存在诸多的不足,有待进一步的完善。首先,其只关注MO对祈令语的功能控制,而淡化甚至忽略SDs的作用,是不全面的。诚如斯金纳在其《言语行为》中所描述的那样,祈令语延伸可以是不同SDs或者MO控制下的同一反应形式,MO决定祈令语的形式,而SDs则决定祈令语是否可以出现。所以,SDs的作用在祈令语的界定中必定会有所体现。其次,斯金纳只关注MO对反应形式的控制力,而未能认识到祈令语泛化还可通过SDs来增强则是不完善的。斯金纳虽然指出祈令的形式不受制于先前的SDs,但是SDs的出现却会增加反应的强度。例如未开启的啤酒瓶,其作为MO,会提高帮助喝到啤酒(强化因,reinforcer)的刺激物(如开瓶器)的价值,而放置于啤酒瓶旁边的开瓶器则可以强化“(递过)开瓶器(来)!”这一反应的强度。在此例中,是MO和SDs的共同作用才实现了对该称呼祈令语的聚合控制。再次,斯金纳未能从现实关怀的角度厘清祈令语泛化中MO和SDs之间的关系,而此关系对于患有自闭症儿童祈令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由于自闭症儿童无法实现已习得祈令语在不同的场景及人群之间的泛化,对他们而言,不仅要促进其单一祈令语的发展,更要确保这些祈令语可以在不同的刺激条件下实现泛化[21-22]。
综上所述,鉴于祈令语的泛化同MO和SDs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祈令语的定义可以进一步完善为:作为一种言语操作反应,祈令语泛化其形式受制于MO,而其是否出现则由SDs决定,且无须直接训练就可出现新的祈令形式—反应泛化。
六、结语
虽然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祈令语有诸多批判,但借助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成果简要概括而成的祈令语的概念,是斯金纳的贡献所在,也是诸多学者不断尝试进一步完善言语行为的基石。其中,迈克尔在将短缺和反感性刺激扩展为EO后,又承认MO控制祈令语的具体反应形式,从动机的角度对祈令语重新界定。本文在EO、MO以及祈令语泛化的基础上,深入阐释祈令语泛化与MO和SDs之间的关系,并从患有自闭症儿童祈令语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祈令语进行了重新界定。该界定不仅考虑到了祈令语同时受制于MO和SDs,也考虑到反应泛化的出现是判断祈令语成功习得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祈令语的习得既要确保相同的反应形式受制于功能对等的不同MO,也要确保不同反应形式受制于相同的MO,即祈令语应涉及不同的听话者,不同的环境,也应该包括所有形式的祈令语。同时,该界定也重新评估了MO同SDs在祈令语泛化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这无疑将有助于在对自闭症等儿童祈令语的研究中,提高对该类儿童在不同场景中、不同人群中实现祈令语泛化的重视。但限于篇幅,本文尚未涵盖祈令语的其他方面,如祈令语与反照之间的功能独立关系等。总之,祈令语作为斯金纳极具创新性的一个概念,仍需更为全面系统的解读。
安:当然是范·克莱本的演绎!关于你说的解构,我认为他是第一个抛开此曲极其复杂的技术,而以更高的视角审视此曲完整艺术价值的演奏家!这样的视角也是极有前瞻性的。他的演奏不追求极致速度,却是满满的音乐性、歌唱性。他无须用这首曲子证明什么,也并未因为其中的技术而歇斯底里。他把“拉三”当成纯粹的音乐。
[参考文献]
[1]Skinner B. Verbal Behavior [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7.
[2]Chomsky N. A review of B. 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J].Language, 1959 (35): 26-58.
[3]Skinner B. About Behaviorism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74.
[4]Skinner B.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operant behavior[M]//Reiber R, Salzinger K. The Roots of American Psychology: Historical Infl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77: 374-385.
[5]Lechago S A, Howell A, Caccavale M N, Peterson C W. Teaching“How?” mand-for-information frames to children with autism[J].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13 (46): 1-11.
[6]Sundberg M L, Michael J. The benefits of Skinner's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J]. Behavior Modification, 2001(25): 6 98-724.
[7]Pennington R C, Ault M J, Schmuck D G, Burt J L, Ferguson L L. Frequency of mand instruction reported in behavioral, special education, and speech journals[J]. Behavior Analysis in Practice, 2016(9): 2 35-242.
[8]Hall G, Sundberg M L. Teaching mands by manipulating conditioned establishing operations[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1987(5): 41-53.
[9]Michael J. Establishing operations and the mand[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1988 (6): 3-9.
[10]Miguel C . The generalization of mands[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2017 (33): 191-204.
[11]Rosales R, Rehfeldt R A. Contriving transitive conditioned establishing operations to establish derived manding skills in adults with severe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07 (40): 105-121.
[12]Barnes-Holmes D, Barnes-Holmes Y, Cullinan V.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and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 a possible synthesis [J].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0 (23): 69-84.
[13]王宗炎. 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 [J]. 国外语言学,1982(2):15-45.
[14]MacCorquodale K. On Chomsky's review o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1970(13): 83-99.
[15]Richelle M. Formal analysis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notes on the debate between Chomsky and Skinner [J]. Behaviorism,1976 (4): 209-221.
[16]Palmer D C. On Chomsky's appraisal o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 A half century of misunderstanding [J]. The Behavior Analyst, 2006, 29(2): 2 53-267.
[17]Salzinger K.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y, 2008 (8): 287-294.
[18]郑亚,章淑慧. 国外关于已形成事件的研究综述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5): 101-104。
[19]Laraway S, Snycerski S, Michael J, Poling A. Motivating operations and terms to describe them: some further refinements [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03 (36): 407-414.
[20]Sundberg M L. Thirty points about motivation from Skinner's book Verbal Behavior [J]. The Analysis of Verbal Behavior, 2013 (29):13-40.
[21]Chezan L C, Erik D, Mcwhorter G Z, Kristine I P S, Brooke M H.Discrimina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negatively-reinforced mands in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J]. Behavior Modification, 2018:1-32.
[22]Falcomata T S, Wacker D P, Ringdahl J E, Vinquist K, Dutt A. An evaluation of generalization of mands during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J].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2013 (2): 444-454.
Interpreting and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mand
XU Fei, FAN 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verbal behavior i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 mand promotes novel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s via non-verbal stimulus, hence the great attention from many researchers. Since Chomsky launched a fierce attack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nd by Skinner,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been devoted to improv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mand.The two most important definitions of the mand are based on established operation (EO) and motivation operations (MO).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concept of man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few studies have deeply scrutinized the mand, so the definition of mand based on MO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n view of this, through the systematic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nd, in reference to different scholars'viewpoints and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 and SDs in mand generalization, this study sets out to redefine the mand as a kind of verbal operant whose form is controlled by MO, and occurrence by SDs with new mand topographies'possible occurrence in the absence of direct training —response generalization.
Key words: the mand; motivating operation; discriminative stimulus; the generalization of mand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72(2019)01-0111-0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6CWZJ16);2016年度外研社项目(2016121604)
[收稿日期] 2018-09-05
[作者简介]
徐飞(1983-),女,山东新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讲师;
范 琳(1965-),女,山东高密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祁丽华]
标签:祈令语论文; 动机化操作论文; 区别性刺激论文; 祈令语泛化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