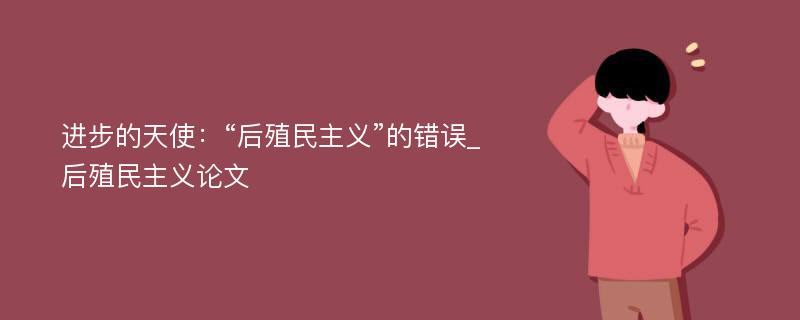
进步之天使:“后殖民主义”的迷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天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流派纷呈、新论接踵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界,“后殖民主义”正逐渐取代德里达、福柯、拉康等法国名字而成为新的“流行词”。作为一门“建立”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是收拾解构主义留下的碎片的有效工具,它摆脱“历史文本”的羁绊,面对动荡未定的现实世界,为急于“行动”的青年学者提供了一种文化干涉的战略。但由于时间短暂,批评家们对“后殖民主义”的内涵和指向还未能形成共识,争辩和反驳却也有益于日益扩展“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与国内朋友的交流之中,得知这影响已传及中国。安·麦克林托克教授作关于“文化批评”及女权主义的文章多篇,在批评界颇有影响。她的新作《进步之天使:“后殖民主义”的迷误》是译者在密执安大学一门博士课程的选篇之一,作为一家之论,译出以飱读者。本文不同于“后殖民主义”的一般倡导性文章,作者锐利的笔锋直接指向“后殖民主义”具有巨大诱惑力的“标语效应”,指出其在僭越空间的标志下埋伏了时间上的自我保守性。文章收于Colonial Dis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199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是迄今美国最全面的“后殖民主义”论文集。原文注释简短,且多为统计报告之类,故从略。
·译者·
天使的脸转向过去…他希望留下,以唤醒死者,修复破碎的世界。可是风暴从天堂刮来,巨大的力量缠住了天使的翅膀,使之无法合拢。这场不可抗拒的风暴把天使倒退着推向未来;他眼前的碎片越聚越高。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特·本杰明
观看座落于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混成状态展览》,要先进入“走廊”。在通常为画廊的地方,你发现一间灰暗的接待室,一行白字:“殖民主义”邀你向前。进入殖民空间之后,你弓背通过一扇低门,旋即陷入另一个黑色空间──举办者隐约地让你回味法农(Frantz Fanon)的名言:“土著即被镶住者。”然而,走出殖民主义之路似乎只有向前。又一行白字:“后殖民主义”邀请你经一扇稍大的门进入下一历史阶段。之后,你挺胸阔步地步入明亮而又嘈杂的《混成状态展览》。
展览内容本身引不起我多大兴趣,而体现在“走廊”的历史意识和《混成状态展览》的历史意识之间的悖论却引我思绪万千。这个展览在庆贺一种“平行历史”:
“平行历史揭示的现实是,把美国艺术分为“主流”及次要的“他者的作法不再成立。“平行历史”的存在正在改变我们对跨文化现象的认识。
然而,展览对“混成历史”(多维时间)的张扬却为“走廊”的线性逻辑所抵消,因为它只是在重演殖民主义最顽固的喻体之一。在“走廊”所包含的殖民话语里,空间即时间,历史由两个必要运动所组成,一是人类从懒散贫困的状态“进步”至挺立明朗的理性。另一逆行的运动从成年(男性白人)退步至原始的黑人,女性通常为其化身。“走廊”重演这一时间逻辑:进步沿着递升的门,沿着没有语言和灵光的史前史,沿着分为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混成理性的分期史诗。出了展览,历史被反向僭越。一如殖民话语,在空间前行的运动在时间反行:从挺立的言语意识和混成自由──漫游于展览内外被称为“自由”的白兔为其象征──向下经意义渐减的历史分期到前殖民的无言区,从言语到沉寂,从光明到黑暗。
这个展览的结构性矛盾引人深思,因为它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局限。我以为当代文化批评中“后”这个词语的仪式化的滥用现象(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冷战,后马克思主义,后种族歧视,后苏联,后福特,后女权主义,后民族主义,后历史,甚至后当代)表明历史“进步”概念中划时代的普遍性危机。
在1855年,也就是首届巴黎博览会的那一年,维克多·雨果宣告:“进步是上帝本人的脚步。”“后殖民研究”旨在抵抗帝国的线性时间,即波莱德尔所称的“进步与完美的宏论。”然而,“后殖民”这个术语,正如前文的《混成状态展览》,恰恰为它意图肢解的线性“发展”的影子所缠绕。“后殖民主义”把历史比喻为多级台阶,这台阶沿着时代之路从“前殖民”移到“殖民”,再到“后殖民”。如果把“第三世界”文学看成是从“抗议文学”到“抵制文学”到“民族文学”的递次进步的理论受到批判,因为它重操了启蒙时代关于有序的“线性”进步的喻体,“后殖民主义”理论因同样的理由也疑问重重。这个术语的喻体骑跨在新与旧、首与末的边界之间,预告一个世界纪元的结束,却又同时自我局限于赋予那一纪元以活力的关于线性进步的原喻体之中。
假如“后殖民”理论试图靠召唤其“二元纵队”(自我──他者,都市──殖民地,中心──边缘,等等)来迎战西方历史主义的大进军,“后殖民”这个语词却把世界绕单一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定位:殖民──后殖民,它的理论基点因而从二元轴心的权力(殖民者/被殖民者)移向二元轴心的时间,而时间作为轴心的政治意义则更为反动,因为它不区分殖民主义的受惠者(前殖民者)和牺牲品(前被殖民者)。“后殖民景观”发生于被悬挂的历史之外,似乎具体的历史事件已超前于我们,每时每刻不在被制造之中。如果这个理论意在对历史作“反中心化”处理,推崇混成性、合成性和多维时间,这个单数的语词实际上是在围绕欧洲时间的单元重新使世界历史“中心化”。于是,殖民主义在消失的片刻再现其身。
进而言之,“后”这个词把殖民主义之外的人类文化样式简约为“前置”时间。“后殖民”如此拱手抬升欧洲殖民主义至历史正统的地位,使之成为历史决定性的标志。其他文化与欧洲中心的关系仅仅是纪年性或前置性的(“后”或“前”)。换言之,世界上多种多样的文化样式的标志不是它们实在的独特性,而是它们与线性的欧洲时间的从属性的、回溯性的关系。
我相信单一化的历史无益于蓬勃而兴的思想与政治研究。“妇女”作为代表了女权主义虚假的普遍性的单一范畴已失去信用,因为它无法区分妇女之中多态的历史和不平衡的权力。同理,“后殖民主义”的单数性也许易于助长全景式的世界观,但却以范畴的抽象来消抹政治上的复杂性。于是,地平线上宏伟的全景变得如此辽阔以至于国际社会间不平衡的权力模糊不清。抽去历史内容的语词如“他者”、“所指”、“能指”、“主体”、“法老斯”(phalluo)与“后殖民”尽管有其学术效力和职业专门化的市场价值,但很有把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特征放大到无影无踪的地步的危险。
最近有人从如下三个方面维护“后殖民文学”:它“注重于在创作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想象力和心理刺激的那种关系”,它“表述了建立在共同传统基础之上的群体意识的理论依据”,它“指向更自由、更实际的未来。”然而,这种把历史规结于单一“延续的使命”和“共同传统”的作法忽略了观照我们至今对之理解甚少且缺乏适当理论归纳的重要的国际社会特征。这些人还自以为是地断定,“后殖民主义”并不是指欧洲殖民主义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而是涵括自殖民主义以来所发生的一切。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倒拨时钟,把“后殖民主义”的版图扩展至1492年或更早些时候。于是,他们大笔一挥,亨利·詹姆斯和查尔斯·布诺克顿──仅举两人为例──便从沉睡的时间中唤醒,被引入“后殖民景观”,与象恩枯格瓦·斯昂果和沙曼·拉什迪这样的常务成员为伴。
更让人担忧的是,介词“后”暗含的历史断裂抹去了构成前欧洲殖民帝国遗产的延续与断续的权力,且不论伊斯兰、日本、中国等殖民强权。文化之间的政治差异因而从属于它们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时间距离。然而,“后殖民主义”一如后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独立于西班牙帝国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阿根廷和香港的“后殖民”并不一致(后者到1997年才能脱离英国)。巴西的“后殖民”与津巴布韦也不一样。宣称世界各国共享一个“传统”或“条件”即“后殖民条件”或“后殖民性”有何理论上的意义?毫无疑问,非洲殖民史的很大一部份是欧洲帝国与阿拉伯帝国、无数非洲部落和文化内部碰撞的历史。这些国家能够说是欧洲殖民化“共同”经历的唯一结果吗?事实上,当代许多非洲、拉美、加勒比海和亚洲文化虽然受殖民化的影响深远,并非仅仅从根本上纠缠于她们同欧洲昔日的接触。
在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在许多场合却是过早地自我庆贺。爱尔兰也许可以硬凑为“后殖民”,可是对于英占北爱尔兰的居民,殖民主义远非“后”,更别说居住在以色列占领区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南非是“后殖民”吗?东泰莫尔呢?澳大利亚呢?历史健忘症的何种魔法又能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后殖民”的一员呢?我们也可以问一下,自1992年以来逐渐兴起的欧洲堡垒是否意味着一个新帝国的兴起,一个目前还未能确定自己的疆域和全球影响范围的新帝国。
这里我对“后殖民”的忧虑并不在于它的理论内容,其大部份我倒是非常赞同的。我只想质问一下这门新兴学科建立在一个单一的且又包罗万象的语词之上的理论取向及其共生理论与革新的课程内容。由于其结构的中心是时间而不是权力,因而它在过早地庆祝殖民主义过时的同时却有可能抹消殖民和帝国权力的延续与断续。我并不想把这个语词流放到言语的爪哇国里去,它完全有理由在适当的场合,在由其他语词限定的语境里被谨慎地使用,而不应充当宏大的全球性的角色。
也许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区分控制世界的多种模式。殖民化是对一个地理政治实体领土的直接占领,并同时赤裸裸地剥削其资源和劳动,且依靠对其文化(不必是一个单质的实体)的系统性干涉来组织权力的分配。内殖民化是指一个国家内的强力派别象对待外国殖民地一样对待某一群体或地区。依此而推,帝国殖民化涉及大规模的领土占用,如过去维多利亚英国和欧洲的“人类救世主们”控制了全球的85%,又如本世纪前苏联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强权统治。
殖民化一般只涉及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在东泰莫尔、以色列在被占领区域和西岸、英国在北爱尔兰都是范例。自1915年起,南非的殖民铁靴践踏着纳米比亚的土壤,她先以国联的名义,后则无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1971年国际法庭的裁决。直至1990年,在纳米比亚的钻石资源几乎被掠夺已尽的情况下,南非才同意把这个经济空壳还给纳米比亚人。以色列占据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一部份,土耳其占据了塞浦路斯的一部份。所有这些国家在法理上都不能称为“后殖民”。
殖民化的多种模式于是产生了非殖民化的不同方式。在阿尔及利亚、肯尼亚、津巴布韦和越南这些移民殖民地,殖民权力靠特别野蛮的武力自守,非殖民化运动的胜利往往很不平衡。津巴布韦经历了残酷的七年内战,其最激烈时期每月死亡500人,多达40%的国家预算用于军事开支。英国在1979年策划的“兰开斯特协定”保证津巴布韦三分之一的可耕地(四百万公顷)为白人所有,而白人只占总人口的极少一部份。换言之,虽然津巴布韦在1980年获得了正式的政治上的独立(1986-1989年任由103国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主席国),在经济上,她的非殖民化却是不完全的。
脱离移民殖民地的特点是她们从宗主国获取了形式上的独立,而又对被夺取的殖民地实施持续的控制,但这殖民权力已从宗主国让位于殖民地本身。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属于未经非殖民化的脱离移民殖民地,除了南非以外,她们将来非殖民化的可能性很小。
有些国家以她们与昔日的欧洲主子而言也许是“后殖民”,但以她们的新殖民邻居而言却并非如此。以莫桑比克和东泰莫尔为例。七十年代葡萄牙帝国瓦解,这两国几乎同时变为“后殖民”,然而,“乌托邦”的理想与介词“后”的世界浪潮却未能带来福音。葡萄牙人前脚刚走,印度尼西亚人后脚就踏进了东泰莫尔,其结果是至今已二十多年的一场尤其血腥的殖民统治。对东泰莫尔的殖民奴役,联合国基本上充耳不闻,这是那些“口袋不深,说话不响”的国家的众所皆知的困境。
经过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莫桑比克的社会主义独立运动终于在1975年赶走了葡萄牙人。一墙之隔的罗得西亚白人敌视莫桑比克的独立和其社会主义倾向,扶植了“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MNR)”,由一伙专事毁灭的土匪军人组成。MNR十年之久的杀戮加上南非的掠夺使莫桑比克血流成河,近两百万人流离失所。迫于内战的残酷性,社会党人只得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考虑与土匪讲和。一个潜在的“后殖民”的样板变成了南部非洲的屠场。
不管是“后殖民”还是“新殖民”都无法解释MNR现象。新殖民主义不是对殖民主义的简单重复,也不是黑格尔式的“传统”和“殖民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历史混合物。近几年,MNR更紧密地与地方部落纠纷、宗教信仰冲突及时间与报应的观念(尤其是祖先干预)联系在一起,根本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西方的线性时间。
“后殖民知识分子”这种单一的普遍性范畴抹杀了文化权力、电子技术和新闻信息传播上国际间的差别。“后殖民理论”中的非洲与非洲的“后殖民理论”大不相同。198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估算非洲仅占世界用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二千零七亿美元的0.3%。1975年整个非洲大陆仅有180家日报,而美国有1,900家,世界总数是7,970家。1980年非洲生产了70部电影,与之相比,亚洲在1965年就生产了2,300部故事片。印度是世界第一电影大国,而非洲的电视接受机、收音机和其它电子硬件的占有量微不足道。
“后殖民主义”在妇女问题上尤其软弱无力。在今天的世界,妇女干2/3的工作,挣10%的工资,拥有不到1%的财产。“后殖民主义”缄口不言受益于“后殖民”“进步”和工业“现代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掠夺阶层绝大多数是男性。没有哪个“后殖民”政权在权力和资源上给予男女同等机会。不仅“后殖民国家”本身基本上是男性冲突、男性理想和利益的产物,就是“民族权力”也是前期性别权力构造的再现。既使在法农──一个往往很明事理的人──看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也是自然地同为男性:“土著人对殖民者的目光是嫉妒的目光……上殖民者的餐桌,睡他的床,拥他的妻,如果可能的话。被殖民者是个嫉妒成性的男人。”尽管多数民族运动充满联合大众的语词,实际结果往往是使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制度化。婚姻法通常规定妇女的公民权必须通过婚姻关系的中介,所以妇女与国家的政治关系从属于她与男人的婚姻关系。
殖民主义不是造成妇女持续困境的唯一原因,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新殖民”两难处境的脚注而轻松地忘掉。由于男子自我经济利益的重复和以父权为中心的基督教、孔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多重牵制,妇女继续被合法地阻挡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大门之外,遭受不公平的教育机会,家务的双重之日、不平等的孩子抚育任务、性暴力、性器人为致残和丈夫虐待。虽然这些偏向男性的政策与殖民主义有共生的关系,但它们不等同于殖民主义,因此只能用有关性别权力的理论来解释。
象“后殖民妇女”和“后殖民他者”之类的虚假的普遍性范畴不仅模糊了男人与妇女的关系,也模糊了妇女之间的关系,一个法国旅游者和替她洗床单的海地女人的关系不同于她们与丈夫的关系。《走出非洲》之类的电影,“香蕉共和国”之类的服装连锁店以及“狩猎之旅”之类的香水都在兜售新殖民的纪物念,以召唤欧洲女人穿短衫和猎装的时代,她们管理咖啡农场,猎杀狮子,驾机巡游殖民者的蓝天──帝国里所谓的自由。可是,这种白人妇女“解放”的可鄙的商业化无助于任何地方有色妇女与白种妇女的联盟,更不能化解仇视女权主义的男性民族主义者的攻击。
前文谈到“后殖民主义”在当代学术、知识界的流行以及介词“后”的滥用反映了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的一场全球性危机,尤其是“进步”思想的危机,而这场危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进步”思想的第一次大转向源于80年代美国第三世界政策突然转向。挟50年代的“经济起飞”之勇,美国相信其它国家如果走美国的大众消费之路也能“进步”。W.W.罗斯托的“非共产主义宣言”认为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将摆脱传统造成的贫困,经历相似的发展过程,在美国、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组织的监督之下通过工业化达到大众消费的繁荣,可是除了日本“奇迹”和亚洲“四小龙”之外,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至40年代以来却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制订的消费水准。
从1977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之间,世界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人们逐渐认识到美国不再注定是未来唯一的经济大国。巨额债务和日本与德国的双重进逼迫使美国迅速放弃了“进步”与“发展”的全球性策略。里根时代,美国对贫穷国家奉行以威吓为主的债务政策,同时又在市场上凶狠地竞争,不时还挥舞军事干涉的大棒。许多贫穷国家不得不紧缩腰带偿还债务以维护基本信用。1974年非洲的外债率仅4.6%,13年后猛升至25%。美国“进步”模型的失败,对许多政权而言,也就是它们民族政策合法性的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全球性的经济恐慌、生态灾难和不断加剧的大众绝望心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能不说与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进步”模型的失败有关。正如利比亚政府一位资深官员针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阿尔及尔的命运所言?“掉头转向已不可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历史达成了一个协议,它不会错过机会。”
于是,世界各国被纳入一个单调的发展图案。尽管殖民主义在50年代就卷起了大旗,重起的经济帝国主义保证美国和欧洲的前殖民强权变得更富,而昔日的殖民地除极个别的特例外变得更穷。世界银行在非洲的开发项目支持形式上的非殖民化,但真正的受益者却是跨国公司的冒险商人和当地的强人与独裁者。在经历了绝望的80年代──债务、干旱和动乱──之后,黑非洲人为和自然的灾难仍然有增无减。二千八百万非洲人面临饥饿,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扎伊尔和苏丹等国的经济已彻底崩溃。
美国的“发展”神话对世界生态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至1989年为止,世界银行为贫穷国家作出了二千二百五十亿美元的承诺,条件是她们必须承受“结构调整”的炼狱,以出口换进步,裁减政府在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妇女首当其害),贬低本国货币,消除贸易障碍,砍倒森林以偿还债务。“四小龙”的代价是污染的水源,中毒的土壤,赤裸的山坡和死去了的珊瑚海。在台湾,估计有20%的可耕地为工业所污染,30%的大米含超安全标准的重金属、水银和镉。世界银行1989年的一份报告沮丧地承认“调整开发项目”的副作用是贫困线以下的人在健康、营养和教育方面有可能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目前,日本因其对木材和原材料填不饱的胃口成了主要外援国,每年给出100亿美元。简言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进步之路”已证明不过是通向苏珊·乔治谓之为“比债务更糟的命运”的死路。
美国“进步”神话瓦解之后紧接着的是苏联的崩溃,与之陪葬的是共产主义关于“进步”的大叙事,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黑格尔──马克思的曲线“进步”和官僚管理的计划经济必将逃避不了其乌托邦的命运。苏联帝国的灭亡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某种特殊历史关系(即线性的或间断性的线性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官僚经济在提供充足的全民消费方面有一天将超过美国的幻想的终结。工人阶级(其实是白人)作为历史的特殊主人的政治信心也因此丧失不少。苏联官僚阶层的失败不是由于民众运动而是由于经济腐败和疯狂的军费开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和德国经济上升与两国在历史上被迫卸除了军备竞赛的压力有关。所以,尽管人类在全球各个角落相互杀戮,人们已多少失去了对男性军事主义作为历史“进步”的保证因素的信用,而由科技开发推动的工业“进步”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遇到了自然资源的局限。
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而言,“进步”既是前进之旅,也是回程的起点,因为在所有关干“进步”的叙事中,走“进步之路”只不过是走已经走完的路。“路”或“铁轨”的喻体表明“进步”只能用于完成时态。旅程可走是因为路已事先修筑好了──上帝、辩证法、史之鉴、市场规律、科学唯物主义,等等。正如黑格尔所言:“进步”在历史王国里之可能是因为它在“真理”王国已经完成了。可是,如果智慧之鹰已展翅飞去,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飞回。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关于“进步”的目的论的双重瓦解加剧了未来时间意象的危机。世界形势的动荡不安助长了一种为历史所抛弃的绝望之感,暗含时间停滞之意的语词“后”的广泛使用便是其症兆之一。“进步”的风暴曾经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助威助力。现在风停了,耸翼的天使对着脚下的一堆废墟沉思不语。在“历史的尽头”的平静里,2000年来得太快,空气里充满了不祥之兆。历史被宣称已经死亡,因为资本主义取得了对共产主义最后一战的“胜利”,现在成了“后历史”。可是第三世界依然滞留在“历史”的王国,那里武力依然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宣称“历史的尽头”和美国消费资本主义的胜利还为时过早。现今世界秩序更有可能是日本、美国、欧洲堡垒和中东四个决定性区域之间的多元竞赛。军火贸易将继续进行,军事工业的死亡之神将把注意力从冷战转向往复持久的耗费战。它们将是由美国雇佣军及其代理人出人、由日本和德国出钱的战争。在美国国内,军事主义在失去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假想敌之后将寻求新的敌人,如毒品贩子,国际“恐怖主义”,日本,女权主义者,“政治正确”的倡导者与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同性恋者和国际社会“少数民族”群体。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迫切需要创立有关历史、民史,尤其是大众媒介传播史的新理论。我们面临的不是什么样的语词可以准确地替换“后殖民主义”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理论语词的大旗,不管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都无法完全覆盖现今多元历史与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势。干预历史并不是重披“进步”的披风,重操“经验主义”的鹅毛笔。法农早已断言:“客观性总是与土著人作对。”我们应该呼吁富于清醒历史意识的理论和战略,以便于我们更有效地投身于结盟的政治,向现存灾难性的权力分配制度挑战。如果在无理的现实面前怯步,我们将面临在一个历史的虚空里被驯化的危险,那时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后视身后的时代,因而被锁在标着“后”的永远的现在里。
李点 译
标签:后殖民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