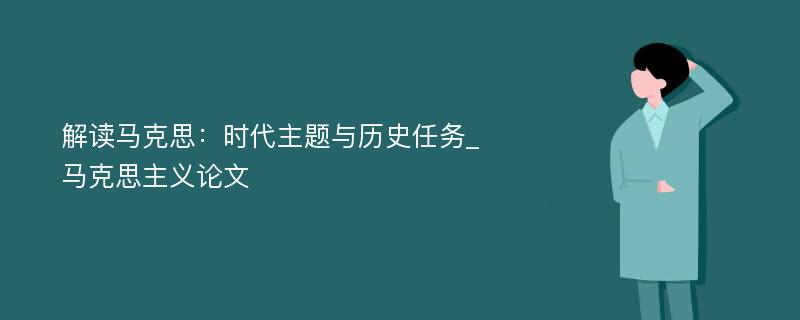
阅读马克思:时代的主题与历史的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040-04
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变得陈旧,他的思想不是像凡尔赛宫那样 的缅怀一个过去时代的纪念碑,而是以亲切的态度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读者。然而,正像 许多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思想也面临着被不同的诠释者分割、拆解 并重新赋值的历史境遇。一个操着黑格尔式辩证法术语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伦理 学的马克思,一个宣讲着末世论的宗教学的马克思,一个在青年激进、在晚年却陷入困 惑的马克思,一个摇摆于爱欲与死欲之间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不同的理论目的与 不同的价值选择造成了对马克思的不同理解,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马克思只有 一个,马克思的形象却多种多样。如何看待这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马克思的肖像?这就 需要将阅读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
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在事实上改变了世界,而且表现在他在观念上改 变了世界。由于马克思理论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人们不得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对 马克思的观点作出回应。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你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 ,但无法绕开马克思。
马克思对当代理论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马克思的名字仍然频频出现在当代各 个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中,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卓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 法国的萨特与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 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 他却在苏东剧变、理论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公开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敬 意。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虽然曾明确表达对马克思理论的批判态度,却 没有放弃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反而向世人宣布“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英国首相 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认为马克思虽然不再时髦,但仍然值得人们关注。美国后 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则一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勇敢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这些思想家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在各自的社会科学领域中 执掌牛耳,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重视不是出自盲目的信仰,也不是出自政治的压力, 而是出自现实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源自于对资本主义时代重大历史问题的独立思考 。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确是当代人文学科学研究“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其次,马克 思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渗透到人文社会科 学的各个主要领域,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研究 领域,都可以发现马克思思想的痕迹。人们已经习惯于将马克思的名字置于亚当·斯密 、施密特、马克斯·韦伯、沃勒斯坦、福柯等的名字中间去比较、去讨论。可以说,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仍然为许多理论家所津津乐道甚 至争论不休,而在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时候,人们也总要 不断地返回到马克思汲取理论资源。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早已充分渗透到人文社会科 学各个学科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而不仅仅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 工。
以上分析有助于提醒我们:马克思并没有过时,他的思想仍然对我们现在的理论生活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必须不断地阅读马克思,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正如德里达所 言:“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 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 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机构(国家、政党、党支部、工会和作为理论产物的其他方面)全部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时 ,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而辩解。没有这种责任 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 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 种精神。”[1](P21)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仍然继续发展的今天,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以及它所具有的对当今理论界广泛而巨大的 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其中不乏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 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从中获取理论的灵感和方法的启示,才能对新出 现的现实问题作出理论概括。于是,阅读马克思重新成为一种理论风尚。这样,在我们 面前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的读者,也出现了林林总总的对马克思的解读。笔者认 为,对于这些解读不能简单地进行肯定或否定,必须将对马克思的阅读这一现象本身进 行反思,而将阅读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出,就意味着对阅读进行反思的开始。
首先,反思意味着怀疑。近代乃至现代哲学的发展证明,只有永不寂灭的思想的怀疑 能力,永不停止对明晰与确定的东西的质疑,经常性地探讨所谓常识的思想根据,对被 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另一面”保持持续性的关注,哲学才能得到发展。对马克思进 行反思性阅读,就是要摆脱对马克思的习惯性理解,直面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对马克思 进行再次阅读。中国的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不陌生,甚至耳熟能 详,然而“熟知并非真知”,越是熟悉越是不加思索,这比思想错误更可怕,因为思想 错误是一种“破坏”,而没有思想则是一片“荒芜”。
苏联、东欧的剧变,不仅改变了现实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着巨大 的震荡。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构也随 之消亡,苏联时期关于马克思的一整套解释体系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人们开始对那 些已经习以为常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和结论进行反思,并对思想中预设的理论框架进行 全面的检验。我们知道,在苏联时期,对马克思解读的最大失误就在于使马克思理论与 苏联的政治制度直接发生关系,使马克思的思想高度政治化,把马克思变成政治的装饰 品,于是,马克思思想不再作为权力的目标,而是作为权力的手段,制约着人们的独立 思考。这种手段的具体化形式就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它一方面建立了完整而融贯的理论 传统和方法学训练,把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分类,并将这些基本观点和 概念以简明清晰的叙事形式表述出来,为马克思思想的普及化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 但另一方面,苏联教科书的学术研究体制也通过学科规训的方式将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 教条化、统一化、规范化。这种教科书体制本身兼具知识及权力的双重含义,既是一种 知识形式,又是一种权力技术。它通过频繁而严格的考试检查、考试评分、大量的学生 收写作业,控制着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从而生产、积累、流通着权力的意志。苏联教 科书对马克思的解读模式成功地冻结了人们精神思考的独立性,在这里,马克思的思想 被令人难以想象地简单化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成为一种十分干瘪的、与现实并 无关系的东西,但人们依然得把它们当作一种学说来相信,不得提出疑问,任何个人思 考的努力,任何批评的态度,任何精神的自觉性都被排斥,人们被要求像坚信《圣经》 一样坚信教科书体系。苏东剧变使人们从苏联教科书的正统解释体制中解放出来,人们 可以从容地探讨以往研究中被人所忽略的理论问题,对已有的权威性解释进行重新思考 ,对当代社会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全新的理论诠释。更重要的是,这种解放促使人们抛开 苏联模式的束缚,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重新面对马克思的原始文本,重新品味那些最根 本的阅读感受。事实上,与苏联教科书所传授的冷冰冰的马克思的形象相反,马克思的 文本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它是强有力的逻辑与华美的修辞的完美结合。重读马克思的 文本,也让我们去重新体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并在他对各种事件的评述中体会马 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从而达到对马克思的切实的理解。这种理解本身就是一个 对马克思进行再发现的过程。而在这一再发现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反思以往阅读的成 就与失误,去反思各种阅读方法的得失成败,从而达到方法论的自觉。
其次,反思意味着二度思考。在德语中,反思即后思(nachdenken),即跟随在事实后 面的反复思考,将原已思考过的东西再思考一遍。马克思主义诞生将近一百六十多年以 来,对马克思的阅读从未间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厚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 其中不乏熠熠生辉的名字:普列汉诺夫、列宁、卢卡奇、葛兰西、卢森堡、阿尔都塞… …但这些大思想家并不能保证我们对马克思理解的正确性,真正的阅读就是要“跟着” (nach)这些大思想家一起去思考,把原已思考过的问题再思考一遍。二度思考意味着双 重阅读:读马克思本人以及读马克思的读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通过一系列的科 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想象的方式被人为建构起来的,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 自身的历史、思维、意向和词汇传统,同时也隐含着阶级、政治和权力关系。这是因为 ,阅读马克思的不仅有马克思的战友、学生和追随者,也有他的论敌和反对者;不仅有 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也有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相隔久远的当代思想家;不仅政 治领袖阅读马克思,纯粹的书院中的学者也阅读马克思;人们不仅通过各种文本——德 文版、英文版、意大利文版、俄文版、中文版——来阅读马克思,也通过各种对马克思 的解释性读物来了解马克思,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个体的生活经历来阅读马克思。因 此,不同读者眼中的马克思的形象自然不同。比如,在1932年以前,人们主要依据《资 本论》和表征马克思“新世界观”基础、核心、纲领和思想构架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理解马克思,把马克思视为一位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他教导工人阶级为推翻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斗争。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发表,引发了把马克思思想人本化的思潮,这就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起 点。对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胡克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被 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奇异景象,即卡尔·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弄得困惑不解。他的第 二次降世不像是《资本论》的作者那样身穿风尘仆仆的常礼服的经济学家,也不像革命 的长裤汉,《共产党宣言》中很有鼓动性的作者。他穿上了哲学家和道德预言家的衣服 ,带来其作用超乎阶级、政党或宗派的狭隘圈子的关于人类自由的喜讯。”[2]随着被 称为“历史学笔记”的《编年摘录》和“人类学笔记”(包括“摩尔根笔记”、“菲尔 笔记”、“拉伯克笔记”、“梅恩笔记”、“柯瓦列夫斯基笔记”)的发表,人们又开 始关注一系列新的问题: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不集中精力完成《资本论》的写作而关注远 古与东方的情况?他在体衰多病的晚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欧美人类学家的人 类学著作,其目的是什么?这种研究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研究重心的转移?由此,人们似乎 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他是一位被暮色笼罩、受着疾病折磨的历史老人,由于关于 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落空,马克思的革命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化成了泡影,晚年的马 克思陷入了“困惑”之中。于是,他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势将视线射向东方,开始寻找新 的理论出路。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形象并不是一个现成的形象,相反,他的形象是在时 间中被“建构”起来的。所以,不论马克思为人所推崇、所称道,还是为人所非议、所 排斥、所指责,人们都只能依靠对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对读者的身份立场、对阅读方法 与结论进行反思,才能评价某一解读是否合理。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马克思的 形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同时也在于人们是怎样建构起马克思的这种形象的;不仅在于我 们阅读到了什么或我们应该怎样阅读,同样也在于在我们所阅读的背后发生了什么。
最后,反思意味着批判与重建。唯有出现障碍时,反思才会产生。如果不是传统的阅 读方式遇到困难,如果不是传统的解读模式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说明现实的实际问题,那 么,对阅读的反思就不可能发生。在马克思的阅读史中,对斯大林解读模式的批判出现 了以人、人的异化、人的解放为中心范畴的人本主义马克思,而对人本主义马克思的批 判又形成了结构主义马克思……在这里,阅读中的困难往往可以成为新的理解的契机, 诚如诗人荷尔德林所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愈是接近危险,通向拯救之路 就愈益明亮。”对马克思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只有在不断的 批判与重建中才能树立起来。
苏东剧变曾一度使人们对共产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对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产 生怀疑。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也许不是马克思而是人们阅读马克思的方式和方 法出现了错误,于是,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与研究人们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方式成 为评估马克思理论正确性的两条主要线索。对于第一个线索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 确立马克思的本真形象,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回答马克思思想究竟“是什 么”;对于第二个线索而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考察人们是“怎么样”阅读马克思的, 也就是考察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解说背后的立场和方法。事实上,“是什么”之类的 问题是蕴涵在“怎样是”之类的问题之中的。这是因为,任何阅读总是有条件的阅读, 任何读者都必定属于某个历史时代、某个阶层、某个民族、某种文化,每个读者的阅读 视域都要受到社会环境、历史景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的制约,并且, 每个读者都是带着自己的时代问题去阅读马克思的文本的。以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 为例,在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期间,人们将其主旨意图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 裂”、“两个不可避免”;近年来,人们又从同一文本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思 想,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提供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研究视野及理 论问题,从而使马克思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中的不同方面凸现出来。如果能够对“怎样 是”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是什么”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以“怎样是”的问题去涵盖“是什么”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摆脱“独断论”与“ 相对主义”的干扰。“独断论”指以一种权威的姿态从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理论态度。 独断论者往往将自己对马克思的某方面研究看作是理解的真理,认为只有自己才勾画出 了“本真的”马克思的肖像,从而拒绝承认对马克思理解的历史性与多元性,认为存在 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解释框架,借助这些解释框架,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达到对马克思思 想的正确认识。苏联教科书体系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框架,这种解释框架要求读者将其 视为包含着绝对真理的神话,读者可以在这个解释框架里达到对“本真的马克思”的理 解。而相对主义则从根本上否认本真的马克思的可能性,认为“我们不是非得要得到马 克思的同意——他甚至在未死之前就反对这么做——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而是要继 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观点。我们不是非得要假设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意见是 一致的”[1](P49)。在这里,马克思变成了一种激进政治的象征,一个造反的符号。至 于马克思到底说了些什么、马克思的原意是什么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只是读者 对马克思的理解。究其实质,相对主义与独断论一样,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相对主 义者那里,马克思的形象变成了一种主观的、为我的存在,人们可以依据实用主义原则 随意制造马克思的形象;在“独断论”那里,马克思的形象则被专断地、唯我地凝固化 了,并被排除了任何异质性的可能的解释。笔者认为,阅读必须遵循马克思思想的内在 逻辑,努力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本真含义。任何否定存在有马克思的本真的意义的观点都 是错误的,然而,人们要达到对马克思本真含义的认识却是一个逐步逼近的历史过程。 人们只有通过对各种已有的观点进行不断的批判和反思,才能重建马克思的本真的形象 。这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同观点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相互批判的过程。
收稿日期:2004-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