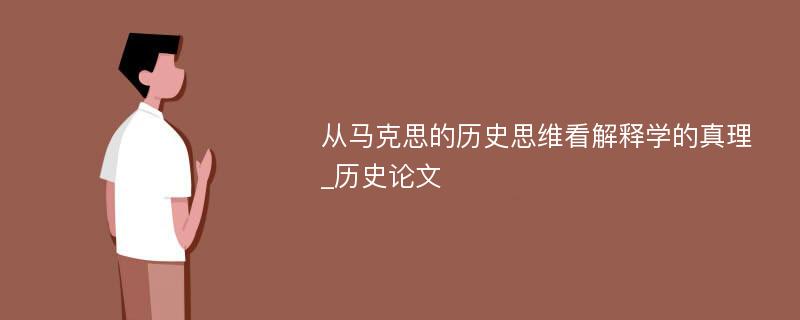
马克思历史之思对诠释学真理的洞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真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存历史性的本真道说
马克思说: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马克思这里重点突出的几个关键词耐人寻味,它们直接指证着“自然物”和“人”的区别。马克思曾说过,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由此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动物的本性是前定的。其二,动物受其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所约束。一言以蔽之,动物的本性是现成的,是依照某种先在模式的被规定。由此说来,一切自然物固然都是永恒变化的,但它们的存在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而要服从盲目的线性因果联系。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是通过“感性活动”——“异化劳动”是特定表现——而自我创生的。而且,这种创生具有普遍性——“工人”还生产出“其他人”。这表明马克思真正抓住了人的根本,崭露了人之为人的初始根据地。
所谓人的自我创生,是说人固然不能没有自然生命,但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现成的自然生命体,相反,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必定要通过自己的现实活动而自我筹划自己的生活。就此试问:人开展自身的基础究竟何所在?问题的这种提法已然需要上升到生存论的存在论高度来思考。在此,海德格尔的直白论说,把马克思未曾明言的对人的生存时间性的承诺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在世本质上就是“操心”,时间性乃是人生存在世界臾不可或缺的生存论基础,人正是在“时间性”中才完成了自我创生。
显然,以海德格尔关于此在操心结构的深思为参照,马克思“人之自我创生”所蕴涵的深意就可以得到解读,由此也确证着马克思把“历史”与人“自己的形成过程”相勾连的合法性。可见,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沉思中已然道说着人的生存故事,指证着人原本就是历史性的存在物,以及历史性之于人的源始性。无须赘言,这一伟大发现是超越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关节点。而且,从诠释学之为自身的自律性来看,这里具有两点意义:其一,诠释学经过海德格尔的转向,遂把理解看成是人的生命本身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激动。就此而论,马克思对于生存历史性的承诺,就先行为诠释学的这种确当性做了奠基。其二,马克思的所论在“现身说法”的意义上实行着这样一条诠释学原理:理解一个文本,不应仅仅停留于作者之所说,还要澄清作者何以说;不应仅仅执于作者的话语,还要阐扬话语之所云亦即话语所传达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海德格尔20世纪在生存论基础上开展的诠释学转向,不仅确证着19世纪的马克思面向生活世界而持守的生存论哲学路向,而且还在与马克思的“交谈”中不可避免地获致思想上的开启。由此我们便要追问:在海德格尔伟大转折的对照下,马克思之于诠释学还有怎样的深入?
二、历史的可理解性
马克思说: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从此有这样的推论:虽说生存历史性乃是真正的源始性,但一点也不神秘,它能够被认识而得到现实的澄明。既然是认识,就必定牵扯到人的意识。当下的任务就是要关注马克思对“内在性”的基本态度,从而展现意识在马克思哲学境域中的基本含义。
近代哲学的“内在性”,肇始于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由黑格尔在绝对精神基础上论证“思有同一”原理而形诸为体系。从实际影响来看,以“内在性”为存在论基础的近代哲学,高扬“真理内在于人心,人心可以把握真理”的信念,达到了对于近代社会精神气质的建构。然而,近代哲学执于意识“内在性”所谓的无所不能,用逻辑思辨遮蔽着“内在性”的来历,就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由之毕竟要对这一世界的故事进行彻底的歪曲,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论说乃是有力的证明。
黑格尔只是在思辨的过道上匆匆看了历史一眼,让历史从属于精神并由精神规定其存在范围。很明显,这是真正的本末倒置。而且,从性质上来看,“内在性”是一个封闭的区域,虽说可以在内部“不停息的旋转”,但企图“出来”而贯穿对象领域乃是十足的自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内在性”必定要把对象“嵌入”自身,使对象成为“正在消逝的东西”。这样,通过“内在性”来把握历史,历史自然就被葬入虚无而变成“非存在”。
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思维“内在性”乃是由“现实生活过程”的源始历史性派生出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源始地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活动”或“感性活动”而自我生成,意味着人乃是“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就是“对象性的存在”。这里需要明确,对象之于人,在近代哲学视域中被逻辑认定是二元劈分关系中的客体,但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对象是另一个感性存在着的人。人与周围世界乃是原初地关联,人的生命存在本来就是敞开的,或者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惟有人才坠入追赶“绽出之生存”的天命中。
马克思明察到意识终止于现实生活面前,遂在人的生存筹划历史性中确立了意识之来历,从而凸现了意识与历史的必然关联。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意识已然具有概念前的原初性,有着全新的追求和承当,其基本思想可以从马克思所说的“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来予以体会。在这种意义上,作为“感性意识”的人的意识,与其说是意识,倒不如说就是存在,恰如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意识”所期许的那样。由意识与历史的必然牵挂,我们看到,意识之“认识”历史乃是铭记“自身”。换言之,我们从马克思语境中“看”出了意识不可悬置的此岸性。基于此,人的意识认识历史,乃是人操持自身的呈现,是人之生存的自我把握和自我领悟,从而真正是人的自我造就。
就此看来,当代诠释学所操持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呈现了马克思历史之思隐而未发的诠释学寓意。
三、历史性生存的人扬弃自身
马克思说:历史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作为”形成过程,直接申说了人不能指望着能够被给予一个理想化的生存环境,而是注定步入自我创生的生存之路。马克思在此不仅再度强调了人的“绽出之生存”而与前面的论述相呼应,而且,这里的“作为”结构显示了人的生存历史性是与“现成性”绝缘的,从而执于逻辑范畴的非历史地描画就是对人的宰制。易言之,由此“作为”结构我们所照面的乃是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过程”的生存论哲学路向。
既然是自我创生的命运,人就必定要沉沦于探索和尝试之中,于是,人的生存迎面而来的是大于现实性的可能性,是多于确定性的非确定性,是高于现成性的选择性。就此说来,人不仅必须义无返顾地就生存可能性做出决断,而且还必须时时刻刻审视和考问自己的生存状况。如此这般的行动肯定不能是人时可有时可无的率性而为,而是人操心生存的基本需要。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激情是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规定,从而人的行为皆出于自愿。就此而论,人“有意识”地扬弃自身,乃是生存历史性的常规现象和当然要求。
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是用“自我异化”来指证资本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从而“自我异化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状态下人的现实生存的基本努力。既然二者“走的是一条道路”,那就有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判断:资本社会人的异化生活为扬弃这种生活做了准备。这就呈现了马克思批判否定与实证肯定相结合的理论品质。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所说的人“扬弃自身”,就不是指人消极地逃逸或让自身虚无化,而是自身生存的激活,表现为行程乃是人的现实生活,表现为结果乃是人的成长进入崭新的阶段,真正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海德格尔曾把语言视为人的“寓所”,伽达默尔也认为语言是人在世存在的基本活动模式。照此说来,人“扬弃自身”是否也有指向“语言”的要求?马克思实际上已然展开并执行了这一要求。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之后虽说涌现了批判和叛离这位大师的风潮,但是,“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这一“本质的”问题仍告阙如。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无疑涵纳着把扬弃这种形而上学语言对人的专制作为人“扬弃自身”的当然任务。
如果说马克思的这一洞见具有隐然未发的性质,那么,海德格尔作为形而上学反叛者明确开始的对形而上学语言的批判,自觉不自觉地给马克思作了注解。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霸占了语言,造成了“语言之荒疏”,其突出症候是“技术”语言的盛行。于是,当人们热中于技术语言来想人,以为能够切近于人,实际却疏远于人。所以,一力于“思想的技术阐释”的形而上学语言,当然是人筹划生存所不能容忍的。
我们知道,揭破形而上学语言对人的戕害,高扬语言之于人的意义,这不光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兴趣,也是当代诠释学的理论重镇。就此而论,马克思具有先行者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