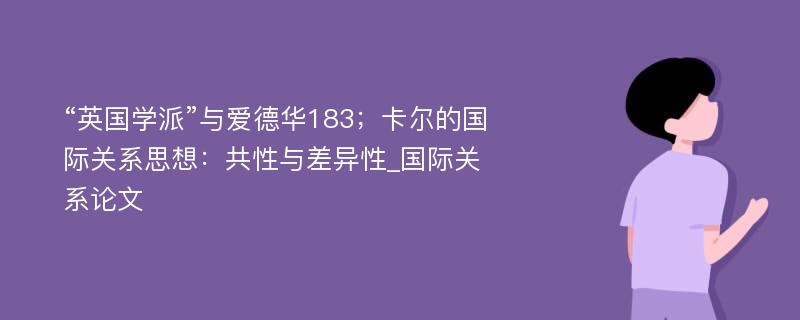
“英国学派”与爱德华#183;卡尔国际关系思想:共性与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德华论文,卡尔论文,英国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5-0030-04
英国学派与爱德华·卡尔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由于两者都坚持欧洲的学术研究传统,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联系一直颇感兴趣。有一种观点认为,卡尔是英国学派的经典作家之一,或者是英国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P362)。另一种观点认为,卡尔不是英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会成员,并且他的现实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因此被排除在学派之外。
本文认为,两者既有共性,也有显著不同。鉴于英国学派和卡尔都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议题,本文仅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共同的“理论综合”努力
“英国学派的独特要素就是它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它的历史主义以及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2](P471)。英国学派试图综合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把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3R传统)看做共同起作用的三个因素;其方法论基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三分法,以国际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国际社会理论为核心,以世界社会的可能性为理论扩展的领域。这种三分法是英国学派突出的方法论特征,分别与3R传统相对应。
国际体系是基本思想。布尔指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影响并形成某种行为,国际体系就出现了。国际体系与国家间权力政治有关,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结构及其作用过程,权力与国家利益观念起到“控制或惩戒”的作用。怀特则使用“国家的体系”阐述国际社会。他认为国际社会是一个国家联合体,它们之间有可能因共同的文化纽带而彼此承认,并认同它们所组成的整体[3](P234)。国际社会是比国际体系更高一层的国家联合体,国际体系是国际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而国际体系可以在国际社会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存在[4](P7—9—10)国际社会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国家接受共同行为准则,共享规范和制度,这是理性主义理论阐述的核心,规则、程序和国际法起到“教化或调节”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世界社会是国际社会的逻辑延伸和可选择的一种路径。布尔认为,世界社会“所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而是由个人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或共同价值,即世界共同善的观念”[4](P66—67)。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重大区别是,前者建立在国家间相互认同的基础上,而后者则建立在超越国界的个人之间共同规范、规则和认同基础上,“它的范围较之国际社会更大,它的规则可扩展到全球所有个人和集体的机构”[5](P144)。世界社会对应革命主义视角,强调个人层次上的共享规则和价值的理论中心地位,普遍人权和人类共同体观念是“激励或刺激”因素[6],具有比较强烈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和使命色彩。
综合3R传统并建立中间道路(via media)是英国学派的主要理论框架。3R传统在思想上是独特的,但是在实践上并不相互排斥。除了某些典型或理想模式,它们的界限决非泾渭分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应该是三R传统之间的对话,正如怀特指出,对国际关系的真理性认识不能依靠仅仅寻求这些理论传统中的任何一个得到理解,而只有通过寻求这些思想传统之间的争论才能理解[7]。
同英国学派相比,卡尔的主要理论标志是其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但是,他并不以构建现实主义理论为目标。卡尔认为,国际研究的两种趋势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而健康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糅合在一起,因为“理想和现实是政治学的两个方面。成熟的政治思想和良好的政治生活只能存在与理想和现实融合的环境之中。”[8](P10)通过对幼稚的理想主义和对极端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组成了卡尔现实主义的现代视角。对于卡尔来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必要阶段的理论武器。理想主义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指明了目标和研究意义;现实主义则为学科指明了研究对象和研究的途径。但是两者都存在重要缺陷。理想主义过于强调意愿对国际问题的塑造,忽视了现实条件的限制作用;纯粹的现实主义则过分强调决定论和过分排斥目的,缺乏感召力和行动的依据,最终丧失生命力。并且,政治现实主义一旦成为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可能演变成一种代表特权集团利益的价值观从而丧失现实性,这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一样。因此,现实主义仅仅是卡尔批判乌托邦的“工具”,在摧毁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基础后,卡尔并没有成为更加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相反,他开始试图把理想主义的目的性和现实主义的观察与分析融合在一起来分析未来世界的政治秩序。正如批评者认为,卡尔在《20年危机》之后的著作中逐渐偏向了他所批判过的“乌托邦”,虽然有可能因为卡尔的“权力”、“道德”等概念的模糊导致前后不一致,但也是他融合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思维的努力。
英国学派试图综合三R传统,而卡尔试图建立一种包含了乌托邦与现实、道德与权力这样两种互不相容成分的国际关系思想框架,两者都拒绝承认思想传统具有独一性和绝对的不可通约,这种“综合”可能是当前两者国际关系思想重新被“发现”的原因之一。当然,英国学派更加青睐格老秀斯的理性主义,而卡尔则是以“无所不在的权力”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更多体现现实主义特征,卡尔也被称为国际关系“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9](P46—47)。
二、一致的传统研究方法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涌现了一批被称为“行为主义”的研究模式,对传统研究方法提出强烈质疑。“行为主义”学派试图建立一种实证的、符合“科学”要求的、具有“硬”理论内核和研究方法的体系。而英国学派认为这种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看做具有同样的客观性、经验可验证性等特征的“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这门社会学科,国际关系是人类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规范领域,其中许多核心问题的伦理性质决定了纯粹实证研究的困难。
在方法论的层面,英国学派主要采用人文主义而非行为主义的方法论,认为国际社会不能只用利益、权力这些术语来理解,必须考察外在于国家的国际社会因素即共同规范、制度和文化价值观在维系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及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依托历史、哲学、法律等传统学科,依靠研究者的判断而非严格的验证程序,广泛采用描述、比较、归纳等传统研究手段。“传统的现实主义,以及特别是英国学派,将历史学看做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学科”[10](P115)。正如布尔等认为:“国际社会只有放在历史的视角之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如果人们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国际社会产生的历史,那么目前的世界性国际社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11](P9)当然,英国学派绝对不是反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是反对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全盘倒向。怀特曾经指出,国际政治是一个事情不断出现和重复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治行为大多具有规律的必然性,但是,“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数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12]。因为国际关系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领域,人类的思想能够创造思想以及根据环境变化改变思想,只能采取诠释的方法才能理解人类独具的直觉、情感和判断,从而理解他们的活动。因此,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是英国学派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行为主义盛行时期的特征。
同英国学派一样,卡尔更加强调历史、文化、哲学的方法。卡尔早已认识到实证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研究方法。这同他关于历史学研究中主体与客体并非二元对立的论断一脉相承[13]。卡尔指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解决人们的问题为目的,但是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不像自然科学中的事实那样是纯粹客观的,目的本身与探索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就是事实的一部分。因此,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分”并不适合用于国际政治科学研究。在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卡尔的非实证主义倾向则通过他所采用的卡尔·曼海姆所发展的知识社会学表现出来[14]。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卡尔也充分显示出他对历史经验分析的重视,其历史主义倾向得到了学者们的共识。罗伯特·考克斯指出,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如摩根索、沃尔兹等人,将现实主义改造成了某种形式的问题解决理论。虽然他们本人饱读史书,但是却倾向于运用表现问题解决理论特征的行动框架,采取静止的、非历史的观点。而卡尔与他们不一样。卡尔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力量、国家本质的变化以及全球关系的连贯性;他还将历史的思考方式融入其写作中,认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杰出的个人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了时代的发展进程[15](P189—194)。
根据历史来解释和关注人类社会是英国学派与卡尔的主要视角和途径。这种对历史的强烈关注,有可能与英国的学术传统、外交政策历史上的曾经辉煌以及当前的相对凋敝有关[16](P59)。英国的大国经历以及20世纪初期大师辈出的史学传统,吸引了他们对史学方法的关注。当然,两者的历史观并不完全一致,例如马丁·怀特认为国际关系历史不是进步的,而是基本事实不断重复的历史;而卡尔则坚持历史在曲折、间断中仍然保持进步的趋势[17]。
三、对西方价值的不同态度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在布尔看来,现代国际社会是“欧洲古典文明的放大与延伸”,因为“欧洲是现代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的体制和习惯代表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创造的最优秀的文明成果”。这就决定了英国学派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强调用西方价值尤其是欧洲大陆的价值来判断、研究国际社会的问题。
英国学派认为,国际社会的建立基于一定的共享文化历史或者对共同利益的信赖之上,这些条件只有在欧洲大陆才能得以满足,因为近代以来的欧洲是以一个整体而非纯粹国家集合体存在的。国际社会理论正是以欧洲为中心,构建一个以西方价值规范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哈里丁认为:“欧洲各国组成的‘社会’,是一种(西方的)基督教君主制成员的俱乐部,它最早出现的形态是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的’土耳其的。”[1](P378)因此,英国学派是通过界定他者为“从属”或“异端”来构建自身价值规范的中心地位,其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及其扩展意义。虽然布尔等人对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及结果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但是他们完全以欧洲意义上的主权、人权、民族自决观点来研究第三世界的正义要求,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而在看待西方文明方面,卡尔似乎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卡尔对西方的信念发生动摇,认为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基础上的西方价值观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要求而逐渐破灭。而通过研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著作,卡尔对新崛起的苏维埃联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认为,苏联的集体主义社会民主形式有可能代表了未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组织的形式。作为西方学者,卡尔对苏俄的赞赏是较罕见的。他认为,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军事、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苏联的政治和社会文明可能更加适合未来世界。这也使得卡尔被指责为“亲苏”分子。
另一方面,卡尔对西方的批判不是表示对西方文明的抛弃,而是关注如何使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保存。他的政策意图在于维持英国战后三大势力之一的地位,使英苏美一起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力量。这就需要英国适当采纳“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式,并与苏联暂时妥协。卡尔指出:“西方世界应该通过研究新的社会和经济行为方式来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这种新的行为方式中,民主传统和个人主义中正确的信条应该且能够被运用于解决大众文明中的问题。”[18](P243)因此,西方要摒弃那些过时的价值观和哲学基础,从其他文明主要是俄国文明中学习和借鉴。总的说来,卡尔是拒绝西方中心主义的。怀特曾经抱怨,认为卡尔对于不能降低其自己文明价值或者某种程度上割裂传统没有发表任何观点是不能容忍的[10](P84)。
四、对理性主义的不同态度
英国学派的基本共性之一是理性主义倾向。在3R传统中,英国学派更加重视格老秀斯主义。他们认为,形成国际体系的现实主义因素和构成国际社会的理性主义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理性主义的因素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常常比现实主义因素要强大,因为国际社会的核心是规则、制度和价值,国际秩序不只涉及物质力量,更主要是一个由共有规范和制度管理的社会。英国学派从人类理性、自然法观念出发,将当前国际体系看做无政府但有秩序的国际社会状态,并强调理性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和演绎推理的重要性。因此,英国学派堪称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一贯实践者和当代典型[6]。
而在卡尔看来,对理性的绝对信奉代表了乌托邦的视角,是国际联盟等失败的国际组织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根源,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武器,国际关系的改善依赖于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而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出发,卡尔对人类能够依靠理性走向完善的论断持怀疑态度。在曼海姆看来,信息只有通过主体的认识与整理,才有可能组织成有意义的知识。而在观察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主体不可能同客体完全分离,因此知识的形成不可能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任何观察都带有角度和偏见,这种角度和偏见是由观察者的位置所决定的。人不可避免地处在某种社会位置上,因此人们思想的形成不可能全部是理性的结果,非理性因素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学的指导下,卡尔摧毁了利益自动和谐及舆论一贯正确的理性主义内涵。他认为,国联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把民主和理性主义从国内领域移植到国际领域,这同利益和谐论具有同样的错误。因为理性主义者总是使用抽象的一般性原则来对待具体问题,而不是按照具体问题的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理性主义绝对和先验的普遍性原则实际是由历史所创造的,是环境和利益的产物,也总是为促进利益而服务的工具。因此,乌托邦对理性的信奉反映的是既得利益的需要,不能作为研究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
卡尔对理性主义的态度是现实的:一方面,理性主义在人文主义浪潮中作为思想武器确实起到了反抗神权的作用,卡尔也承认人的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卡尔所反对的是理想主义者忽略权力的现实存在,认为仅仅依靠理性就能够解决人类冲突的观念。因此,卡尔并不是反对理性主义,而是反对关于世界真理性和客观性认识过程中“理性至上”的观念。
五、小结
卡尔与英国学派的共性在于,两者都拒绝单一的理论分析路径,都坚持用综合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研究,都强调社会、历史、人文的研究方法。但其差异也是显著的。
英国学派衍生于二战之后,其创立者巴特菲尔德曾指出,(英国学派)“不研究通常意义上的外交史和当前的问题,而是确立外交活动背后的基本命题、国家推行某种外交政策的原因、国际冲突的伦理假设,以及国际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7]。而卡尔指出,国际关系学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战争爆发。当时,欧洲局势正在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避免战争成为卡尔一切研究的首要考虑。加上多年外交官经历的影响,卡尔把主要研究重心放在具体问题,在他看来,“时势”远比程式化的“原则”更重要,“读者可以批评我这本著作,不是质疑著作的真实性,而是质疑它的观点是否合乎时宜”[8](P6)。这种对“时势”的强调既符合国际局势的要求,也符合他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思维特性。
因此,在较为抽象的层面,比如对于英国学派的主要关注点:国际社会如何界定、如何发展以及发展条件等问题,卡尔没有过多涉及。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看做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和着眼点,而卡尔把国际社会作为现存之物而不是需要研究的核心概念,也并不重视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与3R传统之间的联系。能够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实实在在的作用,是卡尔国际关系研究的目标所在。因此,虽然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有共性,但在理论的标志特征和研究目标方面,卡尔与英国学派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卡尔不能被归为英国学派的重要原因。
标签:国际关系论文; 理性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