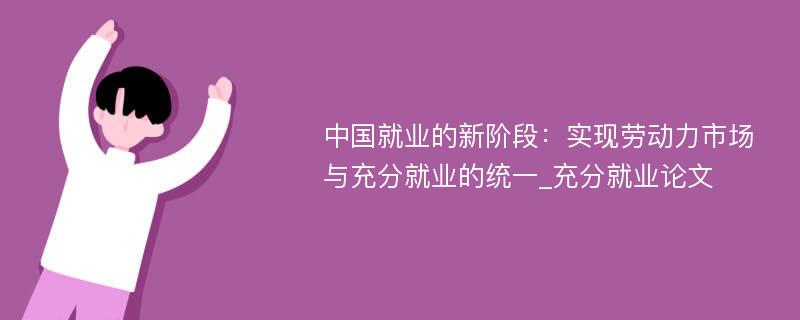
中国就业新阶段:实现统一劳动力市场与充分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阶段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的就业已经走出二元结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进入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就业与周期性失业的统一劳动力市场阶段。“十二五”时期,正是中国就业发展到统一劳动力市场阶段和周期性失业阶段的新时期,就业问题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以及政府调控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在2001-2008年的这一轮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实现了三个转变:1.从二元型劳动转移到一元型充分就业;2.从外延式总量增长到内涵式结构调整;3.从市场配置型就业到政府保障型就业。与之相对应,政府的就业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三方面:1.政府的职能从城市就业保障到城乡统一的就业保障;2.就业的重心从重视增长的就业转移到结构调整的就业促进;3.宏观经济目标从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导向转移到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的导向。
“十二五”时期,政府要完成统一劳动力市场就业保障、就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本合理配置、减少隐形失业三大任务,实现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体制与均等公共服务保障的充分就业服务体系两个目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全社会非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是40%,其中14岁以下和60岁以上统计意义上的非劳动人口为35%,残疾人非劳动人口约为5%。我们根据城镇人口和就业人口,乡村人口和就业人口,计算出了城镇和乡村非劳动人口及其占各自人口的比率,其中,城镇非劳动人口比率约为48%,乡村非劳动人口比率约为35%。通过将这两个数字和全社会非劳动人口比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乡村存在过度就业现象,过度就业率约为5%。乡村向城市转移出去约5%的非劳动人口。其中,一部分非劳动人口就是农民工子女,还有极少一部分跟随儿女进城的老人。而城镇非劳动人口比率约为48%,减去乡村转移进城的5%,比全社会非劳动人口比率仍然高约3%-4%,约为900万-1000万人。这一部分恰恰反映了城镇中的制度性隐形失业。
我们根据全社会经济人口和城镇与乡村劳动人口的统计数据,计算出调查的全社会失业率约为2%。我们假定乡村劳动人口等于乡村就业人口,也就是说假定乡村人口实现了充分就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失业只是一个城镇的经济现象,失业率也就是城镇失业率。由此,我们通过用非就业人口除以城镇就业人口加非就业人口,大约为6%,再加上城镇的制度性隐形失业率,就可以计算出全社会的失业率,或者说城镇失业率,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和比率,即9%-10%。又由于此轮经济增长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且在2007年超过潜在增长率,达到13%。根据这轮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以及就业水平的分析和比较,可知2006年经济增长率为11.6%,通货膨胀率为1.5%。2003年持续的民工荒和2006年乡村劳动工资大幅度提高,农村实际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劳动工资,由此,我们认为2006年达到了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11%可以确定为潜在增长率。与此相对应,当年的失业率为6%,就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自然失业率。而这一时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中间相差约1.9%。1.9%恰恰反映了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与财政体制的城乡分离,导致了城镇结构性和自愿性失业。
此轮经济增长,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关于二元经济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弹性为无穷大的理论和现实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形成了有弹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均衡状态。
由于这轮长达七八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民工的就业已经固定化、城镇化,进而促使家庭的城镇化。稳定的增长本身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保障,而这种就业保障也为他们提供了收入、医疗、子女教育等经济保障,他们已经与土地和乡村形成了相当固化的隔离。失业,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失去就业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失去收入、医疗,尤其是子女教育等的经济保障。因此,当下及以后的失业农民工劳动力不同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农业兼业就业的流动性劳动力,农民工已经是完全脱离了农业,形成了专业的、固化的劳动力市场要素资源,其家庭也成为城镇家庭的重要组织部分。因此,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及以后的经济波动带来的失业就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冲击,因而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冲击。正确认识中国劳动力具有的这一新特征,正确认识当前就业与社会稳定的密切关系,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真正把就业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是十二五时期以及后二元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与重要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