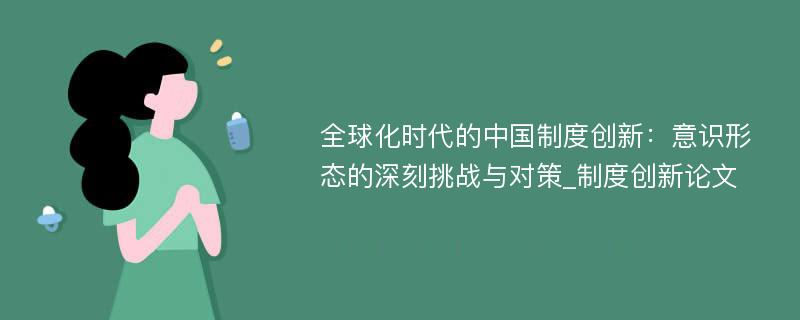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来自意识形态的深刻挑战及应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中国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深刻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6)03-0009-03
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保持着生机活力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和支撑制度创新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面对全球化挑战和已经接受全球化挑战20多年的当代中国,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在支撑体制和制度创新方面存在着复杂的两重性:第一方面是面对全球化进程冲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而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建设中,从极“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破除僵化的体制和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成功地支撑着20多年新型制度和体制创新,成为指导当今中国变革的强大精神力量;第二方面是面对全球化进程冲击的当代中国,伴随着原有极“左”理论思潮和僵化体制的解体,开放的环境和改革中各种机制和体制的借鉴或移植,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社会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各种意识形态也在不断浮现:有的是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不矛盾,并可以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借鉴的意识形态;有的是伴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产生的一些新理论和新思想,但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加以分析和批判的意识形态;有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形成直接挑战的、并构成当今中国制度和体制创新走向相反方向的异质意识形态。上述两个方面,对于关注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挑战的人们来说,不仅要求其看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对中国改革开放制度和体制创新的支撑和指导的主导性。还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面对来自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要求进而继续的制度创新,其自身怎样不断地与时俱进仍然是一场深刻的挑战。另外还要现实地看到,全球化冲击所形成的当代中国复杂的意识形态局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深刻挑战形成的对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创新的解构作用。
因此,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状况以及从世界全球化进程和各种思想意识形态深刻交锋的现状,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创新面临着意识形态越来越深刻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层面:
第一,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的深刻巨变,使得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对中国制度创新的支撑动力构成一种摧毁性作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格局的深刻巨变,就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实践虽然取得过辉煌成就,然而它却在继续证明社会主义自身的价值性实践上遭遇重大挫折,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加速进程的世界巨变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滑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这一轮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极其张扬地将其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展现在世界面前。这种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推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称霸全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20世纪所有社会制度较量的结局,概括为是掩藏在制度背后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并终结其他意识形态的历史。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依靠一定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力量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了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而今天全球性大变革再次证明了它永恒的力量,不过这一次它战胜的是社会主义。所以,他说“人类越接近千禧年的终点,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式中央经济计划越面临相似的危机,以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站在战斗圈内的竞争者也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1] (P59)为了进一步强调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跨越社会制度和民族界线的决定性力量,他还指出:“以胜利者状态出现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际,不如说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总之,世界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没有一种伪装普遍的意识形态足以跟自由民主竞逐,也没有一种普遍原理比人民主权更具正统性。”[1] (P62)这种极其自负的和张扬的政治意识的霸权心态,驱使着“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纳入他们的体制”[2]。所以,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上,当代资本主义将其视为对一切社会制度都具有解构作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伴随着全球化的大潮到处播撒,中国当然不在例外。
第二,在全球化加速进程中,世界各种非传统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思潮、新认同范式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使得支撑中国制度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当代世界全球化进程最为迅速,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冲击当代中国最为猛烈的时期,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化在当今世界上所导致的极为深刻的变化,就是根本改变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范式。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时空巨变和社会组织巨变,作为时空巨变的全球化,即“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无论其是否是经济方面的,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更为迅速地对我们产生影响”。作为社会组织的巨变,“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3] (P33,P36)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巨变中,当代世界许多与过去意识形态范式大不相同的非传统意识形态运动此起彼伏。例如,民族主义的崛起振荡整个世界,甚至在苏联和东欧成为颠覆社会主义力量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说:“俄罗斯及其他联邦共和国中的政治精英是拿民族主义作为反对失势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武器,以此来打击苏联政府,以便在各共和国内的机构进行夺权。”[4] (P45)例如,伴随着全球化加速进程而出现的以反抗全球化为特征的环境运动、反对社会排挤运动、极端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等,它们很难用“好”还是“坏”等传统意识形态的范式来判断,但是对至今为止人类思想的方式和认知方式提出了挑战。因此,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无论是其制度创新的层面还是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层面,都不能免于受到这些社会思潮和运动的挑战。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能够有力地回应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复杂局面,并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提供理论的指南、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持,其自身的建设是非常艰巨的。
第三,我们应该在承认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和发展的前提下,还要客观地看到在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面前,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任务是紧迫和繁重的。过去的20多年,由于在全球化条件下,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制度的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解体,对外来与传统社会主义具有异质性的体制和制度的移植——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企业、资本、分配等制度的引进,对一些长期以来作为是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非公有制经济制度、非按劳分配制度被确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等等,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面对着来自指导自身体制和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伴随着外来体制引进的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这些挑战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直接地相对抗,有的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现成原理或在知识框架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有的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进行的崭新探索和实践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总结和提升。
总之,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制度创新面临来自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挑战呈现出一组复杂局面,有来自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有来自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给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的机遇,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因此,在当代中国以及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处于世界全球化格局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处于深刻的世界历史变革的时期。制度和体制在全球化的世界面前处于一系列创新连续性进程之中,这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连续性创新要求也十分迫切,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变动世界的创新进程之中,才能推进适应这一世界的国度进行制度和体制创新。在未来全球化世界挑战面前,我们如何应战来自强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如何应对出现的各种非传统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思潮、新认同范式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如何适应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不断创新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要求,特别是如何保持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进程而不逆转,都关系着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笔者认为,针对当前世界全球化进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现状,可从建构新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四维”结构,来推进新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
第一,指导制度和体制创新的现实起点——从全球化的世界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性”。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使得整个社会系统的文化—制度特质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改变人们各种社会交流的本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具体性基础,其实质仍然与当年立足于工业革命一系列经济技术革命范式基础之上一样,必须深刻研究全球化世界变革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形式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研究当代世界包括中国越来越复杂的阶级和阶层结构变动,研究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全球性物质条件的变化与整个社会结构带来的变革,研究借助于全球化和广大人民在电子化媒体面前的意识形态分析能力大大提高的现实。只有严肃地面对今天的现实和变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同样具有当年的客观性、真理性和具体性,为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创新提供现实的起点;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无论怎样强调保留当年的纯洁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能是刻舟求剑式存在,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毫无帮助。
第二,汲取制度和体制创新的丰富理性营养——从当代世界各种思潮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包容性、彻底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鲜明地体现在它所针对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战斗性,体现在它对各种思潮和学说真理方面的包容性,体现在它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又过了150多年,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的并行轨道上: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有了重大发展,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头号挑战者;从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分化出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化,至今也已经成为西方最大的左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自身在西方也由于150多年的发展而分化成为多流派的思潮,其理论和学派的复杂程度令人眩目;另外,伴随着新科技革命、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出现的许多新的社会运动和各种形形色色思潮在当今世界也是层出不穷。事实上,在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环境中,一些思潮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头号敌人,一些思潮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可缺少的参照系,一些思潮仍然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而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并且是能够指导当今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与现代社会与时俱进的特质,具有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潮的能力,不断地进行从创立初期其意识形态交流环境走向当代意识形态交流环境的现代转型,创新其意识形态的战斗性、包容性和彻底性。
第三,保持制度和体制创新的连续性和创造性相统一——从世界历史深刻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变革性、现代性”。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在意识形态上创新的连续性、变革性、现代性的要求,只有保持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的连续性与创造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才是无穷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始作俑者吉登斯在提出社会主义衰落的论点时这样说:“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严密、精确的经济理论。他还把社会主义放到一种对历史加以全面审视的背景中去……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衰取决于它能否创造出一个社会的能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这个社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且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分配这些财富。如果说社会主义现在衰落了,则正是这些主张落空了。”[3] (P3-4)我们说,吉登斯这里批评的社会主义,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他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种失误归结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是不对的。但是,他的批评也让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始终具有对今天的指导性,其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保持从其创立时所具有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保持其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深刻变革进程中的解释力和作为一种严密、精确理论在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当代马克思主义。毕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在以英国为核心的积累周期以及自由竞争时期中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育程度、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方面,与以美国为核心的积累周期以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大不一样的。只有深刻地观察着这一过程,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适应着当代世界各种新的变化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我们提供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内在的连续性和创造性。
第四,为制度和体制创新提供真实的对象——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变革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科学性”。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遭受过严重的挫折,而作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与这种挫折有着深刻的联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曾经因为被“左”的思潮所影响,长期被蒙上了一层虚假的外罩。例如,阶级斗争越激烈越社会主义,公有制越纯洁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越彻底越社会主义等等,甚至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家长制和终身制、种种特权现象,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残余都被当做社会主义来大加提倡,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和科学性受到严重损害,而我们又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这样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与真正的现实隔离开来,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其制度和体制的创新也失去了其意识形态指导的真实性。只有在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后的反省,经历了中国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后,才越来越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和科学性还原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才真实地看到我们进行制度和体制创新所面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环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建构选择等等。21世纪,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面对的矛盾将更加尖锐,环境将更加复杂,实践历程将更加艰巨,事业将更加伟大。我们在这样的进程中,只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开放性、科学性,才能使我们在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以直面现实的严谨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断地将新型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创新推向新的高度。
标签:制度创新论文; 全球化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