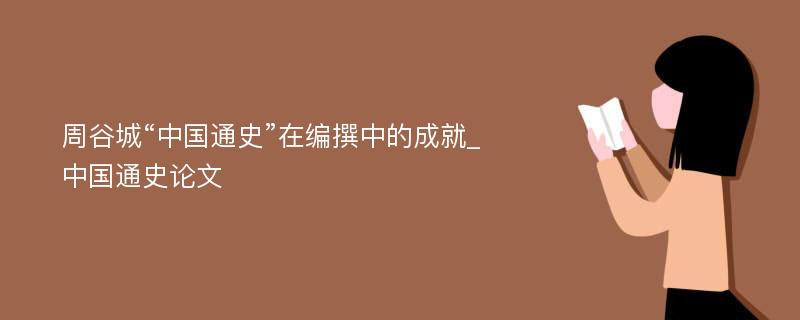
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城论文,成就论文,中国通史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积极倡导以进化史观为指导重新撰写中国历史,并提出了新型中国通史的写作框架。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中国通史编纂高潮,出版了不少的中国通史著作。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注:1939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至1957年再版了13次,1957年修订后,又多次重印。) 以其独创的通史编纂理论和严密的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通史代表作之一。当年开明书店重版《中国通史》的广告(见1948年出版的《中国通史》下册)曾自豪地宣称:“书中有任何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所未曾运用过的史学理论,未曾采录过的新鲜材料,未曾使用过的编制方法。”周谷城的通史编纂理论及其方法,是20世纪中国通史研究和编纂的珍贵史学遗产,对当代中国通史的编纂仍有参考价值(注:张志哲《〈中国通史〉与周谷城教授》(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杨志刚《略论周谷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与成就》(《社会科学》,1998年第11期)、孔繁敏《纵论古今,横说中外——周谷城史学成就述略》(《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2期)等文章对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及《中国通史》的成就,有一定的研究。)。
一、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编纂旨趣
新型中国通史的编纂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初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不少中国通史编纂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通史编纂理论。钱穆研究历史着眼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认为中国通史著作,一方面要写出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找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源泉,民族之精神;另一方面要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征侯,为有志于改革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1](引论)。张荫麟关注于通史著作的可读性,重视选择史实的标准、统贯史实的范畴、文字表达方式,要将所纂之《中国史纲》写成一部人人喜欢阅读的史书[2](自序)。吕思勉以为人类的一切现象无不与文化有关,其《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篇,上篇中国文化史,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下篇中国政治史,叙历代之治乱兴衰[3](自叙)。周谷城《中国通史》则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显示出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他曾说:“我著《中国通史》时曾力求得到通史的统一整体,其初版导言曰《历史完形论》,意在指出历史事情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 这里的“历史完形论”就是所谓《中国通史》所运用的其他中国通史著作中未曾有的史学理论,其核心是如何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后来周谷城又将历史完形论贯穿于其《世界通史》之中,编著《世界通史》时,他首先考虑的也是“统一整体问题”。若干年后,他依然强调:“今后编纂世界通史在认真审核史料的同时,务必力求有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以便得出历史的规律性。”[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 这表明,写出统一整体的历史是周谷城通史撰述的追求和目标。
周谷城认为,史料只是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留下的痕迹,史观则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二者都不是历史自身,历史自身是客观独立存在的人类过去的活动。“史料史观都非历史,然则独立存在,不因吾人之知识而始存在之客观的历史,究竟是什么呢?这很易回答,即人类过去之活动是也。”[5](p.4) 所以,历史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史料,也不是史观,而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人类过去的活动是完整统一的,其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也像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部分之所以为部分,只因其构成全体;全体之所以为全体,只因其成于部分。“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既不是空洞的‘一’,也不是散漫的‘多’。”[4](史学上的全局观念) 因此,历史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以获得对历史自身的认识。“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研究人类过去之活动,分解此活动之诸种因素,寻出诸种因素间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明白此活动之自身而已。”[5](p.7) 这里所说的不可移易的关系,就是历史的有机组织和发展规律,通过分析人类过去之活动找到其发展规律,自然就认识了历史本身。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没有什么区别。“自然科学固然要寻出事物之诸现象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该事物;历史科学亦必须分析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的诸因素,寻出诸因素间不可移易的关系,始得谓之认识了历史。”[5](p.12) 周谷城认为,通过对客观历史自身诸因素分析,寻找出了其不可移易的关系,那么编纂通史时就应该将这种关系表述出来,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历史自身既为‘整个的’,则处置历史自身的史学著作,便不能将此整个的自身,寸寸断之,使各个成体,如是则有机组织尚焉。”[4](中国史学史提纲) 所以,无论是撰写《中国通史》还是《世界通史》,他始终将写出统一整体历史的史学观念贯穿其中。
从维护历史自身的完整出发,周谷城既要求研究历史时“便始终应当追随着维护着它那客观的独立存在,不应将客观独立存在化为主观的。”[5](p.7) 也主张在中国通史编纂中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历史自身完整的作法。他指出,历史编纂中的分类和分朝两种述史方法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应予以根除。使用分类叙述方法的史家,只注意到了文字的记录、个别的史料及典章制度等,并将这些分成世系、疆域、内政、外交、文治、实业、民生、学术、思想等子目,然后将资料编入其中,没有认识到其中还有历史之自身存在。其书编得愈有条理,而历史自身或活动自身之完整愈被支离,历史书变成了资料书或历史辞典。每一个子目均有独立的意义,而从诸子目的联缀上,始终看不出历史之自身或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分朝叙述的方法,以朝代为叙述对象,一则按子目将一朝大事编排起来,一则将朝与朝之间的历史一分为二:一半划入前朝之末,作为其灭亡的原因,一半划入后朝之端,作为其开创的工作,割裂了朝与朝之间完整的活动。所以,这两种写史的方法,都应该予以摒弃。我国史学上源远流长的以史为鉴的资鉴说,尤其为周谷城所反对。他指出,“资鉴的观念不打消,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终维持不住。”[5](p.9) 这并不是因为资鉴说强调治史的目的, 而是资鉴说者将客观历史当作一种可资借鉴的宝库,任取所需要的部分,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必然联系,从而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资鉴说与完形论的根本区别在于:“资鉴说不惜破坏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摘取个别的先例,以作今人的训条;完形论则务须维护历史之客观的独立存在,以明了历史之自身,以增进今人的知识。一则以治史以受训,一则以治史以求真;一则把历史当作一种可供我们摘取先例的宝库,一则把历史当作客观的独立存在,应当从正面研究的东西。”[5](p.9) 因此,以史为鉴的资鉴说不予以根除,历史自身的完整性难以维护。
为了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周谷城编撰《中国通史》时,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史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达、篇章节之标目,都是以维护中国历史的完整为目标。
二、“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
编纂史书对体裁的选择和要求,往往反映了编纂者对历史的理解和撰述目的。周谷城旨在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中国通史》必然要采用能体现出历史自身之完整的体裁。周谷城认为传统史体纪传体、编年体不适宜于撰写中国通史。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常将一完整之事情分述于纪、传之中,又常将同一时期同作一事之人分开叙述。这种分类以叙事的方法,必然将历史自身之完整加以破坏。“纪传体之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厥在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一点。通史所求者为历史自身之完整;纪传体则恰恰破坏之。”[5](p.19) 编年体按年月之先后排比事情,虽将同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合在一起叙述,但这同时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将其并列在一起,并没有反映出历史自身的完整。同时,编年体将一件完整的事零碎地分散于不同的年代之下,以致其完整性被破坏。所以编年体也不适宜于编纂通史。比较而言,周谷城认为,纪事本末体较为接近于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要求。一是其叙述对象比较接近于人类过去的活动。纪事本末体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以历史事情为叙述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二是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较少。其因事命篇,自为起迄,能体现所述之事之完整。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事情与事情之间或篇与篇之间缺乏联系,每篇所述之事,与前后各篇所述诸事的必然关系没能显示出来,彼此都是孤立的。同时,对所叙述的事情缺少分析,反映不了其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所成之篇,就不是辩证的完整,而是笼统的含糊。由于这两大缺点的存在,纪事本末体也未能充分表现出人类过去的活动[5](pp.22—23)。
20世纪史学著作,大多用章节体写作。这种新史体更为周谷城所反对。他认为章节体史书,事情纵剖,依门类而分,时间横断,依朝代而分,纵横交错,可称之为新体或坐标体。倘若以这种史体编纂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将被破坏无遗。章节体中国通史每叙述一朝代创业的种种情形之后,不接着叙述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发展变化,而是立刻将典章制度插入,叙述了典章制度之后,又不接着叙述其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演变的趋势,而立即将经济民生等插入。这样纵剖出来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固不明白,而各部门前后的发展演变,亦令人茫然无知。“所有史料之排比,乃至典章制度之说明,虽井井有条,然都离开了完整的历史,或离开了完整的人类活动,成了无联系的零碎东西。”[5](p.26) 所以章节体对历史完整性的破坏更甚于纪传体。周谷城对各种史体的批评,重在能否体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当然,仅从一个角度评价史体,难免失之偏颇。
通过对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史体的分析,周谷城选择了破坏历史的完整性较少的纪事本末体来编纂《中国通史》,同时,尽量克服以往的纪事本末体自身之缺点,以便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章学诚曾赞扬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周谷城指出,“应改为‘因事命篇一依历史事情发展之次序为常格’”。“历史学之对象或人类过去活动有其发展之次序,历史学即用之以为常格。袁枢之因事命篇,是有常格的,不过他尚未能完全依循常格耳。”[5](p.22) 这是说,依中国历史事情的发展次序因事命篇,即是编纂中国通史的体裁。《中国通史》将从北京猿人到1927年北伐战争之间的中国史,分成游徙部落定居时代(周平王迁洛邑以前即公元前770以前)、私有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即公元前770年至公元9年)、封建势力结晶时代(自新莽元年至北宋元年即公元9年至960年)、封建势力持续时代(自北宋初至鸦片战争即公元960年至1840年)、资本主义萌芽时代(鸦片战争以后即公元1840年以后)等5编,即是依据中国历史之发展阶段,即中国历史自身发展之次序来叙述其过程。如将周平王东迁以前作为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因为这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段落,中国部落从游徙到定居,中国民族的初步形成,皆完成于这一时期。“自人类与天然战争,及人类彼此相互战争开始,到次序之建立及生产之发达告终,恰好成一单元;中国民族生活之初步形成,恰在这一单元之内。”[5](p.133) 周谷城认为史家通常以秦始皇统一以前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只考虑到政治的发展,没有考虑到经济的发展,是以政治史代替中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往往被史家分裂为二,一部分作为前朝灭亡的原因,一部分作为后朝所开创的事业。《中国通史》对改朝换代之际历史的叙述,则十分注意其完整性。如第三编第一章社会的剧烈冲突,将西汉的社会矛盾、东汉的建立合在一起叙述,突出了两汉之际的社会变动;第四编第一章宋帝国的建立,将唐中叶以来的社会变乱与北宋的建立综合在一起叙述,鲜明地反映出唐宋之际历史的变化;第七章由蒙古统治之瓦解到大明帝国之树立,叙述了元明之际的历史变化。这样,朝与朝之间历史的变化就完整地显示出来。
孤立叙事是以往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严重缺陷之一,因而未能表现出所叙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自然难以充分显示历史自身的完整。《中国通史》注意编、章、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注意分析所叙之事自身之因果关系,尽量克服这一弊端。如第一编第五章宗教在上述诸问题中之地位,与第二章先民怎样对付自然、第三章诸种部族怎样相处、第四章社会次序怎样树立,密切关联,反映出宗教帮助先民征服自然、解决部族间的战争问题、进而稳定社会次序。第六章新次序下的经济盛况,与前面四章亦有联系,显示出部族间的战争源于生存竞争,战争中酝酿出等级的次序,而社会次序的确定,促进了西周社会经济的繁荣。在这里,不仅显示了各章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社会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进步,酝酿着新的历史变化。“西周经济的发达,恰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之变动的原因。”[5](p.143)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共主地位的丧失、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地主的出现、商人地位的提高,皆直接或间接由西周经济的新发展所引起。这样,第一编游徙部族定居时代(周平王迁洛邑以前)与第二编私有田制生成时代(自周平王元年至新莽元年)的关联,就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同时,也反映出了从远古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中国通史》采用的依中国历史事情之发展次序因事命篇的表现形式,吸收了传统纪事本末体的优点,便于从整体上显示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而叙事时注意编、章、节之间的关联,则克服了传统纪事本末的缺点,便于体现历史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是从史书体裁出发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
三、关于选材、文字表述和标目
着眼于整体统一来撰写中国历史,周谷城指出选材应以历史自身为标准,行文应说明史事间之必然联系,标目应表明所述之内容。
史家编纂史书,对材料的选择也与撰述目标密切相关。周谷城认为要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编著通史之时,始终应以历史自身为选材的标准,或以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选材之标准。”[5](p.30) 章学诚曾指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在史实选择上,“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周谷城认为应改为“决断去取,一依历史事情自身之完整为标准”。“历史学者之取材,如欲‘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则历史自身之完整,或人类过去活动自身之完整,即是一绝好的标准。”[5](p.22) 这说明编纂中国通史所选择之史实必须是构成历史自身必要的环节。这就要求对人类的活动之自身与活动成果应加以区别,不能将活动之成果视为活动自身。周谷城指出,马端临曾将历史分为不相因的治乱兴衰、与相因的典章制度,所谓不相因的治乱兴衰似近于活动自身,相因的典章制度似近于为活动之成果。郑樵曾立志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而极古今之变。所谓极古今之变,近似于活动之自身,天下之文近似于活动之成果。活动之自身是通史的对象,活动之成果是专史的对象。专史之和亦非通史,只有以人类活动自身为对象的才是通史。当然,活动的成果也可以用以说明活动自身。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通史》重在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突出了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斗争、阶级斗争,而略于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如第一编游徙部族定居时代(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前),着重阐述了中国先民如何对付自然、诸种族间怎样相处、社会秩序怎样树立,以及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周谷城认为,先民为解决这三大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种种作为,实足以代表当时整个社会活动的全部,宗教也是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三大问题的逐步解决,生活才逐渐安定,生产才逐渐发展。《中国通史》中也有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等内容,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阐明典章制度或学术文化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历史发展的有机组织和规律。“完形论虽坚持着人类过去活动之自身为通史之对象,却不是说专史所叙述之事情,完全不能入通史;反之通史之美备,也许完全要靠专史之精进。”[5](p.28) 也就是说,要说明人类过去的活动,可用活动之成果以为材料、手段。《中国通史》第三编第七章记述了唐代官制、刑制和兵制,其着眼点在说明社会活动。对此,周谷城特意加以说明:“我们于前此各篇各章,从未单独的叙述过官制。一则因通史的任务,应该置重整个社会的活动,不宜多涉静止的制度。二则因静止的制度如官制等,应由专门史(如法制史之类)去叙述,通史中大可不必多谈。但这里却又专述官制者,盖有两个理由。一、隋唐官制,含有外族所创的成分;述之,可以显示种族斗争对于文化的影响之伟大。著重之点,仍在整个社会的活动。这样的叙述,与第一篇里叙述怎样建立社会次序,第二篇里叙述集权帝国之诸制度,其用意正同,都是拿所述的制度以显示伟大的活动之影响。并不是为着静止的制度本身而叙述,乃是为着阐明整个的活动而叙述。二、隋唐官制,既是集汉民族与其他各民族之大成,且其体系又较完备,如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之分,几乎成为后世的典型;我们于此,顺便知道中国史上官制的大略,亦是一种收获。”[5](p.534) 《中国通史》有关学术文化的记载,如第二编第六章“随着社会而演变的学术思想”、第三编第五章“六朝时代江南的文化”、第十编第十章“巩固统治的理学”,都是通过学术来说明社会活动。“六朝时代江南的文化”,本应是文化史叙述的对象,在此却是通过对六朝文化的叙述,以说明北方侨民与南方土著之合作。“江南文化云云,正是中原南下的大家世族与江南本土的大家世族合伙造成的伟业。正是侨民与土著之和同的表现”。[5](pp.431—432) 对理学的叙述也是着眼于说明社会活动。“理学,活动之成果,若进一步曰:理学可以巩固统治,那便成了活动自身一种很好的说明。”[5](p.29)
编纂中国通史所选的材料,关键在能说明历史之自身,那么文字表述亦在表现出历史事情之间的必然关系。人们多认为历史教科书枯燥无味在于其缺乏生动优美的文字,周谷城则认为在于其没有显示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每一段、每一节、每一章都是孤立的,而与前后的章节全无联系,读起来如读历史辞典,不能获得有关历史自身的完整知识,当然不可能有深刻的印象了。一本史书,每一段事实,如果是读完了前一段之后不可不知的,则文字虽拙劣,读起来仍有先得我心之感,必有趣味。反之,文字虽美,仍将是干枯无味的。解决历史教科书缺乏可读性的最好办法是显示出所述事情之间的必然联系,体现出历史自身的完整性。大凡读过周谷城《中国通史》的人,多有这样的感觉:其文字并不优美,但前后连贯,脉络清晰,能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因其所叙之事相互关联,显示出了事情之间的必然联系。
周谷城认为,历史著作是反映客观历史的,其编、章、节表征着历史自身之各部分,因此,应以有意义之标题表示出所叙事情间的必然关系。“维护完形之通史,其文章之内容应与有意义之题目相符合;诸有意义之题目所代表的诸事情,应该彼此相关联。事情与事情之联系,反映为文章与文章之联系;文章与文章之联系,反映为题目与题目之联系。倘标题全无意义,那便不能表明文章内容之彼此相关,而显示着历史自身之完整性了。”[5](p.33) 《中国通史》的编、章、节标目逻辑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如第五编第一、二章之章、节的标题为:第一章列强对中国之压迫。1)由英国之对外发展到中英鸦片战争。2)各国继续以武力逼订不平等的条约。3)在不平等条约下之中国之殖民地化;第二章中国之图强御侮运动。1)经济方面的图强御侮。2)政治方面的图强御侮——戊戌维新。3)政治方面的图强御侮——辛亥革命。4)教育学术的图强御侮。这些标目,反映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图强御侮运动也不断深入。
周谷城曾这样评价自己的通史教学与撰述:“我教世界通史或写世界通史,首先考虑的是统一整体问题。”“我所著的世界通史,虽谈不上高瞻远瞩,得出了统一整体,但在寻找有机组织、希望得出统一整体方面,我是化了工夫的。”[4](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 这虽是就世界通史而言的,同样适合于对《中国通史》的评价。解放后,周谷城对《中国通史》作过修订,其中,某些观点也有了改变,但写出统一整体的中国历史的编纂旨趣始终未变。修订版《中国通史·导论》指出:历史学的对象“是斗争的过程,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是完整统一的。我们通过史料,能看得见,抓得住,重点突出,如实表达即可成史书。中国通史的编著,只能是这样。书要用主观的努力来写,但所写的却只是客观存在的、完整统一的斗争过程。”[6](p.15) 这里,周谷城仍然将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作为撰述目标。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批评20世纪前期的中国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并指出“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7](p.81) 周谷城所撰《中国通史》旨在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都贯穿着这一撰述宗旨,因而结构严谨,观点鲜明,克服了中国通史编纂中存在的条列史实的弊端,历史发展脉络清晰,自成一家之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通史”家风。当然,由于周谷城过分地关注通史著作表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对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史体一概否定,有失偏颇。应该说纪传体、编年体等与纪事本末体一样都适合于撰写中国通史,同时也都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一点章学诚就已经认识到了,所以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以本末之法”,作为史书体裁的发展方向[8](p.61)。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9](导论·题记) 为了实现这一撰述目标,在体裁方面,吸收我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优点,使之与章节体相配合,创立了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组成的新综合体,也说明了这一点。周谷城区分了史料、史观和客观历史的不同,将人类过去的活动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在史学认识上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他将人类的活动分为活动自身与活动之成果,认为只有活动自身才是通史叙述的对象,学术文化被视为人类活动产物而摒弃于通史之外,至多只是作为说明人类的活动自身的材料,所谓“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斗争。”[4](中国学史史提纲) 中国通史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变化方面,这样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个人的活动、学术文化等被忽略,难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
标签:中国通史论文; 周谷城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世界通史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学论文; 中世纪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