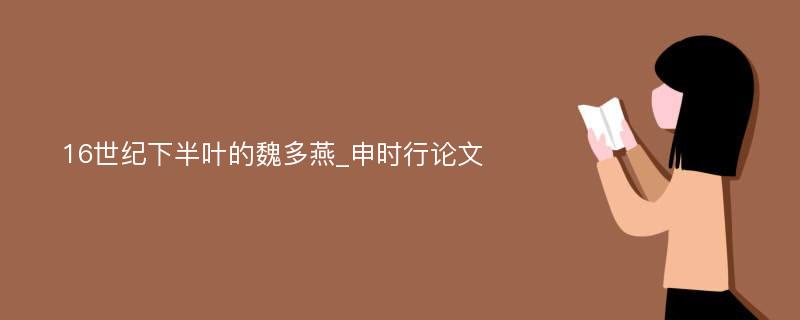
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朵颜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后半叶论文,颜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4)03-0049-07
朵颜卫是明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的羁縻卫——兀良哈三卫之一,其部众是兀良哈蒙古人。大约在明宣德、正统年间,三卫南迁,朵颜卫占据明朝蓟州镇边外的燕山山脉地区。到16世纪中期,朵颜卫归附右翼蒙古,其主体部众成为喀剌沁、土默特等右翼蒙古万户的属部。后金天聪年间,朵颜卫部落以领主的名义归附后金,构成清代喀喇沁三旗和土默特二旗的基础。朵颜卫由明代蒙古部落到清代扎萨克旗的变迁过程代表了明清蒙古部落发展的一种类型。日本学者和田清先生《察哈尔部的变迁》疏理了朵颜卫部落变迁的线索,具有里程碑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蒙文史书《阿勒坦汗传》的点校出版以及大量汉文新史料的发掘,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蒙古文文书档案的影印出版,使得17世纪上半叶的朵颜卫历史的画面越发清晰。但是,在16世纪后半叶朵颜卫的研究方面,有很多问题仍然停留在和田清的水平上。本文试图在和田清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阶层所蕴涵的实际内涵、阿勒巴图首领所任官职等问题,为朵颜卫认同于领主万户,最终以领主万户的名义归附后金寻求合理的解释。
一
根据蒙古文史书佚名《阿勒坦汗传》的记录,以朵颜卫为首的“乌济业特兀鲁斯”即兀良哈三卫是主动投降,成为蒙古本部右翼的“阿勒巴图”的。此书以韵文的形式记录了朵颜卫左都督影克率领“乌济业特兀鲁斯”归附右翼蒙古的具体过程:“久为外敌的乌济业特兀鲁斯,以恩克丞相为首的诸诺延,(慕名)举族携带乌格仑哈敦之宫室来降,山阳万户自行降为阿勒巴图之情由如是这般。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将恩克丞相赐予其弟昆都楞汗,将其(恩克)弟兄分别占为己有,将其收为阿勒巴图之情如此这般。”[1](46-47)这里,“乌济业特兀鲁斯”是对兀良哈三卫的泛称;[2](113)所谓“恩克丞相”就是影克,著名的朵颜卫左都督花当的后裔;“乌格仑哈敦”即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哈屯;“额尔德尼菩萨土谢图彻辰汗”就是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其弟昆都楞汗”即喀喇沁部首领老把都。学界对这些皆无异议。笔者以为,影克的投降可能只是名义上的归附,1550年“庚戌之变”以后,蒙古本部对朵颜卫进行武力征服,朵颜卫与蒙古本部才形成了稳固的附属关系。[3](211-220)无论如何,朵颜卫在影克时期成为喀剌沁和土默特等蒙古万户的阿勒巴图,形成了属部与领主的关系。汉文史书《卢龙塞略》卷十五《贡酋考》也将朵颜卫各部作为“东虏属夷”和“西虏属夷”分别胪列。在朵颜卫各部拥有“阿勒巴图”(即所谓“属夷”)的名分这一问题上,蒙、汉文史料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根据达力扎布先生的统计,包括左都督影克及其继承者长昂领导的部落在内的14支朵颜卫部落都附属于左翼蒙古的喀喇沁部。[2](114)“阿勒巴图”一词的词根是“阿勒巴”(Alba),意谓赋役。阿勒巴图(Albatu)指承担赋役的人或纳贡的人。符拉基米尔佐夫在他的巨著《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说:“属民对于领主——各级封建主——的最大义务是提供alban(阿勒巴、阿勒班)即‘服役贡赋’。阿勒班是蒙古封建社会的纽带,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服务与忠诚’(hominium et fidelitas)因此,属民常称为——阿勒巴图(负担赋役义务的人,纳贡的人),即vassalus,feodatus。最普通的平民阿拉特是其领主的阿勒巴图,而领主自身,甚至诸王,对其额毡、可汗的关系,也可称为阿勒巴图。”[4](249)符氏所讨论的是明代蒙古鄂托克或万户内部属民与领主之间的本质关系。朵颜卫作为一个集团,主动投降而成为喀剌沁万户的阿勒巴图,他们对于领主万户喀剌沁部的“最大义务”也应该是“提供alban(阿勒巴、阿勒班)”,不会有什么例外。但是蒙文史书《阿拉坛汗传》所记仅仅是上引两段概述性韵文而已,关于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的具体义务,没有其他叙述文字。宝音德力根先生说“朵颜卫各部对于领主鄂托克或(领主)万户所尽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兵役,发生战争时,跟随鄂托克参战。除此以外,还缴纳徒具虚名的牛马贡赋。”[5](52)但是没有进行论证。
汉文史料为我们了解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的“阿勒巴”,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居正《答吴环洲策黄酋》说俺答汗长子辛爱黄台吉“威胁属夷,为之纳进”。[6](280)这里所说的“属夷”是指附属于辛爱黄台吉的朵颜卫部落,主要是李家庄朵颜别部和游牧于潮河流域的伯颜打来部。这反映了西部边缘的朵颜卫部落与黄台吉领导的“土默特别部”的关系。关于朵颜卫与喀喇沁万户的关系,张四维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中说“唯把都立帐宣蓟之交,不畏捣巢,三卫夷人为所略属,凡渠所须中国之物,三卫皆足以给之。”[7](527)这里的“把都”是老把都,即喀喇沁万户首领昆都楞汗。“三卫”所指是朵颜卫,看来,明蒙之间实现“隆庆封贡”之前,被“略属”的朵颜卫向喀剌沁老把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明朝物产,明朝方面是知道的。但是,朵颜卫给喀剌沁部“所需中国之物”是否就是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向领主所提供的“阿勒巴”呢?所谓“阿勒巴”应该是阿勒巴图定期向领主提供的赋役,但是从上引汉文史料的记载还看不出这种迹象。
与上述史料相比较,瞿九思《万历武功录》的记录更耐人寻味,从老把都时代开始,喀剌沁万户的首领多次到朵颜卫首领的驻牧地“祭神”。我们把相关记载录于下:
居亡何,庄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黄台吉起自插汉脑儿,把都儿起自火郎不喇酥,并治兵黑汉脑儿,图我蓟门。适安滩病,弗可行。独把都儿往影克营祭旗纛。[8](卷之八,787)其明年二月,青把都与属夷讨孙卜赖有隙,欲因缘子婿长昂以报之。遂与母哈屯及其弟莽古大、莽古塞、哈不慎等驰昂营祭神。[8](卷之八,850b)
明年……五月入贡,赴张家口市,皆如初。其九月,长昂罚诸败北者马牛。已,青把都从所居白言举儿克引众驰长昂营,声言祭神,又言欲驼米,号召诸酋。[8](卷之八,852b)
上引第一条史料记录的“祭旗纛”发生于“庄皇帝即位”之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此时喀喇沁部的首领还是老把都,而朵颜卫的首领是影克。可以肯定,“祭神”活动从老把都时代就开始了,不能排除“安滩”(Altan)即俺答汗也曾经和老把都一同到朵颜卫牧地的可能;根据《卢龙塞略》的记载,朵颜卫首领的驻牧地在老哈河流域大宁一带。那么喀剌沁万户首领所至应该是这一地区。第二条史料记载的事情发生于万历六年,喀喇沁首领青把都在征服朵颜卫讨孙卜赖部的绕道“驰昂营祭神”。昂就是长昂,影克之子,隆庆元年(1567)影克死后,袭职为朵颜卫左都督。子承父业,青把都继续到长昂营地“祭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长昂营地所祭何“神”?是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太后的宫账,泰宁卫的首领是辽王脱脱后裔,而辽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裔的王号,乌兰博士在她的新著《蒙古源流研究》中考证:“月伦哈屯的宫帐确在斡赤斤后裔处。”[9](313)大概在正德年间花当领导的朵颜卫强盛以后,月伦哈屯的宫帐转到朵颜卫的牧地,影克归降俺答汗的时候,就是“举族携带乌各仑哈敦之宫室来降”的。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哈屯确在蒙古社会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的宫帐先后由泰宁卫和朵颜卫负责祭祀,而作为领主的喀剌沁部首领,居然兴师动众到属部朵颜卫的长昂营中“祭神”,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作为领主部落的首领,老把都和青把都到朵颜卫营地的目的仅仅是“祭神”吗?如果还有别的目的,那会是什么?这是真正令人费解的问题。申时行《纶扉简牍》收录的一封信为我们解开了谜团。申时行在《答许益斋巡抚》的信中说:
青酋部众岁一东行,名为祭神,实征诸酋岁献,非有窥间内讧之意也。至于蓟辽属夷假借青酋声势虚喝边人向来有之,此不足虑。”[10](257)
青酋当然是喀喇沁部的“酋首”青把都,“蓟辽属夷”就是朵颜卫部落,他们的牧地南与明朝蓟州镇毗邻,东与辽东镇相望。青把都每年到长昂住牧的大宁城“祭神”、所谓“祭神”只是青把都“东行”的堂而皇之的名目,他真正的目的是“征诸酋岁献”,可以确信,“岁献”就是附属于喀喇沁的朵颜卫部落作为阿勒巴图(albatu)每年向领主万户上缴的“阿勒巴”(Alba,意谓赋役)。申时行的书信虽片言只语,却道破了天机。朵颜卫部落中“附属西虏把都儿”的有十四支,青把都每年到朵颜卫地区,征收的“岁献”想必就是征收这十四支属部所承担的贡赋。值得注意的是,朵颜卫缴纳的“阿勒巴”是领主万户上门来收取的。我们再回过头看前引《万历武功录》的第三条史料,所谓“青把都从所居白言举儿克引众驰长昂营,声言祭神,又言欲驼米,号召诸酋”句提供了三个重要信息。第一,为避免引起明朝方面不必要的恐慌,青把都每次在“驰昂营”之前都事先向明朝“声言”。万历六年七月,“北虏青把都拥二万众欲抢仇夷讨孙卜赖,逼近边塞,乃先期告报,誓称无他,秋毫不犯。”[11](卷七七,1658)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第二,青把都向明朝方面“又言欲驼米,号召诸酋”,说明他曾经向明朝方面明白表露过他到长昂营地的真实目的,所谓“欲驼米,号召诸酋”似乎就是“征诸酋岁献”的另一种说法。《万历武功录》的史料证明申时行的情报并非空穴来风。青把都每年到朵颜卫牧地“祭神”的真实目的在当时可能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申时行只不过偶然说出来,为我们了解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的义务提供了重要证据。第三,关于朵颜卫“诸酋岁献”的具体内容还不是很清楚,张四维说“凡渠所须中国之物,三卫皆足以给之”,应该是就“隆庆封贡”之前的情况而言的。《万历武功录》所谓“驼米”也令人难得其要领。但是,“名为祭神,实征诸酋岁献”的记载证明,朵颜卫诸部作为阿勒巴图,他们向领主提供的阿勒巴的贡赋也确实存在。汉文史料的记录再一次印证了蒙文史书《阿勒坦汗传》的史料价值,朵颜卫作为阿勒巴图的身份是有其实质内容的。
二
朵颜卫各部住牧于燕山山脉崇山峻岭间面积狭小的山地草原。蒙古本部可以用武力征服朵颜卫,却无法长期驻守,朵颜卫地区没有供“号称百万”的蒙古本部游牧的草原。在征服朵颜卫以后,他们只能退回各自的牧地。但是,蒙古侵掠蓟州以及宁远、前屯等辽东边境时,需要朵颜卫各部做向导,要在明朝边境找寻准确的攻击点又需要朵颜卫各部来侦探,所谓“蓟之防虏必假属夷以为哨探,虏之侵犯必假属夷以为乡导”。[12](302)所以蒙古本部又不能将他们消灭或强制迁徙。那么蒙古万户又是如何统治他们所征服的朵颜卫部落的呢?
“庚戌之变”以后,朵颜卫西面门户洞开,俺答汗长子黄台吉“充当经略朵颜卫的急先锋”,[13](600)率先征服了李家庄朵颜别部和潮河流域的朵颜卫部落。他曾经派官员镇守朵颜别部,这种官员类似于蒙元时代达鲁花赤,具有镇守监临之责。《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年六月壬午条记:“先是,宣府边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等,为黄台吉以兵威略属之。因用为导,以内讧,永宁、龙门之间颇被其害。然黄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及所部夷妇有色者多为所渔,并攘其牛马。由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边臣,愿内附保塞。边臣疑其诈,令杀虏自效,以立征信。史夷兄弟乃斩黄酋所署监部夷孙头目忍克等十余人,尽戟其众,以其俘馘来献。”[14](卷四九八,8249)史大、史二就是李家庄朵颜别部的首领。“忍克”可能是“恩克”(Engke)之讹。黄台吉“署监部夷孙头目”来统治已经征服的属部,这是黄台吉的统治方式,他所统治也只是朵颜别部。
对于朵颜卫本部,特别是朵颜卫左都督直接领有的部落,作为领主的蒙古万户是如何统治的呢?申时行《纶扉简牍》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证据。该书第六卷所收申时行《答许益斋巡抚》说:
不他失礼西部大酋也,声势颇大。今止于青酋部内成婚,而以百人东往,其无他谋可知。惟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常为蓟患也,或以不他至彼,假名窃掠,亦不可知,此则蓟镇当备耳。”[10](237)
这里的不他失礼是俺答汗与三娘子所生子,后一句的“不他”是对不他失礼的简称。他到喀喇沁部“成婚”的具体时间无从考证。看来,他当时顺便到过喀喇沁属部朵颜卫的牧地。长昂是明代蒙古朵颜卫左都督花当后裔,革兰台嫡孙,影克之子。在隆庆元年(1567)影克死后,长昂袭职为左都督。申时行此信“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一句为我们考订长昂的名称及官职提供了重要依据。
申时行说庄浪就是经常在蓟州边境制造麻烦的朵颜卫左都督长昂。在汉文史料中,长昂之名还写作专难、砖难等,戚继光《蓟镇边防》谓:“夷人名字东西关口各呼唤不同,仅取其语音相似者,仍从其旧,譬如专难即长昂……”。[15](513)米万春《蓟门考》记朵颜卫左都督“影克隆庆元年导犯界岭口,出义院口,被我官军用快枪打伤,回巢即死。今有伊男专难袭职为首,太平路等边呼为长昂”。[16](505)专难就是长昂,“长昂”是明人使用最广泛的译法。“庄浪”是许守谦任职的宣府地区方言译音。元明时期,汉译少数民族名物制度的时候,泥母字和来母字是经常相混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不能”和“倘不浪”,将专难译为庄浪就不足为怪。“专难”和“庄浪”的译法证明,“长昂”之“长”应读浊音,而影母字“昂”在“太平路等边”是和泥母字相混,读作nang或nan的,这种现象在今天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依然存在。至于用鼻音ng翻译闭音收声n更是常见事。长昂的名字在明代蒙古史书中没有记录,根据“庄浪”、“长昂”、和“专难”等不同译法,乌云毕力格先生将“长昂”还原为蒙文原文Jongnan应该是正确的。[17](8)
申时行说“庄浪恰者即属夷长昂”,证明朵颜卫左都督长昂是一个“恰”。司律义神父(Henry H.Serruys)在参考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和田清波(Antoon Mostaert)《鄂尔多斯词典》后指出:“正如许多其他场合,‘Kiya(恰)’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官职或衔号……Kiya意为‘侍从、卫兵、扈从、副官’。”[18](45)他同样也注意到了《三云筹俎考》的不同解释,该书《夷语解说》说“恰,与首领同”,而对“首领”的解释是“是各台吉门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19](卷之二,24a)就是说,恰(kiya)在漠南蒙古社会,相当于各万户各鄂托克领主辖下的行政官员。鄙见以为,“恰”一词源于突厥语词Kiy-a,意谓“小”,是形容词,置于所修饰名词之后。[20](第三册,164-165)卡哈尔·巴拉提先生在他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九和第十卷译注》中将特勤恰(Tekin Ki-ā),译为“小王子”。[21](IX8b)耐人寻味的是,这个突厥语形容词在明代蒙古社会竟演化为官职名。前引《阿拉坦汗传》说“恩克丞相为首”的“乌济业特兀鲁斯”投降给俺答汗,后者将“恩克丞相”赐给了喀喇沁老把都。《卢龙塞略·贡酋考》说革兰台长子影克一枝“附属西虏把都儿”,[22](494)是“附属”于蒙古本部右翼喀喇沁万户的“属夷”,蒙汉文史料非常契合。如前所论,喀喇沁万户的首领每次到朵颜卫“祭神”也都是到“长昂营”,作为喀喇沁的属部朵颜卫的首领,长昂的恰官号一定是来自喀喇沁万户的封授。朵颜卫首领何时开始有了“恰”的官职,尚难断定。但是,至迟在长昂时期,朵颜卫左都督已经成为喀喇沁万户下“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了。喀喇沁万户征服朵颜卫本部,将其收为阿勒巴图以后,任命朵颜卫左都督为恰,让他代领主万户行使“主本部落大小事情断事好人”的职权,这就是喀喇沁万户对其朵颜卫阿勒巴图的统治方式。
其实,《简牍》所谓“庄浪恰即属夷长昂”的记载并非孤证,当我们重温《万历武功录》的史料,对该书《长昂列传》的记载又有了新的发现:“是月也……土蛮亦帅三万余骑驰专难他不能营,候青把都、蟒忽大,声欲寇我义院口。于是,胡骑并逐水草,壁大宁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妇政从白彦举儿克迎喜神,亦驰专难恰倘不浪营。”[10](卷十三,1172a)他不能、倘不浪,清译塔布囊(tabun-ong),是明代蒙古对黄金家族的女婿的称呼,《三云筹俎考·夷语解说》谓:“倘不浪,是王子家女婿。”[19](24a)长昂娶青把都女东贵为妻,是蒙古本部的喀喇沁部的女婿,所以蒙古左、右翼各部称长昂为倘不浪当然毋庸置疑。那么,“专难恰倘不浪”(Jongnan kiy-atabun-ong)一定是指长昂无疑。看来,长昂的确以“庄浪恰”闻名于漠南蒙古社会,庄浪恰、专难他不能、专难恰倘不浪都是对长昂的称呼。
三
除了征收赋役,设置官员,联姻是蒙古本部笼络控制朵颜卫诸部阿勒巴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蓟门考〉集中胪列了几例朵颜卫与蒙古左右翼各万户联婚而导致被征服的事例。
事例一:
都指挥炒蛮,伊父哈哈赤乃花当妾出之兄弟七人。今哈哈赤等蚤故,止遗弟一人虎头罕,大炒蛮见有亲兄弟小把都儿董灰等十人,叔倒约有部落有千骑,俱在大宁城前后住牧。伊妹系东虏故酋首悲马之妻,先因结亲往还,因而归顺东虏部下,联居兵也[16](505)
此炒蛮是花当第五子哈哈赤之子。悲马即〈蒙古王公表传〉记载的贝玛土谢图,是敖汉旗始祖。蒙古右翼侵入朵颜卫地区时,哈哈赤部是最先遭受抢掠的部落之一。按照〈蓟门考〉的说法,该部最终与蒙古左翼联姻而“归顺东虏”。
事例二:
都指挥故夷伯彦帖忽思、伯思哈儿、伯彦孛罗三人之子并见在弟把秃孛罗等叔侄四枝部落,约有一千余骑,在古北以逊、以马兔一带住牧。因伯彦帖忽思妻名八个镇,伊女是辛爱之妾,今古北哨役入属夷挨合必营是也。(把)秃孛罗是北虏之婿,诸众以亲俱归顺东西虏酋部下。此夷乃影克堂兄弟也,皆为逆虏常调之兵。[16](505)
以逊、以马兔即以逊河、以马兔河,就是清代的木兰围场。在这一带游牧的伯彦帖忽思、伯思哈儿等兄弟四人是花当孙辈,革儿孛罗次子革孛来的四个儿子。据此则兄弟四人的部落分别附属于蒙古左右翼。伯思哈儿的部落在长子脱孙孛来时期被喀喇沁青把都征服以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又成为喀喇沁的属部。
事例三:
都指挥伯彦打木(来)部落,约有七百余骑,在石塘岭境外地方满套儿等处住牧,伊妹名苏不该,系辛爱第九妾也。因亲归顺本虏部下,联络相接,往还不绝。[16](505)
伯彦打木是伯彦打来之误,是花当第四子把儿真之孙,板卜之子。该部应该是嘉靖二十九年以后最早与土默特别部联姻的部落之一。成为土默特别部以后,在明蒙之间骑墙,到万历二十年左右被辛爱之子赶兔吞并,后来成为土默特右翼旗部众。[23](52)史料所见朵颜卫部落中由联姻而导致吞并的仅此一例。
米万春〈蓟门考〉有关朵颜卫诸部“因亲归顺”而成为“东虏属夷”或“西虏属夷”的记载近于公式化。他认为朵颜卫诸部由于蒙古本部万户联姻而成为“东虏属夷”和“西虏属夷”,这种观点明显是本末倒置,不足为信的。我们认为,朵颜卫各部被蒙古本部武力征服是双方联姻的前提条件。〈卢龙塞略〉的记录更为可靠,该书〈贡酋考〉说:
朵颜卫各部虽各住营,皆逐水草地常,俗与鞑靼同。昔世与北虏为仇,故仰命于我。边将多领顽,狃其易制而狎侮之,且缩其赏物,而物不如制,故积愤,且不为主,东西二虏得胁服之。事以子女,不得已也。其种最贵者为之婿,虏酋岁至祭天,以往来其部落,而次则奉女为嬖只者,妾之称也,有小、大,各分部人马,其父兄反为所摄而因亲以居矣。自花当动称解仇结亲迤北,以恐吓中国,至于(今)日者,其妾、夷女缘口分,故我抚赏日增,若诸关口有:在石塘为小嬖只,都督伯彦打赖之女;在古北为大嬖只,都指挥炒蛮之姊也;在曹家有宝兔嬖只,都指挥董狐狸之女;在马兰有猛可充嬖只,都指挥伯牙儿之妹也。伯牙儿妹为老把都妾,其三皆典台吉妾也……既而虏酋青把都以长昂为其婿而亦近关索赏,则凡属夷附属于虏酋者,伯彦主喇其男亦为安滩婿;少炒蛮为黄台吉婿;马塔哈等为为土蛮亲妹夫……[22](529-531)
蒙古本部对朵颜卫各部“得胁服之”在先,然后与他们展开广泛的联姻。联姻是蒙古左、右翼各部强加给朵颜卫兀良哈贵族的政治性的联姻关系,朵颜卫兀良哈贵族作为弱势群体,“事以子女,不得已也。”〈名山藏·王享记〉说朵颜卫在“嘉靖中与北虏为婚媾,时时导虏入我边。诘问之,辄支吾对我:‘中国不能为我主,与婚媾求好而已。’”[24](295)明巡按御史李惟观在隆庆元年(1567)在鲁镇曾“谒之边人,谙夷情者曰:‘影克诸夷虽称变诈,然于中国有德无怨。今与大虏虽和,不过畏其威棱朵。’”[12](365)朵颜朵处于在明蒙两强之间,蒙古本部强兵压境的时候,以宗主自居的明朝却一直在隔墙观火。面对蒙古左右翼强大的武力,接受他们强加的联姻关系以“求好”是朵颜卫兀良哈贵族惟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蓟门考〉史料可贵之外在于,它所记载的联姻关系往往与政治上的附属关系相一致。前引〈贡酋考〉所说安滩就是俺答,做俺答婿的“伯彦主喇其男“就是花当之孙猛古歹的儿子那秃,这一联姻关系与猛古歹部“附属西虏安滩”的记录是一致的。少炒蛮是前引事例二伯彦帖忽思的次子。马塔哈就是马答哈,是花当第三子打哈的儿子,〈贡酋考〉说该部附属于察哈儿土蛮汗,与他们所与之联姻的蒙古万户是一致的。[22](531)另外,最著名的联姻〈贡尊考〉没有记载,即朵颜卫左都督长昂娶喀喇沁青都女东贵,做了喀喇沁的塔布囊。蒙古各部称朵颜卫兀良哈贵族为“山阳官人倘不浪每”[25](23)就是在这样的联姻以后逐渐形成的。
以上只是联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朵颜卫兀良哈贵族的女儿们嫁给蒙古本部的封建主。她们出嫁以后只能做蒙古黄金家族台吉的嬖只(biiji,意谓妾),史料中还未发现有她们中成为哈屯(qatun,意谓皇后)的例子。大嬖只即伯彦帖忽思之女,少炒蛮的姐姐。伯彦帖忽思部与土默特别部有双向的联姻关系,此部“附属西虏辛爱”就不足为怪了。猛可充就是猛可真,是喀喇沁老把都妾。她的哥哥伯牙儿是革儿孛罗之孙,脱力之子。伯牙儿部“附属西虏把都儿”,把都儿就是喀喇沁老把都,正是猛可充的丈夫。老把都死后,她带着子女回到朵颜卫地区。惟独有关宝兔嬖只的记载前后有歧异,这里说宝兔是董忽力之女,是辛爱黄台吉妾,而董忽力部却附属于喀喇沁老把都。
朵颜卫与蒙古本部的联姻是双向的,而联姻导致的结果却是同样的。蒙古本部的公主嫁给朵颜卫兀良哈贵族,来到朵颜卫的营盘,这是可以肯定的;朵颜卫的女子嫁给蒙古本部的封建主做嬖只(biiji,意谓妾)以后,也带领她们的子女回到朵颜卫地区。这样,双向的联姻都导致大量入口内流,“其父兄反为所摄而因亲以居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人口流动极有可能与明朝的抚赏银制度有关。朵颜卫与喀喇沁等蒙古本部的各万户联姻以后,蓟镇边外朵颜卫的牧地很快就出现朵颜卫兀良哈人与蒙古本部杂居现象。〈卢龙塞略·贡酋考〉说:“盖蓟镇边外昔惟属夷驻牧,近因夷女联姻东西大虏,以致各酋子侄 或随母、妻、或因分管部夷,移来蓟镇边外驻牧。故镇臣不知大宁故地与夷既久,任其与虏驻牧,而且抚赏求息边事,至此大舛矣。”[22](400)明朝蓟辽总督蹇达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奏疏也说:“今中东二协,领赏者三卫属夷。而西路领赏者,半系西瞄之裔。如赶兔者,倚恃顺义王之弟,更为桀骜之尤。”赶兔是辛爱黄台吉之子,扯力克之弟,所谓顺义王是指第三代顺义王扯力克。大概从万历十年开始在石塘岭等关领取抚赏。大概从万历十二年开始,小阿卜户在蓟镇喜峰口、马兰谷领取抚赏,一直到万历十八年死,(注:史二官是万历十八年“叛附”赶兔的,申时行万历十九年,“驰驿归”乡。申时行〈答王凤山巡抚〉的信说:“小阿卜户久的为蓟患,今忽自毙,亦天厌其恶也。史、车二酋出境,宣镇殊为□略”云云。则小阿卜户当死于万历十八年(1590)。)明朝蓟镇马兰谷、黑谷关等边才稍得安宁。据张佳胤的说法,“此小酋为青把都部落,”[26](8b-9a)而蹇达〈贼夷境外窃掠查参将领疏〉说:“再照小阿卜户乃系酋妇猛可真部落”,[27](卷之四.51)猛可真是朵颜卫都指挥伯牙儿之妹,喀喇沁老把都之妾。小阿卜户究竟何人后裔尚难考订,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是喀喇沁部的人。象赶兔和小阿卜户这样“既非应赏属夷,又非虏王部落”[10](127)的领赏者在蓟镇边外还有很多,〈两朝平攘录〉卷一之〈附三娘子〉说朵颜卫左都督长昂、右都督把班,“通二酋所辖一百五十枝,今各路徼(邀)赏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28](185)这九十二枝想必都是来自喀喇沁或土默特等朵颜卫的领主万户,或者是朵颜卫与蒙古本部联姻以后所繁衍的后裔及其所领部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