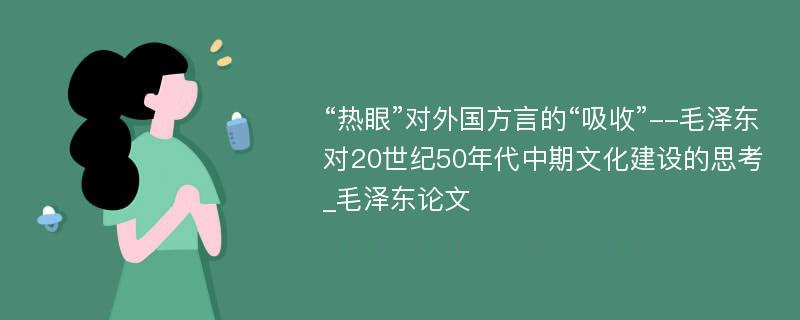
热眼向洋话“吸收”——50年代中期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个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思路论文,年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1954年去北戴河游泳,写出高唱“换了人间”的《浪淘沙·北戴河》之前,参加了6月11日为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会议。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会上提到: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国歌好。
毛泽东发言了:国歌是必须规定在宪法上的。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觉得不舒服。但如果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呢,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的确,50年代的中国,建设刚刚起步,总的说来还很穷;国际环境也颇为恶劣,中国还无法真正地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林的现代国家。毛泽东期望用“最危险的时候”来激励人民奋发图强,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无道理。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只有自己强大了,别人才看得起你,你也才能真正摆脱威胁。这是毛泽东做人做事和治国的一贯信念。
搞建设,谋富强,中国能引为楷模的,只有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几乎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期待和信念。1954年10月,苏联在北京举办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毛泽东看后题词:“我们觉得很满意,很高兴。这个展览会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的幸福。……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里,包括文化事业方面,苏联也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未来的中国,在文化上向先进国家学习,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就定下了的思路。
这种选择并不奇怪。解放战争中美国支持蒋介石一方,这无疑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他在批判美国“白皮书”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里,就自信地表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精神方面”的新中国文化,文学艺术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几年后,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特别是过渡时期完成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明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毛泽东的思路有了变化。
较早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53年2月7日的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那时,还没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代行其职,毛泽东等于是在法律上的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上宣布: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的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数。我是不信言佛的。但那个时候很多人信佛教,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后来人困难得多。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别的民族的优良的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从中日战争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里,全国有一个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他们的科学的高潮。那一个学习对于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帮助的。
言下之意,今天似乎也要来一个学习。要学的对象,当然就不光是苏联了,明显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
要探索创新的人,对自己没有掌握的东西,总是非常向往;他的内心世界总会是开放和渴望开放的;对墨守陈规的作法,就会不感兴趣。毛泽东亦不例外,有时候他甚至在一些小事上借题发挥。
就在讲佛教和许多乐器都是从西域引进的这段话10天后,毛泽东来到了武汉,住进东湖宾馆。这里的建筑风格引起他的注意。在召见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不知为什么,他说到了民族形式:
你们在东湖盖的两所房子像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毛厕,要用抽水马桶?就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这可能是从北京围绕是不是拆除城墙而出现的争论引起的。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是主张拆除的,他一心要把北京建设成现代化的城市,看着满目皆是古里古气的了无现代明快感觉的建筑(故宫这样的文化象征自然例外),似乎总有一种落后保守的阴影笼罩心头。他也是有意识地把这场争论上升到是保守传统还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思想高度来理解的,后来不只一次从建筑角度谈起民族风格问题。甚至直露地表示:在建筑上,我赞成洋气,开封不像个样子,完全是老式的房子,北京的城市建筑是封建主义的。完全老式的,乌龟壳式的,我不喜欢这个乌龟壳。为什么一定要讲保存民族风格,你那个铁路、枪炮、飞机、火车、电影、拷贝,中国与外国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民族风格?我看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
这个话,说得很激烈。在他的思路里,显然不光是建筑风格,而是所有外国文明都要吸收,甚至包括语言文字。
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上,从延安起就主张改汉字为罗马字,搞拼音化的革命老人吴玉章,又提出来拼音化的问题。毛泽东也借题发挥,表示赞成,说得很幽默:
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好,很有理由。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就有几位教授跟我谈,说这个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我就看不出,我也多少学了点汉字,那么“世界万国”,那么“最好”?就不见得。改成罗马字,如果罗马字是中国人发明的,我想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我们决不反对,吃亏的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去学,因为不是“用夏变夷”,而是“用夷变夏”,外国的洋字怎么能作为我们的字呢?但是现在看起来,是采取这个洋字比较好,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的事情早已经有了呀!
有些东西不一定讲民族风格,这个想法无疑千真万确。但变汉字为罗马字这样的事情,却很难当真,做起来,无疑很困难。毛泽东如此说,主要是显示一种摒弃保守走向开放的急迫心态,表达一种在文化上需要大度吸收的气度而已。
当然,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一向是主张民族风格的。一个直观的理由是:我们中国文工团,到别的国家去,演我们民族的歌舞、戏剧,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到外国去演出,人家就不欢迎。
由此,毛泽东得出一个比较内行也显得很直率,并且很吻合他的文化情趣的结论:“艺术的民族 保守性比较强一些, 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特别是一些民间艺术,毛泽东对它似乎有特别的好感。大概是这样一件事给他的印象很深。有一个叫杨士惠的人,是民间搞象牙雕刻的,一次,毛泽东请他吃饭,杨士惠即席就为毛泽东雕了一个像,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他“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丢了。……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当然,在文艺上保持民族风格,并不等于不向外国学习。相反,毛泽东认为外来的东西搞久了,就会积淀为民族的风格,特别是在1956年提倡“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一段时间里,他说的学习先进,便更明确地包括了文艺方面。成为他的重要例证的,还是他此前讲过的唐朝引进外来音乐的事情。他说:
我们要在这十几年之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都是这样做的,汉朝、唐朝就是这样。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是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七种舞蹈,其中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其他的搞久了就成了中国的了。
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当时没有公开,很少有人知道。凑巧的是,当时的音乐界,恰恰在围绕中西方音乐的关系进行着争论。
195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的文章《音乐舞蹈的民族形式》,说目前音乐舞蹈创作中“存在着一种不好的现象,这就是中西混杂、不中不西、看不出民族特色”。作者认为这是个涉及新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的大问题。音乐批评家李凌发表了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说:有人“对音乐风格的‘不中不西’深恶痛绝。‘不中不西’就是不全像中国,也不全像西方。换句话说就是‘又中又西’,这是创作新的民族音乐形式难以避免的情形”。其他人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参加争论。
为此,周扬曾几次召集中国音协理事和正好来北京参加音乐周活动的各省市音乐工作者代表开会,会上争论也是特别激列,乃至周恩来也不得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场争论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而且显然是同意李凌的观点。
8月24日,音乐周活动期间,他和一些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音乐周活动的代表。然后特意把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留了下来,长谈了一次。说的例子,也是他此前多次说过的唐朝的事情:“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
正是这次谈话,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他对中西方文化艺术关系的观点:
——在各国之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承认各国艺术有共性也有个性,这是吸收和学习外国艺术的理论前提。
——把文化艺术的发展,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来审视,由此确认先进还是落后的标准。他说:“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文章,今天用不着。……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这就从政治的角度解决了吸收西方文化艺术的心理障碍,同时说明,继承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绝不是要维护落后的东西。具体说来:“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但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上讲,老是背着深长久远的传统,也是很不利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这就从艺术发展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不能墨守成规,要科学对待文化遗产的观点。而且,民族形式本身也是需要变革的,比如,“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因此,“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他还说:“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借鉴西方,不是全盘西化,因为“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但这个东西又不是纯传统和民族的,那么,它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毛泽东提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概念。他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这是对创造未来新艺术的不拘一格的追求。
总之,还是那个老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古人是为了活人,学外国是为了中国。这里的“今”和“中”,合起来就是中国的时代性。在毛泽东看来,鲁迅的创作就是这样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创造中国的现代艺术,就是毛泽东当时提倡向外国文化艺术学习的根本出发点。“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
这些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有关文化艺术领域中外关系的论述的最高水平。此前,他没有急迫的动力和机会来思考这个问题,此后他虽也偶尔说到这个问题,但总体上是没有这样具体和深入了,而且是逐步地往后在退。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1956年,而不是此前或此后,毛泽东在文化艺术上萌生出这些大胆的探索思路。我想大致有这样几点:
主要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探索,引发他对文化艺术方面的类似思考。也就是说,“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首先是当作政治经济话题提出来的。这年4月谈“十大关系”时,他甚至提到这句话暗含的国际政治背景:“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愿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这样的开放气度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显然是为了改变50年代初期只向苏联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的思路。因为这种做法,事实出现了教条主义照搬的弊端。在4月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举了这样的例子:“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毛泽东在此提出了文化借鉴上一个重要的原则:不要拾人牙慧。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就特别调强文艺的民族性,这个想法没有变,但针对性已经没有过去强烈了,因为环境和任务已经变化了。今天强调向一切国家学习,针对性是要探索,要创新,要现代化的东西。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内容还是形式,都要摆脱旧东西的羁绊,这就需要“标新立异”。当然,他的思路中,文化艺术的“标新”主要是形式方面(这从他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在精神气质上,他一向是特别坚持“原则”的,对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很少有好感。
毛泽东一生对于外国文化艺术的态度,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他呼吁借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成果,用平民主义的文化来反抗中国传统的强权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从事农民运动,着重是了解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初期,出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他讲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热情更突出一些,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任务,对西方的外来文化艺术不怎么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战场事实上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视野更开阔了,说到外国的文化艺术,多强调要辩证吸收,这个思路,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建国初期,说到外国文化艺术,主要是指苏联,一般不涉及西方。正是到50年代中期,由于以上所说的各种原因,出现了毛泽东一生中大讲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