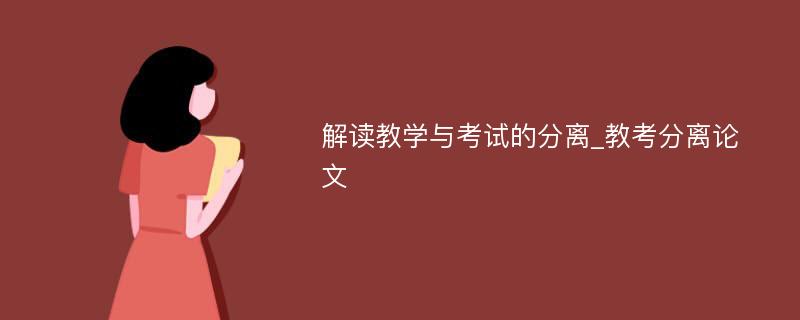
读解“教考分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注册视听生”试点试了3年,“教考分离”依然是个兴奋点, 谈论依然显得浮躁,沟通显得困难和缓慢。
当初,试点伊始,众说纷纭,就是扯得再远,结果还是要回到以及格率为疑点的教考分离上来,那些令人惊讶的话依旧萦绕于耳:“什么教考分离?本身就说不通,教与考原来难道是合并在一起的吗?”明显带有一种调侃的意味。
还有一些人说起来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对注册视听生搞‘教考分离’,是对电大的不信任。”这话已超出对问题本身的看法,带着情绪化的怨气,也不对头。
通常说,考试是一种检验,教育测量学则说,考试是一种测量。检验什么,测量什么,一般说大家都比较清楚,容易忽略的是它的另一层意义。
考试的作用在检测,检测的有效性以严肃公正为保证,使之不失真,不错位。因此检测具有鲜明的监控性质。而怎样监控,谁来监控本身就有选择性。办法不同,其作用和影响也不同;自己临控和他人监控结果显然不一样,要不然就不可能出现教考分离这种形式。招生考试、验收考试、抽查考试、评估考试早已有之,不就有明显的监控意思吗?不就是教考分离的做法吗?
就一所学校来说,办学重数量若成为一种倾向,似乎多多益善,那么,考试就成了发展数量的主宰,所谓“学生容易毕业了,办学就有吸引力了”,这样,监控考试的问题就更为严重。
以审视的眼光看过去,电大办学史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也有堪作教训的实例。1993年和1994年,电大招收基础班,按照入学免试的办法招收进来的学生状况跟注册视听生相类似,教考电大统管,强调一揽到底,结果如何呢?在有关部门没有点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前,难道我们自己心中无数吗?今天在尘埃落定以后再说这桩事,不必遮遮掩掩,倒是应当面对事实、深思一番的。
电大招收“注册视听生”是一项改革,改革扩大了开放,也带来了问题。与通常办学相比,有“不组班、以自学为主”的根本差异。学生宽进了,怎么严出呢?本来就值得考虑。将教考划分开,明确规定“教考分离”,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办学形式变化使然,并非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完全不必扯到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上去,也不必有怨气。
时过境迁,这类场面已经定格,不可能重演。但是偏执成为思维定势,要改变是得些时日的,时下对教考分离的非议和龃龉不断,或许就是它的余波,不过已是零七碎八,不值一谈了。
这里倒是想探讨几个问题。
“教考分离不是教考脱节”。
这话是对教考分离的界定,也是向考试发出的警示。
将“分离”搞成“脱节”,当然说不过去。要是弄成那个样,确实值得深究:是教考分离本身的问题呢,还是操作不对头呢?
从表面看,教考脱节与教考分离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不明或无视教考分离的本义二者是很容易混为一谈的。
“教考分离”,时下还不是理论概念和科学体系中的术语,如果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只能以平常人的眼光谈平常人的看法。
教考分离针对“教考合一”而言,从严格考试管理的资料看,普通院校的说法接触到了它的含义。教考分离“改变了长期以来谁教学谁命题, 谁评卷谁打分, 一人一贯到底的老传统”(见《高校领导参考》1995年第23期《山西大学抓考风的实践体会》一文)。这就是说,教、考不再集于一身,教者只管教,不参与考。
我们实行的教考分离含有同一意思。
教考分离,说是“分离”,不过是对教与考职责的划分,并不是对教学与考试的内在联系的分割,不论教者、考者必须同读教学大纲和教材,依据同一份大纲和同一本教材处理各自事务。这中间要有了脱节问题的话,也就是脱开了大纲和教材。对此考方不会不懂。然而,事实并不会这么简单。由于主考、主教双方处于背对背状态,加之认识和理解问题上的差异,很容易出现不一致的问题,用教考合一的惯常标准去衡量是不现实的,是容易混淆问题的性质的。这就是说,是脱节问题还是一般问题应予区别,分别对待为好。
教考分离,考试必然引人关注。对于考方来说,守住大纲这条线和教材这个圈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一份试题就是一门浓缩的学问,来不得任何马虎。在内容上,试题哪怕有一点超纲,实际影响的不仅是整个考试,因此而受到师生的责难,不论以无关大要辩解还是以脱节问题论之,考方都难辞其咎。
我以为教考双方只要在如何对待大纲的问题上高度一致,不论解决什么问题都能找到共同点,就能更好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3年来,注册视听生考了6次,就教考脱节问题,口头和文字都有议论,就是不见有翔实材料公诸于世,应当进行专门调查、研究、论证,补上这个缺口,并能去做沟通工作,单是嚷嚷于事无补。至于有人点到的试题题量大、覆盖面广的问题,那只反映了考方对试题的态度和及格与不及格区分度的掌握,是人家责权范围内的事,谁也左右不了,无须苛责。
教考分离对“教考合一”有否定的意思,最终要从成绩的差异上反映出来。
学生学得如何,以考试衡量,及格即合格。及格率在文凭热的持续期,学生敏感,舆论关注,及格率低难免有压力,影响所及可至各个方面,对“注册视听生”办学产生的影响更不可低估。
对“注册视听生”的学习,以教考分离的办法进行质量控制,对考试的要求当然非比一般,对及格率的影响同样非比一般。再看这个受教育的群体的自身状况的诸多缺陷,心中越应有数,越不可轻信高及格率。办学者的期望值应当打得低一些才对。这样主张,并不是说不要讲及格率,只是说应有所淡化。
教育的连续性,从一般情况看,不只要求前后衔接,而且要循序渐进。接受大专教育应有高中文化基础,在这之下,差得越远问题越大。“注册视听生”教育,打破常规招生办学,入学条件放得宽,学生基础差、能力低的问题比较突出,很难适应“不组班,以自学为主”的学习形式,要让只有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基础的学员都跟上教学要求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这两类学生所占比例恰恰较大。这都是明摆着的问题。
只要承认这个事实,就得承认是学生的哪些缺陷制约了“注册视听生”的及格率;只要这些因素继续存在就难以改变低及格率的现状,除非你那个地区改变了这些因素,才有望转变过来,才可能另当别论。
撇开这些制约因素谈及格率,难免局限了自己的眼光。在这种情况下,小则将及格率低的原因归咎于教考分离的种种失当,大则说什么“及格率低是改革试点的失败”,都是令人疑惑的。尤其是后者以及格率定成败,对开放学校来说是不是提得不对头;再说改革是艰难的事,不经曲折就想得到理想的结果,是否有些不现实;何况大专教育的质量标准上下左右基本是统一的,由不得谁去变通,主观条件不具备,何以读得上去。
这是招收“注册视听生”遇到的最大的一个现实问题。不过可以肯定,有些学生虽然条件不甚好,但经过检验,证实还有希望,不甘心被淘汰出局,要坚持读下来。对于他们不要强求一次合格,可以按照学分制给予的机会,有区别地加以对待。需要用时间补偿的就得补偿,一日千里、跳跃前进谈何容易。害怕学生掉队,过分看重一次性合格率,欲速则不达,有悖教育规律,能说不是性急了一些吗?
教考分离实行以来,就主考部门来说,对于高及格率实不以为然,甚至怀有疑问;这使许多人无法理解和接受。那么,对及格率提出一个数量范围,用作限制,对超出者予以过问,有没有道理,说通说不通。无须多言,比方说,及格率很高,经不起类比;得分集中,分布不合理,本身就说明没有多少可信度。因此对考试的真实性持有异议能说没有道理吗?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简单,正因为这样,目前的及格率控制还不到十分严格的程度,一些说法本身就带有模糊性,操作上也有一定的伸缩性,从未简单化、一刀切,应当说是考虑到具体情况的。
考试研究,将区分度专列一项。及格不及格大体比例是多少,是测算出来的,同主观判断是截然两回事,是可信的。主考部门依据这种测算法对及格率进行控制,那理由就充足了。
在缺少这个资料的情况下,就我们来说,看一个数字是否合适,也不应将这个数字孤立起来,不加比较。对“注册视听生”的及格率,纵向同历届考试相对照,横向可及非同类班级和地区。要做到这一步,时下遇到的问题多半好回答,好解决。
教考分离,在电大起步于招收“注册视听生”之时(1995年),准备工作不足,后续工作也未跟上。实践中反映出一些问题,有些问题不算小,比如有关材料不配套、“考试说明”下达滞后、考试大纲教学大纲不完全统一,说明基本建设欠缺,确实有碍于教考分离的正常进行,反映比较大,有关方面应当正视。我们相信,既然为“注册视听生”选择了教考分离这种形式,并坚持走下去,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有些人或许是对教考分离暴露出的问题解决不及时产生错觉,又有无可奈何之感,就对现行的教考分离予以否定,提出“在电大内部实行严格的教考分离”(见《内蒙古电大学刊》1997年第5 期《“注册视听生”试点工作初探》一文)。这种分离法仿佛只说了个头,思路便中断了。又过了一年还有这种说法(见《中国电大教育》1998年第1 期《“教”“考”分离之我见》一文),但对怎么分离的框架依然言之不详,让人难以了解,更谈不到深解。只从这点端倪看,就这“内部”二字不是让人想不透,就是让人想偏了。也就是说,分离沾上内部,就总使人有“分而不离”之虞。
现行的开放性大专学历教育,包括社会办学,实行“教考分离”呈现出明朗的走势,而且形式同一。据《上海教育报》报道,国家学历文凭考试的试点范围由3省市扩容到18省市,办学也是宽进严出、 教考分离;自学考试的助学班同考试完全脱离。由此可见电大“注册视听生”的教考分离跟它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这条路在目前来说至少是可行的,可信的,当然还需不断完善。
标签:教考分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