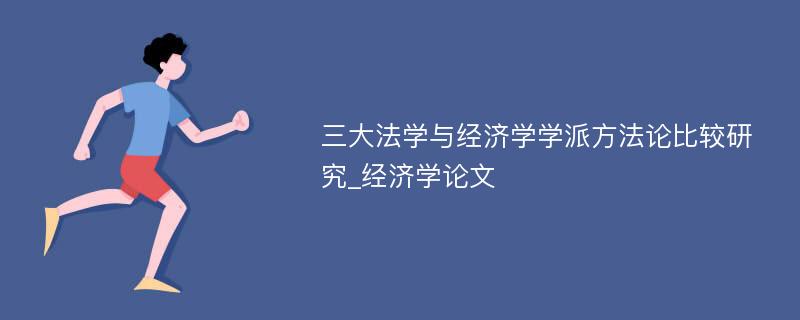
法律经济学三种流派方法论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三种论文,流派论文,经济学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1—0254—04
如果从20世纪初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的出现起算,法律经济学已经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促成了各种不同的法律经济学流派。在这些流派中,主要可以区分出三个比较大的分支,即以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法律经济学、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为代表的维吉尼亚学派公共选择—宪法经济学传统的法律经济学(简称宪法经济学)以及以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罗伯特·海尔(Robert Hale)、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等人为代表的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这三个流派在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结论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说却是源自于其研究方法论的不同。研究方法论是关于学术研究总体分析思路的抽象说明,重点在于解释说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哲学观念和基础认知,更多的反映了研究者预设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基本的学术立场。它与作为学术研究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方法”不同,后者一般包括了数学方法、历史方法、比较方法、试验方法、解释方法、思辨方法等所谓的“原方法”。① 而前者则包括了以下三个层面: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还是规范主义)和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研究方法论中包含了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最初也是最基本的价值预设,本文拟对法律经济学三个流派的方法论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三者在最基本层面上的差异。
一、研究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在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起着基础作用,是理论研究中最基本、最简单的质的规定。
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学和宪法经济学都将“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将社会中的个体假定为总是遵循理性选择的最大化原则做出自己的选择——作为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这种最初起源于经济学领域中的理论假设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最具逻辑连贯性的个体决策行为模式,并被誉为法律经济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关键性发展”。② 例如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导论中开篇就提到:“人在其生活目的、满足方面是一个理性最大化者——我们将称他为‘自利的’”,③ 他将这一点作为其所有法律经济学思想的起点和源泉。这一假设对于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法律经济学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20世纪末行为主义法律经济学对其进行理论挑战时,集中了全部精力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试图推翻理性选择的假设,虽然事实证明这种挑战并不成功,不过,在论战中,波斯纳对理性选择的认识似乎也走向了极端,他在将“理性选择”行为理解为选择“达成目的的适当方式”(suiting means to ends)的基础上,推导出“当理性被理解为以最小的成本达成个体的目的(比如老鼠的生存和繁殖)时,老鼠与人同样具有理性”。④ 宪法经济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布坎南在理论逻辑起点上采取了与波期纳同样的立场。在他的理论中,理性最大化者常常用更通俗的词汇——“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来表示,如布坎南在其确立宪法经济学基本思想的论文中明确指出,应该将理论研究建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经济人和作为交易的政治(politics-as-exchange)”三个基本假设之上。⑤ 事实上,布坎南之所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将经济学领域中的理性最大化假设引入到政治学领域并进而上升到宪法学领域,使人们注意到市场活动和政治活动产生的结果的不同,都来源于这两种领域内制度设置的结构不同,而不是来源于社会个体在这两个领域之间进行角色转换时,其理性最大化的本性发生了什么变化。
与上述流派相反,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公开排斥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这是因为它是美国旧制度经济学(the Old Institutionalism)的理论引入法学领域而形成的一个独特界域,旧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反叛者姿态出现,因此在其理论影响下形成的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排斥作为古典经济学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排斥理性选择理论的同时,制度主义经济学内部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研究范式或研究纲领。学者们在对理性选择模式批判的基础上。转而研究一些整体性概念(holist concepts),如“民族精神”(national spirit)、“社会心理动机”(socio-psychic motive)、“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等等,这些概念不但含糊而且相互之间并不统一,相比较主流经济学来说缺少确定性和说服力,无法为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方法论基础,⑥ 后者也因此一直无法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找到一个稳定的逻辑起点,从而也无法形成得以建立和开展学术研究的稳固的理论框架,显得形具神散。由此,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在法律经济学领域内一直被认为是“异议传统”(Dissenting Tradition),虽然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在美国诞生,并且一度非常鼎盛,形成了第一次法律经济学浪潮,⑦ 但却仅仅存在了一二十年就逐渐势微,近代的研究成果则更加稀少。
二、研究的哲学基础
学术研究总会受到不同哲学的影响,每种哲学都会在学术研究中的活动、态度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方面对什么是“恰当的”持不同观点,提出不同的处理办法,其中最主要的可以区分为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两种类型,⑧ 这种区分最初来源于大卫·休谟在《论人的本质》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由此在事实(fact)领域和价值(value)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形象的称为“休谟的铡刀”。⑨ 这种划分形成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研究和规范主义研究的区别,进而反映到应用经济学方法论的法律经济学研究中。
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更偏重于实证性研究,不过波斯纳法官对法律经济学规范性分析和实证性分析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一版中,波斯纳认为两者对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并且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规范性标准——财富最大化原则。但是几年之后他观点开始发生变化,1973年他指出:“规范分析大大地超过了实证分析作为法学领域的特征是非常普遍的,在我看来这是可叹的……对规范分析的偏好导致了我们关于法律体系的知识非常的贫瘠、不完整和不系统。”⑩ 于是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二版中,波斯纳虽然承认规范分析很重要,但是同时也指出解释法律体系中的规则和影响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实证分析更重要,并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实证性研究结论——普通法的效率理论,认为“效率”(efficiency)是型构普通法的规则、程序以及制度最主要的因素。这种普通法的效率理论事实上改变了1744年英国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在Omychund v.Barker(1744)案中确立的普通法本身纯粹的自我运行的观点,可谓是一场普通法理论的革命。波斯纳甚至还意图将财富最大化原则为基础的效率原则作为法律乃至整个社会的伦理和政治基础,虽然最后他自己承认了这种基础主义的失败。(11)
与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学相反,宪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规范性研究的面貌出现的。布坎南在其1960年的名著《同意的计算》中提出集体政治决策机制双层次结构划分:第一个层次是“普通政治”(ordinary politics),主要指在立法会议中通过多数决策机制形成政治决策的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宪政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指“普通政治”层次包含于其中运行的政治框架本身的决策层次。通过这种双层次的划分,《同意的计算》一书在作为公共选择学派开山之作的同时也隐含了公共选择理论体系内部的分层,即将公共选择理论分为实证的公共选择理论(positive public choice)和规范的公共选择理论,后者正是布坎南极力推崇的宪法经济学。在宪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关注与“理想的宪法”(optimal constitution)有关的规范性问题上,将宪法经济学理解为一种“旨在重新反思对联邦政府拥有的财政、货币和调整权力所进行的宪政限制”的智识活动,(12) 主要研究人们如何可以理想地控制那些他们在政府中的代理人。布坎南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化(legitimizing)问题上,研究集体选择的结果能够被称之为“公正”(fair)或“效率”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并提出了自己的契约主义的新宪政论。在这种新宪政论中,“同意”的概念被认为本身就隐含了“效率”与“公正”,因此具有最基本的规范性功能。在此基础上布坎南假设在人们面临普通政治层面的现实问题——比如如何分配社会财富、如何征税等——并作出政治决策之前达成了一个“先在”(ex ante)的“一致同意”,这种“先在”的“一致同意”即为宪法性的一般性规则,普通政治决策都是在这种“先在”的规则体系中做出的,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正是在这种“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获得了合法性。当然,虽然规范性研究在宪法经济学这一法律经济学流派中具有绝对主导地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实证性的宪法经济学研究也开始出现,这种研究主要分析“各个社会实际上是如何选择他们的宪法规则”以及“各种宪法规则不同的经济影响”,(13) 其研究仍然处于幼年时期,不过发展的前景却非常广阔。与上述两个流派不同,早期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强调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而得出规范性的结论。它主要研究经济体系自身事实上存在的强制力以及国家通过法律以及通过权力对其进行干涉的问题。学者们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表面之下发现了隐藏着的事实上的经济权力(实证性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经济权力的存在应该通过政府权力的干涉予以纠正与消除(规范性结论)。如罗伯特·海尔(Robert Hale)的研究显示,在自由市场中交易主体的“自由度”是和各个个体所拥有的交易的能力、支付的能力等因素密切相连的,所以强制性的压迫实际上是内在于任何交易的。拥有更多能量的经济主体可以强迫其他经济主体服从它所指定的交易条件,同时它也比其他经济主体更有可能拒绝别的主体开出的交易条件。(14) 卡尔·卢埃林(Karl Llewellyn)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分析“一边倒契约”(lopsided contract)——技能与权力几乎都倒向契约的其中一方的契约——时注意到“在这种契约中,从该交易对另一方生活的重要性的角度说,(掌握权力一方)等于就是通过私人法律(private law)在实施一种私人政府的权力”。(15) 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强制”(social control)的概念,认为“强制”的力量可以来源于经济生活中(私领域)的本身,而并非仅仅来自于公领域的政府。在这种实证性分析的基础上,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家们进而得出了规范性的建议,即主张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认为如果考虑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这些强制力量,那么一个政府即使在干预主义的体系下也能扮演最小政府的角色。相比之下,现代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者则明确主张实证分析,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和阿伦·施密特(Allan Schmid)在其著作的开篇即宣称:“我们的主要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希望知道在具有经济意义的法律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辨明发生作用的变量和基础的事实与过程……分析和预测各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制度设置所导致的效果的技巧的发展”。(16) 他们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关注点在于深入研究法律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发展,以便可以了解和分析这一过程中不同的制度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更偏重于实证主义的研究。
三、研究的学术认知立场
学术研究中的学术认知立场是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基本认知态度和立场,它可以区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类型。方法论个体主义坚持对任何社会相互作用过程的解释和理解都必须立足于对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之上,在这个解释和理解过程中任何的结论或者所作出的理论预测都应该被还原为个体选择,(17) 其核心主张在于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个体出发,认为“只有个体在选择,只有个体在行为”(only individuals choose;only individuals act)。方法论整体主义则主张个人行为应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演绎而来。(18) 因此,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核心主张在于认为整体优于个体,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整体出发。
在法律经济学三个主要的流派中,芝加哥学派和宪法经济学派都坚持了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如布坎南指出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经济学中所有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的研究前提。(19) 在他所创立的宪法经济学中,布坎南提出以“一致同意”为规范性基础的契约型宪法规则框架来论证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型构了契约主义的新宪政论体系。在这种新宪政论体系中,布坎南首先就强调价值的定义应该完全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并将其作为最重要的规范性前提。在这种规范性前提下,个体被认为是唯一的价值评定标准,并且个体的偏好对于他人来说是不可知的(inscrutability)。(20) 也就是说应该“完全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定位价值。个人是唯一的意识单位,一切价值评价都是以此为起点”。(21) 芝加哥学派的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法学。(22) 如波斯纳将自己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建立在三个基本的经济分析原理之上:市场经济的需求规律、市场主体的财富最大化倾向和市场交换的效率性。(23) 在这三个基本的经济分析原则中,市场经济的需求规律是建立在对个体主观偏好的假定之上,市场主体的财富最大化倾向是指个体对能以货币衡量的财富的最大化,市场交换的效率性也是从个体在市场交易的结果中所处的相对状态进行判断,均是立足于个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具有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
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则坚持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进路。如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拒绝了传统经济学中所坚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利益协调模式,对经济体系中集体行动与合作行为的角色给予了高度的关注,(24) 将分析重点放在现代经济体系内在的利益冲突之上。在他看来,个体的意志作用于文化环境并转而被相应的环境所形塑,因此康芒斯最关心的是最终将影响经济系统绩效的那些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化和运行。(25) 他的研究显示,当经济体系的变化对政治与法律体系造成影响时,就会产生沿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的法律体系的变化。而当法律体系发生变化时,它同样会影响着经济行为朝某一特定方向发展。现代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研究同样从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出发,倾向于研究法律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对于他来说“法律是经济的一个函数,且经济(尤其是它的结构)也是法律的一个函数……(法律和经济)是连带产生的,而不是孤立给定的,也不仅仅是相互影响的”。(26) 另一位现代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家施密特则继承了康芒斯的研究重点,倾向于分析结构(structure)和绩效(performance)之间密切的关系,致力于揭示不同法律结构所产生的相应的经济影响。他建构了一个特定的“结构—行为—效果”的模型,强调法律经济学的制度主义研究路径必须解决以下问题:法律规则(比如财产权规则)是如何建构人们之间的关系的?当利益发生冲突或要达成共同的目标时,它是如何影响结论的做出?它是如何影响经济体系的绩效?等等。这种分析强调结构和绩效之间的联系,注重从宏观上研究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反映了制度主义法律经济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研究路径。
注释:
① 郑永流:《法学方法仰或法律方法》,《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六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Arthur Leff,“Economic Analysis of Law:Some Realism About Nominalism”,Virginia Law Review,Vol.60,No.3(Mar,1974).
③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④ Richard Posner,“Rational Choice,Behavioral Economics,and the Law”,Stanford Law Review.1998(50).
⑤ James Buchanan,“The Constitutional of Economic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
⑥ Health Pearson,Origins of Law and Economics-The Economists' New Science of Law,1830—193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53.
⑦ Herbert Hovenkamp,“The First Great Law & Economics Movement”,Stanford Law Review,1998(42).
⑧ Herbert Hovenkamp,“The Economics of Legal History”,Minnesota Law Review,1983,pp.65—71.
⑨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34页。
⑩ Richard Pesner,“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Law”,Texas Law Review,1975(53).
(11) 苗金春:《语境与工具——解读实用主义法学的进路》,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
(12) Richard McKenzie.,“Introduction”,Richard McKenzie,Constitutional Economics-Containing the Economic Powers of Government,Lexington:Lexington Books,1984.
(13) Stefan Voigt,Explaining Constitutional Change:A Positive Economics Approach,Edward Elgar,1999(2).
(14) Robert Hale,“Law Making by Unofficial Minorities”,Columbia Law Review.1920(20).
(15) Karl Llewellyn,What Price Contract?-An Essay in Perspective.Yale Law Journal.1931(40).
(16) Warren Samuels & Allan Schmid,Law and Economics: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Martinus-Nijhoff Publishing,1989(1).
(17)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18)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
(19) James Buchanan,“The Domain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0(1).
(20) Geoffrey Brennan and Alan Hamlin,“Constitutionality Political Economy: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mo Economicu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1995(3).
(21) 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2)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23) 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4—19页。
(24) 约翰·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91—196页。
(25) 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吴晓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
(26) 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吴晓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