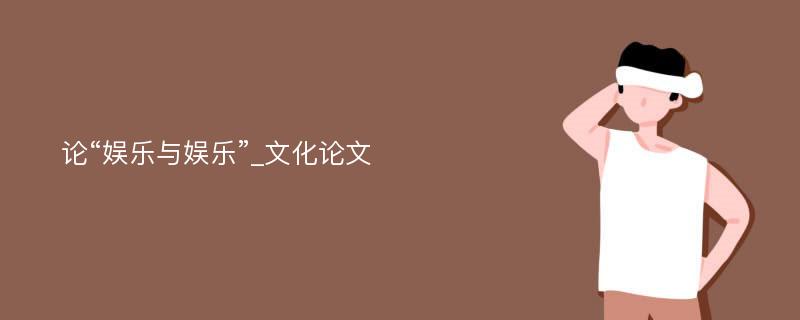
反“消闲娱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文学研究会”发起宣言(1920)
我的一些学富五车的师友,前些时在那里正襟危坐地讨论“文学艺术的消闲功能”,这场景看上去十分滑稽。因为与之对照的是另一场景:真正的消闲的大众此时正在玩麻将、下象棋、打台球、扭秧歌……,有几个专程到影院去看电影,到画廊去观画展,到音乐厅去听乐曲……?真正去的也多半不是为了去消闲;那么,还有一拨在那里制造“消闲作品”的“作家”、“艺术家”,说到底他们自己一点都不“消闲”,他们的动机也并不真的要使大众愉悦,而只是以此为手段去骗取大众的钱袋。两个场景一比较,我的那些个师友的“严肃”讨论,岂不显得滑稽?
这些学者们也许是想以此来引起大众的注意,并进而引导大众。其实,这多半是一厢情愿。消闲的人们,谁会有心思来听学者们的严肃话题?所以,只剩下学者们自己听,这岂不成了自说自语,有何意义?我当初也曾有过这种幻觉,可当我的著作的印数逐本减少时(第一本7550册,第二本5000册,第三本3500册,第四本1500册,而真读的肯定比这印数更少),我失望了,当然个人的遭遇不一定有代表性,但像我这样遭遇的著作者肯定不在少数。所以以此来换取大众的青睐并企图进而引导大众,恐怕终究是徒劳的,说不定倒会被俗世给同化了。多少迎合、迁就、媚俗的学者、知识分子及文艺家,被庸众所同化、吞噬、侵染!
但我们确实面对大众的消闲潮(虽然真拿文艺作品消闲的人并不太多),确实面对消闲作品的一浪高于一浪的热潮,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有所作为,而不能视而不见。问题是,我们应坦率地承认,我们几乎不能直接对大众施加影响,除非继续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那些制作消闲作品的“作家”、“艺术家”施加一定的影响,而还不要为他们所同化。那我们还能怎么办?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张扬我们的理想信念及“人文精神”什么的,唤起那些“作家”、“艺术家”们的良知,在理论上坚定地反“消闲娱乐”论!
这并非是感情冲动,而是基于文艺本身的事实和历史的规律。
(一)文艺的审美特性与消闲娱乐功能
文艺在一定情况下当然可以有消闲娱乐功能。其实何止文艺,政治甚至都可以用来消闲,战争甚至也可以用来消闲。美国影片《生存还是毁灭?》(又译《是死是活》)中的那位中尉飞行员,便以驾机作战为乐。王朔名著《玩的就是心跳》,连生命本身都可拿来消闲娱乐,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
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政治、战争和生命的本性就是消闲,文艺同样不能这么说。文艺的确有审美愉悦功能,具有审美本性,但这和“消闲娱乐”论者的“消闲娱乐”是有本质差别的,决不能混为一谈。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误和偏向,多半都与在文艺审美功能问题上的思想和观念的混乱有关。
文艺的审美功能,是诉诸人的心灵的。它具有感性的外观,也经由感性进入人的心灵。但它决不是纯感性的,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性,像盐溶于水一样渗透其中。连严羽都懂得“羚羊挂角”,严羽总不是文艺的功利论者吧?康德就更深解此中三味了,他将文艺看成是沟通感性和理性、联结此岸和彼岸的桥梁,康德也不是主张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论者呢?就是席勒、斯宾塞主张“游戏说”,也没有完全把文艺当做是消闲娱乐的,而是认为在游戏中达到心灵的超越、灵魂的升华。
而这与大众的“消闲娱乐”是多么的不同啊,简直是天壤之别!大众的消闲娱乐,是艰苦的工作之余的放松,是紧张的劳作之后的松驰,基本上是感性的消遣,甚至是官感的娱乐。这么说并无否定这种“消闲娱乐”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充分肯定这种消闲娱乐的积极意义。首先,从历史价值看,它是社会进步和环境宽松的表现;其次,它也充分表明了人获得自由解放的程度。虽然这么说的时候,我们要补充说,工作、劳作本身也并不总是异己的,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它们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和展现。它们和消闲娱乐的关系,是一张一驰的关系。工作、劳作可以异化,消闲、娱乐同样可能异化,否则怎会有“玩物丧志”的警告,一直伴随了我们几百年了呢?所以,既要看到消闲娱乐的积极意义,也别忘了它们的消极作用。而在今天大众的消闲娱乐中,有时消极面甚至大于积极面,所以要提倡健康的娱乐,不然,往往就滑向赌和嫖及相关的劣行上去了。
也许,可以用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来引导大众进行健康的娱乐。这想法不错,但会有两个问题。首先,文艺在消闲娱乐方面永远不及真正的消闲娱乐品,如麻将、台球、象棋、游戏机等等,真想去消闲娱乐的人们,很可能对你提供的贝多芬、梵高、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不屑一顾,或懒得去顾,你岂不成了对牛弹琴?这并非我们胡说,而是事实,否则就不会有严肃文艺的危机了。其次,为了真正让大众通过文艺去消闲娱乐,就不得不降格以求,制作具有文艺形式的消闲娱乐品,以投其所好。这就是“消闲文艺”。由此我们转入第二个问题。
(二)消闲文艺的品位与格调
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与消闲文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只是文艺的多种功能之一,并且如上所说,是偶尔的功能和某些人临时的用途,与文艺的审美本性很远有时甚至恰好相对。可是,为什么会单独派生出一种“消闲文艺”呢?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兵器是战争的工具,但市场上不也有消闲用的兵器么?商品经济就是这样,几乎可以将一切变成商品,甚至包括友情和亲情,何况文艺、兵器?而商品,除了实用的外,有相当一部分便是消闲娱乐品。“消闲文艺”与其说是文艺,不如说是徒有“文艺”外貌或形式的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最终又还原为商品。从没听说过“消闲文艺”的制作者们愿意像司马迁那样“藏诸名山,传诸后世”,或像曹雪芹那样“举家食粥”而不去换回几文钱,“消闲文艺”最本质的特点,与那具有审美本质的真正文艺有何共同之处?
“消闲文艺”当然还要有故事人物,或线条色彩,或乐句旋律等等,但这些也不同于真正的文艺,“消闲文艺”只是拿它们当素材或手段罢了。最关键的是要有“卖点”,而要有“卖点”就得唯时尚是瞻,就得迎合大众的趣味,就得迁就大众的选择。大众今天喜欢“西北风”,你最好不要唱粤语;明天又流行“东南风”,你就别再唱秦腔。“流行”就是“消闲文艺”的特色。若不流行,“消闲文艺”就会化为纸浆、废品、垃圾,不值一文。昔日的一些流行过的歌带、影带甚至视碟,现在不是在那里廉价处理还无人问津么?
我曾专门考察过大众文艺现象。当然,大众文艺绝不可等同于“消闲文艺”,但其中确有重叠部分。我发现,在所谓的“流行”中,其实也有不“流行”的东西,这就是:官能刺激,情绪煽动,节奏轻快,语言风趣,一方面在表层感染大众的视听感觉,另一方面在深层打动他们的内在欲望。而这欲望通常又与性和力有关,虽说常常经过了艺术的改装,但往往也只在打擦边球。我曾风趣地说,这些作品常有“脱”,但只“脱”到一定程度;常有“露”,但也只“露”到一定分寸。大部分“消闲文艺”不就是这样吗?当然也有逾矩的。于是在“消闲文艺”中,我们时常也能看到一些文化垃圾:诲淫诲盗,凶杀色情,“拳头枕头”,这些东西也并不罕见啊!
应当承认,“消闲文艺”中还是有品位不俗的,格调较高的,如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斯皮尔伯格的影片等等。但就是对这类作品也不宣评价过高,它们缺少个性和独特性,与贝多芬、伯格曼等仍无法相比,还是摆脱不了“消闲性”和“商品性”的胎记。何况像这样的“消闲文艺”在整个“消闲文艺”中仍是凤毛麟角,更多的仍是品位低俗、格调低下的东西。
我们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难道要认同这样的“消闲文艺”,或张扬文艺的消闲功能向这类“消闲文艺”靠拢?这未免太可怕了!如果说有那么一部分“作家”、“艺术家”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狠捞一把,还可以理解的话,因为中国向来有“堕落文人”的一脉传统,那么,学者和理论家们也来媚俗,便很可悲了。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去搞“消闲理论”或“消闲学术”,也就无从去捞一把,另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启蒙职责,他们也就彻底自我放逐自我流放了,最终真正为时代所抛弃。
当然,“消闲文艺”的某些方面,也还是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其平民意识、情感主体、轻快形式等等,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很有效的。有论者也看到了这一点,提出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与大众消闲文化“合谋”。不过,迄今我看到的不是大众文化对其敬而远之,就是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投降”。我倒是看到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合作比较成功,虽然双方都要做出让步甚至牺牲,但更多的时候是大众文化的臣服和被改造。这倒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三)现实的状况与历史的轮回?
许多人认为,“消闲文艺”的兴盛,或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的膨胀,是新形势下的产物。因此为之欢呼,为之歌唱,为之张目。其实不然,“消闲文艺”早已有之,追溯起来,可以到人类社会的早期。当然,今天的“消闲文艺”有今天的特点。
一个方面是今天人们的“闲暇”的确是多了。但是否多到闲得无聊还是太大的一个疑问,更不是普天之下都在悠闲自在。即便每周有了5、6个小时的闲暇,不去做家务,带孩子,哄老婆或丈夫,却还得去看望老人,探望朋友,或者自己上各种各样的进修班,或者带孩子上各式各样的课(从绘画到书法到钢琴等等,注意,这些虽是文艺,却一点也不“消闲”)。这是就个人而言,就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来看,这“闲暇”也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还远未到可以歌舞升平、放纵不羁的时候。大到宏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业,小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改善,一点也容不得我们彻底放松。多少人不是还像东坡那样感慨:“难得浮生半日闲!”
另一个方面是所谓“民间文化空间”的急剧增长。我的另一批强调“理性和启蒙”的师友在这一点上,竟和这批倡导“消闲与娱乐”的学者们不谋而合了。这所谓的“民间文化空间”如果不是心造的幻影的话,至少是对现实的误读。也许将来会有“民间文化空间”,目前何尝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还刚从计划经济社会中走出没几天啊!是有一批将要游离出计划体制的人,但在法制社会没有成熟之前,没有一个人现在已彻底摆脱了计划体制的阴影。讨论这个问题的学者以及作家,谁是真正的“自由民”?姑且同意已有这么一个“民间文化空间”,但同样有两个问题。一是这所谓的“民间文化空间”在什么意义上是铁板一块?“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就算真的已沦落民间了,也与普通市民、与村民乡农完全不同,哪来的一个“民间文化空间”?二是有些“民间”色彩的东西,多半又与“黑社会”、“流氓、地痞”有关,这哪谈得上是“文化”空间?
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消闲文化”的兴盛,那问题简直就更严重了。幸好不是这么回事。但在历史上,倒的确有过与“民间文化空间”、与大众的闲暇密切相关的“消闲文艺”。远的不说,就说现代中国史吧。清末明初,20年代和40年代,都曾涌现过“消闲文艺”浪潮。而每一次,也都有正直的文人予以猛烈的抨击。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当初都对其所含的封建毒素和落后意识进行过深刻分析和尖锐批评,“文学研究会”更将与对它们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旗子。难道历史真的又转回来了么?而若真转回来,为什么鲁迅、茅盾、瞿秋白等批判者却没有转回来呢,一些人反而倒对“消闲文艺”唱起了赞歌?
即使真的历史重现,“消闲文艺”也决不会像有的论者说的那样,经过时间的沉淀,就会升格为经典。真正成为经典的,当初只是沦落民间罢了,它们本身是真正的艺术品,并不纯是娱宾遣兴的。而真正娱宾遣兴的,除了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存留下来外,很少不被历史淘汰。别只看到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存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可知道,还有更多的“休闲”作品早被历史的尘埃遮掩了。《花间词》除了很少一些研究者了解外,还有几人知?(其实其中也还仍有不少艺术成就较高的篇什)有史以来最高产的“诗人”乾隆,他那些游戏应酬之作又还有几人晓?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我前段时间研究电影,电影这方面就更说明问题了。今天的一些“娱乐片”,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也曾有过,甚至连片名都一样。当初的那些影片已消逝在历史尘埃中了,今天的这些会在21世纪成为艺术经典吗?连这些影片的编导自己都不会信!
有时候我常想,今天看来亟需继续搞清一些基本问题。否则,一遇社会变化,特别是今天面临的市场经济大潮,往往就让我们一些人把最基本的东西都丢掉了。文艺的商品属性问题是如此,文艺的消闲娱乐功能问题是如此,“消闲文艺”、“大众文艺”及“商业文化”问题,等等,也均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严肃的学者专家们也不妨探讨一下这类问题。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试图以此去说服、引导大众,可以说“门儿也没有”。看看我们能否以我们坚定的信念,雄辨的理由,去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引导那些“大众的偶像”、“大众的情人”,别再去迁就、迎合大众的趣味,或误导、利诱大众的心理,就阿弥陀佛了;若再能通过他们的觉悟和良知,引导大众,提高大众,则令我们喜出望外了!
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至少要走在正确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