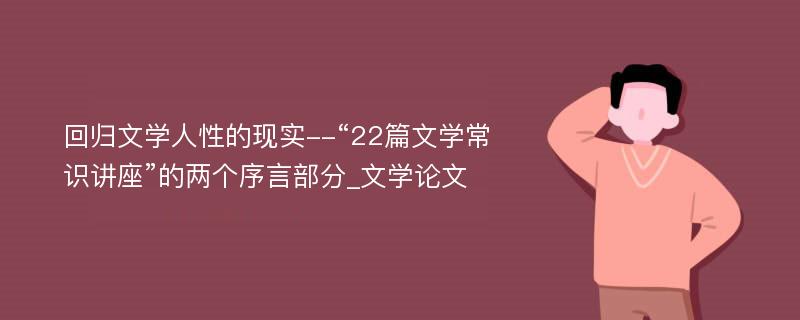
回归文学的人性真实——《文学常识二十二讲》自序二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自序论文,文学论文,二则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常识二十二讲》香港版自序 本书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课堂讲稿。讲述时我只写了提纲,在课堂里面对学生时,再作发挥。幸而有我的学生兼“助教”潘淑阳认真做了记录并及时整理出来,然后我再在整理好的稿子上作些修补与润色。 二○一三年九月至二○一四年一月,我受聘于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和高等研究院。五个月时间,我给选择理工专业的学生讲述了《文学常识》的头十二讲。二○一四年的秋天我再次来到科技大学,便继续把“文学的十大关系”讲完。讲述看似轻松,实际上是“以轻驭重”,仰仗的还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积累。三四十年里,日日夜夜想的全是文学,愈想愈深,愈有意思。这些思维成果本可以在国内好好表述一下,但国内没有我的平台,那就只能借助香港这个自由之所且思且说。尽管难以说得很充分,但毕竟把多年的所思所想作了一次认真的表述。 二○一二年我到科技大学之前,在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教育论语》(与剑梅的对话录)。书中,我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教育理念,这就是教育的第一目的并非提供学生的生存机能(即专业知识),而是提升学生的生命质量,即培育学生全面的优秀的人性(包括卓越的人格、高级的趣味及审美感觉力、判断力等)。理工学生所以也要读点文学、哲学、历史,就因为人文修养可以提高生命质量。我开设文学课,当然也遵循这一宗旨。所以我的讲述,不是重在文学知识,而是重在心灵升华。于是,我的讲义首先是高举心灵的火炬。而文学又恰恰是心灵的事业,我的讲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重心。 《教育论语》还表述了另一个教育理念。我认为,专业教育的基本导向,不是引导学生去竞争专业的“分数”而是点燃学生对本专业浓厚的兴趣。有了兴趣,课程结束后学生还会主动去自学,去钻研。在人生的漫长岁月里,决定一切的还是自学。我把分数压力视为校园里的机器专制。惟有让学生从分数的负累中解脱出来,并从内心深处爱上文学专业,课程才算得上成功。基于这一想法,我的文学讲述便尽可能激发学生对文学的热爱。我记得年轻的思想者刘瑜说过:“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这句话不管是什么人说的,都可算是至理嘉言。我觉得文学课也应当让学生愈来愈单纯。课程固然可以增加他们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文学面对的人性与人类的生存处境是非常丰富复杂的,惟有呈现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才能把握住文学的本性。然而,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本身则应当是非常单纯的。我常说,应当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努力纯化自己,也是这个意思。惟有守持单纯的本真角色,才可能走向文学的高处与深处。一个被世间各种世俗功利所纠缠的作家,很难真正理解文学,更难进入文学的内核。当然,也很难赢得从事文学专业的“至乐”。 “文学常识”课涉及“教育”的基本观念,当然更涉及文学的基本观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一直致力于打破文学领域中的“现代蒙昧”。这种蒙昧便是文学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迷信与顺从,即对各种“主义”的俯就和迎合。世界那么丰富复杂,人生那么广阔无边,人性那么纷繁多彩,文学面对这一切,自然也可以展示自己的一番风采神韵,完全不必去纳入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狭隘框架,无论是来自左方的框架,还是来自右方的框架。自由也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惟有对于自由有了觉悟,才有真自由,完全不必等待自由的客观条件成熟之后才进行创造。文学顺从政治是一种蒙昧,文学企图干预政治,也是一种蒙昧。作家惟一的正确选择是独立不移,自立不同,是返回文学那种“有感而发”,即心灵需要的初衷。我的文学常识讲述,倘若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对现代蒙昧的彻底告别,不再拖泥带水。明白人读后一定也会感到一种“明澈”的痛快。 本书的书名沿用课程的名目,依然叫作“文学常识”。我曾把“识”分为五种,自下而上分别为“常识”、“知识”、“见识”、“睿识”(也可称为“灼识”)、“天识”。我的讲述只属于“常识”与“知识”这两种层面,当然也尽可能掺进一点自己的见识。但说不上睿识与天识。当下世界,谈论文学的书籍文章不少,有的讲得太玄太离谱,例如说“主体死了”,“语言才是文学本体”等等,面对种种高头讲章,回归常识与回归文学的初衷,倒是一种出路。 本书从第一讲开始就在《明报月刊》的副册(“明月”)上刊载,现在已刊登到第十四讲。刊登数讲后,香港三联副总编侯明兄就以其慧眼,认可“常识”,并郑重向我约稿。现在书稿已整理完毕,我自然也就先交给他了,也借此机会感谢他的支持。此外,我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张艳玲小姐,她一次又一次地校阅。没有她,这部书籍不可能这么快就进入社会。当然,我还得感谢“小潘”,因为她的努力,我的言语和思想才能这么快地化为文字与书籍。 二○一五年一月十九日 香港 清水湾 《文学常识》北京版自序 三十年前,我写作的《性格组合论》与《论文学主体性》等,历史针对性很强,即动笔的目的性很强。当时针对的是从苏联那里拿来的“反映论”、“典型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念。文学本来是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也可以塑造典型人物,但是,一旦设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前提,再谈“反映”,就不是真反映了,其典型也不是真典型了。基于此,我不得不以“主体论”这一哲学基点去更替“反映论”,也不得不用“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去打破“典型”名义下的各种假面具。三十年过去了,我现在谈论《文学常识》,则完全没有历史针对性和“目的性”。既不针对外,也不针对内,无论是前苏联的《文学理论》,还是被我国文学界延伸的《文学概论》,或者是欧美正在流行的“现代性”新教条,我都不再刻意去论争,更不去作颠覆性的批评。对于现在的我,“不争”不仅是一种“德”,(《道德经》中讲“不争之德”),而且是一种“方式”,即不以争辩为出发点的建设性方式。所以,《文学常识》只是正面讲述,即只讲“什么是文学”和“我期待什么样的文学”等等。 这种状况,也可以说,三十年前我谈文学,是“主动出击”,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却是“被动讲述”。所谓“被动”,是说,如果不是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所“逼”,我是不会讲述的。二○一二年剑梅从美国马里兰大学移向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我到香港探亲,也顺其自然地接受科技大学的聘请。按照大学的制度逻辑,我必须讲一门课。想了想,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我把自己三十多年来关于文学的思考(关于文学的基本理念)讲一讲。不必刻意去寻找资料,也不必刻意去构筑体系,对文学怎么认识就怎么讲。我不喜欢“倾向性文学”,不喜欢“意识形态化文学”,不喜欢“谴责文学”、“暴露文学”、“讴歌文学”、“隐私文学”、“黑幕文学”,甚至不喜欢娘娘腔的“抒情文学”和爷爷腔的“革命文学”。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可以坦率地表述一下,这也是一种快乐。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我的文学观就大体形成,这套文学理念包括确认文学的天性乃是真实性与超越性,而非倾向性与阶级性;文学的基本要素是心灵、想象力和审美形式,而非“现实”、战斗力和意识形态转达形式;文学既不可以成为谋生手段,也不可以成为匕首与投枪(武器);作家诗人要保持自己的“本真角色”,就不应当去从政或从商;不得不从政的时候,也应当超越世俗角色,而守持独立不倚的文学自性与创作个性;文学天生具有导引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伦理态度,但不是道德法庭;文学无须为政治服务,也无须政治为文学服务。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事业,它实际上是自由心灵的一种审美存在形式。即使书写历史,也是心灵化的历史。因此,凡是不能切入心灵的作品都不是一流作品。我所指的心灵,不仅是情感,而且是思想。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放弃思想。相反,我特别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文学不是哲学,但它又可以“充分哲学”,这个中的原因就是文学可以蕴含丰富而真切的思想,甚至可以具有巨大的思想深度。我在《文学常识》的整个讲座中,有意以轻驭重,尽可能排除过去强加给文学的负累,把文学的功能只界定为“见证真实的人性”和“见证真实的人类生存环境”。并不像前人所讲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那么伟大,也不像近代启蒙家所说的“没有新小说就没有新国家新社会新国民”那么沉重。然而,真的要实现人性见证与环境见证也不容易,因为,作家诗人必须面对极其丰富和极其复杂的人的存在,这一存在并非哲学家描述的那种抽象的存在,也不是超人、天使、魔鬼这种神奇而简单的存在,而是千变万化的活人,即具体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思有想的生命存在。文学与哲学就从这里得到区分。杰出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其哲学明明在场,但又不是哲学著作,原因就在于此。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一百多年来,我国关于文学有过无数的争论,但今天悬搁争论,返回文学的初衷,只是面对最为丰富的人性和人类生存处境,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唯一的出发点,反而透彻明白。这也正是我讲述《文学常识》所要立的“心”和所要立的“论”。 因为在香港科技大学,我面对的是理工科学生,而且多数是本科生。他(她)们对于科学比对于文学更为熟悉。所以我的讲述不可深奥,不可过于“理论化”与“哲学化”。面对这些侧耳倾听的年轻学子,我只能选择讲述“常识”,尽可能深入浅出,尽可能化繁为简,尽可能为他(她)们打开方便之门。所以整部著作可读性较强。这可能是与中国国内的一般文学理论教科书最大不同的地方。 临末,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兼“助教”潘淑阳小姐,她把我的讲述加以录音然后及时整理出来,之后我再加以润色。我在十几年前曾在另一所大学讲述“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流亡文学”、“中国的讴歌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等课程,可惜缺乏一个像“小潘”这样的有心人与勤奋者帮我整理出来,结果讲后便风消云散,有点可惜。《文学常识》曾在香港《明报月刊》连载,首先在香港产生影响,这要感谢潘耀明兄。仅连载了七八讲,香港三联副总编侯明兄就慧眼独到,向我约了书稿,并在今年五月就把《文学常识》推向社会(书名《什么是文学》),这又要感谢侯明兄和责任编辑张艳玲小姐。《文学常识》还有一层幸运,去年秋天,东方出版社的王艳小姐和前华夏出版社总编、我的好友张宏儒及夫人贾达黎到香港来看望我,知道我有《文学常识》书稿,就与东方出版社总编彭哲兄联系,立即决定由他们推出北京版,因此,《文学常识》便一路顺风,从南到北无阻无隔。在此我自然得郑重地感谢这些真诚的朋友们和为此书承担全部打印工作、默默支持我事业的表弟叶鸿基先生。 二○一五年六月七日 美国 科罗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