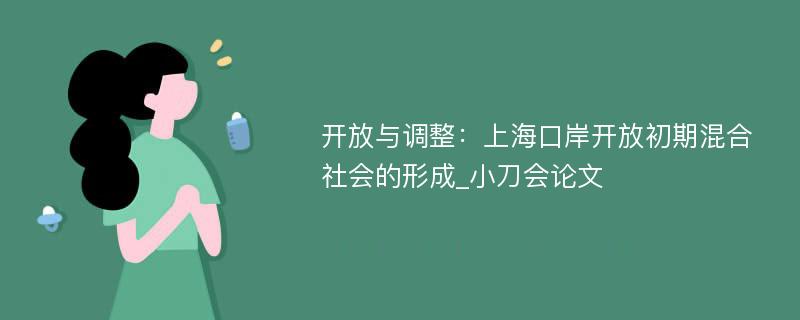
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初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特别是租界建立以后,逐渐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演变为对外开放的城市。小刀会起义以后,租界由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杂处,上海城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由一个独立城市变成一市三治。此后,租界与华界文化相互影响,利益相互交叉。到1869年(注:本文下限定在1869年,因为这年会审公廨正式成立,标志着上海混杂型社会基本定型。),上海成为一种混杂型社会。
所谓混杂型,要素有三:一是中西管理权限交叉,对于英美租界,西人、华人权力均不充分;二是中西利益交叉,华人在租界,西人在华界,均有一定利益,这两种利益有冲突,也有重叠,乃至在对抗太平军方面,租界西人与上海官绅形成统一战线;三是法律混合,会审公廨同时适用中西不同法律,遇到矛盾时就协商、妥协。
一、两种开放:开辟通商口岸和华洋混处
上海在1843年开辟为通商口岸,1845年设立英租界,以后相继设立法租界、美租界。按照《上海土地章程》。三租界开始时均为西人居留地,实行华洋分处原则,华人可以到租界里进行买卖交易,但不得入内租地、造房、租房、居住(仆佣除外)。
华洋分处的原则,并不是按照事先预定的某一条约或某种模式确定的。《南京条约》对于通商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只称“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对于如何居留并无规定。1843年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对此作了一些解释。第七款写道:
在《万年和约》内言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惟房屋之增减,视乎商人之多寡,而商人之多寡视乎贸易之衰旺,难以预定额数。(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页。)
这个附约也没有规定华洋分处的形式。据研究,上海租界华洋分处的原则,主要是上海道台的主张。宫慕久在隔离政策背后的理由,既是担忧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会玷污他所坚信的儒家规范,也是为了有效地控制外国人,而这一想法的源头则是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制度(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在华洋分处格局下,上海租界洋行持续增加,1843年有怡和、宝顺等5家,1847年为24家,1852年发展到41家。上海对外贸易额迅速上升,1852年以后超过广州,名列全国榜首。但是,租界社会发展并不快,人口增加幅度不大。1843年,英租界统计在册的外侨人口为25人,1850年,上海所有外侨为210人,其中法租界约10人。在此格局下,英租界因人少事简,与市政有关的机构,是所谓的道路码头委员会,由三名租地人组成,负责评估租地人的地产价格,确定征收建筑和维修道路、桥梁所需税款,募集建造码头的费用,如此而已。
如果这种格局一直维持下去,那么,上海租界就会如同广州沙面那样,范围不大,市面冷清,影响有限(注:广州沙面租界一直实行华洋分居,不允许华人进入,更不准华人居住。因此,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沙面租界的外侨人口不超过2000人,加上为外侨服务的中国职员、工人、佣人约4000人,实际居住人数不超过6000人。由于人口稀少,租界显得相当空旷。这就使得沙面租界实际上成了一个纯粹、小型、自我封闭的外侨居住区。其中除了19个外国领事馆和外商机构外,只有一个工部局、巡捕房,以及为数不多的教堂、生活服务设施等。租界没有商业街,没有工业区,文化、教育、传媒机构也很罕见。见乐正:《近代上海的崛起和广东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然而事情在1854年发生变化。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爆发,小刀会占领县城,清廷加以镇压,上海战火不断,大批华人涌入租界(注:见梅朋、傅立德著,倪静兰译:《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135页。)。对此,英国领事、租界当局起初都持反对态度,因为这样做既不符合有关章程规定,给租界管理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难民乱搭棚屋,有的就在黄浦滩、洋泾浜岸上搭建住所,这对市政管理、城市卫生,都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外国商人欢迎这样的局面,因为,这么一来,商业繁荣,房地产生意也大有可为了。几个月时间里,租界里便已造成华人居住的房屋800所。
人口的大量增加,华洋由分居变杂居,使得租界社会管理问题一下子复杂起来,先前的《上海土地章程》也显得名滞实后、不敷运用了。
1854年7月5日,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领事爱棠,宣布修改后的《上海土地章程》。7月11日,三国领事召开租地人大会,通过了这一章程,即《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按照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上海土地章程》的修改,应由英国管事官与上海地方官会同酌定,然而这次章程的修改,却是由外国公使、领事单方面草拟、在西人会议上通过,然后才移文上海道台核明办理。当时的上海地方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道台吴健彰正忙于镇压小刀会起义,除了照办别无选择。
比起1845年的土地章程,1854年章程在章程适用范围、租地范围、租地办法等方面都有修改,其中,对于日后混杂型社会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点:
其一,对于华人的规定。第八款规定,洋房附近,不准华人起造房屋、草棚,以免火灾。第九款规定,禁止华人用篷、竹、木等易燃之物起造房屋,不许存储硝磺、火药等易于着火之物,违者罚银25元。起造房屋时,木料、砖瓦等物不得阻碍道路,妨碍行人。禁止堆积秽物,任沟洫满流,放枪炮,放辔骑马赶车,并往来溜马、肆意喧嚷滋闹,违者罚银10元。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华人进入租界,已经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华洋杂处已被认可。与此相一致,先前关于中华洋分居的规定在章程中不见了。
其二,设立工部局以管理市政。《章程》英文本第十款规定,选派三名或多名组成委员会,经收税饷,所收款项,用来起造、修整道路、码头、沟渠、桥梁,装置路灯,清洁道路。这个机构,就是工部局。
其三,设置巡捕以维持治安。第十款规定,设派更夫或巡捕以维持治安。在先前的章程中,仅有设置更夫的规定,其职责只不过是夜间巡逻、报更、鸣警,而巡捕则是武装警察。这次章程通过以后不久,工部局就建立了巡捕房。捕房制定了服务规则17条,管辖范围相当广泛,除了警务,还有道路的整洁与燃灯,有碍公众的事物的取缔,以及搜查军器的输入和解除华人武装,协助征税,筑路,都在其内。
对于工部局的性质,在7月11日通过《上海土地章程》的会议上,英国领事阿礼国有过具体的说明。他说,这一机关应有的各种权力,包括对于租界内外侨生命和财产的保护,一切为了保持租界居民健康、维持租界清洁、组织警察、开发并管理税收所必需的规程和办法(注:《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1932年中译本,第36—37页。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8页。)。阿礼国等人从道理上原本懂得,在租界设立市政机关,是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任何法律原理所不容许的,但是,他们就是要在不合法的大前提下,尽量做得好像合法些,于是,就有了租地人会议等形式。
这样,租地人会议(后来演变为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巡捕,加上在1853年为了对抗太平军而成立的义勇队(日后演变为万国商团),租界就由先前的居留地演变为具有立法、行政、警察、武装的政治实体。
华洋杂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既不是出于租界当局的原意,也不是上海地方政府所乐意见到的。在华洋杂处的开始阶段,上海地方政府还试图继续管辖租界华人。1853年11月,吴健彰曾致函阿礼国,要求英国领事馆编造一个名册,载明在领事馆及租界商业机构的译员、买办和仆佣等人的姓名、年龄、住址等情况,以便将来查考,结果遭到拒绝。1855年2月24日,清政府恢复对上海县城统治之下以后,上海道又公布《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对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作了许多规定。内称:
凡华民在界内租地、赁房,如该房地外国人之业,则由该业户禀明领事官;系华民之业,则由该业户禀明地方官,将租户姓名、年、籍、作何生理、欲造何等房屋、作何应用、共住几人、是何姓名,均皆注明,绘图呈验。如地方官及领事官查视其人无碍,准其居住,该住户即出具甘结,将同居各人姓名、年、籍填写木牌,悬挂门内,随时禀报地方官查核,遵照新定章程,并按例纳税。倘若漏报,初次罚银五十元,后再漏报,将凭据追缴,不准居住。该住户若系殷实正派之人,即自行具结,否则别请殷实之人两名代具保结。(注:《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3页。)
上海道台所争,实际是对租界华人管辖权的问题。租界当局对此不予合作,上海道台也无法执行登记、具结等规定。
上述两种开放,第一种开放,即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是上海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关键;第二种开放,即租界向华人开放,由华洋分处变成华洋混处,是上海由普通沿海城市变成特大城市的基础。第一种开放是第二种开放的基础,第二种开放对于晚清上海政治、社会的发展,影响更为深刻。众所周知,近代上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与租界的繁荣、租界的特殊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租界人口主体部分是华人。如果没有华洋杂居,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后来的上海。
第一种开放与第二种开放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知道,华洋混处的直接导火线是小刀会起义,而小刀会起义的发生,与上海开埠以后人口结构、官员结构发生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开埠以前,上海本有不少外地商人,主要来自山东、山西、江西,浙江的宁波、绍兴,安徽的徽州、宁国,福建的泉州、漳州、汀州、建宁,广东的潮州等。开埠以后,客商更多,有不少人在上海定居下来,其中,广东籍、福建籍最多。至1853年,上海据说有广东人8万,福建人5万。其时,上海县城人口总共20多万,粤、闽等客籍占了一半。粤、闽、浙濒海之人,每多恃勇好斗、愍不畏死之辈,这些人来到上海,给上海民风、社会秩序带来新的问题:
上邑濒海要疆,莠良错处。闽广之徒,有睚眦怨辄械斗,虽戕人勿论,盖旷悍慓疾,其习常然也。(注: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35页。)
历史很有趣。小刀会起义首领刘丽川和上海道台吴健彰都是广东人,都是在上海开埠以后,由广东北上上海的,两人也相识。上海道台吴健彰的上台与活动,与上海开埠以后官员结构变化很有关系。吴本为广州十三行之一同顺行的行商,以捐纳而为候补道员,早在1842年便来到上海。他从宫慕久担任上海道台开始,便事实上成为上海地方政府办理外交的参谋。宫慕久曾以他为助手,咸龄去职、麟桂到任以前,他还代理过一段道台。上海开埠以后的第一任道台宫慕久,并没有什么外交经历,在职四年,处理外交事务还算平和得体。其继任者咸龄、麟桂,均为满人,都有一些外交经验,在处理外事方面,均“墨守广东经验”,不明西方情形和近代外交特点,不是以理服人,而是注重个人关系,都被证明是无能的外交官员(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44、50页。)。1848年青浦事件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很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知道外国情况、容易打交道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合适人选。吴健彰是上海第一个由商人、买办而担任道台的人。可以说,没有上海开埠,就没有吴健彰这段仕宦生涯。
吴健彰做上海道台,其政策是为广东商人买办服务的,广东商人买办在承揽业务、走私贩毒、偷税漏税方面的便宜沾了不少:
鸦片战争后,有一批广东和福建的商人、买办、语言学者来到上海,他们被相似的生活习惯、相似的社会风俗、相似的语言和经济目的维系在一起,吴健彰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领袖和政治代表。(注: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44、50页。)
道台衙门里所有下层工作,包括书役、差役,都由广东人充任。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40名广东人为警卫。
小刀会起义很快取得成功,与刘丽川在吴健彰周围的广东人当中策反有关。刘丽川于1849年来上海,贩糖,为丝茶栈伙,来沪以前就参加了天地会。他利用同乡关系,将吴健彰身边的警卫都发展为小刀会会员。起义一爆发,衙门上下都变成头裹红巾的小刀会成员。起义军冲进道署时,吴健彰还蒙在鼓里,下令开炮,左右随从都推说不会。
小刀会起义提前爆发,也与吴健彰左右随员通风报信有关。小刀会原定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发动起义。这时,隐蔽在吴健彰身边的小刀会成员报告,道署中藏有40多万两银子,近期将被运走。为了这笔巨款,小刀会决定将起义提前。9月3日(八月初一),吴健彰到天后宫进香,小刀会拟在途中袭击,后因吴加强了防卫而未下手。9月7日(农历八月初五),县城内的文庙照例要举行祭祀孔子的大典,小刀会借着这个机会发动了起义。可以认为,假如吴健彰身边没有小刀会的暗探,则小刀会起义将是另外一番情景。
二、华洋关系:抗争与合作
上海开埠以后,华洋关系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协商、合作的一面,从总体上说,还是比较和谐的。
以开辟通商口岸而言,在第一批通商的五个城市中,上海开埠最为顺利,宁波其次,最为复杂的是广州。
在上海,尽管1848年发生了青浦教案,但那是在上海近郊土地上发生的传教士与山东水手的冲突,上海外侨并不认为那是与上海当地居民的冲突。上海外侨在圈建跑马场时,与土地主人发生一些矛盾,外侨认为那是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挑拨离间的结果,不能把责任推到上海人身上,“界内界外所发生的一些纠纷,大多是福建帮和广东帮所引起的。我们没有发现过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53、753、752页。)。小刀会起义期间,1854年4月,上海也曾经发生清军与西人武装的“泥城之战”,但那仅是为时两小时的军事摩擦,很快就平息下去。从总体上说,开埠以后的20多年中,上海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与西人相处都还是比较和谐的。西方人对上海也感觉颇好。英国领事、传教士不止一次说到:
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大部分居留在上海的外侨,对古代吴国的历史,是幸运地一无所知的,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吴国人民(上海人)和南越国人民(广东人)是截然不同的。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53、753、752页。)
1848年,英国领事认为,“一般上海本地人与外侨之间业已形成一种融洽无间的谅解”(注:《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第753、753、752页。)。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满意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各项条约规定的外国人不得超越短程距离远入内地乡村,应由地方官和各领事协议决定一节,在上海是作最广义解释的;在英国领事的倡议下,游历的范围规定为游历者可以在一天内往返的路程,这就可以远达运河交叉处的乡村。在以后几年中,游历的范围约定为三十英里的距离。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在上海,虽然是一个外夷,但是在他的每天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进健康的散步,并不会对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么危害,并且他还可以带着枪和他的“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里捉一只雉鸡,或十分钟内捉一只鹬鸟。传教士不像在广州时那样要自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向中国兄弟宣讲福音;在1855年我们发现香港和其他五个口岸总数八十五名基督教传教士中,三十四名是在上海的。这种传教的自由同官吏和该县人民都建立了很大的友情;这种友情就是在叛乱和秩序失常的年月中还是一直维持的。(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401页。)
上海地方政府在治安、市政建设方面,还与租界当局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首先,资助租界巡捕费用。1854年10月17日,通过协商,议定巡捕费由上海地方政府负担三分之一(注: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的开辟和早期工部局职能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1855年1月4日工部局鉴于经费透支,决议请求领袖领事立即向中国政府索取他们已答应支付承付的每月500元津贴,用于维持到1月12日为止为期6个月的工部局捕房经费。随后,上海道台如期支付了经费,包括捕房津贴3000元,另加加强租界防御力量的经费1000元(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578、627、590页。)。1856年,上海道台补助租界巡捕房费用5500元(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1861年10月,工部局与上海道台就建立虹口捕房问题达成协议,道台愿意就此捐献一笔款项,数额与已从该区居民所收得的金额相等(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578、627、590页。)。1863年,上海道同意每年给租界4000至5000两津贴,作为资助巡捕的费用。之所以要资助巡捕经费,因为在上海道台看来,维护租界地区的治安,上海地方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在租界华人税收方面进行合作。1854年工部局成立以后,鉴于租界内华商使用租界码头,决定对其征收码头捐,每家每年征收50元,实行不久,因遭到华商和上海道台的反对而停征。租界当局多次向上海道台交涉,1857年上海道台同意每年统一捐钱给工部局,抵充租界内华人的码头捐,1858年定为2000元,以后不断增加,1863年为4000元,1864年6000元,1865年8000元,1866年10000万,1867年增加到14000元(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杭州,江南震动,迁居上海租界的华人增加到30万,两年后增加到50万(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为了筹措军饷,上海道台与租界磋商,要求对租界内华人征收各种货物税,遭到拒绝。英美租界同意,中国政府放弃对英美租界华人征税,将租界内华人房捐的一半让给上海地方政府。同年,上海道台与法租界议定,从7月1日起,法租界内华人税收全部归法租界,但要将增加的房捐收入与上海道台对分(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上海道台之所以要代租界内华人缴纳码头捐,因为在他看来,租界无权向中国商人征收捐税。至于军饷与房捐的交易,那虽然是权宜之计,但其潜台词是上海地方政府依然有向租界华人征收捐税的权利。
其三,联合禁止赌场。1864、1865年,上海道台与两租界在禁止开设赌场问题上进行合作,共同禁止在上海开设赌场。赌场多开设在租界,租界的行政费用,很大一块来自赌场,同治初年每月达五千两。1864年春,署上海道应宝时与英国领事、租界当局商量联合禁止赌场,没能完全达成协议。同年夏天丁日昌接任上海道台以后,经与外国领事、两租界当局一再磋商,英美租界态度比较积极,法租界一开始不予合作,到1865年,终于达成联合禁止赌场的协议。
其四,联合进行洋泾浜疏浚和造桥工程。洋泾浜是英美租界与法租界的界河,也是租界西面华界地区通往黄浦江的一条重要河流,由于倾倒垃圾,河泥淤塞,航道不畅。1864年,工部局开始制订疏浚洋泾浜的计划,翌年,工部局与道台联系,希望获得支持,道台慨然允诺。1866年,道台允支疏浚工程总经费4000两银子的一半,即2000两。工部局计划在洋泾浜与黄浦江交汇处建造一座新桥,道台亦允支其经费的一半。工部局在洋泾浜的山东路、福建路、江西路口造桥或修桥,道台均分担了费用(注:马长林:《上海公共租界的开辟和早期工部局职能考察》,《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
此外,1856年英租界扩建外滩30—40英尺,上海道台资助了一笔钱(注:《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578、627、590页。)。1866年,英美租界、法租界共同办理消防事务,上海地方政府也予以资助,费用由租界、保险公司、中外商家、上海道台共同承担(注: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324、368、368、335页。)。
1860年代,华界与租界最大的合作,是成立中外会防局,联合抵抗太平军。
自租界实行华洋杂处以后,华人便成为租界居民的主体,华人绅商在租界的利益日见加大。至于租界的洋商,其商业伙伴本来就多为华商,彼此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此外,租界西人与华界有多方面的联系,单传教士在华界所设的教堂便有多座,诸如南门外有法国传教士的董家渡天主堂,县城里有英美两国不同差会的教堂六座。基于在上海城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租界西人与华人官僚绅商结成了反对太平军的同盟。
1860年5月,正当太平军准备进攻上海之时,英、法两国公使在上海联合发出公告,表示决心以武力保卫整个上海,“上海城区亦在保护之列”,上海道台吴煦则将此公告四处张帖。英法联军千余人布防在上海各处,包括县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大门。华尔组织的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是外国出人、出武器,上海官绅吴煦、杨坊等出钱。1862年1月,外国殖民主义者和上海官绅联合成立中外会防局,正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太平军,英法等国驻沪领事、驻沪军队司令、上海道台、著名绅商等均参与其事,乃至合署议事。
在上海历史上,外国殖民主义者与华人绅商联合反对或抵制战乱,比较重要的有三次,这是第一次,另外两次是1900年中外东南互保事件与1924—1925年反对北洋军阀的齐卢之战。
三、混合法庭:会审公廨
关于会审公廨,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里要特别论述的有三点。
第一,会审公廨的产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1853年以前,上海租界司法状态是华洋分理。按照不平等条约下的领事裁判权,凡外国侨民与中国人之间的案件,如遇该国侨民为被告,应交该国领事按其本国法律处理。凡该国侨民相互之间的案件,中国官厅不必过问。根据这些规定,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立了领事法庭,受理各种以本国侨民为被告的民刑案件,至于租界内以华人为被告的案子仍交华官处理。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也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章程》第8条载:倘有租主逾期不交地租,领事官应按本国欠租律例处理。第12条载:倘有赌棍、醉汉、乞丐进行扰乱并伤害洋商,领事官知照地方官员,依法判处,以资儆诫。1853年华洋混处以后,鉴于中国地方政府无暇顾及租界内的司法,外国领事和租界当局遂自动担负起界内的司法管理。在英、美租界,华人的违警案件和民刑案件概由英、美领事受理。其中,除将案情十分重大的移送华官外,余皆由领事审结,在界内处以拘役等刑。1854年工部局成立后,决定各董事依其姓氏的第一字母为序,每周轮值,审讯巡捕拘捕之人,并在听诉后决定将其释放或移送领署。1855年,仅英领署审结的案件就达500余起。这是演变的第一步。
1855年以后,随着小刀会起义的失败和清朝上海地方政权的恢复,外国领事一度将对华人审判权力移交给中国政府。但是,英国领事和租界当局对于上海地方官的司法状况相当不满,据说:
所有由工部局巡捕在外国租界(法租界除外)内拘捕的案犯,每天常有20起,均被带到英领或美领处,然后由他们交捕头解送邻近城里的中国地方官厅。由于证人没有到场和准备华文材料之困难,有相当一部分案子虽然起诉书写得很详细,但在中国地方官面前,诉讼往往徒有虚名。据报,在许多案件中,罪犯稍事拘留即行释放,而且复回租界,窃盗犯罪如故。(注: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p.46.)
这种司法方式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绝大部分案子中,县城里的地方官仍仅仅停留于指控,除非犯人自己坦白或强迫使之招供,实无其他方法据以定罪。于是,相当一部分罪犯在过了几天难受的监禁生活以后就逍遥法外了,而一个清白无故的人却常常因待审而长期被拘押。(注:A.M.Kotenev: Shanghai: 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 p.46.)
上海地方政府的司法状况,直接影响到租界的治安。鉴此,1863年,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在与上海道台黄芳订立的美租界划界章程中,首先剥夺了中国官员在美租界的逮捕权和对无约国人民的管辖权。同年12月,以英、美为首的各国驻沪领事联名致函上海道台黄芳,要求代表中国官厅将管辖公共租界内无约国人民的权力授与工部局。其理由是上海地方政府对于无领事代表之外人“既不愿行使职权,又鲜他法加以取缔,此类危险分子实有制定取缔条例之必要。”黄芳为了省事,居然复函同意,表示“无领事代表之外人与大众杂交,同用外国语言,本官厅实无从辨别管理。来函请由贵领事等代表本国授权与工部局,取缔此类外民,同时由贵领加以监督,以免贻误等情,尚觉妥善。”(注: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36页。)这是演变的第二步。
1864年5月1日,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主审官为上海道台委派的理事。首任理事为陈宝渠,首任陪审官为英国副领事阿查立。这个衙门每晨在英领署开庭。最初仅受理公共租界内的华人违警案件与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以及以无约国人民为被告的刑事案件。至于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初由领事与华官文件往来办理,到1864年10月,始与以无约国人民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同归该衙门审理。其中,华人违警案件一般由工部局捕房拘解,理事单独审断,而民刑案件则均须有外国陪审官陪审。由于理事官职低微,凡民事案件,道台另委海防同知于下午开庭主审,平均每周2次。上述案件如有上诉,均由道台受理;如其有涉及外人利益者,则由领事陪审。凡平时审案中有外国陪审官与中国审判官意见相左而无法审断者,也作上诉案件处理。这是演变的第三步。
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运行几年,因为中西法律制度差异,在理事与陪审官之间屡生矛盾,终因是否实行来自西方的苦役制度而激化。经过谈判,1869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式成立,廨址设在南京路。
第二,会审公廨是上海地方政府设在租界的法庭。根据《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组织办法及管辖权限如下:
会审公廨由上海道选派同知一员主持。廨内应用通事、翻译、书差人等均由该谳员雇用,并酌雇外人一两名,为办理无约国人犯罪案件之用。公廨所需经费按月赴道台处具领。
受理租界内以华人或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其中,凡民事案件,公廨可以提讯定断“钱债与交易各事”,刑事案件则限于“发落枷杖以下罪名”。军流徒罪以上案件均由上海县审断。倘有命案,亦归上海县相验。凡公廨受理的涉及外人的案件,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所派之人会审。受雇于外人的华人涉讼,领事或领事所派之人可以到堂听讼,倘案中并不牵涉外人,即不得干涉。无约国人与华人的互控案件,由中国谳员自行审断,但仍应邀一外国官员陪审。如无约国人犯罪,则由中国谳员拟定罪名,详报上海道核定,并与一有约国领事会商酌办。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案件,领事不得干涉。
租界内的中国人犯,由谳员派差径提,不用巡捕。唯为外人服役的华人,应先通知该管领事,由其传令到案。凡为领事服役的华人,须经领事同意方能拿捕。凡华洋互控案件,包括华人与无约国人的诉讼,倘有不服谳员所断者,可向上海道及领事官上诉。
由此可见,会审公廨是中国政府设在租界的、审理以华人或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事案件和小的刑事案件、权力不充分的司法机构。
第三,会审公廨适用的中西两种法律。在会审公廨,中国谳员依据的是中国法律,外国领事依据的是西方法律。两种法律混用在同一个法庭上,矛盾自然会经常发生,这个时候采取的办法就是协商和妥协。比如,对于笞杖这一中国传统刑罚,会审公廨在外国陪审官的影响下,使用就比较谨慎,从1878年4月1日到1880年7月31日的28个月中,仅在47个案件中责打人犯。会审公廨还变通枷号的办法,减轻木枷重量,将示众地点选在可避风雨之处,并允许受刑者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早饭后再重新枷号。这些都是在矛盾中变通、调适的结果。会审公廨规定适用西方律师辩护制度,无论民事、刑事案件,华人都可以聘请律师辩护。
在公共租界设立会审公廨的同时,法租界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法租界于1865年决定,当界内华人与法国人之间发生商务纠纷时,就召请上海道台来领署会审。
中国政府通过会审公廨,保留了在租界里一定范围的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权;西方殖民主义者则通过会审公廨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把未享有领事裁判特权的无约国人也纳入了外国领事的保护范围,将租界内为外人服役和非为外人服役的华人区别开来,事实上将为外人服役的华人变成治外法权的保护对象。
由独立审判到会审、由理事衙门到会审公廨,从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上海租界的司法制度,是随着上海社会变迁、政治变动而不断衍化的,是在复杂的矛盾中谈判、妥协的结果,也是中西文化混合的产物。
上海开埠以后混杂型社会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因缘际会的结果。如前所述,华洋分处变为华洋混处不是条约的规定,也不是西方殖民主义者预设的结果。这个变化的发生,有难民涌入的因素,有上海地方政权瘫痪的因素,也有西商图利的因素。对于工部局之在租界行使行政权,英国政府本不同意。1862年9月8日,英国公使卜鲁斯曾训令上海领事麦华陀,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同意英国商人在上海租界的侵权行为(注: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0页。)。对于租界华人的管辖,租界与上海地方政府权力交叉,租界西人与华界官绅在历史特定时刻利益的一致性,会审公廨的设立,中西法律的混合使用,也有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混杂型社会的形成,主要是谈判、协商的结果,华洋杂处是协商的结果,越界筑路、巡捕费用、华人税收、会审公廨,也都是协商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