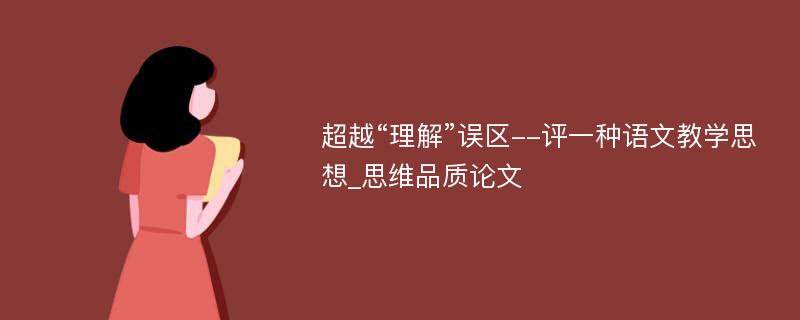
超越「悟」的误区——评一种语文教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学论文,误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悟”及以“悟”为核心的教学思想在语文教学中日渐流行起来。该思想提倡者们企图以“悟”作为突破某些建立在抽象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语文教学模式的武器,赁借它并通过它,达到语文教学“教为不教”“无法是为至法”的境界。由于他们高举人文的旗帜,而“悟”的精神确实包含有对教与学的主体人格力量的张扬(这正是长期以来中国语文教学所缺少的),因而使得这种思想极富人情味和影响力。这一思想的产生有其必然性。清理它的历史渊源有助于我们对其本质的探讨,所以不妨多说几句。以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不谐调,终于使人们惊讶的发现,自己所创造的物质世界逐渐将自己甩开,或者已经或正在变成可怕的异己的势力。十九世纪中期人本主义(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西方人开始对此作出妥协。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始终沿着这条否定理性、强调直觉、撇开事物本质、注重感性研究的路子发展着,而且越走越远。
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有一大优点,就是始终将人的研究与社会联系起来。但它和马克思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有本质的区别,它几乎总是强调牺牲人以适应社会。为了解决或逃避这种“个体与类”的矛盾,中国人从老庄开始就形成了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自己的内心,突出个体对自然对社会的感受的能动性。但因为这种思想以逃避现实矛盾为主要倾向,这就注定了其消极性因素,终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佛教合流。哲学意义上的以“悟”为特色的认识方法也便宣告诞生。
毋庸讳言,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社会,多少有与稳步发展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共通的地方。发展到相当阶段的西方社会突发的对“直觉”对“感性”的狂热,恰好给商品经济刚刚起步但已飞速向前的中国社会敲了警钟,而事实上,现代西方人热衷的那些反理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不难找到伙伴。许多中国人因此陡增了强烈的自豪感与信心,并开始对传统文化中诸如“悟”类的思想肃然起敬来了。这种态度当然会在语文教学思想里有所反映。
语文教学中“悟”的思想产生的“内因”是语文教改劳而功微的现状以及存在的方法论流弊。这种现状的症结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论弊端里面无疑有大量是受抽象唯物主义哲学甚至还有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而存在的东西,其特征是形而上学与蔑视情感。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看来最为便捷的办法就是请出既有悠久的历史而又时兴的、注重“人”本身的“悟”的思想了。
“悟”能否完成其提倡者们所赋予它的使命呢?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必须首先搞清楚“悟”的思想的一般特点与实质。
在语文教学中,“悟”的思想体现出来的特征大致而言有三点:整体性,非规则性与主体自觉性。整体性原则主张“文”“道”合一,既不能将语言所蕴含的人的精神因素以及所体现的对物质世界的规律的研究抽象出来剔除出去,而作纯客观纯逻辑的“语言”解析,也不可无视具体语言所揭示的具体的“道”的内容,而作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道”的灌输。而且,语言的学习只存在因语言材料不同或角度不同而呈现的不同的“悟”,不存在对某一语言的一点一点一层一层的接受,也就是说“悟”只有“顿悟”而无“渐悟”。既无解析语言之说,解析语言的规则与模式也就变得无足轻重,这就是“悟”的非规则性原则,它强调语言学习的多角度切入与化出,注重“契机”与“火候”,鄙视僵化的招式与系统主体自觉性原则是“悟”的思想中很有特色也是最为基础的原则。既然语言是“文”“道”统一体,离开人的主观意识的语言根本不存在,那么,对语言的学习就不可能是对语言的机械的操作,而是对语言的整体的把握。而这种把握,在他们看来,心的体验亦即“悟”乃是最佳的办法。因此,教学中老师对语言的把握应该是饱和情感的,其目的则是为学生的同样的把握创设氛围,“悟”的思想的上述特征无疑充满许多有价值的合理内核,它也必然会极大的冲击语文教学思想中存在的机械的而非生命的、形而上学的而非辩证的方法论。
可见“悟”的思想相当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两个功能:其一是警醒人们重视语文教学中的“人”;其二是冲击现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但是,除了“警醒”与“冲击”而外,恐怕也再难有所建树了。关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们先对语文教学的工具、对象和载体──语言作一番了解后,再予说明。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这是一个似乎古老但却通俗的比喻,它主要向我们提示了三点。第一,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而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统一的,可见语言与存在也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这就告诉我们,通过语言是可以认识和掌握存在(自然、社会、思维本身以及它们的内部的相互的本质规律等)的。第二,由于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是能动的而不是镜子似的机械的反映,而且被反映的存在本身就包括具体的人及其独特的精神等等,另外,思维在物化为语言的过程中同样会渗透思维者的个性与风格,因此,语言是有着主观色彩的。不过,语言是主观的,但存在是客观的,把握存在的出发点与归属是主观的,但其过程却必须“远离”作为主体的“人”(虽然必须随时观照它),这就正如一个农人要赡养在家的老母必须“远离”她而下地耕耘一样。它表明认识存在、掌握真理的艰苦性。学生对语言的学习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有其必然的艰苦性。忽视这一点,而作美妙的、人本主义的幻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认识语言的主观性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第三,对思维的认识是通过且仅通过语言而获得的,而思维与其物质外壳──语言,虽然呈现同一性,却不是同一个东西,语言有其独立性,有它的特殊规律。有了第一点:语言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性,知识与思想的传播、继承才成为可能,各门科学也才成为可能;有了第二点:语言的主观性,语言(主要指文艺性作品及主观色彩较强烈的语言材料)才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它的审美意义思想意义才得以显现;有了第三点:语言对存在对思维的独立性,才使得语言的研究成为可能,我们的语文教学也才成为可能。
语文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其根本的依托则是语言对存在对思维的独立性。它是语文工具性的基础。掌握语言这门工具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虽然正如上述分析表明的,语言自身有它的认识的、审美的、教育的价值等等,语言的独立性,是与它的这些价值统——体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语文这门学科以掌握语言工具为其教学根本目的的特殊性。换言之,语文教学中,接受其它各门学科的知识,进行审美教育与思想教育等,是从属于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的。因此,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关键就是探索掌握语言这门工具的规律,具体的说就是探索阅读与写作的规律,即:探索阅读与写作教材的编纂的规律,阅读者与写作者接受与创造的规律,以及更为重要的阅读与写作行为本身的规律等等(这的确是老生常谈,但不如此不足以正本清源)。不论这种探索呈现什么样的局面,是步履维艰还是一帆风顺,作为这种探索的理论基础与指导原则都必须是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注定这种探索是一条从感性到理性不断超越不断发展的曲折道路,而不存在某种包揽所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渲染气氛,激活兴趣,强化主体自觉性等等,也只能是达到目的的辅助手段,既不能代替这种艰难的探索,也不可能使这种探索一蹴而就。
显而易见,“悟”的语文教学思想存在根本的局限性。现试作分析。
尽管“悟”这种与灵感相类似的心理现象时常活跃在审美、艺术创造以及其它一些偏重创造性的思维过程中,但它的意义是与知性的理性的认识相随而且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没有理性的认识为其基础的“悟”只能是初始的、浅层的甚至无由产生或者趋于神秘与宗教。“悟”的境界无论多么高远多么神奇,却终究是为科学的理性认识服务的,否则,人们的认识就不可能往更深处发展而趋向真理的认识。然而,“悟”的提倡者往往将“悟”“理”对立起来,重“悟”轻“理”或者扬“悟”以抑“理”,在语言学习与审美判断之间简单的划上等号,以对自由的幻想掩饰甚或代替对必然的艰苦探究。这必然导致认识的停滞或蒙昧化,滑向主观主义和信仰主义。也有人将形象思维搬来,垫在“悟”的脚下,想以此为“悟”构建宏伟的宫殿。殊不知形象思维也得遵循思维的原则,而且和抽象思维一样属于理性的范畴!那些花花绿绿的形象,天才的灵感,看似纯粹自由的想象,只有在理性认识的大厦上方才显示出可贵的品质。
理性认识本身确实始终是人的本质力量所支配的,但是这种力量也只能是伴随这一过程而显现的。“悟”的思想在认识语言客体的过程中对主体人格的强调时常以理性的丧失或被漠视为前提和代价,因而必然是肤浅的更是脆弱的。
语文教学中,“悟”的思想难以避免的倾向是:无标准、无序列、不可操作与不可深化。以“意会”为主要形式的“悟”要求它特别珍视每个个体对语言感受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所以,几乎不可能对这种感受提出明确的目的标准。一种庸俗辩证法会对每一个个体的千差万别的而且有时是相互对立的感受体验都给予肯定。无标准即导致教学无意识与随意性。又因为“悟”讲究整体性,敌视理性分析与训练序列化,所以,知识的积累与技能的培养十分困难。教学保持在固定的层面上变换花样,多角度的切入与化出因其摈弃“破”的辨证思想而不得其所,终究不能“披文”以深入到语言的内部里去。不言而喻,缺乏序列,不可操作,在写作教学中则更是寸步难行。
结论是,以强化主体自觉性为其鲜明特色的“悟”的语文教学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冲击现行语文教学思想中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始终提醒我们切实关注作为教学主体的“人”──语言的“人”,教与学的“人”等等。但是,“悟”的思想只有胶着在科学的理性认识的支柱上才能显示它的生命力。只有理性,不过不是孤独的,而是有“悟”的精神胶着其上的科学的理性,才能引导我们进步,引导我们超越“悟”的误区,继续人类合目的合规律的语言探索与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