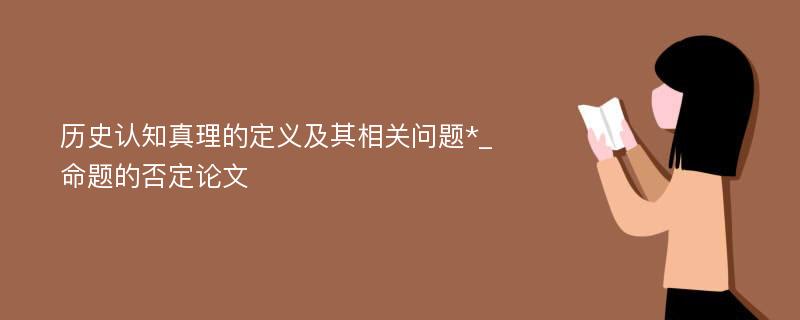
历史认识真理的界定及其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及其相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沪版《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上刊出的赵吉惠先生《科学主义、 教条主义对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影响》一文(下文简称赵文),对历史认识真理的含义作了如下的阐述:“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我们可以说:符合实际的认识便是真理。过去我们一般也把这个真理标准应用于历史认识领域,认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便是历史认识的真理。但是,细致推敲起来,这是有问题的,谁能知道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所谓‘历史实际’,便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这个‘重构’的历史,是不是原来发生过的那个历史的样子呢?历史学家只能根据历史文献资料提供的信息,做出历史假设性的描述和根据历史假说所做的历史推断,而难以得出像自然科学真理那样经过确证的结论。因此,教条式地说历史真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这句话,就可能成为一句无法落实的空话。这个说法本身的方法论、认识论根源,就是把历史真理等同于自然科学真理,就是否认历史真理的特殊性,就是历史认识领域的科学主义、教条主义影响的表现。脱离主体的纯客观的作为史学家研究、追求的历史事实不存在,脱离主体的纯客观的作为史学家所探讨的历史真理也不存在。历史真理既是由人提出的,又是由人确认、由人验证的。因此,必须从历史认识的间接性、特殊性,认识主体经由史料中介与认识客体发生特殊关系中去考察历史真理问题。历史真理的确认和验证,既有史学家主体的参与,又有史料的确证与定位。……把这样的历史真理与其说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不如说成是经过可靠史料的验证,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更为科学”。赵文又特别指出“在这里‘历史实际’与‘历史真实’不是相同的概念,‘历史实际’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真实’则是有史料根据并能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所谓‘符合历史真理’的认识,既应有可靠的史料根据,又是反映历史的本体与本质的认识,其内容是真实的,因而也是科学的”。赵文从历史认识活动的特殊性来界定历史认识真理问题,似亦言之成理。然而,仔细推敲,仍有不少问题。比如,“历史实际”,通常是指客观的历史事实,它的既往给我们对它的认识带来许多困难,以致我们常常感叹“谁能知道这早已过去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感叹历史认识往往难以证实。但是,事实总是事实,认识总是认识,怎么可以说历史认识活动中的“历史实际”就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呢?如果把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称为“历史实际”,那么那个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又该称作什么呢?又如,按赵文的说法,历史实际早已过去,谁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所以,历史认识与历史实际的符合关系的检验是无法落实的。然而,赵文提出的历史重构与历史本体的反映关系又如何证实呢?凭什么说某一个历史重构反映了历史本体,某一个历史重构没有反映历史本体呢?如果是以史料为根据,那么历史认识真理能不能说是一种有史料依据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呢?历史重构就是历史认识,历史本体就是历史实际,为什么可以称反映历史本体,不能称符合历史实际?既然历史认识与历史实际的符合关系的检验无法落实,那么历史重构与历史本体的反映关系的证实是不是也是一句无法落实的空话呢?再如,在哲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对符合说真理的批评由来已久。自康德以来,不少哲学家针对符合说真理的具体环节及其有效性的验证等问题提出过挑战〔1〕。 其主要困难是:检验认识,不得不涉及事实,而人们只能在观念之中涉及事实。如此,要将认识与那个未被观念涉及的独立的事实比较验证又如何能实现呢?赵文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只是肯定自然科学的真理可以用符合说。于是,符合说能否运用,主要取决于事实是否是既有的。对象是既有的,可以用符合说;对象是既往的,不能用符合说。可是,事实总有一定的时空定位,今日的当下的事实到明日就成了既往的事实,那么有关这一事实的认识,能不能说它只是今日的当下的符合,到了明日,事实过去了,无法验证了,我们就不能仍然说它是符合事实实际了呢?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细致的分析。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曾认为,有关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及其真实性问题,是“批判的历史学中最为重要而又最令人困惑”〔2〕的问题。笔者不敢奢望能解决这一难题, 只是在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一些讨论的线索,提出若干个人思索的心得,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广泛的讨论。
二、对符合真理论的二点诘难
符合真理论是一种历史最悠久的真理论,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必相符合〔3〕,被称之为关于真理的古典定义,在古代、近代一直颇为盛行。 符合真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在认识与事物的关系上来界定真假问题,但在符合的具体环节、有效性的验证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受到了自康德以来的许多学者的批评和诘难。
首先,符合真理论把认识与事实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照相式的符合关系,看作是照片和底片的关系。这种看法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意像、想象,确有照相式的符合情景。但是,一旦进入到知识领域,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就无法用照相式的符合来描述了。哲学家詹姆士批评说:对于可感觉的事物的真实观念的确是摹拟这些事物的,可是像对于钟的机件的观念就很难说是一个摹本了,至于说到钟的“计时功用”和发条的“弹性”等等, 那就更难看出观念所摹拟的是什么了〔4〕。这是符合真理论的一个不合理的地方。
其二,符合真理论对认识检验过程的理解过于简单。在他们看来,外在的事物在被用作检验证据后,仍能像它在未被用作证据时一样,以其纯粹的原貌参与对认识的检验。他们看不到事物在被用作证据时,它已经被渗入了若干检验者的主观因素。这种自然主义的理解最早受到康德的批评。康德认为,不论是真理,还是对真理的检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还有大脑思维的作用”〔5〕。 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说:符合真理论的“难点却一直也没得到澄清。……我们大家都倾向于设想,理论就是只存在于人们头脑里的东西;而事实则是摆在那里的,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它们。理论采取的形式是判断,是肯定的或否定的命题,或者(在技术性上更小一些)是说出来的、写下来的或者是蕴涵着的陈述;而事实则是据以做出陈述或总结出判断的材料。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乃是,我们是怎样获得那些我们的理论必须与之相符合的独立的事实的;而这却是一个一点也不容易给它找出答案来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想它的时候,我们的理论本身(它以实际的或可能的陈述的形式而存在)就要靠与别的陈述相参证而加以检验。……经验本身并不能用来检验理论,它们在能用之于那个目的之前,必须先被表述出来,被赋于概念的形式并被提高到判断的水平。但是在这一表述的过程中,我们所由以出发的那个实际经验就不可避免地是被改造过了。它是由于被人解说而被改造的,——它被带入了与以前同类经验的关系之中,并被归之于各种普遍概念之下。一种经验只有在这样加以解说时,才能被描述,并且只有它在被描述时,——或者至少是被具有它的人有意识地领会了的时候;——它才能用来核察一种理论。一种未经描述而单纯是被感受到的经验,是不可能在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陈述必须与之相符合的那些事实的那种意义上而为人知道的”〔6〕。也就是说, 符合真理论“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语言表达与语言之外的实在的对应情况进行检查,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谈到实在,而要谈到实在,我们必然已把自己语言所特有的某种概念系统强加给实在了。这样我们就仍然是在语言的界限内涉及实在。如此推论下去,那个把语言与未被概念化的实在进行客观比较的任务就像西西弗斯的不幸劳役一样永远不可能完成”〔7〕。
当然,上述问题对于一些机械的反映论者、历史学中的客观主义历史认识论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相信认识过程和检验过程中的主体因素是可以消除干净的,只要做到这一点,外在的事实就可以以它纯正的原貌来检证我们的认识。然而,认识过程和检验过程中的主体因素是不可能消除干净的。一些学者认为,命题与事实之间的符合关系的检验无法实现,因为命题与事实之间有一条不可渡的鸿沟。哲学家金岳霖对这派学者的鸿沟问题作了这样的概括:命题在我,事实在客;命题在内,事实在外。……大致说来,用得着符合说的时候,事实一定在外在客,如果它不在客在外,我们用不着符合说,……事实既非在客在外不可,符合说似乎不可能。如果事实在客在外,我们怎样知道它与命题符合与否呢?如果我们知道它,它又已经在内。真要坚持事实在外,则命题与事实之间有鸿沟一道,命题过不去,事实过不来,而我们老在命题这一岸。……符合本身既得不到,符合说当然说不通”〔8〕。
三、一种弱化的符合真理论
符合真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在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上来界定真假问题,一些学者看到命题与事实之间有着不可渡的鸿沟,符合与否无法验证,便放弃了符合真理论的立场。既然“求真于主客二者底合”不可能,“不如求真于主”〔9〕。 转而在实际效用上或命题与命题的关系上来讨论真理问题。前者强调真理的有效性,后来发展为工具真理论;后者强调命题间的融洽一致,后来形成了融贯真理论。有效性和融洽性都是真理的必要条件,这两种真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认识是关于事实的认识,检验它的真假而不与事实相联系,不考虑它与事实的关系,总是悖谬。而且,离开了客观实在来讨论真理问题,很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工具真理论和融贯真理论的实际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符合真理论虽有漏洞,但它的基本立场是合理的,不应该放弃。
要从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上界定真理问题,必须解决上文列出的两个问题。如上所述,照相式的符合只有在想象、意念之中才有,只能描述想象、意念与外在对象的符合关系,而不能描述知识与对象的符合关系。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采用对应式的符合说来替代照相式的符合说。如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写道:“符合是3命题和实在符合。 一命题与它所断定的实在符合就是一命题有它底相应的实在,而该命题底命题图案有和它一一相应的实在”〔10〕。符合的具体形式可以有多种多样,如地图与地域实际的符合,图书馆的目录卡片与它的藏书实际的符合等。“符合与否为真假底定义”,它的主要点是一一相应〔11〕。也有的把真理定义为“经人的认识过程形成的与其对象具有对象具有对应性统一关系的知识”〔12〕。
符合真理论把命题与事实的检验看得过于简单。仔细分解一下认识的检验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将事实转变为事实命题的环节。实践活动的主要功能是为我们的检验工作提供切实可靠的证据材料,从而避免了那种以某种权威言论、神灵启示、宗教教义等为标准的检验方式。但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证据材料本身并不会充当检验的仲裁人。一个是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物质性的东西,还必须把客观的事实转变为事实命题,即对客观事实作出一定的语言陈述,成为事实命题,才能和某一命题比较对照。在日常生活中,将客观的事实转变为事实命题这个环节是非常自然地进行的,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自觉地体会到它的存在,以致我们常常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东西的两相对照。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错觉)推及到知识领域的检验问题上,就会产生一种对认识检验问题的简单化理解。
外在的事实只有被理解、被描述后,才能用来同其他认识比较对照,而理解、描述的过程又不可避免地会渗入一些检验者的主观因素,这是无可否认的。指出并强调这一问题,是康德以来许多学者们的贡献。但因此而认为认识与事实的符合检验无法实现或放弃符合真理论的基本立场,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知道,认识是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它的实现是以整个物质世界的相互作用以及与这种相互作用相伴随的信息的传递、接收、保存等过程为基础的。在发生相互作用的两个物质系统中,物质系统甲会在物质系统乙中留下“痕迹”或“印记”。这种“痕迹”或“印记”同物质系统甲的作用的方面具有同构性,因而是物质系统甲的某些特征、特性在物质系统乙中的再现,也就是物质系统乙以自身的某些对应的回答性变化把物质系统甲的某些特征、特性的复制或再现〔13〕。人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也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在认识过程中,外在的事物及其状况以信息的方式为我们接受,经过思维的加工整理而转变成我们观念的内容。真不仅表示认识与对象的符合一致,而且具体地表示它具有与对象符合一致的客观的内容〔14〕。一个认识是不是真,取决于它是不是具有了来自客体的客观性内容;一个认识是不是比另一个认识更真,取决于它是不是具有了更多的客观性内容。认识的客观性的内容以及各种认识所具有的客观性内容的程度差异都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判明。如日常生活中的看一看、尝一尝。要检验杯子是否是圆的,应该看一看;要检验苹果是不是是甜的,应该尝一尝。在看与尝的过程中,主体就与客体发生了实际的信息交流,就可以获得有关客体的真实情况,就可以用来与原有的观念比较对照。虽然我们只能在观念中谈论事实,但观念中的事实并不是主观的事实;为了把握事实,我们不得不使用语言、概念,不得不进行描述、解说,但是语言、概念只是观念的形式,观念还有内容。观念获得了来自客体的客观性内容,就意味着“有经验之内的客观的事实”〔15〕,将它与我们原有的观念比较对照,就体现了认识与事实的符合检验。当然,这只是一种弱化的检验,像传统的符合真理论所设想的那种将事实原封不动地搬进观念或“骑”在事实与命题之间将两者相互比较的符合检验是无法实现的。在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传递、加工整理的过程中,在检验比较的过程中,都会渗入一些检验者的主观的因素,从而使得证据所给予的支持或反驳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16〕。
总之,需要放弃的是传统符合论的那种理想式的检验方式,而不是它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反对符合真理论的,实际上也不自觉地在采用了符合真理论的立场,因为他们也在进行着这种认识与事实的弱化检验。沃尔什说,“一种未经描述而单纯是被感受到的经验,是不可能在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陈述必须与之相符合的那些事实的那种意义上而为人知道的。”“一种经验只有在这样加以解说时,才能被描述;并且只有它在被描叙时,——或者至少是被具有它的人有意识地领会了的时候,——它才能用来核察一种理论”〔17〕。这里所说的“能”和“不能”的判断又是依据了什么呢?这又何尝不是将认识与事实实际比较之后所得到的判断呢?可见,认识与事实的符合与否的检验是可以实现的,传统的符合真理论只有经过弱化的处理才能成立〔18〕。
四、关于历史认识真理的特殊性
与一般认识活动相比,历史认识活动更复杂些,历史认识真假的检验也更为困难。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曾专门分析符合论是否适用于历史学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中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有着一种可以重建起它的基础,但却没有办法能面对面地观察它。他说:“我们必须试图着不是要在我们所掌握的大量坚实过硬的过去事实之中,而是更为模糊地要在历史证据的给定成分之中,去寻求历史知识的基础,正如我曾试图表明的,记忆使得我们接触到过去,但并不给我们一幅对它的直接景观。因此,我们所能要求的一切,就只是有一个与过去事件的接触点,使我们能够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猜测到它们的真实形象;但又并非是以这两者进行比较,看出它们正确到什么地步,从而能够检验我们的重建工作”〔19〕。历史认识对象的非直观性给历史真理的检验带来了许多困难。既然对象是不能为我们直接观察的,认识与事实的符合与否的检验又如何落实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历史真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呢?这就是赵文提出的问题。赵文认为,自然科学的真理可以用符合说,历史认识真理就不能说是符合历史实际,它只是假设性的描述或推断。并把这一点看作是历史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真理的特殊性。
按赵文的区分,自然科学的真理与历史学的真理的不同特点主要来自证实上的直接性和间接性。我们知道,认识真假的检验,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对象是现有的存在并能为我们直接观察,是直接证实;对象是既往的、或虽是既有的但不能为我们直接观察,是间接证实。如果把经过直接证实的认识称为符合说上的真理,把只经过间接证实的认识称为假设或推断,那么,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历史学,都存在着这两种情况。
在自然科学中,有一些普遍性的命题是可以直接证实的,如“两个质量不等的小球从高处自由下落时将同时落地”这一命题就可以直接证实。有一些普遍性命题的对象虽然是现有的存在,但是它不能为我们直接观察,通常也只能进行间接的证实。如分子的热运动就无法直接证实,人们能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分子热运动的结果布朗运动,而分子的热运动的存在与否则是通过逻辑推理间接证实的。此外,自然科学中也有许多学科是专门研究特殊现象的,其认识结果只能作出间接证实。真正能够作出直接证实的只是自然科学中的部分普遍性命题。
历史学的情况更为复杂。
从狄尔泰、文德尔班起,相当多的学者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研究和描述个别事件的学科。他们认为,历史中只有特殊,个别的东西,没有普遍、一般的东西,所以历史学的工作只是对特殊、个别的东西的描述,并把这一点看作是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主要区别。如果我们同意上述说法,那么赵文所说的历史真理的特殊性就可以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特征。但是,在我们看来,历史中既有个别、特殊,又有普遍、一般的东西,历史学中既有对个别、特殊的描述,又有对普遍、一般的概括。一般性的历史认识,涉及的是历史运动中的某些通贯古今的普遍性现象。有关这类认识的检验,不仅可以通过既往史事作间接证实,也可以通过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现有的事实作直接证实〔20〕。如果一定要以直接证实的认识才能称为符合说上的真理,那么历史学中也有符合说上的真理。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只能作出间接证实的,主要集中在特殊和个别性的认识层次上,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哈斯丁斯战役发生在1066年”等。但是,个别、特殊的命题也并非都只能间接证实,如对古代历史的遗物、遗迹的认识与检验就是直接的。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历史信息记录、储存方法上的革新,越来越多的既往的事实通过摄影、录像、录音等手段,使我们能身临其境地考察它们。如本世纪初的一位银行家阿尔贝·卡恩把镜头对准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法国巴黎的一些繁华大街进行摄像,留下了一整套电影资料〔21〕。又如因“水门丑闻”而出名的美国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将他在白宫任职期间所收集的有关1969年至1973年白宫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包括轰炸柬埔寨、尼克松中国之行、斯皮罗·阿格纽辞职、“水门丑闻”等大量文字、磁带、照片,录像、录音材料以多媒体形式出版了一本《霍尔德曼日记:尼克松白宫内幕》〔22〕。这些历史信息的留存、使用,使得有关个别性的历史事实的认识和检验也可以直接进行了。
史学自诞生起,一直沿用了它古已有之的名称〔23〕,然而它的对象、内容、目的等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历史学是一门极为复杂的人文研究,它不仅要考实历史上的个别、特殊现象,还要概括历史上的普遍、一般的规律;不仅要探讨“历史是什么”的问题,更要解决历史的意义与价值问题。要对这样一种复杂多样的认识活动作出一个普遍有效的概括是有困难的。笔者同意赵轶峰先生的说法,即通过史料中介去复原原本客体的认识格局可视为某种情况下或某种意义上适用的概括,而不能作为普遍适用的概括〔24〕。
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变化,历史认识间接性的问题已不像在客观主义史学时代那样凸现和烦人了。就客观主义史学来看,历史研究中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只要能获得史料,历史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全部历史还原”〔25〕。只要获得全部资料,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26〕然而,对于当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即使获得全部的历史资料,也并不意味着能解决一切问题。马克·布洛赫曾深有感触地写道:“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27〕这种压力和苦恼不是来自于史料的缺乏,也不是靠获得史料就能解决。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认识的间接性已不存在或解决了。历史研究不是无所为而为的,它总是与某种当前的实际目的相联系,人们认识历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在“为我关系”中理解历史。历史本身是历史的,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只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它的意义。于是,有关历史真理问题转向了一个更复杂、更烦人的问题上,即这样一种变动不居的历史学,能不能产生一些经久不变的真理呢?或者说作为一种价值认识的历史学究竟有没有可能获得像自然科学那种的真呢?哲学家金岳霖在《真小说中的真概念》一文中,曾讲到过知识领域中的几种不同种类的真,他说:“与科学中的真的无情感性和外在性相比,与逻辑命题的严格精确性和优美空洞性相比,历史学家发现的真相应地渗透着一种类似家庭的气氛”〔28〕。如何理解这种渗透着类似家庭气氛的历史之真呢?这是历史认识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五、间接证实与符合真理说
历史学中有相当部分的历史认识只能间接地检验,对于这一类只经过间接证实的历史认识,我们能不能说它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呢?赵文认为不能。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谁能知道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事实不能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我们也没有将认识与事实直接比较对照,怎么能说它是符合历史事实实际的认识呢?
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较为普遍:即认为由于历史认识对象的非直观性,使得一些适用于一般认识活动的概括、原则,不适用于历史认识。如,有同志认为,历史研究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的提法不科学,因为历史事实是既往的事实,它们看不见、摸不到,无法用实验的方法来再现它,当我们对历史实际茫然无知的时候,怎么能够做到从历史实际出发呢?历史研究包括若干必经的阶段或层次,其中弄清历史真相,认识历史实际是它的基础阶段或层次。如果否定认识历史实际是历史研究的必经阶段和不可逾越的基础层次,而倡言什么历史研究要从历史实际出发,那就是无视了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29〕。显然,按作者的逻辑,只有对象是现有的存在,才能做到从事实实际出发。赵文似乎也是这种理解。
历史事实早已过去,谁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历史学家经常碰到的烦恼,就好像某甲说苹果是红的、甜的,只要苹果未吃光,就可以亲眼看一看、亲口尝一尝,就可以检验某甲的判断是不是正确。如果苹果已经吃光,我们看不见、尝不到,不知它究竟是什么模样,又怎么检验某甲的判断呢?然而,这里仍有不少课题。
首先,如果事实是现有的存在,是不是就不存在“谁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
按赵文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真理可以用符合说,历史真理则不能,因为认识与事实的符合关系无法检验,事实早已过去,这里存在着一个“谁能知道早已发生过的‘历史实际’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然而,我们要问:如果事实是现有的存在,是不是就不存在“谁能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关于这一点,本文的第二、第三部分已有讨论。苏东坡《前赤壁赋》中有这么两句:“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不仅某甲的判断(苹果是红的)是一个“目遇之而成色”的过程,我们的检验也有一个“目遇之而成色”的环节。苹果虽然还是现有的存在,可以让各位检验者亲眼看、亲口尝,但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将事实证据变为证据命题的环节,存在着对事实证据的不同理解问题。说苹果是红的,既有客观“之”的规定,又有:“目遇”的作用。如果某乙是色盲,那么“目遇之而成色”的“色”,就同某甲不同。所以,对象的现有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对它一目了然或看法一致,它同样存在着一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我们常常看到某一命题的验证之所以意见不一,不是由于没有事实证据,而是由于对事实证据的不同理解。所以,通常说的“事实胜于雄辩”,也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
其二,如果我们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无法直接检验,而在界定历史真理时说它的真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真,那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
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认识的检验较为困难,受到较多的限制。这是历史认识检验方面的特殊性,它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许多历史认识无法证实,许多历史认识只能作出间接的证实。但是,历史真理就其本质来说,应与自然科学中的真理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不能因为检验方面的特殊性,而去改变历史真理的本质(笔者认为,赵文的界定已改变了历史真理的本质)。真假表示的是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不管是对现有事实的认识,还是对既往事实的认识,都只能在与对象的关系中去界定它。某一历史认识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可以不称它为真;某一历史认识只得到间接证实,我们也可以不称它为真。但是,某一历史认识一旦称其为真或真理,我们就应该肯定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我们可以因为不知道它是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而不称它为真,而不能说历史真理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如果我们按照赵文的逻辑——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过去无法直接验证,而在界定历史真理时,说历史真理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还会引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果。我们知道,特殊认识和个别认识的对象总是随时光的流逝而流逝的,昨日还是未然的事实,今日就成了当下的既有的事实,到明天,它又存而不在,成为既往的事实。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的性质,是不是也要随着事实在时间轴线上的变化而变化呢?昨日只是假设,只是推测,因为事实还处于未然的状态;今日可以称为真理,因为事实正在眼前,它是符合事实实际的认识;到明天,事实已经过去,我们不能再称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它只是有可靠史料的依据,符合历史真实而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这样的结果,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甚至是危险的。
其三,间接证实是不是也体现了认识与事实的检验呢?赵文之所以反对将历史真理界定为符合历史事实实际的认识,恐怕与历史认识的间接证实有关,既然检验者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直接考察,认识与事实的符合检验没有落实,又怎么可以在认识与历史事实的符合关系上来界定历史真理呢?其实,认识也好,对认识的检验也好,都是一个主体对客体的信息的接收、加工、整理的过程,当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接收到客体的信息,并把它整合进我们的观念,观念就具有了来自客体、与客体相符合的内容,以此来比较对照待检验的命题,就体现了认识与外在对象的符合关系的检验。如上所述,苹果尚未吃完,我们可以直接看、直接尝,直接感受客体的信息来检验某甲的判断正误,这当然体现了认识与外在对象的检验;苹果已经吃完,我们无法直接看和尝,无法直接感受客体的信息,只能通过接收它留存在现存物质系统中的某些信息来间接检验某甲的判断,这也体现了认识与外在对象的检验。我们切不能把直接证实看作是把事实原封不动地搬进观念进行认识与事实的两相比较,或看作是“骑”在事实与命题之间将两者相互比较。如果抱着这样的看法来考察历史认识活动,就会感到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的符合与否的检验无法实现。当然,直接证实和间接证实都是一种弱化的检验,这一点在历史认识检验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间接证实不仅也体现了认识与事实的符合检验,而且还可以达到相当的可靠性。间接证实的可靠性常常受到怀疑,部分的间接证实有些不可靠,但不是所有的间接证实都不可靠。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类命题(有关历史的特殊命题)底证实比B 段所论的(有关当前的特殊命题),要困难得多,也许有人会想到,这类命题底证实不大靠得住。一部分的证实也许有这一问题,但不是所有的证实都有这一问题。问题不在于证实靠得住与否,而是在形成证实底困难,表示历史的特殊命题是不容易证实的”。“假如一表示历史的特殊命题,不但有记载上的证据,而且有古物上的证据, 这一命题底证实和B段所谈的命题底证实同样可靠”〔30〕。在历史学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只能作出间接证实的个别性历史认识,常常被冠之真理的“大字眼”。如,有同志认为历史认识的绝对性只存在于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人类历史认识无限发展的承继系列的只能逐步接近的方向,另一种是某些关于具体史实的单称判断。〔31〕也有同志认为,这些认识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不可能被推翻,它反映了确凿无疑的个别事实,也可以称它们为永恒真理。〔32〕这两种说法是否妥当,这里暂且不论,〔33〕但也说明了间接证实可以获得与直接证实同样的可靠性。
六、对赵文的真理定义及相关问题的几点商榷
赵文对历史真理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历史真理是经过可靠史料的验证,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并指明这里的“历史真实”与“历史实际”是不同的概念,历史实际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真实则是有史料根据并且能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这个定义的特点是避免在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中界定真理。然而,这一避免又引出了许多问题。
首先,真理定义的陈述有矛盾。
赵文的真理定义有三个要点:(A)真理是经过史料验证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B)历史真实不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事实;(C)历史真实是有史料根据并能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A)、(B)、 (C)各自的含义是清楚的,但我们无法将这三个要点合并成一个融洽而无矛盾的真理陈述。将(A)与(B)合并,可以形成陈述(D):历史真理不是符合历史实际而是有史料验证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将(A)与(C)合并,可以形成陈述(E);历史真理是有史料验证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历史本体就是历史实际,历史重构就是历史认识。因此陈述(E)又可以简化为:历史真理是有史料验证反映历史实际的历史认识。至此,我们无法再作进一步的合并,因为由(A)(B)合成的陈述(D)与由(A)(C)合成的陈述(E)所表达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真理观。
其二,“真实”一词的含义不确切。
真实一词,通常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客观的事物或事实本身,如我们说,桌子上有一只苹果是真实的,这可以表示苹果的客观存在。另一种是与“假”相对,表示与事实相符合。真实一词的第二种用法,实际上是一种关系范畴,在认识论的研究中,通常用来表示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单个的命题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命题与命题之间也无所谓真实不真实〔34〕。当我们说某一命题比另一命题更真,或说某一命题比起另一命题不那么假,那已是指命题与事实的关系了。同时,事实本身也无所谓真实不真实。只有命题与事实之间才有真假关系。赵文说历史真理是“经过可靠史料的验证,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里的“历史真实”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有史料根据并且能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历史重构上,历史真实就是历史重构,符合历史真实就是符合历史重构。这样理解的话,真理就是符合某种历史重构的认识。这是在认识与认识之间界定真假,恐怕不是赵文的原意。另一种是把重点放在反映历史本体上,历史真实就是反映历史本体,符合历史真实就是反映历史本体。这样理解的话,真理就是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这是不是赵文的原意呢?恐怕也不是,因为这样的理解与我们通常所说历史真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使我们不解的是:既然可以说有史料根据并反映历史本体的历史重构,为什么就不能说有史料根据并符合历史实际的历史认识?如果说历史实际早已过去,它与认识的符合关系无法验证,那么历史本体也早已过去,它与历史重构的反映关系又如何验证呢?由于“历史真实”一词的含义不确切,我们很难明白赵文所说的“符合历史真实”,究竟是符合什么。
其三,历史认识领域里的历史实际就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的说法不妥当。
历史实际,通常是指客观的历史事实。赵文在谈到“历史真实”不同于“历史实际”时也说历史实际是指客观的历史事实。然而,赵文更多的是强调历史实际就是历史学家的主体重构。这就是把客观的历史事实与我们观念中的历史事实等同起来了。这种观点,在赵吉惠先生的另一篇论文中阐述得更加清楚。在《当代历史认识论的反省与重建》一文中,赵先生认为,当代东西方的某些历史哲学家,为了准确界定“历史事实”这个概念,曾经试图把它区分为“科学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的历史事实”等不同概念。这些概括、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包含着对“历史事实”概念的深刻理解。但是,细心推敲,存在着矛盾:“把“历史事实”区分为“科学的事实”或“史学的事实”与“客观实际的事实”,就等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实,一个是的客观的事实,一个是主观的事实,而且二者是对立的。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只存在一种事实。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记载的或者历史学家著作中陈述的事实,虽然包含科学重构的性质,但其真实内容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的部分或片断,是客观实际历史事实的陈述或表现形态。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所谓“科学的历史事实”或“史学的历史事实”不过是从“实际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整理、概括的结果罢了。〔35〕
与一般的认识活动相比,历史认识活动中的命题与事实的密切关系十分突出。就特殊或个别命题及其所指称的对象来说,“发现一特殊的命题之为真也就发现一件事实,发现一件事实,也就是发现了一真的特殊命题”〔36〕。这一现象在一般认识活动中也存在,只是不太明显、不太突出。在一般认识活动中,对象的现实呈现使我们获得一种确实强烈的实在感,受这种实在感的制约,我们通常总会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和唯物的立场来理解命题与事实的关系,如事实在先、在外,命题在后、在内,命题是对事实的反映等。这种态度和立场有助于正确理解认识的本源问题,但也容易助长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尤其当讨论深入到认识的发生问题上,就会忽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的作用。
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往的事实不能产生像上文所说的那种确实强烈的实在感。相反,认识过程中的主体的作用是能确实和强烈地体会到。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风趣地描述了一个单纯的历史事实如何在历史学家的推荐之下而成为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俱乐部会友的过程〔37〕。这种状况很容易产生一种主观的态度和唯主的立场来理解命题与事实的关系。究竟是事实在先,还是命题在先?是命题反映事实,还是事实靠命题而存在?贝克尔曾嘲笑客观主义史学家把事实看作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像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38〕。卡尔也说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那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39〕。这些都体现了这种态度和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有助于正确理解历史认识的发生问题,尤其是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问题。但是,一旦把它延伸到认识的本源问题上,就会忽视和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
一般说来,当代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者并不是笼统地否认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40〕。只是在他们看来,过去存在的那个历史事实,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那么它们又在哪里呢?谁又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呢?能够知道它们的存在,说出它们的模样,那已是我们认识的结果了。所以贝克尔说:“事实的存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存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识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41〕。
可见,将客观的历史事实与我们观念中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等同起来,是历史认识论中较常见的一种看法。其实,这两者还是可以区别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也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不能因为所“看”到的只能是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就说只有一种历史事实;也不能因为“科学的历史事实”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中整理出来的,而说这两者是一个历史事实;更不能因为认识具有真实的内容,就说它就是历史事实本身或它的片断、部分。总之,历史实际就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历史重构就是我们对这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认识,因为历史实际的存而不在而说历史实际就是我们的历史重构,是不妥当的。
*怎样的历史认识才能称之为真理,这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理解。一些学者认为,真理必须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只有普遍的知识才能称之真理,而像“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样的命题不能称为真理。也有学者认为,它反映了确凿无疑的个别事实,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不可能被推翻,可以把它称为永恒真理。本文讨论的历史认识真理,主要是指历史事实认识领域里的真理,它既包括普遍的命题,也包括特殊的命题,统称为真理,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注释:
〔1〕参见陈德荣:《符合真理论的困境:康德的挑战》, 载《德国哲学》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3 页。
〔4〕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102页。
〔5〕麦基:《思想家》,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42页。
〔6〕〔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 第72—73页。
〔7〕张盾:《无须存在公理的指称理论》,《哲学研究》1989 年第6期。
〔8〕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11月版,第913页。
〔9〕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11月版,第892页。
〔10〕金岳霖:《知识论》,第917页。
〔11〕金岳霖:《知识论》,第916页。
〔12〕苏富忠:《思维论》,香港中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 页。
〔13〕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 第164页。
〔14〕夏甄陶:《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352页。
〔15〕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到,反对符合真理论的总认为,“命题和事实非有鸿沟相隔不可,因为所有的关系既都是内在的,则在经验中的事实,我能把它和命题相比较的事实,一定和在经验之外的事实不同;此所以客观的事实只能在外,可是,这又是学说底影响。如果我们不接受内在关系学说,我们不至于有此结果。如果鸿沟是不可免的,它的确给符合说以致命的困难。但是鸿沟不是不可免的,它只是在接受某种学说之下的困难而已。”他又说:“本书有经验之内的客观的事实。其所以如此者,主要点在本书以正觉为出发点。正觉所供给的所与本来就是客观的,它是客观的呈现”。(《知识论》第913~914页。)
〔16〕认识检验中的不确定性有两种:一种是由实践本身的局限性所决定。实践是一个过程,就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的实践活动来说,它“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表象”。(《列宁选集》第2卷, 第142页)具有不确定性。 另一种是由于在实践结果转变到检验证据的过程中,因主体的选择、陈述等而使得事实证据渗进了许多主体的因素,影响或破坏了它原来的纯客观性和确定性,使得证据所给予的支持和反驳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17〕〔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第73页。
〔18〕沃尔什曾说:“我们不可能实现符合论的全盘纲领,因为我们不可能考察过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对它的重建却并不因此就是随意的。历史思维是受着对证据必须做到公正这一需要所支配的;虽说这并不是以某些人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被固定下来的,然而却也不是由历史学家所制造出来的。它里面有着某种‘过硬’的东西,那是辨驳不倒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无疑地正是这种成份,才引导符合论的拥护者们试图去发见那种能与之对独立的已知事实的陈述相一致的对历史真实性的检验标准。这个计划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然而却始终都存在着一种持久不断的诱惑,使人要进行这种计划。”(《历史哲学导论》第89页)这里所说的历史思维受到某种“过硬”东西的制约,实际上就是指观念接受了来自历史客体的信息,并按信息所表征的历史客体的特征、状况来形成观念的内容的过程。肯定这一点,也就肯定了认识与事实的弱化检验是可以实现的。沃尔什的配景理论也肯定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只是在一种弱化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这实际上已不是事实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了,而涉及历史价值认识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
〔19〕〔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第92页。沃尔什在这里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指出事实与认识并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对照,事实只有被理解、被描述,至少被人有意识地领会时,才能用来核实认识。所以,事实即使呈现在眼前,也无法实现认识与事实的相应对照。另一方面,在讨论历史认识的检验时,他又感叹我们不能在与历史事实的两者比较中,看出认识的正确性。
〔20〕有关运用现实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历史学中的一般性认识,可以参见:姜义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历史研究》(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曹伯言:《“史学概论”三题》(《学术月刊》1987.6);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页);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3~268页);赵吉惠:《史学概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208页)。
〔21〕〔法〕勒高夫等主编,姚蒙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22〕《多媒体形式出版〈霍尔德曼日记:尼克松白宫内幕〉》,《青年报》1994年12月13日。
〔23〕〔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0页。
〔24〕赵轶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 年第1期。
〔25〕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2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7〕〔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2页。
〔28〕《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29〕王正平:《历史实际与史学研究》,《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30〕金岳霖《知识论》,第870、871页。括号中的文字是引者所加的注释性文字。
〔31〕赵轶峰:《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研究》1988 年第1期。
〔32〕齐振海:《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366页。
〔33〕参见拙文《论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34〕命题与命题之间只有一致不一致的关系。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一致是就命题与命题底关系而说的”。“所谓一致就是多数命题底彼此无矛盾”。(《知识论》,第928页。)
〔35〕《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6〕金岳霖《知识论》,第915页。
〔37〕〔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8页。
〔38〕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39〕卡尔:《历史是什么?》,第7—8页。
〔40〕这对于正确理解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陈启能先生较早就指出这一点,参见《论历史事实》,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41〕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260页。
标签: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特殊过程论文; 科学论文; 赵文论文; 重构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