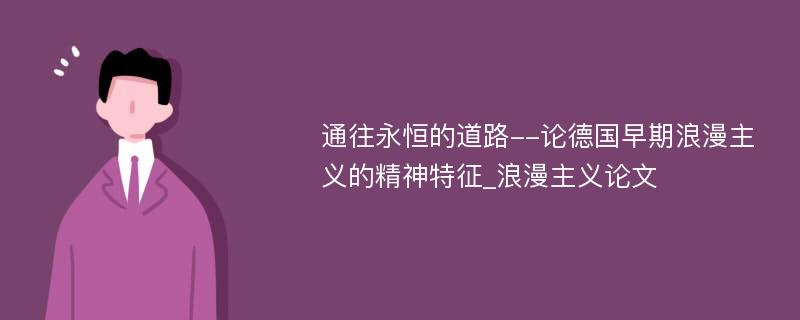
通向永恒之路——试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德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试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伽达默尔曾言,审美的人文主义传统是欧洲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方向,这主要是由德国浪漫精神形成的。德国浪漫精神从未中断过,从狄尔泰、尼采、海德格尔一直到伽达默尔,从里尔克、黑塞、卡夫卡、特拉克尔一直到托马斯·曼,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精神形式追随并延续着“浪漫精神”。然而,长期以来,一谈到德国浪漫精神,“浪漫”一词不是常常被置于流俗的解释,就是被附着以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以至于它的本真含义变得晦暗不明了。那么德国浪漫精神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在此可暂先设定一个简单的思路:德国浪漫精神即是通过诗的方式渴望永恒,追求绝对的精神。这一原则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人物弗·施莱格尔明确地言述出来:浪漫精神就是“向人类昭示至高无上者,或者把人类提升到最高的和无限的境界”,并“重新诗意地塑造生活”。(注:弗·施莱格尔《文学的历史》,1803年11月25日至1804年4月11日在巴黎的讲演。)
德国浪漫精神的真正出现是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它首先以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为代表。如果不囿于一种“流派”的概念,而是从总体精神范畴着眼,歌德和席勒也应属于德国浪漫精神之一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两人甚至比一些浪漫主义作家表现出更强烈的“浪漫精神”。渴望永恒、追求绝对作为德国浪漫精神的质的规定,使它与其他种种形式的浪漫主义区别开来。当然,无限、永恒、绝对并非是德国浪漫精神所独有的概念。自西方基督教文化产生以来,它们就是人类殚精竭虑所思索的问题。但是,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那里,这一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被越来越强烈地提出来加以追问,并由此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最激动人心的精神倾向之一。
一
18世纪,由温克尔曼研究古希腊造型艺术而开始的崇拜古希腊文化的风气在欧洲蔓延,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片真正的美和自由的净土。在那里,人处于自然整体之中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发展,人不仅实现着个体自身的目的,同时也实现着整体的目的。整个希腊精神显示出人与自然、存在与绝对律令、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古代希腊人的心灵就是完满与和谐。然而,这种对古希腊文化的羡叹并没有带来现代人的满足和充实,反而使他们对自己的现实状况生出了忧郁的痛苦。现代人看到,当他们超越完满与和谐的古希腊文化进入到近代之后,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完满与和谐的阶段,相反却陷入了一种“普遍分裂”的困境,这就是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精神、理智与情感、存在与意识、必然与自由的分裂。这种普遍分裂使人类产生了不安的焦虑,造成人的心灵的根本匮乏与不和谐。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对这种普遍而巨大的分裂的痛苦体验和深刻意识。弗·施莱格尔把近代称之为“化学时代”,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分裂”和“分解”。在他看来,造成近代这种“普遍分裂”境况的重要原因是“理智的解放”,理智成为近代的“引导和立法力量”。“理智”(Verstand)不同于“理性”(Vernunft),如果说理性的始源意义是“倾听”(Vernehmen),即在良心中倾听启示的召唤和神的声音,那么理智尽管是一种洞察和透视的能力,但理智的本质却在于“分解”。在理智面前,一切整体关联都要受到怀疑和破坏,“孤立的理智所着手进行的就是割裂自然整体并使之个别化”(注:《弗·施莱格尔早期文集》第1卷,维也纳,1882年,第105页。)。
理智使人与自然的原本统一的整体崩解了,人作为“我思”被确定下来,并与我思之物相对立,人不仅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不属于他的且与他对立的客观世界,而且发现自我也被客观化了。他必须反复地问自己:“我是谁?”然而,这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追问。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深深地感到了这种“自我疏离”的生存痛苦,因为当整体存在被褫夺后,人的生存便摇荡在万丈深渊里,找不到立足之地。
理智的片面发展在近代人心灵上的突出表征就是对自身和世界的怀疑,以及由此而来的行动的犹豫不决。他们已不再具有古希腊人的那种来自内在天性的坚定和统一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成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言述近代人心灵分裂的符码:“由于奇异的生活境遇,他高尚天性中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不停思虑的理智上,他行动的能力却完全被破坏了。他的心灵好像绑在拷刑板上向不同的方向分裂开来。这个心灵由于无止境地思虑着的理智而陷于覆灭。这种理智使他自己比所有接近他的人遭到更大的痛苦。人类心灵的无法解决的不和谐——这是哲理悲剧的真正题材——也许比起哈姆雷特性格中思考和行动力量的无限失调来,没有其他东西更能完美地表现这种不和谐性了。”(注:弗·施莱格尔《希腊诗研究》,译文引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75页。)哈姆雷特的根本处境乃是理智造成的自我分裂,而“一个分裂的存在”是不可能创造完善和满足的,他只能“鄙视世界和自己”,使“可怕的虚无成为其最内在的存在”(注:奥·瓦尔泽尔编《弗·施莱格尔致奥·施莱格尔的书信》,柏林,1890年,第94-95页。)。
如果说对古希腊文化的崇尚带来了“和谐”与“分裂”的巨大反差,那么,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则使存在的分裂和人自身的分裂更其尖锐。如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指出的,由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人分裂成了碎片,人被物化,成为职业和科学知识的一种标志。人不仅与物分离,甚至成为物的奴隶,这种“异化”现象使人的整体生命“零散化”。对于这一新的历史命运,荷尔德林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以隐喻的语言表达了人与自己的创造物的分裂,人的价值生存与技术文明的分裂。他敏感地觉察到技术文明的不断扩展所带来的人的灵性的丧失,人不再倾听神灵的呼唤。
在荷尔德林那里,“普遍分裂”更多地连结着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他在给黑格尔的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我自身就是这个客体,那么我作为我就必然有局限性,也就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也就不是绝对的了。”(注:引自《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页。)这里,人作为主体是有限的,因为主体只是一个不属于他的客体的主体。客体被给予主体,后者只能去感知和接受客体。于是,这一作为主体的人就成为一种外在的存在,一种不完善的有限的存在。在荷尔德林的后期诗歌中,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表现在与神的远离,这是一种本体论的分裂。神的隐匿意味着人的“沉沦”和“无家可归”。当然,对于荷尔德林来说,只有在此一“沉沦”中,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才成为可能。
在近代的“普遍分裂”中,诗也呈现出不可避免的分裂。理智对诗的侵入使诗原有的那种自然、朴素的有机统一性不复存在。诗不再直观地面对整体自然,它成了对个别的模仿。诗的客观性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趣味性”。“趣味”所追求的不过是偶然性、瞬间性和感官的刺激,它所满足的恰恰是人类分裂的心灵,而每一次满足都引发另一次更强烈的刺激,诗就在这种刺激中一次次循环,而人的心灵也一次次地分裂。因此,诗不再是对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揭示,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美。弗·施莱格尔很早就看到,近代诗已渗透进对“丑”的描写。“丑”即是不和谐。这表明,近代诗不仅在形式上不和谐,而且就它所模仿的对象而言也是不和谐的。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看来,这种“不和谐”就是人的生存的匮乏和本真性的失落。近代诗已经不能诗意地塑造生活,人类陷入了可怕的“散文化”。由此可见,人类若要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就必须改造近代诗,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显现出自由的“客观美”。
如果说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把近代以来现实的存在状况看作是“普遍分裂”,并对这一“分裂”有着痛苦的体验和深刻的意识,那么他们的根本愿望就是“综合”,无法再重新使存在获得普遍的统一性。只有在追求统一性的过程中,人类才能诗意地生存,而“诗意地”在世就是面向永恒和绝对实在。“浪漫”之路也就是通向永恒和绝对之路。
二
存在的普遍分裂是和谐状态的丧失,没有统一性,人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立足之处。如何使人类重返完美和谐的“家园”,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面对着三种途径:其一是“回归自然”,其二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楷模,其三是使人类走上一条永无止境的接近“绝对”的道路。
第一条途径是由卢梭提出的。1750年,卢梭发表了论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他在文中批评了文明所带来的道德堕落和理智对情感的压制,赞美了自然状态的简朴、纯洁。卢梭“回归自然”的主张是对人的情感和本能的张扬。对于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来说,卢梭的主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又不能完全遵循这种主张。他们认为,人类既然超越了自然也就无法再回到单纯的自然状态中去,无法再回到纯粹的“感性”中去。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历史观在于承认人类的进步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在自然阶段,人与自然虽然和谐统一,但其中的“引导和立法力量”是本能,而本能则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看来,理智是人类不得不承受的命运,人类不可能以纯感性的方式重获自身的统一,而必须在一种同时超越了片面理智的更高层次上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主体与客体、理智与情感的统一。这一更高的层次就是“诗”。关于诗的绝对实在性,将在第三部分论述。
前文说到,自温克尔曼始,崇尚古希腊艺术的风气蔚然,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人都赞美希腊文化,认为那是一种和谐、明朗、宁静的文化。他们希望通过对古希腊文化的追怀为近代人分裂的心灵找到一条获得慰藉的途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也对古希腊充满了赞美之情,例如弗·施莱格尔曾有“希腊崇拜狂”之称号。荷尔德林的小说和诗歌始终流溢出对古希腊精神的向往。但是,他们同时也在思索:作为一次性美的希腊艺术是否能够企及或重复?古代希腊精神能否容纳浪漫的心灵?尤其是第二个询问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来说更为重要。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诗人们喜欢用两个比喻来说明希腊文化与浪漫精神的区别:“圆”和“直线”。“圆”是封闭性的,它的每一个移动点都与中心保持相等的距离。圆是从自身开始又回到它的起点的循环运动。因此“圆”是完善的象征。“直线”是向着一个确定方向的延伸,它始终超越每一个点,而不是返回自身。因此“直线”是变化、生成,是对目标的无限逼近。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把古希腊文化看作是一种“圆形”文化,而把“直线”看作是“浪漫心灵”的象征。在古希腊文化中,人与自然处于完善统一的循环往复中,不存在有限与无限的两极性,因而也就无所谓“超越”的问题。自近代以来,由于普遍的分裂,有限与无限成为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这样,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倾向中,个体偶在向无限和绝对的超越便突出出来。浪漫的心灵就是把全部的力量投射在一条无限的直线上。对于这个“心灵”来说,“直线”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无限”的,不仅在起源方向上是无限的,而且在目标方向上也是无限的。人类和世界的起源同其目标一样都是从有限向无限的超越,都是向“绝对”的逼近。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为克服“普遍分裂”所面对的真正选择就是如何为人类启引一条通往“绝对”的道路,而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在此澄亮出来。
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那里,绝对、无限、永恒具有等值的含义。谢林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等值性”:绝对是主体与客体的“纯粹同一性”。绝对即是无限,而绝对和无限又是“无条件的永恒”。绝对具有无穷的超验性。在此,“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与事物的割裂,而是在自身包容着宇宙整体。因此每一事物都是绝对的载体,它们只有从无所不包的“绝对”那里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
毫无疑问,对“绝对”的信仰构成了“浪漫精神”的基点。它不仅是导向浪漫哲学的第一步,亦是导向浪漫诗学的第一步。意识、思维和存在无不根植于“绝对”,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的同一也只有在绝对中才能得到解决。
“浪漫精神”中的“绝对”观念显然有着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但我们又不能简单地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理解“浪漫精神”的“绝对”。基督教是以“无限”的观念摧毁古希腊文化的,在这一观念中包含着对现世存在的否定。然而,“浪漫精神”的内在品质并不鄙视和否定人和世界的有限存在,人和世界被看作是“神灵的庙宇”,映射着“绝对”和“无限”的镜子。这种对“绝对”的禀有乃是在于感性个体由绝对同一体设定。从这方面看,“浪漫精神”的“绝对”观念似乎更接近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这种泛神论断言:自然中的万物都源于一个最高的实体(神),是这个最高实体的属性。然而,在斯宾诺莎那里,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或者说感性个体与超验本体之间的关系是静止的,而且也看不到有限向无限、个体偶在向绝对的不断超越的运动。
“浪漫精神”面对的重大问题是:在个体偶在与绝对存在、有限与无限之间,个体偶在如何达到绝对存在,有限如何上升到无限?弗·施莱格尔在其《哲学讲演集》中把此一重大问题给突出了出来:“无限与有限似乎被一条巨大的裂隙分离和割裂开来。它们之间的联结和融合,从此过渡到彼如何才能达到呢?这不仅是本体论,而且也是全部哲学所具有的重大和最难的问题。重要哲学体系的论争和矛盾都围绕着这个根本点,即确定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两个分裂的世界之间找到一个中介原则。”(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8卷,慕尼黑菲迪南·舍宁赫出版社,1979年,第275页。)以往的哲学没有解决有限与无限的关系问题,正在于它把“存在”看作是不变和持存的。因此重要的是把一种运动过程置于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之间。谢林这样说道:“有限自我的终极目的就是一直扩展到与无限的同一”,这种扩展“不仅包含有一种认识,而且也包含有一种变化和追求”。(注:谢林《论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见《谢林选集》(6卷本)第1卷,慕尼黑,1946-1954年,第124页。)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普遍承认一种“生成”原则,这就是弗·施莱格尔意欲找到的那个“中介原则”。“生成”不仅显示出有限与无限关联的可能性,而且也显示出有限与无限在根本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生成着的无限只是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最高完满,它同时就仍还是有限的;同样,生成着的有限只要在自身有一种永恒的流动性、运动、自我变化以及转换的活动性,那么不管它是多么的有限,都“包含着一种无限的、内在的完满性和多样性”(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8卷,慕尼黑菲迪南·舍宁赫出版社,1979年,第277页。)。
向“绝对实在”的超越在“生成”中实现自身,但其前提条件是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包容。在此,施莱尔马赫的言述具有典型意义。他不断地强调了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通往“无限”的道路只能经过“有限”,“有限”在自身就含有“无限”的意义,在“有限”之外去寻找“无限”只是一种虚幻。“无限”普遍存在,它通过感性个体对现实世界的直观而被领悟。人的使命就是在一切个别的东西中发掘无限的东西,把一切有限的东西都看作是“绝对”的体现。在个体中所发现的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人类整体”;在历史中所发现的不是事件的序列,而是“支配整体的精神”。施莱尔马赫甚至认为,精神如果在“有限”之外寻找自己,就会误入迷津,但它越是认识到个体性,就会越多地认识到永恒性。“有限”与“无限”的这种交互流动性之所以可能,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乃是因为人既是被创造者又是创造者。
从“有限”向“无限”,从个体偶在向绝对实在(神)的生成超越是一个永不停顿的运动,任何僵滞、中断和犹豫都意味着精神的“沉沦”和心灵的“靡萎”,从而也就是作为有限存在的人与神性的远离,在大地上漂泊无依。因此,“生成超越”的可能,必须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提升。但何为精神?按照浪漫哲人谢林的定义,“精神的本质在于活动性”(注:谢林《论启示和民众教育》,见《谢林选集》(6卷本)第1卷,第401页。)。诺瓦里斯也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活动性的精神成为一切真正精神的基础。”这类表述也许过于哲学化,而对精神本质的一个更富于诗性的表述则是“渴望”(Sehnsucht)。这种渴望并不针对一个具体对象,或者最终将其获取和占有,而是“一个把自身伸展到各个方面的不确定的活动性”和“一个不确定的无限冲动”(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7卷,第430页。)。在浪漫诗人看来,人是动物性和神性的综合。如果说“动物性”是人的肉身偶在,它勾划出人的生存的界限。那么,人的神性就是那个“不确定的无限冲动”,在生存的界限中它揭开了一个缝隙,使人可以瞻瞩和预识有限肉身之外的精神未然之境。因此,“渴望”是人的神性一极的显现,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构成:“人最必要的东西正是对无限的渴望。”(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18卷,第420页。)在渴望中,人不断地向着绝对,向着无限“绽出”。在诺瓦里斯的《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中,我们读到的就是一种对“渴望”的隐喻:奥夫特丁根寻找的“蓝花”并不是一个实有的存在,而是心灵从庸俗、狭隘、空洞、肤浅中提升出来,不断走向永恒的一种方向、渴望和可能性。对这个寻找者来说,真理在于:只要“渴望”在,就有永恒,就有神性之光的朗照。
在浪漫精神中,渴望更深地植根于“爱”,它是人的渴望的原创性力量。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所说的“爱”首先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基本的宇宙元素:“爱是最高的实在,原始的根基。”(注:《诺瓦里斯文集》第3卷,莱比锡,1929年,第254页。)“一切开始于爱,也完成于爱。”(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18卷,第353页。)爱使神灵、世界、人相互牵引于原初的统一性之中,只要有爱,人便诗意地居住在天空下、大地上,并承纳着神灵的慈爱。近代以来,人对大地的征服,神灵的远遁,以及人由此而产生的无所凭借的傲慢,都是在于对“爱”的远离和遗忘,或陷于一种狭隘的爱的迷误。因此,浪漫诗人一再强调作为一种无限超越活动的“渴望”便意在重新唤起“爱”,因为正如弗·施莱格尔所言:“渴望是一种爱的形式。”(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18卷,第373页。)
以上讨论的逻辑次序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为人类开启一条通往永恒和绝对的道路,而这关键在于有限与无限的关联,为此就需要重新唤起以“爱”为基础的渴望,并使“生成”成为人的生存的基本可能性。到此,我们对“浪漫精神”的讨论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当然不是。因为“浪漫精神”的是终实现必须通过“诗”。如果说“浪漫精神”的基本内质或它的根本追求是克服普遍分裂,重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那么这最终必须在诗的王国中,正如诺瓦里斯断言:“通过诗,最高的同情与活力,即有限与无限的最紧密的统一才得以形成。”(注:《诺瓦里斯选集》(3卷本)第2卷,卡尔·汉泽尔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
三
“浪漫精神”在根本上就是诗的精神。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浪漫化”等同于“诗化”。如果说“浪漫化”在于“赋予平庸的东西以更高的意义,使落俗套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知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使有限的东西重归无限”(注:《诺瓦里斯选集》(3卷本)第2卷,卡尔·汉泽尔出版社,1987年,第334页。),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使世界和人的存在与诗合一。
在这里,“诗”首先不是从诗学和体裁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那里,“诗歌”(Dichtung)和“诗”(Poesie)并非等同。“诗歌”可视为艺术种类之一种,但“诗”却不是一个艺术种类,也不是一种审美方式。它必须从更本源的意义上来理解。“浪漫化”的可能性便包含在诗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诗”呢?综合早期浪漫主义诗人们的看法,我们不难看到,“诗”首先是一种宇宙性的元素。弗·施莱格尔在《关于诗的谈话》一文中最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见解。他把“诗”看作是宇宙之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和无意识的诗”(注:弗·施莱格尔《关于诗的谈话》,见《弗·施莱格尔全集》,第2卷,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它无处不在,在植物的生长中,在阳光的照耀中,在孩子的微笑中,在年青人的勃勃生命中,在女人的爱之中,都有“诗”的闪现。整个大地就是“一首神圣的诗”(注:弗·施莱格尔《关于诗的谈话》,见《弗·施莱格尔全集》,第2卷,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80年,第134页。)。在这里,“诗”原本就是宇宙的一种无限创造性,是生命和实在的自我显现。因此,这个意义上的“诗”必然先于一切艺术和艺术创作的欲望,它是“原初之诗”。
“诗”本质上不是人的产物,正如荷尔德林所说,它来自于“神”。荷尔德林的“神”,当然不是彼岸之神,而是“自然”,是“宇宙”。“诗”乃是“自然”和“宇宙”中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中,自然或宇宙才充满着和谐,在“诗”中,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存在赫然显现。
人虽然不创造“诗”,但人可以觉知和感受到宇宙的“原初之诗”。根据早期浪漫主义的普遍类比性的原则,在人的心灵深处也必然存在着一种与“宇宙的原初之诗”相应的“诗性力量”。它不是理智和理性,而是人身上的一种灵性,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它作为人身上的“诗”,始智与作为宇宙元素的“诗”相互作用的。只有当人的诗性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时,才可能去符合和响应作为宇宙元素的“诗”。因此,诗人写的诗乃出自于这首“唯一的诗”,也就是说,作为艺术种类的“诗歌”是以“原初之诗”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原初之诗”,也就没有“诗歌”。一切诗都是对这首唯一的诗的模仿。这样,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就建立了一种“本体论的诗”(ontologische Dichtung)。
“本体论的诗”有一个基本主旨,它要使一切都回归到一个无限统一的整体存在,它处处都要在短暂中发现永恒,在有限中发现无限,正如谢林在其《艺术哲学》中所表达的,艺术和诗本身是“绝对之流溢”(注:谢林《艺术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1986年,第26页。)。
显而易见,在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那里,“诗”被置于一个极其崇高的地位。在这方面,他们与黑格尔是完全不同的。在黑格尔那里,“诗”(艺术)仅仅是“绝对”的感性显现,要达到他所说的那个“绝对精神”,诗显然不及哲学。黑格尔认为,只有在概念思维的哲学中,“绝对精神”才返回到自身,即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才会实现。因此,就哲学是“绝对”的最高认识方式和显现形式而言,诗必然要消逝,只有哲学才奠立了一切生活的基础。与此相反,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则认为,“诗”才是全部生活的基础,是最高的实在。在与“绝对”的关系上,“诗”高于哲学。尽管哲学和诗都有同样的对象,然而只有诗能够对“整体即真正的实在给予肯定的显现”,相反,哲学则是“否定的、间接的”显现,只具有一种准备性的功能,只是工具和方法,只有“诗”才是真正的和神圣的“思”。弗·施莱格尔在谈到诗和艺术与“绝对”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较高的艺术形式的本质就在于同整体的关系。因而作品是绝对合目的性的,并且是绝对无目的的。我们把作品看作是如最神圣的东西一样神圣,……因此,所有的作品都是一部作品,所有的诗都是一首诗,因为一切都要求同一的东西,即无处不在的一和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注:《弗·施莱格尔全集》第2卷,第414页。)
当然,早期浪漫主义诗人并不是要否弃哲学,他们反对的只是哲学的日益概念化和抽象化。在他们看来,一种缺少了“诗”的哲学只能在单纯的概念化和抽象化中将整体割裂,而且这种概念化和抽象化也削弱了人内在于心灵的诗意的感觉。因而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基本要求是,哲学必须诗化,即哲学与诗的融合。从本源性上讲,哲学与诗并不是分离的,诗是哲学的始与终。荷尔德林就是这样说的:“诗是哲学的开端和终结。正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头颅中飞出,哲学也源出于无限的、神圣的存在之诗,在哲学中分裂的东西,最终在诗的神秘源泉中达到融合。”(注:弗·荷尔德林《徐培里昂》,《荷尔德林选集》第3卷,岛屿出版社,1983年,第80页。)诗充满了创造性和“爱”,而这也必须是哲学所具有的。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一种“浪漫诗”就是去言说那首唯一的无限神圣的诗。但为了能够去“言说”,人必须培养一种诗意的官能,也就是说,要把心灵深处的那个原初的创造性力量发挥出来。浪漫主义之成为“浪漫主义”(此就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而言)正是在于他看到了人的“心灵”的沉沦,“灵性”的丧失。“灵性”的丧失使人的生活陷入了“庸俗”,而只拘缚于“有限”。因此,“诗化”首先是人的诗化,它意味着人的心灵世界必须充满想象、情感和爱。在一切人中,诗人是首先完成“诗化”即“浪漫化”的人,他们比其他人更多了一份“神秘主义的感觉”。在浪漫诗人看来,所谓“神秘主义”不是那种让人不可捉摸的神秘兮兮的东西,而是一种诗性的想象力的直观,它在有限中直观无限,在自然中直观精神,在客体中直观主体。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无法用概念去描述的,他只能在诗的神秘的直观中才能显现出来。
在早期浪漫主义那里,只有人诗化后,才可能达到世界的诗化。世界原是一个生动的、有机的、充满生命和奥秘的世界,但在近代以来的理性和技术的宰制下,变成了一个僵死的东西,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存在。在这里,人与自然是分裂的。因此,为了达到统一整体的存在,必须使僵死的世界重新充满生命,使自然与精神重新融合。这个任务只有通过诗才可能完成。在这里,诺瓦里斯的“魔化唯心主义”可以说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的“诗”的核心。
在诺瓦里斯那里,“魔化”与“诗化”与“浪漫化”是同一个意思。“魔化”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人的心灵的提升,一是世界的“灵化”,即重新使这个世界具有神秘性。诺瓦里斯曾这样说道:“诗化(即魔化)世界也就是建立童话世界”(注:《诺瓦里斯文集》第1卷,第246页。)。童话世界不过意味着世界本身的神秘性。在童话中,一切都是神奇的,一切都是关系、转化、形成和变形。在这里已经没有了机械性和僵化。在这个意义上,童话乃是诗歌的最高准则。童话的本质是对原初的整体统一状态的回忆。
“魔化”作为诗化,首先是一种“心灵”的活动。正如诺瓦里斯所言:“神秘的道路走向内心。”(注:《诺瓦里斯选集》(3卷本)第2卷,卡尔·汉泽尔出版社,1987年,第232页。)在这里,走向内心的“魔化”并不是脱离世界的内心化,也不是走向一种主观的自我,并由这个自我来统治世界和自然。尽管“魔化”或“诗化”强调了人的精神的活动性,但这种“精神活动性”与费希特的“精神活动性”是不同的。在费希特那里,一切都是由“自我”设定的,世界即“非我”,其本身是没有自由和自身性的。而诺瓦里斯的“精神活动性”不是去设定世界,而是让世界以其自身方式显现出来,是在走向内心的过程中,使世界的丰富性和神秘性显露出来。因此,在“内心化”的过程中,诗人的心灵是开放的,虚怀若谷的。在诺瓦里斯看来,世界的意义只吐露给向无限敞开心灵的人:“我们不能看见女妖的世界,只是因为我们心灵的虚弱和自我关联。”(注:《诺瓦里斯文集》第2卷,第352页。)诺瓦里斯所说的“魔化”就是对这种“自我关联”的超越和破除。“魔化”使人进入到自我与世界、精神与自然的统一。
在这个作为“绝对”的统一整体中,诗人不是超然的决定一切者,诗人只是一个“中间人”。他以词语的方式去言说整体存在。诗人是写诗者,他必在语言之中。那么,诗歌的语言必须成为一种真正的言说,而这种真正的或纯粹的言说也是一种“诗化”的可能性。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普遍认为,诗的语言不同于理性的散文化的语言。诗的语言不是逻辑,不是抽象。在诗的语言中,一个神圣的整体性存在得以守护。诗人作为“中间人”更多的是倾听宇宙的神秘声音。宇宙是不需要解释的“神圣的文字”,它向一切对它具有感受的人敞开。诗人作为具有诗意感受力的人,他写的诗乃是对宇宙的原初文字的复写。诺瓦里斯这样说过,并非只是人在言说,首先是宇宙在言说,一切都在言说着“无限”的语言。诗就是对“无限”之语言的言说。为了达到这一纯粹的言说,诗人必须像奥尔弗斯那样去言说。因为在奥尔弗斯的歌唱中,整体存在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存在融为一体。 诺瓦里斯的这个观点,我们在荷尔德林那里也可以清楚地见到。荷尔德林把诗完全看作是来自于“诸神”的,“诸神”即自然的统一整体的存在。诗人只是“诸神”到达的消息的传达者,然后诗人再以词语的方式把此一“消息”传达给民众。
在这个意义上,浪漫诗人普遍相信诗的力量,相信在一个日益理性化和技术化的世界里,只有诗人可以拯救世界。“拯救”即意味着让世界与人进入整体的存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浪漫主义对里尔克、海德格尔的影响。
我们在以上三个方面着重探究的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世界,这种探究主要是从一般意义和整体关联上展开的。实际上,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更生动地显现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在这里我们没有做详细的探讨,容后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