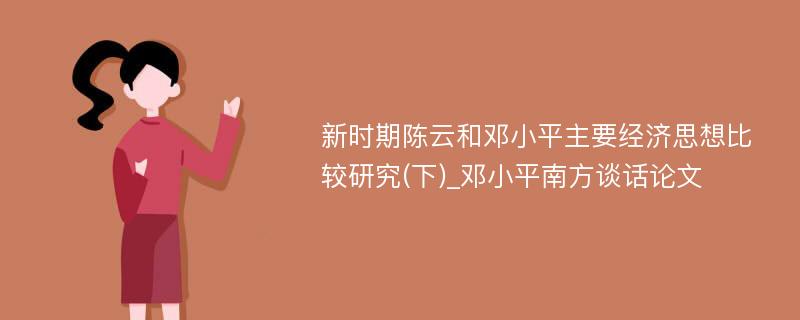
新时期陈云与邓小平主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新时期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四,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就计划与市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把计划、市场与姓“社”姓“资”相分离,重新赋予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经济意义。1990年12月24日在同薄一波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他在上海视察期间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根本上冲破姓“社”姓“资”的枷锁。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他更加直截了当地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邓小平的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引导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取得重大突破,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
(三)其思想异同及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的作用
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认识和实践,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不能混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指以对经济生活的计划调节作为基本和主要手段的一种体制,当然在这种体制下也可以或多或少地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则对经济生活起着基础的和主要的调节作用;这当然也不排斥计划调节的作用,但计划调节必须以市场关系中的固有客观规律尤其是价值规律为基础。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陈云与邓小平在经济体制问题上的主张,是有根本不同的。陈云虽然首先明确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市场调节”的新观点,但他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和主张,在总体上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范围。而邓小平所主张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调节在市场经济体制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我们不能因此来否定陈云在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贡献。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云提出这些主张,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在改革初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实践基础。
从思想发展来看,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如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表示,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293、353页。)
之后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探索与推进,主要是由邓小平来进行的,陈云对这种探索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对于中央在这一问题上的发展也表示了赞同的态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念,陈云对于这种发展表示“完全同意”,称赞“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同一位领导人讲话时又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困难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1992年7月,陈云又表示了支持党的探索的态度,他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第416、442页。)。
三、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
在新时期,“对外开放”这一概念,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的。从建立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到建立浦东开发区所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也是在邓小平的倡导、推动下逐渐形成的。毋庸讳言,邓小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陈云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也十分丰富,他在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指导原则等方面的论述与邓小平十分类似;他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经济特区等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一)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指导原则
邓小平对对外开放必要性的阐述,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利用外资开始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时,他又说明了对外开放的可能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355、161、354、236、91、127页。)在他的倡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最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1980年8月,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谈话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初步论述。他当时讲“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们要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之后,他又明确提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149、203、364、367、373、195页。)。这就是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
同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一概念,作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对外经济交流、技术和外资引进、建设经济特区的统称。他指出:“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这就是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邓小平还指出了在对外开放中必须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的原则。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还指出,“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但我们不要怕,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2、409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陈云也主张对外开放。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说: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有用的东西加快国内建设,这是完全正确的。1985年9月24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六次全会上作书面讲话,他又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第339、385页。)。
他也强调对外开放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
对于对外开放后带来的消极东西,陈云也多次呼吁要抵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他指出:外国的办法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澳门的赌场、香港的夜总会总是不可取的;开放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有些人看到外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等等,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对这些人要进行批评教育。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不可改变的法则(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第288、339页。)。
可见,在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的认识上,陈云与邓小平是基本一致的。此外,在对外开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上,陈云提出了需要注意的方面。如关于利用外资,他指出利用外资要慎重,要警惕。1980年12月1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又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对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如果低于平均利润率,他为什么不把钱存在银行里稳拿利息?为什么要搞冒险的投资呢?”他接着说“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只是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外资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本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它有两种效应,机遇与风险并存,成绩与问题共有。实践证明,陈云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警示意义。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也是我国对外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云指出了在技术引进中,要结合我国的国力和技术结构,合理地确定引进的项目、布局、重点、规模和对策的原则,而且主张要择优选用,不可盲从或重复引进,更不能长官意志,一个人说了算。1980年12月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对于外债,陈云也主张要具体分析,“现在有些带援助性质的外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低利自由外汇贷款,将来使用起来可能对我们有利”;而有些自由外汇,“利息高达15%左右,这是相当高的利息……这种自由外汇,我们借多了也还不起。”1979年3月,在《关于财经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也特别提到:“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76、248页。)这些意见,对指导当时的具体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还卓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的主张,较早地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
(二)关于沿海经济开放战略
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不仅如此,我国对外开放中采取的从建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发区到建立浦东开发区的沿海经济开放战略,都是在邓小平的倡导、推动下逐步形成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仍然沿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处在十分封闭、落后的状态下。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中,要进行全新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能渐进式稳步推进。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谈到对外开放时就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他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邓小平的倡议,1980年我国首先在广东、福建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邓小平对特区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特区开始创办的前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疑虑很多,阻力很大。1984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他说,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样了。他分别为三个特区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更快些”,对特区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从特区回来后,2月24日,邓小平邀请了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发行特区货币、增加对外开放港口城市等问题,指出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扩大厦门、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漳泉三角地带及环渤海湾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结原有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气魄提出并决定创建海南特区省和开发上海浦东,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对于这种开放战略,陈云多次表示完全支持。1984年4月,陈云听取谷牧关于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情况汇报时指出:我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8年2月,陈云再次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确立的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指出:“两头在外”好,但要贯彻这一战略也有一定难度。你们年轻、有希望,工作可以搞得好,应该搞得好。1992年,他又表示“非常赞成开发、开放浦东”(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七五)下卷,第353、410、441页。)。
对于经济特区,陈云说:“我虽然没有到过特区,但我很注意特区问题。”的确如此。自1981年起,陈云多次就特区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总起来说,有如下几点:(1)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1981年12月22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说:“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现在第一位的是总结经验。”1982年10月30日,在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报告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之后,11月16日,他又专门做出解释:我讲过的“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的工作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来拿出新办法(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307页;《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七五)下卷,第308、310页。)。
(2)在还没有总结经验的情况下,特区不能多搞。“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特区。”1982年1月25日,他又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306页;《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七五)下卷,第290页。)。
(3)特区产品,可有一定比例的内销。1984年4月,陈云指出,特区产品要有“一定比例”的内销。国内市场不能不让出一些,否则对外资没有吸引力。问题是让出多少,“一定比例”,可大可小……由计委掌握,研究个办法。对国内工业,保护落后我不赞成,但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这还是应该提倡的(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九五)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3、293、353页。)。
(4)关于特区货币。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完特区之后,在同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4月6日召开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也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在这一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中央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对于特区的货币流通问题,陈云一直十分关心。早在1981年12月22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就指出:在特区,“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因人民币腿短,外币腿长”(注:《陈云文选》第3卷,第264、253、250、267~268、279、244~247、276、277、307页。)。1984年4月25日,在听取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情况汇报后,陈云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对是否搞特区币,我考虑比较多。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实际上就是两种货币并存。而两种货币并存,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因为,“优币驱赶劣币”,是货币的客观规律(注:“优币驱赶劣币”是由“劣币驱逐优币”转化而来。在金银复本位制条件下,市场实际价值较高的铸币必然要被市场实际价值较低的铸币所排挤,这种现象被16世纪英国财政家托马斯·格雷欣表述为“劣币驱逐良币”。但在使用纸币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则会出现相反情况,即币值相同而实际购买力高的货币驱逐实际购买力低的货币。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优币驱赶劣币”。)。5月26日,陈云又在中国银行两位工作人员为反对发行特区货币写给邓小平并陈云等人的信上批示:“特区货币发行权必须在中央。决不能让特区货币与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流通。如果不是这样做,就会出现国民党时期法币发行之前的状况。”10月27日,他又专门把谷牧和刘鸿儒找来,谈特区货币问题。他说,如果大家坚持要搞,我提出两条: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
陈云负责财经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他又是党内有名的经济专家,对很多经济问题有着较深入、正确的认识。陈云在特区币问题上的观点,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是卓有远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意见得到重视。尽管那时特区货币已印好,后来,特区同志自己感到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就搁置起来了(注:《陈云年谱》(一九○五——一九七五)下卷,第353、355、367、408页。)。
综上所述,陈云与邓小平都主张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必要性、指导原则等问题上,他们的论述是类似、一致的。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不同,那就是,相对而言,邓小平更关注宏观层面的问题,从对外开放的战略、步骤上进行了大胆的设想与推进;陈云则更关注对外开放中的具体问题,对经济特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当时的对外开放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年来,有的海外学者在分析邓小平与陈云的经济思想时,扩大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甚至认为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本质上的(注:罗兵:《陈云与邓小平的分歧》,香港《争鸣》1984年第6期,转引自[美]大卫·M·贝奇曼:《陈云》,孙业礼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3页。)。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基本问题上进行了同步的探索,有着许多一致的见解,如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等,这无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一些具体方针措施上,他们观点不同时,注意吸收对方的意见。陈云经济思想的许多方面,为当时的经济工作实践所吸收,如发行特区币要慎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可重复引进等,都对当时的实际工作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的一些主张也很有远见,如利用外资、外债要慎重,对外开放要“走出去”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些,无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标签: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经济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深圳特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