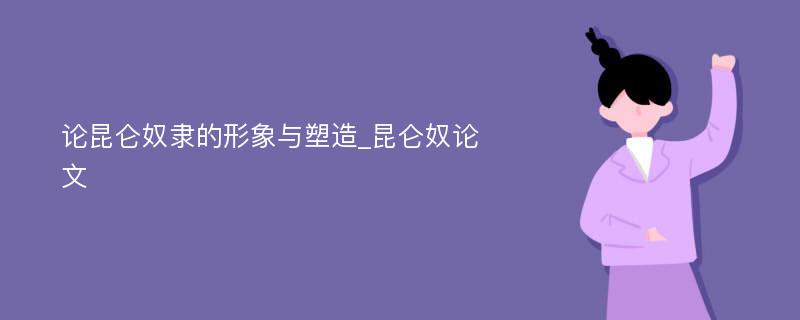
浅论《昆仑奴》中“昆仑奴”之形象及其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仑奴论文,形象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11)02-0043-04
唐代裴铏的传奇小说《昆仑奴》塑造出了一位智力兼济的昆仑奴形象,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由于历时久远,今天人们对昆仑奴已较为陌生,因此,在解读《昆仑奴》时,有必要先对昆仑奴的外貌特征、来源、职业及生活背景有所了解,如此才能更深一步理解《昆仑奴》中的人物形象。
“昆仑”最早指山名。《淮南子·原道训》云:“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高诱注云:“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千里”,此处“昆仑”,是指地处西北的昆仑山。此后一些历史文献中却将“昆仑”用来指人,指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周一良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昆仑》中指出:“东晋南朝之昆仑,疑指西南少数民族而言,非唐宋时南海之昆仑,如朱彧《萍洲可谈》所云‘近海野人’之昆仑,更非非洲之黑色人种”。该文指出,在我国一些古籍中,肤色较黑的人也常常被称为“昆仑”,[1]如《资治通鉴》卷一○三《晋纪》云:“有李陵容者,在织坊中,黑而长,宫人谓之‘昆仑’”,此书注云:“谓其人如‘昆仑’也。昆仑国在海外”,与李太后在一起的宫人,因其肤色黑而称其为“昆仑”;此外,《旧五代史》卷一三○《周书·列传·慕容彦超》中也有类似记载,云:“尝冒姓阎氏,体黑麻面,故谓之阎昆仑”,慕容彦超系五代周兖州节度使,吐谷浑部人,曾经冒姓阎,因体黑面上多麻,故被称为“阎昆仑”;《旧五代史》卷五四《唐书·列传·王镕》中也称肤色黑者为“昆仑”:“真定墨君和,……肌肤若铁,……赵王镕初即位,曾见之,悦而问之曰:‘此中何得昆仑儿?’问其姓,与形质相应,即呼谓墨昆仑,因以皂赐之”,墨君和因肌肤黑若铁,被赵王呼为“墨昆仑”。据有关学者考证,“昆仑”用来指人,多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海诸岛以至东非的卷发、黑身土著居民或昆仑人。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史地考证》一文中指出:“昆仑为南洋国族之称者,实始于《临邑记》(《水经注》卷三六)之‘昆仑单舸’”,“人因其肤黑,凡皮色相近者又均以昆仑呼之”。[2]岑先生《南洋昆仑及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一文又从语音上考证南洋之地的“昆仑”即“金邻”,并提出“古金邻之疆域应为今暹罗西部迤至下缅甸一带”,“必不能在马来半岛”。然而苏继卿遗著《南海钩沉录》中却称:“鄙意金邻国当为大唐西域记卷一三之迦摩浪(Kamalanka),拥有马来半岛北部与大钦河(Tacin)以西之一部”。[3]《旧唐书·南蛮传》则称:“自临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一九云:“秋,七月,戊午,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且书中注“昆仑”云:“昆仑国在临邑南,去交趾海行三百余日,习俗文字与婆罗门同”。“临邑”所在地,据陈桂荣等主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记载即“占波”,又作“占婆”,亦“瞻波”,为古印度鸯伽国都城,遗址在今印度巴迦普尔(Bhagalpur)附近。[4]翻检以上文献不难发现,中国古籍中所称南海之地的昆仑,范围比较宽泛,因该地黑色人种多,且又都为异族,故多以“昆仑”泛称。
唐传奇《昆仑奴》中的“昆仑奴”有体黑卷发等特征,古籍中对“昆仑奴”的体貌特征多有记载,如《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幼敏》中有《咏昆仑奴诗》,云:“指头十颋墨,耳朵两张匙”,诗中“昆仑奴”的外貌特征是手指黑,耳垂大。此外,《全唐诗》卷二六五顾况《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亦云:“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江村小儿好夸骋,脚踏牛头上牛领。浅草平田过攃时,大虫着钝几落井。杜生知我恋沧州,画作一障张床头。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诗中刻画出一位矫健善骑的昆仑奴形象。与之相应,《全唐诗》卷三八五张籍的《昆仑儿》一诗写到:“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诗中讲述了一位昆仑奴的来源、语言、耳环、发式、皮肤、服饰等的特征,该“昆仑奴”由“海中州”被“蛮客”带至“郁林洲”,隋唐时的“郁林洲”也称“郁林郡”,在今天广西兴业县西北40里(同上)。唐传奇《昆仑奴》中的“昆仑奴”也可能指矮黑人,李长傅《南洋史纲》云:“小黑人,后印度(中印半岛)之原住民人种。学家名‘小黑人’,属尼格罗系(Negritos),身躯短小,肤色黝黑。”《太平广记》卷四八二《流仇国》有“流仇人形体矮小,像昆仑奴”之说。此外,唐张鷟《朝野佥载》载朱宽所俘虏来的流求人“人形短小,似昆仑”。由这些记载不难获知,昆仑奴形体不会很高大,可能是一种体型较矮的“小黑人”。
有关“昆仑奴”的来源,李季平《唐代昆仑奴考》一文指出:“唐宋时所谓昆仑奴,既可能为非洲的黑人,也可能为南海各地卷发黑身的昆仑人,也可能为南海的矮黑种人”。[5]该文认为《昆仑奴》中的“摩勒”名字颇带阿拉伯人名字的色彩,“因而似可作为大食国人曾转输昆仑奴于中国的旁证”。但就唐传奇来看,昆仑奴来自非洲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他们形体矮小,再者,《昆仑奴》中的摩勒会武功,而且该传奇有“摩勒”后来在洛阳“卖药”的情节,这些似乎与非洲黑人生活情况不符。由域外来唐的昆仑奴,有的是被贩卖的战俘,有的是进贡唐政权的贡品,还有的是随使节入华而遗留下来的。此种现象反映了唐政权阔大纳异的心胸,强盛的国力,强大的国际辐射力。唐王朝广为吸纳外来文明,使当时的社会颇有一些异样的文化情调。王建《凉州行》中有“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的诗句,元稹也以“史诗”的笔法记载了当时胡文化的盛行:“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可见,当时胡乐、胡服极为流行,唐代士大夫对其他乐曲似乎不太感兴趣,多醉心胡乐,妇女也偏爱胡服。在这样一个宽容的大的文化背景下,昆仑奴以其忠厚、能干赢得了唐王朝各阶层人士的好感。除唐传奇外,其他艺术形式也多有昆仑奴或昆仑族人形象的塑造,如今天存放于陕西省博物馆的干县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神龙二年(706)唐三彩昆仑俑;敦煌莫高窟158窟《各族王子举哀图》,有肤色赭黑、卷发、戴耳环、项圈的昆仑国王子图像等,艺人以唐三彩俑、塑像、壁画等形式,通过对昆仑奴艺术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对他们的喜爱之情。
有关昆仑奴所从事的职业,古籍中多有记载,如《隋书》卷八一《列传·流求》载:隋炀帝派武贲郎将陈棱攻打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破解其(流求)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昆仑奴参加隋军,并作为流求语的翻译。“昆仑奴”除在军中作为翻译人员外,还有许多善潜水的记述,如唐《太平广记》卷四二○《陶岘》记载昆仑奴摩诃善泅水而勇捷,常为主人下水取物而最后惨死的故事;同书卷四二二《周邯》记载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昆仑奴潜在水中如走平地,且“经日移时,终无所苦”,周邯买下了他,改名为“水精”;同书卷四六四《鳄鱼》载李德裕贬官至潮州,途中船漏,宝玩书画落水,“遂召舶上昆仑取之”,却因鳄鱼太多,无法靠近而作罢。与此有类似记载的另如宋朱彧《萍州可谈》,该书卷二云:“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此外,古籍中还记载昆仑奴的特殊音乐才能,甚至还有昆仑奴在唐宫廷中担任乐工,如《新唐书》卷二二《志·礼乐》载:“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合诸乐,则用黄钟宫。其后方镇多制乐舞以献。”该书卷二二二下《列传·南蛮(下)》亦载:“乐工皆昆仑”。除史书外,元稹《琵琶歌》一诗亦云:“琵琶宫调八十一,旋宫三调弹不出。玄宗偏许贺怀知,段师此意还相配。自后流传指拨衰,昆仑善才徒尔为”,诗中“昆仑善才”是指在演奏琵琶方面才艺超众的昆仑奴。昆仑奴除在音乐方面有特长外,在舞蹈方面也有突出表现,如《新唐书》(同上)有这样记载:“有云头琵琶一……覆手皆饰虺皮,刻捍拨为舞昆仑状而彩饰之。”昆仑奴也有从事训狮行业的,如《太平广记》卷三四○《陆顼》载:“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尔昆仑奴操辔”。对此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旧唐书·音乐志二》记载唐代宫廷中的乐舞《太平乐》,由人装扮成狮子、装扮成昆仑奴,表演最古老的狮子舞蹈,其中“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唐代昆仑奴训狮子是常见之事。昆仑奴也有从事农耕的,如《太平广记》卷一六《张老》载:“适遇一昆仑奴,架黄牛耕田。”当然,昆仑奴中的大多数还是作为官私奴仆,多从事家政服务,伺奉主人或担当护卫人员,裴铏《昆仑奴》中的昆仑奴即是伺奉主人的家奴。
作为常人或以智胜,或以力胜,也就足矣。且以力胜者,遇怒辄拔剑而起,以泄匹夫之愤,虽力能扛鼎而智谋不足;以智胜者,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可常常手无缚鸡之力,因人成事。唐传奇《昆仑奴》中的摩勒智力兼济,颇具传奇之神秘色彩,其形象历千余年而不衰,拨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弦。明李贽在《焚书·杂述·昆仑奴》一则中盛赞昆仑奴云:“侠士之所以贵者,才智兼济,不难于死事,而在于成事也”,唐传奇《昆仑奴》中的“摩勒”才智兼济成就一代奇事,千百年来为人所称道。
作为一篇传奇小说,《昆仑奴》中的叙事模式存在一种所谓“有意味的形式”,即从小说中能探求出文化背景的某种折射,或某种变化着的“意识形态要素”。陈平原指出:“小说叙事模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那么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型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不能说某一个社会背景必然产生某种相应的小说叙事模式;可是某种小说叙事模式在此时此地诞生,必然有其相适应的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6]唐传奇《昆仑奴》小说的创作及广为流传,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朝代分合变迁,思想交融激荡,蕴蓄了隋唐文化喧腾、高亢的精神风貌和宽容、恢弘的气象襟怀。西域外族豪强任侠的风气与汉代儒雅礼让的文明造就出了生机勃勃、异彩奔腾的唐帝国的大千世界。这是一个尚武任侠的时代,当时许多诗人的诗中都有此种意绪情感的流动,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在文人的妙笔下生花。李白《结客少年场行》中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孟郊《游侠行》中有“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温庭筠《侠客行》中亦有“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文弱的书生对仗剑行侠充满了向往,在诗中流动着一种杀人的快感,这或许是豪壮狂荡之气的发泄,或许是对阔大雄奇阳刚之气的欣赏,这更是与唐文人士子昂扬奋发、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特质相契合。这样的文化沃土滋育出了《昆仑奴》中摩勒这一形象,他身怀绝技,力大过人,轻功绝伦。当小说中的崔生,为情所困,难解歌姬红绡“立三指,又反三掌,然后又指胸前小镜子”的隐语,而精神委顿、容愁食减时,摩勒挺身济难,对崔生说:“但言,当为郎君解释,远近必能成之。”口气之坚定,信心之十足,非常人所及。当崔生将实情告知摩勒,摩勒未假思索,脱口说出哑谜之解:“有何难会?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数十五指,以应十五日之数。胸前小镜子,十五夜月圆如镜,令郎来也。”其答案让人不禁眼前一亮,心中的疑团顿消。解隐语,若无深厚文化底蕴,恐无能为力,即便是有,无聪慧机灵之头脑,也会茫然无序。摩勒解得很轻松,又合情理,其阅历之广,知识之富,头脑之灵,让人叹服,由此不难推断摩勒居东土已日久,阅历深广,世态人情都很了然。然而摩勒何以知晓“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读者却无从得知。随后摩勒锤杀猛犬,负崔生“逾十重垣”,可见其气力之大,武功之高,对此宋朱彧《萍洲可谈》中有类似记载:“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惇,不逃徙,亦谓之野人”,“鬼奴”就是昆仑奴,说明昆仑奴力大能负物,可看出摩勒负生逾十重垣是有所本,当然小说重在表现一种超越人类体能极限的美感,并不排除夸张的成分。
红绡对崔生以身相许,欲随其出走,可崔生“愀然不语”,可能有此心却无力或无胆。一旁的摩勒不禁插话说:“娘子坚确如是,此亦小事耳”,豪爽之情溢于言表,对摩勒而言世间似乎无“困难”二字,常人难以企及之事,对其都是“小事耳”。“一品”权势倾国,手下的侍卫皆非等闲之辈,可摩勒多次为红绡背负“囊橐妆奁”,侍卫却浑然不知,可见摩勒武功之高,特别是“轻功”了得。最后,摩勒“负生与姬而飞出峻垣十余重”,让人叹为观止。
当“一品”手下发现红绡在崔生家,“召生而诘之事”,软弱的崔生轻易便把多次为其解困的摩勒出卖。50名甲士手持利器围住崔生家院,读者不禁为摩勒捏着一把汗。但见摩勒手持匕首飞出高墙,身轻如羽,迅猛如鹰,虽乱箭如雨,可摩勒却毫发无损。众人慌乱之时,其已不知去向。只是十余年后崔家有人看到摩勒在洛阳卖药,且容貌依旧。
裴铏《昆仑奴》小说一出,千百年来,一直为读者所衷爱。由于作者在创作此小说时采用了一种所谓的“虚白”手法,即用跳跃性的语言将一些内容隐去,由此而形成的空白,读者只有通过联想才可领悟,这就使这篇小说充满迷人的魅力,“小说的主人公是摩勒,可读者读完全篇对摩勒所知依然甚少,摩勒从哪里来,怎样到的崔府,他如何知道‘一品’有十院歌姬,如何知道‘一品’院中有猛犬,最后摩勒怎样生活等等问题,都没有交待”。[7]小说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与作者一同完成作品。小说由此而充满了张力,也为后人的再创作留下了大片空间。因此,明人梅鼎祚将此剧改编为杂剧《昆仑奴剑侠成仙》,明代梁辰鱼据红绡身上所具空白改编出《红绡杂剧》,与《红线女》并称双红剧。此外,京剧《盗红绡》《昆仑剑侠传》,川剧《红绡》,昆剧《击犬》《盗绡》也是据《昆仑奴》改编而成。《昆仑奴》不断被改写,除了说明原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力以及人们对摩勒形象的向往和喜爱外,原作品以诗歌的创作手法留下的广阔想象空间,为后世的创作者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余地,因此,这篇寥寥1400余字、构思精巧、情节宛转、新奇突现、引人入胜的小说也就焕发出一种常青的生命力,而摩勒这一人物形象也在这常青的艺术生命里熠熠生辉。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称唐人小说特色之一即在“传写奇事,搜奇记异”,《昆仑奴》也以“奇”著称,该小说最奇异之处除摩勒武艺高强、击毙猛犬、负主人与红绡进出“一品”府如入无人之境外,面对50甲士追捕摩勒却能从容应对,飘然突围而去,此外,摩勒又如神仙般不老,使小说更具神秘性。小说最后交代:十余年后昆仑奴又在洛阳城出现,容貌依旧,这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将昆仑奴的“奇人”“奇事”带到了另一高点。明代徐如翰《云合奇踪序》云:“天地间有奇人始有奇事,有奇事乃有奇文”,清代寄生氏《争园春序》云:“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奇人奇事俱奇,无奇人演说之亦不传”,汤显祖《点校虞初志序》亦云:“以奇辟荒诞、或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正是因为这种“奇异”手法之使用,才使《昆仑奴》充满迷人的魅力。《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第一回有这样的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之秘法亦不可少。”《昆仑奴》中的摩勒集“奇人”“奇事”于一身,小说叙事又深得叙事技法之“奇”,故千百年来能一次次拨动读者之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