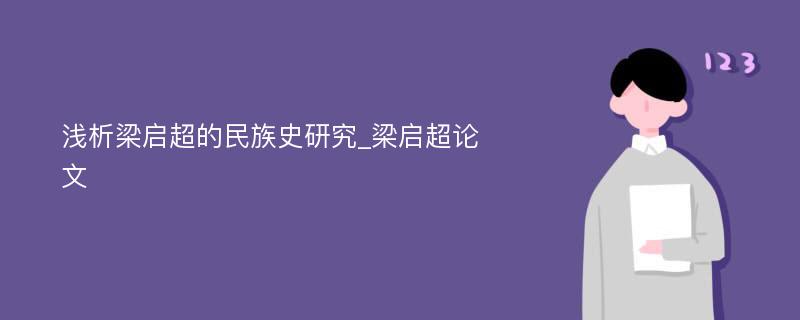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民族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7)04 —0090—06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大学者,其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多方面而又十分厚重的。就史学领域而言,学术界已有许多论著对梁氏的贡献和成就做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总结,而关于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方面的总结和论述,仍然显得零碎和不足。① 本文力图通过对梁氏民族史论著的解读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对其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成就和影响以及不足和缺陷等问题做一简要的分析,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和当前该领域学术研究的相关问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
一、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梁启超一生著述繁富,内容涉及诸多领域,但如其好友林志的所言,梁氏“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已”。[1](P9) 仔细品读梁启超有关史学论著不难发现,其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大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族”的概念问题
引进、介绍和厘清“民族”的概念问题,是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汉语“民族”一词的来源和概念问题,学术界已有多篇论文探讨,[2] 但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和学术研究话语被国人所熟知,却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僻居日本,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极大关切之情,开始大量、热情的介绍和研究西方思想文化及社会政治学说,这一过程也是他引进、介绍和厘清“民族”的概念问题的过程。首先,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多次使用“民族”一词,如“东西民族”、“支那民族”、“民族之变迁”、“民族之立国大原”等。[3](P90,94,100) 由此,“民族”一词开始大量地被引入了中国思想界。随后,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将“民族”的概念加以介绍和分析研究。在文章中第二节“论国民与民族之差别及其关系”中,梁氏首先介绍了伯伦知理民族理论关于“民族”概念的界定:[4](P71—72)
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
他接着强调“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特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4](P72) 同时, 参照伯伦知理的民族理论,梁启超还对“民族”的概念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地域与血统的标准会发生变化,同地域只是民族最初形成时的特征,而以后“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居一地”;血统更是如此,“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4](P71) 很显然,梁启超看到了伯氏将“地域”、“血统”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之一的局限性。后来,他又多次发表论著对民族一词作了较详细的学理界定。1906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语言”是区分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德国人种学大家麦士苗拉尝言:‘血浓于水,语浓于血’一时以为名言,盖谓以皮肤骨骼辨人种,不如以言语辨人种。”[5](P2) 随着梁启超对“民族”概念认识的深入他又将一直以来模糊不清的民族、种族、国民的概念加以了区分。他指出:“民族与种族异,种族为人种学之研究对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区别为标识……民族与国民异,国民为法律学研究之对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国籍之区别为标识”。[6](P1) 在谈到民族的划分标准时,他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利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达与确立。何为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而具有此意识者,即为民族之一员”。[6](P1—2) 这里,他讲的“民族意识”是抓住了“民族”几个标准中最实质的标准,基本上完成了对“民族”概念的科学解释。
(二)关于中国民族的来源问题
关于汉族即梁启超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来源问题,是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内容。
20世纪初的中国,有关中国境内民族来源问题的争论在思想界莫衷一是,而所谓“西来说”更是甚嚣尘上。对于这一问题,梁启超也做了研究和探讨。早在1901年《中国史叙论》中他就涉及了此问题,当时他认为中国汉族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但此后他逐渐改变了这一观点,而认为中国各族是本土发生的,且我族至少已在此地居住了五万年以上,至于发现并非我土所产的物品也只能作为交流频繁的证明而不能认定我族就是外来的,最终得出了“迳指彼为我之所自出,恐终涉武断也”[6](P3) 的结论。
而对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来源问题梁启超更是作了深入的探究。早在《中国史叙论·人种》中他就提到了这一问题:“今且毋论他族,即吾汉族,果同出一祖乎,抑各自发生乎,亦一未能断定之问题也。”[7)(P7) 模糊地表达了汉族不是同一祖宗血脉衍生而来的观点,此后这一观点得到了不断的明确和深化。1906年梁启超依据“语言”这一界定民族的标准,认为中华各地的语言风俗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可能是同一祖宗演化而来的,从而明确地提出了“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的论断,并通过对先秦以前八族历史的考察,对各族的起源也作了判断:“大抵诸族之起,非沿大江,则缘大河。黄河流域,则有我中华民族焉;洞庭湖,鄱阳湖,及扬子江中游灌域,则有苗族焉……夫初民之起,必沿河流,此尽人所能道矣。”[8](P12—13) 同时, 他还对各个流域上发祥的民族一一作了对应,从而明确了各族乃各自发祥的历史事实。五四时期,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依据我国多民族融合的事实进一步指出:“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起初不过小小几个部落,在山东、河南等处地方有些根据地。几千年间,慢慢地长……长……长成一个硕大无朋的巨族。”[9](P40) 而形成这一巨族的重要途径便是对“无数异族”的同化。梁启超用通俗的语言再一次明确了汉族是多元融合而成的观念。1922年他再次论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从我国古帝王各异其都,可知古代各部落都是在各地发展、各戴各的尊长,这即是多元结合的一种暗示。另外汉族自名曰夏,而“夏”前冠以“诸”,更是多元结合的一种证明,而随着“诸夏一体”的民族意识的不断深入,汉族才“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6](P4) 随后,他又通过对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详细考察,一一介绍了各族是否已融入汉族的历史事实,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汉族是吸收了众多其他民族化合而成的事实。由此,梁启超通过长时间的反复论证,对汉族是一元发展还是多元融合而成的问题给予了相当明确的答复。可以说,汉族多元起源、多元融合的论断是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核心成果和主要内容之一。
(三)关于中国民族的分类问题
梁启超在多篇论著中都对这一问题有过研究。早在《中国史叙论·人种》一节中,他就将中国史范围内的人种分为六种,分别为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古种、匈奴种和通古斯族。在《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中他又对人种做了分类,将人种分为“历史的人种”与“非历史的人种”两类,而“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10](P12) 虽然当时梁氏对种族和民族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但仍是较早地触及了有关民族的分类问题。后来随着梁启超对民族概念认识的不断完善与深化,在这一问题上逐步明确和提高。1906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将先秦以前除炎黄一派本部诸族外分为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等八族,并对各族做了简单的介绍。而至其1922年完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则对中国民族的分类认识更加深入、细致,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论层次:即将现今之中国民族分为中华族、蒙古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和突厥族等六族,而将春秋中期的古代各族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和群貊组等八组,从而着重考察各族古今演变的联系,并对每一民族的起源、族系、分布地域、发展过程、迁徙路线、生活习性和心理特征等都作了详细的探究,第一次较清晰地勾勒了中华民族发展演变史。
(四)民族间的关系问题
梁启超在民族史研究中比较重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他认为只有相互化合才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他指出:“凡一民族之组成分子愈复杂者,则其民族发展之可能性愈大。……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底亦因之加厚。”[6](P8) 在论述春秋战国历史时他也歌颂了化合的伟大作用,认为当时的兼并战争所引起的民族融合是推动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动因,他说到:“非经此阶段,则此后一流之家决无自而成”,“徐徐蒸变化合而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二千年来颠扑不破的‘中国之国民性’。”[11](P2—3) 充分表达了他对春秋战国交往、战争对促进经济交通发展、中华民族形成、统一国家建立的伟大作用的热情歌颂。在此基础之上,他还对汉族对其他民族的同化的程序和路径作了8点规律性总结, 对汉族总能为同化之主体的原因也作出了相当高度的归纳。
综上所述,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可谓是触及了近代早期民族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较为细致深入,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开创了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影响披及后世。
二、梁启超民族史学的成就及影响
梁启超的民族史学研究的成就及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轨迹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改变了古代民族史学的从属、分散的地位,促进了近代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
众所周知,所谓古代民族史充其量不过是传统政治史的附庸而已。至二十世纪初,在“新史学”的民族史研究中,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不仅使民族史基本上摆脱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且逐渐向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
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过程中十分强调民族史研究。早在20世纪初,梁氏就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民族史学的重要性。他在《新史学·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中说到:“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2](P11—12) 在《中国史叙论·人种》一节中也提到:“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13](P6) 在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又坦言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史的内容和精要,他说到:“举要言之,则中国史之主如下。第一,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族几何,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生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其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14](P1) 可见梁氏中国史构建的核心就是一部中国民族史, 中国史撰写的内容就应该是各民族发展变化的历史,对民族史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实践,民族史学才开始成为独立的史学部门并逐步走向繁荣。在梁启超的相关论著发表后,一些全局性的、综合性的民族史著作亦相继问世,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缪凤林的《中国民族史》等都是此后一个阶段中综合性民族史研究中的代表作。[15] 另外,专门性的民族史的研究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至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而正是这些成就的取得终于使得民族史学作为一个有丰富内容和学科体系的独立学科而傲立于中国史学界。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如果将中国民族史的任务和学科名称的发端归之于梁任公在本世纪初叶的大力倡导,想能为学界所认同。”[16] 诚然,是梁启超把民族史的地位上升到了中国史核心的位置,开启了从民族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这对民族史学由附庸分散的“四夷传”走向独立完整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贡献可谓是居功至伟。
(二)为民族史学注入了近代的观念,为后世确立了写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史书的编纂权一直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体现在民族史上更是如此,一直都无法摆脱以“王朝”和“民族”正统论为核心的封建民族史观和民族偏见的制约和影响。从先秦时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到司马迁的《史记》及以后历代正史、典志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记载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一话语霸权。而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和他的民族史研究,则是对传统民族史观的突破和挑战,开启了民族史观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中坚持多元、进化的民族史观,即认为中国民族的来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结合而成的。针对旧史认为汉族纯以血缘相属而成立的观念,梁启超指出:既然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就不应该出现《史记》所记三代世表出现矛盾、漏洞百出的失误,更不应该出现《诗经》关于商周之祖“无父感天而生”的怪论,由此可以知道“一元说”是不可信的。进而他又多次从多角度考察出了各少数民族在各自地区独立发生的结论,认识到了民族起源的多元性现象,从而肯定汉族不是出自一祖的历史事实,最终得出了“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7](P4) 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不断地融合其他民族,最终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割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的论断。[6](P4)
在此基础上他还认为“诸夏”与“夷狄”的概念是可变的。他说到:“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且时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6](P8) 这里他一方面说明了“诸夏”是包含了众多“夷狄”的多元混合体以外,更是指出了“诸夏”与“夷狄”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恰恰许多的“诸夏”却正是由“夷狄”转变而来的,这样就从多元、进化的角度对古代一元、凝固的正统观念发出了严厉的挑战。
同时,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也包含了民族平等的观念。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他依次论述了八族的历史、地域分布及发展演变情况,并指出:“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5](P13) 即把各族统一列入中国历史的大视角加以平等的考察和对待。另外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的开篇又指出:“本篇即五千年史势鸟瞰之一部分”,[6](P1) 更是把各民族历史置于中国五千年历史一部分的重要位置。
上述多元、进化、平等的观念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了梁启超总体的民族史观,它不仅动摇了传统的华夷观的立论基础,而且冲破了华夷之辨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正统观念,从而为客观的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可能。自此之后,多元平等的民族观成为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指导思想。20世纪30年代先后出版的几部民族史就已都认同了此观点,把民族起源发展的多元观点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② 经过多位民族史学家的反复论证和弘扬,梁启超的民族起源、发展的多元、平等观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被学界所认同,而中华民族一元论或汉族一元论的说法逐渐销声匿迹。此后,这种史观也一直指导着新中国的民族史研究,而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也可看做是梁启超首创的多元、平等的民族史观的继承和升华。[18] 另外像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等著作,同样是梁氏“各族都是中国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平等观念的继承和深化。[19]
(三)打破了古代民族史学以往的研究范式,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基本路径
古代民族史学在撰述上的一个主要的缺点就是“把主要民族一个一个地单独写出来,而没有把所有民族从总的方面去概括和论述,尽管它们对某些单个民族的论述比较系统而深入,有不少精辟的见解,成果甚丰,但由于他们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从民族总体的大角度去看,它们的视角比较狭窄。”[19](P9) 因此,古代民族史中十分缺乏对民族关系史的论述,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各族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而梁启超则十分重视从全局的观点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以分析民族间的融合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在分类论述各族历史时,他就比较重视考察各族之间交往、融合、同化的史实,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融合对于进化的伟大作用。在《春秋载记》、《战国载记》中,他更是积极歌颂了由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引起的各民族频繁交往、快速融合对历史上中华民族形成以及战国学术高峰出现等的伟大作用。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广纳而治化之,缘地运民情之异谊,卒乃孕育一新文明统系。”[20](P8) 可见,梁启超从全局的、 进化的观点对民族的融合做了考察并上升到理论的程度,弥补了以往只孤立的研究单一民族而不注重考察民族关系及所引起的结果的不足。
此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都十分重视考察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史实,并力求通过对各族交往的研究以总结出其对各民族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如王桐龄通过对汉族的几次蜕化、休养的论述详细地介绍了汉族发展壮大的历程,并用蜕化来解释汉族至今仍庞大不衰的原因,同时对族群间融合的程序做了六种分类并对汉族善与外族融合同化的原因做了探讨归纳,其研究路径是梁氏关于融合途径、原因的初步探讨的一个继续和发展。[21] 而建国后翁独健先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也对同化途径做了总结,并认识到自然的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而战争只是特殊的形式,这也与梁启超关于自然融合是普通程序的观念十分相似。[22] 可见, 梁氏在民族关系探讨中重视同化途径的探讨这一研究路径被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目前,民族史学界不仅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论文不断涌现,而且更是有专门研究断代民族关系史、区域民族关系史的著作不断面世,成绩斐然。
梁氏不仅重视对横向的民族关系的考察,更是十分注重从纵向上探讨各民族古今演变的联系。他在分类论述各民族历史时先将现今各民族分了六类,然后简单的考察了各族的历史渊源,随之又将古代民族分了八组并详细考察其古今演变过程,最后讲出其流为现今哪族。总之,从古今两方面入手考察每一族的古今流变,从时间的纵向上使人们清楚的了解各族的发展脉络。这种按族类安排史书以考察古今演变的编排方式也被后人继承下来。如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运用的“二重分类法”即以历史上之民族与现代民族各为一种分类,然后将前者连合于后者的研究方式就是受了梁启超很大的启发。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也是按类讲述每族的古今发展的。[23]
此外,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探究,改变了古代只重王朝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研究模式。梁氏的民族史研究与其“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新史学思想一脉相承,力求打破以君史和政治史为主体的旧史结构,写出真正的“民史”。因此,在对各民族历史的考察中,他较重视抛弃王朝史和民族征伐史的内容,转而对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史注入了较多的关注,关注人民的生产生活,关注与其他各族的交往,总之是关注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发展历史。此后,民族史家也都较重视挖掘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发展的历史材料,不断的丰富了“民生”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写人民群众的历史”更是深入贯彻进到民族史的研究中,民族史书中无论哪一本都少不了各民族社会历史的章节。显然,这也与梁启超在世纪初的倡导和实践的研究路径不是毫不相干的。
(四)改变了只依靠文献的传统研究手段,促进了民族史学方法上的更新
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史学的主要成就就是发达的史料学、目录学和考据与训诂,但任何史籍都是作者的主观产物,尤其是在王朝史观、正统史观占主导的古代中国社会,史籍的客观性就更不好把握了。所以,要取得相对客观的研究成果,只依靠古籍的这种从主观到主观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而其他研究手段的介入就显得必不可少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的新史学方法就要求史学研究不仅要重视文字记录的史料,更要善于借鉴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多学科多角度帮助达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而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可谓是亲自实践了这一系列新史学方法,其所使用的多种近代方法首次打破了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尴尬,并为后世史家提供了方法上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如他在文章中写道:“据近年地质学者发掘之结果,则长城以北,冰期时已有人迹,即河南中原之地,亦新发现石器时代之遗骨及陶器等多具。”[6](P3) 这显然是运用了地质学方法;再如《中国史叙论》中专列“人种”一节来介绍西方流行的人种分类法,并对中国人种作了划分,这即是把人种学也引入了民族史研究。此外他还借鉴了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指出:“吾确信高等文化之发育,必须在较温腴而交通便利之地。”[6](P5)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研究方法的介入基本改变了古代民族史学仅依靠史料进行研究的局面。
此后,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方法的指引和带动下,人们开始注重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推进民族史研究。③ 于是,在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史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的突破,使民族史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趋近于客观了。
三、梁启超民族史学的不足与缺陷
梁启超对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可谓是历史性的,功不可没,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是史观方面的大民族主义比较严重,未能摆脱开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作为标准的研究思路和模式。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开篇介绍了其民族史研究所关注的八个问题:[5](P1)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民族为何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多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迹,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迁徙交通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术以进化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关注的重点主要是汉族的问题,指导思想仍是要探讨汉族的起源、探讨汉族的组成分子、探讨汉族的发展流变、探讨汉族同化异族的程序及汉族同化力极强的原因,并对汉族日后的发展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所以可以说当时的梁启超虽然已抱着民族平等的观念来考察各民族历史,但在指导思想上他的重点无不倾斜到了汉族的一方,受阶级和时代历史的局限较大,并不能脱离当时大民族主义观念的思维定式,可以说是新时代的汉族中心论。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其研究路径也必然出现了一点偏差,总是以汉族与别的民族的“混合”与“同化”为中心展开论证。他在对各个民族进行具体论述时,总是较为重视他们融合于汉族的史实,在介绍的最后也总是要加上是否融合于汉族的结论,而其目的就是以此来论述汉族成长的过程,解释汉族是如何一步步吸收他族而成长壮大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氏的中国民族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部汉族发展史,着力于汉族的痕迹太过明显。而他将汉族与中华民族等量齐观,又表明其民族平等的不彻底与严重的局限。
另外,梁启超虽然对近代民族史学有开创之功,为后世确立了宏观的框架和模式,但在具体实践上他的民族史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其专门研究民族史的论文只有《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篇,且只是泛泛的讲了各民族的概况,没有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华民族之成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等文章中也只是稍有提及,具体的、专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在对各个民族的分别论述和古今民族的演变上错误很多”。[24](P29) 由此我们可以说梁氏对具体的民族史研究的着力并不大,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意义上的民族史学研究者。这一点,又似乎与他在其他学术领域的情形大致相埒,时代使然亦乎个人使然?
总起来说,梁启超创造性的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研究了中国民族问题,对中国民族史学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促成了民族史这个学科的独立与繁荣,更是为后世民族史研究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路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到见解也为后世做了重要示范和引导。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史著作都是按梁启超的思路写成的。而今日的民族史研究虽然已是日新月异,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看法,但基本思路仍不脱梁氏之窠臼。面对21世纪全球化中的中国和世界民族问题,民族史学研究需要哪些发展和创新?这显然已经超出了本文论题范围。
收稿日期:2007—06—15
注释:
① 目前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主要有孟祥才:《梁启超民族观简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安静波:《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安静波:《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学术交流》1999年第6期)、汪平秀:《梁启超民族思想研究》(宁夏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4月)、张子辉:《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民族史学》(《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等。
② 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各族群经过了几千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了一个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体,他曾说到:“实则中国民族本为混合体,无纯粹之汉族,亦无纯粹之满族”。林惠祥在其《中国民族史》中也表达了多元的民族史观:“今日之汉族所含成分尽有匈奴、肃慎、东胡、突厥等……今日之汉族实为各族所共同构成,不能自诩为古华夏系之纯种,而排斥其他各系,其他各族亦皆有别系之成分,然大抵不如华夏系所含之复杂”。吕思勉在其《中国民族史》中讲匈奴历史时也说到:“晋初内附武帝使居塞内者,亦辄千万落,此等非融化于汉族果何往哉?然则中华民族中,匈奴之成分,必不少矣。”
③ 如林惠祥对民族进行分类时就介绍了许多学科的不同分类法,如钦氏的人种学分法、李济的语言学生物学分法。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专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民族史,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提倡人们要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以达到相对客观的研究,而“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则是专门从考古学、人类学的方法对古史进行了重建,通过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中华民族及中国文明的发生成长等民族史问题都做了很好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