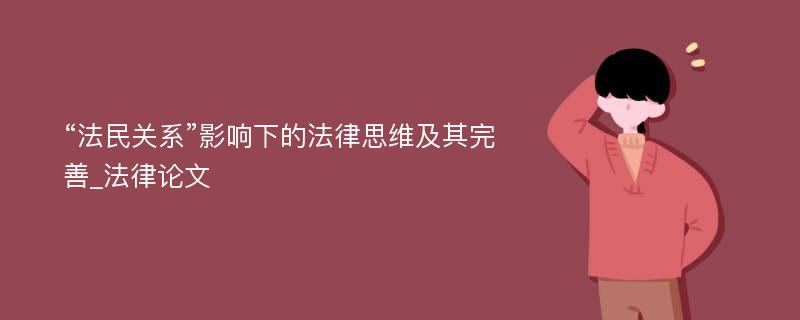
“法民关系”影响下的法律思维及其完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关系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法学界的一个流行主张,尤其是法教义学者的雄心壮志,是以法律思维统一裁判说理,通过控制法官如何思考来约束法官如何裁判,最终借助法学教育重塑中国的司法实践。这突出表现为法理学界关于“法律(人)思维”的理论争议,争议的实质是何为“理想的法律思维”。当苏力教授提出“法学院教育应当融入更多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的能力”时,①当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官在多数情况下是需要用教义学方法”时,②他们心中的理想法官显然都不是中国法官,而是美国法官和德国法官。学者们的最终分歧,在于应该以何种思维方式改造中国法律人特别是中国法官的说理方式。而部门法学者则几乎是一边倒,将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当作评价和改造中国法官裁判说理的唯一标准。葛云松教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笔者通过法律数据库读过的判决书有上千个,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许多判决。其中没有一份判决书可以令人完全满意……从一般的法律解释、推理过程来看,基本是不及格的……法官的专业能力离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法学教育的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具备理想状态下的法官应有的知识和解释与适用法律的能力。”③很显然,葛云松教授的批评源自他所秉承的“理想的法律思维”并将这种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当作对中国法官裁判说理的评价标准和改造尺度。所谓“法学教育的理想”,就是灌输“理想的法律思维”。 这些关于法律思维的论述,不论是批评中国法官“裁判不说理”,还是相信法律思维训练可以有效改变裁判说理方式在学理上都是一脉的,即认为法官怎么想就怎么说、法官如何思考就如何说理。④因此,要评价和改造现实的裁判说理,只需依据和贯彻“理想的法律思维”即可。这种观念反映的是一种典型的单线思维。心口如一、表里如一构成了学者对法官的标准想象。因此他们以为,自己读到的美国司法判决书就是美国法官的思考方式;德国的法学教科书怎么写,德国法官就怎么判案。⑤ 实际上,有待追问而非理所当然的前提性问题恰恰在于:法官怎么想与法官怎么写是否一回事?很显然,如果法官的思考与说理是两码事,那么以法律思维改造裁判说理的主张就成了无本之木。由此出发,有待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常常内外有别,究竟什么是影响法律思维的主要因素,法律思维是否仅限于法律教义和法律关系,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有何基本特征,从完善裁判说理的角度看应当如何总结和提炼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 一、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存在内外之别 法律思维(“法官如何思考”)与裁判说理(“法官如何说理”)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两相分离是常态,是许多国家司法实践的一个共性。像德国法官那样将基本的推理过程全都写入判决书中的做法反而才是特例,并不常见。⑥即使在欧陆国家,也并非都是德国式的“推理型裁判”。法国的“公文型裁判”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初看起来,法国法官的裁判说理与中国法官极为相似:“法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想方设法使判决书的内容缜密而紧凑,附带性论述一概排除;当判决基于某一理由应予撤销,其他理由便弃之不顾。另外,那种游离于正文之外的闲文漫笔从来不能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中发现,在下级法院的判决书中也很难找到;并且也不涉及案件的背景、法律史、法律政策或比较法”。⑦“法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般非常简短、概要,常常是寥寥数行或一、两节……在解释和适用制定法上往往不是证明性的,而是结论性的。它非常简单,常常只是意在陈述结论而非证明结论。”⑧比较法国、德国和美国的裁判说理字数可见一斑:论述同样的问题,法国判决300字,德国判决2000字,而美国判决则是8000字且还不包括附带的不同意见。⑨ 然而,拉瑟教授的出色研究表明,法国法官尽管对外表现为“公文型”的形式主义裁判说理,在法院内部却有另外一套极为不同的思考系统。与机械适用法律的“三段论”推理和“被动、隐形的法律代理人”这类官方形象不同,法国法官还有其“非官方”的一面。⑩法国法院在审判法官之外设有“法律顾问”和“报告法官”,他们都被称为“法官”。“法律顾问”会在案件当事人双方做完各自的陈述之后写一份“案情总结”给审判法官,而“报告法官”则不仅参与审阅案件、判决讨论以及投票,而且会将其法律意见和决议意见写成一份“裁判日志”交予法庭。“案情总结”和“裁判日志”都属于法庭的内部文件,很少被公之于众。(11)与公之于众的公文化的“官方”裁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两个“非官方”文件体现了法国法官更为完整和充分的法律思辨。从内容上看,“案情总结”和“裁判日志”虽然极少引用相关的法律文本,但是大量引用先例判决和学术论文,不仅包括对个案的不同判决结果的讨论,而且涉及对类似案件的讨论,甚至涉及有关公共政策和基本价值的考量,如人道、平等或者其他实用主义原则。写作风格也非常随意和个性化,经常使用第一人称,以对话的形式来展开对法律问题的讨论,并且毫不避讳表达个人观点。(12) 法国法官显然秉承了一种内外有别的法律思维。“官方”的裁判文书体现的是法官对外的裁判说理,而“非官方”的“案情总结”和“裁判日志”则体现的是法官内在的法律思维。两者内外有别,迥然不同。法国法官从不像德国法官那样把讨论过程和推理逻辑完整地写在判决书里。要理解法国法官的法律思维,需要在其“非官方”的司法文件中追根寻源。 美国司法也是如此。相比于法国法官的“公文型裁判”,我们可以称之为“修辞型裁判”。我们能看到的是美国法官的说理方式而非思维方式。我们所能看到的法律解释都只是其公开部分,是“那些公开陈述不会尴尬的理由”。(13)即便是大法官们的宪法解释,也是精英团体秘密商议后的公开表达,是针对美国民众的公共修辞。(14)而其个体思考和内部协商总是封闭的、秘密的——波斯纳称之为“秘密体制”。(15)实际上,美国司法也有类似法国的备忘录制度,并且也不公开。(16)更重要的是,不论是最高法院还是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绝大多数法官根本不再书写判决,而是交给法官助理来起草甚或全然代笔。(17)这意味着,美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已经彻底在人员上实现分离了。人员分离、分工负责,是最彻底的“思”与“说”分离:不仅思考的内容不会直接写在判决书里,而且连思考与说理的人员也都已经一分为二了。(18) 总之,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是两码事,常常并不一致。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内外有别,是颇为常见的法律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这既意味着通过法律思维制约和统一裁判说理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司法实践和法律思维,也意味着美、德两国法官在说理方式以及法学教育上的基本差异并非单纯的“法学方法”问题,而是有着深层的思想根源和制度支撑。 二、影响法律思维的主要因素是“法民关系” 为什么会有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的内外之别?在笔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影响法律思维的主要因素不是法律关系而是“法民关系”。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恰好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过一个困惑:为什么解释法律的人会给出一些如此荒谬的法律理由,为什么“本来有许多好的理由,他却有意识地给出一些没有道理的道理”?(19)对于这一困惑,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思维的孟德斯鸠之惑”。孟德斯鸠写道:“一条罗马法规定盲人不能进行辩诉,因为他看不见法官的服饰。本来有许多好的理由,他却有意识地讲出一些没有道理的道理。法学家保罗说过,婴儿到第七个月就已经发育完全了,而且毕达哥拉斯的‘数论’能证明这一点。用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来裁决这些事物是非常奇特的。几位法兰西法学家说过,当国王占领了某个地区后,这一地区的教堂就得由国王特权法来管辖,因为王冠是圆的……有谁看到过一种高贵显赫的真实权利是依据这一高贵显赫的记号所显露的意义而建立的呢?”(20) 这些例子涵盖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体现的正是一种内外无别的法律思维。孟德斯鸠之所以无法理解那些法律理由,是因为他自己怀有这种法律思维:“当人们为一项法律说明理由的时候,这种理由应该符合法律的尊严”。(21)但是,这些在启蒙时期不再“符合法律尊严”的理由在其提出的那个年代也是荒谬的么?如果“看得见法官的服饰”就是当时人们对法律尊严的一般认识,那么以此为由剥夺盲人的辩护权岂不是理所当然?很显然,即使孟德斯鸠的“法律尊严说”是对的,他的适用也未必正确。更何况,这一主张本身也是错的。正确的道理是,当人们为一项法律说明理由时,这种理由应该符合受众的预期。这就是孟德斯鸠所注意到的问题:这些看似“没有道理的道理”是“有意识地给出”的,而非随随便便找来的借口。因为罗马法时代的“看不见法官的服饰”、法学家保罗时代的“毕达哥拉斯的数论”以及法兰西王国时期的“王冠是圆的”,就是各自时代里最容易让受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律理由。正如理性、自由、平等、博爱在孟德斯鸠的时代成为他所欣赏的“好的理由”一样,这些理由放到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就与“王冠是圆的”在启蒙时期一样可笑,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根本不能为法律的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同样,反过来看,不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都不过是当代欧美国家的“毕达哥拉斯数论”而已。在后世或者其他地方的人们看来,也会与“看不见法官的服饰”、“王冠是圆的”一样滑稽可笑,变为“非常奇怪的”、“没有道理的”道理。例如,在秋菊眼里,孟德斯鸠式的法律理由就完全无法理喻。(22) 这其实反映了有关法律思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否存在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古今而通用的法律思维?还是说,法律思维总是因时因地而异、取决于具体时空的受众思维?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都在潜意识里将自己的学说当作普遍适用的“科学”。因此,法教义学者常常把法律思维视为与2+2=4一样的客观真理。而社科法学者也往往不假思索地把汉德公式直接用来分析中国的侵权案件。然而,“法律思维的孟德斯鸠之惑”所揭示的是,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上“正确”的法律思维,只有“适当”的法律思维。所谓“适当”,就是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符合当时当地的受众预期。 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于,预期受众决定说理方式。或者说,是“受众思维”决定“法律思维”。如果孟德斯鸠能够明白这一点,那么他本该从自己的困惑出发,分析这些法律理由在被提出时的预期受众,探究什么样的说服方式易于被他们接受,以及他们与释法者之间的相对地位如何。如果是从法律的受众预期、而不是从所谓法律的内在本质出发,那么他本该看到,决定法律思维的是法官的解释对象(说理受众)和解释地位(说理权威),即法官在裁判说理时所处的“法民关系”。 所谓“法民关系”,不是法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法律过程的参与者围绕法律解释而形成的主体间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维度就是法官在司法裁判时所处的解释地位和所面对的说理对象:法官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乃至与法律职业和一般公众的相对地位如何,哪些人是法官做出解释和说理的最重要的预期受众。(23)“法民关系”不同,即解释地位(说理权威)和解释对象(说理受众)不同,法官所必须承担的解释(说理)责任、采取的解释(说理)方式、面对的解释(说理)难度也就必然不同。 相比于法律关系,“法民关系”对法律思维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全面。法律思维是双向的,一端是解释法律的法官,一端是有待说服的受众。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官与受众的相互地位,二是两者的交流方式。法学训练乃至所有的学术训练都是单向的,最多只能改变法官一方的部分思维方式,而改变不了受众的思维模式,因此也就不能彻底改变两者的交流方式,更改变不了法官与受众的相互地位。相比之下,“法民关系”对法律思维的影响则是双重的,因为“法民关系”是双向的。“法民关系”一方面体现为法官与受众的相互地位,即法官所处的解释地位和说理权威;另一方面体现为法官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即法官面对的解释对象和说理受众。两者都深刻地影响着法官的思维方式,并制约着裁判说理展开的可能方式。据此,要理解一种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不能仅从其法律关系的单一逻辑来看,而是必须理解其“法民关系”的双重逻辑。归根结底,这就需要重新理解何为法律思维。法教义学者受到德国法学和德国司法的深刻影响,因此将法律思维仅仅理解为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甚至很多时候法律思维直接被理解为法律推理。然而,这种关于法律思维的认识过于狭隘。如果按照这一理解,不仅许多中国的司法裁判,而且不少法治发达国家如法国和美国的司法裁判,也都要被视为“从一般的法律解释、推理过程来看,基本是不及格的……法官的专业能力离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还差很远”。(24)这种德国法中心主义妨碍了我们关于法律思维的一般理解。 法律思维不仅仅是关于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的思维方式。仅限于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的法律思维,是初阶的法律思维,是单向的、一维的思维方式。这种单向、一维的初阶法律思维,表现为内外无别、表里不分的思维方式,因此将法律以外的其他维度都视为“没有道理”。信奉初阶法律思维的学者和法官易于认为,存在一种仅属于“法律人的”、仅限于“法律”的思维方式,其只能够也只应当在“法律同行”即“法律共同体”内部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律”也只能是实定法。他们对于“法律”、“法律的”、“法律人”这些概念大都持有一种单向、一维的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本质主义的理解。与之不同,高阶法律思维是多向的、高维的思维方式。这种多向、高维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内外有别、表里相辅的法律思维。高阶法律思维不仅限于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而且还要综合考虑法律以外的其他维度,特别是“法民关系”。如果说法律关系反映的是单一的、同行内部的法律人受众,那么“法民关系”反映的就是既包括法律同行也包括法律外行的复杂受众。从高阶法律思维来看,“法律人”的“法律”思维不仅限于“法律同行”内部,不仅限于解释和适用“法律”,更不限于实定法,不限于法律关系和法律教义。与法律关系和法律教义中的“法律”作狭义理解不同,“法律(人)思维”中的“法律”和“法律人”的含义是广义的。 一如前述,并不是法律思维的完整过程都会出现在判决书中。法律思维在裁判说理中常常隐而不显。要从裁判说理的文字中直接推导出法律思维的内容,往往只是盲人摸象。因此,在区分“纸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之前,应当首先区分的是“纸面上的法律”与“头脑中的法律”。纸面上的裁判理由只是“看得见的法律”,而在头脑中推动做出决定的法律思维,则是“看不见的法律”。要探究一个国家的法律思维,就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可见的法律部分,而必须深入到法官的头脑当中,对那些影响法官判断和推理的“看不见的法律”一探究竟。 三、“法民关系”如何影响法律思维 “法民关系”如何影响乃至决定着不同国家的法律思维呢?为什么德国法官的裁判说理可以大致符合其法律思维和法教义学,而美国、法国乃至中国的法律思维却与其裁判说理内外有别?这就要从各自的“法民关系”来看。 德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之所以能够表里如一,专注于法律推理、集中于法律教义、聚焦于法律关系,不是没有“法民关系”的影响,而是有其独特的“法民关系”。一方面,德国法官的说理对象和解释对象是一致的,都是法律内行,是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另一方面,德国法官处于超然的解释地位,并不直接对民众负责。德国的“法民关系”,是立法面对外行,承担法律的民主性要求;司法面对同行,实现法律的专业化要求。普通人与法律人因此被立法特别是法典隔离开。法典权威构成德国法官裁判说理的天然保障。这使得德国法官不必直接面对公众,而只是在法律共同体内部进行交流。既然是同行之间的内部交流,就如同关起门来的家庭聚会,也就易于畅所欲言,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时,对法律思维的强化训练就易于反映在裁判说理之中。总之,在这种“法民关系”下,说理与思维一样是共同体内部同行之间的交流方式,法学教育如何训练学生,学生毕业后就如何说理。这就是德国“推理型裁判”能够表里如一以及主要集中于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的主要原因。这也反映出德国司法的官僚制特征。 但是,如果受众从内行变为外行,如果法官必须面对普通人、必须面向公众说理,那么仅仅是基于法律关系的法律思维就是不够的。这种“法民关系”必然要求,法官除了常规的法律推理之外,还要能够用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做出裁判说理。易于理解,如果法官必须兼顾内行和外行,那么就很容易趋向法律推理与裁判说理的内外之别:见“法”说“法言”,见“民”说“民语”。 美国的“修辞型裁判”就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法官没有法典的外在屏障,必须直接对公众负责。即使《美国联邦宪法》的至上权威绝不亚于《德国民法典》,美国法官也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制宪机关和立法机构。美国法官不能说,自己的法律解释虽然不合理,但这是立法乃至宪法的规定存在缺陷所致,因此只能通过修改法律加以解决。美国法官必须直接承担“制造善法”的职责,而不能宣称“恶法亦法”。另一方面,美国法官拥有极高的解释权威。即便他们从来不想自己到底写给谁看,“他们写的东西趋于高出外行(诸如诉讼当事人)的理解力,而是写给他们的职业受众的”,其法律解释仍然能够获得美国民众的普遍接受。(25)因此,他们可以“法官造法”,并“超越法律”,乃至运用社会科学给出全然超出“法律思维”的公共修辞。(26)这反映了美国司法的民主制特征。因此,“修辞型裁判”的法律解释在法律推理之外还必须发展出一套说服公众的修辞技术。这种修辞技术究竟是法教义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形式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归根结底,取决于哪种技术的修辞成本更低。美国法学的社会科学取向并非偶然,并非只是从霍姆斯到波斯纳这些法律巨匠的单方面塑造,而是源于美国民众的公共偏好。(27)之所以霍姆斯说“当前的主宰或许还是白纸黑字,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28)就在于19世纪的美国人热衷于“白纸黑字”,而20世纪之后的美国人则更喜欢“经济学和统计学”。(29)最终,美国法官形成的是一种思考与说理内外有别、修辞与推理表里相辅的法律思维。(30) 类似地,法国司法尽管属于欧陆法系的解释传统,却也发展出了不同于德国模式的内外有别的法律思维。只是,法国法官的解释地位低于美国法官,尤其是法国强大的行政体系使得其司法体系处于从属地位。法国法官的“公文型裁判”也是对法国行政主导的一种顺应。通过模仿行政公文,法国法官的裁判方式也就更加易于为公众所接受。也许可以说,法国司法裁判的“公文化”实际上正是其对外行说理的修辞方式。当然,法国法官有一点与德国法官一样,那就是也有法典权威的外在防护。这就使得法国法官可以安心于对外的“公文式裁判”,同时在内部交流法律思想。法国的“法民关系”,尤其是行政力量的主导地位,使得法国法官对外展现的“官方”形象,是机械适用法律的“三段论”推理的、被动的、隐形的法律代理人。(31)这反映的是法国司法的行政化特征。 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同样是一种基于“法民关系”的思考方式。只不过,相比于欧美法官,中国法官受到外行即普通公众和普通官员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强烈。对中国司法实践有过深入了解或亲身经历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除了法律关系,总是离不开对当事人和普通民众的重重考虑。不仅在热点案件中是如此,而且在常规案件中也是如此。并且,与美国和法国的同行相比,中国法官尽管没有相应的解释地位(说理权威),却要面对类似的解释对象(说理受众)。这种中国司法裁判的受众特点,就是笔者所称的积极“法民关系”:法律外行和一般公众不愿承认法律人对法律解释的垄断,而是会积极参与到法律解释权的争夺当中。(32)处于积极“法民关系”中的中国法官,没有先知地位和法典权威可以作为屏障,只能处于当事人乃至普通民众这些法律外行的直接质疑之下,处于与法律外行近乎平等的解释地位。这种“积极法民关系”使得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必须格外注重当事人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33)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就是屈从民意。当“法民关系”中法律职业一方的压力更大时,法官也会将裁判说理更加倾向于法律关系、法律教义和法律推理。例如,在知识产权、反垄断等技术性极强的案件中,当面对的是大公司和大公司背后的专家团队而普通民众对此毫不关心时,法官的法律思维自然会倾向于法律和技术问题。即便是“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与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34)(“3Q大战”)这个“中国反垄断法第一案”,涉及两家超级公司,也备受媒体关注,但是除了少数法律和技术专家外,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大多兴趣。这就迫使法官的裁判说理更为专业化,更多回应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但是从“法民关系”的角度看,这与中国法官通常侧重对外行说理的法律思维是一样的,都是特定“法民关系”的产物。 一般而言,法律思维总是处于特定的“法民关系”中,受到法律教义和民众情感的双重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特定的“法民关系”下,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给法官施加的现实压力究竟怎样,要求法官侧重哪一方面的说理要求。一般而言,基于“法民关系”的法律思维是,“法民关系”中“法”与“民”哪一方面的压力更大、需求更强,法官在思考时就会侧重哪一方面。(35) 总之,特定的法律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法律人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法民关系”。这是不同国家各自形成适合本国司法实践的法律思维的共同原因。 四、“法民关系”影响下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如何展开 “法民关系”如何塑造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笔者拟以“张学英诉蒋伦芳案”(36)(以下简称“张学英案”)为例,通过对“张学英案”二审判决书的解读和分析来展现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之所以选择“张学英案”,是因为该案是一个探讨法学方法、法律思维所绕不开的经典案例,(37)而该案的二审判决书在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如何基于当时当地的“法民关系”来给出相对稳妥的判决理由。 另外必须予以强调的是,选择本案作为中国法官法律思维的例证,也不是因为其裁判说理完美无缺——本案在学术上和社会上的争议一直很大,而是因为本案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法官法律思维的难得机会。一如前述,法律思维隐藏在裁判说理之中,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也是如此。在绝大多数常规案件中,由于裁判说理与法律思维的分离特征,因此我们很难看到裁判说理背后的法律思维。加上中国司法没有类似法国的“裁判日志”制度,这也导致在常规案件中研究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当法律教义与民众情感发生严重分歧时,运用什么样的法律思维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正是在法律教义与民众情感产生严重分歧的地方,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才会充分显现出来。如同火山喷发会敞开地表,我们也得以从那些重大、热点案件中看到通常隐而不显的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只不过,这里区分“常规案件”与“疑难案件”的主要依据并非单纯的法律关系,而是双重的“法民关系”。实际上,如何区分“常规案件”与“疑难案件”,也正是一种法律思维的要害之所在。不仅法教义学不会赞同社科法学擅长处理“疑难案件”的主张,所有法学方法和法律思维都有自己的独特界定。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以“法民关系”的分裂程度作为区分“常规”与“疑难”案件的首要标准。“法民关系”意义上的所谓“疑难”,归根结底是“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这些重大、敏感的“疑难案件”,有机会将高维的法律思维在低维的裁判说理中部分或全部展开。 “张学英案”就是这样一个将高维的法律思维在低维展开的案件。本来,对于这类触动社会深层秩序的“疑难案件”,法官的通常做法都是尽力避免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如“彭宇案”的二审以调解结案,就很典型。然而,在本案发生的当时当地,双方当事人已然势如水火,法律意见与社会舆论激烈冲突,法官面前已然没有了调解空间,留给法官的只有判决这一个办法。 作为一个已将全国民众卷入其中的案件,本案的“法民关系”在微观结构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案的受众已经不仅是案件当事人,甚至不仅是泸州市本地人,而且是全国各地关注本案的普通民众。“法民关系”的这一显著变化,意味着判决的结果和理由,主要不是为了说服案件当事人,而是必须能被这个国家的大多数社会公众理解和接受。同时,这一举国关注的热点案件也必然为法律同行所格外看重。法官的裁判理由,因此要经受当事人和全国公众、代理律师和所有同行的多重检验。本案的“法民关系”决定了法官必须给出一个能够兼顾民众诉求与法律规定、协调法律教义与民众情感的判决理由。 一方面,面对举国汹汹的民意,法官首先要做的是给出一种“最少冒犯公众”的判决理由。不理解这一困难处境,一味批评法官没有遵照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的法律思维是极不负责任也极不厚道的做法。法官面临的困难首先是判决结果对于普通人的可接受性。不论其判决理由如何,不难想见,但凡法官判决张学英胜诉,这一判决以及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乃至全国法院系统的公信力都将荡然无存。因此,法官实际上只有一个判决结果可以选择:判决张学英败诉。那种以为法官应该对抗民意、表现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人不仅幼稚和愚蠢,而且显然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思维。学者们应当关注的,不是我们是否赞同这一案件的民意取向,而是要从中看到什么是中国法官在处理重大、敏感案件时的法律思维。法官面临的困难还在于,如何给这样一个结果已定的案件找到普通人可接受的判决理由。考虑到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不难想见,不论是搬出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都无济于事。再充分的“教义分析”,不论概念有多严格、逻辑有多严密、体系性有多强,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听来都会与“王冠是圆的”一样滑稽可笑。同样,不论是调动科斯定理还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也都不过是老百姓眼里的“毕达哥拉斯数论”罢了。这时的法官也许有很多理由可讲,但是他们根本没有长篇大论、摆出所有理由的余地。只要这些法官没有糊涂到孔乙己的地步,就不会以为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要比“一种写法”更有说服力。最少冒犯公众的理由,只能是公众自己的理由。(38)另一方面,法官还必须确保给出的是“最小扰动法律”的判决理由。中国法官清楚自己的“法律人”职责,还必须坚持法律思维,不能直接把老百姓“反对包二奶”的主张径直写在判决书里。法官还必须“找法”,必须给出足以体现和容纳民情的法律依据。法官必须是一个好的“翻译”,能够把民众“反对包二奶”的外行诉求,转化为“保护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主张。 以下就是本案法官诉诸《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公序良俗条款”(第7、58条)入手,取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原则”(第2、3、4条)的法律思维。法官在判决书的结论部分,用了很大篇幅来表明,依据《民法通则》判决本案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民法通则》为基本法律,依《立法法》第5章之规定,上位法效力高于下位法效力。《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在法律体系中仅次于《宪法》,高于一般法律、法规和规章;后者若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应适用《民法通则》。加之《民法通则》是对我国民事法律基本制度的规定。故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在适用各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应结合适用《民法通则》相关规定,遗嘱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除应当具备继承法所规定的有关构成要件外,还必须符合《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39)更为重要的是,本案的法官并没有宽泛地适用《民法通则》的“公序良俗条款”,而是做了极为重要的限定:《民法通则》第7条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往往是模糊不定的,而此处的社会公德已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是一种被法律予以认可的较为固定的事物,因而是有强制力的,违反此种社会公德的行为依法应为无效民事行为。紧接着,法官就用《婚姻法》第2条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第3条的“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以及第4条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清楚界定了什么是本案所谓的“被法律予以认可的较为固定的事物”。(40)这是明明白白的法律条款,也是实实在在的民众意愿。这未必是三段论和法教义学的逻辑,也许是社会科学之外的道理,但这还真就是孟德斯鸠所讲的“没有道理的道理”。那些批评本案以德入法的学者没有看到因而没能正确看待法官在法律解释上所做的努力。这些批评者甚至没有阅读法官的判决书就做出了自己的“复审”判断,他们才是以德入法、才是被自己过于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冲昏了头脑。先进的法教义学应当能够提出更为细致的法律分析,但是不应忽略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找法”的努力和对法律的尊重。 总之,从中国自身的司法实践出发,我们很容易看到,不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都不是“中国法官”的思维方式。这固然是学者们致力于学术拯救的原因之所在。然而,从实际的“法民关系”出发,综合考虑法律教义与民众情感,寻求法民兼顾与情法协调,这就是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41) 五、完善中国法官法律思维的学理路径 本文希望能够增进法学界对于中国法官法律思维的深入理解。这一理解不仅是颠覆性的,而且是建设性的。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出于对裁判说理的完善,应当如何总结提炼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以及对此学者能做什么。 本文质疑了通过法律思维训练改变裁判说理方式的理论依据。由于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相分离,更由于中国现阶段特定的“法民关系”,德国式的法教义学和美国式的社会科学尽管在学理上颇有启发却很难在实践中、特别是法官的裁判说理中直接运用。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已经臻于完善。这只是表明,完善的方向不是简单地引入更多的国外法学训练模式,不是用各种格格不入的方法继续干扰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那么,应当如何呢?学者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研究中国法官现有的裁判说理,发掘出更多优秀的裁判文书从中总结和提炼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吏为师”! “以吏为师”是法家的主张,(42)历来受到批判。(43)然而,从法治的发展规律和法学的成长历史来看,“以吏为师”是再自然不过的法学成熟的必由之路。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每天在判案、写判决书的法官不知道该如何思考和说理,反而是一天案子没判过、一个字的判决没写过的学者,拿着国外的教科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指手画脚。相比于“以师为吏”的“教鱼游泳”,(44)“以吏为师”才是法学发展的正道。正如欧美法官的法律思维提炼自其司法裁判,我们同样也可以从中国法官的裁判说理中管窥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 “以吏为师”不是要把所有法官的所有裁判都当成范本,而是要从其最为优秀的司法裁判中提炼法律思维的典范。实际上,不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其法律思维的来源也是其本国司法实践中极少数法官的优秀经验。社科法学的法律思维,就是对霍姆斯、卡多佐、汉德等极少数杰出法官思考方式的总结提升。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虽然更多来自法学教授的归纳提炼,但是所设想的也是理想法官的思考方式。法律思维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法律思维不是所有法官乃至法律人思维的最大公约数或者交叠共识。法律思维是高于法律人平均水平的规范性的思维典范,是理想法官的理想思维方式。因此德沃金在描述这一法官形象时,直接以一个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来命名。(45) 同样道理,我们也应当从中国法官的优秀判决中总结提炼出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的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给予理论升华,再通过法学教育,以之培养和塑造学生以及职业法律人。我们要克服把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直接相等同的简单思维,但是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全然否定法律思维对裁判说理的任何作用,甚至否定法律思维本身。尽管中国的法律人不具有德国式的法律思维,也不会“像美国法律人一样思考”,却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国法官自己的“法律思维”,不能“像中国法律人一样思考”。正如文本所努力揭示的,“像中国法官那样思考”植根于当代中国的“法民关系”,因而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既不是单纯考虑“法律关系”,也并非贸然“超越法律”,而是必须充分考虑法律人与当事人、法律人与普通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寻求法民兼顾、情法协调的法律思维。这意味着,对优秀法官和优秀判决的判断标准,不应是德国式的法教义学标准,或者美国式的社会科学范式。否则,就还是“以师为吏”,“换汤不换药”。试想,如果教的还是法教义学的那种法律思维,必然(如同葛云松教授所抱怨的那样)找不到合适的中国案例。就是找到了,“半吊子”的中国案例也不好用,反而不如直接用德国“原汁原味”的案例更有效率。同样,如果完善中国法官法律思维的出路就是找一些具有社会科学思维的中国案例,那还不如直接翻译美国法官的案例来得痛快。 总之,学者必须清除自己由于长期研习欧美法学而形成的认知偏见,从中国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求出发,找到真正适宜中国法官运用的法律思维。就本文的研究来看,优秀的司法裁判需要对案件的“法民关系”有着清醒认识和敏锐预判,能够有效避免一个常规案件由于处理不当而激化成为“重大、敏感案件”,以及在迫不得已面对“重大、敏感案件”时能够兼顾法律教义与社情民意,尽可能给出让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一如前述,这不是通过简单阅读判决书的文本就易于看到的。法律思维的总结提炼离不开学者的理论工作。而这也正是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和职责所在。一方面,法律思维尽管是不可见的“头脑中的法律”,却依然会在裁判说理中留下蛛丝马迹。法律思维既源于也化身于裁判说理。正如谢晖教授所说:“无论如何,法官总会或多或少地把他处理案件的思维路径、思维方式、判决理由、判决结果以及判决的技术因素等等,在判例中得到呈现的”。(46)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是否愿意从中国法官的真实裁判出发从而读懂中国的法律思维,我们是否愿意放宽对法律思维的狭隘界定,将之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法官基于“法民关系”而非仅仅法律关系的典型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从中国的司法裁判中发现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要从“看得见的法律”中发现“看不见的法律”,要从“纸面上的法律”发现“头脑中的法律”,还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有格外的手眼,能够“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毕竟,法律思维不是法学家的臆造,而是对司法实践中的裁判说理方式的学理总结,“是对法律方法之知识对象——法律、特别是判例的知识加工……法学家通过加工、提炼、总结、升华而得出的法律方法,应当是对这些材料的一个命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法学家的法律方法,就是对法律家法律方法的重新命名而已”。(47)中国的法律思维,也应当是中国法学家对中国法律人在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方式的归纳、总结和命名。 如今,中国的法官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并且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是继续站在他们后面批评他们,还是不断跑到他们前面阻拦他们,抑或尽快加入他们的队伍帮助他们?中国的法学学者正在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中国的法治进程和社会发展将对中国法学学者的选择做出最终的审判! 注释: ①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4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②孙笑侠:《法律人思维的二元论——兼与苏力商榷》,《中外法学》2013年第6期。 ③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④实际上,国外学者也常常持有这样的误解,波斯纳就严重误解了这一差别。他在批评法律形式主义的时候,就是将法官如何说理径直当作了法官如何思考的证据。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6页。 ⑤参见王春业、张忱子:《论法官的依法裁判——兼论法教义学方法对法官裁判的意义》,《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⑥这也是只有德国的法学教育需要长达十年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德国法学教育和裁判说理的特点,反映的是德国“法治国”的“法理型支配”方式。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的类型》,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4页。 ⑦[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⑧张志铭:《司法判决的结构和风格——对域外实践的比较研究》,《法学》1998年第1期。 ⑨参见张志铭:《司法判决的结构和风格——对域外实践的比较研究》,《法学》1998年第1期。See Michel Troper,Christophe Grze-gorczyk,Jean—Louis Gardies,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France,in Nell Mac Cormick and Robert Summers eds.,Interpreting Statute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1,p.172. ⑩See Mitchel Lasser,Judicial(Self—)Portraits:Judicial Discourse i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104 Yale Law Journal,1325,1327~1328(Apr.,1995). (11)See Mitchel Lasser,Judicial(Self—)Portraits:Judicial Discourse i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104 Yale Law Journal,1356~1357(Apr.,1995); Mitchel Lasser.Judicial Delibera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J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Legiti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988~1300. (12)See Mitchel Lasser,Judicial(Self—)Portraits:Judicial Discourse i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104 Yale Law Journal,1362~1363(Apr.,1995); Mitchel Lasser.Judicial Delibera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J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Legitim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1029~1300. (13)[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14)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15)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16)法官助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法官撰写备忘录。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17)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8页。 (18)实际上,中国法官在人员分工上也在日益转向思考与说理、判断与写作相分离的司法体制。一种典型的组合方式是,资深法官负责思考和判断,助理法官负责撰写裁判文书。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员额制”设计。客观上也会导向和强化这一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在人员上相分离的司法模式。 (1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8页。 (20)[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8~299页。 (2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8页。 (22)参见凌斌:《普法、法盲与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23)参见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4)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25)[美]理查德·波斯纳:《波斯纳法官司法反思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页。 (26)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2~606页。 (27)See Barry Friedman,The Will of the People:How Public Opinion has Influenced the Supreme Court and Shaped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0,pp.14~17. (28)Oliver Holmes,The Path of the Law,10 Harvard Law Review 457,469(1897). (29)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那样:“在经济学领域,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科学修辞蒙人的潜能特别巨大”。[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0页。 (30)美国法官的公共修辞,从最近引起全球热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合法”的判决中可见一斑。不论是多数意见还是异议意见,都为美国民众乃至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所津津乐道。人们因为大法官们的公共修辞而已然忘却了判决书中的判例援引和逻辑推理,甚至连法律人也都不关心那些技术问题。这鲜明地体现了美国“修辞型裁判”内外有别的特点。 (31)See Mitchel Lasser,Judicial(Self—)Portraits:Judicial Discourse in the French Legal System,104 Yale Law Journal 1325,1402~1403(Apr.,1995). (32)参见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33)尤其在民事和家事领域,“法民关系”对法律思维的影响最为明显。实际上,“法民关系”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不仅仅体现在不同法系以及法域之间,在一国内部的不同法律领域、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法民关系”也会有所不同。对法律思维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应当将这些“法民关系”的差异性考虑进来。 (34)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35)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法律思维侧重“法民关系”中的某一方面,并不意味着裁判说理必然也会侧重同一方面。这就是前文强调的法律思维与裁判说理的内外有别。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在法律思维上侧重教义分析,在裁判说理时反而会避免过多的法律解释。 (36)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 (37)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案件能够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法学争议。围绕这一案例产生了大量的论著,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何海波:《何以合法?对“二奶继承案”的追问》,《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郑永流:《道德立场与法律技术——中德情妇遗嘱案的比较和评析》,《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金锦萍:《当赠与(遗赠)遭遇婚外同居的时候:公序良俗与制度协调》,载《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314页;萧瀚:《被架空的继承法——张××诉蒋伦芳继承案的程序与实体评述》,载易继明主编:《私法》总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13页。 (38)正如波斯纳所说:“老道的修辞家会在听众现有的信仰与自己希望诱使听众接受的信仰之间精心构筑桥梁”。[美]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3页。 (39)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 (40)参见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 (41)实际上,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不仅体现在裁判文书中,而且体现在调解过程中。如何从司法调解中提炼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是另一个也许更具根本意义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即便在判决书中,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也贯彻了调解的实践智慧。如果非要命一个名,那么相比于德国式的“推理型裁判”、美国式的“修辞型裁判”和法国式的“公文型裁判”,中国法官的法律思维是一种“调解式裁判”。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42)参见赵晓耕:《韩非子》,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22页。 (43)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06页;李力:《从另一角度审视中华法系:法家法律文化的传承及其评判》,《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宋晓:《普法的悖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44)参见冯象:《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读书》2002年第2期。 (45)参见[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46)谢晖:《判例阅读与法律方法论之展开》,载广州市法学会编:《法治论坛》第1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页。 (47)谢晖:《判例阅读与法律方法论之展开》,载广州市法学会编:《法治论坛》第1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