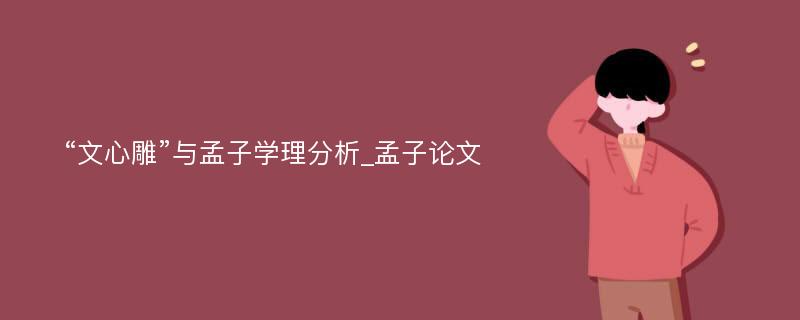
《文心雕龍》與孟子學說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文心雕龍论文,學說論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齊代劉勰所著的《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代表作品。《文心雕龍》之于孟子學說,關係較爲複雜。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于孔子可謂五體投地。《序志》中自叙:“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至于全書中的頭五篇作爲文之樞紐的原道、徵聖、宗經中更是竭盡對于孔子學說的禮贊,並且將孔子的文論思想貫徹到文體論與文學評論之中。
班固《漢書·文藝志》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爲子書,但東漢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爲《孟子》是“擬聖而作”。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漢代人已經把《孟子》一書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劉勰繼承班固的看法,將孟子列入子書之中。在《文心雕龍》的《諸子》中,劉勰提出:“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劉勰對于諸子雖然不及列入聖人的孔子那様崇敬,但是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認爲他們是“入道見志之書”。在《諸子》中,劉勰將孟子與莊子並列評論:“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蜂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于地利,騶子養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勛,尸佼兼總于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禄而餘榮矣。”劉勰對于作爲諸子的孟子給予較高的評價。在《時序》中,劉勰又指出:“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飈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這裏將孟子、荀子相提並論,稱贊他們在戰國時代文章才學的卓越,開一代文學風氣。
劉勰在《文心雕龍·諸子》中,還對孟子和諸子的文章風格特點進行評價:“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和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奥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泛采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劉勰慨嘆:“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可見,對于諸子懷才不遇,發憤寫作的遭際,他是深深同情的,其中也不難見到他的自嘆。
不過,劉勰認爲,從治國之總綱來說,諸子之學只是一孔之見,無法與江海之行,日月之明的五經相比。他指出:“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孟子的地位,也無法與孔子比肩。在《奏啓》一章中,劉勰對于諸子頗有微詞:“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爲文,競于詆呵,吹毛取瑕,次骨爲戾,復似善駡,多失折衷。”劉勰將孟子與墨子相提,認爲他們攻詰對方有些偏激。《論說》中還指出:“暨戰國争雄,辨士雲涌;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顯然,劉勰對于辨士是有微詞的。
通檢《文心雕龍》全書,對于孟子一直用孟軻的稱謂,並没有稱孟子,可見,在劉勰對于孟子缺少後世那樣的亞聖敬畏心態。
那麽,是否可以據此說,《文心雕龍》之于孟子學說就是缺失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通過對于《文心雕龍》內在思想邏輯進行深入分析,便可以發現,孟子的思想學說,特別是他的文論思想,對于《文心雕龍》的浸潤與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並不亞于孔子的思想學說。孟子的憂患精神、批評精神,以及知言養氣、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思想學說,深入到《文心雕龍》的文學批評語境中,融入到劉勰的文學批評體系之中,成爲劉勰從事文學批評的內在精神動力與思維方式。有的地方劉勰直接引出孟子的學說,有的地方雖然没有直接說出,但可以明顯地看到孟子的影響所在。包括孔子、孟子與荀子在內的儒家思想學說,與六朝時代的玄學、佛學一道,構建成《文心雕龍》博大精深又多元融合的思想體系,沉潜著深厚的人文藴涵。關于《文心雕龍》與孟子學說的關係,雖然有一些片斷的研究成果,但没有系統的考論。因此,筆者擬從這樣幾個層面去加以系統之探討。
一、孟子的憂患精神與劉勰的文學批評
憂患精神的强烈是從孔子、孟子到劉勰從事創論的共同血脉,體現出一種精神傳統,生生不息,孕育出《文心雕龍》這樣的文論巨典。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自叙作《孔子世家》:“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于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司馬遷這裏强調孔子擔憂禮樂文明的斷裂,爲此修訂《春秋》,整理《詩》、《書》、《易》等經籍。司馬遷又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孔子坦陳自己的憂慮:“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這種憂患精神在孟子那裏更加張大了。孟子與荀子不同,荀子是隨順時代的人物,他申張王權,擁護一統,鼓動變革,順應時代,提出“法後王”的政治主張與“化性起僞”的人性論。而孟子則立志于法先王,激勵性善。
據《史記·孟荀列傳》記載:“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生當戰國中葉,早年與孔子一樣,游說于各國,推銷仁政,但是被梁惠王認爲“迂遠而闊于事情”,受到冷落。晚年與孔子同樣,“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中將孟子與荀子列入《諸子略》中的儒家類,著録曰:“《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指出:“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耻没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趙岐强調孟子出于憂患意識在當時而著書立說。而孟子的這種憂患意識與傳道精神,直接繼承了孔子的人格與思想。
孟子稱贊孔子在亂世中作《春秋》以興廢繼絶的魄力:“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孟子十分欽佩孔子的這種文化批判的勇氣與魄力,並且提出要效法孔子對于當時的邪說進行批評: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孟子對于當時楊朱與墨翟的看法並不見得正確,但是他的這種批評精神與勇氣却是有其價值的。劉勰《文心雕龍·史傳》中亦傳述孟子之言,指出: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静居以嘆鳳,臨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于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可見,劉勰認爲《春秋》是孔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而寫就的。
孟子的憂患精神,培養了劉勰與韓愈等許多文論家的憂患精神,這種精神傳統是孟子文論思想中的靈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没有提到孟子作書,是因爲孟子生前没有留下著述,同時也没有遭受那麽多的苦難,但是我們可以說,孟子內心的憂患精神與批判精神却是更爲强烈的,所以孟子地位到了唐宋時代上升,韓愈在《原道》中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愈倡導道統說,認爲孟子在儒家道統的傳承中功不可没。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爲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朱熹在《孟子序說》中指出:“揚子云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朱熹强調孟子的可貴在于他的憂患與批判精神。
孔子與孟子的憂道精神,在劉勰那裏得到了傳承與光大。在《文心雕龍》一書的布局中,我們看到了劉勰仿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其一不用的思路,將《序志》篇作爲全書的總結,與其他的四十九篇相配合,從中見出他寫作此書的苦心孤詣。漢魏六朝是文學自覺的時代,文學創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文學批評也發展起來,出現了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等文論專篇。這些都是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歷史資源。當然,僅僅從時代的必然性還遠遠不能說明與評價劉勰的貢獻與意義,還應當看到劉勰在當時整個浮靡文風中的毅然决然地擔當起文學與文化批評的責任,以儒家當仁不讓的精神、人格去從事寫作的可貴之處。劉勰自己在《文心雕龍》的《序志》中是這樣叙述的: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這段引文中的“豈好辯哉?不得已也”,顯然是從《孟子·滕文公》的“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引用而來的,這說明孟子的憂患意識與批判精神在劉勰那裏是多麽强烈而真誠。劉勰自覺地將自先秦孔孟那裏繼承發展而來的憂患精神用來從事文學批評,他自叙《文心雕龍》的寫作時說: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
這說明劉勰對于漢魏以來論文發展的態勢以及短長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是自覺地擔當起文藝批評的社會責任,傳承了先聖的憂患意識,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體驗,從而寫出了這本流傳不朽的文論經典,使漢魏以來的文學批評達到極致,彰顯出中國古代優秀文化經典中人品與文品的一體性品格。今天我們解讀這本經過時間考驗的優秀經典,首先要傳承的不僅是具體的論述,而是這種把生命體驗與文論寫作融爲一體的精神境界。
劉勰的寫作《文心雕龍》的動機,蓋源于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孟子·盡心下》記載:“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提出士的人生志趣與追求即是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的結合,這一人生理想也深刻地影響到劉勰對于人生與寫作的選擇。劉勰早年入寺是爲了“待時而動”(《程器》),立志有所作爲,但是到了晚年又重回定林寺,這個結果無疑帶有一種悲劇的意味。東晋南朝是一個非常看重門第的時代,高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權,可以“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禇淵王儉傳論》),寒門庶族在仕途上往往受到歧視,地位也不穩定,士庶之間有著嚴格的區別。劉勰在《文心雕龍》的《程器》篇中就透露出這一點,所謂“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外,在《諸子》篇中,他感嘆自己“身與時舛”,在《史傳》篇中又批評史家不能“按實而書”,任意褒貶,所謂“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其實也有借題發揮,寄寓身世之意。劉勰在《程器》中提出: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這正是劉勰的夫子自道。他提出的“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顯然是演繹孟子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劉勰自叙他在無法實現“奉時以騁績”的願望時,只能“獨善以垂文”,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寫作中,這就是他在《序志》篇最後所說的“文果載心,余心有寄”。劉勰的人生與寫作歷程,正是傳承了自孔子開拓的“詩可以怨”與孟子“窮則獨善其身”,以及司馬遷“發憤著書”的傳統,《文心雕龍》作爲經典的傳承性首先來自于這種優秀文化精神的澤溉。
二、“知言養氣”與文學批評
《孟子·公孫丑上》記載孟子與他的學生公孫丑有一段對話: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
孟子在回答學生公孫丑的問題時,坦言自己擅長知言養氣,養“浩然之氣”。“氣”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是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基本範疇,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氣”的概念已被廣泛運用。《管子》中的《心術》、《內業》諸篇(據郭沫若考證爲宋妍、尹文學派的著作),提出“精氣”說,以爲天上的星辰、地下的五穀,以至鬼神、聖人都是精氣變化而成。這可以說是氣本論的先導。孟子坦言自己善于養氣,而這種浩然之氣的內容便是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正氣,並且由天地而及于人身,與人的道德禮義相結合,成爲人自身特有的秉賦與後天修養相結合的産物。養氣說對于文學藝術的批評産生了積極的影響,它倡導文學活動必須以浩然之氣與天地之氣相配合,通過擴充自身的道德修養來充實文學之美,故孟子在論人格之美時提出:“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所謂“充實之謂美”,即是謂道德修養充實之美,它依靠陶養“浩然之氣”來獲得。
孟子之後,東漢的哲學家王充認爲人所禀受的元氣的精粗厚薄决定了人的强弱、壽夭、智愚、善惡、貧富、貴賤。漢代以後,在文藝領域,最早引入氣本論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寫了《典論·論文》,提出:“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氣分清濁,這是元氣論的觀點。人禀受元氣的精粗厚薄决定了人的個性,因此是天賦的,“不可力强而致”。曹丕爲了論證這一點,用音樂來比喻:“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唱歌與吹奏都是要“引氣”的,各人所禀受的氣是天生有別的,而氣同聲音是有直接聯繫的,這就引出了發音巧拙的不同。
劉勰《文心雕龍》論氣,吸收了孟子論“浩然之氣”與王充的養氣說,强調作家從事文學創作時的道德修養以及個性氣質要兼而善之。在《風骨》篇中,劉勰提出:“《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劉勰將氣視爲作家內在道德修養與個性氣質的統一體,認爲《詩經》中六義的風教乃是作家志氣與教化功能的內涵與動力,故作家的養氣是很重要的,他在《體性》篇中提出:“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而先天的才氣須與後天的學習相結合,養氣自然也就不單是生理的範疇,而同孟子所謂養浩然之氣相結合了。在《風骨》篇中,劉勰强調,那些詩文中風骨剛健,氣調不凡的,大都與養氣相關。他說: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劉勰從曹丕的文氣說出發,明確指出“風骨”實际上是作家“重氣”的表現,它體現在“文章才力”上,如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風骨”具有一種由作家內在的生命力所表現出來的精神氣質之美。《雜文》中指出:“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劉勰針對當時浮華綺靡的文風,倡導一種生動感人、明朗剛健的理想文風,這是他提出風骨論的意義所在。
王充的養氣說,與孟子既有相關之處,又有不同之處,孟子是從主觀精神修養上去談養浩然之氣的,王充則引伸到養生的角度上。王充論氣,不僅强調氣一元論,强調元氣乃天地萬物與人類的本體,而且從主觀角度提倡養氣。他在《論衡》的《自紀》中提出:“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時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劉勰既傳承了孟子的養氣說,同時也吸收了王充的養氣說,並且巧妙地與文學創作心理學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劉勰的時代,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批評經驗,其中陸機的《文賦》涉及文學創作心理過程中的虛静原理,即“伫中區以玄覽”等論述。劉勰深契于文學創作心理之奥秘,爲此他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專門寫有《養氣》篇,提出: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
劉勰首先認同王充《養氣》中對于人的性情之理的分析,認爲人的精神與寫作狀態是直接相關的,必須把握其中的道理。他總結了曹丕與陸機等人的論述,提出:“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嘆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于文也,則有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劉勰分析學問與文學寫作有不同之處,學問需要刻苦與積累,因而用功是必須的,但文學創作則不需要如此刻苦,而且這種刻苦會影響寫作的心態,所以需要提倡一種從容自如的申寫心志,吟咏情性。何况,這種創作有著許多作者無法控制的因素,文思的開塞運作非自己所能知曉與控制,既然如此,還不如從容應對,任從自然爲妙。
劉勰《文心雕龍》中有《養氣》、《附會》、《總術》三篇,是對整個創作論的補充和總結,而《養氣》篇所論,則是對《神思》篇中所說的“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的發揮。由于靈感的來去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所謂“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所以作家應該静心養氣,保持最好的精神狀態,爲靈感的到來創造條件。清人紀昀對這段話有一個批語:“此非惟養氣,實亦涵養文機。《神思》篇虛静之說可以參觀。彼疲困躁擾之餘,焉有清思逸致哉!”所見極是。黄侃在《文心雕龍札記》中進一步指出:“恒人或用養氣之說,盡日游宕,無所用心,其于文章之術未嘗研煉,甘苦疾徐未嘗親驗,苟以養氣爲言,雖使頤神胎息,至于百齡,一旦臨篇,還成岨峿,彥和養氣之說,正爲刻厲之士言,不爲逸游者立論也。”劉勰反對“鑽礪過分”,主張“率志委和”,這是針對在創作過程中思路不暢的情况而言的,並不意味著作家可以不做艱苦的努力。總之,從孟子開啓的養氣說,中經王充的養氣說,一直到劉勰《文心雕龍》的《養氣》篇,標誌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在總結文學創作經驗的同時,在汲取哲學思想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展。
三、孟子的“以意逆志”與劉勰的知音說
孟子時代,《詩經》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于《詩經》的闡釋,大都依據人們各自的需要與理解而進行。孟子本人也是一位主觀精神很强的思想家。從現在流傳的《孟子》一書來看,孟子是自覺地運用《詩經》來解說政治和人生,爲他的仁政思想服務的。基于這一思想觀念,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詩學闡釋觀念,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古代詩學。
《孟子·萬章上》記載了孟子和他的弟子咸丘蒙討論上古堯舜時代一些政治傳說的對話。其中有一段這樣的記録: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從《孟子·萬章上》全篇的內容來看,是討論堯舜時代社會與政治一些傳說情景的,其中有著許多臆測與主觀發揮的成分,因此,對于其中引用的《詩》、《書》也就難免有著主觀理解的成分在內。這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因爲所討論的問題本身就含有許多傳說的因素在內。但咸丘蒙却犯了膠柱鼓瑟的毛病。他向孟子提出,舜因爲堯是一位賢王,所以在堯活著的時候始終没有當天子。而賢明的天子以孝治天下,是不能以自己的父親瞽瞍爲臣子的,但是《詩經》中却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的說法,這豈非自相矛盾?孟子一方面向他解釋,國無二君,舜既爲天子,舉天下而奉養父親,以瞽瞍爲臣並非不孝。另一方面提出,《詩經·北山》是說別人都能奉養父母,而自己却成天忙于公事,不能盡孝,心有所不平。因此詩中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有所指的,也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如果照咸丘蒙的理解,《詩經·雲漢》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遺”,豈非是說周初經過一場灾害之後,没有剩下一個活著的人了?可見咸丘蒙的理解太過于死板了。孟子提出的這一說詩觀點,藴涵著很深的詩學思想。
首先,孟子提出了詩有“文”和“辭”、“志”三方面的要素。它們是一個依次遞進的關係。“文”是表面的文字,“辭”則是詩句結構,而“志”則是“文”與“辭”後面的深層的精神意藴。孟子强調三者當中“意”是最基本的因素,而語辭文字則是表面的因素。“詩言志”,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說法,另外,在《莊子》和《周易》中就有“言不盡意”等說法,張揚意藴的作用。而“志”在詩中實際上就是意的因素。所以後世文論有志意一說。同時,《詩經》中表達志意時往往運用比興與誇飾的手法,造成志意的含藴。這就决定了說詩者要善于從精神實質上去領會。而不能膠柱鼓瑟。其次,孟子從主體論的角度提出,既然《詩經》有這樣的表現特徵,因而說詩者就不能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所謂“以意逆志”,就是通過自己的理解,去領會詩經的精神實質。這樣既賦予讀者的解詩權利,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區分了賞詩與識文的不同之處。孔子所說的“詩可以興”,其中“興”也包含著感發志意,以意逆志的意思。說明孔孟深契于說詩之道。而咸丘蒙所以不能正確說詩,在思想方法上來說,除了對于作品的片面理解、望文生義外,還在于對詩學鑒賞的一般規律與特點缺少瞭解。因此,孟子除了幫助學生正確理解原作外,還提出了說詩的一般闡釋道理。事實上,孟子所批評的咸丘蒙這樣的說詩方法,在後世一些大思想家那裏也時有出現。比如王充《論衡》中對于《詩經》的一些詩句的解讀,采用了用自然常識參驗的批評方法,結果自然出現孟子所批評的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理解成是“周無遺民”的意思的情况。如果依此而推,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也可以理解爲燕山雪花真的大如臥席了。
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誇飾》中直接受到孟子學說的影響,提出: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贊,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録,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劉勰提出:“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言外之意,運用誇飾的手法可以更好地表達某種情理,達到一種難以言傳的效果。黄侃把劉勰的這個意思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文有飾詞,可以傳難言之意;文有飾詞,可以省不急之文;文有飾詞,可以摹難傳之狀;文有飾詞,可以得言外之情。”(《文心雕龍札記》)我們從本篇所舉的例子中,可以更好的體會到這一點。“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猫頭鷹的叫聲很難聽,不會因爲它停在學宮的樹上就變得悅耳;“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荼菜的味道苦澀,不會因爲它生長在周朝的原野上就變得甜美。然而,在詩人的感覺中,它們却是非常美好的。雖然拗于常理,但却能够很好地表達作者的褒贊之意。
可見,誇飾雖然在客觀上違反事實,但主觀上却符合情理。所以劉勰說:“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誇飾運用得好,的確可以收到一種出奇制勝的效果,正所謂“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絶,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戚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藴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劉勰最後引用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的話,說明“誇飾在用,文豈循檢”,正是由于孟子的啓示,使得劉勰得够在談文學誇第問題時,能够言之有據,持之有故。明代謝榛《四溟詩話》中提出:“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如果說一味拘泥于文字層面,反而會略其神韵,很難不犯咸丘蒙那樣的錯誤。故到了宋代嚴羽《滄浪詩話》時,就特別强調學詩、賞詩時要依靠“悟”。所謂“悟”就是借用禪宗的妙悟天機的直覺感悟的方式去進行賞評。孟子的“以意逆志”當然不同于“悟”,但它和嚴羽都涉及審美賞析與批評是一項主觀性極强的活動,不能依靠簡單的字面把握。
孟子的“以意逆志”之說,發展到漢代,産生了董仲舒的詩無達詁之說。以意逆志作爲一種文論命題,强調文學藝術鑒賞時的主觀差异性。文學藝術的鑒賞不同于認識活動,在審美鑒賞的過程中,存在著主觀差距,這是不争的事實。同時,對于欣賞者來說,也要善于發揮自己的主觀再造性,入其契機,達到一種再創造的境地。如果没有這種體驗與再創造,就無法體會作者的苦心孤詣。漢末建安二十三年,曹丕爲太子時在《又與吳質書》中就慨嘆:“昔伯牙絶弦于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湣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劉勰《文心雕龍》的《知音》篇專論知音即文學鑒賞之難。他也慨嘆:“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劉勰認爲,産生作者與鑒賞者隔閡的原因是多種因素組成的,其中一個原由即是人們的以意逆志,即以個人主觀心情去解讀作品,産生了不同的理解,客觀上會造成見仁見智。他說:“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醖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异我則沮弃,各執一偶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這種由個人原因而造成的對作品的過度解讀自然是要不得的,會造成對于作品的誤讀,使知音無法尋找。但是劉勰又知道,在鑒賞過程中,完全否弃個人因素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因爲文學作品的鑒賞與解讀與認識活動不同,在于它的主觀差异性與創造性。如果没有以意逆志的實現,則作品的解讀很可能出現膠柱鼓瑟般的情况,就像孟子批評咸丘蒙那樣的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情况。所以劉勰又强調: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衆不知余之异采。”見异唯知音耳。
劉勰認爲:“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這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以意逆志”的意思在內。《章表》中提出:“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劉勰認爲,以意逆志難免會産生見仁見智的差异,爲防止主觀之意的過度蔓延,他提出了樹立一定的客觀標準來與主觀之意相結合,以鑒賞出作品的優劣。爲此,劉勰在《知音》中認爲:“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劉勰强調,知音的前提是除了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外,還要從六個方面去觀察與識別,這樣纔能正確地進行文學鑒賞,成爲作者的知音。
孟子雖然没有像劉勰那樣,作爲專門的文學批評家確立專門的文學批評標準,但他對于“以意逆志”容易産生的歧義也有所知曉。孟子對于《詩經》妄加揣測,大衍發微的做法也是不贊同的。在他看來,不妨通過外表的直觀來由表入裏,領會作者的意圖與詩的意義。爲此他提出“知言養氣說”。
在孟子看來,人的外表與內裏有著一致性,當人內心的道德修養達到一定的地步時,就會在外貌上呈現出相應的神態。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所謂“不言而喻”也就是魏晋人物品評時常說的那種若有似無的風神儀態。而眼睛是最能表現出一個人的內心世界的。所以孟子又說:“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上》)孟子提出一個人的眼睛是最能再現出內心的精神風貌的,當他道德高尚時眸子則正,當胸中有鬼時則眸子斜視。這顯然有些牽强,但是在古代重視直覺的風尚中,這種觀念却也反映出人們內外一致、表裏如一的識人法,並且自然而然地延及文學批評活動中。《世說新語》的人物品藻與文學品評就表現出這一點。
既然人的內在精神通過行爲舉止可以表現出來,那麽也必然會在言語中顯示出來。循此思路,孟子提出由外及裏的文辭識鑒法。孟子在回答學生“何謂知言“時提出: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發于其政,害于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公孫丑上》)
孟子是從政治識別的角度去申說的,但是這段話的方法論意義却是很大的。它告誡人們要善于從外在的言辭表現去識察一個人的心理活動,將言辭方式與心靈活動統一起來。循外入內,沿波討源。《周易·繫辭下》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其中說的也是一個人的性情與心態往往反映在言說形態之上,中國古代人深信人的情性與心理可以通過外在的言說方式來知曉。
《文心雕龍·體性》顯然也受到孟子思想的啓發,劉勰提出:“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强調作家文辭風格與內心精神的一致性,也是建立在這種觀念之上的。由此可知,先秦時代思想家的許多言論,雖不是專就文學問題而發的,但是在當時將文學置于大文化範圍的情况下,他們的思想方法却構成中國古代文論的文化底藴。
四、“知人論世”與文學批評
孟子倡言在讀詩與說詩時,要善于領會其內在精神。孟子對齊宣王宣講仁政時,也是對《詩經》中的作品依據大概的意思來作解說的,說明孟子對《詩經》的運用是比較靈活的。但同時這種理解也不是完全主觀臆斷的,而要通過“知人論世”,總體把握的方式去領會。內心的理解與外在的社會歷史的瞭解應當有機地事合起來。這樣纔不致使說詩成爲臆測。可以說,“知人論世”是對“以意逆志”的進一步補充。孟子提出: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萬章下》)
這段話原意是從士的修養去說的。意爲善士應當與善士交游,即人以群分,但善士不應囿于時間所距,還應與古代的善士相交流,從他們那兒汲取營養。爲此必須誦古人詩,讀古人書;而要懂得古人的詩書,就必然要論其世,知其人。孟子雖然不是從賞析詩的立場去說的,但他認爲要瞭解古人,必須把讀他們的書與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考察,以最後瞭解古代善士。文學是作者思想情感與時代環境相結合下産生的精神作品,因而要瞭解作者的思想性格當然必須讀他們的書,並從時代上去考察其思想與創作。這也即《文心雕龍·時序》所說的“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孟子的這段話啓示人們,從事文學批評必須顧及作者本人與時代背景,片面地從作品本身去分析,就事論事,是無法全面而正確地賞評文學作品的。
在《孟子》一書中,“以意逆志”、“知人論世”、“養氣知言”是在不同的地方講的。但他們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像《論語》、《孟子》這一類語録體,是後人根據孔孟生前的言論加以輯録整理的,不可能像一本體系嚴密,邏輯分明的書,把每個觀點絲絲入扣地演繹下來。但孟子既重“以意逆志”,同時强調“知人論世”,其思路是十分明顯的。孟子所說“以意逆志”的“意”即主觀之意,並不是脫離詩作之外的任意猜測,而是依據作者與環境,以及作品本身的特徵去說的。就這一點而言,它與“知人論世”可以互補。因爲批評者對于作品的主觀賞評與分析,不能游離于作品所賴以産生的客觀的時代背景與作者本人情况,否則就成了痴人說夢。王國維在《玉溪生年譜會箋序》一文中談到:“善哉,孟子之言詩也,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顧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意,不失古人之意乎?此其術,孟子亦言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則古詩雖有不能解者寡矣。”王國維認爲孟子的這兩段話可以互相發明,互相參照。如果没有知人論世的功夫,就很難避免將以意逆志變成主觀臆斷。當然,孟子的時代,詩畢竟還没有完全獲得獨立的形態,是作爲禮樂文化的餘緒而被廣泛運用于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方面的。孔子和孟子說詩,也大多著眼于用詩的角度。是從他們的政治與倫理人意義去加以發揮的。到了魏晋時代,詩賦隨著文學的獨立而重新爲人們從審美形態上去加以分析與解讀。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古代的文理論始終是以哲學和倫理學作爲內在的精神來源的。孟子的文學批評觀對于後世文學理論産生的影響也證明了一點。
在劉勰之文學批評理論中,既非常重視對于作者個體心性與情志的解讀與鑒賞,在《知音》篇中,劉勰主要强調鑒賞者如何披文以入情,吸收了孟子的以意逆志的思想;同時,在文學批評的社會學領域,他更是强調指出,善于從社會與時世的情境中去理解與解讀作品。本來,在《禮記樂記》中,作者就提出:音樂傳達出特定的倫理內容,而人們的倫理觀念與感情又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是故審聲而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而知樂,而治道備矣”。從這段話可以見出,中國傳統的文藝觀十分重視美與藝術之中的社會藴涵,認爲從中可以捕捉社會情緒與信息,以調整自己的統治。這也是《樂記》與先秦兩漢儒家文論思想中極有價值的一個觀點。這些觀點與孟子的知人論世觀點可以互相補充。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既倡導作品來源于作者情志的宣發,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同時,也認爲這種情志並非孤立地産生的,而是在一定社會情境下形成的,有著無法抹去的時代因素在內。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寫有一篇《時序》,指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政阜民暇,熏風詩于元后,爛雲歌于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劉勰此篇通過對于文學史發展的考察,强調歌謠文理,與世推移。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文學活動與文學現象,是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的。
劉勰在此篇中,還通過具體的文學史來說明這一點。在劉勰的心目中,以三曹與建安七子爲代表的建安文學是體現他文學理想的一個時代,他在《文心雕龍》中給予高度評價。在《時序》中,劉勰則重點分析了建安風骨的産生原因:“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歸命于河北,偉長從宦于青土,公幹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劉勰認爲建安文學的慷慨仗氣,是因爲時世的刺激與感染所致。
劉勰在論及二十篇文體批評時,也貫穿了這種知人論世的觀念與方法。比如在《明詩》篇中,劉勰就詩這種文體的産生與變化指出:“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黄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劉勰認爲,從上古之詩到《詩經》與《離騷》之形成,一直到秦始皇的《仙詩》,無不受到時世的影響。劉勰在論及建安文學中的五言詩到正始五言詩的風格特點時,也分析道:“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争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在《明詩》篇的篇末,他贊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論說》篇中指出:“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争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晋書·王衍傳》提出:“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從這段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劉勰對于玄學與文學關係的論述,有著歷史事實的驗證。劉勰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理論,構成了《文心雕龍》的人文性與科學性相結合的批評理論構架。後世人多引用他的這些話語來說明上古文學史至中古文學演變的原委,成爲經典理論。其中的來源,顯然受到孟子“知人論世”說的影響。
《文心雕龍》成爲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的經典,體現出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體系的兼收並蓄,其中儒玄佛互補互融,即使在對儒家思想的吸取過程中,劉勰也是融會貫通。其中易學與荀子思想,構成劉勰“兼三材而兩之”、天人合一的文學觀,孔子的思想學說,主要構成劉勰的文學政教觀念,而孟子的思想學說則融入到劉勰的文學與人格精神境界,以及主觀修養論與鑒賞方法論中,深入到文學理論批評的深層結構與範疇領域,從而共同托舉起《文心雕龍》這部文論巨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