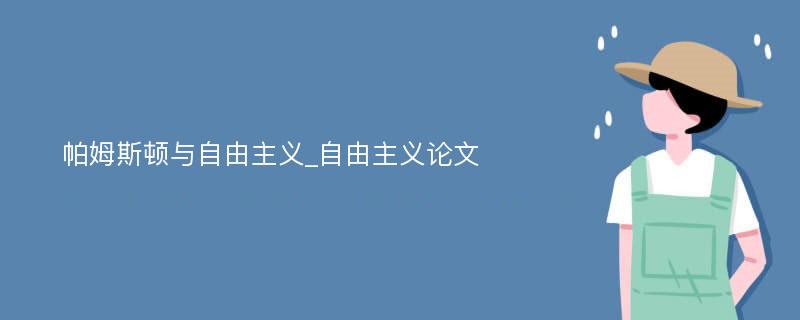
帕麦斯顿与自由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斯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自由主义政治舞台上群星闪耀,J.S.密尔、R.科布登、J.布莱特 以及晚出的W.E.格拉斯顿,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领域中无可争议的象征。相形 之下,帕麦斯顿子爵H.J.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1784—1865),这位现代意义上的英 国 自由党的第一任党魁,不但与自由主义的当然象征无缘,反而以自由主义改革的制动刹而闻 名,其显著的保守特征使得人们似乎难以将他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麦斯顿时代(1855—1 865年)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帕麦斯顿在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实践中的地位 与影响,也由于其政治立场的模糊难辨,而成为不易澄清的话题。多半是基于这一原因,长 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少有问津。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以期有益于 对帕麦斯顿的保守性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而对19世纪中期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实 践作进一步认识。
一
帕麦斯顿的政治生涯漫长且富于戏剧色彩。与格拉斯顿一样,帕麦斯顿在19世纪30年代初 年成为温和的辉格党人之前,也有过二十余年的托利党经历时[1](P124)。19世纪50年代之 前,帕麦斯顿的声名一直是与历届辉格党政府的外交、对外战争和武力威胁相联系的。进入 50年代之后,帕麦斯顿最终证实自己在国内事务方面同样卓有潜力,在阿伯丁联合政府倒台 后,1855年2月4日,女王在尝试各种组阁努力失败后,不情愿地诏见帕麦斯顿。两年后,已 年逾古稀的帕麦斯顿正式就任首相。“这个老骗子终于达到了他长期以来不择手段追求的最 大目标”[1](P126),持激进反战立场的J.布莱特的评语不免有些尖刻,而迪斯雷利也没有 放过显示其文学特长的机会,在他那里,帕麦斯顿被描绘成一位“上了年纪还化装上台表演 的戏剧丑角,既聋又瞎,还带着假牙”[1](P126)。帕麦斯顿的年迈体衰使同时代的政治家 们很容易轻视、低估他的政治潜能。不过,出乎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意料,从1855年至1865年 ,其间除了1858—1859年德比内阁短暂的16个月的间断,帕麦斯顿主宰英国政治生活近十年 ,这一时期在英国政治史上被不无贬抑地称为“帕麦斯顿时代”[2](P88)。
帕麦斯顿政治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其强烈反对改革,尤其是对议会改革的深闭固拒,使他 成为这一时期自由派阵营中最具保守色彩的前台政治家,按后来的保守党首相、第三代索尔 兹伯里侯爵、当时的罗伯特·塞西尔爵士(Lord Robert Cecil)的话说:每一位保守党人都 应当感激帕麦斯顿,“因为他成功地做了每一届议会最难以做到同时也是最有益的事情—— 那就是什么也不做。”[3](P49)而当时任保守党领袖的德比伯爵也认为:“在帕麦斯顿及其 追随者的阵营中,拥有与我们保守党内一样多的坚强的保守派。”[3](P65)德比、迪斯雷利 与其他一些保守党人一度曾希望帕麦斯顿能重返保守党[4](P134)。帕麦斯顿在自由派与保 守党之间不偏不倚的“中庸”政策(Centrism)使得一些学者不难断言,帕麦斯顿是保守党人 的同盟者,“因为他们并不存在分歧的基础”,他“在对内政策方面是保守的”[3](P65)。
不过,如果据此就遽然认定帕麦斯顿是一位彻头彻尾、一以贯之的顽固守旧分子,则对帕 麦斯顿来说,未免失之公允。事实上,帕麦斯顿并非一向反对改革、冥顽不化的守旧派,其 早年的经历可以让人略见一斑。早在20年代,他就是坎宁等“自由派托利党人”的追随者。 1828年,为抗议威宁顿政府拖延解决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帕麦斯顿竟愤然辞去陆军大臣之 职。帕麦斯顿当时说的一段话值得在此加以引用,他说:“在这个开明的时代和文明的国度 ,人们竟然还要争论将四、五百万人化敌为友是否明智以及给爱尔兰以和平是否安全这样的 问 题,简直令人奇怪。”[4](P131)在随后的议会改革问题上,帕麦斯顿同样表示了支持。其 后的20年,帕麦斯顿的主要兴趣在外交方面,其间,帕麦斯顿曾在1844年投票赞成有关工人 工时的“十小时工作法案”[4](P132)。
事情还远不止如此。进入50年代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当他有机会接触内政事务时, 帕麦斯顿立即显示出他本人简直就是改革的化身。在1852—1855年的内政大臣任内,帕麦斯 顿通过1853年的“工厂法”,将女工和童工的工时限制在早六点至晚六点,其间还留出一个 半小时作为用餐时间。1853年他还推出了最早的环保举措“减少烟雾法案”。该法案意在控 制城区的环境污染,减少烟雾排放。同时,帕麦斯顿也表现出对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的关注 ,他支持强制接种疫苗的个人提案,立法禁止在教堂内随意埋葬尸体,扩建伦敦的下水系统 。最后,他还进行了司法方面的改革,将单独监禁从最多18个月减至9个月,通过1853年的 法案取消流放,采用了对表现良好的狱犯实施缓刑的早期形式,1854年的“感化院法”大大 改善了少年犯的处境[4](PP132-133)。对此,帕麦斯顿同时代的人道主义改革家沙夫茨伯里 爵士(Lord Shaftesbury)赞赏备至,他说,帕麦斯顿所完成的工作“超过了他的十位前任者 的总和”,他接着说:“在乐于从事每一项友善、人道和社会公益的工作方面,尤其是对 儿童和工人阶级,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内政大臣堪与帕麦斯顿相提并论。”[4](P132)一些学 者如P.格达拉(P.Guedalla)据此认为,帕麦斯顿是“最具改革意向的内政大臣之一”,另一 位学者朱迪(Judd)也说:“总之,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缺少内政管理经验的老人来说,帕麦斯 顿在其内政大臣任期内所表现出的进步性令人称奇。”[4](P132)
如此看来,在进步与保守之间,帕麦斯顿并非截然排斥进步。至于他1855年之后趋于保守 ,他本身的保守倾向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不用说托利党的影响,单是几十年的辉格党经历 已 使他不可避免地染上该派传统的贵族精英政治的气息,对民主的恐惧即是典型一例。然而, 除此之外,不容忽视的是,帕麦斯顿的保守性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气质,否则就无 法理解一个完全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龙钟老人,能够长时间地支配政治生活而不致被淘汰 。事实上,倘若帕麦斯顿不是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而卒于首相任内,可以想象,他仍将作为 自由党的领袖而稳居政坛之首,这一点,1865年的大选结果足以作为佐证[5](P105)。
维多利亚中期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保守心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50年代初,科布登 就不无伤感地对布莱特说:“我一直在找寻预示着政治未来的迹象和征兆,不过我不能说我 看到了一丝改革之风。”[6](P33)事实是,从40年代末就开始的经济大繁荣,消蚀了人们对 现存体制的不满与怨愤,人们更多地关注眼下的社会与经济实惠;同时,自1846年保守党分 裂 以来,英国政坛上长期存在的政治混乱、政党组织的不健全,也阻碍了议会的改革冲动。而 同一时期对外部事务日益增长的关注也转移、分散了人们对国内事务注意力。对改革的冷漠 ,使得《泰晤士报》对布莱特1858—1859年的新一轮议会改革鼓动作出这样的评论:“布莱 特先生对改革谈得越多,国民的改革愿望却似乎越来越少。”[6](P35)而对整个50年代充满 悲观的科布登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缺乏对军备、殖民地、税收等等方面信息的了解 与认识,有一大堆偏见与无知驱使人们撇开这些话题,只要这些偏见与无知依然存在,你可 能会争取到对议会的改革,但你不会得到一个改革了的政策。”[3](P61)
进入60年代,一向以议会改革倡导者自居的罗素,在1860年提出一项议会改革动议却又不 得不因未有反响而主动撤出后,这样说道:“事情很清楚,唯一可能被通过的改革措施将会 是非常温和的,……但谁希罕这样一种改革呢?”罗素接着说:“整个国家对改革之淡漠已 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似乎更是一种肯定的心理习惯。在过去的一些年 里,有四个改革法案被提交议会,而其中没有一个人们对它表现出哪怕是最小的一点热情。 ”[6](PP36-37)在随后的1862年和1863年,议会内的自由党激进派分别提出过扩大选择权范 围与实行秘密投票的有关改革提案,均未引起反响,于是,甚至连激进派也从此在国内改革 问题上暂时沉寂下来,将目光转向国外。这就难怪帕麦斯顿能够宣称:“我坚信……英国国 民在总体上,包括自由派的绝大部分在内,不想也不期盼我们的选举体制有任何大的变动。 ”[4](P134)看来,帕麦斯顿并未创造一个时代。面对一个激流涌动的改革时代,单独一个 人无法也不可能抗拒整个时代;如果置身于一个保守气息弥漫的时代,即便保守如帕麦斯顿 亦无可指摘,因为他只不过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典型。19世纪英国的政治作家 特洛罗普(A.Trollope)的一番评价或许是较为中肯的,他指出:帕麦斯顿是“一位关注现时 的国务活动家。所有不为时下所需的,所有对时下而言非实用的,他一概拒不考虑。”[2]( P89)
值得一提的是,帕麦斯顿在改革问题上的保守态度也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就在1865年大 选之后不久,帕麦斯顿曾经对人说过:“在改革问题上引起骚动,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关于 这个问题,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甚至在那些除此以外在其他问题上行动一致的人当中也是如 此。”[5](P105)这里,帕麦斯顿流露出对因改革问题而可能导致的自由党内尤其是辉格派 和激进派的严重分歧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一定程度上,以罗伯特·洛为代表的“ 阿德拉姆集团”,在后帕麦斯顿时期对1866年格拉斯顿的议会改革案的坚决抵制,充分证实 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2](P236-237)。
二
关于保守或者一般的守旧思想,休·塞西尔在《保守主义》中明确指出:“天然的守旧思 想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倾向。……对未知事物的怀疑以及宁可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这种心 理,根深蒂固地存在几乎一切人的心中。”[7](P3)对于帕麦斯顿而言,这种保守倾向或许 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而由于他晚年所处的特殊地位,也更为引人注目一些。但无论如何, 就其最终的政治认同与政治归属而言,帕麦斯顿仍然应归入自由主义的行列。不妨说,帕麦 斯顿是自由主义阵营内的保守派,抑或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 实是,当德比和迪斯雷利在1852年热忱欢迎帕麦斯顿重返保守党阵营时,帕麦斯顿的保守倾 向使这种回归看似不成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是帕麦斯顿并未背弃他从30年代就开始追随的辉 格党[3](P40)。就19世纪的情形而言,不论辉格党在格拉斯顿时代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趋于严 重保守,但自30年代大改革以来至格拉斯顿之前的60年代,英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却始终 是与辉格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更进一步地说,辉格传统也是英国自由主义一个不容忽视的 重要组成部分[3](P44)。帕麦斯顿在拒绝重返保守党时这样说道:“为辉格党工作了22年, 如果说正是与他们合作让我赢得了一点政治声誉的话,那么要我投奔到对立的阵营,对我来 说,完全不是一件快意的事。”[4](P134)由此可见,帕麦斯顿在主观上更倾向于代表自由 主义的辉格党,选择辉格党作为自己最终的政治归属,并不意味着帕麦斯顿不再是保守的, 但至少表明,他不愿让自己的保守倾向成为他本人公开的、压倒性的政治标识。
帕麦斯顿作为保守的自由派,不仅在于他在政治上认同于辉格党,更在于他在奠定自由党 这一自由主义政治组织中所起的突出作用。自由主义组织的焕散,到19世纪50年代已是有目 共睹,包括辉格派、皮尔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在内的自由主义进步力量,不仅彼此独立、各 立门户,更有甚者,其内部如辉格派和激进派的对立与相互攻讦并不亚于它们与保守党之间 的冲突[3](P36)。自由主义各派之间的大联合已为所有各派深切感受到,是否能将自由主义 诸派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议会政党,不仅关系到现实的党派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自由主义进步 事业的成败和未来。安格斯·霍金斯(Angus Hawkins)指出:帕麦斯顿的最高成就“是把汇 集在他的内阁中的各种因素调整为一个持久的政治结合体”,“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的自由 党是在帕麦斯顿的领导下开始定型的。”[5](P78)威利斯厅会议和1859年帕麦斯顿内阁的形 成,已普遍被人们视为英国自由党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帕麦斯顿第二届政府时期,自由党首先在议会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非保守党议员(non-Conservative)愈来愈多地使用“自由主义的”(Liberal)一词来描述自 己的政党归属。1859—1865年间,仅有7%的非保守党议员不使用“自由主义的”一词来指称 自己的政治身份,其中有9名议员自称辉格派,另有22名议员称他们是激进改革派[5](P84) 。因此,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与分歧,1859年之后,“自由主义的”这一术语,已成为当时人 们广泛接受的政党名称,在它的名下,以前的非保守党人开始一致行动。
自由党在议会内的形成与发展,也使它得以在60年代超越威斯敏斯特,成为议会外范围广 泛的各种组织与团体寄托政治抱负的中心。“自由党向进步的贵族、雄心勃勃的工业家,寻 求投票权的工匠和劳工积极分子呼吁,它也向高教会派教徒和非国教徒们发出呼吁。”[5]( P85)总之,它已不再局限于议会一隅,开始和地方上的各类人群对话,向议会外的社会大众 发展。自由党赢得了一些全国性组织如非国教徒的“解放协会”和“大英联盟”的大力支持 [5](P85)。与此同时,自由党的出现,使60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廉价报纸,有了明确的追随 对象,而大多数报纸因此能够宣称其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党的。其中包括全国性的 报纸,如《每日纪事报》、《每日新闻》以及伦敦的晚报如《星报》、《太阳报》,还有其 它地方性报纸如《伯明翰每日邮报》、《哈里法克斯信使报》、《里兹信使报》、《曼彻斯 特卫报》等等一大批报纸[5](P85)。在大众社会日益临近的时代,新闻舆论对自由主义理念 的传播与渗透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自由党在议会内外的进展并非完全归功于帕麦斯顿,但是,诚如S.J.李所说:帕麦 斯顿第二届政府时期自由主义各派从政治联合向政党组织的发展,“倘若缺少帕麦斯顿所提 供的稳定的领导权,则是否能取得这种进展就大可置疑了。”[4](P135)这意味着,正是帕 麦斯顿政府的长期存在和帕麦斯顿领导地位的持续稳定,才保证了自由主义各派持续地、日 益紧密地凝成为一个整体。
帕麦斯顿在成为自由党的领袖,尤其是在凝聚、整合自由党内各路精英的过程中,也的确 展示了他在政治策略及其性格上的一些过人之处。最为突出的是他的政府的广泛的包容性, 这同他漫不经心的随和性格和宽容大度是分不开的。1859年的帕麦斯顿政府被当时的人们视 为奇怪的组合,科布登称之为“各种不同见解的联合”[3](P46)。关于这一点,帕麦斯顿后 来解释说:“基于不同的原则,由更大范围的诸政治党派参与以重建政府,这在1859年是必 要之举。”[5](P79)作为自由主义政党统一的象征,帕麦斯顿内阁汇聚了诸派精英,尤其是 ,激进派在科布登拒绝应邀入阁之后,M.吉布森(Milner Gibson)和维利尔斯(C.P.Villiers ) 被先后延揽入阁,此乃帕麦斯顿政府真正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一向与激进改革派恶意相向的 帕麦斯顿显示其保守亦不排斥进步的成功之举。
帕麦斯顿的宽容与温和使得他能明智而适时地作出妥协甚至让步,这一点,在处理与财政 大臣格拉斯顿以及激进派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削减财政开支问题上,帕麦斯顿一度 曾坚决反对,但经过格拉斯顿的努力,“1861—1866年间,尽管发生了通货膨胀,格拉斯顿 仍将公共开支减少了约10%。”而在与财政开支密切相关的军备和对外政策问题上,帕麦斯 顿差不多完全成了科布登的和平与不干涉主义的俘虏。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3年沙 皇出兵镇压波兰起义、1864年俾斯麦对丹麦的战争,在这些事件上帕麦斯顿政府基本上持中 立与不干涉立场,至少名义上是如此。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为帕麦斯顿成功赢得了激进派的 支持。科布登说道:“这是我们外交政策上的一次革命。”[3](P63)布莱特也认为它意味着 “均势政策理论的几近死亡与被埋葬”[3](P63)。当帕麦斯顿不意之间成了激进自由主义政 策的执行者时,激进派也认可了这位偏于保守的党的领袖,正是由于激进派的倾力支持,才 使得帕麦斯顿政府面对1864年7月保守党提出的谴责动议,能够在议会继续保持相对多数, 度过一劫[5](PP100-101)。
三
迪斯雷利曾戏称帕麦斯顿是“领导一个激进内阁的托利派阁首”[4](P134)。他的话本意是 讥讽帕麦斯顿的保守,但细究起来,却发现这句话已超出迪斯雷利的原意,为人们理解帕麦 斯顿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启示。
首先,它提醒人们,自由主义并非信奉相同教义的纯洁教会,而是兼容不同色彩的多样化 的组合,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激进自由主义者是自由主义政治运动 的前锋,那么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则构成了它的殿后部分,二者并非势若水火的对立两极,而 是同一阵营中在一定时期内相互制约又彼此合作的伙伴。其次,保守与激进在自由主义旗帜 下的共存,为彼此的自身完善与相互影响和渗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帕麦斯顿之被激进派外 交思想同化,格拉斯顿之向激进派靠拢,辉格派之走出议会与广大的中等乃至下层社会建立 联系,都是明显的例子。说帕麦斯顿麾下有一个激进派内阁,无疑暗示了激进色彩在自由党 内的日趋浓烈,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守的帕麦斯顿政府恰巧成了助长激进自由主义的温床, 并进而为即将到来的格拉斯顿时代准备了改革资源。最后,帕麦斯顿以保守形象而居阁首之 位,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由主义的激进 改革主张与公众的普遍心理需求尚存在一定距离,甚至在自由主义阵营内亦属超前,激进自 由主义理念的实现,尚需假以时日,而当务之急则是使自由主义力量汇聚为一个整体,自由 主义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积聚力量、蓄势待发的过渡时期。帕麦斯顿的贡献在于,他的政府 的稳定存在和他的领袖地位,为过渡时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证。
诚如休·塞西尔所言:“虽然乍看起来守旧思想似乎是同进步直接对立的,但它却是使进 步变得稳妥而有效的一个必要因素。”[7]如果说帕麦斯顿意味着保守,自由主义象征进步 ,则帕麦斯顿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政治自由主义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使进步变得 稳妥而有效”,而由于帕麦斯顿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则其在19世纪英国 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势必应占有明显的一席之地。
